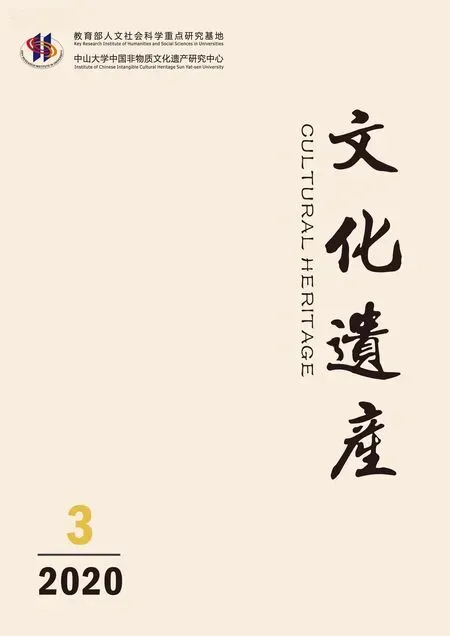粤北两座古戏台及其演出习俗考述
2020-12-01康保成
张 哲 康保成
一、镇溪祠古戏台与晚清乡村戏金制度
镇溪祠古戏台,位于广东省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宋田新屋东侧约300米处的镇溪祠内,2008年列入广东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然由于乡镇改造、地名与地形变迁,我们寻找这一戏台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在一位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才在一家公司的墙后找到了此台。彩图一为镇溪祠院门,门前立有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2006年3月29日立的“古戏台”碑一座,上刻简略介绍文字。
进入镇溪祠,戏台正在门楼之上,这是一座倒坐式山门戏台。正脊案式垅,饰1米长,0.1米高,侧面塑花雕山仙境,葫芦刹,2侧2神兽稳守;距刹0.2米处蹲2只脸朝外,无所作为的神兽甍;牛角勾正吻;垂吻如灰蛇下滑吐长弧舌翘。
戏台面阔三间,表演区一间居中凸出,两旁各有一间耳房,直接与后台和两厢看楼左右相连。登台观察,后台与耳房之间有拱券形门可供出入。两耳房墙壁正中各开有一圆形通风窗口,直径约0.6米。台口坐东朝西,正对祠堂正殿,台下悬空,是通往祠(庙)内的通道。
戏台整体为穿斗式结构。台前左右两檐柱从地面石础穿过台板直通屋檐,并穿起额枋。檐柱内、外侧分别有云形雀替,支撑额枋和斗拱。额枋上的木雕为二龙戏珠形,雕工十分精细。
台上表演区有木隔断区分前后台,木隔断左右两侧为上、下场门。台上左右两金柱支撑房梁,金柱下有方形石柱支撑。除支撑木质金柱外,方形石柱还穿起台板下木梁,抬起台面,显得非常坚固。经现场测量,其数据如下:
表演区面阔5.471米,耳房面阔各3米,前台进深5.719米;后台进深1.805米,下层(台基)高2.249米,台口高3.026米。彩图二是从戏台右侧回廊上层平视拍摄的照片,彩图三为后台:
台面为木板铺设,戏台顶部方形藻井彩绘云龙纹,四周彩绘暗八仙图。彩图四为藻井,彩图五至彩图八为暗八仙中之四幅。
在木隔断上端正面,用墨笔楷书书写“神安人乐”四字,见彩图九。
在额枋上端左右两屋檐下,两斗拱之间的屋顶木板上,用行草墨笔书写古诗各一首,其中右侧为王维《田园乐》诗:“桃红复含宿雨, 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 莺啼山客犹眠。”见彩图十。
戏台正对庙堂正殿,中间有一块空坪,地面铺设鹅卵石。四周有两层回廊相接,整体上呈封闭式四合院形制。院深约15.5米,宽(不含回廊后壁)约10米。回廊上层有栏杆,高约1.3米,演剧时可做看台。一般而言,回廊上层为身份较高的人或女性专用。院子里的两棵小树,当是后人种下。彩图十一是从戏台台口正面拍摄图,彩图十二是回廊底层。
庙堂正殿神龛,安放“林大夫昭德爷爷”执剑戎装雕像。相传林大夫为当地一名被明崇祯皇帝封为大夫的官员。原为白面,有年金銮殿火灾,林救火时烧成红脸。附近村民每年农历9月19日举行庙会,演出戏剧。
值得提出的是,对这一戏台,《中国戏曲志·广东卷》《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均未著录,惟王子初任总主编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广东卷》予以著录,并有戏台正面照片、局部照片9幅,为迄今所见介绍该戏台之最详者。《大系》指出:“该戏台是我县境内目前发现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戏台。其建筑结构具有典型的江浙地区建筑风格,是研究古代北方庙会南移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的重要佐证和实物资料,极具历史、艺术研究价值。”诚哉斯言。惟以“祠内保存有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石香炉一个”为据,将戏台始建年代断为“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1)《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编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广东卷》,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258页。,似显证据不足。
幸戏台背面左右墙壁嵌入清代碑刻6通,其中不乏和戏台有关者,可据以推断戏台始建年代。先看嘉庆十五年所立之《永远常注碑》,见彩图十三。其碑文略云:
从来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我寺扩修富申以来,增置神田钟鼓,招立庙典祀奉,又复营建戏台一座。此诚较诸前美而益彰也。然犹虑乎灯油钱供,仍未足以传其盛耳。于己未上元日,纠集首事十二人,各捐祀银壹员,合本壹拾贰大员……
碑文落款:“飞龙大清嘉庆十五年岁次庚午正月上元日,信士邱濬灵、邱□□、邱焕新、邱世克”。
显然,碑文中所云“复营建戏台一座”,是最近之事,前所未有也。但也非立碑的嘉庆十五年,因为后文说得明白,此次立碑,为的是捐银解决“灯油钱供”。故戏台创建是嘉庆十五年前不久的事。另,祠中又有嘉庆八年所立之“众信捐建寮宇芳名勒碑”一通,上有“濬灵”“焕新”之名,应即十五年碑中之邱濬灵、邱焕新;又有“世科”名,或即十五年碑中之邱世克。后碑落款者四人中,至少三人参与了七年前之捐款,故有“此诚较诸前美而益彰也,然犹虑乎灯油钱供仍未足以传其盛”语。可以推测,嘉庆八年捐建“寮宇”,应当即是十五年碑中所云“钟鼓”“庙典”“戏台”。若这一推测不误,镇溪祠戏台的始建年代应是嘉庆八年即公元1803年,而不是明嘉靖三十四年。从戏剧史的发展看,明代中后期,在粤北乡下有如此完美之戏台恐无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镇溪祠虽名为“祠”,实际上却不是单一的祠堂。从碑文看,当地乡民多称其为“寺”。但“寺”内祭祀的却不是佛道之神,也不是邱氏的先祖,而是当地一名林姓官员。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值得民俗学界关注。不过,镇溪祠的四合院建筑,周围回廊,正殿面对戏台,和江浙一带的祠堂建筑如出一辙。
祠庙内壁还嵌有道光六年《永远戏金常田碑》一通,文献价值极高,碑文略云:
尝谓倾圮者风雨,修理者人力。我等宏创前规,扩充栋宇,不能长保无虞,亦将嘉庆丁卯年题奉戏金银,汇共□□零三元,公议着缵父生放。未经八载,不幸父故。缵承父志,协力生放,逐年当众算明,除公项消用外,尚余银两,置□田种。迄今道光丙戌年,又经众算明,新旧共置田种九桶半,其田租谷□首轮收,有圮即修,无修酌用。或为圣□而齐同恭祝,或为兴至而歌舞梨园。有美毕彰,无瑕百掩。休哉,何风之□欤!谨将田种、土名、田丘、粮租,并题奉人等,一应勒石,永垂不朽……沐恩信生邱鸿缵稽首拜撰
以下依次记录了捐银者姓名及所购买田种数量、土地名,捐戏金者姓名及捐银数额等。落款时间为“大清道光六年九月吉日”。值得注意的是,在捐银者姓名中,仍有邱濬灵和邱焕新,却没了邱世科(克),或世科即鸿缵之父亦未可知。碑文中所说的 “嘉庆丁卯年”即嘉庆十二年(1807)。很显然,在嘉庆八年戏楼建成之后,邱氏一族四年后再次发动捐助戏金,以供演剧之用。这笔钱公推邱鸿缵之父存放,并负责平时开销。缵父故去,鸿缵接办此事,在保管费用,维持日常开销的基础上,还购置了种子、田亩等,用戏田的收入支付演剧和修葺戏台费用。彩图十四即为道光六年所立的《永远戏金常田碑》照片。
1990年11月,在浙江省嵊县四明乡上江村西发现了两块清乾隆年间的戏田碑,曾引起学者关注。(2)吴戈、施玉兴 :《清乾隆年间的戏田碑记》,《中华戏曲》总第十三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所谓“戏田碑”,是指在某些乡下,为春祈秋报和演剧需要,从农户私人耕种的田地中自愿捐出某些田亩,或由农户捐钱购置田地,雇请佃农耕种,其所得收入用于维修戏台或演剧使用,村民为此立碑为据。我们在镇溪祠发现的这通《永远戏金常田碑》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碑文对戏田的规定更详细。例如碑文云:“买得一处,田种二桶半,土名大庙前杨梅江,计田大小四丘;系岩前二坡;水灌荫铁屎墩大路下,计田二丘。”“买得一处,田种五桶,土名门前峒,计田二丘……年租谷乙十四石”云云。这表明,此地乡民为长久解决观剧和维修戏台的需要,由乡民自愿捐钱,购买种子、田亩或土地,以“永远”解决“戏金”来源问题。碑文对捐献者姓名,所捐款项的用途(购置田种、土地等),一一记录在案。既为永久之凭据,具有法律效力,亦为弘扬捐银者不世之功德。
乳源县镇溪祠古戏台及其祠内碑刻,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戏剧史研究价值。“寺”“祠”不分的称谓,庙祠合一的四合院建筑模式,倒坐式的过街戏楼,在广东省众多古建中首屈一指,值得深入研究。而祠内碑刻之多,保存之完善,令人惊叹!而其中嘉庆年间的碑刻记录了戏台的始建年代,道光六年的《永远戏金常田碑》,是迄今国内发现的第二通有关戏田制度的碑刻,均非常珍贵。
二、连州马带村戏台
清远市连州马带村戏台,《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和《韶关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均有著录,二者文字几乎全同。前者出版于1993年,后者为2001年内部印刷,后者应从前者抄来。现迻录《戏曲志》介绍文字如下:
连南马带村戏台,坐落在连县西岸镇马带村,与唐家祠相对,中间面积约二十五平方米。戏台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修,光绪三十四年又重修。青砖木石构筑,台围石砖,中间填土,单檐悬山式,梁架为穿斗式结构。戏台占地三十一点三平方米,台基高一点四米,台口高二点八米,宽五点二米,深五点二米。台平面近方形,台中有四根木柱支撑,中间两根书有楹联:“永乐庆无疆自宥(有)笙歌(箫)雅韵,盛世欣萃荟常闻鼓乐和声(钟鼓锣声)。”左右无遮拦,可作三面观,台中有一挡墙分隔前后台,两旁有门出入,门额书“出将”“入相”字样。后台是供演员化妆及出入的房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修戏台,现保存完好。(3)《中国戏曲志·广东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3年,第424页。
根据我们的现场考察,《戏曲志》对戏台楹联的释文有几处不实,《文史资料》因之。上联中的“宥”实为“有”,“歌”应为“箫”字;下联中的“鼓乐和声”实为“钟鼓锣声”。此外,谓此台“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大概和台内木屏风正中悬挂的“永乐盛世”匾额和楹联中的“永乐”二字有关,此外缺乏其他证据。匾额落款清楚地题写书写者为“唐水秀”,《戏曲志》谓楹联书于戏台木柱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写在隔离前后台的木隔断上,落款时间是“一九九九年,唐水秀”。也就是说,楹联和匾额都是1999年才出现的。匾额下、楹联上下联间的木隔断上有南极仙翁图,并有“马带村委嘱”的落款,估计也是此时的作品。见彩图十五。
这样一来,戏台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说法就很成问题了。从木隔断区分前后台的结构和风格看,此戏台应是清代建筑。所幸戏台下右侧并排立有两块石碑,左碑刻有“连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马代村戏台”,右碑刻文:“马代村戏台简介:始建于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4)重修,是马带村民为看戏剧表演而建。戏台坐东北向西南走向, 2011年7月连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连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保护》”云,下署“连州市人民政府,2017年7月立”。见彩图十六。
看来,此戏台始建于清代是文物部门鉴定的结果,当无疑问,而《戏曲志》著录不确。只不过,碑文云戏台“坐东北向西南走向”,恰与我们的测量相反(见后文)。我们的测量是以台口的朝向为准,很可能石碑的介绍以戏台对面的庙口为准。关于“光绪三十四年重修”,有戏台脊檩上题字为据:“时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仲秋月吉日合乡众信等重建”。但题写时间却是“一九九九年”。见彩图十七。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相信这一题字是有根据的。据马带村党支部书记唐玉良(男,54岁)介绍,此戏台始建年代不详,原不在此处,而是在南边一两百米的地方,光绪三十四年移建于此。移建后保留了原貌。关于移建的原因,据说是由于风水不好,对附近的两个村都有影响,故移建于此(4)唐玉良,男,54岁,中共马带村党支部书记。访谈时间:2019年4月5日下午2时。以下引唐玉良访谈内容,不再注出。。彩图十八为戏台正面照,彩图十九、二十分别是左右两侧照片。
此戏台为单檐歇山顶,坐西南朝东北,三面观。戏台基座用石块砌成,舞台为木板铺就。屋顶上为阴阳板瓦面,以板瓦跌砌正脊,正脊中间饰宝瓶,两端各有脊兽,四角飞檐。前檐下横额呈凹形,随屋檐向两端翘起,似在托起屋檐。整座建筑为穿斗式与抬梁式相结合的梁架结构。两檐柱分别座落在石台基两侧的石础之上,在离飞檐约50公分处依次穿起斜梁、横梁和斜枋,与里面的金柱呈外八字形。横梁距柱一米处架其两根短梁,与台内两金柱相穿联。两檐柱与两金柱之间各有斜梁相连,斜梁穿出檐柱之外约50公分,再穿起瓜柱,顶起檩条,支撑椽子和屋檐。
屋顶两侧山花处均设大梁及其上的五架短梁,从下向上、从低向高均衡排开,越高越短,两架梁之间均用短柱穿起,形成三角形梁架结构。上、下场门向外伸出约15°,亦呈外八字形,门上分别书写“出将”“入相”,并有绿叶红花陪衬。见彩图二十一。
经现场测量,戏台面阔7.158米,前台进深6.985米,后台进深3.985米,台基高1.303米,台口高2.675米。这些数据,与《戏曲志》的记载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后台左侧山墙开有正方形窗户,右侧山墙则无窗。
戏台面向唐氏宗祠。我们考察的当天是清明节,前来祭祖的唐氏后人络绎不绝,戏台与祠堂之间停满了汽车。见彩图二十二。
这里的唐氏家族,号称“金马唐氏”,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据“百度百科”的“唐氏公孙三进士”条介绍,唐氏先祖,宋代曾连续三世中进士。唐元是宋雍熙年间(984—987年)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唐静是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唐炎是景祜元年(1034年)进士,官至太子赞善。该条目还说,唐氏家族是从湖南蓝山县迁徙过来。这一说法得到宗祠墙内嵌入的乾隆丙申年(1776)所立的《金马唐氏宗祠碑》的证实。由于年代久远,碑上的刻字多已模糊不清,但唐氏从湖南蓝山县迁来韶关北之白鹤山,到乾隆间立碑时已有“二十余代”,这些字迹还依稀可辨。
据唐玉良介绍,这里流行的大戏是祁剧,小戏是采茶戏。每年秋收过后,会请祁剧大班演戏,一般连演五天,演出前贴出海报。以前曾演出过《薛仁贵征东》《珍珠塔》和杨家将等剧目。当我们问:“为什么不演粤剧”时,唐书记和村民异口同声地回答:“听祁剧习惯了。村里的老人很懂戏,哪句唱错了都晓得。” 至于小戏,本村就有业余采茶团,随时可以演出。唐书记说:“今晚可能就有演出”。可惜我们还有考察任务,不能在此观看演出。
唐书记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一个元宵节,位居太子太傅的唐炎,就是皇帝的老师,要到这里看戏。但人山人海,难以入内。太子命令在灯笼外面写上‘金马世第’,人们看到这个灯笼,就自动给他让开道路。后来,为不至于扰民,这灯笼唐炎轻易不用,就把它挂在自家大院门口。唐炎退隐后,在祖居地建造了一座三进院落的祠堂,祠堂对面建造了一座戏台。并组建了家族戏班,让子孙于扮演帝皇将相中体会成王败寇的残酷,演绎悲欢离合中品味淡然处世的福祉。”传说不能当真。太子赞善并不是皇帝的老师,皇帝或太子也不可能下这样的命令。宋代戏曲尚未成熟,也不可能传到粤北乡村。更需指出的是,戏台是别处迁建此处的,并非唐炎始建。只不过,这里的人爱看戏,却是千真万确。
在马带村,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戏曲还非常兴盛。“文革”期间戏班停止活动,“改开”以来再度兴起。过春社,是村里戏班最为活跃的时节。他们会演以祈福为主题的戏剧,为村民祈祷丰年。冬季,则会请湖南道州、蓝山县等地的祁剧团,连演七天七夜。不过如今境况已大不如前,戏曲演出虽然还有,可因为业余演员越来越少,本地戏班的活动已经很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