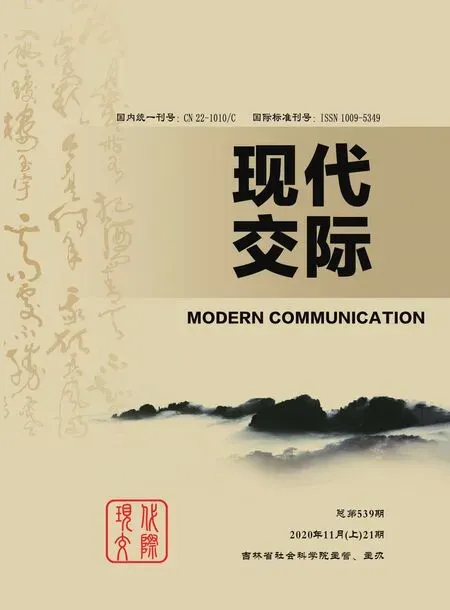浅谈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的特点
2020-11-30傅志海
于 芮 傅志海 李 艳
(德州学院 山东 德州 253023)
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 阿列克谢耶维奇(С.А.Алексиевич)于2015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其颁发的颁奖词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1]她的复调书写即她以当事人口述实录的写作方式,再现20世纪俄罗斯发生的历史性灾难——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二战”、苏阿战争、苏联解体等。众多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口述自己的回忆,记录自己的苦难,形成多种声音即复调。她的这种基于历史真实、历史文献、亲历者回忆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她自己称之为文献文学或纪实文学(документализм),她的“乌托邦之声”(“Голоса Утопии”)系列纪实文学作品已经译为多国语言,闻名于世。该系列包括五部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1985,2015年新版译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最后的见证者——100个非儿童故事》(《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и -сто недетских рассказов》,1985,2013年新版译为《我还是想你,妈妈》)、《锌皮娃娃》(《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1989)、《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1997,2015年新版译为《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二手事件》(《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2013)。相比于俄罗斯作家布宁、索尔仁尼琴荣获诺奖后在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喧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在俄罗斯和中国引起的反响并不大,这也许是和其白俄罗斯身份相关。就现有研究来看,研究者们主要着眼于其非虚构纪实体裁的真实,叙事策略如复调叙事、创伤叙事、废墟叙事、生命叙事,知识分子话语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但对其纪实小说的整体特点研究还鲜有涉及。
纪实文学体裁从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始在当代俄罗斯文学创作中成为最强有力的艺术发展趋势,甚至可以看作时代的代表体裁。纪实文学又被称为文献文学、事实文学、人性文学、非虚构文学等。在《文学定义辞典》中Николаева将纪实文学定义为文献和文献文学类型的总和(文章、随笔、信件、访谈、回忆录等)[2]。在《文学定义百科全书》中Муравьев将之定义为从研究文献材料的方式研究历史事件或社会现象的文学散文[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纪实文学都是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对象,以事实或文献材料为参考(这些文献包括多种渠道,如官方文献、见证者、作者回忆、口述者笔记等)而创作的以文学美学意义为目标的作品。历史人物、真实命运、依靠文献创造的情节被认为是纪实文学的表现形式。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乌托邦之声”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纪实文学具有新闻性、历史性和文学性等特点。
一、新闻性与政论性
纪实文学本身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上,有推动和反映现实的功能,现实事件和真实人物能让读者产生亲密情感并了解那段历史,这是其他文学作品不可比拟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除了作家身份外还有记者的身份,她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的纪实小说里有记者和新闻的影子。她选取的都是具有爆炸性的、敏感性的、曾经轰动一时的真实的历史大事件,如“二战”、苏阿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联解体等。战争、核事故、苏联解体这些决定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与20世纪苏联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的发展密不可分。阿列克谢耶维奇选取的这些题材和角度相对来说都缺乏时效性,但却是未被深入挖掘过的旧新闻,或者说是被官方数据官方文献所遮盖了真相的旧新闻。她以搜集文献、采访当事人等方式选取与以往不同的视角再深挖这些事件、回顾这些历史,寻求他们历史的真相和在当前时代的新解读。
纪实文学是一种借助文学艺术,更真实地反映社会事件、人物的体裁。而涉及社会事件、社会人物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这个主体及其颁布的政策等。阿列克谢耶维奇所描写的历史大事件,政府在事件发生时的姿态与态度,所扮演的角色,所下发的命令,都决定了事件的发展方向,因此由其写作体裁和题材所决定,其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性是不可避免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中的政治倾向能够从各类情节、场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还可以借助人物自身的叙述表达出来,尤其是其小说中有作者直接对各类人物或事件的评论或其写作的心路历程,都能体现其爱恨态度。而把对事件、场景、人物的描述,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与评价,会使小说更生动更富有情感与态度,使之与读者产生更大的共鸣。例如,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随处可见的是对政府行为不当的控诉,众多人物和作者都在责问政府不顾人民安危、隐瞒真相的做法,这极大体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本人在核泄漏事件中的态度。
二、历史性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4]阿列克谢耶维奇极大地实现了诗与历史的和谐。她描写历史上真实事件的同时,思考具有普遍性的、全人类共性的人性问题。极大地实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以“诗”的形式对历史上“个别的事”做出了回顾与反思,使之具备普遍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以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和现实的人文关怀来关注历史、记录真实,回顾历史、反思历史。她带有一种悲悯情怀关注个体命运在历史中的沉浮,她带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来记录被历史裹挟的小人物的疼痛、困惑、情感,并对此提出质疑和反思和抗辩。比如,在小说《我是女兵,也是女人》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关注了“二战”中的参战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关注她们在战争这一环境下的生存状态,在战争中的身体上、心灵上的不适及创伤,关心她们战后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她重视大历史中的平庸个体的价值,为小人物作传。也对柔弱的、衍生生命的女性群体不得不男性化参与战争而产生的系列问题做出反思。在小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视角放在“切尔诺贝利人”这一核事故受害者群体,通过表现他们在事故发生后的遭遇:普通人被迫放弃土地、放弃这一生经营好的一切,离开家乡;受到核辐射、身体严重受损,受人歧视、心理压抑;被苏联政府的谎言欺骗,被英雄主义的托词蛊惑,清理者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为核事故善后。报纸上冷冰冰数据的背后,是真实存在的为这一事故埋单的个体的遭遇,阿列克谢耶维奇让这些被裹挟进历史旋涡的受难者自己开口,讲述这段历史。这比战争还可怕的核辐射,该如何去战胜?而这场灾难,究竟是该记得还是忘却,阿列克谢耶维奇对此提出疑问和反思。
三、文学性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纪实文学是非虚构的、现实的、批判的、反思的,同时也是文学的、审美的、创新的。如果说新闻性和纪实性是其文体的基本特征,文学性与审美性则是纪实文学所要追求达到的目标。如果说虚构能力是作家创作水平的体现,那非虚构性纪实文学更加考验作家的创作水平。纪实文学受到事件真实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生活严格的逻辑限定,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凝练、人物情节的安排、语言的调度方面所受的限制更大,因为这种体裁作品不能指鹿为马,也不能添油加醋,而是要以反映真实反映历史为最终目的。纪实文学通过不虚构、不夸张的叙述,对多种材料进行总结概括,用曲折的情节、生动的语言、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其他表现手法等反映社会现实中的人和事,来达到文学性和审美性。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文学性首先体现在典型人物和典型情节的选择和安排上。她选取了最能反映历史真实的人和事来叙述,比如在小说《我是女人,也是女兵》中,选取了“二战”中参战女兵上前线,第一次杀人,如何在前线生存,战争中对敌人的同情与怜悯等典型情节。人物形象的丰满程度是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的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独具匠心,采用了细节、对比、反差、心理描写等表现手法,使人物形象饱满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书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真实的,他们从自己侧重的方面讲述自己经历的历史,通过他们的叙述,营造出此情此景。他们的叙述一般都是生活中琐碎平常的小事,叙事十分细节化。对比和反差的使用也非常多,比如《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中,许多人的讲述都包含了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前和发生后的对比。叙述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去时经常讲述自己的内心感受,阿列克谢耶维奇非常重视对人的内心的描摹,心理描写也是非常常见的表现手法,心理描写主要体现在主人公的独白和对话中。
其次,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文学性体现在语言的朴素平实和口语化,使得行文流畅,平易近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几部纪实小说都采用了当事人口述回忆的叙事方式,由于叙事人身份多种多样,既有受教育水平高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从事普通工作的小市民,语言表达符合个人身份,因此也造就了其小说平易近人的口语化特征。小说多个叙述人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使得情感的表达自然直接,语言的口语化表述平易近人,仿佛读者正在与书中的人物面对面谈心,更能摄人心魄,抓住读者的心。这种叙述人口语化的表述在几部纪实小说中都随处可见,例如在小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一位老奶奶和医生的对话:“我去看医生。我说:‘医生啊,我的腿不能动,关节好痛。’‘婆婆,你不能再养牛了,牛奶有毒。’我说:‘不可能啊,我的腿好痛,膝盖好痛,但我不会抛弃我的牛,它供给我食物。’”[5]
再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叙事艺术的高超上。“乌托邦之声”中的五部小说均采用当事人口述实录的访谈体裁,小说以一个又一个叙事人讲述自己的回忆与故事的方式展开。在这五部纪实小说中,阿列克谢耶维奇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作者将每个叙事人的所见所感重叠起来,以蒙太奇的手法呈现在同一时空体内的所有人物的整体图景。但每部小说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如都是描写“二战”,在《妈妈,我还是想你》中,是以孩子的视角看待这场战争,而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则是以参战女性的视角看待战争和这段历史。视角不同,呈现的内容也不同,也是这两部小说与其他战争小说的不同之处。再者,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全由叙事人的讲述来呈现,且叙事人就是人物形象本身。我们从叙事人的话语中来了解他们的人生,了解过去这段历史,使得读者有极大的在场感,仿佛参与这段历史本身。例如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中,通过女兵生动地描述战壕生活,读者仿佛置身于1941—1945年的卫国战争战场,壕沟的两侧,安扎了德军和俄军,甚至都能听到对方开火做饭的声音。女兵们,穿着大好几码的军装,衣服上布满血迹,就地躺在冰冷的冻土上。其叙事技艺的独特之处还体现在她重视小人物的存在和生命体验,一反描述重大历史事件的宏大叙事手法,不是为英雄发声,而是为小人物做传,让在大历史中没有一席之地的普通人说话,这既显示了其叙事的独特,也显示了其作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
四、结语
阿列克谢耶维奇选取20世纪具有标志性的大事件进行写作,从另一个角度挖掘官方数据背后的小人物、普通人的故事。正如她本人所说:“历史,就是通过哪些没有任何人记住的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讲述而保存下来的。我对此兴趣浓厚,我想把它变成文学。”[6]从她的代表作“乌托邦之声”纪实系列小说中,我们看到其纪实小说具有新闻性、历史性、政治性,更具有文学性的特征。其新闻性体现在叙事题材选取的是20世纪爆炸性的、敏感性的历史性大事件并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且纪实文学的体裁本身具有新闻性特点。而历史性则体现在她以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对这些题材的选择以及纪实文学的体裁本身必然与政治性分不开,从她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政府和政策的鲜明态度。而她小说的文学性则体现在情节安排、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运用、叙事风格等方面,具备审美特征。侯海荣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的评论非常中肯:“阿氏口述小说极度贴近地气,个体苦难的真实与历史苦难的真实就在历史和个体的张力中产生,尽管‘真实’包含回忆之真、叙述之真与艺术之真等多个维度,但作品内蕴的历史之真仍旧无法撼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