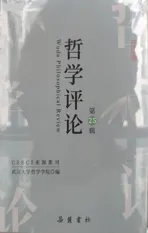纳斯鲍姆对自然主义女性角色论的批评
2020-11-29左稀
左 稀
在《女性与人类发展》一书中,纳斯鲍姆对有关女性角色(女性是爱与关怀的给予者)的自然主义观点展开了批评,并尝试论证所谓女性专属情感和行为模式的社会建构性。她指出,无论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都存在将女性角色看作自然的存在,否认习俗、法律和制度在塑造这些情感及相关行为方面的作用。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1871年,布雷德利法官在支持伊利诺伊州一项禁止女性从事法务工作的法律时陈述了下述理由:“女人特有的那种自然的、适当的胆怯和娇柔显然使她们不适于从事许多与公民事务相关的职业。家庭组织结构建立在神圣法令和事物本性之上,它表明家庭是恰当归属于女人的领域和职能范围……女人最重要的命运和使命就是履行贤妻良母这个高贵而良善的职责。这是造物主颁布的律法。公民社会的规则必须适应事物的一般结构。”[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53.纳斯鲍姆认为,自然主义者若要避免在“关系R 自然存在”的几种不同含义间来回推导,只能承诺某种目的论的理论框架。布雷德利法官关于女性家庭角色的这段论述之所以是融贯的,恰恰因其承诺了一种有关自然秩序的宗教目的论解释。为了澄清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入手。
一、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
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自然”是自然物因其本性而非偶性运动和静止的根源。自然物包括动物及其各个部分、植物以及一些简单的物体(土、火、水、气),人造物不是自然物,因为它产生的根源不在自身之内。自然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质料的自然,即每一个拥有自身运动变化根源的事物所具有的直接基础质料。例如,如果种下一张床,腐烂的木头若能长出幼芽,它一定会长成一棵树而不是一张床,决定这种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床的质料——木头。另一种是形式的自然,即事物的定义所规定的它的形式,形式是一个事物成熟的自然形态,对于事物本身而言,达到它的成熟形态被视作善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事物的自然形式也就是它整个生成过程的目的。两相比较,把形式作为“自然”更为确当,形式自然才是自然的本真含义。(《物理学》192b8-193b10)[2]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 页。自然哲学家主要研究第一个意义上的自然,他们常常通过质料或质料之间的关系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诉诸质料的自然原则不足以解释所有的运动变化。比如,当温暖湿润的东西(产生动物胎儿的东西)受到雄性精液中水状的、可活动的东西的影响时,按照自然哲学家的自然原则,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种东西会产生一定的凝固效果,却没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凝固必定会形成一个动物胎儿。要解释这个转化过程,必须诉诸自然生物通过繁殖保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倾向,这种倾向无法被还原为质料的力量或特性,它只能是目的论的。
约翰·库珀认为,“亚里士多德正是基于物种永存的原则,才最终确立起对自然目的的一般信念”[1]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 in Language and Logo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presented to G.E.L.Owen, ed. Malcolm Schofield and Martha Craven Nussbau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16.。物种永存的假设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它容纳了对生物的全面功能主义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目的论论证,并允许关于物理环境、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各种目的论解释,甚至容许这种主张:有益于某一物种存续的物种是为了这个物种而存在的。尽管亚里士多德对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单向分析在库珀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但倘若物种永存的一般原则为真,那么植物和动物为了彼此而生存的基本观念就是合理的”。[2]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pp. 219.然而,在《论动物部分》和《论动物构造》中,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器官或其他部分所处位置给出一种颇为不同的目的论解释,此种解释并不诉诸物种永存原则,而是诉诸某种一般性的“高贵”原则,其所传达的大致意思是,前面比后面好,上边比下边好,右侧比左侧好。(《论动物部分》658a15-658b15)[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 页。亚里士多德把这种一般性的“高贵”原则视为另一个基本的自然原则,即自然界会服从优先满足物种永存的原则,以便使自身趋向任何事物的前部、顶部和右侧。库珀以为,与诉诸物种永存原则的低层次自然目的论相比,诉诸高贵原则的自然目的论似乎是更高层次的。更重要的是,低层次自然目的论所蕴含的目的构成个体生命物自身的目的,因为任何一种生命物都有维持生存或实现良好功能发挥的目的,高层次自然目的论所蕴含的目的却并不构成个体生命物自身的目的。[4]John M. Cooper, “Aristotle on natural teleology”, pp. 220.对于这两个不同层级的自然目的论,我们无法提供统一的解释。但是,两种自然目的论是彼此分离的,对高层次自然目的论的质疑并不影响我们承认低层次自然目的论的合理性。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思想贯穿于他对女性角色的论证中。首先,在低层次自然目的论体系中,由于人类这个物种同样具有通过繁殖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倾向,生育便构成男女两性的一个重要功能,拥有这种功能并实现它对两性来说都是一种善。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家庭是自然的,它意味着家庭的产生源于人类渴望维持自身物种永存的自然倾向。不过我们很快发现,在涉及女性问题时,亚里士多德除了采用这种低层次自然目的论解释家庭的产生之外,几乎不再运用过它,取而代之的是诉诸一般性“高贵”原则的高层次自然目的论。例如,在《政治学》第一卷他便指出,自然的特性表现为,一切联合的事物和由不同部分构成的事物都存在统治元素和被统治元素的区分。很明显,他有意重申其自然哲学中的基本观点: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不仅受到物种永存原则的驱使,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受到偏好更高贵元素的自然倾向的驱使。正如生长在动物身体顶部的器官优越于生长在其底部的器官一样,人类作为由不同部分构成的生物,其各部分之间必然也存在高贵与低贱的区分。譬如,人有肉体和灵魂,灵魂因为拥有形式而高于肉体,并以专制的方式统治肉体;鉴于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而情欲往往与肉体相连,所以灵魂对肉体的统治便是理性对情欲的统治。
紧接着,亚里士多德说雄性更高贵,雌性较低贱,而相关论证却呈现在《论动物生成》中:在物种繁殖的活动中,雄性贡献的是拥有潜能的形式和运动的本原(精液),雌性贡献的仅仅是被动接受形式的某种质料(构成月经的东西)。(《论动物生成》737a15-35)[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第265 页。就任何一种生命体而言,赋予肉体以形式的灵魂都是生命的本原,因此灵魂对肉体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就人类而言,这表明两点:第一,男性天然地趋近心灵和理性,女性则出于本性地亲近肉体和情欲;第二,男性更高贵并占据统治地位,女性更低贱,受男性统治。把这种生物学结论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心理学结论延伸至人类政治生活领域,亚里士多德很快证明了男性对女性统治的天然合理性。他说:“男人在本性上比女人更适合于发号施令,除非是偏离自然的偶发情况,这就像年长者和成年人要比年轻者和未成年人更优秀一样……然而,一旦有人统治而另外的人被统治,人们便会竭力在形象、言语和名位上造出差别来,正如阿马西斯就他的脚盆所说过的话,男女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这种关系。”(《政治学》1259b1-10)[1]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6 页。例如,娴静是女人的本分,不是男人的本分。发号施令是男人的勇敢,不是女人的勇敢,女人的勇敢表现为服从。像妇人那般勇敢的男人是懦夫,像男子那般自我约束的女人是多嘴多舌、不思节制之人。女人是操持家务的人,男人是享用家务劳动成果的人。公共事务是男人的职能领域,女人不宜涉足,否则就会像斯巴达那样招致政权衰落。之所以呈现这些差异,主要还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天生分有不同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的养成除了习惯化也要遵循自然的逻辑,正如灵魂理性部分的德性和非理性部分的德性是不一样的,男人和女人的德性也是不一样的。男人的灵魂服从理性的指引,他需要也能拥有统治者所应有的完美的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女人的灵魂尽管有理性部分,但由于受肉体情欲束缚,终究缺乏权威,她不需要也不能拥有统治者所应有的完美德性,只要拥有适合她们自己的德性即可。
亚里士多德不仅仅认为政治生活中的这种安排是自然的,而且也认为它是有益的。类似自然哲学中两种不同层级的自然目的论,政治学中也涉及两种不同层级的目的论。在较低层次,政治共同体满足人类想要生活得好的自然本能和冲动;[2]详见刘玮:《亚里士多德论人自然的政治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5 期。在较高层次,政治共同体自然地趋向更高尚的理性。[3]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3a21-1333b2:“较为低劣的事物总是以较为优越的事物为目的,这种情况无论是在技术造成的事物还是在自然造成的事物中都极为明显;而优越在于具备理性。根据习惯的划分理性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实践的理性,一是思辨的理性。如此一来,灵魂的部分显然也必须作进一步的划分。行为也就有了类同于此的区分,那些有能力实施灵魂的全部三部分或其中两部分的相应操行的人必定更加愿意选取本性上更为优越的行为……一个政治家在拟定法律时应当注意到以上所有事项,并且要考虑到灵魂的部分以及相应这些部分的操行,尤其是那些更为优越的作为最终目的的事物。”〔译文参考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不仅如此,这两个层级的目的论同样存在一种不对称性。想要生活得好明显构成每个政治共同体成员自身的目的,但趋向更高尚的理性却很难被理解成每个共同体成员自身的目的。更要紧的是,就女性(和奴隶)而言,为何安于现状、俯首听命才构成趋向更高尚理性的正确方式呢?
为回应这种质疑,亚里士多德很可能回到他的生物学立场:女性天生无能、低贱,她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况且,维持现状对她们来说是有益的。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关于友爱的论述中,丈夫和妻子的友爱关系便被视为施惠者与受惠者之间的友爱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施惠者更爱受惠者的原因在于,他把受惠者看成自身活动的产品,产品往往体现实现活动过程中制作者的存在自身,所以施惠者会如同热爱自身存在那样去热爱受惠者。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曾经在《家政论》中说道,“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并勤勉地服侍丈夫的原因是,‘他确实以极大的代价买下了她,在他的生活和孩子的生育上建立了伙伴关系;没有什么比这更伟大或更神圣的了’”。[1]Susan Moller Okin, Wome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Debra Satz,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88.一言以蔽之,男性赐予的恩惠是如此这般伟大和神圣,以至于妻子希望自己的爱获得同等回报看起来都很可笑,因为两种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如此,通过对斯巴达政体的经验研究,亚里士多德一早得出结论,放纵女性会导致政治灾难,有害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幸福,因此确保她们接受男性的统治不仅对她们而且对全体共同体成员都是有益的。基于上述理由,亚里士多德证明了对于女性来说,扮演自身角色、顺从男性统治、发挥专属功能、实现适合于自身的德性不仅是自然的、必然的、永久的,而且是应当的。
二、纳斯鲍姆:女性角色并非“自然的”
在反对自然主义女性角色论时,纳斯鲍姆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有关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义解释——女性天生就是爱与关怀的给予者。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定位确实建立在心理层面的两性差异之上。对男人是理性的动物、女人是情感的动物的普遍认知,使得女性常常被认为只适于从事与情感关系密切的学问和行业。对母爱这种情感的关注致使人们认为,她们在家中给予爱与关怀是顺应本性、理所应当的。除此以外,承认此种情感心理的两性差异,也意味着支持相应的行为模式和品德规范。譬如,由于女人是情感的动物、天生富有母爱,因此她应当是温顺的、娴静的、慈爱的、大度的,她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抚养孩子、照料家庭方面,并且不求回报地关怀和支持她的丈夫。就这些方面来看,选择从对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义解释入手显然是选择从问题根基处入手。
纳斯鲍姆首先指出,在女性问题上,诉诸“自然”是一个极端狡猾的策略,因为“自然”一词的含义非常模糊。当人们说某种行事方式R“自然地”存在时,可能涉及以下几种含义[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54.:
生物学的:R 建立在一种先天的禀赋或倾向之上。
传统的:R 是我们知晓的唯一方式;事情总是这个样子。
必然的:R 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事情不可能是其他样子。
规范的:R 是正确且恰当的,事情应当是这个样子。
对密尔《自然》一文以及《妇女的屈从地位》的考察,使我们获知在政治论证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不加论证地从其中一种含义滑向另一种含义。譬如,因为R 是一种先天禀赋,所以情况必然是这个样子,也应当是这个样子;因为在某个社会中,R 历来如此,所以R 具有某种生物学基础,或者R 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又或者是正确且恰当的方式。纳斯鲍姆赞同密尔的意见,认为这类推论没有一个是合理的。首先,某件事是传统的,并不意味着它建立在某种先天禀赋之上,某事具有一种先天的基础也并不总是意味着它会成为一种惯例。婴儿出生时总会携带许多自然倾向,但其中一部分会在其成长过程中改变或消失。其次,认为某事源于先天禀赋或者某种传统,也不意味着它必然如此且不可更改。譬如,没有人认为一个先天近视的孩子应该满足现状,我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为他/她提供良好的视力(接受手术、佩戴眼镜等等)。最后,从前述三种含义中的任何一种含义出发,都无法合理地推导出规范性含义。对于一些有缺陷的或不好的先天倾向,我们会试图加以纠正。对于无法促进福祉或实现正义的传统,我们可能采取同样的态度。对于必然性,我们并不总是通过使它成为一种规范来视之为善,人类肉体的脆弱性和有朽性是必然的,但这种必然性本身并不是一种善。反过来,说某事是正确且恰当的,也不能说明它是先天的、传统的或必然的。[1]Martha C. Nussbaum, Sex and Soci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55.由此可见,从女性具有爱与关怀的自然倾向直接推导出女性必然且应当扮演爱与关怀的给予者角色,是何其任意、武断甚至居心叵测的一个推论。
滥用自然主义论证常常是根基不稳的,那么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呢?纳斯鲍姆明确表示过,只有“在一种宗教性或其他规范性意义上理解生物学倾向,把它看作事情应有的样子,我们才能从第一点稳步推进到第四点。但那种对自然的理解在主要宗教中极富争议,必定不能充当政治的重叠共识的基础”。[2]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54.在低层次自然目的论中,由于亚里士多德关注的是形式的自然(形式因与目的因合一),因而在自然哲学领域,他得以从“物种永存的自然倾向”中推出“维持物种永恒存在是正确而恰当的”,在伦理政治领域,他得以从“人类追寻美好生活的自然倾向”中推出“追寻美好生活是正确而恰当的”。然而,高层次自然目的论中的情形不太一样。由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原则的假设内在隐含某种等级制划分,因此,这个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它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不可能在低层次自然目的论的意义上被看作是每个成员自身的善。纳斯鲍姆自然不会赞同高层次自然目的论及其蕴含的等级制度。对于低层次自然目的论,考虑到她所支持的罗尔斯式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以及一些宗教徒(他们构成达成政治重叠共识的多方主体)对此种自然观念的拒斥,她不得不弃之不用。纳斯鲍姆对自然主义目的论的全面拒斥,致使其能力进路的政治理论带有浓厚的直觉主义色彩,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学说是“瘦身”之后的格劳秀斯自然法理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尊严的功能主义解释以及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念的结合体。
总而言之,以某种关系或某种行事方式的“自然性”为出发点展开伦理和政治论证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这种论证极可能具有武断性,无法应对各种反例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这种论证是精致的(如亚里士多德低层次自然目的论),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它也无法满足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然而,关于女性情感角色的自然主义解释不单单呈现出论证薄弱或缺乏辩护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这种所谓自然的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完全是人为创造的东西。纳斯鲍姆当然不否认女性在抚养孩子和照料家庭方面的情感和行为倾向可能有其生物学基础,但有关人类这个物种的研究终究太少,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很难获得十分可信的答案。即便两性之间存在生物学差异,也只是倾向上的差异,这并未给我们提供充分理由去推广或压制它。关于女性情感角色的社会建构性,纳斯鲍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证。
第一,诉诸情感概念。认为情感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肉体性的”观点常常与非认知性的情感观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情感包含有关情感对象的评价性信念,这类信念构成情感的意向性成分。情感涉及那些被我们珍视的、不完全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的人或物,它是对此类需求和依赖的承认。对情感概念的澄清使我们发现,情感之所以与女性而非男性关联起来,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她们相信,对他人产生强烈依附感是正确的,她们自身的善应当呈现为某种极具关系性的善;另一方面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自主和社会控制方面存在非常大的能力差异,女性对自身环境缺乏控制的强烈无力感往往造就了她们丰富的情绪感受。[1]Martha C. Nussbaum, “Emotions and Women’s Capabilities”, in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 ed. Martha C. Nussbaum and Jonathan Glov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90.
爱与关怀的情感都包含大量信念。譬如,关于哪些人或事物具有重要性和价值的信念,关于什么是正确的和恰当的信念,以及其他一些关联信念。其中许多信念都具有规范性,它们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即便这些信念可能建立在某种先天禀赋上,后天训练也激活了此种禀赋,给社会解释和文化多样性创造了很大的运作空间。关于母爱,纳斯鲍姆则认为,人的部分情感形成于婴幼儿阶段,此阶段涉及大量复杂的社会互动和情感体验,但由于这些互动和体验出现的时间过早,且常常达到意识分析难以企及的心理层次,因此这个阶段形成的情感模式构成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对于这些情感,我们虽无法简单通过指向在儿童可识别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行为模式来进行解释,却也绝不意味着它们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母爱正是以这种方式代代相传的。在育儿过程中,父母与女婴的互动会重现母性人格,使女婴认为成熟意味着某种亲密的养育关系;相反,父母与男婴的互动倾向于使男婴认为,成熟和独立是通过否定需求和依赖来实现的。[1]Martha C. Nussbaum, “Emotions and Women’s Capabilities”, pp. 393.
第二,诉诸文化影响的广泛存在。这个论证较为简洁。纳斯鲍姆大致认为,环境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充斥于各个领域,在性别差异领域,我们拥有大量关于早期文化影响的证据。当然,在有关爱与关怀的问题上,我们可能无法运用早期文化影响的证据来彻底排除生物学差异的影响,但考虑到母爱情感形成的方式,那些容易被我们视为与生俱来的“天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早期的和隐性的文化影响,我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
第三,诉诸文化差异。自然主义者认为,女性天生就是情感的动物,她们是爱与关怀的给予者。说这种现象是“自然的”,意思是它的产生和形成具有某种稳固的、普遍的生理原因,不会受到社会文化及其特殊性的影响。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女性在给予爱与关怀的过程中呈现出文化差异(即便在一个国家之内)已是不争的事实。首先,由于受到阶级和地域文化的影响,人们在表达这类情感时所遵循的规则常常是不一样的。其次,关于什么是爱的典范,什么是良好的亲子关系,西方女性和印度女性会呈现出规范性判断方面的差异。最后,人们关于爱与关怀的恰当对象的看法也经常受到不同文化和环境的影响。
第四,诉诸家庭的社会建构性。有些人从家庭组织具有某种固定的习俗性质得出家庭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结论,纳斯鲍姆认为这种观点完全不合情理。美国家庭由于不同的种族来源和地域来源,常常呈现出巨大的结构多样性,印度的家庭女性在不同习俗和法律的影响下产生截然不同的家庭观念,并且不论是相关习俗还是法律都在持续地变化中。家庭实际上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无论其结构形成还是成员权利都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塑造。“结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公开的、受国家管制的仪式。有一些国家法律对它下定义,这些法律对进入那个特权领域作了限制。国家不只是对结婚进行外部监管,它还宣布人们结婚。其他不符合国家要求的非常相似的人不能算作已婚,即使他们符合一切私人的甚至是宗教的婚姻标准。”[1]Martha C. Nussbaum,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pp. 263.相较于宗教组织和教育机构,家庭以更为深入的方式受到国家法律的影响。倘若“家庭”即便在统一的意义上也非“自然的”,那么任何独特的家庭形式便都非必要且必然的。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家庭作为爱与关怀的私人领域,天然地属于女人的职能领域和势力范围。
三、挣脱思想漩涡:性别本质论与反本质论
试图把女性看作一个“种类”统一起来的女性主义者常常面临“女性共同属性”是什么的问题。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会走向亚里士多德式“生理决定论”,即相信某种心理属性(如关怀)之所以构成女性共同的特点或本质,是因为它建立在自然的生理差异之上。人们常常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性别本质论”。性别本质论者一般都是生理决定论者,她们主张男女两性存在本质性差异,这种差异是自然的而非建构的。然而,性别本质论面临广泛的批评。其一,这种理论承认了父权制文化中的二元对立。其二,作为本质的属性因独立于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而常常容纳不了现实的变化。其三,作为本质的属性很难囊括一切情形而具备普遍性。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受到后现代理论家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若要彻底推翻父权制文化,首先就得消除性别本质论的二元划分。女性群体中呈现的多样性足以表明,普遍的女性本质是不存在的,一切生理差异和心理差异都具有社会建构性。可是,这些性别反本质论者同样遭遇棘手的问题——代表问题(representation question)。女性主义不是也不应当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它拥有独特的政治诉求,如果不存在某种普遍的女性本质,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仍可以将理论标榜为“女性”主义的呢?更重要的是,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我们又该团结谁,孤立谁,和谁保持一致,共同来反抗谁呢?
为了解决生理本质主义遭遇的“共性问题”(commonality question)以及反本质主义遭遇的“代表问题”,一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女人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的,但使她们统一起来的根源是社会性的而非生理性的。例如,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将男女两性的差异理解为男性重视分离性的自我意识和女性重视关系性的自我意识的差异;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则把女性的统一性理解为性屈从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基于某种生理事实,而是通过偶然的社会制度来表达,如色情文学。然而,这些社会本质主义者显然与生理本质主义者一样面临“共性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难题,萨利·哈斯兰格(Sally Haslanger)的“社会客观主义”理论应运而生:第一,根据抽象的关系属性来定义女性,使女性定义能够灵活容纳多样性;第二,把“客观性”作为一个薄的形而上概念来加以使用,表明女性仍然构成一个客观种类,从而解决代表不足的问题。有人质疑说,这种非本质主义的性别概念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呈现某种实在的结构,以区别于单纯建构性的性别分类呢?哈斯兰格回应道,我们不需要把种类的客观性想象得过于神秘,就像我们可以通过办公桌上的各个物件都“在办公桌上”这个共同特性,把它们看作是客观的一类事物,我们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理解女性类别的客观性。[1]Theodore Bach, “Gender Is a Natural Kind with a Historical Essence”, Ethics 122 (January 2012) : 231-272, pp. 238.批评者或许会说,把书桌上的物件看作统一的一类事物,本就是观察者有意屏蔽视野中任何其他物件以及相对位置的一个结果,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统一性具有与人类意识建构无关的客观性呢?哈斯兰格倾向于告诉我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我们会把某些特性看得比另外一些特性更重要,但这些特性是什么仍然不由我们决定。当我试图收拾办公室准备离开时,在我桌上摆放着的这些东西就会具有某种特别的重要性而使我忽略其他、将它们看作一个集合,但是这些东西“在办公桌上”这一共同特性并不是由我主观构建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一种客观性。[1]萨利·哈斯兰格:《形而上学中的女性主义——对本性的讨论》,收录于米兰达·弗里克、詹尼弗·霍恩斯比编,肖巍、宋建丽、马晓燕译,《女性主义哲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 页。类似地,某些人被认为是女性,常常源于政治和法律上的重要性。出于斗争需要,我们会把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等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称之为女性,尽管她们各有不同,我们也难以找到某种共同的“本质”来描述她们,但她们仍会呈现出某些非建构的客观特征,例如,体现她们在生殖中的生物学角色的那些被观察到或被想象到的身体特征。哈斯兰格相信,“性别可以被富有成效地理解为一个更高阶的种类,它不仅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等级制社会地位,而且还潜在地包括其他非等级的社会地位,这些地位一定程度上是由生殖功能来定义的”[2]Sally Haslanger, “Gender and Race: (What) Are They? (What) Do We Want Them to Be?”, Noûs, Vol. 34, No. 1 (Mar., 2000) : 31-55, pp. 43.。
当这些女性主义者都忙于捍卫、批判或重构一个既定社会中两种实际的规范时,纳斯鲍姆把注意力投向了其他地方。她认为,这些理论家都忽视了男女两性同为人类这一事实。在女性问题上,如果我们需要某种规范,那将是超出两种实际规范(分别适用于男女两性)的某种单一规范——人性规范。这种规范之所以单一,是因为它“雌雄同体”或“不分男女”,但它并不是具体的一套有关男女两性如何生活的理想规范。为了顾及女性视角中那些可能具有独特性和有价值的东西,它“作为对所建议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原则的一种限制,以一种不很具体的、否定性的方式起作用”[3]朱丽亚·安娜斯:《妇女与生活质量:两种规范还是一种?》,收录于阿玛蒂亚·森、玛莎·纳斯鲍姆主编,龚群、聂敏里、王文东、肖美、唐震煊译,《生活质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 页。安娜斯在文中表示,她的许多思想受益于纳斯鲍姆。。这就是纳斯鲍姆开列出来的核心人类能力清单。这份清单是“厚实的”,同时是“不明确的”,它虽不试图告诉女性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完全正义的生活,但确实告诉她们什么样的生活是绝对不正义的、不值得过且不应当过的生活。它充分尊重女性的多样性,在接受实践理性和依附能力所施加的基本限制之下,允许根据不同的地方性观念或个人化观念对清单中的某些条目做出具体规定和说明。
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争论中,纳斯鲍姆基于核心人类能力的人性说明承诺了某种内在主义的本质主义立场。纳斯鲍姆认为,采取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是行不通的,因为对本质主义的彻底拒斥会走向主观主义。采取形而上的、实在论的本质主义同样行不通,由于这种本质主义认为世界的真实面目必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有别于生物的认知功能所给出的解释,存在着一些先在的、独立的形而上实体来决定世界的本质,它引发了最广泛的怀疑论:一个独立的形而上实体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假定它存在,我们也无法认识它。就人类的本质而言,我们无法从人类在历史中的自我解释和自我评价之外获得有关人性的说明,即使有某个独立的存在者给出这样一种说明,它也无法把捉到真实的人类生活特征。受亚里士多德本质主义和“现象”方法的影响,纳斯鲍姆主张通过有关人类历史和经验的内在考察来解释人性,这要求我们对人类自身展开伦理探询,询问哪些是人的本质属性,哪些是人的偶然属性,只要一个人尚且具备被界定出来的本质属性(如推理能力、回应他者的能力或选择、行动的能力等等),我们就可认为他仍在过着一种属人的生活。
反对者会说,一旦给出确定的有关人性的观念,并赋予这种观念以道德的和政治的规范性力量,在适用观念时,我们首先就得询问哪些存在者能被恰当地归于“人类”这一概念之下。如此一来,别有用心之人便可据此将少数人群和弱势群体排除在这个概念之外。例如,亚里士多德便从强调理性的人性观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妇女、野蛮人和奴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对此,纳斯鲍姆做出如下回应:能力清单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人类能力(综合能力)清单,它构成对最低限度的美好人类生活的说明,即便某些人未能满足这个规范,我们也不能据此否认他们的“人类”身份。应当说,“两个人类父母的每一个后代都拥有一些基本能力,除非并直到长期的经验使我们确信,这个人遭受到如此巨大的伤害,以至于无论如何巨大的资源支出都不可能使他达到更高的能力水平”[1]Martha C. Nussbaum, “Human Functioning and Social Justice: In Defense of Aristotelian Essenti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2 (May. 1992) : 202-246, pp. 228.。至于亚里士多德为何没能免于此种批评,那是因为他没有一如既往地贯彻他的内在主义的“现象”方法,只要他深入考察人类的日常信念,就会发现妇女、野蛮人和奴隶都无法被排除在“人类”概念之外。受历史与文化局限的亚里士多德始终相信,家庭和亲人是人类美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妇女对于维护家庭结构来说极为关键,他无法想象一种既能维护家庭的重要性,又能使妇女得到同等的教育和从事卓越活动的机会的生活结构,故而为妇女的家庭角色寻来了一种形而上的、实在论的本质主义解释。
作为最低限度的本质主义的人性说明将在何种意义上解决女性主义者面临的问题呢?对于“共性问题”,雌雄同体的单一人性规范展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容纳各种群体,同时也与任意两种有关人的实际规范(如男性规范和女性规范)相容;对于“代表问题”,它主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少数群体都以人类名义争取正常功能发挥所需核心能力,反抗一切反人类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由此可知,纳斯鲍姆虽批评自然主义女性角色论,但并不反对女性主动选择爱与关怀的给予者角色。不过,女性的选择空间始终是由关于人性的最低限度规范——核心人类能力清单所提供的。纳斯鲍姆明显认为,深陷性别本质论和反本质论争议的女性主义者都忽视了根本问题,性别差异(以及性向差异)本身并不值得忧心,值得忧心的是将差异关联于一种等级制度,只要我们确保底线意义的平等,让所有人都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那么各类差异均可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