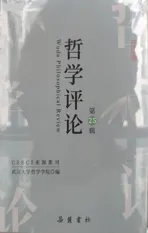论“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之理论架构
2020-11-29田希
田 希
五代、宋初永明延寿(904—975)之《宗镜录》,融合禅宗与华严、天台、唯识诸教教义,集佛教思想之大成,堪称“中国佛学精华录”或“中国佛学通论”[1]陈兵:《中国佛学的第二位集大成者——永明延寿》,杭州佛学院编:《永明延寿大师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 页。。目前,学界对《宗镜录》虽有研究,但多是从禅教合一等专题入手,并未从理论架构层面提纲挈领,总体把握。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冉云华曾对《宗镜录》论断:永明延寿思想(主要体现于《宗镜录》)“以佛性为中心,理论架构是依《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而建立”,这是中国佛教思想的总相。[1]冉云华:《永明延寿》,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155 页。但至于延寿为何以“一心二门”架构《宗镜录》,冉云华未曾交代,学界亦未曾重视。问题在于,《宗镜录》有何旨趣、特色,“一心二门”有何内涵、实质,“一心二门”又凭何作为其理论架构,其原因何在呢?
一、“一心二门”与永明延寿思想之渊源
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大乘起信论》(以下径称《起信论》)作为标志性论典,开中国宗派天台、华严、禅三宗之先,平衡各家争论,着实为一大要论。元晓(617—686)称《起信论》为“诸论之祖宗,群诤之评主”[2][新罗]元晓:《大乘起信论别记》卷一,《大正藏》第44 册,No.1845,第226 页。,并不为过。《起信论》不仅将如来藏系统与阿赖耶系统融为一体,并以中国式体用范畴、自性本觉来诠释,以“一心二门”架构使其各安其分,恰如其当。
永明延寿本人思想宗旨属于“一心二门”范畴。据《联灯会要》载:
僧问:“如何是永明旨?”……师云:“听取一偈:‘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池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3][宋]悟明:《联灯会要》卷第二十八,《卍新续藏》第79 册,No.1557,第243 页。
从佛教义理角度来诠释,永明佛学就是“一心二门”。“一池水”即是“一心”,心如水,能随圆就方,“随缘”变化形状,适应万物状态,但无论相状如何变化,其内在特性“不变”,仍是水。这就是《起信论》中所说“一心”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之义。进一步,“日照光明生”即“心真如门”,“日照”即真如,“光明生”即自性清净,“风来波浪起”即“心生灭门”,“风来”即无明,“波浪起”即妄心发动。这四句偈,后三句即是“一心二门”思想之表征。
延寿采用《起信论》“一心二门”理论架构,因其与《宗镜录》思想相通。《宗镜录》卷八云:
空有二门,亦是理事二门,亦是性相二门,亦是体用二门,亦是真俗二门,……各各融通。今以一心无性之门,一时收尽,……咸归《宗镜》。[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 页。
将“真如门”“生灭门”二门扩大到真妄、空有、性相、理事、本末、体用、禅教、心行等范畴,《宗镜录》便是以“一心二门”与华严理事构建禅教、性相统一为归趣。
《宗镜录》引用《起信论》百余次,可谓着墨甚多。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忽滑谷快天(1867—1934)指出:
延寿所宗乃唯一真心,《起信论》所谓一心也。千经万论皆说此一心法。……一代时教折衷综合而来,唯是一心,何须立宗分派相竞为哉!延寿著《宗镜录》,即以此折衷综合为目的。……惟延寿著《宗镜录》有二动机。一为祖教同诠,二为示性相融合。此二动机通全篇一百卷,到处皆得看取。[2][日]忽滑谷快天撰,朱谦之译:《中国禅学思想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 页。
他明确阐明《宗镜录》所宗“一心”,即是《起信论》“一心”,此心是心真如门与心生灭门所依。忽滑谷快天认为,延寿撰著《宗镜录》是为了和会禅教与性相。会通性相、禅教,其实就是以“一心二门”会通空有、理事、性相、体用、真俗等范畴,打通华严、天台、唯识诸教。以“一心二门”融合禅教、性相,是延寿《宗镜录》思想的构建方式。
二、“一心二门”之内涵
《起信论》创造出中国式体用观,即体即用,而能涵摄大乘佛教空、有二宗于一体,形成一个中国式整体架构。可以说,《起信论》为中国佛教思想之开展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一心二门”作为其核心部分,则为中国佛教思维方法提供了共同范式。
《起信论》将如来藏缘起与阿赖耶缘起相结合,以“一心”随缘开显染净、凡圣、迷悟诸状态,以觉与不觉诠释迷悟状态及流转还灭过程,通过去妄归真,最终复归于“一心”。新罗元晓认为大乘诸法以一心为体:“是心通摄诸法,诸法自体唯是一心。”[1][新罗]元晓:《起信论疏》,《大正藏》第44 册,No.1844,第206 页。隋代昙延(516—588)认为真如与生灭非一非异,“真如为本,妄为末,无相离义,故言和合”,生灭与不生灭非一,但“虽不同而无别体可相异”,故也非异。[2][隋]昙延:《起信论义疏》,《卍新续藏》第45 册,No.0755,第159 页。隋代净影慧远(523—592)认为“一心二门”结构中所有范畴互相联系,“此真法中,同一体中万义互相缘集,不相舍离”[3][隋]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大正藏》第44 册,No.1843,第178 页。,但体不变,“生死涅槃,体皆是性”[4][隋]慧远:《大乘义章》,《大正藏》第44 册,No.1851,第483 页。。法藏(643—712)云:“此心体相无碍,染净同依;随流返流,唯转此心。”[5][唐]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大正藏》第44 册,No.1846,第250 页。并以不觉诠释世间法,以觉诠释出世间法。
近代以来,关于中日《起信论》真伪之辨,争论歧出。时贤论述甚富,故略人所详,兹不赘述,谨就思想价值层面稍作撮略。
“一心二门”涵摄般若、法相,可以调和矛盾。梁启超(1873—1929)指出,在《起信论》中“般若、法相两家宗要摄无不尽,而其矛盾可以调和”[6]《〈大乘起信论〉考证》,梁启超:《中国佛学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 页。;《起信论》“在各派佛学中能撷其菁英而调和之,以完成佛教教理最高的发展”,“而隋唐之佛学,宋元明之理学,其渊源所自,皆历历可寻”[7]同上书,第283 页。。他对《起信论》评价甚高,认为该论是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理论源头。印顺(1906—2005)在《佛学大要》中言:“北土唯心论,有法性为依持(如来藏说),阿梨耶识为依持之诤,《大乘起信论》颇能统一而调和之。”[8]《佛学大要》,印顺:《华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3 页。诸家对《起信论》不吝褒扬之辞,可见其在中国佛教义理上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特点。
实质上,“一心二门”结合了实相论与缘起论。日本学者汤次了荣认为:“今就《起信论》看来,所谓一心,所谓心真如门,主要是就实相方面说明;所谓心生灭门,主要是就缘起方面说明。”[1][日]汤次了荣著,丰子恺译:《大乘起信论新释》,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8 页。可见,“二门”是从实相层面和缘起层面进行诠说。从真如门而言,纯为实相本体;从生灭门而言,则是缘起与实相相即,故成“真如缘起”。“一心二门”是般若实相思想与赖耶缘起思想之综合,并以“本觉”“一心二门”“体相用”等中国化哲学范式予以确定。
正如杨维中所说,“一心”既作为众生本体之心体,又是佛界、法界以及众生界之真如理体,是心体(主体之心)与理体(本体之性)之合一,这种“心性合一”理论模式正是《起信论》对中国佛学的贡献。[2]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48 页。周贵华认为,《起信论》阐明了中国化佛教两大理论支柱,即本体论意义之“本觉说”与缘起论(发生论)意义之“真如缘起说”,其“一心二门”理论结构模式,成为中国佛教心性如来藏学说最精致的理论形态。[3]周贵华:《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 页。
由此,“一心二门”作为《起信论》理论核心,自然成为诸宗义理的共同源头与思维方法。方立天(1933—2014)认为《起信论》是“大乘佛法概论”[4]方立天:《法藏与〈金师子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 页。,杜继文将“一心二门”称为“中国佛教哲学大纲”[5]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37 页。,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理论中介、方法论以及思想架构意味。
《起信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尊崇,不仅仅在于其中国化的义理结构,而且更在于其在宗派论争中起到的重大作用。蒋维乔(1873—1958)认为,法藏“称扬《起信论》以对抗玄奘”,澄观(738—839)“更盛用之,以性相融会差别平等不二一体之说,为性恶不断论之一依据”,“使侪于圆教之列,遂为证明教禅一致之根据”,而宗密(780—841)则“达乎其极”,“于是《起信论》位置,在佛教教义史上,大为重要”。[6]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239 页。由此可见,《起信论》“一心二门”之重要,不仅有理论本身的原因,更有人为推重的因素,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占据话语中心地位,成为中国佛教思想之正统,亦是宗派斗诤、争夺正统之利器。鉴于这两方面原因,它业已成为中国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显要,意义非凡。
在中国佛教发展中,诸家对“一心二门”的利用与诠释已然超出了《起信论》的原始文本意义,故此,应从融合空有、性相问题等层面来理解。《起信论》“一心二门”不仅是中国佛教思想的理论中介,而且是中国佛教思维的方法论,这是“一心二门”成为《宗镜录》理论架构的深层意蕴。可以说,永明延寿之所以能平衡华严、天台、唯识各家理论,秘密就在于《起信论》“一心二门”架构。所以在《宗镜录》里,“一心二门”成为一种阐释模型。一切佛法,诸家义理,不出性相、理事、空有等范畴,共成“一心二门”。
三、《宗镜录》之旨趣、特色与架构
(一)理论旨趣:以教补禅,融合宗教
冉云华认为,《宗镜录》一百卷,是中华佛教哲学最大篇幅之百科全书,书中教义,“乃是集天台、华严、唯识及禅宗四家之教义,而加综合讨论”,“主张禅教并重,性相合一,以一心而统万法,顿悟渐修以证道”[1]冉云华:《永明延寿》,东大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54—55 页。。四家之中,禅宗为宗,华严、天台、唯识为教,“以宗摄教,借教明宗”,归于一心。
《标宗章》对《宗镜录》主要内容有所概括:“详夫祖标禅理,传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门,立诠下之大旨。”[2][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8 页。以“一心”为宗,此“一心”既是法界理体,又是众生心体,人人自性本具,只是被无明、妄染所覆,只要返本还原、除妄归真即可。此心不可言说,也无相状,超出言语思维逻辑之外,唯有不断反观体认、直觉体悟始得。而华严、天台、唯识诸教不离文字言诠,是以佛教经论使人通晓佛理,以便契入自性、自证心源。故延寿以禅摄教,借教明禅,以有言之教明无言之宗。
延寿在《宗镜录》卷一中说:“若欲研究佛乘,披寻宝藏,一一须消归自己,言言使冥合真心。但莫执义上之文,随语生见;……假以宗镜,助显真心。”[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4 页。可见,华严、天台、唯识诸教义理,只是一种媒介,是“假借”来作镜子用,用以照显真心。所以延寿固然引用诸多经典教义,但并非为了卖弄炫耀,而是作为一种方便权法,使人借助经教来发明本心,体会诸法实相。
实际上,禅教可以融合,也实质一致。日人小野秀原曾论及“教禅之区别”,认为“教是表禅是里”[2][日]小野秀原著,张绂译述:《佛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06 页。。一言以蔽之,教禅是一回事,禅是单刀直入,直接进入直观世界,教则是先借助文字语言作为方便之门,但终归入于直观之禅,禅教殊途同归。蒋维乔更有“举教皆禅”之说,认为,所有佛教宗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禅宗,“全体佛教,自一面观之,皆为禅宗”,“唯禅之内容、解释,互有差异”,“禅之形式,为佛教之通则”,但实际“为唯一之修行方法”。[3]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 页。可见禅、教只是表现方式不同,但论其实质,终归非异。所以永明延寿将诸教融合于禅,也不奇怪。
(二)思想特色:一心为宗,圆融会通
《宗镜录》将禅宗与华严、天台、唯识诸教融合,其中诸教以华严为尊,有“禅尊达摩,教尊贤首”之说,故在“一心”指导下,凸显出圆融色彩。正如吕澂(1896—1989)所说,延寿思想以南宗顿悟与《华严》圆修相结合为基础。[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3 页。在此基础上,广摄诸法,而后以“一心”融摄诸教义理,诸法皆得会通。
在义理上,“一心二门”本有圆融特色,不过经过华严宗阐释发挥后,四法界、六相、十玄遂成为极致圆融之代表。故诸教义理被华严收摄殆尽,而总体以“一心”摄之,这“一心”为禅宗、诸教所共有。如延寿在《宗镜录》卷第三十四中云:
此论见性明心,不广分宗判教。单提直入,顿悟圆修,亦不离筌罤而求解脱,终不执文字而迷本宗。若依教,是《华严》即示一心广大之文;若依宗,即达磨直显众生心性之旨。[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578—579 页。
此段可以作为“禅尊达摩,教尊贤首”之最佳说明。克实而言,不论南宗、北宗,或者天台、华严诸教,其实宗旨一致,都是为了明心见性,只是方式不同。所以《宗镜录》主旨在于“见性明心”,求其大同;不在于“分宗判教”,辨别诸异。禅宗固然讲究顿悟,不执迷于文字相,但在修行过程中又需要以经教为辅,以资对证。在主旨上,《宗镜录》广引诸教,仍是禅宗本意,华严、天台、唯识只是说明“一心”之工具,最终仍回归到达摩禅。
延寿在《宗镜录》卷一中说华严自性清净圆明体“即一切众生自心之体,灵知不昧,寂照无遗。非但华严之宗,亦是一切教体”[2][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29 页。。延寿将华严自性清净圆明体即真如心作为众生心体,其不仅是华严宗之体,而且是天台、唯识等教之体,这就在“一心”基础上统摄了诸教。从根本宗旨来说,禅宗诸教平等,法法无碍,理事圆融,这为延寿会通禅教奠定基础,使《宗镜录》思想呈现圆融色彩。
(三)架构方式:“一心二门”
《宗镜录》以“一心”为宗,但“一心”不可说,只能依照真俗、空有二谛说法,因此,要表达“一心”这一特性,“一心二门”便成为最佳理论模式。“若约正宗,心智路绝;若离二谛,断方便门。以真心是自证法,有何文字?凡能诠教,无非假名,故云依二谛说法。”[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7 页。故而“一心”权开真如、生灭“二门”,即是依二谛而说法,一切法尽摄其中。
延寿明确指出,“一心二门”这一法门可“全证《宗镜》大意”:“于真俗二门,则收尽染净诸法。……斯乃是诸经旨趣之门,亦可全证《宗镜》大意矣。”[2][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504 页。诸法不出空有,“一心二门”摄尽诸法。“一心二门”即真如即生灭,即是《宗镜录》宗旨。
为了阐明佛理,延寿在《宗镜录》中多次援引“一心二门”理论架构。《宗镜录》卷第二十七说:
总立一心,别含多义。真如门内,无自无他;生灭门中,有善有恶。随缘开合虽异,约性一理无差。……“开则无量无边之义为宗,合则二门一心之法为要。二门之内,容万义而不乱;无边之义,同一心而混融。……是为马鸣之妙术,起信之宗体也。”[3][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63 页。
“二门”随缘能容万法,“一心”不变能摄“二门”。《起信论》开“二门”而不显繁乱,合“一心”而不显义少,立“一心”而实无所立,破边见而实无所破,所以被众多宗派所尊崇、吸收、借鉴。真如与生灭虽然呈现不同,但不生不灭之性与生灭之相其实一体。“一心”开出“二门”,实含无量义理,举凡禅教、性相、理行、一心万行,都是“二门”所延展开的。诸教如华严、天台、唯识,教义不同,而都能被“一心二门”所摄,融合会通而不相杂乱。
《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也是《宗镜录》之本怀。延寿在卷第三十九论及《起信论》与《宗镜录》之关系:
亦如祖师马鸣菩萨,……名《大乘起信论》云:“……立心真如、心生灭二门,总论一心,别开体用。……”以此一论之要义,总摄诸部之广文。以源摄流,有何不尽?亦是诸圣制作大意,亦是《宗镜》本怀。[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664 页。
《起信论》以“一心二门”义理架构开中国佛教哲学体用范式,并以此范式发起众生信心,融摄诸教文字义理。延寿坦承,《起信论》这种“以源摄流”方式摄尽佛教义理,也成为“《宗镜》本怀”。正如杨维中所说,永明延寿“一心”与《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完全一致。[2]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50 页。
学者认为,《宗镜录》“一心说”圆融法相与法性,与《起信论》“一心二门”有关联,因为后者正是从不生灭之性与生灭之相“二门”分别诠说“一心”,以会通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永明在“一心二门”基础上按圆教之意趣建立了“一心说”。[3]周贵华:《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 页。其说法有一定道理。
四、永明延寿以“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理论架构之原因
(一)历史原因
永明延寿为何以“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理论架构呢?
在佛教经论中,《起信论》是佛性思想唯心化之集大成者,是中土佛性思想(特别是天台、华严、禅宗)所依据的最重要经论之一。[4]赖永海:《中国佛性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 页。《起信论》既融摄中观、唯识,又作为中国化佛教宗派之共同理论基础,深深影响了天台、华严、禅宗。延寿以《起信论》“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理论架构,有其历史原因。
华严宗思想受到《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影响,“法界缘起”“理事无碍”等观点以《起信论》“真如缘起”“真生不二”思想为基础。在延寿之前,华严宗各祖师就对《起信论》进行征引、解读、诠释,以发挥华严宗要义。华严初祖杜顺(557—640)曾以“一心二门”来诠释“理事”范畴:“心真如门者是理,心生灭门者是事。即谓空有无二,自在圆融。”[1][隋]杜顺:《华严五教止观》,《大正藏》第45 册,No.1867,第511 页。三祖法藏《起信论义记》云:“如来藏随缘成阿赖耶识,此则理彻于事也。”[2][唐]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大正藏》第44 册,No.1846,第243 页。以《起信论》“如来藏缘起”解释“理事”。《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云:“止观两门,共相成助,不相舍离”[3][唐]法藏:《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大正藏》第45 册,No.1876,第639 页。,其“止观”即来自于《起信论》;又引用道:“《起信论》云:‘若有众生,能观无念者,是名入真如门也。’”[4]同上。四祖澄观也受到《起信论》影响,《唐代州五台山清凉寺澄观传》云:“传《起信》、《涅槃》,又于淮南法藏受海东《起信疏》义。”[5][宋]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五,《大正藏》第50 册,No.2061,第737 页。五祖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云:“故马鸣菩萨以一心为法,以真如生灭二门为义,《论》云:‘……心真如是体,心生灭是相用。’”[6][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大正藏》第48 册,No.2015,第401 页。《华严原人论》云:“初唯一真灵性,不生不灭,……名如来藏,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相。所谓不生灭真心与生灭妄想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7][唐]宗密:《华严原人论》,《大正藏》第45 册,No.1886,第710 页。通过直接、间接方式反复引用。华严法界缘起就是建立在《起信论》真如缘起基础上的,其理事圆融观就是《起信论》真如、生灭二门“二而不二”的另一种表达。
天台宗对《起信论》“一心二门”相关义理亦有所摄取。比如,唐代天台宗九祖湛然(711—782)在《金刚錍》中云:“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8][唐]湛然:《金刚錍》,《大正藏》第46 册,No.1932,第782 页。这里便借鉴了《起信论》真如不变随缘之义。知礼(960—1028)也曾引用《起信论》:“故《起信论》云:‘一切众生从本已来未曾离念。’”[9][宋]知礼:《十不二门指要钞》,《大正藏》第46 册,No.1928,第707 页。以《起信论》为理论基础发挥天台教义。后期天台分为山家、山外二派,也是由于对《起信论》“一心二门”理解不同,导致分裂,从而产生真心、妄心二派。《起信论》“一心二门”与天台宗内在思想关系之深,由此发见。
唯识与《起信论》思想也联系极大。在弥合摄论宗和地论宗矛盾方面,《起信论》起到重大作用。而从唯识三自性角度看,圆成实与依他起非一非异,与《起信论》有某种契合性。《成唯识论》云:
圆成实与依他起不即不离。……真如离有离无性故。由前理,故此圆成实与彼依他起非异非不异。……由斯喻,显此圆成实与彼依他起非一非异。法与法性理必应然,胜义、世俗相待有故。[1][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大正藏》第31 册,No.1585,第46 页。
周贵华据此认为,《成唯识论》谈依他起性与圆成实性非一非异,而圆成实性即真如,依他起性法为阿赖耶识,所以亦有阿赖耶识与真如的非一非异。[2]周贵华:《〈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与唯识学相关义的一个比较》,游斌主编:《比较经学与〈大乘起信论〉》(比较经学第3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231 页。亦即是说,唯识中的依他起、圆成实对应《起信论》阿赖耶识、真如,都是非一非异、真如生灭不二的关系。由此可见唯识与《起信论》思路的内在同一性。而杨维中更认为,《宗镜录》以《起信论》为锐器融合唯识古今学[3]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下),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54 页。,唯识今学与唯识古学被延寿以“性识不二”的方式巧妙地圆融于“一心二门”架构之中。
禅宗初宗《楞伽经》,后转向以《起信论》为重,如印顺所说:“《楞伽经》为《起信论》所代,《摩诃般若经》为《金刚般若经》所代”,这是秀、能时代共同趋势。[4]印顺:《中国禅宗史》,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 页。禅宗以本觉为根本,以“一心”为宗,也是受到《起信论》思想之启蒙。五祖弘忍《最上乘论》中就明显地糅入了《起信论》思想。其云:
一切众生清净之心亦复如是,只为攀缘、妄念、烦恼诸见黑云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清净者,心之原也。真如本有,不从缘生。……此真心者,自然而有,不从外来。……了然守心,则妄念不起。……识心故悟,失性故迷。……但信真谛,守自本心。……故知守本真心是涅槃之根本。[5][唐]弘忍:《最上乘论》,《大正藏》第48 册,No.2011,第377 页。
这正是《起信论》真如不变随缘、心性本觉、除妄归真之义。可以看出,弘忍在禅修实践上采取“守真心”方法。这在《宗镜录》中也有所体现与证明,如延寿云:“弘忍大师云……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门。”[1][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1 页。有学者认为,东山法门重视《起信论》,神秀建立“离念门”,慧能标举“无念为宗,无住为本”,均可视作对《起信论》的不同发挥。[2]龚隽:《〈大乘起信论〉与佛学中国化》,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 页。宗密以菏泽禅与华严教相结合,借用《起信论》“一心二门”架构,形成“三宗三教”说,对延寿撰著《宗镜录》予以深刻影响和启发。历史地看,诸师受到《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影响,而延寿又受到诸师影响,也可以说延寿间接地受到“一心二门”思想影响。
鉴于诸教与禅宗都受《起信论》思想影响,延寿欲会通禅教,以《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作为《宗镜录》理论架构便可谓正得其宜、恰如其分。
(二)现实原因
再从佛教现实情况分析,永明延寿在当时时代背景下,面临种种问题,不得不以“一心二门”为架构,“借教明宗”,融合禅教。
一、禅宗空疏。后慧能时代,“不立文字”为不读经、不学教大开方便之门,禅门中人以此为最高凭据,思想行为放任、狂诞、极端,好谈虚空、不修实行,禅门面临危机。有感于此,文益(885—958)曾作《宗门十规论》提出十条批评意见,并主张以教辅禅,“然虽理在顿明,事须渐证”,“苟或未经教论,难破识情”,所以作此论,目的在于“用诠诸妄之言,以救一时之弊”。[3][五代]文益撰:《宗门十规论》,《卍新续藏》第63 册,No.1226,第36 页。延寿也对此现象予以驳斥:“指鹿作马,期悟遭迷;执影是真,以病为法。只要门风紧峻,问答尖新,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4][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 页。禅宗偏于空慧,口口谈空,步步行有,极不踏实,禅弊深重。
《宗镜录》以“一心二门”作为构架,其现实原因在于治南禅之病,清代悟开云:
湛寂灵明,本来无病。情生智隔,诸病生焉。于中偏病最大,贪病最多。然非独念佛,一切修行同此。故永明延寿禅师,著《宗镜录》百卷,《万善同归集》六卷,皆医偏病之妙药也。[1][清]悟开:《念佛百问》,《卍新续藏》第62 册,No.1184,第361 页。
禅宗本来无病,只因后学“情生智隔”,执权为实,于是“生病”。这成为延寿撰著《宗镜录》的一大诱因。
二、诸教“冰炭”。“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碳(炭),不达大全心”[2][宋]惠洪:《林间录》下,《卍新续藏》第87 册,No.1624,第275 页。,诸教不和,亟需会通。对于教内矛盾,延寿采取调和态度,以“一心二门”收摄诸教,故能悬搁诸教差异,而专求会通。延寿将华严、天台、唯识三家融会于“一心二门”,正好解了教内互诤之困。
三、禅教互斥。永明延寿对于此问题也有所批评:
夫听学人诵得名相,齐文作解,心眼不开,全无理观。据文者生,无证者死。夫习禅人唯尚理观,触处心融,暗于名相,一句不识,诵文者守株,情通者妙悟。两家互阙,论评皆失。[3][五代]延寿著,刘泽亮点校整理:《永明延寿禅师全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771 页。
学禅者与学教者自以为是,偏于一端。学禅者只知观心,不通义理,难以借助佛法经论提升境界,助己印证。而学教者专务名相,使经教成为外在文字,不能契合内心,进行观照印证。前者好高骛远,不落实际;后者咬文嚼字,死于句下。禅归禅、教归教,禅教互不往来,造成佛教内部隔阂,嫌隙深重。
四、法眼重任。法眼为禅宗五家最晚出一宗,延寿身为法眼三祖,值此佛教危机,为了续佛慧命,不得不扭转困局,为会通禅教做出理论尝试。在当时情势要求下,延寿以“一心二门”架构《宗镜录》思想理论,恐怕也是唯一出路,对禅宗、佛教来说,可谓逢其时,得其人。
以上几点,也与宋代惠洪(1071—1128)《林间录》所载相契合:
寺有老衲为予言:“永明和尚以贤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碳,不达大全心。……更相质难,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名曰《宗镜录》。”[1][宋]惠洪:《林间录》下,《卍新续藏》第87 册,No.1624,第275 页。
永明延寿撰著《宗镜录》之初衷,与“一心二门”有密切关系。诸教纷争,禅教互斥,急需一中立性、综合性思想作为理论中介,借以调和矛盾。“一心二门”既有调和摄、地矛盾之历史先例,又对中国佛教宗派有思想奠基作用,且思想上有调节空有、圆融性相之综合性,故成为“心宗”之“衡准”。
五、结 语
综上,“一心二门”与永明延寿思想渊源甚深,由其思想可见“一心二门”特色。《宗镜录》的思想旨趣是以教补禅、融合宗教,思想特色是一心为宗、圆融会通,架构方式是“一心二门”。“一心二门”对于《宗镜录》而言,内涵丰富,已经超出《起信论》的原始文本意义,应从中国佛教哲学的理论中介和佛教思维方法论层面予以诠释。永明延寿以“一心二门”作为《宗镜录》理论架构,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心二门”不仅是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华严、禅宗的思想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会通禅教的可能性,而且在永明延寿之前,就存在以“一心二门”为基础会通禅教的先例;从现实角度来看,晚唐五代时期佛教内部流弊深重,禅宗空疏、诸教“冰炭”、禅教互斥,而延寿作为法眼三祖肩负振兴法眼之重任,各种问题的交织,促成延寿以“一心二门”为架构撰著《宗镜录》的现实动因。
总而言之,永明延寿《宗镜录》将“一心二门”作为理论架构,以此耦合禅宗与华严、天台、唯识诸教义理,从而达到“以宗摄教,借教明宗”之目的。从某种角度上说,“一心二门”在《宗镜录》中既是理论纲骨又是黏合剂,具有中介性的工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