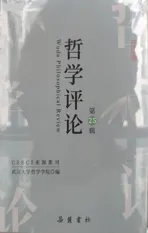孔子成《春秋》何以乱臣贼子惧?
——汉唐《春秋》学的视域
2020-11-29张立恩
李 颖 张立恩
众所周知,在《春秋》学史上,孟子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其《春秋》说几为后世《春秋》学家之普遍共识,[1]如程颐(字正叔,1033—1107)、焦竑(字弱侯,号漪园,1540—1620)及《四库总目》皆以为知《春秋》者,莫若孟子。(说见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84 页;焦竑:《焦氏笔乘》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129册,585 页;《四库总目》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97,336 页)以至有论者称:“秦汉以后,《春秋》学的发展,都是在孟子所定的框架内进行的。”[1]戴维:《春秋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20 页。曾亦、郭晓东则将孟子事、文、义之说视为“《春秋》书法之总纲”。〔氏著《春秋公羊学史》(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5 页〕《孟子》一书言《春秋》者四处,[2]分别见:《滕文公下》2 条,《离娄下》《尽心下》各1 条。现代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其中有关《诗》与《春秋》的关系问题展开,[3]可参杨朝明:《孟子的〈春秋〉观与儒学“道脉”》,《管子学刊》2011年第3 期;骆扬:《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4 期;杨海文:《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 期;夏德靠:《孟子〈春秋〉学考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对于《滕文公下》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则或直译其意而不解其由,[4]如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117 页)、杨逢彬《孟子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94 页)即属此类。或对其可靠性提出质疑,[5]如本田成之斥其说为汉代谶纬之信仰(氏著《中国经学史》,桂林:漓江出版社,54 页),赵伯雄称:“其实这只是一句空话,《春秋》真的对‘乱臣贼子’有这样大的震慑作用吗?很令人怀疑。”(氏著《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4,94 页)或径取一说以释之,[6]如曾亦、郭晓东说:“正因《春秋》一王之法,遂能惧乱臣贼子。”〔《春秋公羊学史》(上),307 页〕但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上,历代学者多有异见,因此,要准确认识这一经学命题,就首先需要对这些看法进行理论清理。本文不揣浅陋,拟以汉唐《春秋》学为视域对这一问题做一考察,以就教有方。
一、借褒贬以立法,由立法以惧贼——从董仲舒到司马迁
在《春秋》学中,对“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诠释可溯源于董仲舒。其《春秋繁露》引述《孟子》凡15 条,直称“孟子”者5 条,所引《孟子》文本与《春秋》直接相关者4 条,间接相关者3 条。[7]刘振维:《董仲舒〈春秋繁露〉承继孟学与荀学之研究》,《德州学院学报》2018年第3 期。如对《孟子·尽心下》所谓“《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春秋繁露·竹林第三》先借“难者”之口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进而做出解释。[8]文繁不具引,原文见:张世亮、钟肇鹏、周桂钿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51 页。以下本文所引《春秋繁露》原文,如无特别说明,皆以本书为准。董氏先以亩有数茎可谓之无麦苗与《春秋》所记战争中仅有两次复仇战争故可谓之无义战的类比关系,[1]董氏有关复仇为正义战争的观念是承《公羊传》而来。(《公羊传》说见庄公四年经“纪侯大去其国”条之传文)来论证“《春秋》无义战”之说的合理性。其次,又从诈战(偷袭)与偏战(阵地战)、战与不战的相对关系指出“彼善于此,则有之矣”的合理性。前者虽与孟子本义有异,[2]依《孟子》,说《春秋》无义战是因各诸侯国具有同等政治地位,无相互征伐之合法性,所谓“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赵岐、朱子之注亦皆同之。(说详李学勤主编:《孟子注疏》卷14 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48 页;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59 页)但后者则可视为对孟子之说的合理解读,[3]如就战与不战而言,《孟子·离娄上》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四书章句集注》卷7,359 页)可见,孟子明显主张不战胜于战。是以焦循(字理堂,一字里堂,1763—1820)在疏解孟子这段论述时即引述董氏上述言论,并称其说能“发明《孟子》‘无义战’之义”。[4]焦循:《孟子正义》卷28,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7,790 页。
可见,董氏对孟子思想不可谓不熟稔,因此,尽管其未明确提出针对“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诠释,但《春秋繁露》中完全有可能存在对这一观念的理解或运用,事实上,此由后世学者对《春秋繁露》之诠释即可窥见。《春秋·昭公四年》:“楚子”(楚灵王)及诸侯“伐吴,执齐庆封,杀之”。依《公羊传·宣公十一年》所云“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灵王此举有僭天子、方伯专讨之嫌,但《春秋》书“楚子”褒之,[5]《公羊传》认为《春秋》以七等名号区分贵贱等级,所谓“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公羊传·庄公十年》)董氏承其说,《春秋繁露·爵国第二十八》曰:“ 《传》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命曰附庸,三代共之。”论者以为此篇但以人、氏、名、字区别得地多少,所以只引《公羊传》之四等。〔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524 页〕故惑者疑之,董氏云:
《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诸侯之不得专讨,固已明矣,而庆封之罪,未有所见也,故称“楚子”以伯讨之,著其罪之宜死,以为天下大禁。(《春秋繁露·楚庄王第一》)
按: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齐庄公,庆封为其同党,楚灵王杀庆封是为齐讨贼。[1]《公羊传·昭公四年》:“其言执齐庆封何?为齐诛也。”董氏认为《春秋》书“楚子”是以褒扬楚灵王的方式来肯定其行为为伯讨,从而表明庆封应被诛,由此起到一种“以为天下大禁”的效果。苏舆(字嘉瑞,号厚庵,1874—1914)注云:“《春秋》,明是非之书也。记行事以加王心,凡以禁奸而劝善而已。虽以楚灵无道,诸侯外讨,不以贷庆封当死之罪。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4 页。就是说,《春秋》通过赋予楚灵王诛杀庆封的正当性,申明弑君之贼应被诛,从而使乱贼惧。[3]钟肇鹏先生亦持此说。〔见《春秋繁露校释》(上),7—8 页〕依此,则《春秋繁露》中亦渗透着对“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观念的理解。
从另一方面来看,《春秋繁露》对《春秋》的很多解释,至少在客观上亦表现出使乱臣贼子惧的效果,如《正贯第十一》称《春秋》“论罪源深浅,定法诛”,苏舆注曰:“论罪本之深浅,定法诛之轻重。”[4]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5,126 页。《王道第六》称:“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刺恶讥微,不遗小大,善无细而不举,恶无细而不去,进善诛恶,绝诸本而已矣。”苏舆注曰:“善恶之著者,进之诛之。其或嫌于恶而有善心,嫌于善而有恶心,亦为表而出之。故有事同而论异,或事异而论同。一人之身,前后不相掩;一人之事,功过不妨殊。《春秋》好微而贵志,绝诸本所以杜其渐。”[5]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4,96 页。依此,对董氏而言,《春秋》具有明显的刑书性质,[6]依《春秋繁露》,《春秋》还可为改制之书〔“王者必改制”(《楚庄王第一》〕、明存亡之道之书〔“《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观也”(《王道第六》)〕等。故不能不使乱臣贼子有所惧。
董氏认为《春秋》借褒贬实现其功能,故《春秋繁露·盟会要第十》盛赞《春秋》以“两言而管天下”,苏舆曰:“两言,谓褒贬管键也。”[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5,125 页。《史记·太史公自序》云: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司马迁:《史记》卷130,北京:中华书局,2011,2855—2856 页。
董氏前云“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后云“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可见,所谓“是非”就是对天子、诸侯、大夫之贬、退、讨——准确地说,是对天子、诸侯、大夫之褒贬,因为,贬、退、讨固然可概括为贬(“非”),而“是”则显然含有褒义。在此意义上,唐司马贞(字子正,约660—721年前后在世)解“是非”为“褒贬诸侯之得失”,[2]《史记》卷130,2856 页。虽将“天子”移出褒贬的范围,不免对董氏之意有所曲解,但将“是非”解为褒贬,则可谓知言。
综上所言,依董氏语脉,《春秋》正是通过褒贬而使乱臣贼子惧。《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谓“王心”即“采摭托意”(《盟会要第十》)之意。苏舆注云:“空陈古圣明王之道,不如因事而著其是非得失,知所劝戒。”[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6,140 页。就是说,孔子认为,空谈道理不如褒贬《春秋》中的人物和事件更能表达是非和价值判断,以实现劝勉、戒惧之效。依此,则《春秋繁露》亦含《春秋》借褒贬以惧贼之意味。实际上董氏上述言论在《太史公自序》中亦有转述,所谓“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4]《史记》卷130,2856 页。而司马贞之注解正是从使乱臣贼子戒惧的角度展开:“空言,谓褒贬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乱臣贼子惧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簒逆,因此就加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5]《史记》卷130,2857 页。司马贞对“空言”的解释未必准确,如上所引,苏舆以“空言”为“空陈古圣明王之道”,但其对《春秋》由褒贬是非而使乱臣贼子戒惧的观念的揭示则显示出董仲舒对“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理解的某些特点。
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借记事阐述其王道之说,所谓“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俞序第十七》,标点有改动)苏舆曰:“假位号,因成败,此圣人作《春秋》之意。因故事以明王义,事不虚而义则博贯。”[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6,144 页。具体方式就是前引所谓“两言而管天下”。可见,从诠释“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角度而言,内蕴于董氏《春秋》学中的理解可概括为:褒贬→立法→惧贼,即孔子在《春秋》中借褒贬以立王法,而王法的施行,则可使乱贼惧。
事实上,这种观念在继承董说以作《史记》的司马迁那里得到进一步展现,[2]《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余闻董生”一语,真德秀(字景元,号西山,1178—1235)据此认定“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氏著《董仲舒论春秋》,《文章正宗》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55 册,348 页)真氏之言未免推之太过,但史迁继承董氏《春秋》学则颇为可信。事实上,史迁在《史记》中不但反复申述董氏明于《春秋》,亦直接征引董氏论《春秋》之语申述己说。除了上引董氏之言,又《太史公自序》称:“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而相似说法亦见于《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可见,史迁之说实出自董氏,是以段熙仲称“史公此说,盖本之董君”。(氏著《春秋公羊学讲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 页)《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3《史记》卷47,1738 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史迁之意,《春秋》借褒贬书法确立起一应然的政治原则——贬损之义,后世王者若依此而行,则乱臣贼子惧。清人钱大昕(字晓徵,1728—1804)将其说概括为“防其未然”:
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为后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春秋》之法行而乱臣贼子无所容其身,故曰惧也。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渐,圣人随事为之杜其渐。[1]钱大昕:《答问四》,《潜研堂文集》卷7,《嘉定钱大昕全集9》,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99 页。(标点有改动)
钱氏之说颇有所见,其所引出自《太史公自序》,在上述引文之后,史迁接着指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所谓“禁未然之前”即防其未然之意。不过,钱氏将刺其已然与防其未然截然二分,强调《春秋》仅为防其未然,并不准确。因为,一方面,就《春秋》性质而言,称其具有防其未然之功能只是史迁对《春秋》性质理解的一个方面,其所谓“礼禁未然之前”只是强调相对于仅具“施已然之后”功能的法而言,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春秋》具有防其未然的功能。实际上其同样承认《春秋》具有刺其已然的功能,在上引《太史公自序》中,其既取董仲舒之言,显然认同其说,即承认《春秋》具有褒贬进退天子、诸侯、大夫的作用。况且,其明言孔子要推《春秋》褒贬之义评判当世(“推此类以绳当世”),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亦称孔子作《春秋》之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可见,其承认《春秋》具有刺其已然的功能。
另一方面,就《春秋》之宗旨而言,司马迁固然承认《春秋》之目的在于防其未然,但防其未然与刺其已然并非两橛,而是有内在联系,《太史公自序》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而依其所引董仲舒之说,《春秋》试图通过褒贬天子、诸侯、大夫确立天下仪表、以达王事,史迁又将实现王道的途径诠解为“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即将《春秋》确立的褒贬原则展开于具体的政治活动,由此即可使“天下乱臣贼子惧”。可见,依史迁,刺其已然正是为了防其未然。
二、褒贬立法惧贼说之理论困境及汉儒之解决方案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孔子身为人臣,借修《春秋》而褒贬天子、诸侯、大夫,显然有僭越之嫌,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构成宋代《春秋》学对汉儒《春秋》说质疑的重要方面。[1]如吕大圭(字圭叔,南安人,称朴乡先生)云:“圣人作经以示万世,固未尝有一毫私意参于其间,而顾欲窃褒贬之权以自尊乎?且鲁,一国也。夫子,匹夫也。夫子因一国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则是私鲁也;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窃天子之刑赏,则是私己也,圣人宜不为是也。”(氏著《春秋或问》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57 册,478 页)就董仲舒《春秋》学及汉儒之相关诠释来看,其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方案是“素王作《春秋》代汉立法”说。从逻辑上看,其对这一方案的建立有两个层次:
首先,论孔子为素王。“素王”一词出自《庄子·天道》,郭象(字子玄,约252—312)注云:“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2][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庄子注疏·外篇·天道第十三》,曹基础、黄兰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249 页。即以有德无位者为素王。《春秋》学中最早明确以素王论孔子者为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称:“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即以哀公十四年经文“西狩获麟”为孔子受天命之符瑞。其《天人三策》云:“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3]班固:《汉书》卷56,北京:中华书局,2012,2175 页。可见,董仲舒以孔子为有德无位之王,故其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4]班固:《汉书》卷56,2183 页。
相较于郭象,董氏之说除了强调素王的有德无位,更强调“素王”一词所表征的孔子意志对于褒贬赏罚的决定性,这与《春秋繁露》所谓“吾(孔子)因行事,加吾王心”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思想被汉儒广泛接受,如王充(字仲任,27—约97)继承董氏之说[5]就王充《论衡》中论及《春秋》之处来看,其说无疑有取于董仲舒。论者认为,就《论衡》中涉及董仲舒的言论来看,王充对董仲舒的人格、思想和历史事实皆持肯定态度,尤其对《春秋》学和天人对策等方面的董仲舒的学问、文章、文风等表示了最大的赞意和尊敬。(邓红:《王充论董仲舒》,《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 期)而将之阐述得更加清楚,《论衡·超奇》称:“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6]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530 页。又云:“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1]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8,532—533 页。即孔子对《春秋》人物的褒贬赏诛取决于其自我意志,其意即王意,故孔子为素王。相关说法还见于两汉其他文献,[2]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春秋》学,得到当时学术界的广大承认,此即《汉书·五行志》序论所说的“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更通过纬书及《白虎通德论》中的大量吸收而成为一般的通说。〔氏著《两汉思想史》(二),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331 页〕如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3]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卷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9 页。贾逵(字景伯,30—101)《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4]《春秋左传正义》卷1,29 页。郑玄(字康成,127—200)《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5]同上。可见,《春秋》学中由董仲舒明确指明的孔子素王说,经过汉儒传衍,成为两汉经学共有之观念。
就《孟子》本文来看,以孔子为素王亦有其合理性,《孟子·万章上》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荐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依此,则孟子实有以孔子为素王之观念,事实上,赵岐(字邠卿,约108—201)注《孟子》时即发挥此说,如其注“《春秋》,天子之事”称:“孔子惧正道遂灭,故作《春秋》。因鲁史记,设素王之法,谓天子之事也。”[6]李学勤主编:《春秋公羊传注疏》卷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0 页。又注“其义则丘窃取之”称:“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7]《孟子注疏》卷8 上,267 页。又其注《公孙丑上》所引孔子弟子宰我所谓“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时,称:“以为孔子贤于尧舜,以孔子但为圣、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8]《孟子注疏》卷3 上,95 页。可见,汉儒只是将《孟子》本有的孔子为素王之观念明确揭示出来而已,[9]有论者提出,是孟子开启了汉代孔子为素王之观念。〔夏德靠:《孟子〈春秋〉学考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而董仲舒对这一观念的明确标示,则使孔子具有王的身份,成为政治的君主人格。[10]黄开国:《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4 页。易言之,经由如上诠释,孔子被赋予素王身份,从而具有了对《春秋》人物施以褒贬赏罚的合理性。
其次,论素王作《春秋》代汉立法。上述说法在赋予孔子素王身份的同时也带来另一问题:在周天子尚在的情况下,以孔子为素王,褒贬诸侯,形同叛乱。不过,对汉儒而言,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孔子作为素王的合法性在于《春秋》代汉立法。《论衡·程材》云:“《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1]《论衡校释》,475 页。又《须颂》云:“《春秋》为汉制法”,[2]同上书,748 页。又《佚文》云:“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3]同上书,757 页。王充之说实系推演董仲舒之意而来,如前引“垂遗于汉”之说即是,所谓“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4]同上书,474—475 页。“然则”二字尤可见出前后二句间之推衍关系。
相关说法广泛存在于汉代纬书之中。如《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云:“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何休注云“待圣汉之王以为法”,其说即从纬书而来,何氏引《春秋演孔图》为据:“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5]《春秋公羊传注疏》卷28,719 页。徐彦《公羊》疏亦引《解疑论》云:“西狩获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为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故孔子曰‘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修为《春秋》。”又引《春秋说》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6]《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3 页。徐彦认为“以此数文言之,《春秋》为汉制明矣”。所谓“赤”“火”即汉德为火。[7]参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139 页。依徐复观,纬书之说亦系推演董仲舒之意。[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332 页。
孔子为汉制法说与谶纬的结合,成功实现作为素王的孔子从“受命王”到“制法主”的转变,[1]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399 页。进而成功化解素王说所隐含的理论危机。正是为此,《春秋》在汉代成为最为官方所重视的经典,并在汉代政治的建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关于《春秋》与汉代政治建构之间关系的论述可参阅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后世亦有疑《春秋》为汉制法之说者,如欧阳修云:“谶纬不经,不待论而可知。甚矣!汉儒之狭陋也,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氏著《后汉鲁相晨孔子庙碑》,《集古录》卷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1 册,25 页)皮锡瑞(字鹿门,1850—1908)驳之,称其“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氏著《经学通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375 页)二说虽异,但实际上都未认识到,汉儒对《春秋》为汉制法观念的推崇,不仅在于论证汉代政权之合法性,更在于为《春秋》在汉代政治中的合理性做出说明。
三、由褒贬以惧贼:东汉及晋唐《春秋》学之诠释及其对史学之影响
东汉时期,由于古文经学的兴盛,重视文字训诂而非发挥微言大义的诠释方法成为经学中的主流方法。在对孔子形象的理解上,相对于今文家以孔子为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古文家将孔子视为史学家。[3]参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4—5 页。从《春秋》之褒贬的角度来说,将孔子视为史学家,就是将《春秋》视为只具有历史批判功能的史书,而否认其为立法之书。这一特点即反映于赵岐《孟子章句》[4]关于《孟子章句》重视章句训诂与考据的诠释特点的介绍,可参陈韦铨《试论东汉赵岐〈孟子章句〉之诠释方法》,《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 期;郭伟宏《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三章第四节《赵岐〈孟子章句〉的特点》。一书,[5]汉儒注《孟子》之书有程曾《孟子章句》、高诱《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刘熙《孟子注》、赵岐《孟子章句》等,今存其书且流传最广的唯赵岐《孟子章句》。是书中,赵岐对从董仲舒到司马迁以来所形成的《春秋》由褒贬以立法、由立法以惧贼的诠释理路进行转换,对“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做出新诠,其称:“言乱臣贼子惧《春秋》之贬责也。”[6]《孟子注疏》卷6 下,211 页。又其注《滕文公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称:“知我者谓我正纲纪也,罪我者谓时人见弹贬者。”[1]《孟子注疏》卷6 下,210 页。赵岐认为“乱臣贼子”特指《春秋》中所弹贬的人物。乱臣贼子惧是因受到《春秋》之弹贬。可见,在赵岐这里,《春秋》作为立法之书的功能不再被强调,而是主张径由《春秋》之弹贬而使乱贼惧。此义宋人孙奭(字宗古,962—1033)之疏[2]关于孙奭与《孟子注疏》关系的考证及《孟子注疏》学术史价值的介绍,可参董洪利:《〈孟子注疏〉与孙奭〈孟子〉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 期;高丁国:《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亦有所彰明,其云:“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贬著,而乱臣贼子于是乎恐惧之。”[3]《孟子注疏》卷6 下,213 页。赵岐言“贬责”,孙奭云“褒贬”,二者稍有异,但从其对《春秋》性质的理解来看,二者并无本质不同,因为,孙奭以《春秋》为“褒贬之书”,“以赏罚之意寓之褒贬,而褒贬之意则寓于一言耳”(《孟子注疏》卷8 上,267 页),而赵岐亦以《春秋》“举毫毛之善,贬纤芥之恶”(《孟子注疏》卷14 上,448页)。清人焦循为反驳顾栋高(字复初,1679—1759)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理解为“防微杜渐之道”的说法,对赵岐“贬责”之说提出另一种解释,认为《春秋》惧贼功能的实现,靠的是讲明君父不可弑不可逐之理(说见《孟子正义》卷13,381 页),此为焦氏新说而非赵岐本义。
经过董仲舒、司马迁、赵岐等汉儒的诠释和阐发,[4]《汉书·艺文志》承司马迁之说,称孔子作《春秋》,“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又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将褒贬与惧贼联系起来理解“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成为晋唐《春秋》学之主流。由上分析可知,在褒贬惧贼的问题上,区分今古文的关键在于是否承认褒贬具有立法之功能。东汉以降,随着公穀式微,左氏独兴,晋唐学者主要继承了古文学的思路——从刺其已然即《春秋》之历史批判的角度理解褒贬,并因其对孔子素王之观念的批驳,进一步将“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从经学命题转换为史学命题,这一点尤见于杜预《春秋》学。
如所周知,东晋以后,在《左传》学上经过服(虔)注与杜(预)注之争,最终杜注胜出,直至唐初,在《春秋》学上所盛行的基本是杜注,《隋书·经籍志》称:“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无师说。”唐代颁定《五经正义》,又将杜注定为一尊。因此,杜注对褒贬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晋唐《春秋》学之褒贬观。杜预一方面主张从史的角度理解《春秋》: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1]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左传正义》卷1,12—13 页。
孔颖达疏亦以为“仲尼修《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公之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2]《春秋左传正义》卷1,20 页。依此,则鲁《春秋》所记乃承赴告策书,而孔子删定鲁史是为恢复周公礼制。在此意义上,皮锡瑞将杜说概括为“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并认为若如其说,则《春秋》“只是抄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3]皮锡瑞:《经学通论》,365 页。
但另一方面,杜预又主张《春秋》有所谓“一字褒贬”,似与其前说相左,但实际上其所谓“一字褒贬”并非如公羊家所主张的那样,认为《春秋》的语词差异蕴含着孔子的微言大义,而是强调:褒贬的形成取决于历史语境,所谓“ 《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因而他主张解经“当依传以为断”,[4]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左传正义》卷1,24—25 页。即依《左传》史实及经说解经。可见,杜预所理解的褒贬削弱甚至取消了孔子意志所起的关键性作用,[5]有论者指出,杜预所谓“须数句以成言”实际上是对“一字褒贬”的反对。(赵伯雄:《春秋学史》,212 页)而强化其中的历史批判意味。
同时,杜预亦反对汉儒的孔子素王说:“子路欲使门人为臣,孔子以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6]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春秋左传正义》卷1,34 页。孔颖达疏称:“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借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1]《春秋左传正义》卷1,35 页。可见,其反对孔子借素王之名以立法。
杜预的上述观念影响到晋唐《春秋》学对褒贬之理解,典型者如《隋书·经籍志》称:
《春秋》者,鲁史策书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沦废,鲁以周公之故,遗制尚存。仲尼因其旧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顺,或直书其事,以事首恶。故方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乱臣贼子,于是大惧。其所褒贬,不可具书,皆口授弟子。
其说几乎就是杜说之翻版。其强调《春秋》通过褒贬历史人物以戒惧乱臣贼子。这种对褒贬惧贼观念的理解亦融入晋唐史传、谥号等史学实践当中,如唐陆贽(字敬舆,754—805)《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称:
褒贬之词,《春秋》所重。爵位有侥幸而致,名称非诈力可求。……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岂必临之以武,胁之以刑哉?褒贬苟明,亦足助理。[2][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75,北京:中华书局,1983,4845 页。
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知惧。虽窃位于当时,死加恶谥者,所以惩暴戾,垂沮劝。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3][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56,北京:中华书局,2000,2811 页。
即以死加恶谥惩罚暴戾为例说明《春秋》惧贼靠的是对名称的褒贬。独孤及(字至之,725—777)论谥法亦称:
昔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绳当代,而乱臣贼子惧。谥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惩恶劝善,不在哀荣,在议美恶,不在字多。[4][唐]独孤及:《驳太常拟故相国江陵尹谥议》,载[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86,8 页左,北京:中华书局,1983,3927 页下。
褒贬惧贼观念对晋唐史学实践之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并且,这一观念在史学中的延展以至出现以史学所理解的褒贬反过来衡定《春秋》的现象,如史学家刘知幾(字子玄,661—721)一方面认为“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1][唐]刘知幾:《史通·外篇·惑经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629 页。“《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2]同上书,645 页。但又认为《春秋》并未很好地贯彻褒贬惧贼之观念:“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本国之杀逐其君者有七,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3]同上书,645—646 页。清赵翼(字云崧,1727—1814)对此亦有申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篡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氏著《春秋书法可疑》,《陔余丛考》卷2,曹光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2 页。标点有不同)
众所周知,中唐以后,以啖助(字叔佐,724—770)学派为代表的新《春秋》学兴起,因而对褒贬惧贼说之阐释亦随之有了新的进展,[4]此处不及详阐,笔者另有专文论之。但即便如此,从褒贬名爵的角度诠释《春秋》惧贼之说者仍不乏其人,如宋儒陈公辅(字国佐,1076—1141)称:“《春秋》正名分,定褒贬,俾乱臣贼子惧”。[5][元]脱脱等:《宋史·陈公辅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9247 页。戴溪(字肖望,1141—1215)解昭公二十年经“盗杀卫侯之兄絷”时亦曰:“夫《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者,畏其名也。”[6]戴溪:《春秋讲义》卷4 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55 册,150 页。这一观念后世亦有申之者,如《(万历)滁阳志·旧滁志叙》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春秋》,史之祖也,其操纵予夺,无少假贷。”[7][明]戴瑞卿,李之茂纂修:《(万历)滁阳志》,万历四十二年刊本。
四、结 语
综上所述,自孟子提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命题以来,由汉至唐,在《春秋》学中,随着学术思潮的演进,对这一命题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经学命题向史学命题转换的过程。董仲舒虽然未曾针对这一命题提出诠释,但其《春秋》学中却内蕴着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其说可概括为:借褒贬以立法,由立法以惧贼。这一理解在司马迁那里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展现。为了解决孔子以匹夫身份进行褒贬予夺之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提出孔子为素王,作《春秋》代汉立法的解决方案。东汉时期,受到古文学影响的赵岐不再强调褒贬的立法功能,从而将董仲舒以来的褒贬立法以惧贼说转换为褒贬惧贼说。晋唐《春秋》学亦承继古文学理念,反对孔子为素王,主张从历史批判的角度理解褒贬,进一步将上述命题从经学论述转换为史学命题,并对晋唐史学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