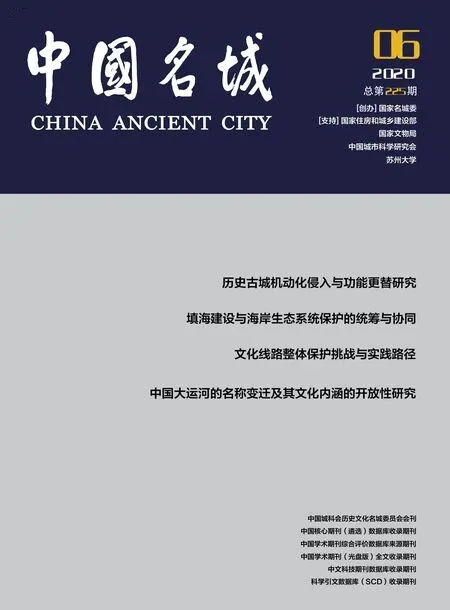中国大运河的名称变迁及其文化内涵的开放性研究*
2020-11-29田德新吴文非
田德新 吴文非
引言
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出现,一是为了成功申遗,二是为了有效地将海陆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1]。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着“大运河保护工作呈现出共识化、专业化、系统化和战略化的发展趋势”[2]。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其科技贡献和文化成就。2017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批示[3],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大运河流动文化价值本身的高度重视与将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殷切期望。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4]。《规划纲要》重申,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3200公里,具有2500年的历史,其规划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35座城市的43段河道及其缓冲区和132个遗产点及其景观区或旅游区。在《规划纲要》的十个章节里,第三、四和七章分别是“深入挖掘和丰富文化内涵”“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足以显示上述两办在顶层设计上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高度重视,对大运河文化“挖掘”“丰富”“强化”与“推动”的坚定信念和决策力度。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运河有关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性及其突出普遍价值等方面所制定的相关标准和要求,两办在《规划纲要》中将上述8省35市43段河道及其缓冲区和132个遗产点及其景观区,确定为大运河规划范围。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此顶层规划,客观、科学、具体、实际,无可厚非。但是,自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过的运河及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吴欣认为,“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5]由于其人工开挖的水利属性,国家航运命脉的制度属性以及连接华南华北的社会属性,大运河文化的特殊内涵包括技术文化、制度文化与社会文化三大类。正如张廷皓所言,大运河遗产至少有三种形态:一是仍然延续初始航运功能的在用河段,二是尚保留完整的断流河段,三是淹埋或半淹埋于地下的大运河遗址。如果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只考虑具有客观性的物质文化遗产,那么大运河三分之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会永远被尘封地下,难见天日,失去其应有的光彩[6]。显然,从学术探索的角度上讲,对大运河无与伦比的科技成就、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及现实功效和长远意义的科学研究不应该设置任何“规划范围”。为此,本文以张廷皓2015年提出的大运河遗产的三种形态和吴欣2018年提出的大运河文化的三类特殊内涵为理论指导框架,以古今文献和考古史料为论据,通过梳理大运河整体名称与其中汴河段名称一点一面的历史变迁,论证大运河文化内涵及其研究的开放性。
1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迁与演变
一般认为,运河是指人工开挖并具有水运功能的航道。运河有人工开挖、自然水道拓宽加深和人工开挖的水道与河流湖泊串联而形成的三种河道[7]。“运河”一词出现在宋代,而“大运河”一词出现在南宋。唐代以前,黄河流域开挖的运河多被称为“沟”或“渠”,淮河流域的称作“沟”或“渎”,而长江流域的称作“溪”“浦”或“渎”。起初,“漕”泛指水路运输,可上溯至西周初年,如:“是故土多发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务方输”[8]。另外,《汉书·赵充国传》云:“漕下,以水运木而下也”[9]。当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在中国建立后,“漕”便成为国家组织从水路运粮的专用名词。《史记·秦本纪》记载:“晋旱,来请粟。……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10]。晋国遭受旱灾,请求秦国借粮。秦国最终答应,并通过漕船和车马,将粮食运送给对方。
在中国的历史上,大运河曾指隋唐大运河,元代以后专指京杭大运河。2006年,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仍沿用京杭大运河。为了推动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进程,2008年才有了“中国大运河”的概念,仅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沿线的33座城市。2009年,浙东运河,又称江南运河,及其沿线的绍兴和宁波也被列入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城市联盟。从此,“中国大运河”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得到确定,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将海、陆丝绸之路有机地连结在一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据《史记·河渠书》记载:“于楚,西方则通渠汗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10]。可见,当时已有楚运河、吴运河与齐运河。公元前591年,在楚相孙书敖主持下,楚国人开凿了连接汉水和云梦之间的杨水运河。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十年),楚国又兴建了连接鸿沟与江淮的运河,上述两条运河即为楚运河。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开凿沟通太湖和固城湖的胥河(胥溪)。此外,吴国人还兴建了胥浦、子胥渎、荷水以及众所周知的邗沟,它们一起构成了吴运河。公元前486年(鲁哀公九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沟通江、淮,即接通东北方向的射阳湖与西北方向的淮河。大约在公元前718年,齐国开凿了淄济运河,加强了齐国与中原各国的联系。上述运河的修建多出于军事和农业灌溉的目的。因此,在其完成了短暂的实用目的后,大多“缺乏细致的维护与管理”[11]。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220年),由于京城供给、边疆军需和农业灌溉的迫切需求,秦朝开凿了沟通湘水与漓水的灵渠,也间接地联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越岭有闸”运河。秦国还开凿了郑国渠和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但造就了秦时关中和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还开启了中国的漕运制度。两汉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建了白渠、六辅渠、龙首渠、阳渠以及褒斜水道和三门峡水利工程。当时的漕运与河运、海运同等重要,其维护和管理直接隶属中央政府,所需费用基本可以保障。而东汉末年,由于战乱,“秦汉漕渠多悉数毁灭,国家漕运不通”。然而,曹操还是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淮阳渠、百尺渠、白马渠、鲁口渠、成国渠及车厢渠,既扩大了农业灌溉水源,又加强了各地之间的物资交流,还在一定程度上为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11]。
隋唐两宋(公元581-1279年)是运河的发展时期,先后开凿了联通长安、洛阳、杭州及涿郡(今北京)的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及江南河,并在沿河两岸设置了一系列漕仓。运河在漕粮运输、军队与辎重运输、商业运输以及运河区域的交流与沟通等方面的功能均已达到中国历史的高峰,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体系。因此,其维护和管理运河的模式亦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两宋时期(公元960-1279年)的中国还未能全国统一。因此,北宋的运河主要集中在都城开封附近,包括汴河、惠民河、广济河及金水河。南宋的运河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和安徽,在维护使用淮南、浙西运河的同时,全力整治了浙东运河,使其发挥了“国之命脉”的作用。当时的中央政府不但重视运河的泥沙疏浚、堤坝加固、闸座建造,而且设立了主管漕运与河道的发运司、转运司、排岸司及催纲司等机构,监督全国漕粮的运输与河道的维护。宋朝人通过建造一高一低两条水道,在高低水道之间修建多道闸门的复闸,在若干地段修筑弯道拉长距离从而降低爬坡比例(即“三弯顶一闸”),成功地解决了运河“爬坡”“过河”及“堵船”的运河建造与管理难题[12]。
元明清时期(公元1271-1912年)是中国运河发展的鼎盛时期。元代开凿了济州河、会通河与通惠河,取直了连接北京与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但是,元代的运河分水口设置不合理,导致运河淤塞,朝廷只好重开海运。明朝先定都南京,后迁都北京,均迫切需求南方漕粮的供给,因而通过疏浚会通河、开挖清江浦、建造旺分水利枢纽,重开漕运。明朝的漕运先后采取了支运、兑运及长运三种方式,将漕粮先集中到指定漕仓,然后由官军统一押运入京。形成定制的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大半壁江山”[13]。为了加强漕运管理,明朝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设漕运总督和漕运府总兵官,一同管理漕政。同样,漕运在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占有三分之二的重要地位。因此,清政府每年花费1000万两白银,用于大运河河道治理,先后开凿了中运河、治理了青口水利枢纽、疏浚了河道,以维持漕运畅通。此外,朝廷还在大运河沿线设置了巡漕御史、镇道将领及漕运枢纽总兵官,以稽查各自管辖的河段与督促槽船有序航运。漕运到了晚清逐渐趋于衰败,加上清末黄河改道,火车轮船最终取代漕运,1901年,清政府遂令废除漕运。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疏浚“河道淤沙”与“黄河倒灌”的难题,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在江苏淮安清口的黄淮交汇处,建造了古代最为复杂的水利枢纽工程。其基本原理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而其中遏制倒灌的创造发明是“挑水木龙”,高效清除河底泥沙的利器是“混江龙”[12]。
民国时期(1912-1949)由于忙于战乱,对大运河只进行了局部修整,无暇顾及诸如水源缺乏和黄河侵害等根本性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运河得到了全面整治。从1958年到70年代末,交通部会同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集中对苏北段运河、鲁运河与南运河进行疏浚整修,实现渠道化通航,并改善了排洪和灌溉条件。从1980年到申遗成功之前,国家依照二级航道标准对苏北运河和江南运河进行了续建,兴建了一系列船闸,使500-700吨级船组和50-100吨级船组拖船队可以分别航行在苏北运河段和江南运河。因此,大运河的部分河段得到疏通与拓宽,部分航道截弯取直,另辟新线,同时兴建了一批新型的水利工程[2]。
2 汴河名称的历史变迁及其文化内涵的拓展
上文探讨了大运河整体名称的历史变迁,下文选取大运河的一段,汴河及其名称的历史变迁,进一步展示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选择汴河,有三个主要缘由。第一,汴河历史悠久。《水经注》卷五记载,汴河的前身乃为大禹治水时所开就的蒗荡渠。北宋后,南宋与金对峙,汴河由于缺乏统一的维护与修葺,开始断流,但金代后期,曾对汴河部分地段进行疏通。元代黄河改道,河患频繁,汴河几乎消失。明代中期,因排开封城内积水,曾于开封城门外疏通汴河旧渠一万余丈至陈留。清朝崇祯15年(1642),开封又遭黄河水淹,汴河自此消失到地表以下。[14]实际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蒗荡渠、阴沟、大沟、鸿沟、汴渠、汴水等,皆指同一条渠。第二,汴河的历史功绩巨大。汴河,又称通济渠或古运河,是隋炀帝在先秦鸿沟、东汉汴渠的基础上兴修的运河,因其主干道紧邻汴州(今开封),故名汴水、汴河。它西起洛阳西苑,终点是扬子渡口(在今江苏扬州南扬子桥附近),沟通了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成为隋、唐时期南北运输漕粮的主要通道。因此,有诗云:“汴河通,开封兴;汴河废,开封衰”,而当时的开封“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可以说,从夏代到唐宋,特别是作为隋唐大运河最长的中段,汴河一直是最重要的灌溉水源和运输航道。[15]最后,汴河开发的现实意义非凡。由于其悠久的历史价值、重大的历史功绩,以及得天独厚地理位置,虽然汴河沉没地下,但是它仍然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著名河流,因此,河南省和开封市计划合力恢复汴河历史风貌,并尽早通航,要使其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中的一个亮点。
历史上, 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相传为大禹治理荥泽水患的分水沟渠,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叫邲水、汳水、大沟、鸿沟;西汉曰蒗荡渠、莨菪渠;东汉(公元25-220年)称汴水、汴渠;隋唐宋(公元581-1279)称为通济渠、汴渠、汴河、汴水等;元明清(公元1271-1912年)叫贾鲁河[16]。所谓鸿沟,是隋朝通济渠的雏形,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大运河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经注疏·河水五》记载:“大禹塞荥泽,开之以通淮、泗。”另记载:“禹又于荥泽分大河为阴沟,引注东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仪县西北,复分为二渠:一渠元经阳武县中牟台下为官渡水;一渠始皇梳凿一灌魏郡,谓之鸿沟,莨菪渠自荥阳五出池口来注之。其鸿沟即出河之沟,亦曰莨菪渠”[15]。由此可知,当年大禹治水通九州,就包括位于荥阳县北的黄河河段,起初名为浪荡渠,又称莨菪渠,二者均为“鸿沟”的别称。
春秋时期的鸿沟被称为“邲水”或“汴水”。《水经注疏·济水一》云:“济水于此,又兼邲目”[17]。《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之战,楚军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其中的“邲” 读音为“汴”,因此“邲水”就是“汴水”。其中的“邲水”和“汴水”都是鸿沟的别称[18]。战国时期,据《史记·苏秦传》记载:“大王之地,南有鸿沟”。《史记·河渠书七》记载:“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且“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记,然莫足数也。”[10]显然,鸿沟从荥口引黄河之水,向南连接淮河与邗沟,与长江贯通;向北通黄河,与渭水和洛河相连;向东通济水,与泗水相接。鸿沟使鸿沟水系、黄河两岸及长江相关区域的宋、郑、陈、蔡、曹、卫等国实现交通往来,为日后的连横抗秦,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秦国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秦国大将王贲因久攻大梁不下,于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引河沟之水而灌大梁”,不但赢得了胜利,而且使大梁成为废墟[16]。其中的河沟即鸿沟,大梁即当年魏国的都城(今河南开封)。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220年),秦国利用鸿沟,进行南粮北运,并在鸿沟与黄河分流处兴建了庞大的敖仓,用作转运站,将众多物资经此或转运关中,供给中央财政,或北运边塞,供应军需。鸿沟在两汉时期被称为蒗荡渠、汳渠、俊义渠。隋唐时期,运河体系得到高度的发展。为了发展漕运,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隋朝政府建立县制于黄河之阴,汴水之阳,以加强对漕运的管理。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19]。通济渠的开通,联通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成为隋朝运河的主体部分。唐朝大运河基本沿袭隋朝,政府对于大运河的管理主要是维护航道、大规模疏浚河道及改建部分河段。如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命令“检行郑州河口斗门”,并“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开旧河口”[20]。
两宋时期(公元76-1279年),汴河作为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国家安全的系带和国家存亡的生命线。天禧三年(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高达八百万石,为北宋漕运的最高纪录。《宋史·食货志上三》记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21]。其中的汴河,即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此,宋朝政府对汴河的维护、疏浚和保养,采用了如下的积极措施:(1)控制汴口,调节流量;(2)清理淤沙,保证水深;(3)种植柳树,加固堤防;(4)设置水柜,调节水量。其效果显著,正如《宋史·河渠志三》所描写的:“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奚由此路而进”[21]。可见汴河已成当时全国的交通大动脉,在北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明清时期(公元1271-1912年),黄河屡次泛滥成灾,汴河被淹没,漕运功能几乎丧失殆尽。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临危受命,出任元朝工部尚书和总治河防使,运用沉船、疏、塞并举的方法堵住决口,运用疏浚、拓宽和连接等方法恢复了战国鸿沟水系、隋唐通济渠、宋代汴河的水运功能,从而造就了运河流域新的航运交通和商业繁荣。为纪念其功绩,人们将当年的汴河更名为贾鲁河,一直沿用至明清两代。贾鲁河在明清时期基本维持现状,继续发挥着沟通南北漕运和沿途两岸文化交流的作用。明代初年,贾鲁河上新建了一座三孔拱桥,名叫惠济桥。有石碑记载:“桥下之渠,本贾鲁河故道,当时自南向北,与大河通,居人颇获舟楫之利”[22:68]。而《顺治荥泽县志》对惠济桥所处的郑州荥泽县惠济镇也有如下的记载:“附居者烟火千家,往来者贸迁万种。民未病涉,诚一邑之雄镇也”[23]。由此可见,汴河在元明清的不同时期,虽经灭顶磨难,但在像贾鲁等政府官员的带领下,广大劳动人民对汴河水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疏浚、拓建、维修及保养,从而保障了运河漕运的延续、运河流域商贸与文化交流的繁荣以及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3 大运河相关考古发现及其文化内涵的扩充
首先,大运河的价值,对世界遗产委员会来说,首先是其起源古老、规模巨大并随千百年来的环境变化而不断地适应环境的特性。以隋唐大运河为例,人们熟悉的是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所开凿的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实际上,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3年(开皇四年)即“命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馀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关内赖之。诸州水旱凶饥之处,亦便开仓赈给……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24]。考古发现,在统领广通渠开凿工程的官员中,除了著名建筑设计师宇文恺任总指挥以外,还有副总指挥于仲文和元寿、总管郭衍以及兵部尚书苏孝慈和郭均。《隋郭均墓志》碑文记载,郭均曾于开皇四年“领开漕渠总监”,该墓碑作为研究隋朝大运河的重要考古物证,现存于陕西省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馆[25]。广通渠西起长安,东至潼关,全长300多里,基本沿西汉运河古道开凿,仅用了三个月便告竣工,并在潼关建造广通仓,以储备皇粮。广通渠的疏通使关中地区的运输条件大为改观,既缓解了都城区域的缺粮问题,又为日后饥荒时赈灾做好了准备。其灌溉功能和绿茵庇护等好处为该人工运河赢得了“富民渠”的美誉。最重要的是它为后世开通大运河、管理维护大运河、设立国家漕运与漕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大运河河道既是大运河遗产的本体,也是其主体。但是,大运河的河道本体历经沧桑,在历史上发生过频繁的变迁。只有考古证据才能解决类似这样“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26]。World Heritage Center of the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对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定义如下:
“真实性”指文化遗产具有原始的、原创的和非复制的特性,体现在外形和设计、材料和材质、用途和功能、位置和环境、传统与技术以及精神和感觉诸多方面。“完整性”指文化和自然遗产符合以下特征:(1)包括所有具备普遍价值的必要因素;(2)面积足够大,能够完整体现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3)关注发展的负面影响和/或缺乏维护状况[2]。
关于大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旗下的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 国际遗产遗址理事会)在其咨询机构评估报告中指出,在与其他五条世界遗产运河比较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规模上,任何其他人工水道都与大运河无法比拟。
第二,大运河上的粮食漕运政府垄断体系独一无二,在其运作的历史长河中,它对伟大农业帝国中国保持统一,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
第三,大运河是一个标杆,稳居工业革命前水利工程技术的制高点。它也是人类文明各个阶段推广人工河道技术的训练场。
最后,大运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而欧洲的水利工程全部都是现、当代的产物[28]。
然而,在其对大运河大加赞赏之余,ICOMOS认为,中国一方面以大运河久远的起源为荣,另一方面却在大运河的原来河床进行了明显的疏浚、加深和拓宽,或在有些大运河沿线临近的地方重修河道。这无疑让专家对古老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产生疑虑。另外,在上千公里的大运河景观带上,出现了有碍大运河遗产、景观及缓冲区保护的住房和基础设施项目,而这与联合国遗产“真实性”的标准有所相左。至于大运河的“完整性”,ICOMOS指出,连续性是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根本特性,但是,中国提供的考古发现很难判断“它们对大运河完整性,特别是在技术操作方面的认可有什么贡献”,还有“大运河在其历史上的多次变道对其航运路线的连续性确认也有所不利”[26]。研究发现,大运河在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范围、起止点、关键地点的改道、重要节点的工程遗存等要素中,有相当一部分很难具体落实”[26]。值得庆幸的是,面对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大运河,我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空间信息技术,可以帮助考古工作者进行相关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
最后,从大运河遗产的构成及其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上看,无论是大运河遗产,还是大运河文化,绝非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方面所能涵盖。大运河是“超时空的超大型遗址,是中华版图上的不可移动文物,是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自然遗产、运河遗产于一体的复合遗产”[28]。其遗产构成可包括运河工程遗产和由运河工程派生衍生的遗产两大类。姜师立则认为,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运河城市的兴起、文学艺术的融合、不同文化背景的参与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思想领域的合成[29]。因此,大运河文化的内涵,既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要素,也同时包括思想领域的精神观念要素。
4 结语
综上所述,大运河整体和点段汴河名称的历史变迁,涵盖了张廷皓于2015年提出的有关大运河遗产的三种形态,即:(1) 仍然延续初始航运功能的在用河段,如浙东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里运河和江南运河;(2)尚保留完整的断流河段,如京杭大运河在天津河和台儿庄地段的北运河、南运河、鲁南运河及中运河;(3)淹埋或半淹埋于地下的大运河遗址,如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通惠河以及隋唐以前包括邗沟、灵渠和汴河等。当然,从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迁过程,也可以清晰地发现吴欣2018年提出的大运河文化在技术、制度与社会三大层面所发生的巨变。
首先,在技术文化层面,从秦朝建造“越岭有闸”运河,到宋朝解决运河“爬坡”“过河”及“堵船”的运河建造与管理难题,都已经迎刃而解。其中,令国人自豪的重要水利枢纽和关键技术工程的代表项目包括:大运河的河道工程,北京人工河湖水系水源工程、通惠河梯级船闸工程,山东南旺运河分水枢纽工程、中运河规避黄河之险工程,江苏淮安清口运河渡黄的运口枢纽工程、淮安高家堰河洪泽湖大堤以及清口的“蓄清刷黄”枢纽工程、宿迁淮安段“束水攻沙”和治黄保运的堤防系统工程等。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所处的区段往往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节点,均按照不同地点的特性和需求,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因而具有极高的技术价值。
其次, 在制度文化层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 大运河起初的名称如“沟”“渠”“溪”“浦”“渎”逐渐被“漕渠”“漕河”或“官河”的称谓所代替。而这些称谓的更替标志着已经成为国家制度体系的漕运,代替了或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大运河曾经发挥过的个体短途航运、农田灌溉、土壤改良及防洪排涝等功能。大运河已成为“世界唯一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以达到稳定政权、维护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水运工程体系”[29]。
最后,在社会文化的层面,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浙东大运河的大运河贯穿中国东西南北,当今又连通海、陆丝绸之路。可以说随着大运河长度的延长和区域范围的增加,漕运更加规范和繁荣,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入,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来各个区域的行政区划、运河沿岸的城市布局,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社会从最早游牧文明或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迈进的步伐。因此,有关大运河的科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任何“规划范围”,因为动态的大运河文化及其内涵具有不断演变、拓展和扩充的开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