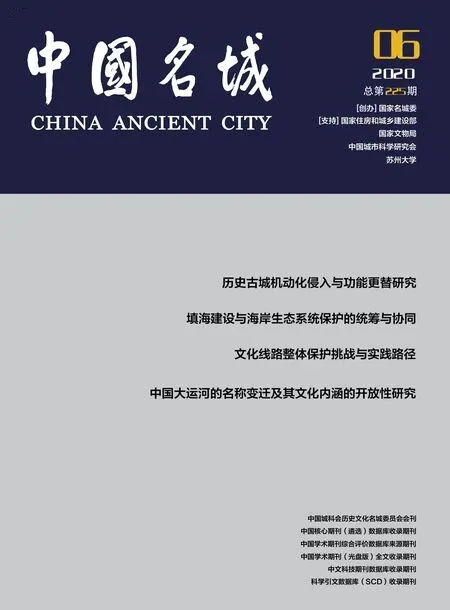“文学之都”的历史源流与建设路径研究*
——以南京为例
2020-11-29朱逸宁苏晓静
朱逸宁 苏晓静
联合国教科文于2004年10月发起了“创意城市网络”(The Creative Cities Network),加入其中的城市将被分别授予7种称号,即“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民间艺术之都”和“烹饪美食之都”。[1]这个项目旨在促进全球各城市的文化交流,让各城市在彼此交流文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世界各国的城市文化多样性,为城市文化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多种渠道和空间。
为了在新时期推进城市文化建设,从2010年以来,我国已经有不少城市申请加入了“创意城市网络”:北京、上海、深圳、武汉——“设计之都”;杭州、苏州、景德镇——“民间艺术之都”;哈尔滨——“音乐之都”;成都、顺德、澳门、扬州——“烹饪美食之都”;长沙——“媒体艺术之都”等。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学大国中,包括南京在内,和文学结缘的城市并不少,“文学之都”的竞争也彰显了我国城市文化的丰厚底蕴。从这个趋势来看,南京入选“文学之都”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的。故此,有必要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城市文化历史中“文学基因”,同时参考借鉴国外“文学之都”的经验,以期为南京这座世界“文学之都”的建设理清思路。
1 中国城市文化史中的“文学基因”
对于中国的城市文化而言,文学早已渗透进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结构之中。无论是文学初兴的时代,还是文学鼎盛的时期,城市从来就是文学表现的对象之一,而文学也是城市精神文化建构的重要力量。
1.1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与文化
早在先秦时期,城市和文学之间就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中的《雅》曾生动记载了周代的城市生活,如《大雅》中描述了文王、武王、成王规划和兴建丰镐两城、东都洛邑,用文学性的语言展示了商末周初人们建城立都的历史。汉代到六朝,文学家通过赋这一文体刻画了当时的大城市,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等,极尽夸张铺叙之能事,反映出当时一些大城市的繁盛景象[2]。一些志人小说如《世说新语》也反映了城市生活。城市文学进入发轫期,较为完整的城市形象和生活形态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进入唐宋时期,长安、洛阳、扬州、开封、杭州等城市,屡屡成为诗人词人笔下的意象,仅仅是描写长安的诗句就数不胜数,著名的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这些诗人笔下的名句,和极盛期的中国古代文化一道,把城市文学推向成熟。尽管今天这些城市已不再具有旧都的风貌和地位,但是,文学意象中的“帝都长安”“东京繁华”等仍留存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同时,城市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各种文学形态的成熟,包括诗歌、辞赋在内的文体成为城市文学与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到了明清时期,城市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不仅城市成为文学创作和消费的中心,文学也使城市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很多作品不再只是描述城市生活或以城市作为背景,而是通过人物和情节的渗透,凝结出一种更具世俗气息的市民生活意象,从而使城市文学摆脱了政治伦理束缚,进入真正的自觉时期。像《儒林外史》,便通过人物杜慎卿之口道出南京的六朝烟水气,高度凝练了南京的城市气质。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近古时期中国很多城市的高度繁荣景象,还揭示出当时城市的显著特征,如市民阶层的壮大、消费文化的活跃、审美趣味的变化等,均可在城市文学中窥见一斑。同时,文学的繁荣又带动了图书出版业和印刷业等文化经济的发展,包括南京、苏州、常熟、无锡在内的城市,相继成为文学图书中心。这就使得城市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体系逐渐完善起来。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已经融进了城市文化精神体系中,而明清的江南地区也形成了一种小说文化[3],小说成为江南城市文化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影响了江南社会。
在中国,古代城市和文学之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良性互动:城市的发展推动了某种文学形态的成熟,而文学则促使古代城市文化和精神体系逐步完善。中国人心中的城市意象很多是从文学描述中形成的,如南京的六朝烟水气、长安的帝都气象、杭州的钱塘盛景等。即使千百年后,城市的物质形态早已发生了巨变,甚至一些城市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其精神文化的内核仍然可以通过文学的传承得以保留或延续。因此,文学就是流淌在中国古代城市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1.2 中国近现代的城市文学与文化
到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和城市的精神连接依旧紧密。文学不仅可以反映城市文化,参与建构城市精神,还可以批判和反思城市文明,而现代城市也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面貌。如京派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讴歌淳朴和原始的人性,“一个重要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近代中国特别是都市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人性异化现象的憎恶和不满”[4]。这些城市文学作家聚集于一座城市进行创作,进而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的作品或以城市为背景,聚焦于城市中的人和生活,或对现代的城市文化进行思考。如中国近代最具现代化特征的大城市上海,其作为“大上海”的城市意象建构离不开文学作品。较为典型的如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及张爱玲等人的作品。他们用文学的笔法形象地描绘了上海的城市生活以及现代城市化进程。人们心中“大上海”意象的形成,可以说正是因为文学作品把分散和零碎的城市记忆凝结起来的成果。在这其中,农业文明瓦解带来的失落感和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时所产生的迷茫感相互交融,构成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城市文学。在此基础上,当代又有池莉、方方、孙甘露、刘恒、毕飞宇、叶兆言等作家,把笔触伸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绘制出中国当代城市的生活画卷。新时期,城市文学的形态并不限于某一种文学形态,包括影视文学在内的多元艺术形式构成了新型的中国城市文学资源体系。
在千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的文学资源,这些资源和城市文化相互融合,是今天建构“文学之都”的基础。这些文学资源的累积向我们揭示出:“文学之都”的源流正是这些文学传统,其中不仅包含文学资源的生产、消费和传播,更是因文学资源自身的特征决定了其“活态”属性。
1.3 文学资源的定义与“文学之都”
从归属上看,文学资源应从属于文化资源这个大范畴:“文化资源是指作为人类精神生产与文化实践对象的生产资料,可分为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三类: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资源(主要是特殊的地质、地貌或水系)、生态系统资源(如可进行文化开发的土地、森林公园等)、土特产品资源、古建筑资源(如老街、老房子等)及它们的具体开发和利用状况;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以其特有的传统农业生活生产方式与田园风光景观满足都市人的农村生活体验与需要)、工业文化资源(以其特有的现代工业系统与景观满足都市人的工业生活体验与需要)、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及它们的具体开发和利用状况;审美文化资源主要是各种世代相承、有地区文化特色、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游戏竞技、民间艺术等。”[5]从这个定义来看,文学资源实际上综合了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三个门类,如书籍文本、作家故居、阅读和出版场所等属于物质文化资源;一个地区的文学传统和历史等属于社会文化资源;各种文学作品内容与形态汇聚则属于审美文化资源,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文学资源。它不仅形态多样,其存在方式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文学资源的呈现方式显示出它是一种真正“活态”的资源。中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和灿若群星的文学成果,之所以长期以来并没有哪座城市被冠以“文学之都”的名号,是因为这些文学资源早已和城市文化精神深度融合在了一起。但是,现代城市文化建设,却需要每座城市去彰显个性,打出自己的“文化名片”,那么,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中国这个文学大国的“文学之都”便呼之欲出了。
当前,中国的城市文化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时期,文学资源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中显得更为重要。现代化的城市在基本解决了人们生存的需要以后,精神文化的需求便凸显出来。人们通过文学,不仅可以把个体的城市记忆融汇凝结成一种群体意识,更可以建构起城市精神的共同体。对于城市而言,如果能有条件去申报和建构“文学之都”,这本身就说明它的发展历程和城市精神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基因,而从历史来看,我们这个国家就有不少城市具备这些条件,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上海等,因此,中国城市成功申报“文学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2 国外“文学之都”发展的经验
世界上已经申报并获通过的“文学之都”有爱丁堡、墨尔本、雷克雅未克等20多座城市。作为“文学之都”,这些城市在文学资源的开放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供我国借鉴。
2.1 国外“文学之都”的基本优势
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优势,这是基本的硬性条件;二是能长期有效地开发和保护文学资源,而且这种意识是深刻于市民内心的,融汇于其城市精神体系中;三是能把这种意识与精神向外辐射,并拥有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在这些特征基础上形成“文学资本”。这些“文学之都”无一例外均为本国文学重镇,和所在国家的文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各国的城市具体文学资源固然有差异,但其中也有不少共性可以供我们借鉴。
以英国的“文学之都”爱丁堡为例。首先,爱丁堡为英国文学贡献了众多作家和经典名著,如罗伯特·彭斯、沃尔特·司各特以及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等英国文学史巨匠,《艾凡赫》《金银岛》等经典作品均与这座城市直接或间接有关。大量的作品构成了爱丁堡作为“文学之都”的必备要素。其次,在此基础上,爱丁堡充分利用了城市的建筑和设施展现文学印记。在爱丁堡城中可见到很多文学家的雕塑和纪念碑,这些视觉景观可以直接引发人们关注其中的文学内涵。比如在新城夏洛特广场,有《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人物雕像,这是为了纪念小说作者——出生于爱丁堡的作家柯南·道尔。随着文学和影视的传播,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传遍全世界,这里便成为“福尔摩斯迷”的一处瞻仰圣地。类似的文学名人纪念碑和作家故居在爱丁堡均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并且通过精心布展供人参观和瞻仰,这就加深了人们对爱丁堡文学历史的了解。同时,爱丁堡拥有50多家出版社,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出版业中心,加之各类书店遍布全城,文学出版业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从创作到出版再到消费,爱丁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学产业链。爱丁堡也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罗琳的家乡,她长期居住于此,并于此中创作。由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影响,爱丁堡更加受到书迷的青睐,成为很多读者向往的地方,由于处处有文学元素,爱丁堡变成了文学之城。再次,爱丁堡还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使得文学不仅是一种靠书本和文字来传承的文化,更是人们进行精神交流的、面对面的习俗和节庆。如各种艺术节、图书节、朗诵会等。这些活动促使文学在爱丁堡成为一种“活态”的城市文化。爱丁堡的国际图书节,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作家、读者、研究者和评论家、出版商和图书公司等聚集在一起以及进行交流,这有利于文学传播,也推动了城市文化的相互交流。爱丁堡在申请“文学之都”的时候认为:爱丁堡是一座建立在文学上的城市。之所以这座城市会这样形容自身,根源就在其无处不在的文学元素。
2.2 “文化资本”与“文学之都”
从这些国家“文学之都”的情况看,普遍具有一些共性:墨尔本,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出版业发祥地,全国三分之一的作家也在此孕育成长。都柏林、雷克雅未克等“文学之都”当选城市具有类似的特点。这些城市和文学形成了良性互动,既保留了城市文学的历史印记,又延续了文学创作和传播,使得文学生产和消费成为一种“活态”进程,成为“文化资本”,这才是“文学之都”的本质意义。
第一,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具有的多重属性和多元特征,决定了它是城市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文学之都”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他们把文学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这一过程和结果。从这里出发,这些城市树立起了属于自身的独有的城市形象。正如张鸿雁所说:“‘城市文化资本’建构就是要整合城市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资源,通过符号化的‘文化再生产’,使‘符号’成为城市社会市民主体认同的认加的要素,并使之成为‘城市文化资本’的组成部分。‘城市文化资本’建构还要对城市所有的可传达信息的载体和媒体进行再开发、再建设,其中也包括对以往落后的文化与信息进行筛选,当然更要对整个城向信息化符号景观进行艺术再塑造,把城市当作艺术品来打造。”[6]也就是说,文学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是一个资源整合的过程,包括文学资源在内的各种要素,都需要经过再创造。比如爱丁堡就利用夏洛特广场举办国际图书节,文学已经成为爱丁堡城市的重要产业,可以不断进行再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基于文学资源的“文学之都”,不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动城市内部的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使之转化成文化资本,而且可以形成文化产业,使文化资本转变成城市产业可持续的“发动机”。
第二,文学作为城市文化资本,意味着它是可以人为设计和运作的,且应当根据城市自身的特点来规划。仔细考察国外这些“文学之都”的城市文化建设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经历了精心设计和规划的过程。在文学生产、消费、传播等环节,有些城市的规划设计可圈可点,充分彰显了自身文化的个性。比如爱丁堡和墨尔本,作家较多,出版业发达,又拥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它们主要便是把文学生产(创作和出版)作为自己的特色着重打造。爱荷华城人口数量不多,规模有限,于是它以原创性写作和阅读为中心,把社区文化作为特色,加强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从而成为一座小而精致的“文学之都”,走出了一条属于小城镇的“文学之路”。
总体来说,国外的“文学之都”建设经验告诉我们:把时代累积的文学资源转化为文学资本,这是“文学之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3 南京建设“文学之都”的优势与对策
3.1 作为“文学之都”的优势与特点
“文学之都”不仅是一个荣誉性的称号,而且可凸显这座城市文学的总体发展状况,文学在城市发展进程的作用,以及文学在城市文化中的地位等。
南京作为“文学之都”,从文学创作、消费与传播以及环境这几个方面来说,其城市文学的优势和特点都是十分显著的。
首先,南京文学创作成果丰硕。就创作来说,与南京有关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三类:在南京诞生的文学作品,以南京作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与南京有高度关联的文学作品。比较早的是左思的《吴都赋》,尽管这篇作品中的南京只是割据政权的都城,但是作者洋洋洒洒写出了南京初为都城的盛况,也是南京作为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大都市的最佳写照。《世说新语》中的许多故事背景就是南京;《文心雕龙》创作于南京的定林寺;《文选》也诞生于南京。由于南京是六朝都会,从东吴到南陈均建都于此,六朝文学的核心地带无疑就在南京,所谓“六朝古都烟水气”正是由此形成的。唐代的金陵虽不是都城,但是依旧文风鼎盛,不少诗人思古抒怀时,金陵时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据戴伟华统计:唐代和五代加在一起,咏金陵诗有354首[7]。这些作品多以六朝南京文化为核心,像李白的“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更是千古传诵的佳句。南唐的都城也在南京,南唐词的创作与南京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诗人的创作,更是形成了五代时期一种独特的城市审美文化精神。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朝初年,南京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更是成为江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中心之一。明清时期江南城市文化的成熟与繁荣,更是促进南京成为明清时期实质上的“文学都会”。小说《儒林外史》对当时南京的城市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按照韩春平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二是对明朝留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慕;三是创作主体的个人记忆。”[8]p.288
其次,南京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比如明清时期,南京不仅是江南地区的文教中心,还是小说等通俗文学的重要创作基地。据学者考证,不仅神魔小说流派开创于此,经过南京书坊的刊刻,世德堂本《西游记》广为流传,还诞生了《英烈传》《儒林外史》等一大批小说,《三言》《二拍》等著名的小说也是在南京选稿和编辑的。南京为明清文学传播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这些作品有的虽不是诞生于南京,但却在南京大量刊刻,方为人熟知。加之金陵周氏醉耕堂、李渔芥子园等大量刊刻印行,以及众多读者的购买、传阅和点评,通俗小说的地位得到了提升[8]p.209。可以说,在明清小说的发展史上,南京这座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它成为当时的“小说之城”。我们后人所熟知的文学大家,如施耐庵、冯梦龙、罗贯中、兰陵笑笑生等人的作品,均在这座城市的书坊中被大量刻印,此后得到了广泛流传。由于书坊实际上是兼具出版与销售功能的商业实体。由此,城市消费文化的活跃,也带动了市民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再次,南京的城市文化环境是非常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南京的文学活动一直很活跃,这不仅是因为南京有一定数量的作家,比较著名的如薛冰、苏童、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赵本夫、朱苏进、韩东、鲁羊、黄蓓佳、储福金、葛亮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南京和江苏省内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在全国范围内也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从年龄层次看,有出生于20世纪50、60以及70年代以后的;从籍贯看,既有南京本地出生的(如叶兆言和韩东),更多的原籍外地、在南京生根发展的。这说明,进入现代以后的南京,它的文学气质依旧是自上而下融合于整个城市精神之中的,因此,它才催生出众多的作家和作品,从而在现代文学的发展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南京城市的文化建设规划设计中,文学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对于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的阅读活动,是十分重视的。这是南京申报“文学之都”的重要优势因素。南京作家、作品、出版社、书店、阅读场所、文学专业等可以量化的指标在全国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有各类读书团体和组织不下三百个,同时,南京还拥有大量各级各类图书馆和书店,“全民阅读”已经初步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南京已经具备了相对来说良性的文学消费环境,从学校到企业,从政府到媒体,鼓励和引导文学阅读已经蔚然成风,无论是读书节,还是讲座和交流论坛等,长年不断。同时在大学中有相当数量的中文专业,不少学者致力于文学批评、研究和推广。这些不仅有利于文学活动的开展,并且已经初步建构起了南京文学的可持续发展环境。
3.2 建设“文学之都”的策略和措施
基于这些优势,南京在建设“文学之都”的过程中,可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在具体建构“文学之都”过程中,南京可以从文学活动、实体景观、文创开发这三个方面着手,使得“文学之都”既能落到实处,又能永续发展。
首先,“文学之都”的核心应是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文学活动的持续开展是必不可少的。南京的人文环境适合文学创作与作家发展。这个传统自古至今仍在延续,这是推动南京成为“文学之都”的必要元素。今后南京应当继续鼓励、提倡以及推动文学的创作,这是“文学之都”的根基。按照叶兆言的说法:“南京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它展开双臂欢迎来自别的地方的作家。和留不住出生在南京的作家相比,客居南京的作家要多得多。民国时期出版的《首都志》上,大诗人李白便赫然列在客居作家的名单上。在这个名单上,还可以算上古文八大家中的王安石,算上写《随园诗话》的袁枚,算上同治光绪年间诗坛的盟主陈三立。历史上的南京从来都是一个适合文化人住的地方……这些不是正宗南京人的作家,目前能活跃在南京的地盘上,在这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真应该好好地感谢南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南京的空气净化了他们,是南京的风水为他们带来了好运气,话反过来说,南京也应该很好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人们所说的南京文学欣欣向荣也不存在,外地的组稿编辑也不会如此频繁地到南京来狩猎。”[9]同时,马克思曾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10]作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只有进入消费渠道,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关注,文学活动的环境才可能真正形成。南京拥有数量众多的国语和民营书店,文学和图书消费潜力巨大。古代的南京是江南图书业中心,现代南京也仍然是东南图书出版重地,这些都是促进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关键性要素。
其次,“文学之都”必须“落地”,也就是借助视觉性的实体景观来深入人心,让市民有真切感知,逐步上升至理性的接受。有学者提出:武汉可以在城市诗词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借助黄鹤楼到武昌江滩的街区打造“诗梦小道”[11],同理,南京作为“文学之都”,也应当建设自己的文学景观。目前,南京已有的范例就是把地铁三号线的各站点用《红楼梦》元素统一装饰布置起来,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南京还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改造建立作家纪念馆,树立作家名人雕塑。在书店或重要的文学纪念场所周边,规划“文学大道”,把文学融合进城市中去。像古代的刘勰、萧统、李煜、曹雪芹,有的对于广大普通市民而言还不十分熟悉,借助景观所传达的信息可以加深对其认识与了解。武汉的做法,其立意巧妙处在于运用了黄鹤楼这一文学意象,使之与现实景观相结合。南京也有不少已经在城市地名或具象实体化的元素,如阅江楼、随园、半山园、秦淮河、江宁织造府等,在这些基础上打造文学景观不仅有文化依据,也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方面,可借鉴日本的伊豆半岛,伊豆半岛由于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名扬世界,借助文学,伊豆半岛上的“舞女小道”也成为一大景观,而《伊豆的舞女》又推动了伊豆半岛的文化旅游。南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可供开发,可以作仔细致的梳理并加以打造、宣传和推广。
再次,文创产品开发可以使“文学之都”的精神内核真正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南京的文学活动,不仅仅是阅读本身,还可以延伸到各种文创产品的开发。而这里的关键,则是基于文学与艺术间的“语-图”关系。由于文学作品主要还是借助文字来和读者交流,不同的作品所面对的对象往往差异较大,因此在普通市民消费者中进行文学推广的时候,需要借助多种形式和手段。基于此,借助视觉效应,在大众心里建立起一条认知渠道,这是“文学之都”建设所必须经历的一个步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传播也离不开视觉形象,尽管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具有抽象的特征,但同样无法完全和形象剥离,正如王东所言:“艺术要建立起自己的意义系统,是没有办法离开形象和语言的。从形象上说,因为它连接着人类及万物世界,已经融入进了各种媒质和领域,形成了‘形象家族’系谱……语言既是形象的最重要承载者,也是人类构建意义的最大基石,它已经融入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12]就这一点来说,文学的传播是离不开形象化的。古代到今天大量的插图本书籍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文学创意产品的研发推广,同样可以借助这种“语-图”关系来展开。有学者认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应当注意:“一是营造文艺与精致的环境。文创手作对于消费者心境有很高要求,所以高水准的设计必不可少。二是文创商店售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体验与服务。顾客在消费时日趋理性,充斥眼球的广告已经很难使其印象深刻,因此体验式营销逐渐成为主流,质量和服务是体验营销的关键。三是通过策划打造知名度,可利用媒体的力量宣传主题活动;借名人效应达到宣传效果;借公益活动造势,提升品牌形象与认知度。”[13]具体到文学资源上,以上这些都可以变成具体措施来落实,把文学文本转化为文学创意产品,使得大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也符合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特征与规律。
4 结语
总的来说,作为古代江南城市的继承者之一,南京的文化基因中已经充满了文学元素,成为“文学之都”实至名归。2018年,“一带一路”文学论坛永久落户于南京。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对于南京来说是一件文化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南京用心去经营和打造“文化资本”,那么,不仅南京的城市文化将会提档升级,而且南京建设“文学之都”的经验也可为国内城市的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