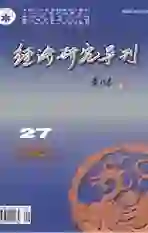村官“微腐败”的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2020-11-23杜诗雨
杜诗雨
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村官“微腐败”逐渐成为阻碍乡村治理水平提高的主要病原体,其所具有的隐蔽性、对价性以及迷惑性特征使此类腐败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与处理,村民对村官“微腐败”也往往采取一种集体沉默甚至宽容默许的态度,村官“微腐败”的治理迫在眉睫。对村官“微腐败”进行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并阐述其生成机理,由此提出社会治理调适路径,以期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村官;“微腐败”;理论现状;概念界定;生成机理;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7-0021-05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由此可见,“微腐败”治理作为党执政能力的映现,是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之一。然而,在我国乡村治理水平普遍不够发达的现实背景下,村官“微腐败”已然成为阻碍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病原体,严重侵蚀着基层治理的根基,破坏了农村地区的政治生态环境,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微腐败”概念的理解在学术上仍是模糊的,“微腐败”无法等同于“小腐败”,其内涵界定理应充分考虑此类腐败行为的具体特征与生成土壤。此外,对于村官“微腐败”的定性也因其双重身份存在模糊空间,村官即是基层自治组织的代理人,也是基层政府与村民对话的桥梁。综上可知,农村成为“微腐败”的重灾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我国农村高速发展进程中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涤清农村社会风气,消除村官“微腐败”的滋生空间对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研究以吉林省为调查主体,以黑龙江省为对照样本开展,以期更清晰地发现“微腐败”的概念本质与生成机理,验证治理路径的可推广性,从而争取为解决实践问题做出参考。调研地点具体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辖安图县长平村、大砬子村、红旗村、四合村和永福村,下辖敦化市小山村和腰甸村,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下辖饶河县小南河村。这些调研地点涵盖了国家级示范乡村、国家级贫困县以及发展较为平缓的乡村,调研中更不乏优秀乡村振兴及村官“微腐败”治理的经典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典型性,对于村官“微腐败”治理路径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理论现状
腐败,按照学者弗里德里克(Fryderyk)的理解,是指“一个负责做某种事情的拥有权力的人,即一个负有责任或有官职的人,受到金钱或者其他报酬的誘惑,如对未来工作的期待,而采取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的行动,因此损害了该官员所属团队或组织”。学者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进而指出,腐败是由于公职部门对手中权力的违法使用,又或者是对于社会资源的滥用。国外学者在之后对于腐败问题的研究中,一再强调对腐败进行明确分类具有重要意义,学者希奥多·洛一(Theodore Lowi)将腐败分类的关注点从腐败的塑性过程转移到它的本质危害性上,他将腐败行为分割成了明确的“大”“小”两种,以英国“报销门”为例,其已经影响到英国的国家事务,是典型的大腐败行为,与之相反,有关个体利益的腐败便是小腐败。不同于希奥多·洛一的理论,戴夫·沃克曼(Dave Workman)和阿伦·科特利伯(Alan Cottlieb)认为,腐败类型应该按照腐败行为者的人数对进行区分,两位学者进而提出小腐败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谣言的事件性质,突出了行为者的个体性,具体包括腐败个体的贪污行为以及利用公权力徇私舞弊的行为,而大腐败就需要腐败行为者与其他相关人员互相合作,因共同的腐败动机集聚并分享利益。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真实的政治环境下,对腐败的分类并不是非“大”即“小”的,在大腐败和小腐败中间其实存在着过渡区域,按照以上西方学者的分类方式,在过渡区域内发生的腐败行为并不容易厘清,因此公众才会对是否应该惩治“大小之间”的腐败行为者态度不一,进而导致社会对于大腐败与小腐败的划分出现自我矛盾。学者阿墨德·海德海莫(Arnold J.Heidenheimer)基于此提出了“白色腐败”的定义,他认为识别官员行为是否属于腐败行为应由群众的价值取向决定,进而他将腐败划分为黑白色两种。“白色腐败”就是指人们对这类腐败现象并没有预期那么排斥 并没有遭到预期排斥的腐败现象,人们对这类腐败的评价并不负面,甚至此类存在一定的民意基础,公众认为“白色腐败”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关于是否需要处罚“白色腐败”行为者也没有过分严肃。而对于大部分公众都嗤之以鼻的腐败行为应该属于“黑色腐败”,公众希望“黑色腐败”的行为者能受到法律层面的惩罚的行为,因为此类腐败已经打破社会各阶层都认同和遵守的日常准则,与大部分公众的价值观相悖。由此可知,虽然国外目前并未存在“微腐败”这一表述,但存在与“微腐败”相似的概念,即“白色腐败”。
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政治现实,学者胡鞍钢对“微腐败”的定义曾这样给出概括,“它是一种游走于规则边沿,在似乎合情理的表面装饰下而形成的腐败现象……从而降低警惕性,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与巨型腐败比较,微腐败的普及性、习惯性和隐蔽性使其同样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腐败。针对微腐败行为,学者杜治洲则将关注点放在了基层政治生态上,微腐败行为导致了基层官员的“逆淘汰”现象,即正直、“情商低”的官员会无法得到基层群众支持与上层重用,基层政治生态逐步恶化。至于微腐败的成因,学者李钺锋从法理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微腐败”是“现如今社会一种普及性广并游走在政策空洞区的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在模糊地带尤其是权力监督空洞区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并且这个行为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为或者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根本不能对其进行惩治的行为”。学者李靖则认为,“微腐败”行为是由于法律失位、监督失效以及制度失灵陷入了治理困境,并提出了党委为核心、政府为主导、基层群众为协同和以基层社会组织为支撑的多中心反腐模式。
在我国,“微腐败”行为诱因可能是多维的,如道德品质下滑、政治软弱以及集体沉默等等,涉及不同社会单元的复杂责任,需要深入的系统分析与研究,作为“微腐败”重灾区的农村更是如此。虽然村官“微腐败”造成危害并不明显,但可能十分深远,村民已经对其习以为常,且行为结果普遍不会受到法律惩罚,行为者的违法成本微乎其微。学者任建明认为,通过强化外部监督与村级民主相结合的村务监督是微腐败治理的重要保障,以此避免村官权力的过度膨胀。学者吕永祥和王立峰提出了异地交叉巡查的方式排除微腐败行为可能产生的人情干扰,从而将其作为应对策略的重要组成以防止微腐败行为的出现。
总结而言,国内外研究对于村官“微腐败”的概念在学术上始终缺少明确的定义,导致其与小腐败行为出现了混淆,无法有针对性地保证“微腐败”防治的具体落地。因此,对微腐败行为进行探讨的前提便是从内涵与特征上将其与其他腐败行为进行区分,着重关注村民为何会出现对“微腐败”行为“政治沉默”,并以此提出村官“微腐败”行为的社会治理策略。
村官“微腐败”能够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质在于村民对于此类腐败行为的集体政治沉默,村民的沉默不仅体现在他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疏远与逃避,甚至还包括了村民对于微腐败行为的默许与认可,沉默之下流动着的冷漠、失望、恐惧、侥幸甚至更复杂的情绪。对于公众政治沉默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学者罗伯特·达尔较早对此现象进行了关注,他从公众政治性的角度将社会公众分类为有权者、渴望权力者,政治阶层和无政治阶层,大多数人则属于无政治阶层,虽然他们与政治活跃分子生存在同一个政治社会,但是他们没必要参与甚至关心政治生活,甚至不需要珍爱所在社会的政治价值与体制现状。政治沉默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政治参与的不充分,对此,学者安东尼·奥罗姆认为公众与政治阶层的信息不对称是其政治参与消极的主要原因,“政治参与要求接收关于政治的一般和特殊的信息,那些获取这种信息的人,即在效应和心理上更多介入的人,就更可能参与政治。”学者Pinder等人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将集体沉默分类为无为沉默和默认沉默,无为沉默是指不赞同的保留观点,旨在避免自己因为发表不同意见而遭遇报复,而默认沉默则是消极的顺从,将自己原本的想法进行处理甚至放弃。学者Dyne则进一步发展了Pinder的集体沉默理论,他将集体的沉默划分为默认沉默、亲社会性沉默与防御沉默三种,不同于默认沉默的是,防御沉默的出发点在于个体希望保护自己,沉默动机更为主动,在不公平的氛围下,集体中的理性人经过利益的心理博弈,选择了沉默作为最佳的应对方案;人天然具有社会性,基于利他与合作的动机,亲社会沉默得以产生,此類沉默人群并非担心自己受到发表观点的负面影响而遭受利益损失,其更多的关注点在于帮助他人,同样属于个体意愿行为。
西方学者关于政治沉默的研究成果对解决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仍需与中国农村的社会背景相结合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讨论,农村的政治环境较为复杂,如若村民对于村官“微腐败”行为进行反抗,可能会导致其机会成本的大量丧失。学者于建嵘认为,基层群体的沉默是一种被压制下的无奈,但如若压抑的怨言积累到一定程度,终究会爆发出来,从而转变为暴力的反抗。因此,改善基层政治生态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学者张劲松和骆永在解释村民对于政治参与的沉默行为时,提出了三个产生原因,分别是不独立的村民经济地位、不完善的农村基层民主,以及村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不足。
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村官“微腐败”行为的村民政治沉默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村民对此类腐败行为的态度是一种不反抗的清醒,不能等同于普遍意义上的政治参与冷漠,国内学界对此暂时缺乏相关的系统分析与研究。村民对于村官“微腐败”的默许为此类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官本位”的思想在农村社会的广泛存在让村民畏于举报腐败行为,担心因举报而发生的损失与代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村民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态度,且村民渴望自己也成为“微腐败”的参与方与受益者,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更是“微腐败”的受害者,村民因而对不公平视而不见,治理村官“微腐败”行为,规范自上而下的监督固然重要,但厘清村民政治沉默的成因更能营造良好的基层政治生态,是治理村官“微腐败”的根本。已有的文献中,社会治理的乡村实践讨论多集中在概念辨析、逻辑和法理意义上概念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缺乏从制度建构角度完善落实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路。传统关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研究往往以理论性较强的规范研究为主,难以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本次研究试图将制度建构作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以社会治理作为建构路径来解决现实中村官的“微腐败”问题。
二、村官“微腐败”的概念界定
村官“微腐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而是与具体实践中的“显性腐败”相对应的概念,我国村官“微腐败”行为往往与农村民生密切相关、与村民生活近在咫尺,呈多发态势。对村官“微腐败”治理进行研究的前提,便是在研究与调查中对该概念的准确定义并一以贯之的坚持,国内学界关于村官“微腐败”这一概念内涵还没有统一的解释,目前存在许多学者以腐败贪污的涉案金额多少来区分腐败性质,认为涉案金额低于3万元的违纪违法行为便属于微腐败行为;甚至部分学者因村官的权力相对较小将村官腐败笼统的等同于村官“微腐败”,以职级权限的大小划分腐败类型,这些将“微腐败”趋同于“小腐败”的分类方式明显是不准确的,因为村官“微腐败”所涉及的贪污绝对数也可能格外巨大。
2016年9月,吉林省M镇E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成刚(化名),组织村内7名符合“XX增信脱贫贷”专项扶贫贷款条件的贫困户申请到了贷款共计人民币70万元,其中3名贫困户实际使用了名下贷款,另外4人的贷款额被其擅自用于个人经营活动,村中多人知晓此事,却没有举报,直到2019年M镇纪委排查该镇经管中心业务时,才从该村村委会其他成员处了解到了此事,王成刚目前因骗取贷款、长期挪用集体资金被撤销党内职务。
由此可知,不同于“小腐败”,村官“微腐败”的区分标准应该在于公众对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村官“微腐败”的涉及领域较为广泛,对公众的迷惑性较强,包括隐蔽性的公权滥用与贪污受贿,甚至如懒政怠政、遇事推诿、工作不积极等作风问题使得公共利益受损都属于此类腐败行为,村民对待村官“微腐败”的态度并不是及时举报或制止,而是不以为然与宽容放纵。因此,村官“微腐败”的治理存在困境,即对于“微腐败”的性质判定不能通过传统的判定标准实现,与一般腐败对比来说,对于“微腐败”的界定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这不仅使其长期与法律法规打着“擦边球”,而且对于村官“微腐败”行为的规范也一直处于政策的盲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政府还不能做到以定量的标准来公正区分村官“微腐败”。通过对村官“微腐败”与其他腐败类型的简单区分并不足以对其形成明晰的认识,充分考虑村官“微腐败”生成的农村社会土壤,对村官“微腐败”的特征分析与认证是准确界定其类型的必然要求。
(一)隐蔽性
村官“微腐败”具有高隐蔽性,这与农村特定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村官“微腐败”行为不会被严格界定,更不易被察觉,例如中国农村社会的“人情”关系,村官“微腐败”也正是借此得以不断延伸。
以H省R县X村2018年农村低保户的评定与评审过程为例,村民老陈(化名)便是村官“微腐败”的直接受害者。他与张五(化名)的家庭条件相似,但是张五是村长的弟弟,其借由探望哥哥请村长吃了顿饭。在评低保户时,村里便没有经过严格的评比过程,将老陈排除在外,然而,由于两人家庭条件相似,选择谁做低保户都有道理,老陈也有苦说不出,便默默接受了。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礼”一直被视为高尚的传统美德,它在无形中长期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国也因此被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所以,每逢节日都会严格强调“节日腐败”问题,这符合国人主流思想与习惯。
(二)对价性
村官“微腐败”行为涉及的主体包括村民和村官两个方面,往往是村民出于自利的目的寻求村官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会产生一定的利益支付成本,且双方是完全自愿的,并不存在村官对村民的胁迫,理所当然地对价自然不会引起其他村民的格外关注与批判,相反,村民对此类违规行为却相对宽容甚至认同。换言之,村官“微腐败”以潜伏的状态存于农村的社会现实之中,改变着村民的价值观念与认知,但其实质上与村民质朴善良的价值观念存在根本的道德矛盾。即使部分村民在利益受损后勇于反对与批判村官“微腐败”行为,但一旦存在寻租空间,这些反抗者却极有可能主动参与到村官“微腐败”之中。因此,村官“微腐败”的对价性实质上在潜移默化地腐蚀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秩序。
(三)迷惑性
村官“微腐败”的界定模糊导致“微腐败”的行为主体进行违规操作却不自知,一旦村官“微腐败”没有得到及时治理,村官得以获利,便使村官的无罪感得以强化,“微腐败”行为主体并不认为自己违法乱纪、触犯法律法规,甚至在个人观念将自己塑造成乐于助人、勤恳工作的形象,“微腐败”的滋生土壤由此形成。村官“微腐败”的迷惑性助长了其发展态势,并使“微腐败”文化持续蔓延,甚至违规主体有可能从“微腐败”发展为“大腐败”。
综上可知,村官“微腐败”即腐败行为的一个重要类别,是指村官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作为对价,建立在村民的宽容之上,用隐蔽的手段谋取私人利益或给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失,其本质仍是公权的私用与滥用。①
三、村官“微腐败”的生成机理
(一)行政与自治在农村的边界模糊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即国家管理的范围到达县一级便终止了。周庆智基于此认为,“从帝制中国到现代中国,乡村小官贪腐源自官治与民治之间的体制性与制度性冲突。如果说,帝制时代,这个冲突还主要源于国家财政能力不足和集权与分权的体制痼疾,那么在现代中国,这个冲突则是以现代国家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利关系的失范和失序为表现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官具有一定的“双重代理身份”。不但上级政府将部分行政权以委托或派生的方式交给了村官,而且村民也将自治权以赋权的方式托付于村官,这导致村官“微腐败”长期处于国家与社会监督的盲区,村支书或村长手中的基层权力过于集中,却又缺少与制約其权力的监督机制,县级与乡镇级的纪委由于精力与财力有限,很难完全知晓各村村务执行情况,只能通过村民的实名举报来处理各类村官“微腐败”问题,但事实上村民缺乏安全隐匿的举报渠道。由此可见,治理角色与身份的模糊性正是受困于基层治理制度的内在矛盾,农村行政权与自治权边界仍然处于模糊状态。
(二)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同级监督不力
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村官同级监督的重要组成之一,对于村务的计划与执行享有重要的知情权,理论上村监委会与其他村两委是平级的,但现实则是村监委会接受村两委的领导,监委会书记往往同时也是村两委成员,村务工作也更多地沦为“一言堂”。村监委会的监督力量较为薄弱,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受限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导致村务监督层级不高、效率较差、稳定性低且落地困难,也阻碍了农村法治化进程。《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指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有向“村‘两委提出村务管理建议”的权力,“必要时可向乡镇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对发现的涉嫌贪腐谋私、侵害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问题,及时向村党组织、乡镇党委和政府及纪检监察机关报告”。《意见》对村监委会的工作路径与职能权力进行了事实限定,其监督权主要体现在发现、汇报和建议,并没有处理腐败村官的权力。如果不能得到上级政府的政治支持,村监委会就很难发挥有效果的监督作用,影响力和执行力较差且效力极低。
(三)不反抗的清醒——村民的“集体沉默”
村民对“微腐败”的态度既矛盾又具有反讽意味,虽村民对于村官的不正当行为普遍憎恨,但一旦事涉其身,他们又会以宽容、默许甚至希望获取“腐败资格”的方式去面对。某些村官的亲属谈及腐败厌恶至极,但当自己家申请低保时就会找自己的村官寝室安排。缪尔达尔(Myrdal)认为,腐败文化使“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自认为应当效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公众对腐败的愤恨也会“基本上变成对于有机会通过不光彩手段营私之徒的羡慕”。因此,我国农村社会对村官“微腐败”认同的普遍性和习惯性使村民价值观的扭曲,村民把权力兑现利益的能力而非廉洁自律作为对村官能力的评价标准,认可“当村官可以发财”等畸形观念,由此便可以解释为何村民对各种村官“微腐败”现象也熟视无睹,甚至认为“微腐败”可被忽视,举报行为显得没事找事。在此背景下,村官易滋长出微腐败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附属物的观点,降低对“微腐败”的抵抗力。另一方面,村民缺少向上举报的隐匿途径,畏于举报腐败村官后的报复与压迫,农村社会是典型的“人脉社会”,村官往往拥有强大的人脉资源,或是宗族,或是亲朋,即使因其“微腐败”行为被举报,腐败行为者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组织报复力量,对举报者施与报复手段,而村民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意识与能力较弱,法律接受和认可能力有限,使其丧失了农村法治主体性能力,只能接受村官的“微腐败”行为。
參考文献:
[1] 习近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 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EB/OL].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官方网站,2016-01-12.
[2] Arnold J.Heidenheimer,Michael Johnson.Political corruption[M].ABC-CLIO,2011:08.
[3] Michael Johnston.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Public Policy in America[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83,(77-01):208-209.
[4] Peter Deleon.Thinking about Political Corruption[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5,(541):197-198.
[5] Alan Cottlieb,Dave workman.Double Trouble:Daschle and Gephardt-Capitol Hill Bullies[M].Merril Press,2001:25.
[6] 胡鞍钢,过勇.地方干部如何看待腐败问题——云南地县级干部的问卷调查[C]//国情报告:第四卷 2001年(上),2012.
[7] 杜治洲.改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治理“微腐败”[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11):37-38.
[8] 李钺锋.对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边缘腐败”零容忍[N].检察日报,2012-04-17.
[9] 李靖,李春生.我国基层官员“微腐败”的生成机理、发展逻辑及其多中心治理[J].学习论坛,2018,(7):58-64.
[10] 任建明.村务监督与微腐败治理[J].人民论坛,2018,(21):100-101.
[11] 吕永祥,王立峰.县级监察委治理基层“微腐败”:实践价值、现实问题与应对策略[J].东北大学学报,2019,(21-1):43-50.
[12] 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129-141.
[13]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张华清,孙家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293.
[14] Pinder G.G.,Harlos H.P.Employee silence:quiescence and acquiescence as responses to perceived injustice[J].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1,(20):331-369.(下转38页)
(上接25页)
[15] Dyne L.V.,Ang S.,Botero I.C.Conceptualizing Employee Silence and Employee Voice as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3,(6):1359-1392.
[16] 于建嵘.沉默抑或暴力:警惕民众政治心态的两极化[J].探索与争鸣,2015,(11):33-35.
[17] 张劲松,骆勇.论农村村民政治冷漠的成因及消解[J].理论探讨,2019,(5):25.
[18] 周庆智.论“小官贪腐”问题的体制与机制根源——以乡村治理制度为中心[J].南京大学学报,2015,(5):128-136.
[19] 冈纳·谬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方福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2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新华网,2017-10-14.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Path of “Micro Corrupt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Based on Surveys of Some Villages in Jilin and Hei longjiang Provinces
DU Shi-yu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f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rural village officials “corrup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s to rural governance level pathogens,it has concealment,consideration and confusing features make such corruption behavior is difficult to be found and processing,the villagers of village official “corruption” tend to take a collective silence or even tolerant attitude acquiescence,village official“corruption” of governance is imminent,the study of village official“corruption” has carri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and expounds its formation mechanism,thus put forward the social governance adjustment path,try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Key words:village officials;“micro-corruption”;theoretical status quo;concept definition;generation mechanism;governance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