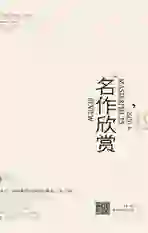文化视野与“才、学、识”
2020-11-19安裴智
著名古典文学专家、红学泰斗、诗人周汝昌先生于2012年6月31日在北京家中驾鹤西去,享年95岁。对一个学者来讲,九秩又五,已算高寿,但当时惊闻此噩耗,我还是不能接受,感到非常惋惜。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红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与周汝昌先生一家保持着20多年的交谊,那年5月,我还给周老的女儿周伦玲女士去电问候,她说父亲身体很好,没病,但毕竟老了。4月14日,周老95岁寿辰时,也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新华社记者唐师曾还去给老人拍了寿照,老人很高兴。谁知,仅仅一个月,周汝昌先生就仙逝离我们而去了。时光荏苒,转瞬已是8个春秋。静静地打开书柜,望着20多年来收藏的40余种学术著作,轻抚着先生亲笔签名赠送我的《恭王府考》《我与胡适先生》《红楼夺目红》《兰亭秋夜录》等10余本红学著作,再一次欣赏先生1995年夏至书赠我的诗歌书法作品,还有他生前的数篇手稿,以及于2003年秋天为我的文学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所题写之书名,透过一个个挺秀遒劲、骨瘦露锋却又饱含深情之书法笔迹,那张慈祥而睿智的耄耋老人的笑脸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认识周汝昌先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那是1988年,我负笈并州,在山西大学攻读元明清小说与戏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幾位授课教师中,就有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先生的研究生梁归智教授。那时的梁师年近四旬,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面容清秀,风度儒雅,仪态谦和,身上流溢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是属于有慧根的那类学者。梁师选择了被称作中国三大显学之一的红学作为学术突破口,年纪轻轻,就在常人不敢问津的红学领域辟山开路、筑疆拓土,成为继周汝昌先生之后《红楼梦》探佚学研究的顶梁柱和重要代表,他的《〈石头记〉探佚》成为继《红楼梦新证》以来又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探佚学力作。
1981年,梁归智老师的红学探佚著作《〈石头记〉探佚》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汝昌先生作序,首次提出了“探佚学”这一概念,认为当代红学已形成了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四大分支学科。在关键意义上讲,只有这四大支才“够得上真正的‘红学”。周先生如此强调这“四学”的重要性,其用意并不是否认《红楼梦》的文本批评,而恰恰是太重视《红楼梦》独特的“这一个”文本,充分认识到《红楼梦》不是一部普通的古典小说,因而,要走进曹雪芹的灵魂深处和文化思想,就不能“用一般小说学去研究”,而必须以曹学、脂学、版本学和探佚学这四大分支学科为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曹雪芹的家世背景、脂砚斋批语的价值、各种版本文字的异同及后三十回被遗失的原稿内容搞清楚,才有可能真正读懂《红楼梦》的文本,才可以去从事“文本批评”,也才能认识到“红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足以与“甲骨学”“敦煌学”相鼎立的当代显学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只有“知人论世”,才可能正确地把握曹雪芹原著的思想内容。
对梁归智老师的探佚学成果,周汝昌先生深为厚爱和器重,给了高度的肯定和赞赏。周先生诗赠梁师:“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那时,梁师以一种富有美感的授课方式,从“谶语”“谐音”“影射”“引文”和“化用典故”等几个方面,畅述了曹雪芹“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奇特创作方法,为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子开启了一扇瑰丽奇异的红楼世界,描绘出一个《石头记》里被迷失的精彩世界,真如琼浆玉液灌心田,使我对《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产生了如醉如痴般的迷恋,从心灵深处感应到其“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的审美价值。
当时,从情感和立场上,我倾向于接受周汝昌、梁归智等先生的探佚观点。于是,我对曹雪芹的家世、家族故事、脂砚斋和畸笏叟的批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图书馆借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几个早期版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从旧书摊上淘得《红楼梦》“梦稿本”。同时,精读了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的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考证力作《红楼梦新证》以及胡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何其芳的《论〈红楼梦〉》、王朝闻的《论凤姐》、朱一玄的《红楼梦资料汇编》等。其中,多次精细研读了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读后觉其体大思精,论证缜密,解决了“旧红学”所遗留的诸多问题,对胡适的“自传说”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证,对曹雪芹的家世、人物、籍贯出身、地点问题、雪芹生卒年等进行了周密的考证。海内外著名学者赞之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由此奠定了周汝昌先生在红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一般学界认同,称周汝昌坐继胡适之后“新红学”第二把交椅。
实际上,《红楼梦新证》是周先生早年的作品,并不代表他一生的红学研究成果。他一生出版了40多部红学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更侧重研究《红楼梦》的文化意义、《红楼梦》的艺术特色,更重“文本研究”,特别看重对曹雪芹哲学思想的研究。所以,他本人对说他是“考证派”是不太满意的。正像钱穆与余英时被称为“新儒家”的代表,而两位先生也是不认同一样。
然而,红学以降的200年来,在多如过江之鲫的所谓“红学家”中,真正能有如此识见、如此认识高度的人,也就如周汝昌先生这样“才”“学”“识”兼而俱备的少数几人。这不能不说是红学的悲剧。周先生的这种感悟,也常常招来那些缺乏鸿鹄高见的燕雀之徒的攻讦。红学界一直有种说法,说周汝昌从不研究《红楼梦》的文本,这是不了解先生的学术得出的妄语。实际上,周汝昌既探源曹雪芹的先祖家世和坎坷人生,又倾力于各种脂批版本的考辨比较,同时也用心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求索,是一种杂糅各“学”的综合研究。如《〈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是探讨《红楼梦》思想意义的《,红楼艺术》《红楼艺术的魅力》二书是覃研其艺术特色的,都是一种纯粹的文本批评。但无疑,贯穿其“为芹辛苦见平生”的60年红学历程灵魂和精髓的是探佚。周先生异于历史上其他红学家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探佚”为精神灯塔,来照亮和统领一切红学。可以说,周先生这一“解味道人”,是以“探佚”为手段来解曹雪芹原著之深“味”,可谓雪芹的“异代知音”!以周汝昌为代表的探佚学者认为,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曹雪芹原著《红楼梦》的四十回丢失了,《红楼梦》成为断臂维纳斯。现在流行的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是真假合璧,其中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的续写,是狗尾续貂,从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作家的美学倾向到作品的思想价值取向诸方面,都违背了曹雪芹的创作原意,是对曹雪芹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的反动和颠覆,因而要找回原著《石头记》里被迷失的世界,从而使“全璧”复原,还原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本”“原本”。可以说,百年红学步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形成了以周汝昌先生为领军人物,以梁归智、刘心武、蔡义江、孙逊、徐恭时、杨光汉、丁维忠等先生为骨干的探佚学新景观。
1991年秋,我从山西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太原日报》编辑部工作,负责“双塔”副刊的“文学评论”版。由于工作需要,从1992年春天开始,我每年两三次要到北京组稿。借这样的机会,我走进自己敬重的周汝昌先生的家里和生活中,得以亲承謦欬地聆听这位古典文学前辈学者的谆谆教诲,面对面地感应这位红学大师的心跳和呼吸,清享这位“新红学”代表人物藻耀而高翔的玉屑之谈。周先生慈祥睿智,却始终有一颗清纯的艺术童心。谈起《红楼梦》来,他神采飞扬,激情洋溢。那时,梁归智老师已成为周汝昌先生的私淑弟子,与周先生的学术来往较多。我就通过梁老师的介绍,开始约请周先生为“双塔”副刊写稿。1994年3月,周汝昌先生给《太原日报》写来了《太原随笔》等一系列文章,文采斐扬,笔法灵动,情思绵长,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渗透着浓郁的书卷气,见出了深厚的文史功底。1995年1月17日《,太原日报》又发表了周汝昌先生的《历史的“逆证”——鄂昌、胡中藻文字狱与〈红楼梦〉传说的关系》,这是一篇很见学术功底的长篇考证文章,資料翔实,爬梳钩沉严密,且具有浓郁的故事趣味性,颇富新见。这其中,有一段红学史上的佳话,值得提出来一说。1993年,受“红学”探佚人物周汝昌、梁归智学术观点之影响,著名作家刘心武开始“秦学”探佚研究。由于我与刘心武先生也走得较近,经常到他家里拜访、组稿,于是,1994年6月至12月,我策划在“双塔”副刊文学评论版开展了一场颇有学术纪念意义的红学对话。这场“红学对话”论述的文学话题重大,持续半年之久。这就是由老红学家周汝昌、中年红学家梁归智与著名作家刘心武三人进行的一场关于“如何进行红学探佚研究”和“进一步肃清程高伪续的思想流毒”的对话。称其为“对话”,是因为这三人主要观点一致,分歧意见不大,但切入的角度和着眼的侧重点有异,探佚思路不同。梁归智、刘心武以商榷、论争的形式展开,周汝昌、刘心武又以书信、互勉的形式收场,共组发了6篇红学论文。周汝昌先生的《探佚与打假》、刘心武的《甄士隐本姓秦?——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问世240周年而作》《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梁归智老师的《探佚的空间与限度——由刘心武、王湘浩的红学探佚研究想起》,以长篇论文的形式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专版中推出。刘心武先生还就红学探佚打假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给周汝昌先生去信讨教、切磋,周先生做了详细的回答,这两封题为《“打假”虽艰势必行——致周汝昌先生书》《致刘心武先生》的红学书简也都在“双塔”副刊文学评论版发表了。老红学家周汝昌一生提倡“尊曹贬高”;否定高鹗后四十回,其《红楼梦新证》被称作“新红学”的一部里程碑意义的扛鼎力作,体大思精,论证缜密,解决了“旧红学”遗留的诸多问题,对胡适的“自传说”做了更详细的论证。梁归智则是较早取得探佚理论成果的一位代表人物,刘心武为“作家学者化”式的探佚新秀。这三位红学探佚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双塔”副刊文学评论版1994年组织的这次“红学对话”将被重重地写进当代红学史中,这场“红学对话”深广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也将会在今后的日子里愈益显露出来。周汝昌先生在《探佚与打假》中一开篇就写道:“《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愿意将几千字的版面惠予学术讨论,而且范围包容了红学中的探佚学,我不知全国市级日报能够这么做的共有几家?令我心中充满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参加争鸣,我真不应该辜负了这个宝贵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挥汗命笔,贡我拙意——用雪芹的话,就是‘试遣愚衷了。”(见《红楼梦的真故事》)
1995年2月中旬,我受太原日报社编委会委托,赴京与中国记协国内部、中国作协创研部接洽、商榷,为下月要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报纸副刊研讨会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纪念会”做策划、筹备工作。除联系主办单位,邀请京城相关文化名人外,我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为《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征集文化名人的书画墨宝。于是,乙亥仲春,我的足迹踏遍了京华的各个角落,迈入一个个耄耋老人的家中。从东郊十里堡到西郊魏公村,从北大畅春园到劲松蒲黄榆,从朝内南小街到安外东河沿,从赵堂子胡同到复外大街,从西便门外到团结湖东里,从沙滩红楼到水木清华,从西直门外到崇文门内,高楼馆所,四合小院,胡同深处,寻常巷陌,凡有人烟处,皆藏龙卧虎,有我欲寻访的高士仙人。周先生作为享誉全国的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又是诗人、书法家,也长期是“双塔”的重要作者,自然在受邀范围。于是,我在电话里把这一心愿给周先生说了。周先生竟爽快地答应了。过了几天,他让我到他家取写好的诗与书法。周先生灵感一来,给《太原日报》“双塔”副刊赋诗一首:“嵯峨双塔比瑜璠,三晋云岚簇太原;为有文章兼学术,两千风日煦花繁。”小字是:“太原日报·双塔副刊二千期,津沽周汝昌半盲七六叟。”
过了几天,北京名人书画墨宝征集工作行将结束。我突然想起应该对周先生做一个学术访谈。于是,2月17日上午,我来到位于北京红庙北里的周汝昌寓所,对其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学术访谈。周先生的大女儿周月苓、三女儿周伦玲女士陪同我采访。周先生给我详细谈了他于1948年六月,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向胡适先生借阅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在胡先生的鼓励下,走上“新红学”考证之路的详细历程。聆听周先生畅谈对红学、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宛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清风扑面,甘泉灌心,真可以“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是一种难得的文化盛宴和精神洗礼。这不仅因为周先生才高八斗,谈吐儒雅幽默,更主要的,是他那超越了世俗功利的冰雪人格,犹如诗仙灵均所讴歌的:“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真正体现了一种“玉是精神难比洁”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品格。周汝昌先生特别单纯,书卷气浓郁,永远葆有一颗童心。走进周先生的心灵世界,仿佛踏入一片未经人踩过的碧绿青翠的芳草地,也如驾着飞艇远离浑浊的岸边驶入一片寂静而蔚蓝的天然海域,使我又看到了滚滚红尘、滔滔浊世中清纯明净的一面,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2月下旬,我返回并州后,就忙着与副刊部同仁准备“全国报纸副刊研讨会暨《太原日报》“双塔”副刊2000期纪念会的具体事务了。如给参会的全国文化界名人寄发会议邀请函,草拟大会领导讲话稿等。当然,也给周汝昌先生发了正式的会议邀请。2月28日,周先生自北京家中给我寄来一信:“安裴智同志:我因患足疾,不能去参加“双塔”2000期的庆典,十分遗憾,特此驰函遥贺。祝你们的副刊越办越有特色,为中华文化的振兴做出贡献!全国政协大会会期压缩了,日程更紧了。匆匆奉启,别不多叙。并颂文荣!周汝昌95年2月28日。”在信中,周先生解释了他因年高不适未能远足与会的理由,语词中寄寓了一位耄耋老人对“双塔”副刊的美好祝愿。
进入夏至日,北京酷暑。周先生不忌高温溽热,心绪极佳地研墨提毫,搦翰铺纸,为我书写了一幅书法作品,是周先生一首诗的旧作:“翠羽明珰事事新,几家疑假几疑真;陈王解道惊鸿赋,自是当时见洛神。”落款署名为“乙亥长至书旧作应裴智雅嘱,半盲七六叟周汝昌”。借曹植写《洛神赋》的典故,表明他对雪芹丢失的三十回原作矢志“探佚”之决心,让女儿周伦玲女士给我寄到了太原家中。如今,周先生的这幅书法作品,作为我的心中至爱,一直珍藏于书房。
2001年2月,我南飞鹏城,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六个月后,转调深圳特区报社,重操旧业,继续耕耘于文艺副刊这块芳草地,再度拿起了为别人做嫁衣的“金针”,在“罗湖桥”这块繁茂的园林,相继编辑“文艺评论”“书香阅读”“学人对话”“名家新作”“文史随笔”等版。于是,已经迈入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先生,再度成为我约稿的对象。那是2003年6月,基于周先生红学研究之专长,我约请他为我报“罗湖桥”副刊的“名家随笔”版开设“红学散步”之专栏,每篇以一千多字的篇幅,以一种富有灵性的散文化笔法,从一些红楼人物的小处与细节写起,持续一年多,见出了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这部世界名著的理解与文本解读。这个专栏的系列文章,周先生写得字字珠玑、新见迭出,颇可见出他对《红楼梦》这一著作的独到理解。后来,周先生结集为《红楼夺目红》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成为《深圳特区报》副刊史上的辉煌一页。
2003年秋的一天,我的文艺评论著作《守望与突进》要付梓。我从深圳飞到北京,驱车红庙北里,登门拜谒周先生,表达了对先生书法的欣赏与喜好之情。应我的盛情,周先生在两耳失聪、双目几乎失明的85岁高龄,搦翰展纸,为我题写书法墨宝“淡远”,寄寓了先生淡泊明志的云水情怀。周先生还挥毫为我的文艺评论新著《守望与突进》题写书名,足见其奖掖后学之苦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汝昌先生一直在从事一种感悟式的红学批评。周先生本身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诗人、书法家,所以,他的学术随笔也就满溢着才气与灵气,不是那种教条的八股文风,不是那种空洞的抽象说教,而是具备了“才情”,是“才”“学”“识”的有机融合。梁归智老师认为,周汝昌在治学过程中,反复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的领悟与感受能力;他论学评文,强调文、史、哲三才会通,强调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强调感悟力、想象力、创造力,反对枯燥、生硬的分析与解剖。所以,周先生虽是一位以考证出名的好像是钻故纸堆的“红学泰斗”、古典文学专家,却也是一位有着曹雪芹、贾宝玉那种真性情与李贽所说的“童心”的才情学者。他是以一颗富有激情的诗人之心来解读《红楼梦》,因而他的红学随笔是他与曹雪芹、贾宝玉进行心灵对话的过程。周先生选择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凌晨静静地离去,也足见先生永葆一颗艺术童心,人品清纯明净,是对传统文化通融于心的通才学者。
周汝昌先生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中华文化研究,尤其是红学研究。他在旧体诗词的创作方面也很有成就。中国词曲界,向有所谓“南吴北顾”的说法,这是研究中国词与曲这两种文体最厉害的两位学术大师级的人物。“南吴”,即是指生在苏州、曾经在南京的中央大学任教的词学家、曲学家吴梅,即吴瞿安先生,他既是曲学研究家,又是曲作家、曲学理论家,创作了不少传奇剧作,在度曲、审曲等方面造诣精深,被誉为“近代制曲、谱曲、度曲、顾曲、校曲、注曲、研曲、藏曲、教曲、演曲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曲海覃游毕生,桃李天下,他培养了任二北、卢冀野、唐珪璋、钱南扬、陈中凡、钱绍箕、赵万里、常任侠、浦江清、王季思、胡士莹、吴白匋等一大批古典文学学者;而“北顾”,即指曾在北京的辅仁大学任教的顾随,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他培养了张中行、周汝昌、叶嘉莹、郭预衡、史树青、邓云乡、吴小如、黄宗江等一批大学者。周汝昌是“北顾”即顾随先生的高足。他20世纪40年代立雪顧门,从顾羡季先生游,而后卓然而为一代学术大家。在众多的顾门弟子中,周汝昌先生不仅是国内坐“新红学”第二把交椅的红学泰斗、古典文学专家,也是诗词修养极高、有诗词天赋的才子学者,同时还是一位风格独特的书法家。
周汝昌先生对中华文化葆有一颗挚爱之心,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是当代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艺宗“书圣”王右军,又承继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自成一家。周先生著有《永字八法》《书法艺术答问》《兰亭秋夜录》等书法理论著作。周先生的书法,瘦而不失其肉,转折处可明显见到藏锋,活用侧锋,笔墨细尖而有力,柔中见刚,遒媚劲峭,很有精、气、神。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文化大视野。梁归智先生认为,周先生从进入红学研究领域的一开始,就把文献考据、义理思辨和艺术感悟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觉地把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的高度。周先生研红,重辞章、考据、义理之结合,也就是文、史、哲的“三才”之美。此即章学诚所谓“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也。进入20世纪90年代,周汝昌提出将红学定位于“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红楼梦》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
周汝昌先生一生清贫。20世纪90年代,我曾去周先生家拜谒过他几次,2003年秋天是最后一次见他。他蜗居于北京朝阳区一幢简陋的楼房里。家里谈不上有什么家具,全是旧的桌椅,几乎没什么装修,很简陋,沙发上的布也是很旧的,也没有太多的藏书。家里简直寒酸、俭朴极了,但是他乐在其中。他是一位把一生献给《红楼梦》研究的老人和学者,心中唯有“红楼”,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老师形容周先生的性格,是“痴人”和“赤子”。他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又单纯。他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为人很率真,有一颗童心。他性情天真,对后辈晚学热情无私地支持和帮助。周先生在《献芹集》扉页题联曰:“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可见他为研究曹雪芹《红楼梦》而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进入晚年,周汝昌先生的学术生命力仍十分旺盛。仅2005年这一年内,他就出版了9本红学著作,这是年轻学者都很难做到的。直到去世前的2012年春天,他还出版了《红楼新境》《寿芹心稿》两本红学新著。这样的研究效率与出书进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周先生5月31日去世前一天,还与儿子周建临谈了《红楼梦》中的两个创新观点,并赋七绝一首,成为95岁高龄之绝笔,建临先生也给父亲回了一首《浣溪沙》。这样动人的细节,足见周汝昌先生对《红楼梦》与学术之爱,诚乃雪芹之异代知音也。他要把更多学问留给后人,此种精神令人十分钦佩。可以说,周汝昌先生是一个为《红楼梦》而生的红学赤子,他的红学研究一直陪伴到他的自然生命停止那一刻。
周汝昌先生的去世是红学界的巨大损失,他是“新红学”的开拓者,同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的逝世是中华文化的巨大损失。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红学研究、古典诗词研究、书法研究的60余本著作和大量珍贵的书法作品,以及中华文化本体性的研究方式仍泽被后世。
2006年4月,我的老师梁归智经过两年的勤奋写作,终于完成了45万字的《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而有学术深度的周汝昌传记。此书以周汝昌的《红楼梦》研究为主线,从一个红学专家的视角,勾勒周先生80余载人生风雨,折射出一代学人的命运,展示了近百年来红学研究的风云激荡,揭示出周汝昌先生一种内在的文化精神。2011年11月,《红楼风雨梦中人——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由译林出版社再版,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作序,称曹雪芹是中国文学第一天才,而其评周汝昌为“中华文学第一天才之旷世知音”。
作者:安裴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