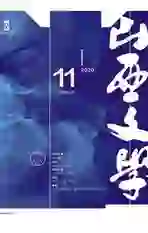林檎(外一篇)
2020-11-18张石山
1
我父亲兄弟七个,他是老六。爷爷1946年下世后,兄弟们分了家。所谓“夫死从长子”,奶奶后来就一直随大伯生活。
我在两岁上,被送回老家交奶奶看护,事实上是和大伯一家过在一搭。我和奶奶,加上大伯大娘,大哥宝山和妹妹莲英,一共六口人合锅吃饭。
大哥宝山,说来就是我在好多小说作品中写到的那个“宝山”的原型。大哥肩膀上是一颗扁骷髅头,脊背后扛着一个罗锅子。念书没有认下几个字,数得来的数儿也有限。我在小说里那样写,写的是实情。我的小说,县里有人看,村里也有人看。看过书的人笑着说宝山:看你兄弟把你描摹的!
大哥宝山满不在乎:我兄弟把我写到书上啦!你们想叫我兄弟描摹你们,还轮?不上哩!
宝山的姥姥家,和我们这道山沟隔一座分水岭,那村子叫个“罗掌”。有一回,大娘回娘家探亲,我和宝山跟着去的。就是在那个叫罗掌的小山庄,我平生唯有的一回,见到了林檎树,还吃到了几颗林檎果。
后来,住太原、上北京,南七省、北六省,跑過不少地方,我再也没有见到林檎树。活了七十年,吃过种种水果,包括如今设法网购,却再也没有吃到过林檎果。
2
我们村子所在的一道山沟,自西而东,从沟口到沟掌不过十里深浅。从沟口到沟掌自外而内,四里、七里、十里依次排列三个庄子,是为红崖底、张家庄和田家庄。沟外大户人家,早年着人来此开荒种地,这些山坡窐地叫做“庄子地”。所谓“田家庄”,说来是大户田姓人家的庄子地,这里就叫成了田家庄。庄子里的佃户其实没有一户人家姓田。至于张家庄,恰巧那佃户或是张姓本家,这个庄子上就全是姓张的。我的村子红崖底,靠着一座红崖建了村落,村名应该是“指地为名”。
三个村子,摆在一道沟里,沟里悬崖峭壁上生长些古柏,还有几处山泉,这道沟叫做“柏泉沟”。民国年间,区公所之下建行政村,我们沟里三个自然村合称柏泉村。村下分闾,柏泉村共分五闾。比如我大伯,还当过我们红崖底的一任闾长。
柏泉沟尽处,一道分水岭横亘。翻过分水岭那面,便是另一道山沟。那道山沟,叫做罗河沟。自北而南,也有三五个庄子,沟口通往县城方向。分开柏泉沟和罗河沟的分水岭,当地人叫做“田家梁”。
大娘的娘家罗掌,坐落在罗河沟的尽端,不过二十来户人家。要是翻越田家梁,我们红崖底和罗掌,相距也就十来里。如果走平路,从罗掌出到沟口,再从县城附近返回我们红崖底,那就有将近五十里地。
大娘做新媳妇的时节,乡俗还讲究坐轿。但我们家和大娘家,都是贫苦人家,便摆不起那样排场。大娘过门,连个牛车都没坐上,是骑着一匹毛驴子翻越田家梁嫁过来的。
今番大娘回娘家,依然是骑驴。1955年之前,还没有合作化,大娘走亲戚,骑的是我们自家的毛驴。我和宝山正在放暑假,宝山赶牲口,我是跟着串亲戚玩儿。1952年,红崖底村立起小学,宝山比我大五岁,十岁入学去念书。到1954年我正式入学读一年级,宝山还是一年级。宝山念书不沾弦,赶车摇耧使牲口却是天生好把式。一杆鞭子使开来,鞭梢子抽毛驴的左耳朵,十准打不住右耳朵。可就是大哥宝山这样的把式,翻越田家梁也傻了眼。
田家梁很陡,仿佛有曲折盘旋而上的路径,但柴草茂密,人们又不常行走,毛驴子就找不见个伸头处。好在我六七岁,个头小,柴火枝叶间隙能找见路子。我在前面牵驴,宝山在后边吆赶。大娘伏低身子,紧紧搂住鞍架。坡太陡的地界,我在前面使劲拉缰绳,宝山在后面扛着驴屁股。就这么,好不容易总算将大娘舞弄上山梁。
上了山梁,栽头去看,罗掌村尽收眼底。高低错落的窑洞院上方,有炊烟缭绕。如今回想,那该是一处深山好景致吧。小孩子时候,哪里有什么审美眼光。觉得宝山的姥姥家村子太小啦!让人有些瞧不上的感觉。
况且,从田家梁下到村子里,大大地发了愁。这面的山坡,更加陡峻。大娘吓得不敢骑驴,下来步行。大娘是那种“解放脚”,玉米棒子似的,倒也勉强能挪动。可是,那毛驴死活不肯开步走路。
山梁子这面向阳,没什么柴火,是那种干石头山岩。狭窄曲折不算,关键是没有崭成台阶,都是凸凹不平的石头疙瘩。钉了铁掌的驴蹄子,在上头一个劲打滑。我在前头使劲拖,宝山抡起鞭子抽,毛驴就是不走。还是大哥宝山看出毛病来了,原来毛驴不驮重,驴蹄子吃不上劲。结果,我们又把大娘弄上了毛驴。如果朝前骑驴,人往下栽,怕得很,大娘干脆来了个“倒骑毛驴”,脸朝后抱着鞍架。这回成了,毛驴蹄子吃上劲,总算迈步行走开来。
后来我还想,当年大娘嫁过来的时候,骑着毛驴是怎么翻越田家梁的呢?
3
我们老家,称呼姥姥是“姥娘”。宝山的姥娘,我跟着也是称呼姥娘。大娘和宝山,片片段段给我说起过关于这位姥娘的一些事情。加上我到过罗掌,这个姥娘的过往,我就牢牢记在了心底。
姥娘生有三个儿子,都是我大娘的弟弟。宝山称呼舅舅,我当然也是称呼舅舅。
有个三舅,在太原工作。我从来没有见到,只是听宝山说起过。有一年,宝山和大娘来太原,自然是在我父母这儿落脚。也去过他舅舅家,可是只待了短短两天。宝山讲,他那三妗子过于讲究卫生,不洗脚,不许上炕。我们柏泉沟自古缺水,哪里有什么洗脚的习惯?宝山和大娘看不得人家脸色,还是回我爹这里住着自在。
在罗掌村子里的,是二舅。二舅精精干干的,当着村长。记得二舅家的院子,大门朝东,西边三孔石窑是上房,姥娘住这儿。三间南房,二舅一家子住那儿。
大娘这回走亲戚回娘家,原来是姥娘病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老人在窑洞的里间炕上,病恹恹那么躺着。
宝山和我是外甥子,登了姥爷舅舅的家门,算是客人。二舅和妗子好生招待,不在话下。我那时小孩子嘛,院子里,窑洞南房,随便串着玩儿。串进南房,这就有了发现。二舅家的炕上,炕席乌黑残破不说,满炕上只有一床被子。被子倒是没有露棉花,看去实在破旧。除此而外,炕上没有什么铺衬,就是一领光板席子。
在我们红崖底,当年全家拢共一床被子乃至没有被子的人家也有,所以我是见惯不惊。好比我四伯,那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庄户人,他家炕上就一直是光板席子。1953年,我记事了,我爹给几位大伯叔叔们家家置办了里表三新的铺盖,我四伯四大娘这辈子才算躺上了褥子。记得四伯躺在被窝里,笑得合不拢嘴,自言自语说:嘿嘿!躺在褥子上,到底是绵绵的好睡哩!
吃罢晚饭,大娘陪姥姥住在窑洞里,我和宝山给安排到南房过夜。这时我才想到:满炕上一床被子,我和宝山黑来盖什么呀?
到了夜间,有了被子,原来是二妗子上邻居家借来了一床被盖。这般事体在山庄里当年常见,谁家来了客人,被盖不够使,找邻居本家借来就是。我和宝山伙着一床被子,被子不算新,比二舅炕上的破烂好得多。我和宝山都累了,好像脑袋一沾枕头,就睡着了。
谁知到了半夜里,半迷糊中觉得发冷,伸手去摸,身上没有了被子。一边,是宝山的光脊背;一边,暖暖的,是一只猫。我搂着那只猫,迷糊着又睡去了。
清晨,覺着身上暖暖的,听得地下有了响动,是妗子在操办早饭。我睁眼来看,变戏法一样,我和宝山的身上又有了被子!
这个被子戏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半猜半蒙的也闹清楚了。
大娘回娘家,二舅总不能让姐姐和病人姥娘钻一床被窝睡觉。穷人家,也得尽量讲究点儿待客的规矩。可是拢共借来一床被子,怎么办呢?那就只好拿一床被子来变戏法。
前半夜,大娘陪姥娘说话;我和宝山两个小客人,先盖被子睡。小孩子睡着了,将被子偷偷揭走,供大娘来用。于是,客人们总算都有了被子盖。免得让红崖底亲家人,说出什么来。天将黎明,大娘早早起炕,算是盖着被子整整睡了一夜。这时,再将被子变回我和宝山的身上,于是,两个外甥也都算盖着被子睡了一夜。
时隔多年,想起二舅家那个被子戏法,我都忍不住要笑。
4
宝山的大舅,他都没见过,我更是没有见过。
大娘选民登记的时候,我记住了她的名字是“王双玉”。大舅的名字,叫个“王九重”。一个沟掌山庄,看来人们取名字照样很讲究。
抗战年代,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根据地,我们老家盂县一带,属于晋察冀边区晋冀二分区。九重舅舅大约在1938年,就早早参加了八路军。自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宝山1942年出生,自然没有见过这个舅舅。
关于这个大舅,大娘断断续续说起来过。大娘不识数,说话也没有什么条理性和逻辑性,若干凌乱信息归拢起来,我渐渐记住一些大舅的简单情况。条理点儿来说,大概是这样:
九重大舅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回乡,村里得知他牺牲去世的消息,是在1951年。他死在了朝鲜战场。这么说,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据说,牺牲的时候,已经身任团长。
团长级别的干部,按照规定,尸骸也不得还乡,留在了异国。还是按照规定,家里得了三担小米的抚恤。三担小米,合600斤。说来是不多,不过,比起一般战士,到底还是不一样。一般战士,政府部门登记为烈士,家里被称作烈属。有的,抚恤几十斤小米,有的,村里得了消息,告知一下家里,就算了事。
早年间,老百姓从没听说过“抚恤”这样一个极其书面的词汇。按照大家自个儿的理解,往往就把这个说白了,叫做“血赏”。为国为民,流血牺牲,国家政府给予奖赏,好像也能讲得通。
大舅九重牺牲的消息,家人始终没敢告诉姥娘。区公所和二舅商量了一下,给烈士王九重风风光光办了个追悼会。三担小米折了价,请到吹鼓手娱乐班,在小小的山庄罗掌村,大吹大擂的, 热闹了一回。自家大门上,这么热闹,给姥娘解释说,是咱九重在部队上打仗立了大功啦,这是政府来给咱家道喜。当下,把姥娘算是糊弄了过去。
给九重贺功,给家里道喜,事实上开的是追悼会,这样的花招,可惜只能哄得了姥娘一时。罗掌村,又不是只有二舅一个人知道实情。人们风言风语,见了姥娘神色也不对,尴尴尬尬的。到底让姥娘猜中了事情的真相。她那儿子九重,不是打仗立功,是打仗死掉了。
姥娘猜中了真相,当下就疯了。
姥娘疯了什么样,大娘颠三倒四给我说过。
“他姥娘给疯了,疯了,实在怕人哩!他舅舅妗子,好几个人按不住。
“头发撕扯得一圪绺、一圪绺的,拽下来。身上的衣裳、裤子,脱得上下没一根线。鞋摱了,裹脚条子也摱了。
“光没拉达的,人家直是往山里跑。就那么疯跑,身上都是柴火拉的血道子。一跑好几天,谁也捉不住。
“还在山里叫唤,唱,也不知道唱的是些甚。叫唤哩,就是叫唤我家九重子哩……”
大娘给我叙说这些,说起姥娘的疯症,说起弟弟九重,也是一个劲儿提起衣襟抹泪。
大娘这回来罗掌沟探视姥娘,是不是因为姥娘犯病啦?我那时六七岁,也不很的确。
大娘探亲过后,过了一年,也许是两年?姥娘来过我们红崖底,住了一段。她是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亲家来了,我奶奶自是好生接应招待。三顿饭,两个老人一道用餐。说些家长里短,村情节气。
饭后,姥娘就在大娘那厢待着,盘腿坐在炕上,帮大娘做点针黹什么的。
有一天早饭后,我上大娘屋子里耍,宝山也在场。姥娘慈祥地冲我笑,和我说话。真是小孩儿家说话不知深浅,我突然就开口说道:
“姥娘,我听说我那个九重舅舅打仗死啦!”
姥娘本来微笑着,这时脸子大变,眼睛突然发痴,定定地看着什么地方,叹了一口气,病恹恹说:
“哦——人家你们都知道哇……”
大哥宝山一把刁住我,老鹰抓小鸡似的,将我拎出门。他压着嗓口冲我说:“这娃子,可不敢胡说!一下子给咱疯了,可咋闹呀?”
我觉得闯了祸,后悔莫及。屏住气去听房间里的动静。听得大娘絮絮叨叨劝慰,听不清说些什么。万一姥娘疯了,可怎么办呀?谢天谢地,姥娘总算没有发疯。
那天,我再没敢走进房间。到中午吃饭时节,给老人端饭,我都不敢再和姥娘对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姥娘。
一个山庄窝棚里的老妇人老母亲,知道儿子打仗死掉了,伤心欲绝,结果给疯了。一个头发蓬乱脱光身子的老太太,在山林间疯狂奔跑、吼唱呐喊,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形象,烙铁烙下印痕一般,刻在了我的童年记忆里。
5
在罗掌沟,姥娘家的院落坐西朝东,位于沟坡西侧。从大门出去,西坡、东坡可见高低错落的一些窑洞院。东坡那面,姥娘家的院子近边,是坐北朝南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格外引人注目的,就是当院里,并排长着两棵树。两棵树,一般粗细高低。多么粗呢,我和宝山两人才能合抱搂住。高度,估量有三四丈。树形直溜,枝杈不少,但树冠不算大,仿佛钻天杨似的。宝山告我说,那是林檎树。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林檎树,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果树。来到罗掌村,宝山的姥爷舅舅家,他有意要给我显摆,领上我大摇大摆的就去了那家院子。或许是姥娘她们本家吧,宝山嘴上呼叫着什么姥娘,一位大娘早从窑洞里迎出来。寒暄问讯了几句,宝山一个劲儿去瞅那林檎树。不等宝山开口,大娘指指立在窑洞屋檐前的一根长竿子,叫宝山自己动手,从树上摘取林檎果。
那竿子,有两丈多长,端头横着嵌了一个镰刀头。林檎树又粗又高,这件家什看来是专门摘取林檎果的。
也是我赶得巧,头一回见到林檎树,恰恰正是林檎果将要成熟的时节。够下林檎来,大娘笑眯眯地看我们吃。我这就记住了林檎果的样子和那果实的味道。
林檎,看那果实,应该和苹果属于一个科目序列。在这个序列里,果实从大到小,我看是苹果、香果、槟果、沙果、小果、海棠、柰子,最后就是林檎。而且,果实越大,把儿越短。
苹果,把儿一两公分长;林檎果,把儿有将近两寸长。苹果有拳头大,林檎果略逞橄榄形,也就小拇指头肚儿那么大个。
听那位大娘说,成熟了的林檎,色彩通红,吃起来又沙又甜。这时的林檎,尚未完全成熟,色彩倒是红绿相间,看着喜人,吃着却是酸中带涩,还微微有些发苦。
也许,是距离造成了审美,我想起平生唯一的一次吃到林檎果,觉得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可一而不可再的味觉体验。
六十多年时光过去,或者只剩下记忆如新。
我们红崖底村,我记事时,有百十户人家。如今剩下不到六十户,而且多是留守故园的老弱。半个村子的老屋,已然倾圮破败。想那深山更深处的罗掌村,更不知还有几户人家?
那合抱粗的两棵林檎树,那双双并立有如旗杆的林檎树,或许还在?
1
杏桃,这种水果,有的地方叫桃杏。我们老家叫做“桃篮篮”。
杏桃与桃子、杏儿、李子应该是同一种属。书上分类是蔷薇科李属植物。它的果核,有普通杏核大小,形状也接近,但果核表面,又逞桃核样子,分出许多细小花格瓣儿。单从果核样态,叫做杏桃十分准确得当。
我们整个红崖底村,拢共只有一颗杏桃。野生的,有一丈多高,树冠团团,长在村里于德明家的地边,是那家的私产。
我们村所处那道山沟,叫柏泉沟。沟底一道干河槽,夏季发山洪,属于泄洪道。通往沟外的大路,也在河槽里。河槽两岸,自然分出许多向阳山窐和背阴山窐。大小山洼,都有名号。比如向阳一面,依次有小红崖、榆树旮旯、麦秸掌、赵家窐、牛角掌等等。大些的山窐又分出若干小山窐,自然也都有名号。
盂县1947年土改,之前在麦秸掌有块梯田,是于家的地亩。根据老来规矩,梯田窐地都有明确四至。地边的山坡,其产权归属随土地主人所有。人们在地里挖点野菜,坡面上割点柴草,这个可以。地边的果树或成才树木,谁都不得染指。
包括开山取石,村里自古有专门的采石场。合作化之后,土地归了集体,山林土地,不知道是谁的。乱砍乱伐和随便开山炸石,于是屡禁不止。老百姓嘛,天然懂得物权法。无主的东西,我扛回家,就是我的。
在我记事时节,合作化之前,别家的田地,不能随便进去踩踏。长在野地里的果木,采摘个把果子尝尝可以,不能替人家收获。至于主家打过核桃、摘过花椒了,人们再去采摘一点残留,好比上收秋过后的大田里去捡拾遗穗,这个也允许。
于德明家的杏桃,我小时候上那山窐里挖野菜,半生不熟的果实,吃过几个。杏桃,一般人嫌其过于酸涩,我的口味,格外喜好吃酸。那杏桃的滋味,觉得另具特色,至今记忆犹新。
2
我们村的住户人家,让一道河槽天然分成南北两边。北边的正街,自南而北,从河槽一直通到红崖根底。
我家的四合院,在正街东边;街道对面,西边巷子里并排两座四合院,头一座院落,就是于德明家。两家院子挨着,我寻常会去和于家的小伙伴玩儿,对这个院里的主家情况十分熟悉。
红崖底村,张家是大姓。之外,于姓十来户,田姓三户,赵姓仅有一户。村人姓氏不同,同姓自然不婚,异姓结亲的不少。或许是历来通婚结为姻亲的缘故,异姓之间,也分出了辈分。比如,于德明就算我的爷爷辈。
这个于姓爷爷我没见过,早年去世了。他的老伴,如同古来村妇,人们不知其名字,按习俗我称呼“德明奶奶”。
德明奶奶比我奶奶年岁小一些,个头长得差不多。在女人里都算大高个,有一米七。脚呢,都裹得格外小,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比如我奶奶,出门去看她的老姐妹,一只手拄上拐杖,另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扭搭扭搭行进,三五丈一段路,要扭搭一頓饭时辰。
德明奶奶很少出大门,偶或露面,满面慈祥,扶着门框和人们打招呼。
突然某一天,她家大门上会围拢好多人,挨挨挤挤的,纷纷伸头看。大家都知道,这是德明老太太又疯了。小孩子家,心里几分好奇、几分恐惧,想看又生怕看见那样一个奶奶疯了的样子。
究竟忍不住好奇心,从大人们的腿旮旯间隙里,朝院里窥视。只见德明奶奶大白天的,手持一盏点着的煤油灯,在院子里旋风似的兜圈子游走。双腿直直的几乎不打弯,两只小脚“噔噔噔”地敲击地面。影影绰绰能看见她的脸,目光直愣、面容僵板,整个气氛森然可怖。
我到底不敢再看,慌慌逃离。
3
德明奶奶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水旺”,抗战年代当了八路军。听大人们念叨,说是打仗死掉了。从那之后,德明奶奶就得了个疯症。不知什么时辰或者什么人不小心提起,老太太就要疯魔那么好几天。疯魔过后,脚疼身子乏,在炕上病恹恹躺那么十天半个月。
她的二儿子名叫“虎旺”,是个盲人,我称呼虎旺叔。这个瞎眼叔叔和我父亲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对他的情况了解得就更多些。
自打阎锡山主政山西,发展现代工业,我们盂县大山里下太原来当苦力工的不少。按如今的说法,应该算是最早的打工族。盂县家,吃糠咽菜的,我爹的说法是:咱们那里的人,生就一副骡马骨头,能受!
能吃苦有力气,扛得动麻袋大件的后生家,农闲时节,奔太原府来找活儿,卖苦水挣钱。挣了钱,回老家买房置地娶媳妇。我爹十五岁扛长工,十七岁下太原来扛麻袋、干脚行,十八岁就当上了太原发电厂苦力们的大工头。当年发电厂的厂址在如今的小北门胜利街,苦力们零时搭建些土坯房子安身,这儿号称太原脚行的“北工房”。
我爹当着大工头,老家红崖底周边上十里、下八里的农家子弟,来这儿下苦挣钱的人不少。德明奶奶家,在村里光景算是富足户头,虎旺叔找的老婆,是我们张家的闺女水亮。水亮的父亲,大号张耧元,土改时划成了富农。由此反证,德明于家的光景够不上富农,但也算门当户对。因为土改,耧元家挨了斗争,土地田产被瓜分。丈人家光景吃紧,运动形势也怕人,虎旺叔就来太原北工房当了苦力工。
干了一年多苦力,这就赶上了解放战争打太原。太原城被包围,苦力们都出不了城,回不了老家。战事渐渐吃紧,阎锡山开始扩充兵员。城市被围,到哪里寻找兵源?只能在打工的苦力们身上打主意。有一天,虎旺叔独自上街,非常倒霉,遇上了抓兵的。不由分说,给抓进兵营穿上军装,成了所谓“常备兵”。等到工房里得了消息,我爹带人去说理要人,哪里还要得出来?一个长官甚至说:
不要再啰嗦啦!你们几个,身强力壮的,再不走,也抓了你们常备兵!
虎旺叔当了人家的常备兵,倒霉接着倒霉。大军围城,太原市供应几乎断绝。市民没吃的,部队也缺粮。中央军的飞机空投些大米,是所谓“红大米”。人们吃上红大米,加之没有蔬菜,结果不少人患上了夜盲症。如今说来,那是营养短缺尤其是维生素缺乏造成的疾病。
等到太原解放啦,虎旺叔的双眼也给瞎啦。好端端一个明眼人,不到三十岁,给半路瞎了眼。
我爹和虎旺叔,本村邻家的,又是工头,于是出面为虎旺叔搞了一回募捐。除了口头呼吁发动,还请人写了募捐文告,四处散发张贴。到我来太原读中学,还见过那麻纸写的文告。文告是请我爹租房的院子里一位同样租房的文化人写的,文化人名叫韩尔双,也是盂县老乡,在老家当过旧政府的区长。国共起了战事,从盂县逃来太原的。文章的句子我还记得一些,毛笔字也写得相当漂亮。
为之,我爹竟日说:要说文化人,我看韩先生算一个。要说写文章,我看韩先生是个会写文章的人。
——这个韩先生,过了不久,在镇压反革命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了。
闲话放过不提。韩先生文章写得好,我父亲人际关系也不错,结果给虎旺叔一共募捐了两千来斤小米。建国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发放小米代替薪资。一个科级干部,薪资48斤小米。两千多斤小米,相当一个科长四年的薪金。
然后,托靠老乡,雇了牲口驮脚,这才将虎旺叔送回了老家红崖底。
4
德明奶奶,大儿子水旺当八路军,死掉了。二儿子虎旺,上太原打工,人是回来了,一对儿眼睛瞎掉了。老太太遭遇的这叫什么事儿呢?
然而,事情还不算完,德明奶奶心头还有一个大牵挂。
我们红崖底一带,既然属于八路军管辖的边区,部队征兵的事情始终不断。只是八路军开初精兵简政,对兵员要求较高,数量也一直有限。到解放战争开始,才大力扩充兵员。德明奶奶五个儿子,按当时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虽然水旺牺牲了,她家还得出一个儿子当兵。三儿子来旺,年龄偏大,五儿子老虎还小,四儿子林旺年龄正合适,结果被抽去当了兵。
林旺去当兵的事情,发生在虎旺跑到太原之后。于是,当虎旺在太原当阎锡山的常备兵的时候,他的四兄弟林旺却成了打太原的解放军。虎旺患了夜盲症,开初并没有全瞎,曾经被派遣到前沿阵地守过碉堡。常备兵没什么训练,不怕,反正就是從碉堡枪眼里朝外打枪。四弟林旺,不知属于哪支部队,既然参加了打太原,冲锋陷阵的,朝碉堡里的敌人开枪扔炸药包。兄弟两个,两不见面,糊里糊涂的变成了打仗的对手。当然,也说不清两兄弟是否直接正面交过手,反正亲兄弟分别属于国共两个阵营打仗的双方就是了。
虎旺瞎了眼睛,总算活人活马回到了村里。林旺是死是活,家里却一直没有消息。
我在村子里记事时节,五六岁,也就是一九五二、五三年。见到德明奶奶发作疯症,就是这个时段的记忆。
按说,林旺当兵是死是活,应该有个结果。红崖底好几个后生参加了解放军,牺牲了的都很快来了消息。张有印、张成明,家里都成了烈属。于秋林、张清和、张贵成等好几个,也都来了书信。只有这个于林旺,一直得不到确信儿。
德明奶奶疯一阵、好一阵,就那样儿。
虎旺叔瞎了眼,他和老婆水亮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女娃娃名叫变香,和我同岁。男人瞎了眼,女人水亮这光景怎么过?好在当年民风淳朴,富户耧元又讲究做人本分,虎旺眼睛好着,成了咱的女婿,虎旺瞎了,耧元不能不当老丈人。家里地亩,耧元帮着耕种;烧柴吃水,兄弟来旺帮忙出力。日子就那么凑合过。
1955年,全国合作化,村里成立了农业社。家家自养的牲口归了集体,社里盖起了饲养院。虎旺叔就常年在饲养院切草。
给牲畜切草,用的是切草刀。两个人操作,一个人抱着青草或干草向刀床里负责擩草,一个人负责压刀把子。虎旺叔就是那个压刀把子的。长年累月切草压刀把,他的手掌全是老茧。手掌中间老百姓所谓长“通关纹”的地方,是挤压出来的筷子粗细一道老茧圪塄。
从饲养院到他家,虎旺叔走多了,也就渐渐熟悉。石板街,高低凸凹的,他走得如履平地。要是闲下来上别家串门,手里持一根棍子,点点厾厾的,也能找到门头夹道。村里金川老汉爱编顺口溜,有的段子还提到过瞎子于虎旺:
“于虎旺眼瞎腿快,厾厾打打就进来。”
虎旺叔的日子就那么勉強过着。他家老四林旺也终于有了消息。
原来,林旺参加过太原战役之后,马不停蹄又随着部队转战大西北,一路打到了新疆。仗终于打完,是不是可以解甲归田?结果是“自由不当兵,当兵不自由”,打到新疆的部队,改称新疆建设兵团。林旺活着,却留在了新疆。
为此,德明奶奶整天念念叨叨的:“那个甚甚,他咋就那么不说理?打完仗了,咋还不叫俺家林旺回来?”
新疆,遥遥万里。捎一封书信都不容易,人哪能轻易就回来?部队纪律,不许战士探家,生怕大家一去不返。多少年之后,到政策容许探家了,德明奶奶已经下世了。
老太太疯疯癫癫的,到底没能见上他牵心挂肚的四儿子。
5
1955年,合作化,村里成立了农业社。社员们都是下地挣工分,按定量分配口粮。德明奶奶跟前还有个小儿子老虎,十五六岁,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妈。
到了1958年,大跃进,成立了人民公社。村里男丁劳动力都抽调出去,有的去大炼钢铁,有的去修水库。一度时间,强行命令,六十岁以下、十岁以上,都得出动。有个任务,要从村里抽调几个人去静乐县修水库,老虎被抽上了。
德明奶奶不同意,说是死活不叫儿子离开盂县老家。村干部们有办法,说村里征兵任务也下来了,不去修水库,老虎就得去当兵。一说又要让这个小儿子去当兵,德明奶奶几乎活活吓死,只好听任人家派老虎去了静乐县。
静乐县在哪里?小山村的人,谁也不知道。我那时已经读五年级,出村跑高小,学了历史和地理,也闹不清静乐县在哪里。
小儿子老虎离开家,德明奶奶就又免不了犯病发作疯症。老太太实在老得下不了地,坐在炕上折腾。还是大白天点着煤油灯,手里来回舞弄,嘴里又唱又念叨:
煤油灯,见不得风,
老天爷爷你坏了心!
人们围拢在房门上朝里看,德明奶奶目光呆滞、面容僵板,旁若无人。
有的女人们知情,看见老人可怜,在那里抹泪;有的人看见稀罕,在那儿笑。有人甚至学扮老太太的腔调,在大街上唱“煤油灯见不得风。”
大跃进当中开始吃食堂大锅饭,大锅饭吃了不到一年,食堂倒闭。社里给人们分发口粮,我们村是一天人均二两五。
到1960年,村里开始流行一种“浮肿病”。得了这种病,腿脚肿得胖大,脸子面盆大小明光明光,哭和笑,都看不出表情,模样十分怕人。
德明奶奶,就在那个年头,得了浮肿病死掉了。
有人知道那是营养不足饿死了,见了村干部立即闭嘴,不敢说是饿死的。大家只能私下议论:德明老婆子五个儿子,“五男二女七子团圆”,结果是饿死啦!
对了,这篇短文的开头,我提到了杏桃。平素,那水果又酸又涩,没人吃它。赶上1960年那号年头,不等杏桃成熟,怕人偷偷采摘完了,虎旺叔让孩子把发青的杏桃都采了回来。
老母亲去世,停灵在正房当地下。在西房的屋檐下,我见虎旺叔嘴里咀嚼着一颗杏桃,瞎眼里扑噜扑噜掉泪。这场景,这画面,成了我少年时代又一段永难忘却的记忆。
【作者简介】张石山,1947 年生,山西盂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 《镢柄韩宝山》 《单身汉的乐趣》《母系家谱》《神主牌楼》等,民俗专著《洪荒的太息》《礼失求诸野》,电视剧本《兄弟如手足》 《吕梁英雄传》 《晋文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