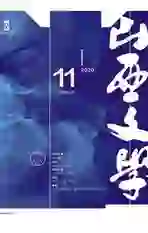珍珠鸡
2020-11-18于则于
1
我给刘晓金打电话,跟他说我找到新工作,不回新蔡了。他让我有空回去玩,我一直没回去,他便给我发语音消息,说我没良心,攀上高枝就忘了他们。他说话阴阳怪气的,像演员演电视剧,对着剧本念台词。而且“攀上高枝”这种话,也不像他会说出来的,就像我那时候离开,他送我到地铁站,竟跟我说“苟富贵,勿相忘”,都是从电视剧上学来的。他痴迷于看电视剧,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他瞅着一点空,就抱着手机不放。回去宿舍,更是能看整天整夜。每次都顶着黑眼圈和鸡窝头去上班,每次都被经理骂。我回他说,老子又不是麻雀,也没变成金凤凰,哪来的高枝。然后又发一条说,你还是少看点儿电视剧吧,小心哪天被开除了,到时候求我帮你找工作。
萍姐正好从卫生间出来,手上拿着梳子梳头发,问我跟谁发消息呢,又要找啥工作?我告诉她是以前的朋友刘晓金。他没工作了?没有啊,开玩笑呢,他有工作,干得好好的,我说。手机叮一声,我拿起看一眼,是刘晓金又发来一条消息。萍姐说,干得好好的,为啥还跟你发消息?我说,他就是想找我玩。有啥好玩的?她又说,我警告你,别把他们弄这里来,小心吓着毛毛跟小乔。我哦一声,表示知道了。等她又进卫生间去,我才拿起手机,把刘晓金发来的语音转成文字,很长,他说最近确实老挨骂,不过还不至于丢了工作。还是说让我有空去找他玩,末了说等我去了,给我看一个好东西。我回他一个嗯的表情。但接下去很长时间,我都没找到机会,刘晓金也没再给我发消息,我就忘了。
来上海三年,我换了七份工作。离开大姑父在的那家饭店,我在便利店当过收银,在商场干过导购,在公园做过保安。做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新蔡的一家浴场端饮料。那里工作简单,常年不用穿太多衣服,又有好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子,我们处得不错,常一起喝酒。但那里太偏远了,天气再好也看不见陆家嘴的“三件套”,感觉不像是在上海。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市里的酒吧上班时,我有些犹豫,但听说只是陪客人喝酒聊天,不用干别的,就答应了。在酒吧里,我认识了萍姐,然后就有了现在的工作。
萍姐是酒吧里的名人。还没见过真人呢,就先听到不少关于她的传说。传说她有钱,出手大方,又为人豪爽,乐于助人。跟萍姐喝酒时,不管是谁,只要跟她说遇到了困难,需要几百块钱什么的,她都会不管真假,随手就给。至于为什么,有传说她是几十家连锁理发店的老板,挣的钱都像是抢来的,所以花起来也不珍惜。也有传说她没结婚,也没孩子,钱留着也是废纸,不如花光。听传说时,我以为萍姐会是武侠小说里江湖奇女子一类的形象,终于见到了,才发现不过是普通的中年女人。脸涂得粉白,唇抹得血红,眉毛也拔去了,又用眉笔在上面画了很细的一道。能喝酒,喝得开心,大笑起来,露出满嘴的牙龈肉。要不是浑身上下戴满金的铂的首饰,珠光宝气逼人,我真不敢相信她就是传说里的那个人。不过在那种场合,还能指望萍姐是怎样的人呢,皇后一般高贵大方、端庄有礼吗?那样的话,估计没人敢靠上去。
萍姐来得不是很勤快,每周一次或两次,来了,都会有一堆人迎上去,等着她点。她点好了,剩下的人也还在她身边磨蹭,不急着走,说不定就有机会捞点儿好处。我虽然个子高,有力气,但因为是新人,根本挤不到她跟前去,只能在外围看着。最多是等她眼角的余光扫过来时,按别人教我的,殷勤地笑着点头。
我真没想到萍姐会看上我,专门让经理把我带到她跟前去。她身边已经有一个男孩子了,经理推推他的肩膀,他不情愿地向旁边挪过去,空出座位给我。经理让我叫萍姐,我叫了一声。经理说,这么干巴巴的干吗,萍姐不是外人,你得热情点儿。萍姐笑着不说话,等经理走了,才转过脸来,对我笑笑,让我坐。我没敢全坐,只屁股在凳子上挨一点儿边,这样好随时站起来。萍姐再喝一口,杯子里的酒没了,我赶紧给她倒上。动作太大,差点带翻旁边的杯子。旁边的人呀一声叫起来。我又赶紧赔着笑,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也跟萍姐说对不起。萍姐说,你们经理说你笨,不懂事,看来还真是呀。我挣了一个大红脸,不知道她是不是嫌弃要赶我走,那样不仅要挨经理骂,也会被其他人笑话。于是便没敢再说话。她却问我怎么不说话了。我回答说,我怕说错话,又惹您生气。她忽然笑起来,用手点了点我胸口说,我又不吃人,你怕啥。我也跟着她笑,混了过去。
萍姐其实挺随和的,没什么架子,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她。那天晚上,她一直让我陪着,问我是哪里人,以前在哪里上班,怎么到酒吧来的等等。这些是每晚陪客人喝酒,他们都会问的,我已经学会了一套说辞。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萍姐说的,比跟其他人说的要多。甚至连我这些年受过的委屈,也跟她说了,她不仅没生气,反而安慰我。她也跟我说一些过去的事,刚来上海时候怎么艰难创业等等,我和旁边的人都听得唏嘘不已。后来,她喝多了,去卫生间吐完,回来时歪斜着身子,几乎没法走路。我扶她到外面醒酒,在旁边的店里给她买热豆浆喝。她很惊讶,问我为什么要喝豆浆。我跟她解释,平时我喝多了酒,吐完,觉得胃难受,喝杯热豆浆就舒服了。她才接过去。
下一次,萍姐再来,跟我说喝热豆浆果然有用,回去没那么难受。我跟她说,其实不仅是热豆浆,喝完酒,只要吃点热的东西都有用。于是那以后,每次喝完酒,她都拉我一起去吃馄饨,或者面条,吃完才打车回去。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胃不好,去医院,医生跟我说的。以前没喝那么多酒不觉得,在酒吧喝酒多了,胃便老是痛。医生还建议我换个工作,我也想换,但临近年底,到处不招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就耽搁了。医生说,你这样喝下去,迟早要出大事。果然被他说中,没多久,我就因胃出血又去了医院。
要手术,医生让我打电话给家里人。我不想让爸妈知道,就打给在上海的大姑和大姑父。大姑忙得走不开,大姑父来了,教训我一顿,丢下几百块钱又走了,说手术那天再来。手术那天,他却没来。估计是忘了。醫生说手术要麻醉,手术后没有人陪不行。我便拜托酒吧的一个同事,他那天休息,答应陪我到麻醉醒来。麻醉醒来的时候,天正是黎明,窗户开着,我先看见外面淡青色的天,然后才把头转过来,看见病床前的人。却不是同事,是萍姐。我没想过会看见她,再加上她脸上化着很浓的妆,十分怪异,我吓了一跳。她冲我尖声说,哟,不容易啊,终于醒了,你再睡下去,你姐的腰都要断了。她已经在病房里坐了三四个小时。
萍姐走后,我问同事她怎么来了。同事告诉我说,萍姐前一天晚上去酒吧了,去的时候已经是凌晨,而且喝得很醉,非要我陪她去吃馄饨。知道我住院,便买了馄饨,打车到医院来找我吃,在病房里吵吵闹闹的,弄得医院保安都上来了。馄饨呢?我问同事。他说,没了,我吃了。又问我说,你饿了?可医生说不能吃东西。我不饿,只是觉得不可思议,想亲眼看看馄饨,证实一下。
萍姐给了我五千块钱红包,我不要,她说,反正你以后也不能在酒吧干了,到理发店来吧,就当是预支一个月的工资。我怕她会觉得我不知好歹,就同意了。出院后,我拎着行李,到萍姐的理发店去报到。走的时候,酒吧的同事说我这是卖身报恩,我笑笑,没理他们。但萍姐的理发店根本不缺人,我进去,什么也不会做,每天只能到处看看,跟人闲聊天。想拎起扫帚扫扫地,立即就会被抢过去,说这不是我干的活。几天下来,我才明白了,他们都没把我当员工,而是当成小老板了。我想让萍姐跟店里的人说一声,我只是来打工的,跟她没什么特殊的关系。但又怕越描越黑。萍姐给我一个月的工资,我干满一个月,辞职就是了。我计划还回新蔡去,就给刘晓金打电话。他说等天再冷一些,浴场客人多,肯定要招人的,让我放心。
理发店多,我在的这个店,萍姐隔几天才来一次。好像是她第二次来,问我身体恢复得怎么样。我已经没事了,跟她说过,又跟她道谢。她让我不用谢,好好干活就行。我正好趁这个机会,跟她表示理发店没有我干的活,恐怕干不下去。她想了想,说再看吧。临走时,她问我会不会开车。我会开,以前在老家也帮人开过货车,技术还行。她便让我开车送她回去。她不喜欢开车,又不愿意老是打车,路上跟我抱怨。我说,你请个司机呀。她沉默一会儿说,那就请你吧,反正你也不想在理发店干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回话,她就又说,你不说话就算答应了。走的时候,她让我把車开走,停在理发店,要用车,她再给我打电话。
成为萍姐的司机以后,进出她家的机会就多了。她家在一个比较旧的小区里,但房子是复式,楼上楼下两层,装修得很豪华。我习惯了住宿舍,跟人挤在低矮的小房子里,到她家,难免露出由衷的喜欢,不停赞叹。萍姐似乎很满意我的表现,一直问我喜不喜欢,想不想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自然点头如捣蒜。但我知道她也就说说,所以并不奢求。萍姐用车不是特别多,我拿她的钱,却不干多少活,觉得过意不去,便瞅着机会帮她收拾收拾屋子遛遛狗,干点杂活。有时候她要求,也做顿简单的饭,跟她一起吃。几个月以后,天渐渐冷了,下雨下雪的,萍姐看我不方便,提出让我住到她家里去。她说总没时间管毛毛和小乔,它们既然喜欢我,我就来照顾它们吧。我同意了。毛毛跟小乔是萍姐养的两条狗,一条是金毛,所以叫毛毛,另一条是秋田犬,不知道为什么叫小乔。
毛毛和小乔确实喜欢我,我住进来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和它们在一起,比萍姐跟它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多。萍姐其实挺忙的,因为生意上的事,要到各个地方去。又有一堆朋友,有钱的家庭主妇、健身教练、开书店的、练瑜伽的,男女什么人都有,她要跟他们打麻将做美容洗桑拿,或者跳舞去,上酒吧去,一周七天,天天有安排。偶尔她也带我一起去,但大多数时候,都只让我开车送她到地方,然后在外面等她。或者是结束时给我打电话,我再去接她。等她的话,有时候要几个小时,我没事干,只能坐在车里玩手机。回到家,还要帮她端茶倒水拿衣服拿鞋,其实挺累的。但既然我都觉得累,想想萍姐,她管店,还这么多应酬,岂不是更累?刚来上海时,我大姑父跟我说,能在这个城市活下去的,个个都是可怜人。那时候我不理解,现在看来还真是。
2
直到五月份,萍姐又要出门到外面去,嘱咐我看好毛毛跟小乔,我才突然想起刘晓金,打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空。他这段时间是夜里上班,白天睡觉,而我只能白天去,他当然有空。于是等把两条狗遛好,牵回去,我就给它们都拴上了链子。它们不愿意被拴,愤怒地叫。我安抚它们一会儿,又给它们放足了食物和水,省得真饿着,叫太响,被人听见,告状到萍姐耳朵里。不过我把窗户也都关上了,好隔音。
新蔡那个地方,地铁不能直达,我又换公交车,折腾快两个小时才到。中间的时候,刘晓金睡醒了,发消息跟我说别来太早,好让他多睡会儿。等到地方,我看时间,已经是下午一点多,算起来,他也睡了六七个小时,应该是起来了。但推门进去,他睡得正香。我把手伸进被子里,摸进他的腋窝,想把他咯吱醒。他受了惊,胳膊向里缩,夹住我的手,反而弄得我生疼。等抽出来,我一巴掌打在他身上,骂了一句操。他坐起来,讪笑着说,我以为你下午才来呢,没想到这么快。妈的,你是不是睡傻了,早就下午了,太阳都快落山了。他慌忙去摸手机,手机黑屏,应该是没电了,他急得从床上直跳下来,光着脚朝门口跑,要到外面看是不是真的太阳快落山了。我在他身后笑起来,他才停住,知道我是故意吓唬他。被你吓死了,他说,我还真以为睡过头,上班又要迟到了。他回到床上,摸到手机,嘴里说,我早晚要把这破手机换了,动不动就没电,设了闹铃也没用。说完,在床边地上捡起充电线,把手机连在电源上,开了机。我骂他说,你是拉不出屎怨地球没吸引力,一定是你看电视剧把手机看没电了,怪不得手机。他笑笑没回答。我让他起来。但他要等手机充点儿电,要不然等会儿出去请我吃饭也没法付钱。说着又打开了电视剧。我把手机抢过来不让他看,你这样能充个屁电!他抢一下,没抢到。我再催,他才起来,趿拉着拖鞋到外面去刷牙洗脸。他还是那么瘦,快一年没见,竟没什么变化。我环顾四周,看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变化。
这个地方是浴场地下室,车库旁边隔出来的一个房间,窄,却很长,大约竖着占三四个停车位。里面除了几张上下铺的床,其他什么都没有。外面有一个水龙头,可以刷牙洗脸,不过没有厕所,就也在那里小便。地下室空气不流通,小便的气味散不出去,臊得很。我以前在这边住的时候,还买过檀香回来烧,弄得真跟公共厕所似的,不过管用。我搬走后,他们肯定就没人买过了,要不然也不会味道这么大。
刘晓金洗好回来,我问他怎么这里就他一个人住,其他人呢?他说还有一个,这几天请假回老家去了,还没回来。他指给我看里面一张床的上铺,上面铺着一领席子。但也就只有一领席子,枕头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睡的。是谁?我问他。他说,新来的,你不认识。原来那些人呢,都走光了?我又问他。他说,嫌这里不是人住的地方,都搬出去了。那你怎么不搬出去?我不是人呗。我笑了下,然后说,你现在还真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你不是要给我看一个好东西嘛,是啥?对啊,我差点忘了,是要给你看一个东西。他打了鸡血似的激动起来,又说,不过要晚一点儿才行,我们先去吃饭吧。他弄得神神秘秘的,不说是什么,我也就故意不问他。终于吃饭的时候,他忍不住,跟我说好东西是在别墅区那边。肯定是你没见过的,你要不要猜猜是什么?像我们这种人,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要一个个猜,猜到明年也猜不完。他便又说,算了,你肯定猜不着,反正等会儿看见就知道了。
别墅区挨着一个公园,走过去大约十几分钟。以前我们上晚班,下午睡醒,就常去那边走走,好散困。别墅里住的都是有钱人,那边能有什么好东西,我还真猜不出。不过也没太大兴趣。在这个城市里,再好的东西都是别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本来就是别人的城市,我们到這里来,不被赶走就不错了。吃完饭后,刘晓金说最好再晚一点儿,不过现在差不多也可以去了。太阳出来,有点儿热,但他起劲,又没其他事做,我也就跟着走了。
别墅区的房子,外面都刷着黄色的涂料,看上去像山上的庙,就差写上“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了。如今在太阳底下照着,更是闪闪发光。我用手挡在眼睛上,问刘晓金到了没有。他说到了到了,马上。可再朝前走,他却又把我拽回去,说走过了。我骂他一句,他把手指放到唇边,示意我小声一点儿。这里的保安很烦,他说。然后就在围栏边蹲下去,手指着让我看。围栏后是常见的灌木丛,其他的我什么也没看见。你到底要我看什么?你看呀,蹲下来一点儿。我再蹲下去一点儿,从灌木丛根部的空隙中间看出去,才看见了,原来是一只灰色的鸟。个头很大,跟只鸡似的。
刘晓金你他妈的有病吧,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一只灰不溜秋的野鸡,头上还长一个瘤子——嘘!嘘!他左右看着,似乎怕什么人看见。
你仔细看,那不是野鸡,是珍珠鸡。
刘晓金按着我的肩膀,让我仔细看,我便又蹲下去一点儿。确实不是我见过的野鸡,尾巴不够长,而且除了头上的红和蓝色,身上全是灰色有点儿泛蓝的毛,上面布满白色的圆点,是有点儿像珍珠。
漂亮吧?刘晓金问我。
挺漂亮的,你刚才说叫什么,珍珠鸡?你确定这是一种鸡,而不是什么鸟?
对,珍珠鸡就是外国的一种鸡。
我还想再看一下,但刘晓金突然站起来,让我快点儿走。怎么了?我问他,他也不答。直到走过别墅区,到公园门口,刘晓金拉我拐进去,才放松下来。我们就像两个被人发现落荒而逃的贼。
你跑啥呢?我问他。
他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然后说,你不知道,我刚才看见有个人影晃了一下,以为是那个保安。我觉得他盯上我了,只要看见我来,就像赶小偷一样赶我。
我知道他一向胆小,不会主动招惹别墅区的保安,一定是经常跑来,所以才被保安盯上。但就算是一只稀罕的鸟,他又何至于这样。问他,他却反问我说,你不觉得很漂亮吗?是很漂亮,可这算什么理由。他说,很漂亮就是理由呀。
公园里有人练剑,我们站着看了一会儿,但练剑的人动作奇慢,像电影回放,实在没意思,我们就走了。边走边又聊了会儿珍珠鸡的事。刘晓金告诉我,那里是某户人家的院子,一定是他们买的宠物,屋子里没法养,所以才用网围起来,养在院子里。说到宠物,我便跟他说了毛毛和小乔,说我每天遛它们,给它们捡屎,像伺候王公贵族一样伺候它们。他听完后说,可惜我没这个命,爹妈没给我像你这么好看的脸,要是有人包养我,别说捡屎,吃屎我都愿意。我在他背上拍一下,心想他是把我当小白脸了,便又骂他一句,他没还嘴。
3
毛毛和小乔也许是不习惯拴链子,平时都不会在屋里大小便的,那天我回去,却发现地上被它们撒了好几泡尿。而且关着窗,味道散不出去,屋子里乌烟瘴气的。萍姐虽然会半夜或第二天早上才回来,但我还是赶紧把毛毛和小乔解开,开了窗,拿拖把拖干净地,带它们出去遛一圈。等回来,发现还有味道,又撒了许多花露水。萍姐回来,问我怎么那么重的花露水味道,我跟她说夜里有蚊子,我被咬了,所以涂花露水。她斥责我说,平时都没有蚊子的,一定是我没关好纱窗,所以才会让蚊子飞进来。我由着她说,没辩解。她每隔段时间都会一个人出去一趟,住一夜,或者不住,去哪里我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回来的时候往往都心情不好,我才不想招惹她。而且她看上去那么疲倦,洗完澡,直接上楼就睡了。睡醒,已经是晚上。我问她要不要吃东西,她不想吃,只想喝咖啡,我便做了一杯给她。她很快喝完,把杯子还给我。我拿去楼下厨房洗。水声中,我听见她也下楼来了,似乎是找东西,找到后又上去。过程中一直在打电话,喊人出去喝酒。我故意在厨房多耽误一会儿,出去时,她差不多已经化好了妆。出门,她不说让我送她,我也没问什么。
真正接触,我才发现萍姐没那么简单。她其实很严厉,我以为我了解她,但我们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以前在酒吧里,她经常跟我们调笑,住进来,却不喜欢我多嘴,也不喜欢我没规矩。她交代我说,不该动的东西别动,不该说的话别说。我故意问她什么是不该动的?又在她胳膊上摸着说,这里是不该动的吗?这里呢?还有这里——她猛地打在我手上,严肃地说,这些地方都可以动,但你话太多,以后不要这样。我的手被她打疼了,抽回去放在嘴边呵着,听她这样说,觉得委屈,便没回答。她却追问我听见没有,我小声说听见了。她说以后听见了就哦一声,我只好又哦一声。她这是给我做规矩呢。那以后,我看见她给毛毛还有小乔做规矩,东西要吃干净,水不要洒得到处都是,脚没擦干净不准上楼,不准在房间里疯跑。不听话就会挨打。是真的打,手起手落,看着不怎么样,却真的疼。两只狗每次都被她打得汪汪叫唤。狗傻,犯过的错误还会再犯,挨过的打也还会再挨,我不是狗,懂得举一反三,她说出来的话学会了听,她没说出来的话,也学会了看眼色行事,处处讨她喜欢。终于,她开始夸我机灵,说我到底上过高中,有眼色。
萍姐不回来,我也不敢睡,怕她打电话要我去接。终于,凌晨时分电话响了。不过不是我的手机,是房间里的固话。萍姐的朋友送她回来,到小区门口了。我出去接,见萍姐喝得烂醉,乱喊乱叫。我费很大力气才把她拖进楼道,上了电梯。我还想拖她去浴室洗澡,但没成功,只好接了水给她擦脸。她安静下来,让我擦完。我以为她睡着了,便没有立即去倒脏水,而是坐在床边看她。擦净脸上的妆,萍姐其实挺好看的,或者说,比化上妆更好看,至少更真实。她老是说自己老了,又吃药又打针的去做保养,但仔细看,连根皱纹也没有,当然也是因为保养得好。她有多大岁数?够四十吗,或者四十多了,我也弄不清楚。
你看啥呢?她突然这么问一句,吓我一跳。原来是醒着。萍姐真好看,我说。她突然又不说话了。
送萍姐回来的伊娃,是她朋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她小时候在法国长大,伊娃是常见的法国名字。我问过她中文名字叫什么,她说她父亲从没想过他们有一天会回国来,所以没给她取中文名字。我问她身份证上的名字是什么,她姓方,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方伊娃。说完大家都笑,我便也没觉得尴尬,只是不知道该叫她什么,伊娃姐?方姐?但她只让我叫她伊娃,她说外国人都是这么叫的,年纪再大,都还是叫名字。
伊娃是画家,经常会有一两幅画在某个地方展出来,她都会带我们去看。在展览上,我听到有人说她的画源自一个什么什么画派,名字很长,我听不懂,也记不住。她在法國长大,在法国学的画,当然是源自法国的画派。伊娃经常画我,有时候是开玩笑地,吃饭的时候在餐巾纸上画,或者趁我看电视时,在拆开的烟盒上画。有时候则是很认真地,带了本子,让我端坐着摆姿势,几个小时不许动。她说我的长相有异域风情,高面颊,深眼窝,所以很入画。她给我看过手机上存的一张画,是另一个在法国学画的中国女画家画的,名字叫什么良,我忘了。画的是坐着的男人,一只手搂着腿,一只手撑在地上,眼睛看着前方。她说我很像画里的男人,但那人分明是外国人,留着络腮胡子,我脸上一根胡子也没有,完全看不出哪里像。但她非说像,还让萍姐看,萍姐瞟了一眼,说她不懂这些,不知道。她让我学画里的姿势坐在地上,拿了本子画,但画半天又说感觉不对。后来终于找到原因了,画里的男人光着,而我穿着衣服,所以感觉不对。她让我脱掉衣服。我脱了上衣,她又让我脱裤子。我不好意思脱。她让萍姐跟我说,萍姐回答说,你们玩,别带上我,我不管。说完就站起来去卫生间了,留下我们面面相觑。
伊娃竟然把一幅画我的画拿去参加了展览。在那幅画上,我脱光衣服趴在沙发上,侧着头向外看,前面是一株绿色的植物,正好挡住下半身。画不是在萍姐家画的,不仅画上的沙发我没见过,而且画上的我,浑身肌肉饱满,粗野有力,也不是真的。我没脱光衣服让她画过,看见这张画,就觉得挺好玩的,没多想。倒是伊娃,专门过来跟我和萍姐解释,说是画着玩的,没打算展出,是他们非要她送一幅新的画,她手头又没别的画,所以才拿出来。萍姐听着,没说话,伊娃问她不会生气吧?萍姐说,你又没画我,我生哪门子气。伊娃说,真生气了呀,小气鬼,大不了以后再画他,我付你租金。说完笑起来,又故意去挠萍姐。萍姐忍不住,终于也笑了。我也跟着笑,没仔细想她们话里的意思。回去路上,萍姐沉默着不说话,我憋不住,起了话头说,伊娃真有意思,画我又不是租房子,还要付什么租金。萍姐没吭声,我便又说,再说付钱也应该付给我吧——好好开你的车,萍姐突然打断我说。她语气里带着不耐烦,我以为她是累了,不想说话,就住了嘴,认真开车。
但回去以后,萍姐仍对我爱理不理的,态度很怪。洗完澡,我问她饿不饿,要不要做点儿东西吃,她也没理我,直接就上楼去了。等再下来,已经化好妆换好衣服,又要出门。她去门口换鞋,我跟在她身后,靠墙站着,问她说,这么晚还去哪里啊?她不回答,我只好去取车钥匙,也走过来换鞋。但我不想再出门了,就试探着说,还去酒吧吗?这么晚,要不别出去了吧?她直起腰,转过来看着我,半天说,你算什么东西,也来管我。我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愣在那里。而她,打开门出去了。
我脱掉穿了一半的鞋,赤着脚走到沙发上坐着,深吸几口气,认真想这都是怎么回事。萍姐难道是疑心我跟伊娃有什么?这不可能呀,她应该知道的,我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伊娃每次来,她都在,我跟伊娃做过什么,她没有不知道的。那她生什么气?毛毛和小乔走过来,围坐在我旁边,我靠着它们,心里才没那么慌了。以前萍姐也生过气,但从没说过这么重的话。我算什么东西?我问毛毛和小乔,它们都抬头看我,意识到与它们无关,又低下头去。我继续跟它们说,我算她的司机啊,还算厨师、清洁工——然后我突然明白了,司机厨师清洁工,这些我都是,而我更是萍姐养的小白脸。伊娃说要付给萍姐钱什么的,就是这个意思,她把我当成萍姐的私人物品了。还有之前酒吧同事说我卖身报恩,刘晓金说我被包养什么的,看来不止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更重要的,是萍姐自己也这么觉得,所以才会生气。
我被这个想法震惊了,以至于就这么坐在沙发上,动也不敢动。但转瞬就想到,我过这么久才明白这一点,也是够迟钝的。说实话,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我也曾有过一些想法,担心别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但我并没有白拿萍姐的钱呀,我给她开车,给她收拾屋子遛狗做饭,整宿整宿的等她回来,并不比以前在浴场或酒吧上班时轻松。再说我也是真心感激萍姐对我好,我做手术,亲姑妈都不来看我,她却能忍着酒醉顶着残妆,在我病床前坐几个小时。我看她孤单一人,生活混乱,也是真心想照顾好她。我以为我们至少是朋友,现在看来,都不过是一厢情愿。
眼泪在脸上变得冰凉,我才醒过来,胡乱擦了一把。手放下来,正好落在毛毛嘴前,它伸舌头舔了几下。它的舌头是温热的,给了我一些安慰。我低头看它,又看看小乔,在萍姐眼里,我大概跟它们没有区别。狗就算付出自己的一生,又能换回来主人的几分珍惜?
我不是狗。
4
我在刘晓金的床上睡了很久,一直做梦。醒的时候发现他坐在旁边,拿着手机看电视剧。他跟我说,你真是够能睡的,叫都叫不醒。我问他我睡了多久,他才放下手机,算着时间说,昨天你来的时候我才刚睡,被你吓一跳,然后我起来去上班,到今天下班回来——差不多一天一夜吧。真没想到,竟睡了那么久。出什么事了?刘晓金问我,昨天你跑过来,倒头就睡,问你也不说话,把我吓得跟什么似的。我回他一句没事,然后就从床上起来,到外面的水龙头下去小便。我一边尿一边开水龙头冲水,尿了足有两分钟。我洗了手,又把手捧起来,接水洗脸。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似乎在水声中听见了笑声,萍姐的笑声,伊娃的笑声,笑得我耳朵里面痒。再睁开眼,用小手指狠狠地掏了掏耳朵,才觉得好些。刘晓金也出来小便,扒了裤子,就站在我旁边尿。尿完,抖干净,跟我说,我困得不行,要睡会儿,你等下走吗?我已经无处可去,一时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便说,你先睡你的,别管我。他犹豫一下,然后说好,就回去了。我在水龙头前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才进去,他已经睡着了。我找到衣服,蹑手蹑脚地穿上,朝外面走。
天气竟出奇的好,阳光很亮,没有风,头上的天,蓝得像伊娃的画,一朵云也没有。一瞬间,我愣在那里,两只脚被固定住了似的,不知该朝哪里去。肚子咕噜噜叫起来,我想管他娘的,先吃饱饭再说,然后脚才走得动。
我吃完饭,沿着街走很远,觉得热,又折回来,到公园里面坐着。坐了很久,才站起来,离开公园。
我去超市买了一支牙刷。看见水果打折,又买一把香蕉和几个苹果。
刘晓金还睡着没醒,我把香蕉和苹果丢在旁边空床上,拆了牙刷,到外面水龙头下刷牙。我刷得认真,按着不记得哪里看来的刷牙方法,把牙齿的外面、里面和上面都认真刷了一遍。漱口的时候,发现流了血,和水混在一起,呈淡红色。我却一点儿也没觉得疼。
我剥一根香蕉吃了,然后就坐在刘晓金的床上,靠着栏杆玩手机游戏。怕吵醒他,我把游戏的声音关上了,玩了一局抬起头来,才突然发现房间里安静极了。所以听见那细小的扑簌声响起来时,我吓一跳,以为是老鼠。但马上又想起来,上次来的时候,刘晓金曾跟我说,这里还住着另一个人,声音应该是他发出来的,便没再当回事。扑簌声却一直没停下来,并且夹着奇怪的唧唧声,似乎不像睡着的人发出来的。我才觉得奇怪,下了床,举着手机向里面走。在最后一张床上,下铺的蚊帐里面,我看见一个圆滚滚的黑影在动,真是个大老鼠。我赶紧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进去,才发现不是老鼠,而是只鸡。珍珠鸡,我想起来刘晓金曾告诉我的这个名字,然后立即想到,这就是别墅区的那只珍珠鸡,刘晓金把它偷了回来。
和上一次看到的相比,眼前的珍珠鸡十分狼狈,身上的毛掉得一块一块的,有些地方甚至露出了皮肉。羽毛上珍珠一样的白点沾了灰,变得很黯淡,头上朱红色的冠子也破了几处,流血干结成黑色的疤。也许是灯光的干扰让它有些烦躁不安,在蚊帐里快速地走来走去,叫的声音也大起来。我想凑近看清楚,却突然闻到一股恶臭,是鸡屎的味道。刘晓金在床板上铺了一层塑料布,鸡屎积在上面很多,应该是很久没清理过。我怕自己呕出来,就没再继续看,关上手电筒走开了。刘晓金把这里弄得,还真不如街边公共厕所干净。
下午四点多,刘晓金睡醒了,我问他珍珠鸡的事,还真就是别墅区那一只。我继续问他怎么弄回来的,他不愿意跟我说详细经过,但听得出,是花了不少力气。至于没清理的鸡屎,他说他是故意的,为的是把住在这里的另一个人赶走。而那人竟真的搬走了。我骂他鬼主意多,又骂他懒。等洗好脸,他走到里面去把珍珠鸡捉出来,又不知道从哪里抓了一把玉米,喂给它吃。你怎么知道珍珠鸡吃玉米?我问他。他说,鸡啊,当然吃玉米了。他又说,珍珠鸡也吃蚯蚓什么的,不过不能多喂,会撑死的。我说,废话,喂啥都能撑死,人吃多了也能撑死。我想到自己,萍姐的出现就像一大块难以消化的食物,卡在我的喉咙,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如果她从来不曾对我好过,或许我不会这么难受,但人终归是要认清自己,萍姐那样的人,又怎么会和我成为朋友。
他说,不是的,你不知道。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小时候的一件事,大概是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他们一个邻居,不知道从哪里弄來一只珍珠鸡,说是外国的鸡,稀罕得很。他们全村的人都跑去看,像看外星人。可惜的是,他们不懂,跟着邻居家的儿子,天天抓蚯蚓、小鱼什么的喂珍珠鸡吃,没多久就把珍珠鸡喂死了。原来你小时候就见过这破鸡,怪不得你这么喜欢,听完后,我说。他说,是呀,就是这么喜欢。他说着还捉住珍珠鸡,拉开翅膀,让我看翅膀下的毛。问我说,是不是很漂亮?漂亮个屁,掉毛的凤凰不如鸡,掉毛的鸡不如麻雀!我随口想到这句话就说出来了,说完才觉得好笑,刘晓金跟我一起笑起来。
刘晓金问我怎么还不回去。你那个老阿姨,怎么舍得放你在外面住?老阿姨,我苦笑一下,没反驳他。他再问,我才说,我跟她吵架了。把你赶出来了?我自己走的,不打算回去了。他小心地问我,吵得很厉害吗,真的回不去了?我点着头说,反正我先在你这里住几天吧。出去吃饭,我把具体的细节跟他说了。我说,我想清楚了,不回去了。也许你觉得我是自作多情,就算自作多情吧,我是想把这份工作只当成工作来做,但又真的没办法只当成工作来做。
听完后,刘晓金放下筷子,长叹一口气。半天说,你想清楚了就行,这事其实也没啥大不了的,就像我那时候——哎,算了,不说了,你以为我不想过好日子?你以为我愿意天天这样混吃等死?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得到就能得到的。
刘晓金比我大几岁,来这个城市的时间也比我长,曾有过什么样的故事,他没说过。我刚想问,但又觉得还是别问的好。我们这种人,要么没故事,有故事也都是伤心事。说出来,不过是把一个人的伤心,变成两个人的难堪,所以还是算了。
刘晓金又拿起筷子,你呀,就是想得太多,像我现在,就啥都不想了。他又说,想那么多干啥,想了也是白想。有时候我都想当一张桌子,每天光站在那儿就行了。
晚饭后,我们又去逛超市,我买了一打啤酒,和他坐在路边喝。一边喝,我一边闲聊着。刘晓金又感叹说,说白了,我们跟他们终究不是一路人,就算撞在一起,最多也就是撞一鼻子血。我说,对呀,我现在就是一鼻子血。我手里的啤酒没了,重新开了一罐,举起来,一口喝完。我把罐子扔出去,在马路上滚得很远,哐啷啷响。我又伸手去拿啤酒,刘晓金拦住我。我跟他说,我心里难受,让我再喝一个。他说,难受啥,你既然有勇气选择离开,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我推他一下,去你的吧,还承担后果,说得这么正经,你以为是在演电视剧呢。电视剧也是根据生活编出来的呀,还不都一样,他说。
电视剧当然跟生活不一样。
刘晓金要去上班,把我丢在路边就走了,啤酒还剩下三罐,我想坐在那里喝完。但一罐还没喝完,就觉得越来越难受,胸口疼,便把酒放在路牙子上,不喝了。提着剩下的两罐朝回走。
也许是喝了酒,神经敏感,回到地下室的那个房间,开灯,吸一口气,味道真他妈的臭。我忍不住嘴上把刘晓金骂一通,然后就跑了出去。我记得地下室有扫帚和拖把的,找到,掩住口鼻回去,想把房间彻底打扫一遍。但走到里面,看见那只珍珠鸡和满床的鸡屎,我又放弃了,想还是等刘晓金回来再收拾吧。我自己,恐怕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我转回身去放扫帚,忘了系好蚊帐,珍珠鸡就从缝隙里跑了出来。我丢下扫帚去抓,不仅没抓住,头还差点磕在床上。再抓,珍珠鸡就钻进了床底下,我趴下去,伸着手向里面够,也没够着。我不抓了,反正这里是地下室,珍珠鸡也跑不出去。
酒喝多了,又趴在地上抓半天珍珠鸡,我感觉头晕得厉害,便倒在刘晓金床上,瞪着眼睛看上铺的木床板。太阳穴里面的两根筋,怦怦怦地跳,有人蹲在里面敲鼓似的。我闭上眼睛,准备睡觉,鼓声却还一直响。我就把眼睛又睁开了。床边上有动静,是珍珠鸡钻了出来。我扭过头去看,珍珠鸡也正盯着我,黑漆漆的眼睛瞪得滚圆。过一会儿,珍珠鸡的头动一下,我看到它眼睛下方的疤,黑黑的几块。我又向下看它身上的毛,想这只珍珠鸡真可怜,生活在别墅区时候,是那么漂亮,现在却这么丑。如果它有意识,恐怕会拼尽全力逃回别墅区吧。
刘晓金成天捧着手机看电视剧,恨不能活在电视剧里。把珍珠鸡偷了回来,却又不好好照顾,弄得它这么丑,再这么下去,死了也不一定。我至少还能选择离开,可珍珠鸡力量太小,别说回别墅区,就连这间屋子也逃不出去。
我决定帮它。
我坐起来,伸出手去抓珍珠鸡,它竟然没躲,也没叫,就那么被我抓在手里。我把它抱在怀里,摸了摸它的脖子,它也没躲。我就那么抱着它朝外面走去。时间没我预想的那么晚,外面的人还很多,看见我抱着珍珠鸡,都纷纷扭过头来看。我后悔没拿个袋子之类的装着,好遮掩一下。而且我也怕珍珠鸡突然叫起来。这两天,我已经见识过它的叫声,吭啷啷啷的,比驴叫得还响。但我不想再回去拿,就把珍珠鸡抱得紧一些,快点朝朝墅区那边走。又用手指握住它的脖子,让它叫不出来。
不过我不知道珍珠鸡原来是在哪家院子,到别墅区,沿着围栏转半天,也没什么印象。围栏上都装了铁丝网,并每隔不远,装着摄像头。每个摄像头上都有一个红色的小点,我走过去,就立即闪烁起来。我担心这么来来回回转悠,会引起保安注意。而且刘晓金也曾说过,这里的保安并不好惹。再转一圈,就瞅着一个空子,把珍珠鸡放在地上,心想塞进去算了。进了别墅区,不怕它不被原来的主人看见。
我怕珍珠鸡逃走,放在地上时很小心,这里地方大,真跑了就抓不回来了。但珍珠鸡瘫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它的头也在地上耷拉着,我用手扶起来,松开手,又耷拉下去。我这才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一路抱得太紧,把珍珠鸡勒死了。我向后倒去,一屁股坐在地上。
结束了。珍珠鸡死了,我脑子里想的却不是如何跟刘晓金交代,而是结束了。什么结束了?我和萍姐之间结束了。我这才发现自己原来还抱着一丝期望,期望萍姐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别离开她,然后让我回去。我跟刘晓金说我不会回去了,但这不完全是真心的。我冷笑几声,然后低头看地上的珍珠鸡,是它彻底打消了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夜色昏暗,珍珠鸡的轮廓变得模糊,看上去没那么丑了。我用鞋尖拨一拨它,没有反应,看来是死透了。我突然接受了自己的生活,接受了我和萍姐之間的那堵墙,不再觊觎墙的另一面。
我坐的地方靠近马路,有车突然开过去,贴得近,像是从我腋下飞出去的。车窗开着,里面传出一阵笑声。我和萍姐也曾这样笑过,在酒吧里,在馄饨铺,在画展上,以后她肯定还会和其他人一起这么笑。我呢?也还会这么笑吧。
【作者简介】于则于,原名于业礼,中医学博士,写作小说、诗歌等。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芙蓉》《山东文学》《青年作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