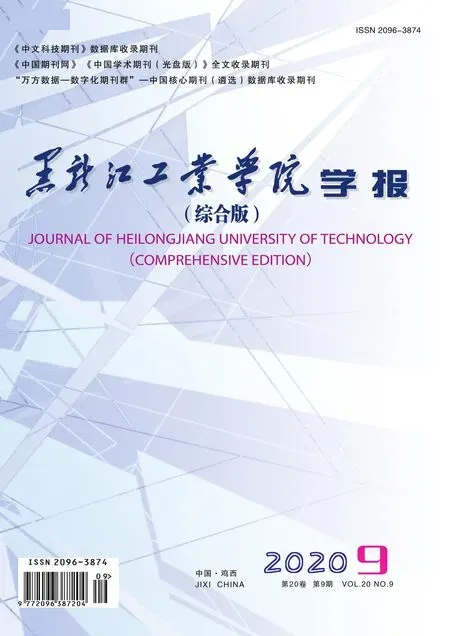论典籍翻译教学的跨文化导向
2020-11-18魏泓
魏 泓
(淮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世界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信息与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不可阻挡。中国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号召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国文化典籍的对外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西文化对等交流、达到世界文化融合的一条重要途径。”[1]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及相关研究愈来愈受学者关注,但关于中国典籍翻译教学的研究发展却相对缓慢,相关教学研究文章甚少,且目前尚未有专门探讨典籍翻译教学中跨文化教学的研究,而跨文化交际与典籍翻译教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拟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进行讨论,旨在促进典籍翻译教学、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典籍翻译教学的目标
典籍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外语翻译人才必须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要以能服务于社会为重要目标。
1.翻译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
在当今的外语类专业教学中,“跨文化能力”已成为外语类专业的核心能力指标之一。“外语类专业的课堂教学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学,外语教育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育”[2]。
跨文化能力是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学要求”(2012)提出:“高等学校本科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的通用型翻译专业人才。毕业生应熟练掌握相关工作语言,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宽广的知识面、较高的跨文化交际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了解中外社会文化……毕业生能够胜任外事、经贸、教育、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中一般难度的笔译、口译或其他跨文化交流工作。”[3]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的总序中说:“首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按口译或笔译方向训练学生的口笔译实际操作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为满足翻译实践积累所需要的百科知识。”[1]
典籍翻译教学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跨语言、跨民族、跨国界的翻译人才,能够处理跨文化交流中有关传播与接受的种种问题,以满足国家对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外语人才的需求。
2.培养学生成为弘扬中国文化的人才
翻译专业应“立足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社会发展需求”[4]。为翻译专业的学生开设典籍翻译课程深有必要。典籍翻译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与跨文化沟通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求,为国家发展服务。
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典籍翻译可谓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在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越来越重要。“文化遗产是文化的根基,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华夏之所以为华夏,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的决定性因素”。[5]当前阶段,在国家号召中国典籍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培养学生成为跨文化交际的人才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典籍文化博大精深,其外译意义重大,具有强国兴邦的作用,是塑造中国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重要举措。中国典籍富有普世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拥有强烈的精神渗透力与感召力。典籍翻译可以增长见识、启迪思想、提高知识品位、提升人文素养。通过翻译而让中国典籍进行广泛辐射,有助于让至真至善、至大至刚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走向世界,有助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取长补短、互荣共生,从而惠及人类的文明发展与世界的文化繁荣。翻译路径是实现与推进全球文化共享与互动的必然途径。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更应大力弘扬中国典籍走出去。
“翻译担负着跨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6]典籍翻译有助于加强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共建“国际汉学共同体”,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翻译专业的学生应勇于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在翻译中自觉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二、典籍翻译教学中对学生跨文化交际素养与能力的培养
在课堂授课中,教师应对典籍翻译的“充分性”(adequacy)与“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进行讲解,并结合学生的翻译实践进行详解,对其优、缺点进行适时讲评。教师事先要求学生对本小组的翻译状况进行讨论,课后让学生就翻译问题及时总结。典籍翻译教学更是语用教学、文化教学。教师应注意提高学生的翻译技能,同时加强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教师应灵活应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典籍翻译中自我提升,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体。
1.注重典籍翻译中的跨文化知识教学
语言与文化水乳交融、相生相栖,它们之间互相反映、互为因果,两者的学习是相辅相承、互相促进的。教师应将翻译教学和文化教学相结合,注意讲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启发学生发现与探索语言应用的特定语境、文化背景等相关知识。老师应注意引导学生进行中西语言对比,结合语用、语篇、文体翻译等方面的教学进行文化对比。通过对比,学生能对中西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深刻认知,掌握语义的实际应用,揣摩语言内在的文化内涵,深入领会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正确运用语言知识,建立起文化自觉与文化身份感。
中国典籍山积海涵、泱泱大观,是中国不同时代与不同社会下的思想与文化结晶,被编入了多重文化符码;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业绩、精善的理论、深刻的思想等都会在典籍中有所显现。科学与艺术相统一的中国典籍洋溢着中国精神,昭示着人类的审美理想,凸显人性光芒。中国典籍是中国文化的视窗,有益于外国读者通过典籍了解中国文化、浸濡于美的熏陶,进行中西文化间的相互比照、相互印证。中国典籍的文化内蕴异常丰厚,学生们需多读书、勤查词典。例如,对《史记》中《刺客列传·荆轲》中这一段话“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其中就有“宾客”“白衣冠”“筑”“变徵”等多个文化负载词,意义不好理解。对于典籍翻译教学,老师还应重视典籍作品的语文教学以及训诂教学,因为典籍作品大都年代久远,又是文言文表述。
文化涉及文学、历史、风俗、礼仪、价值观、社交技巧等诸多要素。典籍翻译关涉到广阔的文化知识领域。“外语学生要广开思路,不仅要精通外语,熟悉所学外语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要学习各科知识,尤其与外语密切相关的外国文化、语言学、文学、汉语、中国文化、哲学、思维科学、认知科学、逻辑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脑科学、电脑科学等等。”[7]翻译是门杂学,要求学生能够广闻博识,而典籍翻译更会要求学生能够博古通今。老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只是沧海一粟,学生们应在课外时间内积极涉猎跨文化交际知识,力求对中西文化有个深广而系统的认知。
翻译专业教学要“处理好中外语言文化知识与相关百科知识的关系。要在重视中外语言文化知识教学的同时,突出跨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的传授和积累”[8]。语言知识、文化知识与相关知识是构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基础,这需要学生对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进行长期的学习、积累、沉淀。老师可以应用启发与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潜力,让其通过自主搜集相关材料,扩展文化视野、提升知识素养。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自主学习的引导者、学习动机的培养者。老师应善于策划,让典籍翻译的课堂教学、网络学习、协作练习等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2.侧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典籍翻译过程就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老师在教学中应注意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让学生在翻译中能够恰当地理解、准确地表达,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交际意图。
学好语言,学生需要掌握涉及语音、词汇、语法、语篇等的语言规则,同时也要掌握“使用规则”。学生不仅理解词语的“语义”,更要能领会其“语用意义”,了解在不同的语境中如何得体地使用语言。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易于构成沟通障碍,不同观念之间难以避免不同程度上的碰撞与摩擦。学生应学习如何处理语言中的文化问题,学会在不同情境中如何运用语言策略,以便成为善于使用语言、善于处理交际问题的跨国际的人才。
学生应认识与把握中西思维差异,能用西方思维进行换位思考,有意识地去除本体思维,避免文化冲突。英、汉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在语言和文化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学生倾向于按照母语的学习经验和思维方式去分析与理解问题,往往按照汉语语言文化的惯性思维去进行翻译,容易产生跨文化交际中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因此,在典籍翻译中,学生要特别注意转变思维方式,努力去除母语迁移。另外,学生还要避免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来理解和衡量其他民族文化,有意识地摒除民族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老师要注意在思想层面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中西文化差异形成高度的敏感性、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老师要引导和训练学生形成求异思维、批判性思维,使学生能够客观、理智地去看待异域文化,站在异域文化成员的角度去理解其思想与情感状态,从而达成共鸣,以实现顺畅沟通与有效交流。
学生应深刻了解典籍翻译中多元文化差异与中西思维差异,拥有科学的世界文化观,平等对待各国文化,尊重与包容他国文化,正确对待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文秋芳教授认为:“跨文化能力由三部分组成: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度,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9]翻译专业的学生应具有多元文化认同感,能以开放的态度、批判的思想和包容的胸襟对待多元文化现象。学生若以狭隘的眼光去看待他国文化,就易于产生误解与摩擦,阻碍翻译活动有效进行。学生只有拥有跨文化交际的宽容性与洞察力,才能得体而灵活地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以适应多元文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典籍翻译课程的教学应着重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加强学生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知,培养学生能够胜任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长期的实践训练与知识积累。
三、跨文化导向中典籍翻译的处理原则与方法
典籍翻译教学应以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为导向。老师应注意采用多种有效的教学方法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素养与能力,引导与启发学生在翻译中秉承跨文化交际理念、妥善处理语言与文化问题。老师首先让学生了解语境变迁、翻译目的等与中国典籍外译的关系,然后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现阶段典籍翻译应掌握的原则与方法。此部分把理论论述与实践翻译相结合进行阐释,并让学生进行讨论与互动,以期让学生全面、深入、动态地掌握跨文化导向的典籍翻译策略。
1.中西跨文化交流语境变迁与中国典籍翻译
20世纪50年代之前,早期西方传教士或汉学家选译中国典籍,多用归化策略进行探奇介绍,意在让西方读者一窥古老的中华文明,以满足其猎奇与浅层了解的愿望。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极不稳定,到了70年代,东西严重对峙的势头减弱,世界格局开始由两极向多极发展,世界跨文化交流快速发展。在社会需求下,大量中国典籍的翻译产生。由于西方对中国文化所知有限,且当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比较盛行,因此归化的意译法颇为流行。随着全球化发展加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与合作日趋加强,文化多元共存与发展成为社会主流发展趋势。综合国力日渐增强的中国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与尊重。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英、美等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西方国家希望对中国文化有更为深入而充分的了解与研究。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译者表现出对中国典籍中异质文化的尊重,多采取保留原文异域文化色彩的异化翻译策略。
以《史记》为例,上世纪50年代之前可谓是零星翻译阶段,译介内容不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的《史记》翻译也只译出三篇秦代人物列传的内容[10]。20世纪50到70年代的《史记》翻译出现了侧重文学效果的大量节译,其中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共译出文学色彩强的80篇,译文注释少,流畅而优美[11];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共译出故事性强、极具代表性的31篇,注释很少,译文简练易读[12];英国学者杜为廉(William Dolby)和司考特(John Scott)全译或节译了7篇《史记》列传的内容,没有注释,表达口语化、颇具感染力[13]。这一阶段的《史记》翻译多倾向归化。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领衔全译《史记》,已精确译出其中81篇,译文文献厚重,译注谨严[14]。英国学者道森(Raymond Dawson)全译或节译了7篇《史记》列传的内容,其注释较多,既关注可读性、亦关注忠实性[15]。这阶段的《史记》翻译以异化为主。
中国典籍的英译以英美为主流。美国的中国典籍英译及其研究起步比英国晚了200余年,但美国汉学发展迅速,20世纪下半叶成为西方汉学中心。中国典籍在西方的传播已经由译介为主发展到翻译和研究并重。早期中国典籍的译者以西方学者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译介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译者加入其中。中西译者两支队伍相互交流,使典籍英译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更大提高。在现阶段,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更为加强,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已有所了解,中国需用异化翻译策略来充分展示自己的文化底蕴,以便让西方读者能深入而真实地理解中国文化。当然,典籍翻译颇为复杂,译者应学会灵活变通。
2.典籍翻译原则——兼顾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中倾向前者
典籍翻译是充分再现原作的语言特点与文化信息,还是侧重译文的可接受性与读者的接受能力?图里(Gideon Toury)把“充分性”与“可接受性”看作翻译的两极(two poles),把倾向于“充分性”与倾向于“可接受性”的翻译看作两类翻译[16]。图里认为:忠于源语规范决定译文的充分性,忠于目标语规范决定译文的可接受性(同上)。图里认为译文总是在“充分性”与“可接受性”两极之间变动,总会在两极之间有所偏颇。“翻译从来不会既是充分的又是可接受的。具体地说,是两者的融合,也就是说,没有翻译能够呈现出零度的充分性或可接受性,也绝不会到达100%的可接受性或100%的充分性。”[17]翻译史上一直存在着以读者为导向和以原作为导向的两类翻译。
在翻译中,学生首先要力求充分译出典籍原作信息及其文化内涵。学生要深入理解原作,对其进行多次与多方解读。中西方之间在语言与文化上差异甚大,文化负载厚重的中国典籍在外译中尤为棘手。典籍往往文字雅奥、内蕴丰富,民族文化负载非常厚重,意义往往模糊、不确定,译者需要对其一再解读与阐释。典籍外译过程相当复杂,需先进行语内转换、再进行语际转换;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理论对典籍翻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典籍翻译过程是阐释与接受、再阐释与再接受的无尽过程。语内到语内的翻译过程要求译者必须精通文言文,而从语内到语际的表达环节上,更会涉及到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屏幕与视阈融合等接受问题。学生需对语内到语际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语言与文化上的问题进行全面认知、把握。
讨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籍翻译策略,必然还要考虑翻译出来的东西能否被目标语读者所接受。典籍翻译不仅是立足于文本信息的“后瞻式”翻译,更是关注读者接收的“前瞻式”翻译。在中国典籍“走出去”的现阶段,吸引读者、根据读者接受进行创造是必须的。“读者接受”要素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效果有着深深的影响。学生在选词、组句、重建语境的同时,要酌情以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与审美习惯来进行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源语读者与目标语读者的“前理解”与“期待视野”大不相同。学生在翻译时心中应有一个潜在的西方读者形象,根据其接受状况而在行文表达上适当地与国外靠拢。
在对中国典籍翻译的过程中,学生既要努力充分再现典籍的文化信息,又要关注读者接受。究竟靠向哪方,学生要看翻译目的与要求而定。学生要保证译文的精确度与接受度。老师应让学生深入认识“充分性”翻译与“可接受性”翻译的内涵及其各自的存在价值,在翻译中应酌情倾向于前者,尽可能充分传递出原作文化内涵。
3.典籍翻译方法——兼顾异化与归化中倾向前者
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是全然充分或彻底可接受的[18]。翻译不可能达到某一极端,也不可能处于两极的正中间,必然会倾向两个极端之中某一端的位置。转换是不可避免的,意在最充分的翻译也会涉及到原文本的种种转换(shifts),这是“翻译真正的普遍规律”[16]。在具体的转换操作中,译者必然要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
美国的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形》(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1995)一书中将施莱尓马赫的两种方法称作异化法和归化法。归化和异化可以看作是意译和直译的概念延伸,包含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异化(foreignization)主张以源语为取向,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力求充分再现原作,尽量重现原作的构思、特色与风格等;归化(domestication)则认为译文应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取向,注重读者的接受环境、接受能力与接受心理,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对于典籍翻译,两种方法都大有裨益。异化有助于传递典籍原文的文化信息和语言表达方式,而归化有助于克服文化障碍,让行文流畅、易于读者阅读。
归化和异化的翻译并非是各自单一运行的,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任何译本都必然是归化与异化混合后的载体。归化与异化是相对而互补的,两类翻译“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类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19]。归化与异化各具优势、相融相生,译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异化有助于在翻译中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差异,尽力传递原作文化思想与风俗习惯,以期西方读者能领略原汁原味的中国典籍,促进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因此,在当今倡导中国典籍走出去的背景下,异化翻译自然是第一选择。但若是原文中有太多晦涩难懂的表达、异化翻译难以让读者理解与联想时,译者应适当采用增减与解释等方法进行适度归化翻译。
老师应着意引导学生认识到归化与异化这两种方法之间的运作关系,并善于启发学生灵活运用这两种方法来处理翻译中的文化问题。
4.灵活处理、适当变通
中国典籍外译极为复杂、棘手。译无定法,典籍翻译尤为如此。不同的典籍翻译技巧各有其优势与价值,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不同类型的读者。典籍翻译见仁见智,虽然我们提倡充分性翻译、异化方法,但学生需依据翻译目的与接受对象灵活处理、善于变通。
例1: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16]
杨宪益、戴乃迭:Several times Fan Tseng shot Hsiang Yu meaningful glances and three times, as a hint, raised his jade chueh.(注释)But Hsiang Yu did not respond.[12]
华兹生:Fan Tseng from time to time eyed Hsiang Yu and three times lifted up the jade pendant in the form of a broken ring which he wore and showed it to Yu, hinting that he should “break” once and for all with the governor, but Hsiang Yu sat silent and did not respond.[11]
倪豪士:Fan Tseng several times glanced at King Hsiang, thrice lifting up the horseshoe-shaped jade disc hung from his girdle to show him.(注释)King Hsiang was silent and did not respond.[14]
对于原句“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以上三个译文大不相同。原句中的“玦”是一种佩玉,圆形,环体上侧有缺口。玉有缺则为玦,“玦”与“绝”“决”同音,含有双关意。范增以玉玦示意,希望项羽赶快决绝,铲除刘邦。杨译在文末加注标明双关意:“An ornament in the form of a broken ring. He was hinting that Hsiang Yu should break with Liu Pang. ” 华译没有加注,在译文内进行解释性增译,译出了双关。倪译不仅在译文内酌情解释“the horseshoe-shaped jade disc hung from his girdle”,而且进行详尽注释:“This disc was called a chÜen玦, since it lack one piece from being a whole circle. chÜen is a pun on chÜen 玦‘to decide’and here was a means for Fan Tseng to ask Hsiang Yu to make up his mind whether he wanted Liu Pang killed”。
在翻译中,杨译、华译、倪译分别以“直译+注释”、“意译+释意”、“直译+释意+脚注”的方式进行增译翻译。杨译字数最少,最为简洁;华译最长,意思表达细腻,最具可读性;倪译简练精确,唯恐未能充分传递原文之意。杨译意在西方的一般读者,以再现源语文化为目标,力求充分传递出原作的文化内容。华译倾向可接受性,意在西方的大众读者,译文顺畅优美,让读者易于并乐于阅读。倪译是为了西方的专家与学者,翻译非常倾向充分性,着力保留源语形式与文化内涵,同时也关注读者的接受能力,译文具有异国情调,也兼具可读性。
例2: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20]
对于原文中文化词语的翻译,以下六位译者的译文各不相同。对于表1中文化词语“白衣冠”的翻译,卜译和倪译是异化翻译,未能译出“白衣冠”所蕴含的“哀伤”之意,而其他几位译者在译文中添加“mourning”一词,让原意显化。英汉语中的“白色”都有纯洁与清白的联想之意,此外,英语文化中white还表示幸福和纯洁,而中国的白色还与死亡、丧事相联系。中英文中“白色”的内涵差距大,不宜直译。对于“击筑”的翻译,杨译“played the guitar”最为归化,其它五个译文反而比较异化,其中倪译“plucked his zither”感觉最为合适。对于“变徵”的翻译,卜德通过加注进行精确翻译;杨译是意译,“变徵”内容未直接译出;华译是意译与直译并用;杜译译得不确切;道译亦是意译,未能忠实译出“变徵”的意思;倪译意译的同时兼用注释,最为精当。六译文各具特色,都有相应的读者接受,都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表1 六位译者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综上可见,杨译多用异化方法,有时也用归化法;华兹生多用归化手法,当然译文中也有异化的成分;倪译在非常倾向充分性中亦关注读者接受。在《史记》翻译中,译者不是只遵循一种原则或一种方法,也并非完全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或以目标语文化为归宿的。任何翻译,都是既无纯粹的异化,也无纯粹的归化,都以混杂文本的形式出现,都是两者的调和。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方法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结语
典籍翻译的终极目标是培养能够胜任传播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交际人才。为此,教师要注意在典籍翻译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教学,引导学生掌握语言与文化知识,转换学生的惯性思维方式,努力培养学生、使之具备能够担负起典籍外译的素养与才能。典籍翻译非常棘手,其中的文化问题如影随形,学生翻译时既要力求充分传达出原作的文化信息,又要兼顾读者的接受程度。老师应教导学生善于应用异化与归化翻译策略,并会善于变通。本文从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角度来讨论典籍翻译教学,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典籍译员,更有助于培育出能弘扬中国文化、善于讲中国故事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