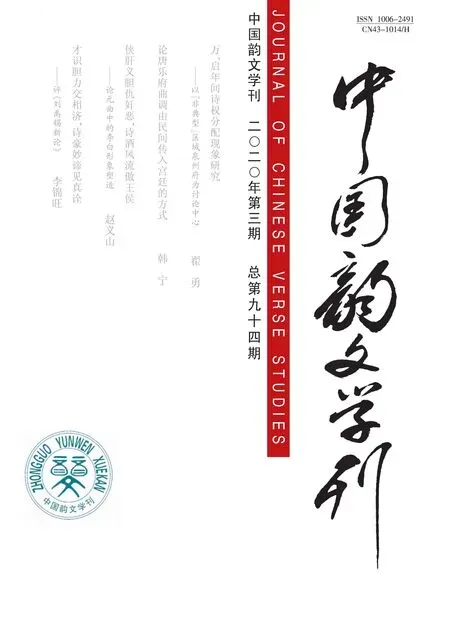厉鹗清雅词学及其创作风格
2020-11-18张燕珠
张燕珠
(香港公开大学 教育及语文学院,香港 999077)
在清代,论浙西词派的发展脉络,学者往往会肯定朱彝尊是开创者,厉鹗是中期巨匠。蒋敦复总结“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1](第四册,P3636),谢章铤回顾“国朝词学,浙最盛行,竹垞倡于前,樊榭骋于后”[2](第三册,P1441),吴梅指出“自樊榭承竹垞之后,以南宋为师,于是词家有浙西派”[2](第四册,P2132)。厉鹗是流派的承先启后者,也是中期的领导者,全面推动流派至全盛局面。这个观点仍然为今人所接受,如认同他是浙西词派中期的代表作家和词学理论家[3](P83-89),指出他是浙西词派中期公认的领导者[4](P175-183),他是继朱彝尊之后的新一代词学领袖[5](P115-1270),等等。《全清词》高度评价厉鹗,指他的诗词俱为浙派大宗,其词“取法南宋,清峭雅洁,继朱彝尊而起,为清代中叶浙西词派盟主,与朱彝尊并称‘朱厉’”[6](第一册,P231),以现代词学精神确立厉鹗及其词的重要性。在浙西词派甚至是在清代词学中,厉鹗的词学地位举足轻重。他的词学理论具有系统性,完善了朱彝尊和汪森的醇雅论。他远取张炎的清空论,从“清婉”“清丽”与“清妍”开拓清雅论,为学词者开垦新的土壤。而他的词创作又能汲取南宋名贤之长,开创个性化的清雅风格,成为学词者的模仿对象。同时,厉鹗的出现,成就浙西词派从醇雅论到清雅论的转向,词创作全面进入清雅的领域。于此,在乾隆词坛以降,不同词学家逐步经典化厉鹗的词文学地位,把厉鹗置入南宋名贤的体系,又与朱彝尊并举或比较。清人十分重视厉鹗,他是后学的学词对象,又成为后学竞逐词学成就的目标。本文析论厉鹗重视“知音”的周邦彦、姜夔和张炎词,重塑“雅”和“清”的词学。同时,他又恪守清雅的创作原则,创造个人的清雅词风,包括广泛选材、冷色字系及个人恬淡的性情,成为后学的经典词文学。他能够“振其绪”“骋于后”,在于其经典化宋贤和康熙词坛名贤的词美学,而流派的后学又致力经典化他的作品,因此凸显出了他是一个时代的经典词人。学词者自觉地吸收厉词的养分,是认同他的艺术成就,在个人的局限与时代创作中,演活经典词人的人文精神,在读者意识中体现经典词人的文化符号的作用。
一 重返“知音”:厉鹗推崇周邦彦、姜夔和张炎词
乾隆年间,厉鹗意识到浙西词派发展上的一些弱点,“向来作者以秦、黄为法,自竹垞翁标举南渡,为此中别开户牖,或剽拟太过,尚雕缋而乏自然,遂成涩体”[2](P467)。厉鹗决心改善这个现象,继承朱彝尊的词学思想,继续弘扬南宋名词家。《国史文苑传》及《杭州府志文苑传》分别指出厉鹗“兼长诗余,擅南宋诸家之胜”及“尤工长短句,入南宋诸家之胜”[7](下册,P1728)。但这只是泛指他取南宋名家词之长,未能具体反映他的词学思想。他的弟子汪沆忆述,他以诗古文名垂东南四十年,“尤工长短句,瓣香乎玉田、白石,习倚声者,共奉先生为圭臬焉”[7](中册,P703)。这里则能够反映厉鹗倾向姜夔、张炎词的思路,予人专取姜、张词的观感。汪沆纳入厉鹗在南宋名贤之后,这是经典化其词的重要一步。吴锡麒应和,“吾浙竹垞、樊榭,皆追姜、张而起者也”[2](第二册,P734),认为厉鹗是姜、张、朱的接班人。王昶分析王沂孙、张炎、周密、朱彝尊、厉鹗等人词“刻意研炼”[2](第二册,P625),欣赏厉词直接继承王沂孙、张炎词。
厉鹗曾为张炎《山中白云词》写跋文[7](中册,P828-829),考证张炎“为循王五世孙”的身份,又分别辑录邓牧心和孔行素高度评价张炎《春水》和《孤雁》二词。“玉田秀笔溯清空,净洗花香意匠中。羡杀时人唤春水,源流故自寄闲翁。”(《论词绝句》其七)他从用笔、风格和意趣评论张炎词,分别是“秀笔”、“清空”和“意匠”,认为张炎词直达姜夔的清空词境[8](P70),概括《山中白云词》的内容要旨,肯定其是词学正始之源,也暗示《浙西六家词》附《山中白云词》于后的做法正确。谭献批评“太鸿思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世人争赏其饾饤窳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碔砆也”[1](第四册,4008),这里说明取法张炎词是厉鹗成败的关键。厉鹗刻意追求“秀笔”、“清空”和“意匠”,用字僻冷,钻研艺术形式美,牺牲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品逐渐趋向偏倚的境地。这个观点将会在后文分析。但厉鹗能够集合群雅之长,又能够秉持风雅之旨,开拓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以致追随者不绝,成为雍正、乾隆词坛的盟主。
另一方面,厉鹗由江南的水土引出同乡的情谊,推崇周邦彦词。“南宗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7](中册,P754),他倾向宋词中婉约协律的审美趣味。宋徽宗年间,周邦彦出任大晟乐府提举官,其词盛传于世,“每制一调,名流辄依律赓唱,独东楚方千里、乐安杨泽民有和清真全词各一卷,或合为《三英集》行世”。(1)见毛晋《汲古阁词话》,屈兴国编《词话丛编二编》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10页。此事迹也为沈雄所转载。见沈雄《柳塘词话》,《词话丛编二编》第一册,第539~540页。因为他上承北宋柳永词的铺排技法,下开南宋巧思铺陈赋化为美的词,特别对南宋一些词人产生重大的影响,[9](P155)在词学发展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从地缘关系来看,厉鹗重新审视朱、汪所推崇姜夔的醇雅词,在南宋链状的雅正词人关系中,以同乡情意为论词的核心,有意把朱、汪推崇以姜夔为首的醇雅词人群,向上推演至周邦彦的婉约雅正词,建构新的雅正词人群体,重新为流派中期的雅正词祖定位。厉鹗纳周邦彦词在浙西词派的词学体系内,重提倚声家的概念,扩充流派中期的雅正思想至词乐合一的整体性。厉鹗特别强调纯美的艺术表现,是重返张炎注重词的正声的举措,意图突出姜、周知音者的形象,整合词文学和音乐的关系。这样可以反拨流派的“涩体”现象,借此为自己争取有利的领导地位。
二 重塑词学:厉鹗推尊“雅”和“清”
厉鹗整合了“雅”和“清”的内涵,重塑浙西词派中期的词学思想。一是重视“雅”。厉鹗分别视《诗经》的风雅及朱、汪的醇雅论为清雅理论与实践的思路。“由诗而乐府而词,必企夫雅之一言。”[7](中册,P755)厉鹗指出由《诗经》到乐府到词都不能偏离“雅”的规范,既指出雅的起源,且以清远淡雅的语言来制约词的“委曲啴缓”[7](中册,P755),并视之为表现雅正的方式。“远而文,淡而秀,缠绵而不失其正,骋雅人之能事”[7](中册,P755),是流派中期雅论的新解。宋人作词喜以雅相尚,出现了冠以雅词为名的选本,如曾慥《乐府雅词》等。在以姜夔为首的雅词人群上,朱、汪倾向张炎的骚雅论,脱变而为醇雅论,标举词需要符合雅正,即高尚风雅、规范,但具体的表达方式如何,则有待厉鹗的补充说明。朱彝尊提出“词以雅为尚”[10](P521)的核心命题,又以雅正作为阐述雅的具体概念,“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10](P492),即纯正典雅,并以协律为雅正词的体现,即汪森所指的“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11](P1)的总论题。汪森提出醇雅论,注解朱彝尊的雅正论,源自张炎的骚雅论,而厉鹗的清雅论则是补充朱、汪的醇雅论。在文学领域中,骚雅往往是借指由《诗经》和《离骚》所奠定的优秀风格和传统。汪森由骚雅转化为醇雅,显示淳厚雅正或淳朴雅致的本质,配合清廷尚雅的文化政策。厉鹗再由醇雅转而为清雅,倾向清净淡雅的审美态度,流派中期词风趋于自然之道。
厉鹗与查为仁以笺注批评方式重塑南宋词选本《绝妙好词》,宣扬流派的雅正理论或思想,全力经典化《绝妙好词》,推向流派至鼎盛期。[12](P33-44)《绝妙好词纪事》记述他性孤但博览群书,尤熟谙宋元史事。他出身寒门,早年丧父,家境清贫,从雍正三年(1725)起,坐馆于扬州小玲珑山馆,三十年来一直投靠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馆内多藏旧书善本,他有缘博览群书而博古通今,闲时鉴赏古器名画,故撰《宋诗纪事》《辽史拾遗》,是南宋史研究的权威。厉鹗从压抑的心理和苦闷的精神中,自觉地选择以审美价值抗衡任何外在的斗争,走上更纯粹的学术道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这也是普通下层寒士的精神出路,无论是个人或是群体,不可以回避牵涉到社会和现实的利益,而真正的美学就是在抗衡外在因素中,产生无法估量的力量。同时,他借助马氏小玲珑山馆之利,结识扬州的文人,与当时名士如陈章、汪玉枢、闵莲峰、施安等人,组织诗会唱和,每分咏一题便结为一集,名流云集西湖,各有歌行,盛极一时。[13](第三册,P89、231)这是重要的扬州词人群体。乾隆盛世,海内殷商甚富,促成不同的文学活动,“扬州有马氏秋玉之玲珑山馆,天津有查氏心谷之水西庄,杭州有赵氏公千之小山堂,吴氏尺凫之瓶花斋:名流宴咏,殆无虚日”[13](第三册,P88-89)。厉鹗当时活跃文坛,亲述“予平生三游,皆马君嶰谷、半查为之主”[7](中册,P750),扬州及天津的文学活动皆以其为中心。那三次的文人风雅活动是在雍正七年(1729)、乾隆二年(1737)及乾隆十三年(1748)发生的。以乾隆十三年的文学活动为例,查为仁宴请厉鹗、英廉、吴廷华、陈皋等人在天津城南门外的南溪草堂集会,同游者九人各赋诗七首、联句一首,合为一集。这类文雅活动频繁,如“药山招同敬身西林集湖舫分得‘人’字”、“西林招看菊小饮分得‘开’字”,等等。这些文学活动促进当代文人创作新的作品,创造群体拉拢或影响群体,汇聚相似的创作心态或目标,彼此经典化对方的作品。
二是导入“清”论。厉鹗以张炎《词源》中所主张的“清空”为总体思想,以“清”补充朱、汪的醇雅论,建构流派中期的清雅论。张炎主张“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1](第一册,P259),以“清空”带出雅正词的准绳,有清新和空灵的意境,使词有古雅峭拔的境界。在清空论下,厉鹗以“清婉”、“清丽”与“清妍”作为审美取向,阐述雅正的思想或概念,而雅正又反过来能够补充“清空”。汪沆概括厉鹗的审美特质,是“以清和为声响,以恬澹为神味”(2)汪沆《汪序》,《樊榭山房集》中册,第703页。此一说法也见于《杭州府志文苑传》,只是把“恬澹”改为“恬淡”。《樊榭山房集》下册,第1728页。。“清和”可以说是他的审美态度,作为审音者的参考指标,而“恬澹”则作为艺术风格的批评方式,也可以视之为修身克己的制约。在“清空”作为思想指导下,厉鹗以“清和”说明自己清净的美学,又以“清婉”、“清丽”与“清妍”来诠释“清”的概念。它们能够具体地表现“清”和“雅”的本质。这是厉鹗从艺术审美领域净化朱、汪的醇雅论,引导流派词风至清雅领域。
厉鹗对“清”的注释,包含“清婉”、“清丽”与“清妍”的特性。在张炎清空论的基础下,厉鹗阐释词作为表达形式上的清脱与空灵,达到词的最高境界,走的仍然是传统美学中“清”的柔美审美特质,与“清壮”和“清雄”阳刚美审美类型相反。厉鹗倾向“南渟以秀淡胜,融谷以婉缛胜”[7](中册,P753),强调“秀淡”和“婉缛”的文辞,是“清婉”的注脚。宋贤方面,有周邦彦词“婉约隐秀,律吕谐协”,时人则有张龙威词“清婉深秀,摈去凡近”[7](中册,P752)、张今涪词“淡沲平远”[7](中册,P754)、吴焯词“纡徐幽邃,戃怳绵丽”[7](中册,P754)等。时人词直逼周邦彦、姜夔与张炎词的境界。“清丽”一词,可以参考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中的“清文以驰其丽”[14](P208)的说法,强调文辞需要清新以显现其文采。“清丽”的表现者有陆培《白蕉词》四卷,“清丽闲婉,使人意消”[7](中册,P752)。
“清妍”见于《论词绝句》其五。厉鹗侧重讨论姜夔的昔日生活,“旧时月色最清妍,香影都从授简传。赠与小红应不惜,赏音只有石湖仙”。厉鹗欣赏姜夔的“清妍”词风,符合自己所推尊的“清”,并强调词作与词人的生活背景不无关系[8](P69),突显词人的作品需要融入生活当中,文人与歌妓自古更是结下不解之缘。姜夔与厉鹗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二人都是投靠当时的名士谋生,周旋于名流之中,同时他们的品格都是清苦高雅,其高超的艺术造诣就是雅正符号的化身,能够迎合当时名士的喜好,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厉鹗从这些相似因素入手,不是借助姜夔的特殊文学地位和高洁的形象来抬高自己,而是在文学艺术中创造纯粹的清雅美学。厉鹗的个人命运、人生遭遇和才华得到普遍下层寒士的回响,词人群心灵上产生了感应,渐次与姜夔的独特形象暗合,就像是郁郁不得志文人的镜子,更多的是负荷千古文人空有才华而无用武之地的情感。毕竟,享有朱彝尊般特殊的厚遇可以说是异数,更多的文人过着如姜夔与厉鹗般的日子。文人赋予姜、厉多重或隐蔽的意义,以及属于他们在本质上的清孤性格和卓越才华。厉鹗终于凭借超群的才学和知识,凝聚扬州文人群,创造新的力量,开拓自成一格的词学道路,也成为后学的学习对象。正因如此,厉鹗把自己纳入姜夔的形象之中,让文人重新认识姜夔所彰显的凝聚功能,与寒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寒士在审视现实生活的苦况,词风和趣味渐次起了变化,随之纷纷转投清雅的创作道路,隐含自我脱离社会的方法。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浙西词派的词风由朱彝尊时代的虚化词貌,转移到厉鹗时代的更虚空境界。
三 展现清雅:厉鹗开拓词的题材
厉鹗针对当时流派被讥评为“涩体”的现象,重新整合不同接受程度的“雅正”,内化和深化“雅”的概念,开拓“清”的内涵,以“清”的思想制约“雅”的词貌。创作方面,厉鹗填词不多,但词风清雅,《全清词》录其词263首。[6](第一册,P230-304)清雅,即清高脱俗、典雅高洁。我们从广泛选材、冷色字系及个人性情几个方面,论述其自成一格的清雅词风。
康熙六十一年(1722),他刻《秋林琴趣》4卷,得词160首,邀请徐逢吉、吴允嘉、陈撰、吴焯、赵信等人写序跋题辞。从南宋名家词的标准评厉词的,如徐逢吉“回环读之,如入空山,如闻流泉,真沐浴于白石、梅溪而出之者”[7](中册,P879);从音律角度赞美厉词的,如吴允嘉指其词“声谐律叶,骨秀神闲”[7](中册,P880),符曾美言“上者海山缥缈之音”[7](中册,P882);从清雅的审美标准评价厉词的,如陈撰认为“清真雅正,超然神解”[7](中册,P880),赵信明言“淡而弥永,清而不肤”[7](中册,P882);从内容、学识和才华方面评价厉词的,如吴焯直言“质也灵虚,学也膏腴,才也佽飞”[7](中册,P881)。他们多角度经典化厉词,群体合力建构以厉鹗为中心的审美活动,而相关的词学活动也被组织,如前文所言的扬州及天津的文学活动,并与流派的清雅系统联系。
厉鹗适应当时的词创作生态环境,选材广泛。有唱和的题材,如“红桥”唱和,包括《忆王孙·怀红桥旧游》《醉太平·戊午暮春,泛舟红桥,同授衣、廉风联句》《采桑子·晚秋同程松门泛舟红桥》等。《忆王孙·怀红桥旧游》调子轻快,忆念秋雨下坐画舫游红桥的情怀,“梦迢迢。曾倚阑干弄柳条”,扣紧“秋雨多从蝉鬓飘”。“柳条”、“秋雨”和“蝉鬓”起衔接作用,物与情合一,拉长追思往昔的绵长。《醉太平·戊午暮春,泛舟红桥,同授衣、廉风联句》属同游者联句成词的作品,厉鹗负责首尾各两句,是文人间文字接龙的游戏。唱和《乐府补题》方面,他按照原题五物写作,细腻勾勒体物的特征,如《摸鱼儿·莼》(过清明)写莼“叶圆似拭”,《齐天乐·蝉》(青林响接炎光水)哀蝉“又咽断残声”“长嘶正苦”。《桂枝香·蟹》(江枫落早)强于刻画蟹的形态,如“不住腥泥郭紫,脐翻红蓼”“骨清沫白,葑湖秋好”,也细致描述吃蟹的过程,如“溢金膏、故国天杪”“依稀粉本,尚留纤爪”。但也有趋于雕琢的,如《天香·龙涎香》(苦竹潭深)喻龙涎香“焚出青芦雨里。伴小舫凉声静敲碎”,《水龙吟·白莲》(绿罗万笠高低)咏白莲“银囊独立,羽衣来暮”。他也拟《乐府补题》,托物言愁苦,是拟补题的典范。如《天香·薛镜》(蓝浪浮花)咏薛家镜忆“最爱是、长宜旧铭字”,《水龙吟·漳兰》(海帆吹送琼姿)咏漳兰“写深林韵”,《摸鱼儿·芡》(趁平湖)咏芡念及“早萦系心期”,《齐天乐·络纬》(夕阳才作微凉意)咏络纬“怕短发难搔,助愁千丈”,《桂枝香·银鱼》(平桥永昼)咏银鱼慨叹“几分纤软,堪人断肠,忆鲈能否”。我们可以以吴锡麒评厉词“清微幽眇,戛然弦外”[2]( 第二册,P734),以及郭麔指出厉词“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厘然一归于正”[2]( 第二册,P736),总结这类唱和作品的风格。“清微幽眇”和“清空微婉”说明作品思想内容的清绝,“戛然弦外”和“幼眇绵邈之音”则是指作品形式的协律。
厉鹗试图寻找自己的创作道路,努力开拓新的题材。如《沁园春》咏心、尘、腕、声和影,他没有沿用朱彝尊的十三种女性身体的经典题材。《沁园春·心》的“一寸通犀,脉脉难窥,含无限情”,具体化心的感性功能。《沁园春·尘》则以“微步凌波”“欲辟还宜旧导犀”等拟人手法,美化尘的形态。他的《天香·烟草》是当时词坛的新题,“继和者几遍大江南北,逞妍抽秘,妙绝一时”(3)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十二册,第6676页。词人开始琐细化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新事物,形成雍、乾年间咏物词的发展轨迹。参见张宏生《重理旧韵与抉发新题——雍乾年间的咏物词及其与顺康的传承和对话》,第115~127页。。而《三部乐·流求纸》相信也是当时的新题,写产自琉球的书画用纸。上片从蔡伦造纸说起,指中国造纸术历史悠久。下片写琉球纸的制造过程。陆培《三姝媚·高丽纸》与这首词相互照应。陆培写产自高丽的贡纸,纸质洁如绫,“雪茧层层,似他光致”。二词均使用“欢斯”这琉球族姓。外物传入中国后,很快成为清代词人笔下的题材。词人趋向追求创新、时尚,厉鹗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然而,厉鹗长期处于比较安稳的生活状态,创作上或受到局限,思想深度也会有限制。如《河传·题顾升山蔬果画册》15首,咏笋、萝卜、枇杷、香橼、水红菱、木瓜、茄、芋、莲子、杨梅、石榴、香瓜、橄榄、桃子和扁豆,细密白描体物,如“一林庐橘,县金欲堕”形容枇杷,“心苦君知否”形容莲子,“树间红碎”形容杨梅,等等。但也有用字雕琢的,如萝卜篇中的“卧龙已去天星陨。军声尽。战土犹微坟”,木瓜篇中的“檀奴有意,为遮交午腮红”,芋篇中的“斫侯鲭。捣金橙”,等等,内容欠缺深度和广度。郭麔介绍厉鹗《河传》词时,指出其源于蒋梦华以顾升山蔬果画册索题,厉鹗创作了18首词(15首传世),一词一题。题图方面,有《菩萨蛮·题呵手梅妆图》《声声慢·题符幼鲁风雪归舟图》《点绛唇·题授衣读书稻田隅图》《清平乐·题饮谷说剑图》《翻香令·题赵意田倚楼图》《南乡子·题挥扇士女图》等。《南乡子·题挥扇士女图》直接刻划挥扇的仕女的神态,唯上下片的结句用语比较浅俗。交游方面,有《夏初临·初夏雨中同蒋丈静山泛湖》《少年游·春日访紫山,同坐学士桥旁望湖》《水调歌头·访吴丈志上寄老庵》等,活动范围和场面有限,围绕泛湖、观潮、访友、登楼等,活动地点集中在扬州、杭州、上海、湖州等。
四 展现清雅:厉鹗创造词的风格
厉鹗喜爱追和前贤的作品,另有创新。于宋贤方面,如“用清真韵”,其作有《惜余春慢·戊戌三月二十二日泛湖》《丁香结·暮春初霁》,“追和草窗韵” ;有《大圣乐·东园饯春》,“用吴梦窗韵”;有《澡兰香·癸丑淮南重午》《霜叶飞·九日葛岭》,“用史梅溪韵”;有《步月·己未岁吴山灯市甚盛》,“效蒋竹山体”;有《瑞鹤仙·咏菊,为楞山生日》。这些都是他努力超越宋贤作品的成果,但当中却没有姜、张的,这或是因为他创作上的焦虑。他知道原典已经难以超越,却仍然坚持创新,故选择追和其他宋贤的作品,可以看出他竞争的决心。咏物原典是清人的竞技场,而姜、张的原典则是浙西词人群的竞技目标。这样或者说明他没有追和姜、张作品的原因,创作上反而“取法南宋”。谭献所言的“太鸿思力可到清真,苦为玉田所累”,指的是厉鹗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词艺与周邦彦词看齐,甚至可以超越张炎词的境界。因朱彝尊的经典名句“倚新声,玉田差近”[10](P312)在前,产生不能跨越流派始创人的心态。厉鹗没有致力在姜夔的自度曲上创造新的境界,只写了三首《疏影》、一首《扬州慢》和一首《淡黄柳》,而《暗香》则欠奉。他也没有使用张炎名作的词调,如《南浦》《解连环》等。但“填词至太鸿,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谭献认为厉词可以与吴文英词争一席位。吴文英《霜叶飞·重九》重阳佳节忆亡姬。上片写登高的情景,“断烟离绪”“香噀西风雨”,相互衔接,以景写情,烘托“凄凉”“咽寒蝉”“倦梦”之伤情。下片由景入情,饮酒治伤却又无法排遣对逝者的思念,“尘笺”“断阙”照应上片的伤情,“早白发、缘愁万缕”则照应上片的情景,也是忆亡姬的结果,期望“约明年,翠微高处”,但只是自我安慰而已。厉鹗《霜叶飞·九日葛岭》景、情、韵和主题承接吴词,写作方式却有所不同。上片写登高的情景,“最愁秋壑”“秋蛩秋草秋树”,四次重复“秋”字,回绕重阳佳节的景况,以景写情,烘托“清觞泛羽”“铜驼恨事”之伤情。下片由景入情,吹笙治伤却又无法排遣对逝者的忆念,“醉中休倚能赋”则照应上片的情景,也是忆亡姬的结果,期望“谩再寻、西峰顶”。结句的“海天空处”照应首句“最愁秋壑”,延长全词的淡淡哀愁,笔锋清绝。厉鹗用同韵同字,“树”“雨”“羽”“古”“素”“赋”“语”“缕”“去”“处”, 虚实相间,创造相同的凄楚情感,但又能贯彻其清雅风格。厉鹗《澡兰香·癸丑淮南重午》写端午佳节怀念琵琶歌姬,与吴文英《澡兰香·淮安重午》写端午怀念能歌善舞的姬妾,异曲同工,各显特色。可惜,“世人争赏其饾饤窳弱之作,所谓微之识碔砆也”,读者的接受与作者的创作出现落差,是时代审美眼光的追求有异所致。
于前贤方面,如“追和曹侍郎韵”,其作有《满江红·钱塘观潮》,“追和陈迦陵韵”,有《摸鱼子·咏窝丝糖》。这些都是他挑战当代经典作品的示范,暗藏超越前贤的创作心态,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由后学建构新的经典。如《满江红·钱塘观潮》,前段写钱塘江大潮的汹涌、英灵不灭的怒气冲天,中段描绘钱塘江大潮吞天地的气势,后段语调由急转缓,抒写观大潮的感受。这种写作手法与曹溶《满江红·钱塘观潮》如出一辙。厉词中的“乍龛赭、中间怒吼,一痕如发”“奇险胜,瞿塘雪。倾城看,中秋月”“想钱塘、破阵万灵归,纷幢节”,分别照应曹词的“谁荡激、灵胥一怒,惹冠冲发”“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月”“是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相同的铺排技法是延续经典作品的方式,作者希望创造与前贤一样的高度,符合读者的阅读期望,容易为新时代所接受。但前贤的作品难以超越时,则作者的创作思维反而为名篇所绊。朱彝尊词的前、中、后段分别是“日未午、樟亭一望,树多于发”“遗庙古,余霜雪。残碑在,无年月”“趁高秋,白马素车来,同弭节”,都是倾向曹词的写作模式,唯渲染钱塘江大潮的气势却稍逊色。而厉词稍逊朱词。《雪狮儿》四首是他追和朱彝尊咏猫的作品,与吴焯约定“戏效其体,凡二家所有,勿重引焉”,坚守创新的原则。内容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猫事,如“扑罢蝉娥,更弄飞花成阵”“忽起惊跳风竹”“携儿乳饱”“食有溪鲜,又上小庭高树”等,细致描写猫的举动,趋于生活化。在经典化前贤作品的基础上,词宗如厉鹗也希望在原典上再献新猷,但在创作心态上暗含影响的焦虑。在期望超越前贤、实现自我的前提下,厉鹗只好在清雅的美学上,在艺术形式和音律上钻研咏物词的技艺。诚如张其锦所言,厉词“琢句炼字,含宫咀商,净洗铅华,力除俳鄙,清空绝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垒矣;又必以律调为先,词藻次之”[2]( 第二册,P630)。唯后人没有他的气质、才华和学问,故只看到其“饾饤窳弱”之处。
厉鹗喜用“清”“冷”“寒”“凉”“淡”“雪”等冷色字词,予人清雅的视感。写景状物方面,如“流金桥下清泠水”(《玉阑干·金沙滩荷花》)描写流金桥下的清冷,“好似秋容惨淡,吹笛夕阳楼”(《八声甘州·京口》)描写建陵和练湖的惨淡景色,《高阳台·落梅》以“雪没鞵痕”“冷梦迢迢”“自裹冰绡”等,映衬梅花无声自落之伤;抒怀方面,如“楝风迟、不觉花深寒悄”(《真珠帘·雨夜汪青渠中看芍药》)写雨夜观芍药花的心情,“似寒鸦身世,惊栖不定”“此中清绝”(《水龙吟·雪中忆西溪》)写雪中忆西溪的孤清;写节令方面,如“余寒犹是连寒食”“文园多病何人惜”(《绛都春·清明风雨》)写清明、寒食节形单影只的孤寂,《永遇乐·戊戌闺中秋》写闺中秋再度月圆,井旁的梧桐树又有新的绿意,此情此景应该是美景良宵,但他却形容为“罗荐较凉前度”,并抒写“此情此夜尤苦”“不少伤心处”等寂寥。厉鹗无论是描写景物,还是咏物、抒情等方面,皆隐约渗透愁绪,冷色字系显现其孤洁的风骨,自怜自伤之情。张景祁评厉词“幽隽”[2]( 第四册,P1670),吴衡照指“樊榭有幽人气,唯冷故峭,由生得新”,转引谢山所言“深于言情,故其擅场尤在词”[1](第三册,P2459),相信就是使用冷色字系的效果。用语生僻反而予人新奇的印象,即现代诗的陌生化表达艺术。
厉鹗词中渗透着个人恬淡的性情。有不少作品是写浴佛、寺院、僧院,如《天香·浴佛》上片写四月初八厨娘准备浴佛的情况,下片写自己虔诚礼佛的过程,抒发“爱淡裹轻”的情怀。《秋霁·金山寺》以“树影中流”“清晓碎霞飞近岸”等形容金山寺的恬静环境。《燕山亭》(劫化荒磷)写龙兴寺的舍利,“比雪后峨眉,佛灯吹遍”。《探春慢》(凤去山枯)写宋宫洗铅池在梳妆台侧今改为僧院,抚今追昔,“换了空门,孤灯春雨鸣磬”,寂静凄冷。对于久居的小玲珑山馆,写来更是淡泊。馆内的淡月下的树影似有还无,“比雪还轻,度水无痕”,而结句“笑雨余、一种沾泥,付与老禅为伴”(《疏影·小玲珑山馆赋絮影》)的低缓回响,隐含出世思想。
五 再续清雅:经典化厉鹗词
挑战经典是清词人的普遍心理,是由当代词人群促成的写作生态环境,发挥无可估量的群体创作力量。一是厉鹗成为学词的对象。汪沆忆及,“余素不工倚声,窃闻余师樊榭先生论词之绪余有年矣,谓词权舆于唐,盛于宋,沿流于元明,以及于今”[2]( 第二册,P503)。厉鹗的词学识见不凡,具典律的意识。王昶忆述,“余少颇喜词,既从樊榭、南香游”[2]( 第二册,P543)、“近则以竹垞、樊榭为规范”[2]( 第二册,P662),提供学习词学的门径,具示范的意识。王昶的《国朝词综》选录朱彝尊(65首)、厉鹗(54首)、赵文哲(46首)、王时翔(45首)词最多。王昶特别重视朱、厉词,把他们的作品独立成卷。这是从选本角度经典化厉词的例证。姚燮忆述“近协竹垞、樊榭之同声”[2](第二册,P814)。二是厉鹗成为词学的目标。蒋敦复指出“奚必口摹朱厉,心追姜张”[2]( 第三册,P1273)。王鹏运指项鸿祚《忆云词》四卷“清空婉约,能化竹垞之方重、樊榭之堆垛”[2](第二册,P878)。厉鹗与朱彝尊并举,是经典化厉鹗的重要里程碑。进入王昶的年代,流派“涩体”的情况更甚,王昶慨叹“自樊榭老仙逝后,武林词学歇绝”[6](第二册,P1210)。陈庆溥也表明“方今词学日盛,人才辈出,岂无樊榭其人者?”[2]( 第三册,P1144)流派后劲不继,只好加强中期词宗厉鹗的词文学地位,巩固流派的领导位置。郑文焯指刘炳熙《留云借盦词》五卷“深美闳约”,“岂近世朱厉雕琢曼辞,衍为浙派,所可同日语哉”。[2](第四册,P1743)三是应和厉鹗词论。如吴锡麒论词时,多次正面肯定厉鹗的贡献:“吾杭自樊榭老人藻厉词坛,掞张琴趣 ,一时如尺凫、对鸥诸先辈,合尊促席,领异标新,各自名家,徽徽称盛。”[15](P282)江浙文人如吴焯等人相继追随厉鹗酬唱。“吾杭言词者,莫不以樊榭为大宗。盖其幽深窈渺之思,洁静精微之旨。”[15](P281)吴锡麒辈的杭州词人群十分推崇厉鹗词,后学以此吸纳新血,创造旧群体影响新群体,或以新群体巩固旧群体。四是追和厉词。如王昶作《天香·烟草和厉太鸿作》两首,陈章作《天香·和樊榭咏烟草》一首。他的《天香·烟草》新题,继和者遍及大江南北。吴锡麒继续“戏仿其体”《雪狮儿》得词四首,扩充《沁园春》的女性身体写作范围,为《西子妆·题樊榭先生〈湖船录〉后》题词,等等。郭麔在《灵芬馆词话》卷一录以补《樊榭词集》不存,以《菩萨蛮》调追和《河传》词,创作《菩萨蛮·顾升山蔬果十五种》15首词。
凡此种种不同年代的文学活动,个人能够影响、被影响或反被影响他人的创作心理。文人往往是在相互竞争中,创造群体内外的力量,又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认同或改变文学趣味,而不同的文学风格就在其中成长。群体发挥深浅不一的影响,但本质上仍然是通过经典化前贤的作品,为自己争取可持续性的发展方向。这是清词人的特殊创作心理。他们根据这种根深蒂固的竞争心态,创造连绵不绝的清词。清雅的审美范畴,是厉鹗以虚化的方式修正流派中期的雅正思想,指示学词门径,指导学词者走上清雅的道路。厉鹗的清雅论隐然再次虚化词的内容或本质,是不可以量化的虚体。在典律过程中,文人重新抬高厉鹗词学及其词来凝聚文人,渐次形成新的力量,建构新的经典。这种方法隐含潜藏在内心回避现实的心态。厉鹗式的艺术形式美,过度强调清新淡雅的韵致,徐珂评其词风“钞撮堆砌,音节顿挫之妙,未免荡然”[16](上册,P187),忽略内容上的开拓及思想上的沉淀,狭獈的词学观遂使流派中、后期的词渐现弊病。
嘉庆以后,常州词派逐步取代浙西词派,词坛出现多样化的局面。浙西词派出现不同的声音,或指斥朱彝尊推尊南宋词之过,或归咎于厉鹗专取姜、张词之失。晚清,常州词派的主将谭献部分肯定厉鹗,使他失去原有的光环,渐次为后学所忽略。至于晚清三大词话,只有陈廷焯集中讨论过厉鹗词,多以“幽” 而非“清”来形容之,如“幽香冷艳”[1](P346)“措词最雅”[17](P347)、“造句多幽深”[1](P429)、“幽艳”[17](P441)等。这是从经典化到去经典化的举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文学或人物,就算是词坛盟主或流派巨匠也需要经受时代的考验。到八十年代,严迪昌高度评价厉鹗,指出他是浙词巨匠[18](P325-336),他的文学地位又再逐渐提升。《全清词》以“清峭雅洁”确证厉鹗词及其词文学的成就,相信研究厉鹗的学者不会间断。
六 结语
厉鹗在清词文学上的意义,表现在凭借文人自觉的创作意识,推动了时代群体的审美经验,而建构经典的意图就在其中发挥凝聚力,成为群体创作的原动力。这种“振其绪”“骋于后”的举措,仍然值得今人借鉴。而经典化厉鹗词是漫长的历程,由“清和恬淡”到“清微幽眇”再到“清空微婉”,反映了新时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的转变,后来又经过“幽香”“幽深”“幽艳”等考验,才成为今天“清峭雅洁”的好评。厉鹗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词人,最终成为经典词人。今人从他的词学思想、创作心态、学问才华、孤高性情等特质,似乎找到精神上的出路,也在创作上得到启发,诸如吸收前贤精髓、博览群书、创造新的写作方向、注重个人与群体的互动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