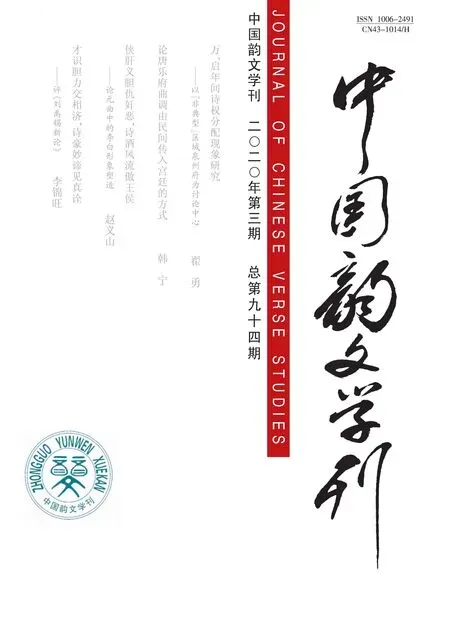“七宝楼台”如何筑成:论梦窗词的文本空间构造手法
2020-11-18宋学达
宋学达
(香港浸会大学 中文系,香港 999077)
吴文英是唐宋词史上最具艺术个性的词人,其词作被喻为“七宝楼台”,出自张炎《词源》卷下:“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1](P259)历代论梦窗者几乎皆将此论奉为经典,但大多同样与张炎一样立足于贬义,批评其破碎与隔膜,王国维甚至在《人间词话》中写道:“梦窗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2](P4251)直接冠以“凌乱”二字。倘若果真如此,则梦窗词之文本空间,应当如温庭筠那些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的词作一样,是一种零散的“拼合”结构(1)参宋学达《碎片化:温庭筠词的特殊文本空间结构及其艺术功效》,《华夏文化论坛》第23辑,吉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6~85页。。但事实并非如是,吴文英在其词作中搭建的“七宝楼台”,实际上是一种经过惨淡经营而精心结撰的文本空间,具有精密的内在结构,虽然“碎拆下来”的确是“不成片段”,但若不去“碎拆”,则这“七宝楼台”无疑是极尽交叠错综、回环往复之妙的。对此,刘扬忠先生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曾有论辩:
所谓“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前八个字算是说对了,梦窗词的确总体上给人以镂金错彩、珠翠满目之感;但后八字却自相矛盾,全然不通情理。好端端的、美轮美奂的七宝楼台,珍之护之尚恐不及,你为什么要想着把它拆碎?凡建筑物,既经“碎拆”,还有成“片段”的吗?再说,“碎拆下来,不成片段”,难道一定是个缺点吗?这岂不是证明这座七宝楼台内部结构紧密而精严,因而是拆不得的吗?[3](P424-425)
“紧密而精严”,证明吴文英对“七宝楼台”构建,并非随意而为之,而应当是经过一番惨淡经营的。那么,吴文英究竟是运用何种巧思去勾勒“七宝楼台”的建筑图纸呢?本文试从其词作文本空间的时空回环、空间转换与布局方式这三个方面进行解析。
一 腾天潜渊:幅度极大的时空回环
清代词学家周济对梦窗词的评论,有“腾天潜渊”与“空际转身”二语,前者出自《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4](P1643),后者出自《介存斋论词杂著》“梦窗每于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5](P1633)。此二语,皆可用以总结梦窗词文本空间之结构特点。本小节先论述前者。
钱鸿瑛先生在《梦窗词研究》一书中曾指出:“所谓‘腾天潜渊’,不过是对其结构曲折多变的形容。”[6](P219)这里的“结构曲折多变”,也就是指文本空间结构的曲折回环。在词史上,吴文英被视为周邦彦词法在南宋的踵步者之一,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十引尹焕语云“求词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7](P172),沈义父《乐府指迷》亦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8](P278),皆指出了梦窗词对清真词的艺术继承关系。周邦彦对词作文本空间的建构,是通过“思力安排”刻意制造时空的回环,这一方面自然也被吴文英所取法,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四库馆臣在《梦窗稿提要》中有论曰:“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9](P822)即指出吴文英作词在“思力安排”上的用心,是要甚于周邦彦的,也正源于此,梦窗词文本空间的“环形结构”,较之清真词更加复杂难解。
吴文英笔下纷繁复杂的时空回环,在其代表作《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中可见一斑。这首词的内容,应如叶嘉莹先生所言,乃是悼念“在感情方面所曾经体认到的一份残缺和永逝的创痛”[10](P168)。吴文英是一个深于情更痴于情的词人,虽然关于他的情感经历,尚有“苏州遣妾”“杭州亡妾”(2)夏承焘《吴梦窗系年》:“集中怀人怀人诸作,其时夏秋,其地苏州者,殆皆忆苏州遣妾;其时春,其地杭州者,则悼杭州亡妾。”见《夏承焘集》第1册《唐宋词人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67页。之二姬或“一遣姬、一故妾、一楚伎”(3)参杨铁夫《吴梦窗事迹考》,见杨铁夫笺释,陈邦炎、张奇慧校点,《吴梦窗词笺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之三姬等异说(4)关于吴文英姬妾诸说及相关考辨,可参考孙虹、谭学纯《吴梦窗研究》第四章《梦窗扬州、杭州、苏州情事考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348页。,但其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旨在怀念永逝的爱情,却是毫无疑义的。通过这首词中的“十载西湖”诸语,可知其中所怀之人乃“杭州亡妾”,夏承焘先生谓之“述离合死生之迹尤详”[11](P466-467)。同时,《莺啼序》这一240字的四片长调,是宋词中篇幅最长者,且以吴文英此作为最佳。蔡嵩云《柯亭词论》云:“填此调,意须层出不穷,否则满纸敷辞,细按终鲜是处。又全章多至四遍,若不讲脉络贯串,必病散漫,则结构尚矣。此外更须致力于用笔行气,非然者,不失之拖沓,即失之板重。此调自梦窗后,佳构绝鲜。梦窗作三首,以‘残寒正欺病酒’一首尤佳。”[12](P4916-4917)蔡嵩云此论,谓填制《莺啼序》首先要“意须层出不穷”,其次要“讲脉络贯穿”,即在文本空间的构建上,一方面要有外在的跌宕起伏,另一方面也应具备内在的精致勾连,而吴文英此作正兼具此二者。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称这首词为“大开大合却又曲折回旋”[13](P385),村上哲见先生则于《宋词研究·南宋篇》中誉之以“灿烂成熟期宋词极为精致的样态”[14](P467),此二论合于一处,正是对此词“内外兼修”的肯定。当然,要真正说明这首《莺啼序》的文本空间是如何“内外兼修”,还是需要对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
因词作篇幅较长,为方便分析,我们直接将其拆解开来,先看第一片: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15](P986)
这一片,可依据“户”“暮”“树”“絮”四个韵脚划分为四个空间单元。第一单元的空间场景为“沉香绣户”,乃室内空间;第二单元描写“飞入西城”的燕子,跳跃至室外空间,且相对高远;第三单元同样是室外空间,但内敛至水中“画船”与岸边“吴宫树”这一相对有限的场景;第四单元则为空间“闪回”,以“念”字将时空转入过去时态的“羁情游荡”,但随即以“随风化为轻絮”又拉回到现在时态。初看这几句词,会发现其中的空间转换虽确有由狭小而高远、进而收敛再转入绵长的腾挪跳宕,但其间的关系却似乎是凌乱不堪的,从狭小的“沉香绣户”转入高远的室外空间,再收敛至烟柳画船,这种转换无法解释为词人的行动轨迹,亦找不到可将其串联起来的故事线索。而倘若仔细品味其中的行文脉络,便会发现前三个单元的空间转换,是可以被第一单元的“残寒”、第二单元的“春事迟暮”、第三单元的“清明过却”这三个包含时令信息的词汇勾连起来的,由此才能领会到词人于此处的匠心所在,乃是借三组包含伤春情绪的画面烘托出一种悲情,进而推出第四单元的今昔感怀。而这种今昔感怀,又直接开启了第二片: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15](P986)
换头的“十载西湖”四个字,将时空“闪回”至过去,而整片所写,正是与情人相识相伴的欢愉回忆。因此,整个第二片实际上都是对第一片中的空间“闪回”片段即“羁情游荡”的展开铺叙。这一片的文本空间并没有什么起伏波澜,反而颇具“有首有尾”式的流畅感。然而,在接下来的第三片中,却陡然转折: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15](P986)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是对时间的拉伸,同时也借花谢花开之意象将第二片中的欢愉转入离别的苦楚,时间拉伸后的“水乡尚寄旅”一句,已经是离别后的境况。其后叙写别后回访,而斯人已逝的深悲剧痛,进而再度回忆“长波妒盼,遥山羞黛”之容颜与“渔灯分影春江宿”的欢愉,又在情绪与时序上做一转折,最后接入“败壁题诗”的临别情境,在时序上补完了第二片到第三片之间因时间拉伸而省略的情节。结合第二、三片来看,文本空间运行的时间线经历了由别前跳跃至别后、由别后推进至重访、由重访“闪回”至别前、由别前推进至别时这四重时空的转折与承接。按照正常的“故事时间”,第三片后半部分的别前与别时,原本应在第二片之后,但词人在第三片起首处直接写别后情状,无疑是有意打乱时序,而这两片中的曲折叙事,又皆可归于第一片的“羁情游荡”之中。同时,文本空间的运行状态由第二片的流畅突然进入第三片的密集转换,更突显出了第三片层出不穷的跌宕感,这种艺术手法上的对比,也体现出了吴文英经过惨淡经营而呈现出的艺术匠心。最后来看第四片: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15](P986-987)
换头处的“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三句,将第二、三片中整体上属于回忆的过去时态重新拉回到当下的现在时态,同时对前文所写的内容作一个承上启下的空间总结。陈洵《海绡说词》云:“望字远情,叹字近况,全篇神理,只消此二字。”[16](P4848)此处的一“望”与一“叹”,正合乎对景怀人之兴发感动的心理时间逻辑,“望”所见乃“草色天涯”,借用秦观《八六子》之“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17](P19),总揽上文之一切伤逝之愁,而“叹鬓侵半苎”除了总括上文所追忆的旧日时光,也关合了第一片中的伤春意绪。其后由检点旧物进而直抒悼亡之情,动人心魄的幽恨出之以比拟借代的形象感,“亸凤迷归,破鸾慵舞”“蓝霞辽海沈过雁”“伤心千里江南”等句亦略有空间腾挪之妙。同时,种种物象和意象又能与前文所叙情事相互关联,形成时空回环,盖如陈洵所析:“‘欢唾’是第二段之欢会,‘离痕’是第三段之临分。‘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应起段‘游荡随风,化为轻絮’作结。通体离合变幻,一片凄迷,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然得其门者寡矣。”[16](P4848)
通过对这首《莺啼序》的拆解分析,可以看到其中看似凌乱、实则暗藏神理关联的文本空间结构。简单说,就是由第一片的伤春之感推出第二、三片的旧日回忆,再总入第四片的一“望”一“叹”,其后直抒悼亡又于细微处关合前文,其文本空间的内在结构不可谓不精致。而就其外在的空间感而言,则又可谓波澜起伏、变化无穷,在第一片之中,既有狭小、开阔、绵长这三种空间感,其后的第二、三篇偏于叙事,又于各臻其妙的“有首有尾”与“转折变换”的艺术对照中突出文本空间运行的层次感,前三片已是多种空间变换的“大开”,而第四片又有一“望”一“叹”的“大合”,这种“大力包举,一气舒卷”[12](P4917)的空间铺展与收束,真可谓有“腾天潜渊”之势,令人叹为观止。
二 空际转身:不着痕迹的空间转换
梦窗词在空间的转换与衔接方面,更有“空际转身”的特点。所谓“空际转身”,即指梦窗词的空间转换往往出人意料,常常呈现为毫无征兆甚至不讲道理的突转与跳接。与前人比较,吴文英在这方面的特点十分突出,如柳永词中的空间转换处,一般都可以找到“记得”“念”“旧日”等明显的提示线索,而周邦彦虽然偶尔会有意隐去时间信息,但其空间转换的脉络也往往是有踪迹可寻的。吴文英却与此不同,虽然在他的一部分词作中也能看到线索明晰的空间转换,但更多的是“一般人不常用的暗转”[18](P824),故意隐去一切提示性的词汇,有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所谓的“于无字处为曲折”[19](P4407)。可以说,“空际转身”是吴文英制造“腾天潜渊”之势的基本手法,而“腾天潜渊”则是“空际转身”所造成的艺术效果,此二者互为“七宝楼台”式文本空间之表里。当然,梦窗词之“七宝楼台”是如何“空际转身”的,还是需要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析来说明。
梦窗词中,至少有九首作品在前辈词学家的笔下获得过“空际转身”的评价,其中也包含上一小节中所分析的《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陈匪石于《宋词举》中赞之云:“此词绵密之情,醇厚之味,炼意琢句之新奇,空际转身之灵活,则由愚前四首所论,可隅反而得之。”[20](P3606),所谓的“前四首”,分别是《霜叶飞》(断烟离绪)、《惜黄花慢》(送客吴皋)、《花犯》(小娉婷)和《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在《宋词举》中,陈匪石对这四首词之章法皆有分析,只是并未具体论述是如何“空际转身”的,而对于《莺啼序》一词“空际转身之灵活”的评价,亦略显笼统。此外,经过上小节的分析也可以发现,《莺啼序》一词虽然在空间结构的布置方面可谓极尽繁复错综之能事,但其内在的脉络线索还算是比较明显的。
另外四首被直接冠以“空际转身”的词作,分别为《齐天乐·会江湖诸友泛湖》、《高阳台·落梅》、《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和《渡江云·西湖清明》,其中前二者皆出自陈洵《海绡说词》,先看第一首《齐天乐》:
麹尘犹沁伤心水,歌蝉暗惊春换。露藻清啼,烟萝澹碧,先结湖山秋怨。波帘翠卷。叹霞薄轻绡,汜人重见。傍柳追凉,暂疏怀袖负纨扇。 南花清斗素靥,画船应不载,坡静诗卷。泛酒芳筒,题名蠹壁,重集湘鸿江燕。平芜未剪。怕一夕西风,镜心红变。望极愁生,暮天菱唱远。[15](P364)
陈洵云:“‘一夕西风’,空际转身,极离合脱换之妙。”[16](P4858)在“一夕西风”之前的绘景与写情中,虽有“伤心水”“歌蝉暗惊春换”“湖山秋怨”等意象,但其运笔的立足点大体上都在现在时态的客观外物之上,其情绪主要为“汜人重见”之惊喜与“重集湘鸿江燕”之快意;而走笔至“怕一夕西风,镜心红变”一句时,却在主客观、情绪、时态方面都有所转换,此处之“怕”是主观情绪,由所见“平芜未剪”兴发而来,因见夏日之草木葱茏起悲秋之意,情绪亦由喜入悲,“镜心红变”则显然是想象中的未来场景。这种由客观而主观、由喜悦而悲愁、由现在而将来的转换,虽然在前文中有所伏笔,亦有脉络可寻,但依然显得十分突然。再来看《高阳台·落梅》:
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 寿阳空理愁鸾。问谁调玉髓,暗补香瘢。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离魂难倩招清些,梦缟衣、解佩溪边。最愁人,啼鸟清明,叶底青圆。[15](P1320-1321)
陈洵云:“‘南楼’七字,空际转身,是觉翁神力独运处。”[16](P4863)此词咏梅,前二韵叙写“无人野水荒湾”中的落梅,其背景空间为野外,所描写的物象立足于客观;而“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两句则陡然转入主观抒情,高建中先生解赏此处云:“‘不恨’与‘恨’对举,词笔从山野落梅的孤凄形象移向关山阻隔的哀伤情怀,隐含是花亦复指人之意。”[21](P140)讲明了这一转换。其后则借此转换处的“南楼”再转入庭园场景,下片铺叙众多与梅花相关的典故再咏之,且以“解佩溪边”关合最初的“野水荒湾”,形成文本空间的“环形结构”。这首词在“南楼”处的时空转换,与前面说描写的落梅形象可以说只有意绪上的关联,而空间的跳接却可谓毫无逻辑关系,此“空际转身”不仅突然,更颇有些不讲道理的意思。
再来看第三首《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覇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阁凭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15](P1419)
这首词的“空际转身”之处,在《唐宋词简释》中被唐圭璋先生点出:“‘问沧波’以下,空际转身,将吊古及身世之感尽融入景中。”[22](P218)邓乔彬先生在《唐宋词艺术发展史》中亦指出:“‘问苍天’(5)按:邓乔彬先生此处依《彊村丛书》本《梦窗词集》“波”作“天”。见朱孝臧编纂《彊村丛书》,广陵书社2005年影印版,第1054页。以下,则是空际转身之笔,换写吊古之意,兼出身世之感,二者融入青山碧水、乱鸦斜日的景色之中。”[18](P825)确如二位先生所言,“问沧波”之前皆为吊古,此后则转入“华发奈山青”的身世之悲,其间情绪虽有顺承,但转折亦略显突然。
对第四首《渡江云·西湖清明》的“空际转身”之评价,则出自杨铁夫。先看其词:
羞红颦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旧堤分燕尾,桂棹轻鸥,宝勒倚残云。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肠漫回,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 逡巡。题门惆怅,堕履牵萦,数幽期难准。还始觉、留情缘眼,宽带因春。明朝事与孤烟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山黛暝,尘波淡绿无痕。[15](P23-24)
杨铁夫在《吴梦窗词笺释》中释“明朝”三句云:“兜头一转,力重千钧,所谓空际转身法。梦窗神力,非他人可及。此等笔法,随处遇之。”[23](P6)这首“其时春,其地杭(州)者”[11](P467)的怀人之作,所悼念之人应当也是“杭州亡妾”。词之上片抒写重游旧地时对旧事的回忆与感念,其用情甚深,以至于出现了“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的幻觉,下片则承接这一幻觉,进入对“题门”“堕履”“幽期”等情事的回忆之中;而在“明朝”一句处,词人的思绪突然从缠绵悱恻的幻境回到“事与孤烟冷”的现实之中,这一毫无征兆的转换,恰如陈洵“明朝以下,天地变色”[16](P4845)之喻。
梦窗词具有“空际转身”特点的词作,绝不止于上述几首,而是如杨铁夫所言,乃“随处遇之”。同时,前辈词学家对梦窗词“空际转身”的论述,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转换的突然性这一点上,而吴文英“空际转身”式的空间转换笔法,还有另一层更为重要的含义,即“暗转”法。这种空间转换手法,在下面这首《踏莎行》中表现得尤为典型,且看其词:
润玉笼绡,檀樱倚扇。绣圈犹带脂香浅。榴心空叠舞裙红,艾枝应压愁鬟乱。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香瘢新褪红丝腕。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15](P1542)
词之上片仅以聚焦法描写一女子之体态及衣饰,而对女子之情绪、行为没有任何交代;下片换头突接“午梦”二句,倘若顺向解读,则做梦者当为上片所写的女子,而女子何以梦到“千山”,亦朦胧难解,其后一句“香瘢新褪红丝腕”又是聚焦于女子之细节,与前两句之间找不到任何过渡或关联,而末二句又突然转入凄风苦雨的相思幽怨,同样毫无逻辑。此外,词之上下片之时令亦有龃龉处,盖如吴世昌先生所言:“此词上用‘榴心’‘艾枝’,是端午景象,下片又用‘晚风菰叶’‘秋怨’,一首之中,时令错乱。且上片晦涩,令人不堪卒读。盖先得末两句,然后硬凑出来。”[24](P287)初读这首词,确实感到不知所云,且颇有“硬凑”的碎片拼合感。然而刘永济先生却有不同看法,其《微睇室说词》指出:
“犹代”“空叠”“应压”等词,明其人不在目前者。其所以如此描写,须至下半阕方知。……换头八字始将上半阕所写点明是一场梦境。曰“千山”,梦去甚远也。曰“一箭”,梦醒甚速也。“香瘢”句仍从端午着笔,《风俗通》谓五月五日以彩丝系臂,辟鬼及兵,名长命缕。故曰“红丝腕”。“香瘢新褪”者,旧事无痕也。歇拍二句言午梦醒来,别无所见,唯有“雨声”“菰叶”伴人凄寂而已。[25](P185)
刘永济先生的观点,是在上片与下片之间的“午梦”一节处不做顺向解读,而将“午梦”视为另一男性抒情主人公的梦,由此则上片所写的女子便成了男子梦中思念之人,其后“香瘢新褪红丝腕”一句乃梦醒后相思的延续,再由相思不得而接入末二句之凄风苦雨,则顺理成章。通过这样的解读,可以发现在这首词中,吴文英在梦境、现实、回忆等空间转换之关节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有的空间转换都是暗中完成的,如果错失了暗藏于文本深处的行文脉络,自然只能得到“不堪卒读”“硬凑出来”的凌乱印象。而就算我们通过非顺向解读对词中的“暗线”有所把握,这首词依然有令人费解的地方。因为末句的“菰叶”这一物象也与端午相关,“菰叶”即茭白叶,乃制粽子所必备,而云“菰叶生秋怨”,则此处时令究竟是端午还是秋季,亦晦涩难解。刘永济先生认为末二句之时节依然是端午,解释云:“方端午而曰‘秋怨’者,愁人善感,‘雨声’‘菰叶’之中,一梦醒来,凄然其如秋也。”[25](P185)然而若作秋季见菰叶而忆端午之人解,同样说得通。如此则“菰叶”二字逆挽全词,梦中见昔日情人,梦醒后见“菰叶”而想起“香瘢新褪红丝腕”,而端午之印象又附加至梦中女子的形象上,故曰“犹代”“空叠”“应压”。可以说,这种“暗转”的“空际转身”手法,是造成梦窗词“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8](P278)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七宝楼台”内部“环形结构”之精微细致的最集中体现。
三 交叉铺叙:情感先行的布局方式
有“离合顺逆,自然中度”[16](P4841)之称的周邦彦词,其“环形结构”的文本空间已然可以让人有“莫测其用笔之意”[26](P56)的感叹,而青出于蓝的吴文英,更是以“腾天潜渊”之势而在“空际转身”之中打造出了“炫人眼目”的“七宝楼台”。但同时,吴文英也从周邦彦那里继承了晦涩的弊病,正如夏承焘先生在《词源注》之前言中所论:“吴词浓丽绵密,本近周词;周词晦涩之弊,表现在吴词里最为突出。”[27](P6)吴文英词的晦涩难解,一方面源于上文所论述的“空际转身”之“暗转”法,另一方面则在于其布景设境的不循常理。
吴文英的创作,明显属于“造境”而非“写境”。陶尔夫先生在《南宋词史》中曾指出:“梦窗词在艺术上能够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拘限,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虚构出许多离奇虚幻的审美境界。”[28](P285)其中“虚构”二字点出了吴文英作词突破时空拘限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吴文英对文本空间的塑造,并非单纯地将其所见所感的现实世界“折射”入文本,而更多是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打造各种合适的时空场景序列。正如杨海明先生所言:“梦窗好以抽象之物(如‘秋’,如‘春’,如‘梦’,如‘思’等等)和具体之物胶葛在一起来写。此种写法,全凭自己之独特的心理感受,而不大依循传统所惯用和习知的修辞法,颇能显出他不同于常人的特色。”[13](P393)而邓乔彬先生则将这种写法更明确地总结为“缘情布景”:“北宋词以就景叙情为多,如柳永、秦观,南宋渐开即事叙景一途,如稼轩、白石。吴文英词多为意胜于实的主观抒情,所以,另走缘情布景的道路,这就形成时空转换自由的特点。”[18](P820)这种“缘情布景”的写法,在上文已分析过的词例中已可见一斑,如《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第一片中的“沉香绣户”、“飞入西城”和“画船”等空间单元,就是以伤春之情绪做串联整合。也就是说,吴文英在其词作中的设景造境,并非源于由现实中的自然或人文空间所引起的兴发感动,而是情感先行,依据情感的脉络调动一切眼前所见的情境、回忆中的情境、想象中的情境、甚至幻觉中的情境进行铺设,如此写来,词作的文本空间就能最大程度地摆脱现实空间的拘限,真正构成惝恍迷离的“七宝楼台”。
吴文英的“缘情布景”,很接近曾大兴先生在《柳永和他的词》一著中提出的“交叉铺叙”法。所谓“交叉铺叙”,原本是曾大兴先生对柳词铺叙技法的一种总结,其界定为:
通过联想、幻觉和回忆等诸多方式,突破自然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将整体的人生历程切割开来,又将不同时空的生活图景和情绪体验组合在一起,多侧面、多层次地描写生活,多角度、多方位地抒发情感。[29](P114)
曾先生视柳永的《戚氏》(晚秋天)一词为“交叉铺叙”的“典范之作”,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分析此作“开阖动宕的艺术效果”(6)参见曾大兴先生《柳永和他的词》第114~115页的相关论述。。然而,《戚氏》词的基本空间结构也不过是只有一次转折的“闪回”结构,窃以为并未达到曾先生所界定的“交叉铺叙”之程度。实际上,柳永词中应该并没有这种“多侧面、多层次”与“多角度、多方位”的作品,曾大兴先生认为柳词中使用“交叉铺叙”法的词作还有《尾犯》(夜雨滴空阶)、《浪淘沙》(梦觉)和《引驾行》(虹收残雨)等“尝试之作”,但也承认这些作品“总的成就不及《戚氏》”[29](P115),自然更达不到“交叉铺叙”的理想形态。
“交叉铺叙”法于宋词作品中的真正出现,应当是在吴文英的笔下。只有在最大程度上脱离现实空间拘限的梦窗词,才能“将不同时空的生活图景和情绪体验组合在一起”。且举《齐天乐·与冯深居登禹陵》一词为例,词曰:
三千年事残鸦外,无言倦凭秋树。逝水移川,高陵变谷,那识当时神禹。幽云怪雨。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雁起青天,数行书似旧藏处。 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剪灯语。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霜红罢舞。漫山色青青,雾朝烟暮。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15](P327)
关于这首词中的时空错综,叶嘉莹先生曾有相当精到的论述。在《灵溪词说·论吴文英词》中,叶先生首先指出此词在时空转换方面的诸多龃龉之处:
其后半阕开端之“寂寥西窗久坐,故人悭会遇,同剪灯语”三句原是写夜间与故人冯深居在灯下之晤对,而其下却陡然承以“积藓残碑,零圭断璧,重拂人间尘土”三句,乃当下又转为日间在禹陵之登览。是其所写者乃忽而为西窗之剪灯夜雨(语),忽而为禹庙之断壁残碑,忽而为黑夜,忽而为白昼,如此自易增加读者之困惑。而且此词前半阕曾写有“倦凭秋树”之句,而此词之结尾乃忽然又有“岸锁春船”之语,其词中之季节竟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这自然也使人感到难以理解。[30](P367-368)
由夜间“同剪灯语”之眼前实景,到回忆日间登览禹陵所见,是一处不讲道理的“空际转身”,而结尾处“岸锁春船”与开篇“倦凭秋树”的季节错乱,也是源于此二者并非处于同一性质的时空,“倦凭秋树”乃与友人登览禹陵的当下时节,而“岸锁春船”则是在想象中的未来时空。除此之外,在上片中还有“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一句之“夜深”与下句“雁起青天”之白昼的时空错乱,而此错乱处亦源于此二句并非属于同一时空。“雁起青天”乃登览禹陵时所见实景,而“翠萍湿空梁,夜深飞去”是处于传说中的时空。盖《嘉泰会稽志》卷六载:“禹庙在县东南一十二里。《越绝书》云少康立祠于禹陵所。梁时修庙,唯欠一梁。俄风雨大至,湖中得一木,取以为梁,即梅梁也。夜或大雷雨,梁辄失去,比复归,水草被其上。人以为神,縻以大铁绳,然犹时一失之。”[31](P6804)而这些看似错乱的空间片段,又皆为抒发与友人相聚别离的沧桑之感服务,正如叶先生在随后的论述中对词中龃龉之处所作的艺术阐发:
“寂寥西窗久坐”与“积藓残碑”上、下数句之承接而言,初读之虽不免会令读者有突兀生硬之感,然而却也正是由于这种出人意想之外的承接,所以才使得故人离合的今昔之感,乃竟而与三千年古史的陵谷沧桑之慨,蓦然间结合成为一体。于是故人离合之感遂因融入了三千年之古史而使其意境更为显得深广;而三千年古史之沧桑,也因融入了灯前故人之晤对,而使其悲慨显得更为亲切。……“岸锁春船,画旗喧赛鼓”二句,乃是自今日秋季对来年春季之推想,而其中则正有无限时序推移之感。[30](P369)
叶嘉莹先生的这一解读,恰到好处地点出了吴文英在这首词中所布置的种种看似错乱的空间片段与其所要抒发的情意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吴文英为了在这首词中将“故人离合之感”与几千年的沧桑之叹融合以抒发,调动了当下、回忆、想象、传说等多种性质的空间片段,综合运用,交错出之,而其转换之间又完全不着痕迹。这种写法,才真的符合曾大兴先生所提出并界说的“交叉铺叙”法。
再来看一首《夜游宫》:
窗外捎溪雨响。映窗里、嚼花灯冷。浑似潇湘系孤艇。见幽仙,步凌波,月边影。 香苦欺寒劲。牵梦绕、沧涛千顷。梦觉新愁旧风景。绀云欹,玉搔斜,酒初醒。[15](P691)
这首词也是吴文英将现实、梦境与幻觉组合在一起以“交叉铺叙”的典型例证。词有序云:“竹窗听雨,坐久,隐几就睡,既觉,见水仙娟娟于灯影中。”[15](P691)根据此序,可知起首二韵之“窗外”与“窗里”,皆为现实所见;其后则毫无征兆地转入幻觉,“浑似潇湘系孤艇”所描述的正是半睡半醒间一种意识蒙眬的状态,而在这蒙眬之中,仿佛望见一位凌波微步的“幽仙”,这只能是一种幻觉。下片主要抒写梦中与梦后所见,梦中“沧涛千顷”,觉来见“绀云欹,玉搔斜,酒初醒”而有“新愁”。吴文英在这首词中所设置的空间片段,既有睡前与觉后的现实,也有梦中的虚境,更有半梦半醒间的幻境,而对这些片段的铺叙,亦非依照时间顺序。根据词序所述,词中的几个空间片段,应按照睡前实境、梦中虚境、半梦半醒之幻境与觉后实境这样一种顺序排列,但是吴文英在词中却将梦中虚境与半梦半醒之幻境对调了位置,且在睡前实境与半梦半醒之幻境之间完全抹去了转换痕迹,明显是一种刻意打造的时空回环;此外,换头处的“香苦欺寒劲”一语应当是促使梦醒的原因,亦是当意识清醒后的身体感觉,将其植入到梦中虚境之前,关合上片起首之“雨响”与“灯冷”,亦有曲折之妙。这首词中被错综布置的实境、虚境与幻境,并非随意走笔,而是系于对去姬或亡姬的怀念。幻境中所见之“幽仙”,化用曹植《洛神赋》之“凌波微步”典故,很明显是将其作为旧日情人的化身。斯人已去,唯余凄苦,是故全词贯穿着一种悲凉的基调。初写睡前的实境,铺设冷雨之背景,其后马上让“幽仙”登场,寄出怀人或悼亡之思;换头处不直接写梦,而关合起首之冷雨,是将悲凉的基调延入下片,最后于梦觉之实境中点出“新愁”,而冠以“旧风景”,则此“新愁”也就是“旧愁”,附着在幻境中的“幽仙”身上。由此可见,吴文英在这首词中对实境、虚境与幻境的“交叉铺叙”,皆以怀人或悼亡之愁为旨归,表面上繁复难解,但于深层却自有情感脉络。
相对于人们所习惯的现实空间,吴文英通过“交叉铺叙”法所构建的文本空间是面貌最为迥异的,因此也最难被读者所理解。加之吴文英又好以“空际转身”的空间“暗转”之法去打造“腾天潜渊”式的时空回环,梦窗词的“晦涩之弊”遭到历代词论家的批判,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这些导致文本空间繁复难解的空间构建手法,也赋予了梦窗词最为独到的艺术特质,正如陶尔夫先生在《南宋词史》中的总结:“梦窗词之所以扑朔迷离、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他不是一般地、直接去描写或反映客观现实,也不是一般地、直接地去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善于通过梦境或幻境来反映他的内在情思和审美体验,并由此构成迥异于其他词人的词风。”[28](P307)吴文英在打造时空回环与错综方面能够达到独树一帜的程度,打造出绚烂至极的“七宝楼台”,也说明在构建“环形结构”文本空间这一点上,他已经做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可以说,梦窗词代表着唐宋词在空间艺术领域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