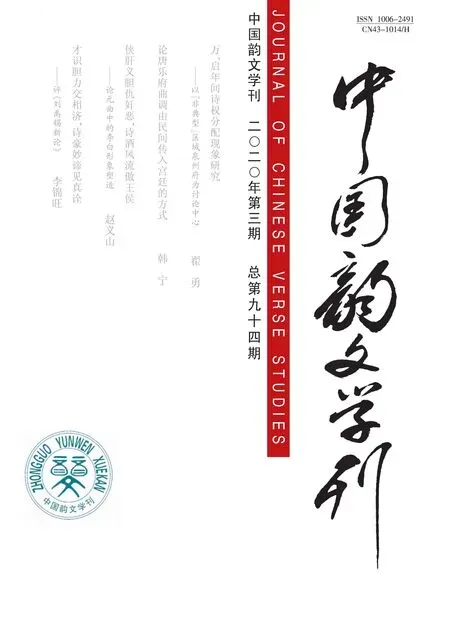元人黄文仲生平及其献《大都赋》时间考订
2020-11-18张相逢
张相逢
(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自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以降,京都赋的创作蔚然成风,代有其制。虽文体辗转相袭,但这些“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P178)的鸿篇巨制也呈现出各自时代的不同气象,可借以考见一朝之制度、一国之光华。元代定都于大都。大都所处的幽燕之地在宋代已进入都邑赋家的视野(范镇有《幽都赋》,仅存残句),但彼时的幽都,就全国版图而言仅是偏方一隅,其作为一国之首都成为京都赋家关注的对象则始于元代。李洧孙、黄文仲相继撰写以呈献翰林国史院的《大都赋》,是当时最有影响且流传至今的两篇力作,其价值一直以来颇受重视。(1)黄文仲《大都赋》撰成后,很快被收入元人所编总集《天下同文集》和类书《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陈栎《〈燕山八景赋〉考评》也曾引用其中内容以资考证。明清两代的一些文献(例如《天中记》《历代赋汇》等)亦多有采录。今人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介绍《天下同文集》,特别提到黄氏《大都赋》,认为“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况”(《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李洧孙的《大都赋》在元代也广为传诵(参黄溍《霁峰文集序》),宋濂《题李霁峰先生墓铭后》即提到他儿时因读李氏《大都赋》而慕艳其人。但因某种原因,此赋明代以来流传不广,罕见文献记载。清乾隆年间,于敏中等奉敕编纂《日下旧闻考》,将此赋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并附按语:“元李洧孙《大都赋》,朱彝尊惜其未见。今从《永乐大典》中录出增载,可以证元都之方位制度矣。”(《日下旧闻考》卷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此外,元代描写大都的京都赋,还有杨维桢《镐京赋》、顾琛《燕都赋》(已佚)。《镐京赋》以镐京(西周都城)、北京(元大都)为描写对象,通过二都的对比,抑古扬今,达到颂扬元朝的目的。其篇幅非京都大赋的鸿篇巨制,而且描写大都的内容较为笼统简略,其价值远不能与李、黄的《大都赋》相比。顾琛《燕都赋》以“燕都”为题,在当时即受到“今天朝四海一统,六合一家,燕盖昔时战国名,何燕之称”(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的讥评。可以说,李、黄二人因献《大都赋》而得名当时,流声后世。李洧孙的生平及其献赋的时间,由于有了黄溍《霁峰李先生墓志铭》的记载而清楚无疑;而黄文仲的生平及其献《大都赋》的时间,则因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或阙焉不详,或存在疑误。因此,考订黄文仲生平及其献赋时间(作赋和献赋是先后之事,时间相隔不会很久,本文暂且忽略其中的时间差),成为本文的两项主要内容。
一 “黄文仲”是《大都赋》的作者
一般认为,在元代文献中,黄文仲《大都赋》仅见载于《天下同文集》。此集是周南瑞所编,兼备诸种文体,卷十六为“赋”,收录黄文仲《大都赋》和释希陵《登太白山赋》。但《天下同文集》只是提供了《大都赋》作者的姓名,并未给出有关“黄文仲”的其他信息,以至于引起研究者对署名的怀疑。《金元辞赋论略》介绍《大都赋》时称:
该赋作者,《历代赋汇》《天下同文集》均题“黄文仲”,疑即字“文中”之黄孚。一来是,古时“仲”“中”二字互通;二来,《吴文正集》中有《送黄文中游京师序》一文,有些内容同《大都赋》相合,故基本可以认定。[2](P208)
黄二宁《元代南人献赋本事考》则认为:“如果黄孚当真曾经写作《大都赋》进献而得官,吴澄、李存等不应该只字不提。”[3]此文仍将《大都赋》的作者视为黄文仲,而非字“文中”之黄孚。但并未给出有力的直接证据。
笔者以为,由《大都赋序》“文仲幸生圣世,获睹大都,……谨摭其事,撰《大都赋》,上于翰林国史,请以备采择之万一”[4](P635)来看,此“文仲”既然是黄氏相对于翰林国史院的自称,则显系其名而非其字。“黄文中”“黄孚”说实难成立。
事实上,与作者题为“黄文仲”的《大都赋》相关的元代文献并非仅有《天下同文集》。就笔者所见,尚有两种。一是陈栎《〈燕山八景赋〉考评》曾引用此赋内容:“‘燕山八景’之名,其昉于何时、何人乎?以琼岛、太液二名观之,想起于中统以后,黄氏赋所谓‘因内海以为池,即琼岛而为圃’者是也。”(2)按,此“圃”字,在《天下同文集》和《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收录的《大都赋》中皆写作“囿”,由上下文的押韵情况来看,当以“囿”字为正。[5](P438)所引黄氏赋的两句正出自黄文仲的《大都赋》,只是陈栎未指明“黄氏”之名。
二是元初刘应李所编《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以下简称《翰墨全书》)后甲集卷八亦收录此赋(无赋序。此据明初刻本)。《翰墨全书》编纂完成于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之前,传世版本中有大德本、泰定本、明初本三种系统,泰定本主要压缩大德本而成,明初本内容基本承袭泰定本。[6]此书所收元代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已引起研究者注意。就《大都赋》而言,明初刻本《翰墨全书》于此赋题下的作者项标“黄文仲”,并于名下以双行小字注称:“三山人。上国史翰林院。”[7](P47)此“上国史翰林院”的内容可由《天下同文集》收录的《大都赋》前序文得到印证。该小字注文的价值在于,有助于进一步确定《大都赋》的作者就是黄文仲,他是三山(福建福州市的别称)人。这也为考察黄文仲的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二 黄文仲生平事迹考
有关黄文仲的生平资料,记载多阙。《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以下简称《言行录》)与《编类运使复斋郭公敏行录》(以下简称《敏行录》)(3)二书书名中的“郭公”指郭郁,字文卿,号复斋,仕至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故有“运使复斋郭公”之称。《言行录》一卷,是福州路儒学教授徐东编辑,主要记载郭郁的为政事迹;《敏行录》一卷,未详何人所编,主要收录郭郁任官所历各地文人的酬赠诗文。二书原本合刊,首为四篇序文(依次是《敏行录》二序、《言行录》二序),次为《言行录》,之后是《敏行录》。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元文宗至顺年间刻本是二书现存的最早版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以影印为二册,收入《金元编·史部》,然而仅题“运使复斋郭公言行录”之名。本文所用二书版本,即《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至顺刻本,但引用二书内容时,则分别标出书名,以免混淆。、《永乐大典》、明代朱存理所编《铁网珊瑚》、《弘治将乐县志》、《嘉靖延平府志》等文献尚存与黄文仲相关的诗文作品,有助于考察其人生平。兹从籍贯、字号、生卒年、行迹等几个方面考述如下。
(一)籍贯、字号考
由前引《翰墨全书》的内容可知,《大都赋》的作者黄文仲是三山人。福建福州因城中有九仙山(一名九日山)、闽山(一名乌石山)、越山,故有“三山”的别称。宋末元初月泉吟社征诗的第一名连文凤是福州人,文献中常称其为三山连文凤,即由于此。黄文仲在其诗文中也曾自署“三山黄文仲”。《永乐大典》卷3144载黄文仲文二篇,一为《题了翁先生论贾谊〈治安策〉》,末署“三山黄文仲敬书”;二为《题了翁手泽》,末署“三山黄文仲独愚敬书”。[8](P1862)结合刘应李的标注和黄文仲的自署,可以断定《大都赋》的作者黄文仲是福州人。
至顺刻本《言行录》卷首第一、第三篇序分别是黄文仲所撰的《敏行录序》和《言行录序》,序末分别署“至顺辛未孟春之望,长乐郡古候佚老独愚黄文仲谨序”“至顺二年辛未上元日,古候佚老独愚黄文仲谨序”。[9](卷首)至顺辛未即至顺二年(1331),孟春之望即上元日(农历正月十五日)。长乐郡是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改福州而置,治所在闽县(今福建福州市);到元代称福州路,治所在闽县、侯官县。“古候”即指候(一作侯)官县,始置于东汉末年,与闽县同为元代福州路治所。“佚老”指遁世隐居的老人。“长乐郡古候佚老”表明黄文仲是元代福州路侯官县人。
又因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曾分建安郡别置晋安郡,治侯官县(今福建福州市),故而黄文仲在其文章中也曾自称“晋安黄文仲”(见于《顺昌双峰书院新建四贤堂记》《灵枝》诗末的署名,详参后文)。其实所指,与“三山黄文仲独愚”“长乐郡古候佚老独愚黄文仲”等是同一人。
古人的名、字、号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美称。由此来看,上面引文中的“独愚”应是黄文仲的别号。黄氏自言“九□山西有愚者”(4)按,原序“□”处字体笔画残缺,无法辨认;然而黄文仲是福州人,当地有九仙山(又称九日山),由残余笔画推测,“□”处应是“仙”字。[10]也隐含了其以“独愚”为号的意思。古代文士往往具有多个别号。黄文仲晚年又自号“古候佚老”,或者称“霄台佚老”。至顺刻本《言行录》的卷首,黄文仲所撰两序末之左,皆有三方印章,自上而下依次是“霄台佚老”“黄文仲”“晋安独愚”。此“霄台”指邻霄台,是乌石山之上的著名景点。所谓“霄台佚老”类似于“古候佚老”,二者皆是取乡土之名以为别号,求其美称。
(二)生卒年考
黄文仲之生年,可以从其所撰《敏行录序》一文推出。此文称:
《敏行》一录,亦孰有之?人之爱公,固非谀非妄也。九□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爱公也,异乎人之爱。其言曰:善颂不如善勉。……至顺辛未孟春之望,长乐郡古候佚老独愚黄文仲谨序。[10](序)
此处“九□山”即福州城中的九仙山;黄文仲号独愚,故所谓“九□山西有愚者”实是这篇序文的作者黄文仲的自称。此序作于至顺二年(1331)正月十五日,其时黄文仲八十一岁。由此向前逆推八十一年,按照古人出生当年即算一岁的计岁方式,可知黄文仲出生于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
考诸文献,能够据以推测黄文仲生年的材料,还有黄氏另一篇文章。《敏行录》之“诸处碑记”内录有《新建南台盐仓之记》,文前署“承事郎、福州路候官县尹致仕黄文仲记”,末署“天历一年六月朔记”;其后又录《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复斋郭公爱思碑》,前署“承事郎、福州路候官县尹致仕黄文仲撰”,末署“至顺二年岁在辛未四月吉日记”。[11]据此,黄文仲在天历元年(1328)六月已经以福州路侯官县尹致仕。又《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复斋郭公爱思碑》称:
迨公久任将归,郡士民耆老巾笠杂沓,踵门谓余曰:“我等群告于有司曰:‘漕运事重,民易罹于辜。自郭嘉议公为政,山海清宁,咸德之。众欲琢坚,以存久远爱思之心,敢告。’录事喜曰:‘尔民怀恩思报,俗之至美也,孰汝止?宜自择乡有齿德、言足听闻之人,为尔文其辞意。’老尹谢闲,年开八,神思尚可强,幸毋逊。”(5)按,增辟学田之事发生在大德九年(1305),而熊禾作记在大德十一年(1307),所云“后甲辰三岁”,乃指大德八年(1304)后三年,即大德十一年。熊禾之所以将“甲辰”作为时间坐标,当是因上一个甲辰年、即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书院始赐名“考亭书院”。熊禾所署的这个时间,与重修书院和增辟学田的时间并无实质性关系。[11]
此文乃黄文仲应福州“士民耆老”之请而为郭郁(于泰定四年十月进授嘉议大夫、福建都转运盐使)所作,时间在至顺二年(1331)四月初一。其中“老尹谢闲,年开八”二句为考察黄氏生年提供了直接线索。因黄文仲撰文之时已以侯官县尹致仕,故云“老尹谢闲”;“年开八”即年开第八秩(也可以说是人生第八个十年的开始,古人以十年为一秩),因七十一岁为八十纪数的开始,故“年开八”指七十一岁。(6)此用白居易诗典。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记载:“(白居易诗)又一篇云:‘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注曰:‘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盖以十年为一秩云。”参见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页。洪迈所引二句,出自《喜老自嘲》(作于840年,时白居易七十一岁)。黄文仲七十一岁当至顺二年,推其生年,则在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
根据同一人在其同一年所作的不同文章中对自己年龄的表述,来推考其出生年份,却得出不同的结果,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两条表述中的数字必有一误。笔者认为当以“九□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为准,而“年开八”疑是“年开九”之讹。一是因为《敏行录序》冠于全书之首,出现手民之误的可能性较小(笔者推测,刊刻此书者不明白“开八”“开九”的真正含义,因见前文《敏行录序》有“年八十一”的表述而将后文的“年开九”误改成“年开八”,遂导致出生年份相差十年);二是“年八十一”是直接表述年龄,较“年开八”的间接表述为可信;三是按照元代官员七十岁致仕的一般情况,黄文仲在1328年已经致仕,则其当时至少七十岁。综合三者而言,黄文仲应出生于1251年。
笔者尚未见到可据以考证黄文仲卒年的材料,只能依相关文献推出大概。《弘治将乐县志》卷十二收录《武略将军广德路同知吴公墓表铭》,作者题为“黄文仲”,并注以“候官县尹”四字。[12](P557)则此人亦《大都赋》的作者黄文仲。《武略将军广德路同知吴公墓表铭》云:“至元丙子春,公嫡子龙溪县尹文让以行状求铭,予敬其于世有功德,举要而书。”[12](P558)元代有两个至元年号,前至元丙子指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后至元丙子指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此墓志铭中的“至元丙子”明显指后至元二年。那么,黄文仲卒年必在元顺帝至元二年以后,其享年在八十六岁以上。
(三)行迹考
至顺刻本《敏行录》之“福建酬倡”内,录“古候佚老黄文仲”《谨和复斋漕使相公与御史尚公唱和三绝》。“复斋漕使相公”即郭郁;“御史尚公”指尚克和,登至治元年(1321)进士第,天历二年(1329)任南台监察御史。至顺元年庚午(1330)至日,郭郁寄三绝与尚克和,尚克和赓韵三绝,福州文士徐东、黄文仲、张复等纷纷奉和。黄文仲和诗第二首云:“曾因堂授识严亲,衣绣南来是后人。有国有家身是本,定须能子便能臣。”诗末小字注:“大德七年春,文仲同七人诣都堂,受敕牒,获拜左丞尚公。”[11]此处“都堂”指中书省官署,“敕牒”指授官的文书。“左丞尚公”指尚克和的从父尚文,大德七年(1303)任中书左丞(其生平详参孛术鲁翀所撰《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由此可知,黄文仲曾于大德七年春接受朝廷的授职文书。
那么,朝廷授予黄文仲的是什么职位呢?这可以从熊禾《考亭书院记》中获得答案。此记作于大德十一年(1307),主要记述毋逢辰主持重修考亭书院和增辟义学田之事。重修书院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而增辟义学田则发生于大德九年(1305)。《考亭书院记》云:
书院之更造,唯公手创,不敢改。栋宇门庑,焕然一新。邑士刘熙实终始之。义学之创兴,宋奕、黄枢首帅以听,华恭孙、叶善夫、赵宗叟、旴江李廷玉,与有谋焉。而厚帑庾、完塈茨,以迄于成,则虞子建、刘实也。贤劳皆可书。时提调官总管燕山张仲仪,教授三山黄文仲,助田名氏,悉书石阴后。甲辰三岁,大德十一年四月朔日,后学熊禾记。[13](P574)
引文提到的“教授三山黄文仲”,显然正是《大都赋》的作者黄文仲。考亭书院在建阳县(今建阳市),属建宁路。元代路、府和上、中州儒学设立教授。黄文仲作为增辟义学田的提调官之一,于大德九年担任建宁路儒学教授。结合前引“大德七年春,文仲同七人诣都堂,受敕牒”的记载,可知朝廷授予黄文仲的职位正是建宁路儒学教授。
建宁路儒学教授之后,黄文仲又曾任延平路学官。《嘉靖延平府志》之《艺文志》卷一所载作者题元代“黄文仲”的《顺昌双峰书院新建四贤堂记》云:“延祐甲寅孟秋,晋安黄文仲始职剑庠,洒扫荐杯水四贤堂下,……丙辰夏五月,山长建阳陈君棠若虚以书抵文仲曰:……”[14](卷一)此文乃黄文仲应双峰书院山长陈棠之请而作。延祐甲寅即仁宗延祐元年(1314),丙辰指延祐三年(1316)。双峰书院在顺昌县,属延平路。延平路在宋代称南剑州,元初改称南剑路,后又改称延平路。此处“剑庠”指延平路儒学,“职剑庠”指担任延平路儒学教授。
延平路儒学教授之后,黄文仲曾任何职,因文献阙载,不得而知。但据前文所述,天历元年(1328)六月,黄文仲已经以承事郎、福州路侯官县尹致仕。承事郎(文散官)、侯官县尹(职事官)是元代朝廷在黄文仲致仕后所给予的政治优待,并非黄文仲真正担任过侯官县尹。
泰定(1324—1327)年间,黄文仲曾题咏王都中《孝感白华图》。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第七卷载《本斋王公孝感白华图》卷,集录众多文士题咏,其中有《灵枝》五章,末署“晋安黄文仲再拜谨书”,序云:“《灵枝》,彰本斋王公之孝感也。忠愍公以国事死海上,子方七岁,母夫人张氏依慈门以贞保幼。公长而仕,报以孝。母亡,公折时花荐灵几,突然有异实如桃,白且莹,朝野瑞之。天人之道密矣。”[15](P488)王都中号本斋。据章嚞《本斋王公孝感白华图传》载,王都中之母卒于至治二年(1322),孝感白华发生于次年三月,则黄文仲诗必作于至治三年(1323)三月之后。又考黄溍撰《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知王都中于丁母忧、服阙后到天历初年之间,历任两浙都转运盐使、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黄文仲为《孝感白华图》题诗约在泰定年间王都中任职福建时。除此之外,黄文仲又曾题咏郭居敬的《百香诗选》。[16]
综合以上考述,兹将黄文仲的生平概况梳理如下:黄文仲,号独愚,晚年又号古侯佚老、霄台佚老,福州路侯官县人。生于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春,诣中书省受官封,出任建宁路儒学教授。仁宗延祐元年(1314)七月,出任延平路儒学教授。后以承事郎、福州路侯官县尹致仕。曾题咏郭居敬《百香诗选》、王都中《孝感白华图》。文宗天历、至顺年间,与郭郁多有交往。卒于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之后,享年在八十六岁以上。
三 北游大都献赋时间考订
黄文仲现存诗文作品十余篇,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大都赋》。关于创作此赋的原因和初衷,黄文仲在赋序中交代得比较清楚:
窃唯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然班固作《二都赋》,天下后世夸耀不朽。今宇宙升平,宜播厥颂。文仲幸生圣世,获睹大都,虽不克效其聱牙之文,繁艳之语;亦不愿闻其奢靡之政,浮夸之言。谨摭其事,撰《大都赋》,上于翰林国史,请以备采择之万一。[4](P635)
据此可知,黄文仲因际遇升平,有感于大元的强盛,故仿效班固创作《两都赋》以颂美东汉的传统,撰成《大都赋》,用来献给翰林国史院,以备采择。对于《大都赋》的呈献时间,目前的相关介绍和研究存在不同意见。
一些研究者认为此赋献于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康金声《金元辞赋论略》介绍黄文仲《大都赋》:“此赋作于武宗朝,其时科举尚未恢复,故一般作者与朝廷没有其他沟通渠道,只能仿汉人献赋故技,上篇章于翰林国史,以备采择。”[2](P208-209)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宋金元卷)的《大都赋》简介、黄二宁《元代南人献赋本事考》皆承其说,但均未举出证据。兹以为其根据是赋中这样一段文字:
嗟夫!饥者帝食之,寒者帝衣之,居者帝安之,乱者帝治之。中统之深恩,至元之厚惠,民之思之,庸有既乎?矧我皇上,缵二世之洪烈,绍六世之宏基。[4](P638)
以“皇上”指武宗,“二世”指世祖、成宗,“六世”指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对比元代历史能够讲通。按照这种解释,《大都赋》必献于至大年间。
另一种意见认为,黄文仲献《大都赋》在大德年间(1297—1307),例如《全元诗》第三十六册中的黄文仲小传等。其依据,正如王筱芸《文学与认同:蒙元西游、北游文学与蒙元王朝认同建构研究》第三章第四节所云:
黄文仲的《大都赋》被刊集在元人周南瑞编的《天下同文集》卷一六,该书元大德八年(1304年)成书,所收诗文限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之前。黄文仲创作《大都赋》应在此年之前。[17](P308)
《天下同文集》卷首《原序》末署日期是大德八年(1304),研究者一般据此认为该书编成于大德八年左右。然据花兴研究,此书收有大德十年(1306)九月的文章,因而应编成于大德十年左右。[18](P40)
笔者认为,《天下同文集》或《翰墨全书》的收录只是为考察《大都赋》的撰写和奏献时间提供一定的参照;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则来自作品本身。此赋种种迹象表明,以上引文中“皇上”是指元成宗,而非元武宗。《大都赋》中以下两段段文字称:
惟我圣皇,五辂不乘,八鸾不驾。雨则独乘象舆,霁则独御龙马。何其然也?念我烈祖,铁衣雨汗,弗敢安也。……
惟我圣皇,奉坤母,建隆福,正事御,构五华。宫不为广,殿不为奢。何其然也?念我先皇,居数十年,弗敢改也。[4](P640)
全赋共出现七次“圣皇”,两次“皇上”,均指黄文仲献赋时的元代帝王。引文中“惟我圣皇,奉坤母,建隆福”之“坤母”显然指皇太后,“隆福”指隆福宫。隆福宫原是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居所,称东宫或太子宫,真金去世后,真金妻仍居于此。成宗即位,尊真金妻为皇太后,于“(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己巳,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19](P383)。隆福宫成为崇奉皇太后的处所。赋文“奉坤母,建隆福”正指此而言。因旧太子府是真金为太子时的居所,故赋云“念我先皇,居数十年,弗敢改也”,此“先皇”无疑是指真金(成宗即位次月加皇考真金尊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故而“圣皇”“皇上”指元成宗之意甚明。“二世”“六世”云云,自当作另外一种解释。若以“圣皇”“皇上”指元武宗,则与事实不合。因为武宗在位时,为太后别建兴圣宫,隆福宫则成为武宗之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住所。又《大都赋》云:
圣皇之德,日盛日隆。……唯其有大德之大,故能成大元之功。唯其有大元之大,故能成大都之雄。……夫元者,天地之苞也;德者,天地之美也;都者,天地之会也。……维此大都,统万方兮。……维此大德,囿万类兮。……维此大元,齐万寿兮。[4](P640)
其中“大德”虽不必指成宗年号,但与“大元”“大都”相对称言,明显带有双关的含义,应是解释成宗以“大德”作为年号的用意。故将“大德”视为年号完全可以讲得通。
由此两条内证可知,黄文仲献《大都赋》必在大德年间。但尚需进一步考察其上下限。关于上限,可从李洧孙《大都赋》寻找线索。李洧孙献《大都赋》的时间有明确的记载。黄溍《霁峰李先生墓志铭》云:“郡府或以先生名剡上,先生为强起,诣京师,述《大都赋》以献。时大德二年也。居亡何而归。六年,乃得杭州路儒学教授。”[20](P284)李洧孙在其《大都赋序》中,于简单回顾都城诗歌和都城赋的发展历史之后,指出:
夫有盛德大业者,必有巨笔鸿文,铺张扬厉,高映千古,以昭无穷。然四海泳仁涵和三十载,未有仿佛商周之歌、二汉之赋者,亦一时遗典也。臣远方书生,猥以词章为业,际遇昌辰,不能默然,辄撰成《大都赋》一篇。[21](P315)
很明显,在元朝统一全国后、大德二年(1298)李洧孙献赋前,还未有人撰写《大都赋》以献给朝廷。那么黄文仲献《大都赋》必在大德二年之后。
关于下限,仍可从赋文内部寻找线索。前引《大都赋》云:“惟我圣皇,奉坤母,建隆福。……念我先皇,居数十年,弗敢改也。”谓成宗改造旧太子府为隆福宫,以尊奉其母皇太后。由此数句事实陈述可知,黄文仲献赋时,成宗之母尚在世。按成宗之母卒于大德四年(1300)二月,那么黄文仲献赋的下限是大德四年二月。
上文提到,黄文仲于大德七年(1303)春“诣都堂,受敕牒”,出任建宁路儒学教授。笔者以为,黄文仲获得这个职位,正是献《大都赋》的结果。此可与李洧孙的经历相参照。李洧孙于大德二年(1298)北上献《大都赋》,虽然得到馆阁诸公的赞赏和举荐,但朝廷并未立即回应,李洧孙也居大都不久即回归台州宁海,直到大德六年(1302)才得授杭州路儒学教授。前后经历五年!这种情况的出现,应缘于当时南方士人纷纷出仕而学官职位有限的现实。张伯淳所作《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云:“吾友白君廷玉为常州路教授,才选也。年来儒官赴选部,如水赴壑,员无穷而阙有限,于是枢机日趋于密。”[22](P194-195)白珽(字廷玉)于大德四年(1300)出任常州路儒学教授。张伯淳所云,正道出了大德初年的严峻形势。黄文仲在李洧孙之后献赋,其授官也不太可能在李洧孙之前。故李洧孙授官于大德六年,黄文仲授官于大德七年,应该不仅仅是巧合。合理的解释是,李洧孙先献赋先得官,黄文仲后献赋后得官。与李洧孙的经历类似,黄文仲献赋后也经历较长的等待时期,直到大德七年才获得儒学教授之职。因此笔者考证黄文仲献《大都赋》在大德二年之后、大德四年之前(即大德三年前后),与黄文仲的这一经历也相吻合。
四 余论
黄文仲献赋的大德初年,车书混同,海晏河清,在时人看来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巨笔鸿文来铺扬其时的盛德大业,以接续班固等人创作京都赋以润色皇猷的传统;这个时期,也正是南北统一三十年左右南方士人纷纷北游的兴盛时期,正如方回《再送王圣俞戴溪》诗所云:“宇宙喜 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23](P538)因此,作为一名南方士人,黄文仲继李洧孙之后,于此时诣京献赋,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上承陈孚之献《大一统赋》,发展了“大一统”主题;(7)陈孚(1259—1309)字刚中,台州临海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以布衣身份献《大一统赋》(《元史·陈孚传》记献赋事,仅云“至元中”,出土的《陈孚圹志》明言在至元二十二年)。此赋早佚,但由这个具有开创性的赋题来看,其内容是歌颂元朝的大一统。作为一名南方士人,陈孚在南宋亡国仅六年之时献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说明江南知识群体已经开始出现分化,部分士人开始公开表示对蒙元朝廷的政治认同”(黄二宁《元代南人献赋本事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4年第14辑,第82页)。陈孚献赋的地点是江淮行省(《元史》本传是江浙行省,兹据《陈孚圹志》),乃由于当时南士北游的时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绾合“北游”主题,表达出新时代下南方士人群体对元朝的政治认同,也反映出他们为寻求出仕机会所做的积极努力。这是元代以大都为题材的献赋所具丰富文化意蕴的重要层面,也是其鲜明时代特色的突出呈现。黄文仲献赋能够得到时人的认可、《大都赋》能够得到时人的传诵,正由于其能顺应时代潮流,符合社会形势。(8)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一文认为:“宋亡之初,遗民抗节自高,对贰臣往往严词谴责。但随着岁月更易,这种情形在二三十年间便发生甚大变化。”又引谢慧贤之言:“至1300年(即大德四年),宋朝遗民已绝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无论就其对宋朝忠心的概念以及对元朝态度的转变而言,他们与包括贰臣在内的一般江南士人并无多大差异。”见氏著《元朝史新论》,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7页。但作为南方士人群体中的代表,黄文仲(包括李洧孙)献赋后并未得到帝王的召见、赐物以及待制等相应的恩荣,其所获得的从八品路学教授之职,也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等待过程。与汉、唐、宋等朝的献赋者相比,其遭遇未免相形见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元代蒙古统治者对献赋这一汉族文学、文化传统缺乏足够的认识。考诸赋史,元代献赋处于宋明之间的低谷,与此密切相关。
京都赋的创作,是源远流长的赋史传统,自汉代以来即备受重视。黄文仲其人虽然不显,但所撰《大都赋》古今知名,屡屡见诸相关文献的载录、征引和提及,在京都赋史和都城文化史中皆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正是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本文通过爬梳文献,勾勒出黄文仲的生平概况,并对其献《大都赋》的时间以及献赋结果等事实进行考订。研究黄文仲《大都赋》,应将之置于特定的时代、社会背景之下,在准确把握“作者”和“世界”的基础上观照“作品”,方能彰显其独特的赋史意义和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