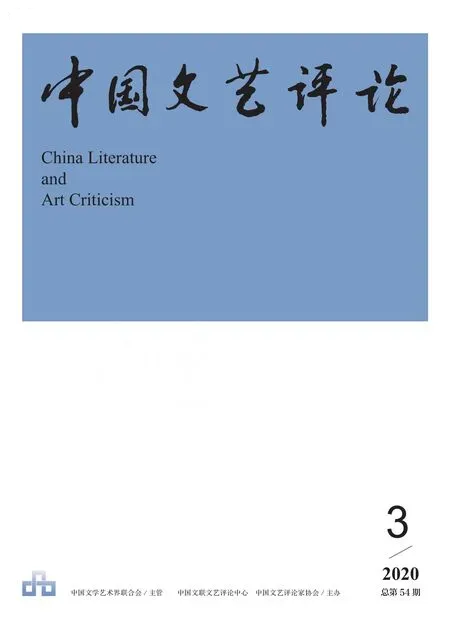媒介变迁与文艺批评的时代新貌
2020-11-17朱晓军
朱晓军
不恰当地套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句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在欧洲的上空”,我们可以说,“一种危机,文艺批评的危机,徘徊在文学艺术的世界”。这绝非危言耸听——随机登录文学艺术的学术网站,以“批评”和诸如“危机”“困境”“状况”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都会跳出不少链接;翻开文艺类学术期刊,做出近似结论的文章也屡见不鲜。王一川先生曾这样诊断,“当前,我国的艺术批评(有时称为文艺批评) 正面临新的挑战。 这里的艺术批评,其实已经不能涵盖所有的艺术批评了,而只能算是所有的艺术批评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学术型艺术批评。这种学术型艺术批评是由艺术界及相关人文社科学术界以学术期刊和书籍形式传输的那种带有学理或学术特点的艺术批评文字,可以简称为学术型艺评。 这种被冠之以‘学术型’的艺术批评, 在过去其实就是艺术批评的主干或全部,而今却已迅速蜕变为艺术批评中日渐丧失话语主导权的被迫边缘化或被边缘的可怜部分了。 这恐怕正是当前艺术批评领域出现的尤其严峻的挑战之一。”[1]王一川:《当前艺术批评的学术自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6期。
实际上,文艺批评的种种症状早已是迁延日久的沉疴痼疾。数十年来,如此多的文章把脉问诊,表明了文艺批评界直面自身问题的清醒与冷峻。然而,若只是着眼于文艺批评本身,恐怕无法找到答案,重新梳理文艺批评与媒介的关系,或许能给我们新的思考。
一、纸媒与职业批评家的建构
文艺批评有漫长的历史。任何一部文学或者艺术批评史,几乎都会将自己的源头追溯到相关门类艺术起源的时期。口传时代的街谈巷议和切磋琢磨,就是文艺批评的滥觞。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直接发端于西欧17世纪至18世纪的沙龙,伦敦与巴黎的咖啡馆成为现代文艺批评早期的生长空间。文艺批评从咖啡馆、沙龙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方式,走向更广泛的大众传播,得益于印刷业的飞速发展。自从15世纪谷登堡在印刷术上的革新,西欧资本主义飞速发展;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版业亦蒸蒸日上,造就了一个新兴的文人阶层。随着职业作家作为一种独立的身份出现,批评家也应运而生,而且这两种身份,在其最初的阶段,往往集于某位作者一身。无论是为自己的文学主张辩护,还是在书籍市场上争夺读者,作家(艺术家)都有很强的内外驱力来直接解释和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湖畔诗人的浪漫主义诗论,莱辛的《汉堡剧评》,司各特历史小说的夫子自道乃至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文论等,都可作如是观。然而,真正意义上,具有独立和自觉意识的文艺批评,是以职业批评家的出现为标志的。从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觉醒,到启蒙运动理性的胜利,天才辈出的文艺创作与恢宏博大的美学思辨比翼齐飞,将文艺批评的水准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批评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担当了引领文艺发展和推动文艺思潮的主角。
整个19世纪,西方文学艺术领域可以说流派纷呈、思潮迭起、群星璀璨、成就辉煌。批评家们不仅躬逢其盛、与有荣焉,而且屡屡独立潮头、指点江山。职业批评家们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洞幽烛微的艺术感受力和抽丝剥茧的美学思辨力,不仅成为普通读者的良师,亦是作家艺术家的诤友。诸如泰纳对巴尔扎克的诠释,与左拉的密切关系,直接影响了法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方向;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推崇,对果戈里的鞭策,从而成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伟大传统的教父;施莱格尔兄弟之于德国浪漫派,等等,都是文坛耳熟能详的经典范例。而在视觉艺术领域,诗人波德莱尔的画评,诸如《1845年的沙龙》,罗斯金的艺术评论等,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延至20世纪,则有英国的克莱夫·贝尔、俄罗斯的康定斯基、美国的格林伯格等,成为当时先锋派的代言人。
职业批评家的出现和文艺批评的自律,实际上正是自18世纪以来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文艺批评实实在在是“现代”的建构,是启蒙话语高歌猛进的急先锋。在学理层面,它依附于自律美学与艺术独立;在文化空间层面,它依赖于由出版与印刷构建的公共领域;在受众层面,它依赖于求知若渴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哈贝马斯指出:“粗略说来,在现代艺术的发展史中可以总结出一条不断前进的独立化线路。首先是在文艺复兴中形成了那种完全属于美的范畴的研究对象。在18世纪的进程中,文学、美术和音乐被体制化,成为了脱离宗教和宫廷生活的行为范围。最终在19世纪中期也产生了一种唯美的艺术观,它已经指导着艺术家们按照‘为艺术而艺术’的意识来生产作品。这样,审美特性才得以成为坚定的信念。”[1][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美学成为“批判的武器”,美学价值与审美判断成为文艺批评的终极标准与方法论基础,这是最典型的现代现象。以先知觉后知,以上智启下愚的启蒙话语,构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理性主体,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哲学家、人文学者、艺术家、文艺批评家的共同事业与集体镜像。
回到百年中国的语境,可以说几乎完整地复制了西方印刷文化建构文学现代性与职业作家、批评家身份的这一进程。从戊戌前后梁启超发起“三界革命”(文界、诗界、小说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鼓吹文学革命,文化领域的先驱们认同启蒙运动的理念,追求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培植“新民”“国民”意识,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否弃儒家价值体系,信奉进步而非复古(所谓“三代之治”)的历史观,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诉求。在这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与文艺现代性滥觞期,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未能引起足够重视的动因,就是以现代印刷技术和报刊为代表的传播工具与传播媒介的登场。在晚清礼崩乐坏“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传媒成了革故鼎新、摧枯拉朽最强有力的武器。自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鼓吹“小说界”革命起,短短数年,以小说为名的刊物如雨后春笋,报纸也竞相开设连载小说的栏目。小说从“言不耻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斥同鸩毒,视等俳优。下笔误征,每贻讥于博雅;背人偷阅,辄见责于名师。”[2]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中华小说界》第一年(1914年)第1期。“君子弗为”的小道,声誉暴涨,一跃而居于“文学之最上乘”“几几出于经史之上”[3]几道、别士(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到1906年,小说家吴沃尧就感叹道:“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翻译之小说,几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4]吴沃尧:《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一号(1906年)。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研究,1873年到1902年发表的创作和翻译的小说作品仅150种,但自1902年《新小说》创刊到1912年的十年间,一跃而达到了2482种。[5][日]樽本照雄:《阿英〈晚清小说书目〉》,转自王中忱:《近代媒体的登场、发展与小说书籍生产的变迁》,《文学评论丛刊》第1卷第2期。小说取诗词而代之,从文学的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没有文学期刊、出版社这些硬件的支撑,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深入。
从小说由街谈巷议的“小道”被奉为“改良群治”的大道,从“诗、文、评”的范式到现代批评话语的确立,从白话文的胜利到国语文学正式进入大中学校的教科书,不仅曾被列为禁书、淫书的《红楼梦》一洗沉冤,成为白话文学的不祧之宗,而且文学革命标举的文学观念以及贯彻这些观念的新文学创作,也被经典化,成为新一代读者头脑中的文学规范——文学变成了“美的一种”,获得了审美自律性。具体而言,以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及现代出版业,教科书的编纂与文学教育课程的设置等为基础而形成的传播机制和文学体制,彻底颠覆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文类秩序,改变了文学的生存形态,赋予“文学”这个概念以全新的含义(比较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对“文学”一词所做的考证)。首先,文学不再是装点盛世、粉饰太平的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再被视为文人才子宦海沉浮、幽居靡闷之时或肥马轻裘、酒酣耳热之际的消遣,而是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灌输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思想的利器,成为启蒙话语最便捷、最有效的载体,与旧文学“宗经、明道、征圣”的意趣相去甚远。第二,传播机制的商业化运作方式,使文学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文化产业。科举废除之后,以帖括为业,以仕进为务的士子必须进行一场痛苦的身份转换,传媒与现代出版业的发展,给这些皓首穷经,做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美梦的读书人提供了角色转换的机会,他们不得不把原准备“货与帝王家”的知识储备作为“文化资本”(布尔迪厄语)拿到市场上来,成为以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为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职业作家(批评家)应运而生。同时,新式学堂的设立和报刊的风行,又培育了新文学的消费市场,现代意义上的读者产生了。第三,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办刊亦或是文人的同人刊物,理念引领的批评机制和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促进了文学的体制化,从而赋予了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第四,五四之后,新文学在五四一代的推动下,进入了教科书和课程设置,文学革命的成果得以巩固,通过教育传承完成了新文学作品的经典化。[1]朱晓军:《传播媒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中文系,2000年,第3-5页。
总之,传媒对中国文学的介入,举其大端,不外乎上述几个方面,这几方面互相渗透、相辅相成,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晚清开局、1919年至1949年30年奠基,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和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正是纸媒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辉煌百年。
二、电子传媒的后现代解构
无疑,纸媒的辉煌,给文艺批评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横空出世的电子传媒,以其无远弗届的覆盖面与雷霆万钧的传播力,给人类的信息传播带来了深刻的革命。这一次媒介革命的主角,是电视。电视在“二战”之后,迅速进入西方普通人的家庭。这是西方社会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标志性事件。1950年代,电视率先在美国进入普通家庭,随之遍及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主导媒介。电视的强势崛起,短短数年即深刻地打破了文化的固有格局。“文字”与“图像”两种媒介所造成的代际分野清晰可见。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就爆发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反文化风暴,这是偶然的吗?关于后现代的缘起,不同领域的学者有诸多大相径庭的立场,但普遍将20世纪60年代末,作为文化转向的时间节点,原因何在?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信息方式在这个时段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印刷文化与文字媒介由盛而衰,以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图像传媒,辅之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彻底重塑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生活和知识文化图景。那个自信满满,居高临下,像上帝一样的精英“理性主体”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电视霸占了人们的休闲空间,宰制了人们的业余时间。图像的跳切、拼贴瓦解了文字表述所遵循的严谨理性与整饬逻辑,扑面而来的“形象流”放逐了文字的间接性所涵养的想象力。不假思索的直观“图像”突破了深奥文字构筑的接受藩篱,抹平了此前森严的文化等级。
后现代思潮对于文艺批评的首要冲击,是釜底抽薪,彻底瓦解了建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现代美学。以主体分裂、中心离散、距离消逝、反本质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思潮,将文艺批评的立身之本——美学价值与审美判断,推向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从而实质上抽空了批评与批判的灵魂。当我们谈论“文学”“文学性”“艺术”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人们突然发现,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给这些最基本的名词下定义、做界定,竟成为不可能之事。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不再是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这样的艺术,能够被“概括”吗?
在文字媒介向电子图像媒介的文化转型中,走向衰微的不仅仅是现代主义美学和艺术,还有曾经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批判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受众,也逐渐失去了舞台。才华横溢、个性张扬的批评家们,在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很难获得足够大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只能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关于这一点,一个鲜明的证据就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埃德蒙·威尔逊、特里林、格林伯格、桑塔格等人之后,几乎没有出现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文艺批评家。实际上,随着报纸本身的数量(及其文艺的副刊)、文艺期刊的数量急剧萎缩,那些曾经活跃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多少栖息之地。容身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已是大势所趋。凌空蹈虚的理论建构、中规中矩的高头讲章多了,意兴飞扬、切中肯綮、酣畅淋漓的文艺批评少了,从而造就了今日文艺理论、(文学)艺术史、文艺批评头重、脚轻、身子大的畸形格局。如果将时间的距离拉长一点,自1830年法国浪漫主义挑战古典主义的“欧那尼”事件始,至1960年代英美“新批评”学派影响式微终,这一个世纪可以称为“批评的时代”的话,那么,20世纪的后半叶至今,则完全是一个“理论的时代”,文艺研究的旨趣,已经大相径庭。两种判然有别的话语方式背后,折射出的正是职业批评家群体的谢幕与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崛起。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开国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让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文化上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80年代兴起的二度西潮,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和文艺理论长驱直入,几十年的时间裂隙被迅速填平、批评话语的中西差异渐渐模糊。20世纪90年代,由忧心忡忡的文学理论家们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与市场大潮席卷而来,文学期刊盛极而衰、发行量急骤下滑,纷纷改版以求生路,文学告别轰动效应的背景,息息相关。那是纸媒在电子媒介冲击下的回光返照,也可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后的辉煌。作家纷纷进入大学担任教授,以大学教授及其研究生为主体的学院派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占据文艺批评的主导地位,都延续了西方国家文学发展的既有轨迹。如上所述的种种现象,或以时差的方式在中国重现,或以同频共振的方式,为中西兼有。
三、传统批评的式微与批评的新生态
世纪之交,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将建基于图像媒介之上的后现代文化,继续向纵深拓展。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社会的“重新部落化”,尽管在电视时代已经初现端倪,但只有在互联网横空出世之后,才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一方面,人类大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另一方面,交通、金融、通讯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地方性和主体性也随之被唤醒,反对强势“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歧与纷争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民族文化、部落宗教、同性恋等少数人的权利以及人类学层面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人类学家格尔茨语)的正当性诉求,连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的大大小小网络“社区”,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层面确证了“宏大叙事”的解体与“普遍理性”的虚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理性的信徒(反理性主义也不例外),他们的共性在于,“知识性工作产生于宗教性的关注。在人类早期历史上,这种工作总是以宗教符号思考,关注的是终极事物或至少是超越直接经验的事物。它始终像真正的宗教体验那样,迷恋于思想和经验的神圣基础或终极基础,并渴望亲密接触这一基础。”[1][法]费迪南·布伦蒂埃等:《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王增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6-47页。比如“真、善、美”这些属于宏大叙事的“终极基础”,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不再牢不可破,而是摇摇欲坠,甚至土崩瓦解。理性的反思转向理性的自反,“批判的武器”反而变成了无休无止的“武器的批判”。对终极价值的质疑,导致非理性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甚嚣尘上。如果知识分子首先在“知识”的确定性上失去了自信,从思想上首先解除了武装,意味着他们面对复杂现实将难以言说;失去了终极价值的最后尺度,他们在审美判断上亦必然首鼠两端、莫衷一是。这正是职业批评家们在形而上层面陷入的困境。换言之,“理性”主体的裂解,必然导致“批评家”这一身份的坍塌。
新媒体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去中心、反权威的革命性力量。自电子影像媒介颠覆了印刷文化精英的文化特权地位和等级秩序之后,数码多媒体技术作为一张无所不包、蔓延无边的“网络”,赋予了人类社会那些长期以来“沉默的大多数”言说的空间和机会。BBS论坛、网络社区、博客、微博、微信社交媒体等层出不穷的技术创新,给网络新一代赋予了话语权。在这里,批评家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一去不返。因为世界是平的,网络不是广场,也没有令人瞩目、高高在上的讲坛。人人都有话筒,而不是仅有一支话筒,且音量都是等值的。拉塞尔·雅格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将20世纪50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职业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欧文·豪等形容为“最后的知识分子”。因为那种超越僵化学术体制的知识旨趣、深广的人文关怀和贴近社会生活的现实感,随着知识人学院化生存的转向,必将曲终人散。参照近年来中国网民对“砖家”的解构和嘲讽,精英们顿时感受到了随网络时代而来的一股他们命名为“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潮流。其实,这些陈旧的词汇被翻出来给新媒介时代的现象贴标签,完全是一种“时代的误置”。众声喧哗的网络世界,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在屏幕后面,隐匿的是千千万万无论年龄种族性别国籍,必须彼此平等相待的网民。人人都是艺术家,人人都是批评家。趣味无可争辩,没有人的趣味比别人的更高雅更纯正。文艺批评家在网络世界里,既没有讲坛,也未必有听众,除了退回静谧的象牙塔,在故纸堆里爬梳史料,抑或在各种舶来的理论中兜圈子,撰写用于同行交流与职称评定的四平八稳的学术论文,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当然,职业批评家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文艺批评的终结。从博客、微信的朋友圈、微博的互听关注,到各种“群”的大小网络社区,以及相关的文艺网站,互联网正在重塑人类社会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乃至大众传播方式,而且这些方式正在前所未有地彼此渗透、互相开放,形成了一个全媒体环境。在海量的吐槽、点赞、转发、评论,灌水的文字、声音和图片中,人类社会史无前例地将从衣食住行到精神文化生活的选择与决定权赋予了个人。在智能手机日渐普及的当下,甚至可以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广义的“评论”和“批评”,包括大量的对一部电影、一本小说和一幅画一首歌的“文艺批评”。以当下中国的网络坏境为例,登录类似于豆瓣这样的网站,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一部公映的影视、公开出版的书籍以及音乐作品的相关评论,这是网民彼此无私的分享,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的趋势在社交媒体日新月异的变革中愈演愈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每一种特别的趣味,似乎都能在网上找到能够与你共鸣的同类。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回到了街谈巷议与咖啡馆时期,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互相交融,瞬时性、互动性与平等性的交流关系,使传统媒体环境下,批评家通过文艺期刊和评论文章建立职业声望的稳定而又持久积累信誉的方式不复存在。而最新的技术手段,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名为“弹幕”的玩法——观众看电影时,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发表评论,这些评论将在现场的银幕上同步显示,在场观众之间,也可以彼此评论互动,成为一种新奇的观影体验。更有甚者,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则以数据挖掘取代了审美判断。以美国网飞公司的热播剧《纸牌屋》为例,观众的偏好在精准的数据分析基础上,早已天衣无缝地融进了编剧的剧情策划中。“趣味无法争辩”的美学难题被“趣味可以计算”的数学模型轻松化解。
聚焦国内,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媒介与文化变迁,文艺界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这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普及电视,大约十年之后大众文化兴起。而正是这个十年,雨后春笋般繁荣的期刊与出版业,孕育了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黄金时代,诸如“崛起的诗群”“新写实主义”等批评家的“命名”引领诗歌和小说创作流派形成的案例屡见不鲜。90年代以来,文艺期刊举步维艰,全中国800多种文学期刊,发行量达到10万份以上者凤毛麟角,低至千余份者比比皆是。曾经栖身于文联、作协系统和杂志社的许多有影响的批评家,纷纷进入高校,转型为学者和教授。职业批评家,作为一种身份,也许还有零星的孑遗;但作为一个群体,却不可挽回地走入了历史,几乎完全复制了欧美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叶的行迹。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鞭辟入里、血肉丰满的文艺批评越来越少;隔靴搔痒、凌空蹈虚的文艺理论比比皆是。20世纪末,复旦大学教授、批评家陈思和先生曾经将当时的文艺生态概括为“庙堂、广场、民间”三种形式,或许对应的文艺批评也可作如是观,尽管这三种样态的面目并非那么清晰,界线也极为模糊。学术圈西方“理论旅行”的后现代盛况风靡一时,“语言学、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术语轰炸屡见不鲜。这种象牙塔里的智力游戏,“边缘化”“丧失话语权”,原本就不足为奇。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那样,批评家需要面向大众,而大众需要美学的启蒙和提升。批评家理所当然地介入公共领域,以自己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和超卓的文艺品味,向普罗大众发言,这正是18世纪以降,文艺批评的天职与批评家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大众传媒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文化空间。这样的文化空间,随着网络作为“第四媒体”的崛起,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网际空间的互动性、流动性、多向性、分众性,给当前野蛮生长、如火如荼的网络文学、网络艺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也给学院派和传统的文艺批评范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1]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国家领导人对文艺新生态发展的深刻洞察,也向文艺批评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文艺批评家们对新生事物的反应并不迟钝、对自身的使命和困境也十分清醒。在2015年10月21日北京晨报的一次访谈中,评论家白烨认为“网络文学需要新标准”,他指出:“评判和分析传统文学的经验,已经不适用网络文学,需要新的标准和评判体系。从去年开始,许多人就在讨论建立网络文学的标准,但总的来说,探讨的人数还比较少,也不够深入,距离新标准的成型还很远。事实上,依靠我们这样研究传统文学的人去研究网络文学,也往往会让人觉得隔靴搔痒,还是需要新的研究者、新的经验和方法”。[1]白烨:《网络文学需新标准 白烨:分析传统文学的经验不适用》《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5/2015-10-21/256010.html,2015年10月21日。无独有偶,在2016年10月28日的文艺报上,评论家南帆也向评论界提出了他的卓见《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相对于印刷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网络小说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类型,诸如玄幻小说、冶艳小说、穿越小说、网游小说,或者架空历史小说、耽美小说、末日生存小说。当然,矜持的学院并不急于表态,大多数文学教授毋宁说置若罔闻。然而,当社会的阅读重心从印刷传媒转向互联网之后,如火如荼的网络小说必然谋求文学殿堂的正统身份。除了拥有不可比拟的读者数量,互联网同时展示了一个新型的知识传播体系。对于门户俨然的学院来说,互联网的冲击可能迅速颠覆沿袭已久的教学体系。”[2]南帆:《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文艺报》2016年10月28日,第2版。他的结论是:“现今,两种文学类型的分歧、竞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尖锐。对于文学想象说来,遵从历史逻辑与遵从欲望逻辑包含了内在的对立,批评必须为两种类型的文学解读设置不同的代码系统。”[3]南帆:《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文艺报》2016年10月28日,第2版。
很显然,与中国网络文学业已取得的惊人成就,其庞大的体量,打造IP的能力,对影视、游戏等文化产业全链条的超强辐射力,在对外文化输出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等相比,很多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黄鸣奋、欧阳友权、邵燕君、周志雄、何平、夏烈等网络文学和网络文艺研究筚路蓝缕的拓荒者和先行者们,把草根属性的网络文学纳入学术殿堂上。但他们也都置身学院体制之中,网络文学更多地是被他们当作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以“课题”或者“项目”的方式被纳入其研究的。囿于学院派的思维惯性和知识系统,目前网络文学研究的路径、评论的学理支撑,仍然未脱传统文学的窠臼,实现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白烨和南帆所期待的“网络文学新标准”与新的“代码系统”,恐怕还需要新的有生力量继往开来。这就要求“评论”必须要“及物”、要“上线”、要“在场”、要“同步”、要“参与”,要接地气,要放下身段,这样才能做到“全员、全息、全程、全效”,才能解决“失语”“失效”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