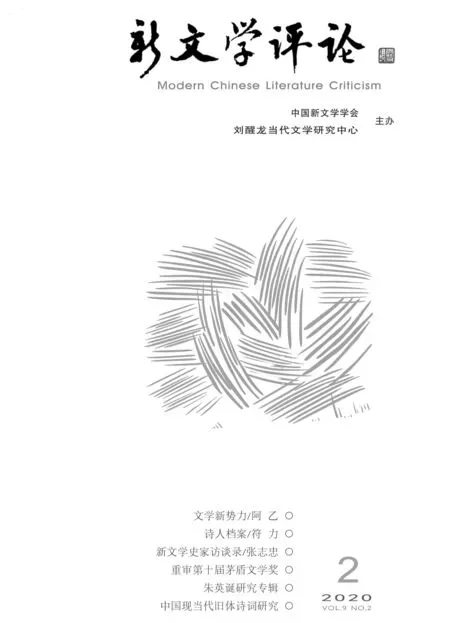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应物兄》与“现实主义当代化”
——兼谈当代总体性之悖论
2020-11-17陈培浩
□ 陈培浩
现在讨论李洱的《应物兄》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这部作品虽为专业读者预留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但其自身的复杂性使共识性判断不易得出;作品于2018年12月出版之后,迅速激起了评论界巨大的热情,短短一年之内,几乎大半一线评论家或著文,或在研讨会发声讨论这部著作。如此密集的阐释,留给后评者的空间并不太多。本文拟从“现实主义当代化”这个角度来讨论《应物兄》。将《应物兄》置于“现实主义”的论域中同样是危险的,首先面对的质疑是:你如何能确定“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抽屉真的装得下《应物兄》?对于这个质疑,我不但不加反驳,毋宁说同存此疑。因此,本文谈论的不是凝固“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应物兄》,而是《应物兄》与“现实主义当代化”。换言之,本文不愿将“现实主义”看成一套确定无疑的准则,而将其视为由多种方案构成、内部充满差异和张力的理论话语。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依然在变化中。我们只有用一种动态的视角来看待“现实主义”的当代生成,才能检验这一理论体系是否依然葆有面对当下的有效性。另一方面,用动态“现实主义”来观察《应物兄》,我们关注的不是它与某种具有确定边界的“现实主义”严丝合缝的关系,而是它对既往“现实主义”的逸出,以及这种逸出的必要性、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新可能等问题。
一、“现实主义”的理论张力:摹仿论、典型论、本质论和总体性
将“现实主义”放入引号中,意在强调它是一个有其特定理论边界和复杂性,不能做普泛性理解的概念。理解“现实主义”,无法绕开摹仿论。一般来说,摹仿论强调文学与世界之间的摹仿性或反映性关系。但是,由于哲学观、世界观的不同,不同思想家的摹仿论实质差异巨大。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通常被视为最早的现实主义摹仿论,他在《诗学》中认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①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背后是一种唯物哲学观。在他看来,艺术摹仿世界,但世界本身具有绝对的现实性,而不是像柏拉图一样认为现实世界只是理式的一个影子。因此,柏拉图虽也提摹仿——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认为艺术在于“摹仿”;在《蒂迈欧篇》,他把诗人称为“摹仿者”。在他看来,文艺作品如戏剧和叙事诗是在摹仿,悲剧和喜剧则是一种从头至尾的摹仿——但是,由于不承认现实的真实性,柏拉图的摹仿论重点不在“现实世界”而在其背后更高的“理式”。不应该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摹仿论看成一种简单的进化关系,似乎作为更高阶版本,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已经完全取代或超越了柏拉图。
在后世不同的“现实主义”方案中,既有亚里士多德的声音,也有柏拉图的影子。事实上,黑格尔哲学里面无疑仍晃动着柏拉图的影子。黑格尔精神哲学的最高阶段是“绝对精神”,在他看来,艺术、宗教和哲学都以“绝对精神”为把握对象,这种“绝对精神”跟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式”不无相通处,它们都是世界或历史的内核和本质。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19世纪的自然主义者是沿着亚里士多德的道路前进,他们将现实的第一性地位绝对化,既然现实就是最终的彼岸,就是意义本身,那么对现实原原本本的摹仿便成了写作的正途,由此发展出文学摹仿现实的复杂而繁琐的技艺。相比之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跟柏拉图、黑格尔则更有某种精神亲缘性。虽然他们强调世界的客观唯物性,但他们更强调世界的内在本质。由于这种本质观,“现实”由此被区分为外在的、现象的“现实”和内在的、本质的“现实”,这更像是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现实”背后的“理式”。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等经典现实主义观念,其哲学观正是来自对深度的、更高的、绝对的“理式”的信奉。换言之,在我们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现实”是存在等级性而不能被等量齐观的,并非所有的“现实”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由此,写作被想象成一个类似于雕刻的过程,那些无用的部分被削去之后,本质的形象就逼真地呈现出来。写作正是挖掘和寻找被掩盖起来的“本质”的过程。因此,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就建构了一种个体与集体、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平衡术,一种由个体而抵达环境,进而触及时代和历史的写作机制。
在写作实践中,把“现实主义”视为一种写实技艺理论上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而要求“现实主义”创造出立体性格,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体现的则是“典型论”。跟典型论相关的还有一种“本质论”,不仅从艺术角度对“现实主义”提出要求,还对“现实主义”的思想内容、倾向和立场做出了规限。这最突出体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中国的“两结合”现实主义中。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跟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区别何在?南帆以为“前者要求在现实的描绘中展现出明亮的历史前景”③,高尔基便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在写出“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之后,还写出“未来的现实”④。事实上,这与其说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准确地预见未来,不如说是以未来的名义为“现实主义”捆绑了给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因为“现实主义”所携带的“真实性”“具体性”中天然地包含着立场失控的危险,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允许真实细节带来立场上的“云自无心水自流”,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乃是一种规定了本质的现实主义。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在1958年有了自己的理论建构——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倡导。“两结合”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样都是预制本质的现实主义,区别在于,“两结合”现实主义既规定了特定倾向、立场的“本质”,又拓宽了“现实主义”的风格规限,使写作上的“浪漫化”获得了混搭“现实主义”之下的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结合”现实主义绝不是空泛的口号,它有非常明确的斗争针对性。规定“本质”事实上就是回收在真实名义下进行社会观察和批判的权力。因此,它反对在真实的名义下描写灰色的小人物、卑污的反面人物甚至是中间人物,反对描写“内心的复杂性”。换言之,正是因为“两结合”现实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艺划定了边界,干预生活、暴露黑暗等文艺功能才被宣告回收或取消,“高大全”“三突出”等文艺原则才获得安置在“现实主义”之下的历史契机。
在“现实主义”的多种思想模型中,有必要特别提到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事实上,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虽跟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主义”本质论有密切关联,但并不完全重叠,这一理论所具有的“乌托邦性”及其在总体上把握碎片化现代社会的问题意识,并未完全丧失其思想潜能。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与他出版于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有密切关系,不同于伯恩斯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蔑视,卢卡契认为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总结为“总体性”范畴。所谓“总体性”,是指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总体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范畴,反过来,现实世界的本质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蕴含在“总体性”之中。不难发现,“总体性”就是理解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偶然与必然等关系的理论范畴。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相信一个更高的历史本质的存在,因此他们也相信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可能性。与柏拉图“理式”的简化和唯心相比,黑格尔到马克思,对更高历史本质的理解向辩证性更靠近一步。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不仅是对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方法的提炼和显形,从总体上辩证把握世界从而认识历史本质一旦被置于“总体性”概念之下,就将“本质”从一种确定的结果转换为一种认识方法。换言之,我们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可能孜孜以求的是“历史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卢卡契“总体性”的概念转换,认识的重点变成了如何“总体性”地认识历史本质。这很可能是卢卡契的“总体性”理论在今天依然具有思想潜能的原因。
有必要指出,在苏联和中国,“本质论”虽然得到文学制度的授权而成为某个时代的文学的思想芯片,虽然“总体性”包含着跟“本质论”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我们并不能将“总体性”完全等同于“本质论”。在卢卡契的时代,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推崇尚没有获得现实体制的加持,“总体性”并非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而是人们追寻历史本质的不懈努力。即使在今天,不将“总体性”视为某个确定的答案,而将“总体性”视为一种认识视野和方法,视为文学为世界赋形的一种探索方向,恐怕依然在诱惑着很多人。
回到现实的文学实践中,“现实主义”概念通常在如下几个层面被使用:(1)指以写实为手段,具有逼真的现实感的作品;(2)指以宏大社会和历史题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3)指具有反思现实、批判现实精神的作品;(4)指自觉运用典型化、本质化手段的作品。当我们企图探讨《应物兄》与“现实主义当代化”关系的时候,有必要认识到:那种为世界预制本质的“现实主义”依然在某种范围内延续着,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文学认同;相比之下以“摹仿论”为哲学基础的写实“现实主义”,以“典型论”为思想基础的“批判现实主义”依然为很多作家所青睐。20世纪90年代以来,种种结合了现代主义手法和现实批判意识的“魔幻现实主义”(也有诸如“神实主义”“深度现实主义”等命名)书写也广受欢迎。
李洱是一个有过精彩的现代主义探索的作家,将《应物兄》纳入“现实主义”的考察视野,基于以下三点考虑:其一,《应物兄》在基本叙事手法上使用的是写实笔法;其二,《应物兄》的写实性叙事中包含着与以人、事为叙事中心的传统现实主义的刻意疏离,从而体现了某种以言为中心的“饶舌现实主义”倾向;其三,《应物兄》不断宕开一笔的饶舌产生的碎片化背后,依然有着非常清晰的“总体性”追求。因此,《应物兄》无疑处在正生成的“当代现实主义”的延伸线上。
二、 《应物兄》:“饶舌现实主义”的悖论
出版至今短短一年多,关于《应物兄》的评论很多。这部作品的反讽叙事、知识分子叙事、当代书写、与伟大文学传统的关联、小说与知识等等问题短时间内获得了大量聚焦。我更愿意从《应物兄》的饶舌叙事来把握这部作品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改写。从叙事上看,传统现实主义基本是以人或事为中心的。以人为中心,遂发展了种种人物塑造法、扁平人物/圆形人物论、典型人物等叙事理论。以事为中心,则衍生诸如草蛇灰线、悬念创设、矛盾冲突、一波三折等叙事技巧。必须说,既往现实主义在以人和事为中心的范式上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李洱在写《应物兄》之时,恐怕已为自己立下目标,就是要在这些现成的范式之外另辟蹊径。用“饶舌现实主义”来指称《应物兄》,无关褒贬,只是希望从某种叙事特征来把握其对现实主义的崭新探索。“饶舌”在此既指《应物兄》在实践一种以“言”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叙事,指它通过不断的叙事宕开来规避了冲突型叙事范式的实践,也指它对文化诗学叙事技巧的广泛采纳。
关于《应物兄》以“言”为中心的叙事,我想援引评论家曾念长的观点,他认为《应物兄》“是一部违背了史诗叙事风格的长篇小说”,因为他“没有故事情节”“没有行动主体”“没有总体结构”。在他看来,长篇小说的这种史诗叙事模式源自西方,而《应物兄》则试图召唤中国小说源于稗官野史、发挥“子集”叙事资源的传统⑤。这些观点不无启示,所谓“没有”故事情节和行动主体不是完全没有。事实上,与很多“反故事”的先锋小说完全没有故事不同,《应物兄》作为一部有具体背景、人物、事件的小说,不仅人物众多,且充满了故事性。就人而言,据统计,《应物兄》中出场的人物共有七十多个,这相对于《红楼梦》《金瓶梅》《战争与和平》等作品虽然不算多,但也绝对超过一大半的当代长篇小说。《应物兄》同样不缺故事元素,小说主线围绕济州大学邀请美国哈佛大学儒学大师程济世回国筹办儒学院展开,涉及的人物诸如应物、费鸣、葛道宏、乔木先生、双林院士、程济世、芸娘、文德斯、栾庭玉、邓林、季宗慈、铁梳子、朗月等等,这些人涵盖士官商艺,每个人的性格、经历都足以延伸出枝繁叶茂、错综复杂的故事。说它“没有故事情节”和“行动主体”是说李洱放弃了以故事情节(事)和行动主体(人)去建构小说的叙事范式。谢有顺就指出,“过去的故事,都是以‘事’为中心的,但李洱似乎想创造一种以‘言’为中心的叙事,至少,他想把小说改造为一种杂语,把叙与论,把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一起。所以,《应物兄》里很多地方是反叙事的,叙事会不断停顿下来,插入很多知识讲述、思想分析、学术探讨”⑥,这是很精当的概括。
以事为核心的写作,无论再气势恢宏、线索繁多,都很难逃脱主体中心化的规划。无论再复杂丰富而富于象征的事件,其覆盖面都是有限的,这与李洱意欲通过《应物兄》织一张具有总体性视野的叙事网是相悖的。为了打破“事”天然存在的界限,他总是不断地在一事将立之时宕开一笔,由琐事衍生琐事,由一人推及另一人,使“事”本身在小说不再重要,反而是“衍生”的惯性在无限延展,成了《应物兄》吞吐“总体”的内在潜能。
《应物兄》自始至终都贯彻着一种无限宕开的“人物衍生术”。第一节就事而言只有一条——校长葛道宏意欲将校办秘书费鸣打发至应物兄正筹办的儒学研究院。若采用冲突型叙事模式,则必沿着葛道宏、应物兄和费鸣三人构成的矛盾潜能展开故事,但《应物兄》则迂回得多,它更多是通过种种细节展示了应物兄无所不在的自我争辩和精神分裂。而后,则以“电话”为延伸媒介,引出了乔木先生和替宠物狗木瓜诊疗的“事”。进入第二节,小说依旧没有奔“事”而去,而是倒叙了乔木先生对应物的提携和教诲,暗示应物兄从一个率直之人变成一个自语者的缘由。第三节顺势宕开逸出到乔木先生及其现任夫人巫桃的家事。第四节才进入宠物狗木瓜在动物医院看病的事,由此而引出华学明、金彧、商人铁梳子等人。这里事实上已经呈现了《应物兄》“衍网成言”的写作姿态。一般小说,往往以一事或几事为种子,铺衍事端而使种子长成大树,如此小说状如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或诸多大树相互掩映的树林。但《应物兄》却刻意使绝大部分“事”蛰伏如种子,它们包含着种子的生长潜能,却尚未长出。它们在小说中只是成为一个“网点”,李洱并不试图将任何“网点”发展成某件重大事件中的关节或机枢。它们只是衍生其他网点的中介,而在“衍网”的过程中,叙事被最大限度转变为“成言”。《应物兄》将枝繁叶茂的故事恢复为种子状态,却将空间留给种种言语所构成的“复调性”。很多论者都论及《应物兄》中不同人的声音构成的“喧哗与骚动”,本文不再赘述,我更想将上述“衍网成言”的写作跟卡尔维诺的“时间零”对读。
在一篇题为《你和零》⑦的文章中,卡尔维诺提出了“时间零”概念,用以阐发一种有别于强调故事来龙去脉完整性的新叙事模式。在他看来,传统小说大都苦心经营故事情节的发展机制,着意写出时间负一、时间负二、时间负三(所谓故事的来龙),并铺陈笔墨,描述时间一、时间二、时间三(所谓故事的去脉)。传统故事遵循着一条完整的时间轴来建构情节链,而一般读者也往往醉心于此,喜欢有头有尾、情节曲折的故事。卡尔维诺却不看重完整的时间轴,而认为“时间零”才是最重要的绝对时间。在他看来,“时间零”就是连接故事来龙去脉的那个中点,它包含了故事发展的前因后果。传统小说由一个点而铺衍成一条完整的线索,卡尔维诺则主张把一条时间轴压缩简化为一个“时间零”点。不难发现,《应物兄》中故事所处的那种蛰伏如种子的状态,跟卡尔维诺的“时间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李洱在《应物兄》中的这种叙事选择,与卡尔维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文化动因。
卡尔维诺的“时间零”是他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过程中叙事“空间化”的一种探索,对于卡尔维诺来说,故事时间性中所寄托的“消费性”和意义神话已经成为必须挑战的对象。将叙事空间化是对时间所虚拟的意义的祛魅,有效地将各种虚构的“意义”转化为延异的游戏。但对李洱来说,《应物兄》之所以选择一种消解故事的模式,其文化动因不在于走向后现代主义,而在于重构现实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意义”常让位于“符号”的嬉戏,所以,其解构故事,目的不过在于创造叙事的可能性。但对现实主义而言,叙事背后的“意义”犹存。对于李洱而言,《应物兄》并非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叙事,而是为了准确抵达时代和现实而不得不创造一种叙事的新可能。换言之,之所以称《应物兄》为“饶舌现实主义”,是因为“饶舌”乃是为了“现实主义”。如果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跟这个圣言不在、大道炸裂、众声鼎沸的时代同构的“现实感”,《应物兄》的“饶舌”便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所以,在“现实主义”的论域中来看《应物兄》,是因为它深刻地关联着“现实主义”的失效和重构的必要性问题。质言之,相对于《应物兄》企图抵达的当代性和“总体性”,原有的“现实主义”可能是失效的,为此,“现实主义”必须重构其属于当代的新范式,才能继续保持有效性。由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以言为中心的叙事选择背后,相对于既往“现实主义”,究竟有何新创?又藏着怎样的观念转型?
三、 总体性危机之后的“现实主义”何为?
在“现实主义”视野中看《应物兄》,会发现它呼应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摹仿论部分,也不是其典型论和本质论部分,而是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方案。《应物兄》最大的企图,可能就是建立一种抵达当代总体性的认识论。从摹仿论出发的现实主义,很难摆脱完整叙事的执念;从典型论出发的现实主义,则更倾向于在人物刻画上下功夫。《应物兄》所受到的诟病,很大部分正是基于传统写人叙事标准的论定。譬如有论者认为,《应物兄》“枝蔓繁密芜杂,人物众多纷乱,用力过于分散”,这里就涉及了叙事结构和人物刻画两个传统现实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叙事方面,《应物兄》“给人以没有精心结构、失之随意之感,好像写到哪儿算哪儿,如山涧水流随物赋形了。尤其是情节枝蔓繁密,推进较慢,加上知识的信息量太大,堪称海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样的叙事方式,实在是令人透不过气来”。在写人方面,涉及人物七十多,“但用力过于平均、分散,造成很多人物形象的塑造面目模糊,性格漫漶”,“平均用力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篇幅,反而冲淡了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次要人物也模糊不清”⑧。
这种批评基于传统以写人叙事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论者也可谓有理有据,而且在一般读者中,恐怕引为同调者甚众。但这种批评的盲点在于,没有意识到其所立为不二法门的正是《应物兄》力图规避的。换言之,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有效性,在李洱眼中已非不言而喻。毋宁说,正是意识到现实主义的危机,李洱才冒着陷入悖论的危险,来重构一种“饶舌”的“现实主义”。事实上,艺术探索的冒险性在于,新范式在刚出现时并非自明地成为“范式”。一种艺术实践在获得公认前并没有相应的阅读解码器,假如它创造了真正的新质,它就必然要进入已有解码的盲区,因而被误解和苛责就是艺术探索的必然代价。因此,艺术探索不仅要负责创作新范式,还要负责培养新的解读方式。但艺术探险之所以依然充满吸引力,正因为旧范式在新现实面前不断失效,而敏感的探索者,往往最早意识到旧范式已然失效。
对《应物兄》而言,“现实主义”在何种意义上的失效支撑起它越界的合法性呢?
有必要提到詹明信的“文化逻辑”概念。在他看来,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不可以任意选择。詹明信认为,“现代主义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自身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文化逻辑体系,因此,从现代主义中抽取某部分或者‘技巧’来借鉴是没有意义的,仿佛现代主义的‘技巧’是中性的、没有价值问题的”⑨。现代主义关联着时代、价值倾向和文化逻辑,现实主义亦然。循此出发,我赞同王富仁先生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区分,他从认识论和价值论出发,指出现实主义在认识论上秉持可知论,在价值论上则坚持有意义论,世界既可以被认识的,也具有确定的意义;现代主义则在认识论上走向不可知论,但依然是价值论上的有意义论者,对于现代主义者而言,世界虽然荒诞不可知,但反抗荒诞本身也构成了存在的意义;至于后现代主义则是认识论上的不可知论和价值论上的无意义论的结合,世界既不可认识,也无所谓确定的意义,由此便走向了符号的嬉戏和狂欢。这套解释模型,同样基于这样的设定: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跟相应的认识论、价值论乃至历史阶段深刻联系的。
按照某种进化论的观点,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后,现实主义就被迭代淘汰了,可是事实并非这么简单,事实是:现实主义的某部分失效了,但另外的部分却可能被拓展并激活出新的有效性。再次回到上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失效的部分是什么?又何以失效?
在我看来,《应物兄》正包含着对“现实主义”可知论及其衍生技巧的某种忧虑。传统现实主义之所以对“完整叙事”和“圆形人物”具有如此大的热情,正源于这样的设定:它相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存在着完美无损的相互映照。因此,它在孜孜不倦建构一件或几件“事”的完整链条时坚信,一与多,有限事体与无限本质之间有着和谐的可交往性;它之所以对立体饱满的人物倾注热情,不仅是对魅力性格的爱好,还因为它相信:人物如果足够典型,就可以通向环境,从而成为有效介入时代和历史本质的切片。如此看,“现实主义”对于写人叙事的热情确实源于它坚定的可知论和乐观的价值论。问题是,在经过“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冲刷之后的李洱,对这种坚定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并不抱有很大的信心。《应物兄》折射的正是作家的这份将信将疑:与其说他对认识世界产生了怀疑,不如说他对传统现实主义提供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怀疑。他并不相信认真经营几条主次分明的事件链就能够抵达历史的总体性。然而,《应物兄》依然相信,世界的总体性可能被小说以某种新的方式所把握,否则,《应物兄》就干脆不会存在。
换句话说,《应物兄》丧失了对某种确定的历史本质论的信心,却依然没有失去抵达当代中国之总体性的雄心。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和悖论,使它的重心从“人”“事”而转向了“言”。这里暗示着作者这样的判断:从对时代之“言”的诊断去抵达总体性的可靠性远大于从时代之“人”“事”出发的诊断。这种写作观念跟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大陆广为传播的存在主义语言观或许有内在的关系。与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不同,存在主义语言观力图确立语言作为世界本体的地位。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界有所谓“语言学转向”的出现。这种转向的基本立场就是相信现实是由语言建构的现实,而语言作为一个总体体系,对于世界而言是第一性的。由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的边界就是语言的边界,以及福柯所谓不是主体在言说话语,而是话语在言说主体等论述广为流传。秉持语言工具论,我们就会认为语言不过是事和人的衍生物,即使通过语言可以建立思想体系,但它依然是从属于人的。但假如相信语言才是塑造世界的前置装置,那么语言当然大于“人”和“事”,从言出发也具有敞开了一条通往总体性的道路。
请想一下,作为一部具有书写当代雄心的作品,《应物兄》为什么要以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心呢?难道仅仅因为李洱更熟悉知识分子群体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对于当代社会的不可取代的代表性呢?那便是从其与当代社会的“语言”系统的关系上。因此,《应物兄》可能不是要成为一部书写当代知识分子的小说,而是一部通过当代知识分子透视当代“语言系统”裂变并进而抵达历史总体性的小说。读者可以轻易发现《应物兄》采用了某种“戏仿经体”的形式,每一节的小标题都取自该节第一句的前二字,这是对《论语》的戏仿。《论语》和儒学在中国文化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古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因为《论语》本身有多么重要的政治指导性,而是因为儒学作为宋以后的奠基性话语地位使《论语》成为了政治文化中的关键节点。因此,《论语》地位来自传统社会的话语团结性,《应物兄》中那班力图复兴儒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企图恢复的正是这种话语的团结性。问题在于,他们不得不面对当代话语四分五裂的状态。《应物兄》有力地展示出,“言”的分裂而非团结才是当代性的典型症候,而当代性的难题就在于,如何在分裂之言中去重建时代的正言和个体的确信。就此而言,它确实通过“言”的通道触摸到了当代的“总体性”之核。但《应物兄》并未将某种路径指认为正确的方向,如是它就陷入了它所反对的先验“本质论”了。因此,《应物兄》是这样一种将信将疑的“现实主义”,他质疑还有某种先验的历史本质存在,却又相信从总体上把握当代的可能性;他不为身处言之迷雾的当代指出一条正言之道,但他也相信,当代人的内心,依然应有对言之共同体、言之肯定性的向往。
结语
李洱的《应物兄》在某种意义上归属于“现实主义当代化”这一当代谱系。作为一个内涵难以简单论定的理论范畴,“现实主义”不可一概而论而应历史化为诸多不同的理论方案,同时“现实主义”依然在新的语境中寻求新的合法性。《应物兄》的写作有意疏离于“现实主义”的摹仿论、典型论和本质论范式,但却在探索着“现实主义”总体性范式的新可能。因为疏离于摹仿论和典型论,《应物兄》刻意打破那种以“人”和“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而创造了一种以“言”为中心的长篇叙事模式。因此,对《应物兄》的评价,不能以既定的、静止的“现实主义”标准为尺度,而应基于“现实主义当代化”的视野,看到它从“言”的维度去抵达当代生活总体性的探索。当代总体性的悖论在于,最大的总体性就是生活和话语的碎片化本身。《应物兄》的写作,深刻地命中了这一文化症候。
《应物兄》这类探索性小说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喝彩和指责同在的处境。以既定的“现实主义”艺术尺度来衡量,它在写人叙事上都过于漶漫,并不足观;站在认可其探索的立场,又会发现,它对情节型、人物型叙事所携带的真实幻觉及快感的放弃,对以典型论勾连现象与本质的“现实主义”路径所投的不信任票,才真正激活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有效性。《应物兄》从“言”的分裂性处入手,反而找到了贴近当代“总体性”的表达。有必要重申一下:“现实主义”必须经历不断的“当代化”才可能持续保持有效性,《应物兄》无疑敏锐地觉察到“现实主义”传统模式的危机,但却并不能宣告既往艺术经验的彻底失效,同样也不能将自身确立为可供袭用的新“方程式”。毋宁说,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时代,唯有承认话语的持久裂变性,才有可能靠近话语的团结性。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诗学》,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②《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③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④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演讲》(1935年),《苏联作家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⑤曾念长:《回归小说的途径》,未刊。
⑥谢有顺:《思想与生活的离合——读〈应物兄〉所想到的》,《当代文坛》2019年第4期。
⑦Italo Calvino.Zero and You.ContemporaryLiteraryCriticism,Vol.73,ed. by Thomas Votteler. Gale Company, 1993.
⑧刘江滨:《〈应物兄〉求疵》,《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2期。
⑨詹明信著,陈清侨、严锋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