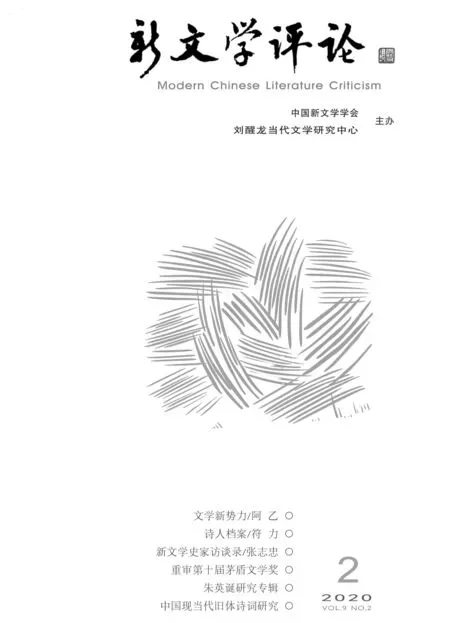余华“自我训练期”创作再解读
2020-11-17李立超
□ 李立超
1987年第1期《北京文学》在小说栏目首篇的位置刊发了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十八岁出门远行》虽然源于从报纸夹缝里看到的一条关于抢苹果的小消息,但是它却是作家自己所认为的“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在当时,很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新的文学形式,也就是后来的先锋文学”①。但是《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发表距离余华开始小说创作差不多已有五年,1984至1986年间余华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作品一直没有收录到各种集子中去。对此,作家本人给出的解释是,这个阶段“是我阅读和写作的自我训练期”②。如果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构成了余华“经典化”的起点,那么这些“自我训练期”的作品则无疑是余华个人写作史的起点。余华将这些作品筛选至文集之外虽说有着“悔其少作”的意味,但是倘若要对余华个人的“文学史”进行深入开掘的话,这些“集外之作”,这个不算成功的开端则必然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 1983—1986年的创作
根据刊物的标示,余华的处女作是发表在杭州的文学刊物《西湖》1983年第1期的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小说《第一宿舍》。《第一宿舍》的故事围绕着只有八平方米的第一宿舍中的四位年轻医生展开,寡言的毕建国是故事的主人公。对病人尽责但也被称为傻瓜的毕建国检查出患有癌症。此时“我”才知道毕建国之所以偏爱海棠花,是因为他的亡妹乳名叫小棠,而且小棠身世曲折,她是毕建国父亲已故战友的女儿。毕建国病逝后,他的父亲,一位考察归国的老干部赶到第一宿舍,将儿子的骨灰带走,想要把他葬在小棠走失的大兴安岭。小说的结尾是“我”眼含热泪地望向窗外,“外面开始下雨了。不知大兴安岭也在下雨否?”③。连同文章一起刊出的还有编辑的“编后”,编辑称赞这篇小说“关键还是比较注意写人物”,但作品也还稚嫩,“最明显的不足也许是焦点人物毕建国尚欠丰满、厚实,若干情节、细节较常见;后半部分,哀伤味过浓一些”④。同年,《海盐文艺》第1期刊出了余华的《疯孩子》,这就是后来发表在《北京文学》的《星星》的前身。《疯孩子》并没有后来《星星》的圆满结局,“背多汗”被送到了乡下外婆家,成为用两根木棍拉琴的“疯孩子”⑤。
“儿童”构成了余华这些“习作”中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198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收录的一篇题为《萤火虫》的短篇小说值得引起注意。小说并不复杂,萤火虫对于小林、小慰两个孩子而言就是故去的外公的化身,整篇小说将孩童的单纯天真与死亡的阴郁神秘糅合在一起。《萤火虫》是整个小说集中唯一没有标注写作时间的作品,而且这个短篇在之后余华的各种作品选集中再未出现过。因此,《萤火虫》很有可能属于作家自己认定的“自我训练期”作品。
《甜甜的葡萄》发表在江西《小说天地》杂志1984年第4期,后被《儿童文学选刊》转载。这篇小说篇幅很短,主题是赞扬了一个小男孩以德报怨的品质,读来有些拙稚,语言也较为口语化,结尾或许是为了点题,缀上了这样一句,“听说,被泪水滴过的葡萄,特别好吃”⑥,难免有煽情之嫌。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的《看海去》是一篇描写少年心绪的作品,描述了已经长大成人的“我”回忆幼时与哥哥看海的经历,现在“我”、哥哥和父母分为三处居住,不能像从前那样朝夕相处,但海依旧。这篇作品收稿时为小说,但刊发时发在散文栏目下。同栏目的有汪曾祺《桥边散文》(两篇),这足见《北京文学》对青年作者的扶持。但这篇《看海去》初初由编辑推荐给副主编李陀看时,李陀看了之后,觉得一般,没什么特别之处⑦。同样是以“海的故事”为框架的《白塔山》(《东海》1986年第6期)则在儿童故事中嵌入了青春期的懵懂情愫以及阴森的气氛:白塔山原是故事中的地方,传说世上哪怕是最丑最蠢的孩子只要进去白塔,出来就会变成最聪明最漂亮的孩子。哥哥声称他见过白塔,在海的中间。于是,“我”和小玩伴琳琳游泳去海里找白塔山,不幸的是,琳琳溺水而亡。多年后,“我”在一个夜晚梦见了白塔山,琳琳说她在山上等我。
这一时期,“爱情”亦是余华着重描写的对象,《鸽子,鸽子》《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两篇小说都带有青年人在爱情中怅然若失的情调。《鸽子,鸽子》(《青春》1983年第12期)沿袭的是传统小说“两男一女”的模式,主人公是“我”、舍友小左以及一位“斜眼姑娘”。“我”,姓李,一名年仅二十岁的眼科医生。因为进修的缘故,“我”离开家乡,来到小城的第一人民医院,和同来进修的同龄军医小左住在同一间宿舍。“我”和小左经常结伴在黄昏时分去海滩散步,我们在海滩上遇见了一位少女,她来放飞驯养的鸽子。偶然一次机会,我们竟然发现这位姑娘患有斜视眼。为此,“我”和小左借机暗示姑娘,斜视眼是非常容易治疗的眼科疾病,她可以通过手术矫正。三个月之后,我们突然在小城里重新遇见放飞鸽子的姑娘,她已经动过矫正手术了,变得十分漂亮。秋天的时候,姑娘成为小城的报幕员,并有了男伴。“我”觉得她的眼睛不再是过去的那双眼睛了,她也不再是过去的她了。某一天,“我”和小左在海滩散步时又遇见了姑娘,她认识海滩上的许多人,却不认识这两个曾想办法让她矫正眼睛的年轻眼科医生了。鸽子许久没有放飞,一放走便再也不回头了。姑娘独自一人坐在大石上垂着眼等待鸽子飞回的模样让“我”和小左回忆起初次见她的情景。在小说的结尾,余华尝试和读者展开对话,写道:“亲爱的读者,当那两只鸽子向茫茫天际飞去的时候,也把这个故事带走了。”⑧相较而言,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第4期的《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则显得流畅圆熟不少,这个短篇小说经过两稿才得以完成。“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取自苏小明演唱的《等到月儿圆》,是一首八十年代的流行金曲,同时也是小说男主人公经常吹出来的一段旋律。小说描写了爱情中的“错过”,19岁的工厂女工兰兰为了得到男主人公的青睐学着穿时髦的衣服,把辫子剪掉,换成张瑜那样的短发。可是男主人公一直深爱并且怀念的是兰兰那一对披在肩头的五十年代式的长辫子。小说虽然缺乏一定的深度,在细节描写上也有些繁冗,但是对青年人心理的刻画却颇为生动。
余华虽表示过这一阶段的写作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响,但此时的不少作品与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亦有着深刻关联。《第一宿舍》中加入了“伤痕文学”的桥段,《竹女》则带有浓厚的汪曾祺气味,《男儿有泪不轻弹》无疑是顺应了“改革文学”的潮流。《竹女》(《北京文学》1984年第3期)充满朦胧的诗意,整个小说仿佛一个被氤氲水汽笼罩起来的梦。竹女和丈夫鱼儿、婆婆一同生活在静水湖上,以捕鱼为生。竹女和父亲逃难来到静水湖,婆婆一家好心收留了竹女,并认她做儿媳妇。十多年来,竹女和婆婆互相体贴关爱,竹女经常梦见小鸟在家乡屋前的两棵老榆树上玩耍,掉下和竹叶一样青翠的羽毛。一日,竹女突发高烧,丈夫鱼儿和婆婆尽心伺候。有位老者也于此时来到竹女家中,他很有可能就是竹女十多年未见的父亲。最终,老者虽然离开了,但竹女的梦里第一次出现了一对美丽的鸟儿,是那位慈爱的老者送给她的。《竹女》的笔调十分温柔,将竹女的身世、经历娓娓道来,虽然遭遇了苦难,但余华将这些苦难包拢在幽远的牧歌情调之下,带有沈从文、汪曾祺一脉京派文学的遗风。《男儿有泪不轻弹》(《东海》1984年第5期)遵照的是“改革文学”模式,小说的主人公“新厂长”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八十年代在全国赫赫有名的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这篇小说被选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生日的礼物——浙江作者短篇小说新作选》,这部小说新作选是纪念建国三十五周年的献礼之作,在《编后》中有这样一句评价,“整本集子也还缺乏正面描写改革形象者的力作”⑨,这似乎也是对《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一种评价。
余华在这段训练期中所创作的作品格局不大,大多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小感触入手,但是,也尝试着对重大历史记忆进行书写,譬如“文革”。发表在《西湖》1983年第8期上的《“威尼斯”牙齿店》表面上看是一则以江南水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但是余华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嵌入了“武斗”故事,牙医诗人老金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头子”,带领一众红卫兵对村里的阿王进行严刑拷打,阿王最终被打死,但是老金在之后的另一桩“武斗”中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阿王的养女小宝并没有嫌弃老金,反而对爱人不离不弃。这个“文革”故事虽然有些生硬,结局也有些突兀,但是能看出余华在努力将自己脑海中的“文革”记忆诉诸笔端。发表在上海《萌芽》杂志1986年第1期的《三个女人一个夜晚》对“文革”记忆的处理则显得流畅自然许多,整个小说也流露出点滴的先锋意味。余华将小说中唯一的男性角色,三个女人在共同等待的一个男人符号化为“顽固”。三个女人在车站等待“顽固”的过程中不断诉说着与“顽固”的回忆,但这其中真假难辨。小说最终的落脚点是三个女人共同回忆起十多年前去杭州的经历,大家都是偷跑出去的,坐车不用钱,住宿也不用钱,杭州到处都是红卫兵,她们住在“红太阳”广场。那次虽然没有去成北京,可是六和塔太好玩了。这个小说篇幅很短,但有限的篇幅中却交织了现实、回忆、梦境,虽然难免匠气,但是在写法上有一定的新意。
从文学性或曰文学意义上看,余华的这些“少作”只停留在“练笔”的阶段,拙稚生硬,更多的是描摹生活的表象。但我们依旧不能忽略这些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对于余华的“个人文学史”而言。这就提醒我们,暂且放下今日批评者的眼光,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或许可以找到一种进入余华文学世界深处的路径。
二、 一个小镇青年的80年代
小镇上的高考落榜生是余华踏上文学创作道路之时的最初面貌。作为1977年的高中毕业生,余华是名副其实的“应届生”,可正因为是应届生,所以与那些在农村、工厂待了几年十几年的往届生相比,一时间尚认识不到高考是一次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况且这一拨应届生是在“文革”中度过了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时光,因此几乎没有认真学习过,连填志愿都闹出了大笑话。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的牙医工作算是解决了余华的“前途”问题,但是余华将医院称为“牙齿店”,自己是一名店员,每日重复托拉斯似的流水线劳动。在余华的描述中,牙医不是现今所认为的知识分子式的体面职业,而是:
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副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来自医学院⑩。
七十年代末伴随着知青返城,青年如何就业成为社会焦点,为了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国家允许年轻人自己找出路,做“个体户”。八十年代初,“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理发的、修鞋的、磨刀的、修自行车的、卖饮料小吃和各种手工艺品或小商品的”。社会的脉动显然不能使余华获得找到出路的快乐,反而让他生出忧伤甚至自卑的感情,他羡慕那些在文化馆工作的人可以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
决定以写作为途径进入文化馆的余华是刻苦勤奋的文学青年。据当时与余华相交甚密的好友蔡东升回忆,一群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余华突然有了灵感,就一个人回去写小说了。夏天的晚上,天热,蚊子多,余华会穿上高帮雨鞋(防止蚊虫叮咬)坚持写文章”。海盐的文学环境虽然封闭,但是余华却积极参加文学活动,1982年的余华已然是县文化馆里的名人了,经常出现在各种创作会上。而且,此时的余华已经建立起了“出走”的意识。余华见到蔡东升在海盐县沈荡镇进行文学创作,便劝他把工作调动到县城武原镇来,并且为了调动工作做了许多事,因为在余华的认识中“县城文学氛围好,你一个人在沈荡要‘死’掉的”。沈荡与县城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差距,这种迫切的不想“死掉”的心情似乎也正暗示出余华自己想要进入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文学中心的企图。尚是小镇文学青年的余华显然已经具备了“全国”的眼光。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后开始写作的这一代作家,余华是这样的描述的——“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候出版成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杂志上发表”。于是,白天拔牙晚上写作的余华形成了一套投稿策略,“完成一个短篇小说总是先寄往《人民文学》或者《收获》,被退回来后寄给《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再被退回来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杂志寄”。余华的努力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寄给《北京文学》的三篇小说都要发表,其中一篇需要修改一下,编辑周雁如邀请他进京改稿。这次进京改稿是余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出门远行(儿时和父亲一起回过山东老家),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从海盐坐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一路辗转,余华终于在1983年11月到达西长安街七号的《北京文学》编辑部。余华花了三天就把稿子改好了,从《疯孩子》到《星星》,主要是给小说一个“光明的尾巴”,《星星》的结局是星星、云云两个孩子合拉一把小提琴,还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登台为小朋友们演奏。再后来,听说梅纽因音乐学校招了两个中国孩子,一个叫星星,一个叫云云。诚然,这个结局过于理想化,也显得生硬,其力度远逊色于原先小男孩成为“疯孩子”的结局。纵观1983年和1984年间的文学创作,其中影响较大的小说多以反思“文革”创伤、叩问严肃社会问题为主题,如路遥《人生》、王安忆《流逝》、阿城《棋王》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星星》倒也显得清新活泼。《星星》为《北京文学》1984年第1期“青年作者小说散文专辑”的首篇,并入选“《北京文学》一九八四年小说类优秀作品”,余华的照片也被刊登在1985年第5期封面内页上,这期亦刊发了余华的创作谈《我的“一点点”——关于〈星星〉及其它》。
小说的发表、获奖以及进京的远行加深了作家的自我审视,余华似乎更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边缘”位置,他不无激动地表达着对《北京文学》的感激:
在编辑部,《北京文学》的一名负责人询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后,很有感情地对我的小说的责任编辑说:“他是来自最基层的。”从这句话里,我感受到了《北京文学》对我们这些在最基层的无名小辈,是如此重视和爱护。
我想,《北京文学》如此培养我,怕是亏本的生意。我只有更努力一点,尽量使《北京文学》的损失小一点。
我只能这样。
1980年到1984年间,比余华小三岁的苏童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环绕着他的是北师大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球场。1984年,已经发表了多篇作品的莫言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利用一切时间阅读、写作。跟他的同代人相比,余华没有在大城市生活的经历,亦没有进入大学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面对封闭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感伤与焦虑相信一直盘旋在心头。
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三篇小说虽然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关注,但《北京文学》开出的证明却轰动了海盐,余华成为海盐历史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星星》的成功使余华赢得了县委宣传部的青睐,被借调到海盐文化馆,主持全县文学创作。在海盐县文化馆的余华经常收到县里文学爱好者的来稿,并通过通信的方式与作者们进行交流。遇到好的作品,余华会将它们编在《海盐文艺》上。王干曾评价余华对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余华的理论建设,对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余华在《上海文学》写过好多篇理论文章,而那些理论文章今天看来都是真知灼见”。或许余华的评论功底和批评眼光就是从《海盐文艺》时期开始的。翻阅当年余华与海盐县文学爱好者的通信,不难看出他在文学评论、文学批评方面的敏锐。读了同县文学青年俞士明的一篇稿子后,余华指出:“这稿比起你以前此类题材的稿子,进步实大。关键在于你写人时开始应用一些生动的细节了。但在立意上欠缺了点,嫌实了点,缺乏空灵感”。在面对一个处理“怪题材”的作品时,余华表示:“这是一个怪题材,处理时也要怪一些,尤其应该是要表现出一般题材不应具有的那种深度来。”1985年下半年因为查禁小报和一些经济问题,《海盐文艺》停刊了。在此之后,余华仍不遗余力地将身边文学青年的稿子推荐给他相熟的杂志和编辑。
透过作家的种种自述、友人的回忆,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隧道,触摸到三十多年前的点滴。气质有些忧郁的高考落榜生余华,一边干着牙齿店的活计,一边刻苦勤奋地开始了写作事业,陪伴他的有小镇上的文学青年,有枕边川端康成的作品,或许还有夏日灯下的蚊虫。但是余华的雄心和视野并没有被海盐这个江南小镇所局限,他用他的灵气打开了通往北京的道路。于此,有一个问题值得引起思考:余华为何将《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自我训练期”的终结,并且这与其被视为先锋文学的标志中间有着怎样的关联?
三、“清理”与“断裂”
《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据现有资料显示,最早对它发出评论的是王蒙。1987年2月,王蒙写下了一篇题为《青春的推敲——读三篇青年写青年的短篇小说》,这篇文章发表在《文艺报》1987年第2期上。王蒙对小说的整体评价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单纯、困惑、挫折、尴尬和随遇而安,在这篇小说里写得挺妙”,“青年作者写青年的理想的失落与追寻,骄傲与困惑,表现出的新意与意中的幼稚,都使笔者觉得亲切。对这样的作者与作品笔者是又理解又不理解”。不难看出,王蒙虽然察觉到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在叙事形式上的一些巧妙之处,但是仍然在现实主义文学、青春文学的框架中对其进行解读。但整体上,评论界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关注是通过“回溯”的方式展开的,《一九八六年》(《收获》1987年第6期)、《现实一种》(《北京文学》1988年第1期)等带来的强烈的阅读冲击使评论家们通过这条理路回看《十八岁出门远行》。《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余华的隐蔽世界》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的综论,目的是对余华小说的主题进行阐释,作者认为余华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他“富于勇气地将他的笔触深入地探寻到了人生的深层结构中”,而这一深层结构正是人性中的罪恶。文章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论述并不多,只强调了“十八岁”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成就了见证恐怖、丑恶的成人世界的仪式。但是,文章中写明《十八岁出门远行》“是目前所见到的余华唯一的短篇小说”,“唯一”这样一个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命名值得玩味。而樊星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的《人性恶的证明——余华小说论(1984—1988)》则难得地梳理了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前的作品,赞美这些作品“都写得精致、写得优雅、写得美”,并且指出《星星》的艺术成就不在《雨,沙沙沙》等篇之下,但影响却远不及这些“抒情散文”的原因在于“1985年前后,冷漠之雾弥漫开来”。《十八岁出门远行》虽然很难说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仍是写实的笔法,格调、主题都变了,“‘恶’主题取代了原来的‘温馨’主题,余华的笔也从表现诗意转向了冷酷描绘恶行”,但是在作者看来《一九八六年》才是余华第一部代表作。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先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当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当时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讨论并不怎么热烈,就连李陀对其的赞扬也是通过“回忆”的方式展开——“我很难忘第一次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种种感受”,“然而《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阅读却一下子使我‘乱了套’——伴随着那种从直觉中获得的艺术鉴赏的喜悦是一种惶惑: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当我拿到刊物把它重读一遍之后,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预感:我们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对于《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读法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它可以当作一篇现实主义小说来进行解读,亦可以接续在余华短篇小说创作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但是,作家和文学史叙述却选择了“断裂”与“遗忘”的方式对其进行阐释。
1989年,余华在其先锋宣言性质的《虚伪的作品》中表示“在1986年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之后,我隐约预感到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即将确立”,“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这里的真实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2017年5月,余华在一次面对中小学语文老师的报告会上专门谈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并且具体描述了当时自己的写作状态——一次“非经验的”写作,“如同小说里的‘我’在公路上‘走过去看吧’和那个司机‘开过去看吧’,我的写作也是写过去看吧”。“对立”“断裂”“遗忘”构成了余华自己解读《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暗合了“制造”先锋文学的外部规则,甚至是整个八十年代的“反封建”思潮。我注意到李陀在《雪崩何处》一文中用到“年纪轻轻的作家”“青年作家们”“不足三十岁”这样的词汇,将“新的作家”与“新的写作方式”进行了对接,这无疑使先锋文学呈现出一副新鲜的、激进的、横空出世的面貌,但是,这也割断了先锋文学中所隐藏的历史脉络。余华清理了自己的“前《十八岁出门远行》”时期,实际上是清理了自己的写作与“十七年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是1985年以前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同样,这样的清理亦可见于余华的阅读史中,对于他而言,只有外国文学是“一位作家的选择”,只有在外国文学那里,才能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于是,我们看到了余华对卡夫卡的无比推崇——“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时间建立起来的一套写作法则在一夜之间成了一堆破烂”,虚伪的形式“使我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犹如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自在”。程光炜在《余华的“毕加索时期”——以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九年写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为例子》一文中曾谈道:“这种从‘传统个人’转移到‘现代个人’、从‘非作家’转移到‘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个人’重建之路,几乎涵盖了一九八○年代大多数作家社会身份转型的过程”,“这些作家与其说在小说中探讨了‘个人价值’,不如说他们在探讨中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印证了自己生活道路的正确选择”。对于余华而言,将1984至1986年间的作品筛选至文集之外正是指向了从牙齿店个体户/小镇文学青年到“青年作家”的转变,这不仅具有“个人史”的意义,更是一种被赋予了“文学史”意义的行为,对于批评家而言,先锋文学的兴起需要的也正是这一股具有象征性的“十八岁”的力量。
细读余华的那些“少作”,它们虽然粗糙、稚嫩、模仿痕迹严重,但并非如批评家所言,只是充满了温馨,至少在我看来,这些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难掩潮湿、阴郁与恐惧。余华曾苦恼于生活中“只有一点点恩怨,一点点甜蜜,―点点忧愁,一点点波浪”,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家也在不断重温、消化这些经验。但是,余华对这些作品鲜少提及,将这些作品筛选至文集之外的举动与将《十八岁出门远行》视为自己“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一次面对八十年代的发言,暗示了作家在“新与旧”“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做出的选择,只是这种选择是通过自我清理的方式而实现的。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余华小说创作研究”(Y201839512)研究成果;浙江科技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余华与1980年代”(F701116H04)研究成果。]
注释:
①余华:《我的写作经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②余华:《我的写作经历》,《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③余华:《第一宿舍》,《西湖》1983年第1期。
④余华:《第一宿舍》,《西湖》1983年第1期。
⑤余华:《疯孩子》,《海盐文艺》1983年第1期。
⑥余华:《甜甜的葡萄》,《儿童文学选刊》1984年第4期。
⑦付锋、李雪:《八十年代是热衷创新的年代——关于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长城》2011年第5期。
⑧余华:《鸽子,鸽子》,《青春》1983年第12期。
⑨浙江文艺出版社编:《生日的礼物——浙江作者短篇小说新作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⑩余华:《我为何写作》,《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