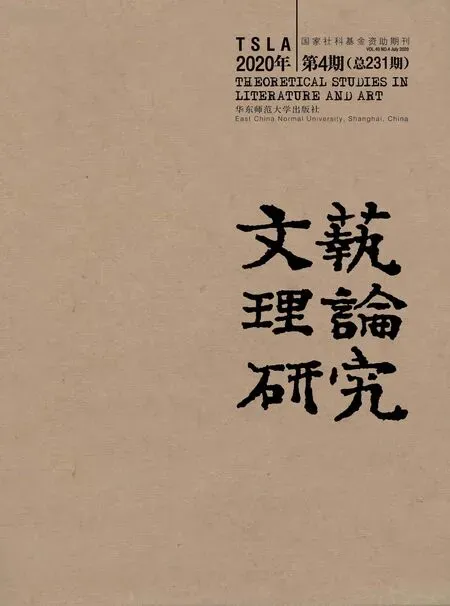数字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从艺术批判到数据生产中的“参与”
2020-11-17张钟萄
张钟萄
“全民参与”是当前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参与”甚至已演变成一种“文化”形态,它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加入文化和日常事件,使他们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创造者。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移动互联网来“参与”网络文化的搭建: 随时随地留下消费偏好,在社交媒体中分享图像,上传展现个性的私人数据等。这些现象最典型的特征是平等参与,人们在其中进行真实的表达和自由的分享。不过,当我们置身于“数码(或曰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语境时,这些现象却恰好符合、乃至顺应了它的生产机制: 数字资本主义一改先前以物质生产工具和强制性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模式,在主张更自由、更真实和更自主的时代氛围下,让广大用户自愿“参与”,甚至无时无刻不在鼓励他们自我表现,上传私人数据,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由此可见,“参与”不仅是一种日常和网络现象,也是一种艺术实践方法。在艺术中,它同样意味着让更多人平等且自主地加入艺术的创作和欣赏,让被动的艺术和美学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践行和创作者。从西方20世纪早期的前卫派艺术,到战后发展至今的艺术实践,无论在雕塑、装置领域,还是在戏剧、文学领域,都已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尝试把观众的参与纳入作品的创制中: 即打破观众与演员和舞台的界线,打破单纯视觉欣赏的范围,打破单纯由艺术家来完成作品的权限等。这些尝试最典型的诉求,一方面是以实践来彰显艺术背后所潜藏的自由、自主和真实性;另一方面,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系统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控制。而后者恰恰又是维护艺术家和艺术自身的自由、自主和真实性的手段。我们看到,艺术实践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参与”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但它的逻辑仍然是以艺术来实现人们的个性表达和自我展现。
这两条分别演进的路线,实则暗含了同一个逻辑基础: 无论从特征,还是从具体方法上来看,它们都表现为让更多的人平等和自由地加入与日常生活相交织的文化生产和个性/自我表达的行列中。此外,从史实来看,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作为生产工具的计算机和互联网,其发展进程更曾直接受到艺术和文化这条路线的影响。最明确的证据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计算机领域的重要技术人员受到主张自由、自主和真实性这类价值诉求的艺术文化运动的影响,部分人甚至将计算机和互联网视为实现这些价值主张的工具。简言之,技术手段被注入了理想和伦理价值色彩,亦极大反映了以“自由、自主和真实性”为基本取向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然而,我们也看到“参与”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发生的变化:“参与”不仅发挥了艺术实践中的“批判”功能,而且还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发挥了“生产”功能。尽管我们很难得出“参与从‘批判’变成了‘生产’”这种简单的结论,但我们确实看到,由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所奠定的“参与”展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功能。在这两种不同的功能和生产机制下,我们甚至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自由表达: 一种是主动的,它是为了批判地参与而出现的自我表达;一种是被动的,它是被裹挟、被制造出来的,是为了生产而进行的自我表达。因此,虽然“参与”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活动形式,乃至政治和伦理手段,曾经将许多人从压抑的等级体系和权力高压下解放出来,并在建构当代多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或者说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该警惕它与资本主义汇合后的功能走向,并借此反思艺术批判和更普遍的文化参与形式。
若想要理解“参与”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功能走向,以及何以诸多用户主动加入看似自由的“个性表达”和数据生产,我们就必须回到作为文化形式的“参与”的历史变迁中,并探讨其背后的伦理价值观(即逻辑基础)。为此,本文将分三个步骤来解释这一点: 首先,“参与”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在艺术批判中发挥了批判功能,并展现了个人主义的伦理诉求;其次,作为批判话语的参与文化与技术发展相汇合,实则是借技术极大地展现了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最后,建立在这种伦理价值观诉求和技术基础之上的参与,在与资本主义新的生产机制结合起来后,不但发挥了其批判的作用,而且拥有了强大的“生产”功能,我们可以借此去思考,针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生产,如何开启一种新的批判。
一、 历史上的“参与”及其批判功能
今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广泛且深入的数据输出是“参与”最新近的表现。从文化氛围的层面来讲,目前已出现了知识问答中的大规模参与、明星培养中的相互参与、虚拟社群的互动参与等参与类型。它们既是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化表现。在当代艺术中,也出现了主张广泛“参与”的作品和项目,它们大多表现出游戏式的娱乐功能。这些现象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希望更多民众能够卷入作品中,展现自由、平等和主动的参与。尽管论述文化和艺术史中的“参与”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无论如何,从历史来看,“参与”都在很大程度上因关乎“个体的自由和真实表达”,而经由各种文化形式指向“批判”。本节将分三步来分析艺术中的“参与”: 首先,它是一种具体的文化和艺术实践形式,并发挥着批判的功能;其次,把“参与”当作批判,是“艺术批判”(artistic critique)大背景下的一种具体表现;最后,作为艺术批判的“参与”,背后暗含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同样倚重的伦理诉求,这奠定了二者汇合的价值基础。
(一) “参与”之为批判
一般来看,艺术中的“参与”绝非新鲜之物。仅以20世纪的艺术为例,“参与”不仅出现在世纪初的前卫艺术实践中,也出现在60年代以后的大量艺术实践中,且种类繁多。尽管它们出自不同艺术流派和门类,但具有类似的诉求: 让观众进入艺术实践的过程之中,唤起其批判性意识(要么针对日常生活,要么针对现实经济政治状况)。在20世纪初,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Bortolt Brecht)试图打破传统的戏剧和剧院形式,让观众参与其中,尤其是通过在戏剧中融入陌生化的效果来唤醒观众的批判能力(Lehmann17)。这一脉络延续到了波瓦(Augusto Boal),以及更新近的后戏剧剧场实践中;另一方面,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dadaism)同样实验了“参与”。比如,1921年4月举办的达达大会(Dada Season),结合了一系列能让更多巴黎民众参与其中的表现形式。达达艺术家走出其主要发源地的酒馆,以多种形式步入公共空间,包括街头、沙龙、审判、投票和教堂等。①这不仅标志着达达主义的艺术表达从舞台和剧院走向了日常生活和街头(Haladyn20),更促发了人们通过广泛地参与艺术创作来批判文化现状。他们通过艺术“参与”来唤起观众自由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最终指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种批判意识延续到了60年代更完整的“艺术批判”中。
在60年代以后的艺术实践中,“参与”被赋予了更广泛但也更细致的批判功能。比如在雕塑领域,极简主义艺术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通过让观众的身体知觉参与艺术经验,从而将作品带入了一个包含了身体运动、光影变化和空间结构的框架中,以此批判基于支架之上的传统雕塑中隐含的艺术家权威。换句话说,观众以身体行动“参与”艺术作品,是从更细致的艺术经验角度,批判了由艺术家预先决定艺术作品之意义的绝对权威;在音乐艺术中也有类似的案例,约翰·凯奇(John Cage)在他著名的《4’33”》中,让观众发出的不经意之声和周遭环境的噪音共同“参与”到音乐的演奏乃至创作中,以此反对传统的音乐结构以及基于其上的艺术家权威;“体制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艺术中的重要代表汉斯·哈克(Hans Haccke)将批判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系统,以观众的“参与”,来反思和批判文化的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框架;其他同时期的艺术家也在艺术中融入“参与”,如巴西艺术家克拉克(Lygia Clark)在艺术疗愈中突显人与物或其他人的关系,让他们相互参与;偶发艺术(happenings)以“参与”来强调偶发性和共同融入(如Allan Kaprow);乃至有艺术家用身体的参与,来消解和批判理性与启蒙主体(如James Turell);或以艺术参与来实践社会和政治行动(如Joseph Beuys)等。
在此种历史语境中,“参与”充分展现出了其具有的批判功能: 批判原有的艺术自主,因为它将艺术和艺术实践框定在固定的空间或艺术家手上。有趣的是,60年代以“参与”打头的艺术批判却把矛头指向了另一种艺术自主: 摆脱经济和政治系统对艺术实践和艺术作品的干涉,摆脱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流通系统对艺术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决定权的攫取。此时的艺术自主虽然仍旧反对范围局限的艺术实践,但更反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系统的侵蚀。概言之,逐渐完善的艺术系统,不仅包含了艺术的生产、展示和流通程序,而且还能决定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价值。于是乎,部分艺术家奋起反抗和批判这种伤害了自主表达的艺术系统。
(二) “参与”和艺术批判
此语境中的艺术“参与”实则是“艺术批判”的一部分。一是因为艺术家为“参与”注入了具体的“批判”功能;二是因为它乃一种历史表现。“艺术批判”原本源于知识圈和艺术圈。根据法国社会学家波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的说法,艺术批判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两种批判之一(另一种是以工人和街头运动为主的“社会批判”)。②它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现代资本主义逐渐发达后,尤其是在巴黎所兴起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当现代资本主义破坏,乃至瓦解了传统的经济生产模式后,标准化和一般化的工厂生产严重影响了人类的自由、真实性、创造力,以及美和意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由此掀起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此批判谱系中的艺术流派,包括了德国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以及战后的前卫派运动,如激浪派、观念艺术、情境主义、贫穷艺术,以及体制批判等。要理解艺术批判和“参与”的批判功能,我们必须回到资本主义发展的语境中。
根据波尔坦斯基们的论述,现代资本主义实际上对应着两种“解放”。第一种是指资本主义在以工厂模式为主的阶段(主要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上半期),将民众和劳动力从原有的家庭作坊和地域局限之中解放出来,民众进入逐渐兴起的现代城市、现代市场和现代工厂。然而,资本主义在将民众从原有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把他们推入了新的压迫和奴役之中,如普遍工厂制的不稳定状态、劳动异化和集体缺失。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的艺术作品和理论,如卓别林的电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应的“社会批判”层面,则出现了大量要求制度公平和分配公平、改善工薪者生活条件、建立保障体制,乃至福利国家的社会运动。然而,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又掀起了另一种寻求解放的诉求(主要在20世纪中后期),因为福利国家引发了关于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的批判。批评者认为,二者的结合限制了个人的自主性,福特主义中的等级制制约了创造力,标准化和规模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更是破坏了人的真实性(或本真性)。因此,“艺术批判”和“社会批判”开始寻求第二种“解放”,包括更自由的工作环境、更具弹性的组织结构、更自主的能力发挥,以及寻求性别、种族和等级上的平等和自由。
总的来说,无论是第一种解放还是第二种解放,艺术批判的基本诉求都是个人主义式的: 要么主张个人从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机制中解放出来;要么主张个人从新近的压迫机制中解放出来。它们最终表现为更加自主、强调个体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主义。而这一切通通反映在了上述更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尤其是以“参与”来实现这一点。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实则是伦理价值观的体现,即将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视为(不可撼动的)“价值”。因此,在涉及“参与“的艺术实践中,这些价值诉求既反映在了赋权给观众的项目中,也表现为艺术家的创作诉求。如前面提到的艺术家哈克,他试图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系统对艺术家自主性和真实性的压制。可以说,“艺术批判”的诉求实际上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不仅渗透了文化艺术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的行为模式,还影响了技术的发展,就后者而言,它尤其体现在网络技术的实用功能和文化意涵之中。
二、 个人主义下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参与”
20世纪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的诉求,这反映在了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就后文论述而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参与之所以发挥出强大的“生产”功能,恰恰是这种价值观强化的表现或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至少需要解释两个重点: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技术自身的变化,如它在功能上变得为个人化服务;另一方面,借助60年代爆发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渗透进技术发展的伦理价值观——它不仅在实质上影响了计算机行业的从业者,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价值诉求。
(一) 计算机技术的个人化发展
在20世纪的技术发展史中,计算机与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参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这种技术自身的发展有关,也与艺术和文化在它身上所寄予的想象有关。从计算机自身的发展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左右,它逐渐突显出在功能上为个人服务的趋势。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间,国际形势还处于冷战和军事对立的状态,这要求冷战国家发展强大的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③为此,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形成了相对严格和官僚化的社会规则和组织形式。在此背景下,计算机得以迅速发展,被视为能推动军事技术和核武器进步(尤其是实现军事指挥和控制)的信息系统,主要服务于大型工程和军工业。然而,到了60年代左右,计算机设备开始进入一个变革期,如50年代还是规模巨大的中央处理器,开始变成可以放在桌下运作的微型计算机。设备上的新变还包括小型计算机的出现、单独使用和交互性功能的出现等。历史学家认为,至70年代,计算机的功能已经开始转向“个人化”(Ceruzzi 207)。尽管设备和技术上的变迁推动了网络技术从60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快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关乎科学家的个人视野、计算机科学的社会史,也不仅涉及冷战时期计算机的军事功能,更涉及“反主流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向了去中心化和非等级制的社会想象——技术被赋予了有助于变革社会的功能。④
这种社会想象更具体地表现为计算机被赋予了“解放”的功能。例如,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化和网络化,来实现人人平等的参与,最终对抗社会和国家日趋集中化的信息和权力途径(特纳14—16)。这一“对抗”有广泛的现实表现,譬如,在经济领域,大众生产转向了即时生产和大众消费,大规模且具有等级制和中心化特征的企业组织模式,转向了小规模和去中心化的项目合作制,特定地域(如底特律的汽车工业)的生产,也转向了一种全球化和跨国生产的模式。总的来说,原先那种固定且相对严苛的生产和管理机制,转向了一种更具弹性和自由的机制。因此,此时的“参与”不仅表现在艺术实践中,还反映在了要求去中心化、去等级制和网络化的生产和管理结构中。换言之,员工要求自己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决策、生产和消费中去。在此趋势下,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不仅被人们赋予了变革的社会想象,而且被视为有助于这种变革的工具,其想象尤以个人化和社会解放为核心。这种趋势在文化语言上的表述就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⑤
尽管计算机身上有了这种社会想象,但它自身和它背后的新技术并不被认为具有完全的积极意义。批判者大有人在,无论是计算机和技术对人际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还是其背后的权力控制,或者是新技术本身对工具理性和效用性的绝对追求,都被他们置于审视台上。德裔美籍计算机科学家维森鲍姆(Joseph Weizenbaum)在1976年对计算机的能力及其对人类的影响作出了批判性分析。他的核心主张认为,不能让计算机做重要决定,因为它缺乏某些人类特有的能力,如激情和明智。尤其是决策不同于选择,选择是一种人类执行其判断力的结果,而非计算的结果。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埃鲁(Jacques Ellul)在更早的1964年就预见到所谓“技术性社会”的来临: 技术不同于机器、工艺或达成目的的过程;甚至于在技术性社会,技术扮演的是一种整体性方法的角色,它能够理性地涉及所有人类活动领域,且具有绝对有效性(EllulXXV)。埃鲁的技术性批判影响了芒福德(Lewis Moumford)一系列关于技术的论述。此后二三十年,当计算机技术越发强大后,波斯曼甚至用更严厉的“机器意识形态”来批判技术垄断背后的专家权力。⑥
(二) 反主流文化与技术的价值化
如上所述,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被赋予了“解放”和变革社会的想象,除了因它是个人工作的办公用具外,实质上更因为它表达了与艺术批判,以及“反主流文化”运动同宗同源的价值诉求: 艺术批判看中“参与”,是因为它以平等的个人参与,来批判福利国家,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等级制对个人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的侵蚀;而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则从技术上实现了去中心化和网络化,从而保障了个人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的科学理论(如控制论)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想象,极大地影响了文化领域;而后者的价值取向又影响了技术的变化。
借特纳的分析来看,若以美国为例,为了应对冷战背景下的官僚系统和社会规则,当时的年轻人发起了两个有所重叠却又不同的运动: 一个是以“新左派”之名而为人所知的民权运动和言论自由运动,主张民权平等,长期反对越南战争(特纳28—30);另一个则是文化领域的产物,如垮掉派文学、禅宗佛教、行为绘画,以及精神药物的运用等,这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反主流文化”运动。⑦其目的,不仅在于应对冷战时期的社会氛围和文化风格,而且还在于创造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特纳将后一运动称为“新公社主义”,它与当时的某些前卫艺术圈受到了同源的技术语言影响,包括前述主张“参与”的艺术家。如在以曼哈顿和旧金山为中心的艺术世界,从计算机和科学领域发展而来的控制论拥有众多追随者,包括约翰·凯奇、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卡普罗(Allan Kaprow)等人,他们阅读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传播学奠基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工程师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等人的文章。结果是,技术语言中的协作和去中心化,在凯奇和劳森伯格看来意味着艺术实践应该是艺术家、观众以及材料之间的相互合作,因而需要引入多维度的“参与”。⑧极简主义艺术的发起者之一贾德(Donald Judd),尽管不是因技术影响才主张观众的“参与”,但他身处同样的时代精神之中。他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促使他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加入了三种民主平权活动。可以说,当时艺术中所谓的“参与”,只是某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它既反映在了网络技术的社会想象中,也渗透到了作为批判的艺术实践中,但二者共同指向了关乎社会政治的现实和理想,最终是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这极大地反映出渗透技术发展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
如前所述,此时的西方社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社会生产和生活从原有的机械化、中心化的状态,转变为信息化、去中心化和网络化的状态。在“反主流文化运动”中,计算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符合,乃至有助于这种新阶段的形成。只不过对运动参与者来说,他们更看重计算机技术所具有的“解放”功能: 促进个人化和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正因为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解放”功能,它才被赋予了合法性。但归根结底,其“合法性”的获得还是因为这种技术“满足”和“符合”了“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艺术批判背后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 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符合它背后的社会精神。由此可见,后工业社会,或后福特主义的技术话语,实际上是围绕福特主义所展开的技术和政治文化批判,也就是批判福特主义那种范式化了的技术形式、组织模式、体制化,以及在文化、政治和个人等方面的缺陷。借用费歇尔的话: 在资本主义的福特主义阶段,技术话语赞美技术有能力通过减轻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来提升保障、稳定性和平等这类社会目标;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技术话语赞美的是技术有能力提升个人赋权、真实性和创造力等个人目标,这减轻了资本主义的异化性质。⑨因此,在艺术批判和“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以“参与”和广泛平等之名所展现出来的敏感和激进态度,不过是表达了社会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当与能够进一步推动这种价值诉求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汇合后,它们不仅在其中实现了强有力的表达,甚至成了这套价值观的载体或技术等价物;或者说,技术通过激进的审美化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化——要知道,它先前是全然为军工业服务的工具。不过,技术的价值化也奠定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 “参与”的生产功能: 迈向数字资本主义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其功能朝个人化和个性化的转变;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了个人化和个性化的技术等价物——计算机的功能以及运用,本身就是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等价值在技术上的某种体现。广大网民借助这类最便捷的技术手段,以“自我表现或表达”之名,展现个人主义所追求的自由、自主和真实性。所以我们在移动互联阶段看到了更彻底的表现: 用户的审美表达、消费偏好、社交情况,乃至私密生活,通通透过网络技术实现了最“真实”的“自我表达”——做自己!更简单地说,席卷全球的网络“参与”,成了这类价值诉求的最新表现。不过,当资本主义通过越发成熟的系统实现了以非物质生产来获益后,几乎所有“参与”网络的自我表达,都成了资本主义麾下的生产数据。就作为广泛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参与”而言,我们看到它曾通过“观众(visitors)参与”来批判资本主义,如今却还透过“用户(users)参与”,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一方面源自资本主义的转型;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则是源自“参与”自身所暗含的价值观内涵。
(一) 资本主义生产的转型: 数据、个性和真实性
对于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资本主义转型,已有学者作过大量研究,它除了“后工业社会”“后人类”,还包括“认知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以及更新近的“大数据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等。无论如何,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网络“参与”都涉及以数字手段来催发和实现的数据生产。它像认知资本主义一样,侧重非物质的生产模式。更具体地来说,由网络技术推动的普遍“参与”,不仅人数更多,且内容更广。先前的“参与”主要是观众参与艺术作品的欣赏或完成,如今的“参与”却囊括了几乎一切真实的个人信息、原创内容,乃至情感感受,且它们以“数据”的形式被资本主义吸收。不同于此前的生产,此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 曾经那种带有合同契约的工厂或在企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还带有某种强制性,如法律规定的劳资关系和权利义务等;如今,劳工变成了一种自愿且免费的信息劳工(inform labor)。这种转变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起来后,尤其是90年代以后,靠信息等非物质要素和手段来生产的模式形成了,研究者称这种生产模式中的劳工为“非物质劳工”。⑩原有的剥削不再只是针对身体能力,而是全天候的大脑工作;生产时长也不再局限于法律保障的范围,而是见缝插针式地持续生产: 用户在工作时生产数据,在吃饭时生产,在度假时生产,甚至睡觉时也通过可穿戴设备生产。
同样,在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中,我们看到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深刻转变: 要求更多参与的文化形式,不再将公众视为预先建构好的单纯的信息消费者,而是把公众当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制造、共享、重构和混合媒体内容的人(生产工具)(Jenkins2),如范·迪克所言:“一种参与式文化的结构,就是愈发要求普通百姓通过应用媒体技术来表现自己,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传播他们自己的创造物,而这些技术曾经是资本集中型工业的特权。”(Van Dijck42—43)因此,大量自媒体、Web2.0,或强调共享的内容生产机制步入主流。这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更为关键的生产转型: 将人的非物质要素作为生产之源,由此解决无限生产与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更具体而言,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积累和生产模式转向非物质生产,其根源是寻求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料。此时,资本的积累和生产不仅强调创意内容的无限性(即取之不尽的“原创性”),更重要的是,“差异性”成了无限的资源(即用之不竭的“真实性”)。结果是,个人数据,再加上个人数据与个人数据之间的排列组合,如身体健康、感情指数,乃至购物心愿清单,所有这些属于不同单个个体的“真实性”,都成了无限资源和无限生产之源。用更简单的话来说,个性化和真实性通通被商品化了,而个人数据是最直接的个性化和真实性的表现。
(二) “参与”的新功能及新的批判
至此我们看到,在当前的“参与”文化中,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提供了技术和平台来网罗最多的参与者。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除了技术本身具有优势外,技术还被一种价值观所价值化。概言之,网络技术是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诉求的技术等价物。然而,仅仅说技术功能展现了这种价值诉求,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广大网民如此自愿,乃至沉迷于网络参与和数据生产,不能解释他们沉迷其中的主动诉求为何。据上文分析,网民的原创内容和数据输出实则是个人真实性和自主性的展现,也是个人自由的某种实现。可以说,网络时代的“参与”是“自我表现/表达”的最新形式。这跟历史上的艺术批判、体制批判、“反主流文化”运动有一致的价值内核和逻辑延续。它们都在追求现代个人主义所推崇的“自由、自主和真实性”。如果说有不同,也是程度上的差异,亦即,当前这种无孔不入的“参与”,之所以发挥着不同于先前“参与”之批判的生产功能,从根本上来说并非因为“参与”自身发生了功能转型,毕竟,它们属于两个生产系统。与其说是“参与”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变得更强了: 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在艺术批判传统中,“参与”主要由艺术家牵头,使观众从“被动”参与和表达转变为“主动”诉求;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则是通过技术的支撑,使得个人的自我表达转变成更积极的主动诉求,但这也意味着某些强烈的个人化和个人主义是被制造出来的。奠定在同样的伦理价值观之上的“参与”,在艺术批判中的个人表达和自我展现是自由的,如今却可能是被资本、数据库或平台所诱导生产出来的;一种是追求自由的主动诉求,一种是看似主动的“被动自由”。当这些被动和被制造出来的“自由表现”和“真实个性”以数据形式呈现出来时,它们必然被非物质的生产方式收编,形成庞大的数据库:“大数据意味着老大哥的权力,意味着巨大的资本主义商机。”(Fuchs58)有人甚至警告,这意味着权力和财富的大数据暗含了一种大分裂(或电子/数码分化),即,分化为拥有和控制数据者与没有和贡献数据者(Andrejevic673—89)。面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迈向数字资本主义的情形,我们不应只着眼于技术性的异化批判,更不应只是把矛头指向资本积累,而是要看到主体或用户主动参与其中的价值诉求。如果我们要开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看到它是社会结构之变的结果。即,它一方面涉及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和生产模式等要素的结构性转变;另一方面,我们还不能忽视技术和网络话语背后的伦理价值诉求提供给它的合法性,以及一种网络精神。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借艺术批判和文化领域的现象来解释当前的网络“参与”文化,不仅因为它们有事实上的交织,更因为它们处于同样的价值谱系之中。发挥“批判”功能的“参与”,如今更多地在商业文化和资本积累中发挥着“生产”的功能。这甚至意味着,“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在文化艺术的层面,掩盖了经济剥削的不道德性;或者说,一种“参与”其中的自主、自由,且真实表达自我的价值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实质的经济剥削;更直接地说,从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的视角来回看艺术批判和数字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了一条以“自由”来掩护剥削的路——行路人似乎以文化平等之名,掩盖或遮蔽了经济的不平等,甚至因此丧失了从社会机制和现实情境出发来进行真正的改变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倒不在于我们不能从文化和艺术角度来展开批判,而是假若文化、艺术、理论和精神层面的批判与强烈的个人主义诉求相结合,便很可能导致这类“参与”同公共生活和群体的现实相脱节,乃至不顾现实,“批判”自身也变成一种“个性化”的自我表现。由此可见,“参与”已经是当代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它不仅出现在了艺术领域、商业文化中,也出现在了网络所提供的技术平台上。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参与”经历了从在艺术领域中发挥“批判”的功能,到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发挥数据“生产”功能的转变。推动其转变的,实质上是一种关于“自由、自主性和真实性”的个人主义伦理价值观。这不仅构成了艺术批判的价值诉求,更构成了与资本主义转型后的生产方式相符合的价值根基。要理解和批判与网络技术和大数据结合的资本主义,我们必须看到这背后的伦理价值观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变迁,很可能涉及在现实中被掩盖之物,而它们曾经是“参与”所力图批判的对象。
注释[Notes]
① 布列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回顾,见: Andre Breton and Matthew S. Witkovsky, “Artificial Hells. Inauguration of the 1921 Dada Season,”October105(2005): 137—48.
② 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述,具体见,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TheNewSpiritofCapitalism(London/New York: Verso, 2005).
③ 席勒给出了此阶段的重要论述,见丹·席勒: 《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翟秀凤译,王维佳校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④ 关于计算机的社会想象功能,参见: Patrice Flichy.TheInternetImaginaire(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7);Thomas Streeter, “That Deep Romantic Chasm: Libertarian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mputer Culture,”Communication,Citizenship,andSocialPolicy:Re-ThinkingtheLimitsoftheWelfareState(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9),49—64.
⑤ 见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关于文化影响网络发展的重要研究还可见: Roy Rosenzweig. “Wizards, Bureaucrats, Warriors, and Hacker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et.”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03.5(1998): 1530—552.
⑥ 关于这一点,见尼尔·波兹曼: 《技术垄断》,何道宽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9年)。
⑦ 对此运动的一个文化史研究见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 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方晓光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19年);一个极富洞见的批判见理查德·罗蒂: 《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⑧ 艺术家论述“参与”的文本见: Claire Bishop ed.Participation(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⑨ 关于这一讨论,可参考费歇尔对“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的合法话语”这一话题给出的详尽分析,见: Eran Fisher.MediaandNewCapitalismintheDigitalAg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219—21.
⑩ 可见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RadicalThoughtinItaly. Eds. P. Virno and M. Hardt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133—48;亦见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8页;新近讨论也称“信息劳工”,见Frank Webster.TheoriesoftheInformationSociety(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Andrejevic, Mark. “The Big Data Divide.”InternationalJournalofCommunication8(2014): 673—89.
Ceruzzi, Paul.AHistoryofModernComputin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3.
Ellul, Jacques.TheTechnologicalSociety. Toronto: Vintage Books, 1964.
Fuchs, Christian.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DigitalObjects,DigitalSubjects. Eds.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ian Fuchs.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53—71.
Haladyn, Julian Jason. “Everyday Boredoms or Breton’s Dadaist Excursion to Saint-Julien-Le-Pauvre.”TheEveryday:Experiences,Concepts,andNarratives. Ed. Justin Derry and Martin Parrot.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20—33.
Jenkins, Henry, et al.SpreadableMedia:CreatingValueandMeaninginaNetworkedCul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3.
Lehmann, Hans-Thies.PostdramaticTheatre. Trans. Karen Jurs-Munby. London: Routledge, 2006.
弗雷德·特纳: 《数字乌托邦》,张行舟、王芳等译。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Turner, Fred.FromCounterculturetoCyberculture. Trans. Zhang Xingzhou and Wang Fang, et al.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2013.]
Van Dijck, Jose. “Users Like You? Theorizing Agency in User — Generated Content.”Media,Culture&Society31.1(2009): 4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