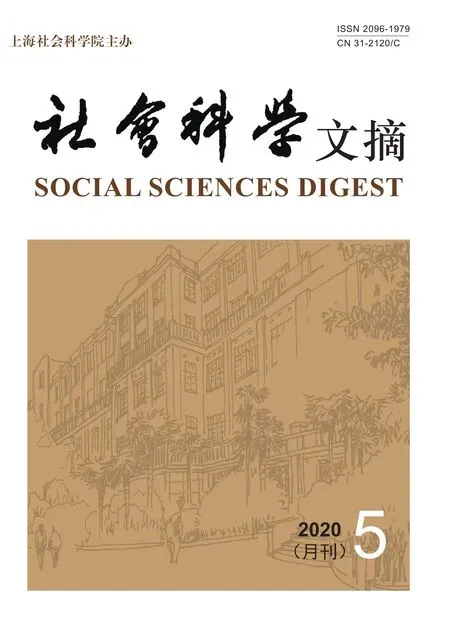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
——以王韬《漫游随录》为中心
2020-11-15魏欣
文/魏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中国的大门。以男权为本位的传统农业文明开始遭受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全方位冲击,同时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也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有识之士或开展洋务运动以图自强,或译介西学以新国人观念,或走出国门遍访欧美以求强国之方。在内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漫长道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晚清乘槎游历西方的智识精英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了推动社会文化变革的思想先导与改革先锋。他们亲身考察过泰西的城市生活、学校教育与社会风俗,经受过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振荡与熏染,因此,他们游记中的西方女性书写,无论臧否,都给沉闷的晚清吹入了新鲜气息,客观上对于加速传统性别观念的裂解、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他们亦难免流露出“过渡人”的性格,游移于“新”“旧”“中”“西”之间,“一眼向‘过去’回顾,一眼向‘未来’瞻望;一脚刚从‘传统’拔出,一脚刚踏上‘现代’”,在热情呼唤社会新生事物的同时,也会因为传统价值的崩塌以及随之而来的失序乱象而沮丧伤怀。在这些方面,王韬及其《漫游随录》堪称典范。
“先路之导”:王韬及其欧洲汗漫之行
王韬本是苏州甫里的一名穷秀才,却成长为备受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尊崇的儒学大师、近代中国最早借重报刊舆论参政议政的公共知识分子、晚清前期最为著名的国际政治专家以及重要的教育改革家。他首倡借西法以自强,深度介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对李鸿章、盛宣怀、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过直接影响。而这些都与他的欧洲汗漫之行密不可分。
与晚清官员奉旨出使西方走马观花式的考察不同,王韬是近代最早以私人身份游历欧洲且居游两年之久的知识分子。因此,他的《漫游随录》对西方文明的体认“在同类作品中最为真切细致”,加之连载于晚清最为重要的通俗刊物《点石斋画报》上,所以受众与影响较同时期的官方纪闻要广得多。
《漫游随录》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由王韬宣扬变法理念的现代性叙事、市场化的都市书写与个人化的情感言说三重文本交织而成,其中熠熠生辉的英国女性形象是这三重文本汇集的焦点与具象化呈现。从《漫游随录》的女性书写,不但能读出王韬师法英国倡导全面改革的现代性叙事意图及其性别意识中的张力,也能窥见他作为现代第一批职业文人主动对接上海文化市场并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异域都市风情的文化展售,还能感受到像他这样落拓的传统文士在近代市场经济浪潮中被日益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以及由此萌生的情感乌托邦想象。
“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漫游随录》中的英国淑女群像
王韬在《漫游随录》中有意识地袭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形式与表现手法,尤其是摹写女性之美的花容月貌式的套话和描述才子佳人爱情的叙事程式,并通过与豪放佻达的法国女郎相比照,最终刻画出了一批光彩照人、令人心仪的英国淑女群像,从而为其社会改革理念的推广、异域都市风情的展售以及个人化的情感抒怀奠定了基础。
(一)雪肤花貌的中国式古典美人。《漫游随录》中的西方女性大都是花容月貌,宛若中国古典美人。比如,旅途中有“月媚花娇”“微笑不语”的日耳曼乐工;马赛酒馆里有“貌比花嫣,眼同波媚”的女侍者;巴黎剧院中的法国女演员“所衣皆轻绡明縠,薄于五铢;加以雪肤花貌之妍,霓裳羽衣之妙”;苏格兰一所女子学堂的师生“珠光四照,花影双摇”,“辨论往复,妙思泉涌,绮语霞蒸”,皆“曹大家、谢道蕴之流”;杜拉书院舞会上的诸女子“其衣亦尽以香纱华绢,悉袒上肩,舞时霓裳羽衣,飘飘欲仙,几疑散花妙女自天上而来人间也”。
(二)爱慕东方才子的西方佳人。王韬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两位爱慕其才华并与其情意相通的苏格兰佳人形象。其一是敦底学者士班时的长女爱梨。她芳龄十五,“妍质羞花,圆姿替月”,“工琴能歌”,“作画俱得形肖”;“雅重文人”,钦佩王韬“旷世逸才”,常教他西文和弹琴;王韬为她吟诵《琵琶行》,她次日“亦能作哦诗声”;两人结伴出游,“余有所欲言未能达意者,爱梨则代为言之,无不适如余意之所欲出”。其二是爱丁堡传教士纪利斯毕的妻妹周西鲁离。她“年十有七,妍容丽质,世间殆罕与俦,尤擅琴歌”。初识不久,她即邀请王韬来家做客,并将闺房让给他住,还热情陪伴他在爱丁堡“排日游玩”。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情愫互生,以致酒馆侍者误以为他们是伉俪,王韬忙作辩解,周西却笑道“余固中华人”。临别时,周西穿上王韬送的华服照一小像并剪下发丝相赠,“双眦荧然,含泪将堕……呜咽不能成声,但道‘珍重’”。
(三)知书达礼的英国淑女与豪放佻达的法国女郎。《漫游随录》还刻画了多位典雅高贵的英国女性形象。爱梨女士的母亲士班时夫人“明敏持重,有大家风”;阿罗威的爱伦女士“工画善书,通法国语言文字之学”,其母出身贵族,是“淹通经籍”的女塾师;雒夫人“能识中国语言文字”,其长女律丽和密友梅丽“美慧知诗,工于六法”,等等。这些英国女性“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其谨严自好,固又毫不可以犯干也”。相较之下,《漫游随录》中的法国女性则多是豪放佻达的女郎。马赛酒馆女侍者见王韬身着长衫“几欲解而观之”,一女子给他端来八杯红酒,王韬如数回请,该女子“饮量甚豪,一罄数爵”。巴黎咖啡馆星罗棋布,妓女每晚“入肆招客,男女嘲笑戏狎,满室春生”。同样是女性自由出入社交场合与男性平等交往,英国风俗“可与中国上古比隆”,而法国“流荡有过于郑卫”,王韬臧否有别的情感态度与儒家伦理立场跃然纸上。
“男女并重”与“以收内助”:早期现代性叙事中的性别意识张力
(一)师法英国的现代性叙事
《漫游随录》并非王韬旅欧途中实时的秉笔直书,也不是对其域外游历严格的客观再现,而是他多年后依据特定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需要对记忆进行的重新编码,其中首要表现的就是他效仿英国变法自强的现代性理念。为此,他一方面按照游历的时空顺序铺陈各种新奇的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又不时跳出时空限制以全知视角对英国进行肯定性的介绍,由此构成了《漫游随录》的现代性叙事。
以《漫游随录》第二卷为例。这部分叙述了王韬初游伦敦的情形,包括在牛津大学的演讲、游览城市景观以及对市政设施的介绍等,并对英国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作了剖析。比如,指出铁路交通蕴含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战略意义,电讯业能加速信息传播、压缩时空距离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精妙的机械制造作了生动说明,对完善的科学技术门类及其社会应用作了扼要的科普。此外,他还努力追溯英国繁荣富强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原因。比如,着重介绍健全的专利制度在鼓励大众投身发明创造方面扮演的角色,高度普及且男女平等的全民教育体制在培养和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方面发挥的作用,等等。
总之,《漫游随录》中的英国是“以礼义为教”“以仁信为基”“以教化德泽为本”而“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的理想之邦,英国女性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才出落成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的淑女。如果说这样的英国形象是王韬为晚清中国之变法树立的效仿对象,那么,这些英国女性形象则是他为未来中国女性塑造的楷模。
(二)性别意识中的张力
以英国女性为理想参照来反思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路早在王韬自英返港后发表的系列政论文中就已确立。《纪英国政治》篇肯定了英国的一夫一妻制,认为这是英国政治之美的一种体现。《原人》篇强调“天地生人男女并重”,主张取消纳妾旧俗,并援引西方国家一夫一妻制“家室雍容,闺房和睦”加以佐证。晚年回到上海后的他在《漫游随录》中指出英国“女贵于男。婚嫁皆自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此外,他格外关注女才和女学问题。1888年为《镜花缘》作序时指出,历史上才女罕出的原因一是道德观念上的偏见,“谓女子无才便足为德”,二是教育制度的缺陷,“特世无才女一科,故皆淹没而无闻耳”,为此他强调女性也要读书识字。1892年发表的《救时刍议》指出,“古叹才难,女才更难。立女学校教之,女才出矣”,呼吁各省“延请女师教之,习六经六学”。在他倡议之后,1897年梁启超《论女学》提出“欲强国必由女学”,1898年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塾——在上海成立。
由此可见,《漫游随录》中的英国女性形象内在地符应于王韬的变法主张,其中折射出的性别意识引领了时代风气,推动了晚清性别观念的转型与妇女的解放,但也暴露出王韬的政治功利性与保守性。《漫游随录》中的英国女性与政教礼俗互为表里,英国女性被渲染得越美,越能衬托出英国政教礼俗的优越,也越能说明师法英国的必要。因此,王韬的性别话语包蕴在他的民族国家话语之中。换言之,从儒家伦理政治角度思考女性问题是他一贯的立场。前引《原人》篇论证“男女并重”的主要论据是阴阳和谐论,认为中国上古“阴—阳”“乾—坤”“夫—妇”各得其位,后世才兴起“媵御之制”,视女性为“玩好之物”,导致夫妻离心离德,“家之不齐,而天下国家之所以不平不治也”。前引《救时刍议》篇提倡兴办女学,其目的却是“以收内助”,让女性更好地履行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传统社会职分。王韬的女性思想首先不是出于对女性独立人格与个体权益的自觉尊重与维护,而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和集体主义的伦理政治使然,与西方天赋人权下的男女平等观念有本质区别。
文化展售与情感乌托邦:近代市场化洪流中的异域都市女性书写
(一)异域都市风情的文化展售
1884年春,王韬返回沪地定居。此时上海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与国际性港口城市,并孕育出了相当可观的近代文化市场,为王韬这样博学多识、科举仕途无望的文士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刚创刊的《点石斋画报》(以下简称《画报》)自1884年第6期起连载其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至1887年第117期止,每月奉送稿酬40银元。稍后点石斋书局以“淞隐漫录图说”为名将之结集出版,宝文阁书庄将之易名为“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石印发售。不久《画报》又推出他的《淞隐续录》与《漫游随录》。前者自1887年第126期起至1888年底止,之后王韬续作数篇,1893年订为《淞滨琐话》,由淞隐庐刊行,1911年由著易堂推出石印本。后者自1887第127期起至1889年177期止,在《画报》首页位置连载50期。1890年点石斋书局以“漫游随录图记”为名将之石印出售,1891年著易堂刊印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入其节录本。
因此,王韬完全称得上是一位畅销作家。而他之所以获得成功,与其身为书贾所具备的文化市场观念密不可分。避居香港时他曾创办中华印务总局,返沪后又创办了弢园书局,故特别在意书刊的适销对路。他曾致信盛宣怀指出,“沪上书局太多……书籍实难销售……当设一代销公司,贩运中国十八省中,为之梳栉一通……开设书局者,既非文士,又非书贾……书虽多,实无可观。若有如明季之汲古阁,专选精本佳构,亦足为书林生色”。这种明确的市场意识也会流露在文学创作中,重视潜在读者的接受状况就是一个表征。如果说《漫游随录》是王韬有意向上海市民展售以英国女性为中心的泰西都市女性风情,那么,借用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意象将西方女性描摹成中国式美人,通过才子佳人的爱情程式来渲染中土文士与英国才媛的交往,依据儒家伦理对英法女性各予臧否,显然是他针对中国读者采取的文化展售策略。
(二)情感乌托邦的想象
成为畅销作家并非王韬本意。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士”才是他自我设定的理想身份。可现实中的他始终是一介布衣,纵然已成为闻名朝野的洋务人才与报界名流,“无奈言之者谆谆而听之者藐藐”;尽管他晚年的教育改革使格致书院成为晚清新式教育的重镇、“中国启蒙的最有力工具”,其平生用世之志稍得舒展,但书院事务繁多又无薪水,为了争取官方支持时常降低身段四处求人,成事艰难,所以他依然得不到完全的满足。
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焦虑让他苦闷不堪,因而借寻花访艳、醉酒当歌来排遣。只是花国冶游也无法让他安适自我。此时的上海已被近代市场经济裹挟,正经历着剧烈的世俗化蜕变。士人阶层普遍陷入贫穷与边缘化的境地,绅商群体迅速上升为社会主流阶层。沪上青楼也高度商业化,由传统士大夫主导的性别权力结构与审美取向已成明日黄花,一掷千金却不知风流为何物的商贾富豪成了欢场新贵;才情俱秀、闲雅脱俗的名妓佳媛逐渐隐退,“金银气重、文字缘悭”的淫娃艳女比比皆是。
面对“情天之变态”,王韬唯有寄情于笔墨之间。他在《淞隐漫录》序言中自白道:“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由此观之,如果说王韬仿《板桥杂记》而作的《海陬冶游录》通过回忆开埠后上海老城厢中的名妓生活“抒发他对晚明理想化、浪漫化的追忆与怀旧”,因而指向的是“亘古以前”“千载以后”的时间性乌托邦;仿《聊斋志异》而作的《淞滨琐话》“于诸虫豸中别辟一世界,构为奇境幻遇,俾传于世”,因而指向的是“鬼狐仙佛、草木鸟兽”的非人类的乌托邦;那么,王韬的《漫游随录》在重组欧洲之行的记忆基础上塑造出英国这个“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的理想之邦以及理想的英国淑女形象,为自己建构了一个能慰藉心灵的共时而异在的情感世界,因而指向的是“遐陬绝峤,异域荒裔”的空间性乌托邦。
总之,置身于晚清近代化进程中的王韬同时在相互悖离的两个方向上遭遇着现代性:一方面,他是上海文化市场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不仅“开创了商业性消费型的市民文学”,而且收获了可观的稿酬回报与丰厚的文化资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与人格独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由传统文士向现代职业文人转变的先行者;另一方面,他作为在近代市场经济浪潮中落败的士人阶层的一员,面对沪上洋场社会的全面世俗化不由得兴起强烈的怀旧情怀与疏离情绪,继而在追忆晚明的秦淮风月、想象山林的花妖狐媚、寄思英国的异域风情中,搭建起了一个个多彩的情感乌托邦世界,并以此来抚慰他颠沛流离无处安放的灵魂。这种生命的张力兆示了王韬这类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型文化人的普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