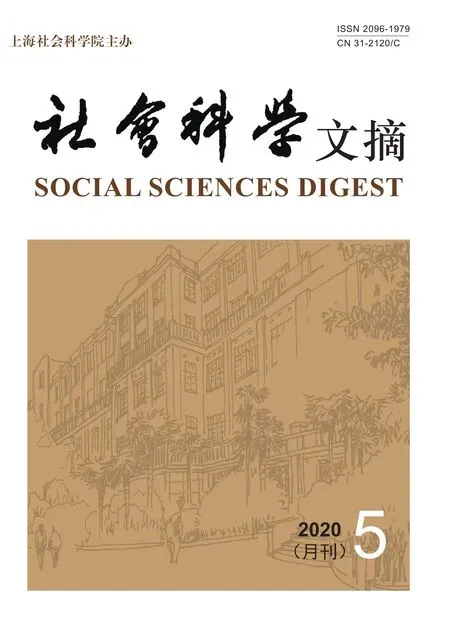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
2020-11-15彭伟步
文/彭伟步
美国智库历史悠久、数量众多、影响巨大,自其诞生伊始,便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思想生产、观点供给、决策参与和学术研究,是美国智库的生存价值基础,并成为美国政治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架构,不仅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为更加深入了解美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及其在全球的舆论生产,笔者于2019年10月15日至11月1日奔赴美国考察,通过与数个美国著名智库的对话和观察,了解美国智库如何形成和发挥影响力,怎样通过多种渠道和平台传播研究结论,牵引世界政治的走向等相关情况,以便为中国智库的学术研究、思想生产,以及开展公共外交,增强我国软实力和智库影响力提供一些借鉴。
国际政治变化推动美国智库发展
美国智库的发展与美国政治制度、国际形势以及国内的税收制度有密切关系。20世纪初,美国智库出现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繁荣。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开始在这一时期诞生,并帮助美国政府制定政策。第二次繁荣是在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战后美国政府急需发展经济,需要学者和研究机构为政府献计献策,提供决策依据,因而非常重视民间研究机构的意见。一大批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智库因此得到迅速发展,并因此获得社会与政府的大量资助,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要力量。
此后,60年代、80年代、90年代,美国智库因为世界冷战与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又实现了三次大发展,从而奠定了今天美国智库的繁荣与运作基础。因为美国智库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故“旋转门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智库研究人员与政府官员的角色不断轮换。政府与智库之间互动密切,一方面总统邀请智库研究人员担任高官,推行符合自己意愿的治国理念;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任职于政府,实践学术理论。因此,智库的“政治化”或者“半官方”的色彩非常浓郁。
在20世纪世界两大阵营冷战期间,为及时掌握世界各地发生的政治动态,预判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手段鼓励民间成立智库并开展相关研究,以便为美国政府应对国际政治变化提供智力支持。
在政府的鼓励下,美国智库规模庞大,研究人员数量惊人,例如布鲁金斯学会有400多名从事研究的专职人员,其发表的研究报告对社会和政府产生重大影响。2019年10月,笔者在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经济研究院等智库的访问期间,了解到美国法律规定美国国会在做出一些重大国际决策前须召开有智库与学者参与的听证会,以便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能够倾听到公众的呼声,使政策更符合民意,更加科学和合理,能够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权衡政策出台后美国利益的得失,避免出现重大政策失误。虽然政府在施政时可以依托行政团队,根据自己的决策意志出台治理社会的政策,但是过去的美国政府均形成了决策之前倾听智库声音,并根据智库的研究观点衡量决策得失的传统,因此,美国的社会制度以及听证会为智库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国际政治变化是推动美国智库发展的外部因素,在这个因素的强力作用下,美国智库从小到大,发展成今天影响美国政治和世界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甚至成为美国政府的“代理人”。研究报告的预判性与精准性显示了美国智库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时局的精准判断。智库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应对策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这就不难理解美国智库为历届政府所重视。
巨额资金为智库运作提供充足经费
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建设的需要,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美国税收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它保证了美国智库能够从外界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美国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很高,但是如果富人把遗产捐赠给学术研究机构,按照美国《国内税收法典》501(C)3条款,捐赠款项可以抵销部分甚至全部应缴税费,捐赠者不仅可以减少纳税,而且提高了社会美誉度。税收减免制度促使富人纷纷向智库捐款。因此美国智库每年都能得到外界的大量资金捐助,这些资金支撑了美国智库的研究,推动了智库的发展。
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美国大财团、大家族或者富有人士的资助,例如美国著名财团洛克菲勒对许多美国智库提供资助,要求智库就其关心的课题开展研究,并提交较为客观、独立的研究报告;二是社会普通人士的捐助,例如彼尔森经济研究院的资金来自大量社会普通人士的资助;三是政府项目资金的资助,政府通过委托或者公开竞标的方式,向社会公布一批亟待开展研究的项目,由各个智库通过竞标来承担研究工作。
在美国富有人士或家族的资助下,智库快速成长。截至2018年,美国智库数量有1872家,兰德公司(Rand Corp)、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城市研究院(The Urban Institution)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资金捐赠额度,都在美国排名前四。例如2018年兰德公司募集到3.27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募集到1.05亿美元的资金。除了美国社会向智库提供资助外,许多外国政府也向美国智库捐赠资金,亚特兰大顾问委员会(Atlantic Council)、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中东研究院(Middle East Institution)、斯廷森中心(Stimson Center)等均获得了外国政府的大量资金支持并从事相关研究。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对美国政府在国内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影响,甚至直接左右美国政府的决策。
美国智库的全球舆论生产
美国总统实施四年一次的竞选机制,这为许多从事智库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从政的机会。许多著名的智库研究人员因为多年从事美国政治和经济研究,对不同时期的美国公众的思想发展与政治诉求非常了解,能够触摸到美国公众的脉搏,了解不同时期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提出许多治理决策意见,而为许多参选总统的政治人士所吸纳,也因此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决策。如果研究报告得不到政府的采纳,智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政治游说,传播思想,一方面为美国公众提供不同于政府的观点,向政府施压;另一方面营造舆论,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攻击,以显示研究报告的价值,增强智库的影响力。例如布鲁金斯学会通过官方网站、自办电视台和电台、社交媒体、周刊、季报、年度报告、书籍等,委派专家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主动接触政府官方,从而产生立体化的舆论攻势,达到营销其观点的目的。由于其多年来已在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又背靠美国强大的军事、美元、媒体霸权,因此其研究报告很容易引起国际舆论的注意并得到西方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全球化舆论因此得以形成,对被研究的对象要么产生强大威慑力,要么创造改善其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氛围。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利益建立在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控制的基础上。美国智库为政府提供了众多研究报告,以维护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利益,左右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美国智库研究人员为了扩大其影响力,经常接受美国电视台、报纸、广播的采访,利用美国媒体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影响全球舆论,或借助官网、社交媒体、学术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演讲等方式发表其观点,实现其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目的。
例如1948年11月诞生的兰德公司利用其与美国军方的紧密关系,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国进行军事刺探和分析,准确预测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兰德公司对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均有非常高的预测水准。这些成功的预测使兰德公司声誉达到顶峰,一举奠定了其在美国政界与军界的地位,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的首席智囊机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Nicholas Lardy)在2018年底出版的《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终止》(The State Strikes Back-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势提出了许多观点,质疑中国“国进民退”的经济发展策略。这种观点引起许多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以及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的不满,因此纷纷支持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开放市场等政策,甚至施压中国改变政治制度。
在访问的过程中,笔者询问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米切尔·汉森(Michael Hansen)“美国精英是否弱化了对中国的支持?”他证实,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精英降低了对中国的热情与支持,而转向支持特朗普遏制中国的政策。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有可能构成对中美关系的持续性伤害,这值得我国相关部门重视。
与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在世界上形成强大的舆论相比,我国智库发表的研究报告,却鲜有西方媒体进行大幅报道。这虽然与西方国家的报道视角与偏见有关系,但也显示中国智库无论是研究水平,还是客观性和中立性均有待提升。此外,我国媒体在国际缺乏话语权,虽然对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智库报告进行大篇幅报道,但是由于影响力远不及西方媒体,因此也就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强大的舆论,从而帮助我国政府阐述外交政策、维护我国的利益。
美国智库的知识生产倾向与职业操守缺失
美国智库的运作离不开外界大量资金的支持,因此其学术与政策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研究基调、领域与课题多少存在一定的倾向性。这就导致美国智库在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以及公共外交等方面存在缺陷。
据笔者了解,几乎所有的智库都在官方网站上列明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捐赠者的名单,再三强调其研究工作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言下之意,他们的研究工作不受捐助人的意志所影响,即使资金来自政府或特定的基金会,也会基于客观和独立判断的智库研究工作原则,向外界提交客观的研究报告,为政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决策参考意见。
然而,笔者发现,美国智库虽然努力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独立性,但是仍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而使智库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使智库的公共外交偏好受到公众的质疑。例如中东财团和政府对美国智库的资助最多,他们是美国智库的金主,也是支撑美国智库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2018年10月2日,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却从此失踪。沙特涉嫌谋杀卡舒吉的行为在国际上受到强烈关注,但是美国智库鲜有对此事的激烈反应和批评性研究报告,而特朗普政府也对此事大事化小,淡化其负面影响。这就说明虽然美国智库再三向外界强调其运作的独立性,但是从此事来看,仍然无法避免公众对其独立性与客观性的疑问、对智库职业操守的怀疑。这背后反映了中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明显影响了智库的研究。
美国媒体、美元、军队是维护美国利益的三大支柱。美国媒体独霸天下,再加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是一个能够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显著影响力的国家。因此,超级实力使美国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发世界政治海啸,造成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动和重组。当美国政府官员与智库高级研究员的观点相契合时,政府便会引用智库的报告结论,制定外交政策,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进行施压,甚至颠覆其政权。美国智库由此实现研究价值的最大化,扩大了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使受到研究报告影响的国家不得不调整政策。一些国家不得不给予智库更多的资金支持,希望智库的研究报告淡化其对美国的威胁,形成的结论对自身更有利。例如,除了中东是美国智库最大的资金来源外,以色列也给予一些亲犹太人的智库巨额的资助,以帮助其获得美国政府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支持,以及促使美国政府出台更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
美国智库除了发表研究报告影响美国政府政策外,还通过智库的游说活动,帮助资金资助者获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有时,为了向特定的对象索取捐赠资金,一些智库还故意出台不利该国的研究报告,以此要挟该国向其投资。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智库当初设立的初衷和中立原则,因此受到公众的强烈质疑。
美国智库是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美国智库通过社交媒体、传统媒体等发布消息,出版研究报告,邀请政府官员宣讲相关政策等方式,加强与公众的互动,在全世界制造舆论,达到影响政府决策与国际政治的目的,进而扩大智库的影响与声望,维护美国利益,但也因为美国智库具有利用媒体制造全球舆论的能力,一些智库为制造轰动效应,夸大研究结论,欺压其他国家,严重误导公众,对被批评的个人、组织与国家极不公平。
结论
特朗普上台后,改变了美国智库的游戏规则,即其在重大决策时减少对美国智库的智力依赖,也不积极吸纳智库的研究结论,并减少了政府对美国智库的资助,甚至限制游说集团的活动,导致一些美国智库缺乏资金来源,也导致“旋转门现象”面临失效的困境,但总体来说,美国智库仍然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国际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智库已经深入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社会运作和国际关系产生显著影响,已与美国政治融为一体,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个人意愿而消失。
智库是公共研究机构,其价值就在于其研究报告的科学性、客观性与预判性。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左右美国和世界政治的发展,除了其具备较高的研究水准外,还与美国媒体、美国政府影响力有密切关系。当前,我国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压,如何更好地促进美国公众对中国走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避免误判,增进了解,携手合作,一方面,我国政府和企业要适当向美国智库提供研究经费,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瞭望中美关系的发展,通过智库直接或间接的游说工作,改善与美国政府与工商界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国智库要加强与美国智库的合作,成立中美联合智库,帮助两国政府和公众相互了解,促进合作,化解分歧。我国学者要积极加入美国智库,帮助美国智库研究者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使其研究报告更加科学、客观,规划中美关系的发展,实现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
智库是集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的机构,能够提供政策导向、分析和咨询服务,使决策者和公众可以就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明智决定。加快发展我国智库,提升智库研究的影响力,是促进我国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在全球的舆论影响力,提升智库在全球地位的主要渠道。我国目前面临许多国内外亟须解决的问题,更需要智库的参与,以帮助政府前瞻性地规划和制定国际政治政策,增强我国应对国际政治变化的能力,谋划可持续的国际政治发展战略,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