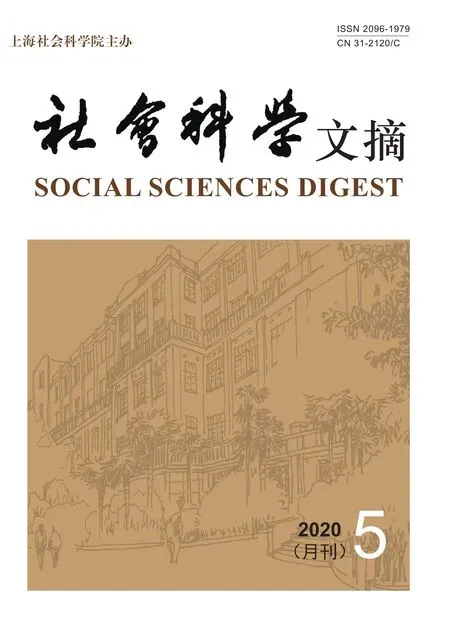四部之学的转换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
2020-11-15常方舟
文/常方舟
在近代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之下,西学的分科观念对传统学术和知识的分类方式产生了新的冲击和挑战,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悄然发生转换。旧有的词章之学因应西学知识分类体系的冲击而发生异变,成为近代文章学理论转型的重要前提。在清末学制设计中,文章流别课程的设置与本土文学史的诞生息息相关。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汲取了传统文章学体用兼论的要素,并在向现代文学学科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与西学知识型的对接,形塑了本土早期文学史的书写范式。
四部之学与四部之文的分合升降:从《昭明文选》到《文史通义》
汉魏六朝渐启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分,展现出文体学的自觉意识。刘勰《文心雕龙·诸子》虽得出“经子异流”的结论,但其畅论诸子、史传,仍未脱离“论文叙笔”的基本框架。任昉《文章缘起》以文章源出六经之论为本。《颜氏家训》谓:“夫文章者,源出五经。”文本于经的思想深入人心,早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型以前,经传在传统文论中的导源性地位业已确立,且鲜有动摇。
而史、子、集部与历代文章学理论交互的情况以及三者之间的升降排序则更为错综复杂。“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刘歆作《七略》,子部始自树立,且其序位仅次于经部。阮孝绪《七录》折衷众录,将《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更名为《经典录》《子兵录》《文集录》,新增《纪传录》,仅次于《经典录》,大致对应后世经、史、子、集的内容秩序也基本落定。相较于类目名称得以沿袭的经典、诸子二编而言,其改《文翰志》为《文集录》的理由是“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至此,作为文词之总名的集部也呼之欲出。《隋书·经籍志》最终成为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目录分类确立的滥觞,该序次也沿用终始。
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将选文标准限定为“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这一取法原则显示出“去笔化”的鲜明倾向,凸显了藻绘文章的纯粹价值,在尊经崇史的时代语境之中实属特出之论,为经、史、子部文本能否被视为文章的合理性质疑埋下了意义深远的伏笔。而钟嵘《诗品》对“羌无故实”“讵出经史”的诗歌批评也颇有微词,对诗文未分阶段诗歌自是一家的独立地位有所回护。
尽管经、史、子部与文论的交互属性长时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此三者作为文章体制取法的根柢之学始终有理论脉络可循,并在从学术流别向文章流别腾挪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差序化格局。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明确将经、史、子、集在词章之学中的序列问题推到时代的前台。《文史通义》在尊经的前提下抛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虽非首创显豁之论,却也为从历史角度辨析文章学的学术源流奠定了方法论范式:
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
另据张之洞《书目答问》集部别集类条下注,其于清朝文人别集“除诗文最著数家外”,仅取“其说理纪事考证经史者”,其《輶轩语》也明确阐发读集不能工文的观点:“近代文集,鄙者无论,即佳者少看数部亦无妨。多读经、子、史,乃能工文;但读集,不能工文也。”张之洞是晚清癸卯学制的制定者,推定这一表述与《奏定大学堂章程》中的“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似未为过。而早在清末新式学堂大量兴起之前,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曾提出在各省设立面向二十五岁以下人士的学堂,规拟课程内容之一为“诵经史子及国朝掌故诸书”,也恰好将集部摒于所学之外。
由于清代向慕实学的治学风气使然,章学诚《文史通义》从史本位出发爬梳历代文章流别,其“子史衰而文集盛”的观念成为近代文章流别论的重要理论渊源,而癸卯学制的纲领性意见也在清末民初词章之学的学科建制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进入近代文章流别论并发挥作用的历史语境和理论传统。
近代文章流别论的生成:经、史、子、集之体与情、事、理之用
清末《奏定大学堂章程》设有历代文章流别一科,明告此科教员可仿照日人文学史著述撰成讲义,为文章流别与文学史的合流开启了方便法门。诸如“若六经之文,非可以文论者”这般,将儒家经典看作文章是对经部典籍和尊经传统“轻渎”的传统观念不再壁垒森严,经、史、子、集四部文本尽皆被纳入文章的范畴。其中,章学诚的文章流别论及其对四部之文分化迁转的叙述逻辑,成为清季民国四部之文“辨体”的理论起点。
如马絅章《效学楼述文内篇》“论古来文章流别”一节所云:“经、史、子、集四部,质言之,经,载道者也,史,记事者也,子以谈理为宗,集以摛词制胜者也……子家各有宗门,而其典章制度之属,多与经史出入;惟文集之名,出现稍晚,其体最裂。”这与章氏之论相近。近代湖北罗田学人王葆心所撰《古文辞通义》书名即步趋章学诚《文史通义》,书中全篇引证了章学诚有关经、史、子、集四部文章的流别叙事,作为撰述宗旨和取法对象。来裕恂《汉文典》把文章体裁分为“撰著之文”与“集录之文”,前者指“君师道判,政教权分”以后诸子百家的著述,后者则是道裂学散之后的产物,这一论述逻辑也和章学诚对经、子、集三者演化关系的看法完全一致。
历代传统文章学不乏关于文章体用关系的表述。王世贞曾以理、事、词三者隐括历朝文学。魏禧提出文章之用不外乎明理、适事。阳湖派恽敬欲以子部救正文集之失,并用言事、言理、言情区分文词的效用。桐城派刘大櫆《论文偶记》也隐约将明理、寓情之文与具体的子、史文章进行勾连。
尽管传统文章体用论对文章表情、言事、明理的作用有所认识,近代文章学著述却首次且集中地出现了大量以经、史、子、集四部的分体学说来对应情、事、理三种文章作用的表述。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提出:“经义分自经类,在著述门,为说理;记载分自史类,在记载门,为记事;论辨分自子,其类亦统在著述之说理。告语一门亦言经,左史之遗,推合其类应并出自经史。三者之外统归词章,词章则抒情一类之汇。而情、事、理三者之流别明矣。”桐城殿军姚永朴《国文学》云:“古今著作,不外经、史、子、集四类,约而言之,其体裁惟子与史而已。盖子有二派,老、庄、孟、荀、管、墨诸家,皆说理者也,屈、宋则述情者也,左邱明、司马迁、班固以下诸史,则叙事者也。”这一观点在其之后所撰《文学研究法》中得到了悉数保留。高步瀛《文章源流》同样也以理、事、情三者分别对接子、史、集三部。刘咸炘《文学述林》将文章归为事、理、情三者,并将其与史、子、集部文字作大体对应,惟经部文字未涉其中:“事则叙述(描述在内),理则论辨(解释并入),情则抒写,方法异而性殊,是为定体。表之以名:叙事者谓之传或记等,史部所容也;论理者谓之论或辨等,子部所容也;抒情者谓之诗或赋等,古之集部所容也。”他阐明事、理、情是文章撰写的目的所在,为文之用,叙述(描写)、论辩(解释)、抒写则是文章撰写的具体方法,为文之体,传记、论辩、诗赋等文类名称,为文之名。
近代文章流别论将经、史、子、集和情、事、理三者进行对接的做法及对后者阐发的深入程度皆为过去所不及,这与近代域外文章学思想的传入有关。20世纪初刊载于《新民丛报》上的马君武《法兰西文学说例》,提出散文分为五种,分别是记事、辩论、学说、戏剧和书牍。这一观点正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所化用,后者遂以记事、辩论和书牍分别对应记载门、著述门和告语门。又比如,来裕恂《汉文典》将文体分为叙记篇、议论篇、辞令篇,叙记篇和议论篇的篇头小序分别采纳了日人儿岛献吉郎《续汉文典》“叙记之文”和“议论之文”的提法,而辞令篇则包括诏令、奏议等文类,与《续汉文典》文章辨体观一致。而集中出现以情、事、理三种统系统摄四部文章的现象,还隐约延伸到了日后经过东洋改造而间接传入国内的“知、情、意”三分法,体现了近代文章学丰富多元的理论空间。
四部余论:纯杂文学观念的引介与近代文章学的骈散异趣
清代以前,经部文字亦鲜少被选入诗文总集,而史部和子部文本被纳入文章选辑范围内却并不少见。姚鼐《古文辞类纂》未将史、子文字选入集中,但据《经史百家杂钞序例》可知,曾国藩明确表示将姚氏不录的六经、史传也采入古文辞的选本之中,且冠以“经史百家杂钞”之名。对此,朱东润先生指出,曾国藩对古文辞内涵的界定最为宽泛:“曾氏之言古文,既包经史百家言之,而旁通之于骈文,故古文之领地,至是遂最为庞大。”这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范围。经、史、子不仅是文章取法的源头,其本身也可被视作文章之一部。对经、史、子、集四部文本所具有的“文学合法性”产生分歧的理论出发点,既与外来文学观念的引介和渗透有关,也与骈散异趣的近代文章学派分理念有关。
清末西方文学进化论和纯文学观念的引入,带来了文学批评方法的更新和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演进,对经、史、子、集四部之文的再认识产生了偌大的影响。朱自清曾指出,新兴的语体现代文学“大部分是受了外国的影响,就是依据着种种外国的标准”,但在文学传统里也能找到它的因子:“‘纯文学’‘杂文学’是日本的名词,大约从De Quincey的‘力的文学’与‘知的文学’而来,前者的作用在‘感’,后者的作用在‘教’。”在破除杂文学体系、建立纯文学观念的进程中,经、史、子、集部文本的“文学性”也迎来了新的验示。
刘咸炘曾指出:“最近,人又不取章说(按:指章太炎),而专用西说,以抒情感人、有艺术者为主,诗歌、剧曲、小说为纯文学,史传、论文为杂文学。”根据他的观点,纯文学将文章格调设为阑入文本的标准,“正与《七略》以后齐梁以前之见相同”。可以见出,由于纯文学设立了以作品美学价值为转移的准入标准,集部反而成为优先同时也是最易被认定为具有纯文学性质的文本,而隶属于经、史、子部的文本却往往被划入杂文学的范畴。这样的处置既延续了清代中后期文笔之分的理论重提,也暗含了近代选学和古文两大阵营文章学思想的对峙。
阮元以《文选》录文原则为准绳,主张辞章理应区别于经、子、史:“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阮元也指出,古文家的阵地往往天然地集中在经、史、子三部,与《文选》的路数截然不同:“昭明选例以沈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梁章钜《退庵随笔》援引阮元《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力排众议,扬骈抑散:“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以为烦,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他对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历代诗文选本阑入经史文字也颇有微词。
另一方面,姑且不论古文先驱韩柳自述为文旁搜远绍,于经史子无所不取,仅就清代桐城派而言,桐城派先驱之一方以智曾论取材次第云:“昔人谓胸中先有六经、《语》《孟》,然后读前史。史既治,则读诸子,是古人治心积学之方,往往有叙有要。”他明确将经史子三者视为文章薪火之要素。方苞奉敕选编《钦定四书文》有云:“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对采撷经史入文予以表彰。吴德旋直接将史书视作文章之一部:“《史记》、两《汉》《三国》《五代史》皆事与文并美者;其余诸史,备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观也。”
清代骈文和古文之间本就存在骈散异趣的分歧,但两者的矛盾在清末民初的文章学语境中显得愈加突出,并鲜明地体现在四部文章与纯杂文学观的呼应关系之中。刘师培凸显选学的文学性:“诚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经、史、子被归入古文的界域,集部的特殊性得到彰显,骈文地位亦得以抬升。郭象升《五朝古文类案叙例》认为选辑一法为集部所独有,进而提出骈文方是承载集部独立价值的唯一载体:“所谓骈文者,义固绝远于经史诸子,而亦以此故,有独立一部之精神,而散不尽然。”
清末的文章流别论逐渐为文学史的书写所替代,其侧重点也从四部文章流变和体用改换到了具有文艺美学价值的经典作品赏析:“《奏定大学堂章程》与《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巨大差别,不只在于突出文学课程的设置,更在于以西式的‘文学史’取代传统的‘文章流别’。”在文学史的演进之中,文学观念自身的演进无疑发挥了极大的催化作用:“近代作家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对文学本体的认同、文学审美特性的论述,都有助于纯文学观念的确立。”纯文学、纯文艺观念的确立,充分肯定了集部的独立价值和地位,也为古代文学史的去取标准设置了新的难题。
结语
经、史、子、集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型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不断遭遇祛魅,势必为新的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所代替。四部之学在近代文章流别论中的演化和新变,折射出过渡时代文章观念和文学概念的变动不居。与此同时,当前本土文学史的书写困境仍未得抒解,与“文学性”更强的诗词歌赋相比,体量庞大的古代文章作品应以何种标准、何种方式、何种比重采入文学史中,始终是困扰文史研究者的难题。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主张回归《文选》传统,将作品有无“沉思翰藻”作为选入散文文学史的基准:“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这部散文史的文体范围,也就不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因为,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家写这类文章,其‘沉思’‘翰藻’,是不减于抒情写景的。”回归近代文章学的历史语境,抉发四部之学与近代文章流别论生成的关系,或许能够对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有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