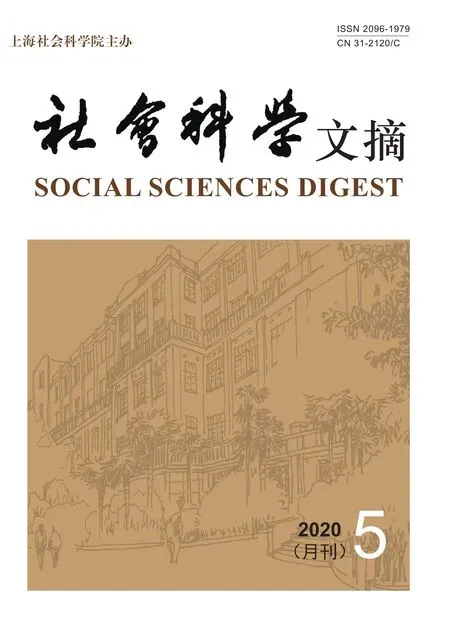乡村社会的另一种“凸显”
——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思考
2020-11-15李红艳冉学平
文/李红艳 冉学平
自圣·奥古斯丁撰写《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一书以来,人们始终在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上帝在世人面前如何显圣的问题。彼得斯(2003)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这一问题并指出:“奥古斯丁对上帝和人交流的描绘,预示着现代的传播,也预示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想象出一个不在场的实体,让一个时间、空间和程度上相距遥远的受众觉得,这个实体的存在是真实可信的。”倘若把该问题置于乡村短视频中加以检视,我们会发现,一定程度上该视角为理解乡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解释:透过城乡边界的消解、时空边界的跨越,使乡村现实原本的“缺场”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可视化、具象化,进而达致一种新的乡村社会的呈现形式。西奥多·罗斯扎克(1994)强调这种“新奇玩艺儿”寄托了人们对幸福、希望和尽善尽美的想象,也象征着流行及进步。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作为新的信息呈现形式或手段的短视频中,乡村社会是如何“凸显”出来的?
本文选择抖音短视频作为研究乡村社会的切入点,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作为短视频行业的翘楚,截至2019年1月,抖音在国内日活跃用户突破2.5亿,月活跃用户突破5亿。这种以“短、快、新”为特点且极具新媒介代表性的短视频精准契合了用户需求,无论是作为生活工具对乡村人群日常的影响,还是作为传播手段对乡村社会未来的作用,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另一方面,抖音短视频在当下的迅猛发展被视作一种乡村自主表达、社会身份认同、乡村亚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之一,毋庸置疑,由这种工具所引发的乡村传播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转向,也需要我们作进一步探究。
笔者借助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或称“四元律”),作如下解释:一方面,不管是“提升”还是“过时”,短视频仅是在新媒介语境下的一种表述,其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归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最终回归到人的尺度的最高准则;另一方面,“再现”或“逆转”在媒介环境学的境遇里体现必然的新科学性,可以将其理解为凸显整体性的去媒人界面较为妥当,进而对来自后人类主义的挑战作出一脉回应。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分别以“人的尺度”和“去媒人界面”进行叙事,由此来呈现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以探究在技术层面上,乡村社会在新技术时代的新特点。
虚拟现实论与经验现实论之间的“媒介人”
亚里士多德把手描述为工具或武器的洞见,使人们认识到手还可以被视为“多种工具组合”或者“工具之工具”的问题(苗力田,1997)。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强调“钱、商品、土地和机器”转换或延伸于人类“基本生产力”或“劳力”(莱文森,2017)。这种思想还可以追溯到卡普那里。卡普围绕技术哲学这一核心范畴提出了“器官投影论”,即把人体器官看成是一切人造机器或工具的投影原型,而器官投影的程度取决于机器或工具与人体本质性之间的勾连程度(王楠等,2005)。弗洛伊德则认为工具通过延伸人的生理或心理,消除了人自身能力方面的限制,如望远镜克服了距离,显微镜克服了视力,照相机克服了瞬间,留声机克服了听觉(莱文森,2017)。波兹曼(2007)指出人类文明演进历经工具使用、技术统治与技术垄断三个阶段,这些阶段都肇始于工具使用,以谋求解决人的进化与发展问题。这些观点阐释了人与工具之间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某些时候是通过某种“扭曲”方式才得以实现的。实际上,这也正是本文强调对抖音短视频与乡村人群之间关系进行讨论的意义所在。
卡尔·雅斯贝斯(1989)指出媒介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人类自身的存在,使得人类免于匮乏,令环境具有诸事取决于自身的形式。在他看来,媒介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类自身。就这个意义而言,雅斯贝斯的焦点从来都不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媒介技术上,而在于人的尺度这一平面上。这也可以看作是人类对媒介技术的回应,由此勾勒出人的最大包容和统一目标。麦克卢汉(2011)认为人类在机械时代完成了身体的空间延伸,在电力时代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了延伸,并正在逼近技术模拟意识的最后阶段。他试图给媒介技术披上了一件“人的尺度”的外衣,并将它与新兴社区、有机平衡、社会和谐勾连起来。这一构想试图将媒介技术奉为社会变革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以及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然而,这一根植于人的主张也揭示出局限性,即人在理解他自身的能力方面存在逻辑上的局限,因为人永远无法离开自身而检视自身的运作,尤其是在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虚拟现实论与经验现实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抖音短视频一方面竭力强调虚拟社交、网络认同、电子匿名的行为,另一方面短视频所呈现的行为又与经验现实社会中呼唤提高向善的能力格格不入。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特别强调,上述虚拟现实的讨论与经验现实讨论之间的关系绝非断然两分,更非简单紧张或对抗。本文讨论的最终目的也并不在于直接回答二者之间的紧张问题,而在于试图揭示隐含于这些乡村社会问题背后的内在逻辑,继而为人们提供以下几方面思考:
其一,人类在认识抖音短视频的影响方面存在着理性限度,这是因为人无法摆脱操纵与影响自身的技术。不争的事实是,后真相时代乡村社会的“拇指运动”表明:冗余化的信息垃圾、碎片化的信息盲点、失忆化的信息黑洞、割裂化的信息茧房、伪装化的信息交流、商业化的信息植入极易导致乡村主体浅层记忆,进而失去追求真善美的主体理性。一方面,从外部性来看,只有通过政治权力的介入,通过遏制短视频技术扩张主义的潜在异化,通过在技术控制范围之外创造新的讨论与参与的可能路径,这种乡村社会偏移才能够得以控制、修正和转变。另一方面,就乡村人群自身来说,如果他们想从抖音短视频那里提取任何支撑乡村生命本体的东西,就必须自己去看、去触摸、去感受、去把玩、去歌唱、去舞蹈、去交流。如果他们自己的灵魂是单一的,那么新技术只能够使他们更加单一。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是消极而无能为力的,那么将使他们变得更加孱弱(芒福德,2009)。
其二,在抖音短视频从拍摄到观看,再到评论、点赞乃至分享的过程中,乡村社会被集体化身为人们所想象的虚拟世界,他们患梦游症似地游离于其中,幻想网络大众可以掌控和征服那个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网上”乡村社会。这一过程最显见于当下流行的“乡村网红”现象,它似乎确立起乡村社会正处在一个“人人是明星的时代”或“以人人是明星为轴心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为乡村人群的深度参与诉求。深度参与“似乎”是抖音短视频的核心景观之一,或者说,抖音短视频的重要任务之一“似乎”在于推动乡村人群的深度参与。然而,由于技术鸿沟、城乡区隔、文化差异的缘故(勒纳,1958),乡村人群的深度参与并不会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开来,这种参与也不会将乡村文明从技术至上的倾向中“解脱”出来,更不可能成为区域、种族、性别之间的公平行动路径。
其三,抖音短视频的极大诱惑还在于它向人们提供了多个虚拟身份,进而替代唯一现实身份,这似乎为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消费的场所”。这些身份通过元叙事的方式记录乡村生活,构建起以乡村文化认同为中心的虚拟社交空间,隐喻着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然而,技术延伸及其带来的文化重置只残留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和叙事,乡村文化已经不再完整(凯瑞,2005)。事实上,人们透过短视频从乡村文化那里所获得的意义或快感,并不会改变其在业已固化的乡村社会中被深描的位置,这也使得研究者从一开始便看穿了这层面纱所遮盖的区域、文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真相,作为一种与主流文化对照的亚文化,乡村文化最终无法逃脱被收编的命运,或被都市话语建构成娱乐对象,又或被商业话语解构(刘娜,2018)。就这种关于乡村文化最终归宿的论断而言,它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的是对都市文化的一种拼贴式、戏仿式、反讽式的仪式反抗,实质上这也是对更大范围“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罗钢等,2000)。
去媒人界面的“新社会”
当本文把论辩的焦点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于乡村短视频,透过对人与媒介之间关系的重述与建构的时候,如下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一是任何关于人的尺度的命题必须考虑到媒介技术进化的逆向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给出涉及本体论问题的回应;二是这种回应反过来对人的尺度的命题提出了严肃的挑战,继而达致一种去媒人界面下人类物种本身的哲学反省与后人类主义发展的本体转向。需要追问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去媒人界面?它将会把人们引向何方?海姆(2000)把这一界面描述为一个“接触点”,即“神秘的、非物质的点,电子信号在此成了信息”。这意味着“人类正被线连起来。反过来说,技术合并了人类”。从某种程度上,海姆这种带有反边疆理论的思想可被视为重构社会秩序与凝聚社会力量的源泉,它指向即将临近的未来,这或许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
进一步就去媒人界面而论,它表现为后人类主义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及主体的建构等问题,强调去人形中心化,即置人与物于同等的本体状态(冉聃等,2012)。梅洛·庞蒂认为这种结合乃是一种“自我—他人—物”的体系的重构,也是一种经验得以在科学中构成的“现象场”的重构(贾撒诺夫等,2004)。这种重构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共同演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统一。拉图尔(1999)称这个去媒人界面的世界为“集体”,亦即“人与非人”在一个整体中的属性交换,在这个“集体”中,科学进步不再是分裂式、纯化式的,而是杂合式、转译式的(吴飞,2018)。这种去媒人界面的叙事转向在乡村社会那里既产生了时间、空间、程度、变迁等新的议题,也产生了符号、结构、性质、权力等新的思考对象。
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短视频可被视作虚拟全景视界延伸人的视觉、立体空间音效延伸人的听觉、隔空动作触屏延伸人的触觉。但这只是乡村社会表征的一个方面,乡村社会表征的另一方面是:乡村娱乐延伸人的心智,乡村民俗延伸人的心理,游子乡愁延伸人的情绪,乡村特产延伸人的情感。透过对去媒人界面的讨论,还可以发现,在最坏的时候,它产生的是一个由冗余信息累积而成的“信息剩余场”,在最好的时候,它营造了一种良好的信息与思想交流的环境,进而解放人类(胡泳,2008)。有鉴于此,一种立基于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未来走向渐趋明朗,亦即抖音短视频不是在创造一种乡村社会的“新未来”,而是让乡村人群参与某种控制或被控制仪式。毫无疑问,这种未来绝对不是一个注定到来的开放空间,也不是真正建立在人的理性需求之上的视听空间,而是建立在技术控制性之上的对抗空间,可以由此延展出如下的问题:
一方面,抖音短视频被移植到人们所向往的田园乡村,试图通过对乡村景观进行选择性的呈现,而使自己与那种从一个非历史观出发认识并建构乡村社会的观念保持一致,这对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一体化带来挑战。这一选择性呈现与豪威尔关于“使城市和乡村从独享走向共享”的设想,或者与凯瑞对于“地方联盟主义”的构想相去甚远(凯瑞,2005)。事实上,抖音短视频不论是竭力表现特定乡村社会的贫穷、怪诞、愚昧、庸俗,或是努力诉诸休闲、搞笑、时尚、猎奇,还是建构、标签乡土记忆及田园牧歌式的身份,都是不可欲的。换言之,倘若要达致城乡之间的整合或统一,那么关键就在于不能把乡村社会置于一个单一的场域而与城市社会分割,因为这只能加剧二者之间的区隔甚至对抗。一如波兹曼(2004)在回答莫尔关于“上帝创造了什么”的问题时所述,涌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的社区,或者说,是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
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抖音短视频扩增了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避免狭隘、琐碎和异化的个性。乡村公共领域的审美意味正逐渐被抖音短视频极力呈现的浅薄、空洞、粗鄙、噱头、戏谑的审丑个性及功利主张所替代,进而导致真正参与乡村公共领域话语的消逝。进一步说,当乡村政治、文化、教育等公共领域皆以娱乐方式呈现,并异化为一种沉浸于快感而缺乏自觉的共同景观的时候,这就形成了他们追求社会认同的两大歧路:自恋与从众(胡泳,2008)。一方面,抖音短视频极力打造的技术专家模式为乡村社会“自恋”提供新路径,诸如星空妆、控雨术、双屏合拍、原声片段模仿等道具,以及猫脸、兔耳朵等特效与花样搞怪场景,客观而论,这些路径仅是现有乡村娱乐与休闲工业的扩展。另一方面,抖音短视频所呈现出来的“从众”效应,或许仅仅是乡村人群被边缘化后被迫提出的一种挑战都市话语的边界,他们试图以新的身份进入其所向往的城市公共空间。然而,这种“从众”是否代表着乡村社会的主流话语?它又能否为都市话语所接受?或者说,多大程度上被接受?接受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观察。
结语
综上,本文立基于抖音短视频的思考,乃建立在以人与媒介之间关系为基本设定的“人的尺度”与“去媒人界面”的论争中。这种思考表现在:一方面,通过对“人的尺度”的追溯与阐释,揭示了乡村社会存在的虚拟现实论与经验现实论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回应了抖音短视频带给乡村社会的新挑战;另一方面,透过对“去媒人界面”的讨论与检视,继而达致一种乡村社会与来自后人类主义思想的一脉关联性的认识论转向、“新社会”反省及新问题思考。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绝对不能简单地把抖音短视频解释成单一的交流工具,也同样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最终立基于人的尺度的生活工具,还要求我们在研究去媒人界面的时候,对抖音短视频与乡村社会之间彼此勾连且更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追究:一是抖音短视频在多大程度上有助益乡村社会治理,在现有国情条件下,它给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治理权利、边界和交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二是抖音短视频在何种程度上提升或减少了乡村社会向善的能力,倘若它提升了人们天性中与善的联系,那么具体哪一部分的善将会被它释放或者扩散,反之,如果它减少了,那么具体哪一部分的善将会被它压抑或者破坏呢?在当下技术创新如日中天的背后,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