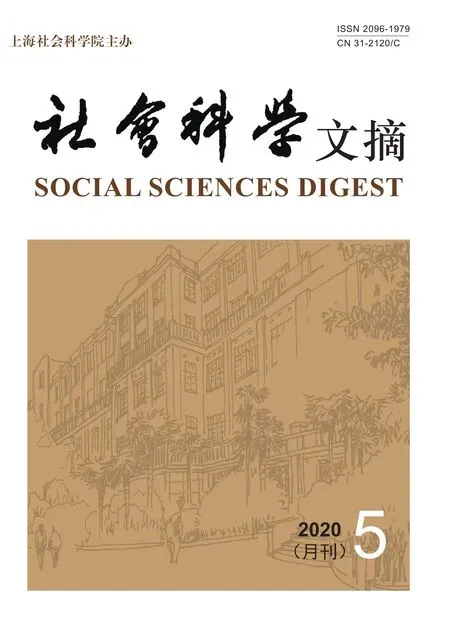最好政体与最坏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及其政体观再评
2020-11-15俞可平
文/俞可平
亚里士多德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他的研究涉及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科,并对这些学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亚里士多德也是对全人类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影响最深刻和广泛的学者之一。他的经济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说至今依然是人类知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众多著作之一,然而却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亚里士多德自己多次明确地说,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更加重要,它超越于其他学科,是“主要科学”。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把政治学当作“主要的学科”“最高的科学”和“最权威的科学”,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政治学事关人类“最高的善”,即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有助于人们寻找和发现最适合于人类“优良生活”和“幸福生活”的优良政体。因而,关于政体的分类和评析,是其《政治学》一书的重要内容,也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这门基础学科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最坏的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最为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是其研究城邦政体的根本目的。长期以来的流行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但在晚近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为,共和民主才是其追求的理想政体。本文将结合国际学术界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其政体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从而确定究竟什么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最佳政体和最劣政体。
城邦与政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类的社会组织,但它不是一般的社会团体,而是人们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城邦的首要特征是其政治性,并以此而与其他社会团体区分开来。作为政治共同体,城邦在所有社会团体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性质,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立城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城邦整体的公共利益,即城邦的“优良生活”。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公共利益视为“善业”(the good),并且是所有善业中的“至善”。与城邦的“至善”这一终极目的而言,其他所有城邦组织和城邦活动,都不过只是手段和工具而已。
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的政治统治方式称为政制,并认为政制是城邦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城邦相互区别的实质性标志。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以“公民政治权利的分配体系”来界定城邦的政治制度,并且把这种政制视为城邦的本质,由此,政制或政体便成了其全部政治学分析的重点所在。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统治权”是区分政体类型的根本所在,“政体(宪法)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其中尤其着重于政治所由以决定的‘最高治权’的组织”。因而,他以城邦最高统治权执掌者的数量和性质为主要标准,来确定政体的种类。同时,他把公共利益当作区分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并以是否增进城邦公共利益为依归,来确定政体的优劣和变异。由此,亚里士多德便发展起了其卓越的政体学说。
按照城邦最高政治权力的归属,亚里士多德将所有政体分为三个基本类别。最高权力属于君主一人的政体,即是君主制;最高权力属于少数政治精英的政体,即是贵族制;最高权力为多数公民的,即为共和制。亚里士多德进而指出,政治统治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优先追求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一是优先追求城邦的公共利益。如果上述三种政体形式,都能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依归,那么就都是常规的优良政体。相反,如果它们不是以追求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而是以追求统治者自身的私人利益为重,那么,这三种政体就会发生畸变,趋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变态政体。君主制的变异是暴君制或僭主制,贵族制的变异是寡头制,共和制的变异是平民制(又译“民主制”,Democracy)。换言之,正如阿奎那所说,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将所有政体分为六个类型,其中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是常规政体,而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则是变异政体。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最优的政体形式,防止最坏的政治制度。为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对各种政体的优劣进行了反复的比较,尤其是对最好的政体和最坏的政体进行了重点分析。
幸福生活与理想政体
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政体和理想政体的大量论述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他所孜孜追求的最佳政体的三个必备要素。其一,最好的政体必须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统治者要“才德出众”,大家都对他们的统治心悦诚服。其二,最好的政体必须有最好的治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优良的政体”几乎直接等同于“最优良的治理”。其三,最重要的是,最优良的政体一定要使全体公民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建立城邦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们过上一种幸福和善良的生活。如果一种政体不能最大限度地让人们幸福,那就根本谈不上是优良的政体。
在他自己确立的君主、贵族和共和三种基本政体中,究竟何种政体是最优良的理想政体,亚里士多德似乎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仅如此,他的观点看上去还常常自相矛盾。根据埃里克·沃格林的考证,在亚里士多德当时的语境中,“最好的”不只拥有一种含义。它可以意指“最强大的”“最健康的”“最稳定的”“作为实现沉思生活的环境最适合的”“最充分地将不能实现好生活的人置于控制之中的”“城邦的成熟”或“城邦本质实现中的最高点”。照此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好的政体,实际上就是根据各个城邦的具体条件最适合的政治制度。只要城邦采用的政体最适合于增进整体的公共利益,这种政体便是最好的制度。换言之,除了寻求统治者私人利益的三种变态政体外,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都可以是最好的政体,都符合正义的原则。
仔细分析亚里士多德关于优良政体的各种论述,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心目中,共和政体或立宪民主制是最好的理想政治制度。亚里士多德确实明确说,君主制和贵族制是最好的政制,但在实际的举证中,他几乎没有把任何现实中出现过的君主制和贵族制当作其优良政体的范例。相反,他最赞赏的政体几乎都包含有共和民主的要素;他最赞赏的政治家是梭伦和伯里克利。
亚里士多德推崇共和民主政治主要有四个理由。其一,任何优良政体最终都会发生变异,而在所有的变异政体中,共和政体的变异相对说来危害最小。他反复说,在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平民政治这三种变异政体中,“平民政体是三者中最可容忍的变态政体”。其二,共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统治权由公民轮流执掌,这最有利于城邦的政治稳定。他公开批评苏格拉底倡导的世袭君主制,杜绝了公民的轮流执政,必然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其三,民主政治的权力基础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掌权有利于城邦的长治久安。最后,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公民对城邦承担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城邦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传统的主流观点一般都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是君主制或贵族制。例如,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学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尽管也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政体的模糊观点,但他最后的研究结果是把贵族制当作亚里士多德内心的理想政体。
与此不同,当代的亚里士多德研究者开始更倾向于民主制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例如,戴维斯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贤人政治最后都是靠不住的,政治统治必须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因此民主政治就成为最后的理想制度。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从轮流执政、中产阶级和集体决策三个方面,考察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政体的论述,认为混合型的宪政民主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好的政体。莫里斯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说,亚里士多德最后没有把信任给予君主或任何杰出个人,他相信中庸之道和多数的公民,最终选择了民主政治。奥伯也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在最好政体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但奥伯认为民主制至少是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好的政制之一。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关于最好政体的观点还比较模糊,从而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那么,他关于最坏政体的观点则非常明确,容不下半点怀疑。在他看来,人间最坏的政体,就是作为君主制变态的僭主制或暴君制。僭主不但垄断权力,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且一旦大权在握,便不受任何制度的约束,以手中的无限权力膨胀私欲,以各种动人的名义危害城邦的公共利益。
归根结底,政治制度是由人建立并由人执行的,制度与人相互影响,对城邦的政治生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忽视人的因素,即使有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起到理想的效果。实际上,政体从本质上反映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政体其实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互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亚里士多德深刻理解制度与人的这种辩证关系,除了考察和分析政体之外,还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政体与统治者
关于制度与人何者对城邦的公共利益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思想家们就已经争论不休。他自己显然认为,制度与人两者都至关重要,因而他既重视政体的作用,也同样重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作用。他反复强调,人类需要生活在社会政治共同体之中,而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均有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基本关系的确立。他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层组合,是组成人类政治共同体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
在这一前提下,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基本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在城邦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有三种类型,它们各不相同。无论在哪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统治者的素质应当都是极其重要的。统治者素质的优劣都会直接关系到政体的安危,也关系到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亚里士多德认为,从维护城邦政体的公共利益角度看,对于城邦的最高统治者来说,必须具备三种基本的素质。一是政治品质,统治者必须忠于自己所在城邦;二是出色的治理才能,统治者要足以胜任城邦管理的职责;三是高尚的道德品质,统治者必须模范地遵守公平正义的原则。
在统治者的所有品质中,亚里士多德最看重的是其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亚里士多德认为,良好的统治者应当追求城邦全体公民的幸福生活,并以此作为评判统治者及其政体优劣的根本标准。因而,在他看来,统治者首要的政治品质,就是不能以自我利益为重,而应以城邦的公共利益为重,这是优良的统治者不可变更的目标。
尽管亚里士多德强调统治者的重要性,但他非常清楚,这样圣明的统治者在现实世界其实并不存在。相反,他看到的是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和相互倾轧。统治者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之争,恰恰是各个城邦政局动态、内乱不断的根本原因。因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其老师柏拉图那样,将全部的政治理想寄希望于一位集智慧与德性于一身的“哲学王”,这也许是他从骨子里赞赏共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
既然统治者就其总体来说都是靠不住的,除了求助于法律和政制之外,亚里士多德还求助于公民。亚里士多德视城邦为公民的政治组合,公民是城邦政治生活的核心角色。因此,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些师辈学者和其他同时代的学者相比,亚里士多德尤其强调公民对于城邦生活和优良政体的作用。公民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对公民的定义和作用,以及如何进行公民教育做了系统的论述。
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比喻公民对于城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城邦是公民的政治社团,由一个个的具体公民组成。公民的素质如何,也直接关系到城邦兴衰和政体的优劣。有什么样的公民,势必会有什么样的城邦。只有公民的素质优秀,所在城邦才能随之成为良好的城邦。
既然公民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城邦的命运,那么如何提高公民的素质,自然就变得极其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公民素质的有三个因素,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性灵)诸善”。“外物诸善”即是财产等物质生活条件;“躯体诸善”即是公民的身心健康;“灵魂之善”即是公民的高尚心灵,包括其内在的品质才能。在这三种决定公民素质的要素中,最后的“灵魂之善”最为重要。培育人们“灵魂之善”的根本途径,就是公民的教育。
遵循上述这样的思维逻辑,亚里士多德把公民教育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公民教育不仅关系到公民自身的身心素质和个人的幸福生活,而且关系到城邦的政治命运和优良生活。甚至整个城邦的兴亡和安危在很大程度上与公民教育相关,而这一点恰恰长期被人们忽视了。公民教育既然与城邦的长治久安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它就不应当只是公民自己个人的私事,更应当是城邦政府的公共事务。城邦政府必须承担起公民教育的责任,通过教育使公民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使其行为受到必要的约束。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公民行为的这种约束并非是对公民的奴役,相反,是对公民自由的拯救。
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统治者是从公民当中遴选产生的,公民也应当具备一定的统治知识。这样,公民教育就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城邦政治的一般知识,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其二是道德品质的教育,使公民养成善良、节制、正义、勇敢,特别是“信从”的品质;其三是普通的国民知识,即学校教育的通用课程,包括读写、体操、音乐和绘画这四门基础课。亚里士多德将公民教育的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在现存《政治学》的8卷内容中,专门有一卷的内容论述“青少年教育”。
不过,“青少年教育”这一卷的内容极不完整,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就青少年教育做出详细的论述,最后结尾也是戛然而止。一般认为,这表明现存的《政治学》内容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原稿的全部内容。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如此重视最好的城邦政体,然而他却在《政治学》一书中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
换言之,现在我们读到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事实上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他研究城邦政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找何种政体是最优良的政体,“什么形式才是最好而又可能实现人们所设想的优良生活的体制”。他所说的城邦的“优良生活”,就是城邦“自足而至善的生活”,即“所谓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亚里士多德没有给我们提供其最终答案,事实上他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终极答案。因为一方面,这一问题是一个动态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答案,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普遍答案;另一方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完成的,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世的思想家和学者继续探寻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努力推动人类的政治发展朝着民主、和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善治的方向前进,正是在续写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