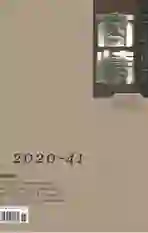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适当扩张
2020-10-20李晓瑜
【摘要】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经历了从放宽到收缩再到适度放宽的过程,但在增设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权的同时,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等私权利主体的限制依然非常严格,不利于公益诉讼发展。建议立法吸收公民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之一,并适度减少对社会组织的限制条件。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 适格原告 公众参与
原告适格是公益诉讼依法启动的前提和关键要素。我国环境公益诉讼法定的原告主要包括法律规定的机关、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和人民检察院三类。
一、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历程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到目前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原告范围也有一个“放宽——收缩——适度放宽”的历程。
(一)探索期:原告范围呈半开放式
第一阶段为2005年——2012年的探索期,以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次明确要“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为标志。2007年贵州清镇市法院开全国之先河率先成立环保法庭,并于2009年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市国土局”这个全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首案,2012年又受理了“蔡某海诉龙某光”全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案。与率先成立环保法庭相呼应的是,贵阳中院、贵阳市人大也同步出台了《关于环保法庭立案范围的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意见》、《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等司法解释或地方性法规,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探索提供了法律保障。之后,江苏、云南、海南、福建、广东、浙江等多地市陆续展开环境公益诉讼的尝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地方法院试水和人大代表、相关学者多年坚持不懈提交“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提案”的多方努力之下,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次被纳入立法。
从地方的实践来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既有公民、法人又有环保组织、环保行政机关、检察院。但在民事公益诉讼立法调研过程中,关于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建议受到了极大的否定,认为个人公益诉讼的放开极易引起滥诉,2011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一次审议时,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仅规定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从立法伊始就被排除在了原告范围之外。之后历经二次审议、三次审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也主要是围绕“机关和有关团体”的具体范围设置了“法律规定的”这一限定词,尤其是对“有关团体”的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
(二)适应期:原告范围被严格限缩
第二个阶段是2013年——2014年的适应期,环境公益诉讼写入《民事诉讼法》后,与其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法》修正工作也紧锣密鼓展开。《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时,出现了“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省辖市设立的环保联合会独揽起诉权”的规定,一时引起巨大争议。第三次审议稿中虽然不再直接将原告范围规定为市级以上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而改为“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专门從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信誉良好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但根据当时民政部门的统计,符合该资格的环保组织全国仅有13家,限制条件不可谓不严苛。在最终通过的2014年《环境保护法》中,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被确定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排除行政机关和公民个人。
令人尴尬的是,立法过程中反复担忧的“放开起诉资格限制会引起滥诉”的现象不仅没有出现,全国公益诉讼的立案数量从2012年的14件下降为2013年的0,符合原告资格的环保联合会提起的8起公益诉讼无一成功立案,2014年全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数量也仅有10起。事实上由于民间环保组织的不发达和公权力主导的法制传统,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大多是由行政机关和检察机关提起,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案件少之又少。同时《民事诉讼法》与《环境保护法》关于“法定的机关”是否属于适格原告的规定不一致,也导致司法实践理解混乱甚至无所适从。
(三)发展期:原告范围适当放宽
2015年至今为发展期。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以后,《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两高分别制定的《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陆续出台,行政公益诉讼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在司法解释中,且明确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四大类受案范围,为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遵循和程序保障,为期两年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在13个省市区稳步推进。自2015年12月山东庆云县检察院提起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以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占据了行政公益诉讼类型的绝大部分。而且由于法律对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条件的严格限制,单独由环保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案量、胜诉率依然非常低,目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呈现为民间环保组织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方式,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所萎缩。
2017年《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进行了修订,试点方案中的做法几乎是被原文植入两部诉讼法,以检察机关为唯一适格原告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被正式写入基本法律中,同时还赋予了检察机关在适格原告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时直接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以及检察机关对民事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支持起诉制度。2018年两高《检察公益诉讼若干问题解释》对行政公益诉讼适用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细化,2018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设立最高检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方案》业已审议通过,全国检察系统自上至下专司行政公益诉讼的专门机构有序设立。
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使得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细分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两大类型,原告范围也从“法律规定的机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扩展为涵盖“检察机关”在内的三类主体。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属于适格原告中的“第二梯队”,即检察机关是替代性的适格原告;在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是唯一的适格原告,由其独揽起诉权。
二、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多元性不足
(一)公权力主体的公益诉权进一步扩张
设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各国通例,从环境公益诉讼产生至今四十多年的国际实践来看,基本上形成了以巴西为代表的检察机关主导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的环保组织主导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公民诉讼模式三大类,而且放宽行政公益诉讼的趋势加快。随着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自上至下各级公益诉讼检察厅(处、科)、环保法庭的设立,我国公益诉讼的重心已经明显从民事公益诉讼向行政公益诉讼转移,凸显以公权力为主导的职权主义特征。
导致地方生态损害、环境污染的主因往往并非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一方面,《民事诉讼法》中只模糊地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这个概括的原告,具体范围并不清晰,而为了防止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简单地以司法权代替行政权“懒政”现象发生和行政权的过度扩张,《环境保护法》中也很慎重地仅将民事公益诉讼权赋予特定的环保组织,将行政机关排除在外。至于检察机关替代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大多是放在污染环境罪刑事公诉中以附带民事诉讼的形式出现,公益诉讼的效果不明显。另一方面,地方环保主管部门受制于人事、财政、地方保护主义等多方面因素,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权的行使上掣肘较多或怠于履职,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环保主管机关主动提起公益诉讼表现乏力,即使提起也多选择性地以个人或中小企业为被告,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无论从权力制约原则还是民事诉讼的功能来看,以环保部门为代表的行政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制度设计,存在逻辑和实践上的硬伤。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负有环境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拒不履行职责致环境公共利益受侵害时,检察机关通过起诉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履职是行使国家监督权的一种表现,具有法理正当性和可操作性,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效方案。当然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益诉讼权必须符合谦抑性,其最终目的还在于督促、保障环境保护行政权的充分行使,因此带有“过滤器”性质的诉前程序就成为必备,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也对此进行了严格规定。
(二)私权利主体的公益诉权被限制较多
环境利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自然性、共享性、基础性特征,破坏生态环境不仅对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命健康权、财产权等私益构成侵权,更是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环境公害行为。从法理上讲,凡与该社会公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具体公民或由不特定公民结成的社会组织,均有权以诉讼的方式对环境公害行为人提起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修复生态、损害赔偿等诉讼请求,但却一直无法突破制度和理念上的重重障碍。
公民既是生态环境维护的最直接受益者,也是生态公害的最直接受害者,“公众参与”是实现环境民主的关键要素,赋予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是其应有之义。以《里约宣言》《奥胡斯公约》为代表的的国际公约均规定了公民环境公益诉权。遗憾的是,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不仅从一开始就将公民主体排除在外,而且还对“社会组织”这类主体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要求必须满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的条件,这个设定在理论和实践上一直都备受质疑。
一方面,我国民间环保组织起步晚、数量少,能够满足如上限制条件的组织基本上仍然是以政府性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及其地市级以上分会为主,而中华环保联合会本身实行的是会员制,以缴纳会费形式入会的企业会员很多就是当地的环境污染大户,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的中立性、公正性从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另一方面,很多环保NGO由于经费不足运行不足三年就面临解散,“连续5年以上”的标准很难企及,更遑论支持公益诉讼的巨额费用,相比荷兰、美国等国家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活跃程度,我国社会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动力保障和激励机制严重缺乏。
三、适当放宽私权利主体的原告资格
如上所述,公益诉讼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前提是公众参与,国家机关固然拥有公民个体和一般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坚强权力后盾、充足经费预算和强大执行力,但环境问题的持续性、隐蔽性、跨地域性、易消逝性、专业性决定了环境公害行为致损范围的广泛性,在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感受性上公民是最有发言权的。而且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技术型”特征,在涉及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认定、致病因素分析、证据保全手段、生态修复技术等专业技术问题上,环境保护团体中的专业人才更加集中,科学判断上比行政机关更加有说服力。
從我国近二十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公民或有关组织滥用诉权、以公益诉讼牟取利益的担忧被证明是不必要的,相反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益诉讼积极性。建议立法将公民纳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范围,放宽对环保组织关于设立级别、注册年限的限制,并增加相应的公益诉讼奖励机制,激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动力,与检察机关行政公益诉讼相协调,健全环境公益诉讼的启动机制。
参考文献:
[1]颜运秋.中国特色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理论和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
[2]李楯.环境公益诉讼观察报告(2015年卷)[M].法律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李晓瑜(1981-),女,河南林州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宪政法学、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