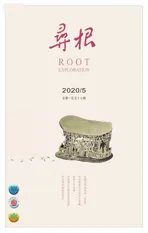风景何时入画来
2020-09-29闵惠泉
□闵惠泉
风景是什么时候作为绘画的对象与主题的?在看《穿越大洋的艺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埃斯凯纳齐艺术博物馆藏19-20世纪风景画展》一书之前我并没有想过。本次画展的策展人、印第安纳大学艺术史博士詹妮·麦科马斯在该书的序文中说:“风景画在西方艺术中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门类。在欧洲,风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题材——也是说,风景本身被作为主题来描绘,而不只是叙事画或肖像画中的背景——17世纪才首次出现。”笔者无法确认詹妮·麦科马斯提出的时间点是否准确,但西方绘画对象的主题是宗教神话类人物在先、风景在后,基本是被公认的。
该书中收入的最早的西方风景画是法国人克劳德·洛兰在意大利期间画的《日出》(约1646-1647年)和荷兰人雅各布画的《瀑布风景》(约1668年)。从18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旅游变得比较普遍。北欧人、英国人,制定了目的地为意大利“大旅行”(Grand Tour)的行程表,“风景画在游客行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本书的另一篇序文中提到的“风景与国家主权”以及它所激发与灌输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的话题,同样值得玩味。

◇雅各布《瀑布风景》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也探究一下中国的风景画是什么时候成为绘画的对象与主题的?
西方人一般用landscape和veduta表示风景与风景画。在中国,“景”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说文解字》中解释“景,日光也”,《释文》“景,境也”,《尔雅》中称“四时合谓之景风”。风和景两字的连用,在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言语》中已见。当时偏安江南的晋人曾发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唐代的杜甫有“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白居易也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名句。中国人心目中的景,从广义上讲即为“场景”“景物”;狭义上则是指“山河”“山水林石”,即“自然景胜”。
绘画的历史与文化,乃至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在某些方面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中国的人物画(最早的人物画即出土的《御龙帛画》,公元前475-前223),也比中国的山水画早,而且早了大约1000年,与西方绘画史可谓“同其径路”。而现存故宫的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为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则又比西方的风景画早了1000年。在对人和自然的感知上,中国人可谓是一个聪慧而又早熟的民族。
中国的人物画为什么早于山水类的风景画?唐代的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个说法:“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对于这种教化之功能,古人恐怕难以寄情于山水之类的丹青。

◇ 展子虔《 游春图 》
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云:“尝考前贤画论,首称像人。”“盖古人必以圣贤形象、往昔事实,含毫命素。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唐韦机为檀州刺史,以边人为陋,不知文儒之贵,修学馆,画孔子七十二弟子、汉晋名儒像。自为赞,敦劝生徒……”郭若虚又说:“中国画体之演变,乃人物牛马盛之于前,山水花鸟盛之于后。”
明代朱濂曰:“古之善绘者……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烈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书并传,助明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
在张彦远、郭若虚著述之后,宋代邓椿的《画继》中分卷为:“一卷至五卷以人分,曰圣艺,六卷、七卷以画分,曰仙佛鬼神,曰人物传写,曰山水树石,曰小景杂画……”看来,在绘事的类型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直到宋时都是分得挺清楚的。
用宋代米芾在《画史》中的话一言以蔽之:“古人图画,无非劝诫。”
不过邓椿曾感慨:“大抵收藏古画,往往不对,或断缣片纸,皆可珍惜……耻于对者,十中八九。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夫岂知古画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年,那得复有完物?断金碎玉,俱可宝也。”
邓椿为北宋末年人,上溯500年,不过是隋代前后。这可能是宋人大多见到或心目中的古画最早的年代,宋人可能罕见晋时“复有完物”的画作。而在宋人看来,不论是圣贤仙佛、人物在画史中的地位,还是其存续的先后,都要高于山水树石一类。
由此可见,在中国绘画史上,甚至在画的分类上,其人、其画,在教化及意识形态的功能上都是唯大、唯重的,真可谓“画以载道”。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不仅中国人物画早于山水画,而且晋代至唐宋时的画家,普遍认为人物画难于、高于山水画。

◇宋徽宗《溪山秋色图》
晋代顾恺之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
唐代朱景玄说:“夫画者,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何者?人物禽兽,移生动质,变态不齐,凝神定照,固为难也。”
不过,唐之后,特别是宋代以来,山水至上渐成画风,这种转型大约滥觞于西晋。这和中国历史上两次南渡,即西晋末年东晋建都南京,以及高宗定都于临安不无干系。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背井离乡的迁徙,江南景色宜人的山水之美,也带来了官宦士人地理与风景的“大发现”和新的眼光,以及由“无以画名者”的匠人画工到文人士大夫绘事群体的凸显。
“汉末历三国两晋,以至南北朝,天下纷争,儒家的纪纲观念,荡然无存,士大夫阶级,崇尚清谈,人求解脱,而实行隐遁的生活。”山水风景成了被消遣、被欣赏、被临摹的对象。
然而,某一对象之所以成为人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恰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我确证与体现。不论是归隐的文人士大夫,还是乐山、乐水的仁人志士,都在山水风景中找到了自我存在与心灵的栖居之地。
宋代刘道醇编纂、符嘉应撰序的《本朝画评》中云:“画之源流,诸家备载。爰自唐季兵难,五朝乱离,图画之好,乍存乍失。逮我宋上符天命,下顺人心。肇建皇基,肃清六合。沃野讴歌之际,复见尧风;坐客间宴之余,兼穷绘事。”
邓椿在《画继》中提到:宋徽宗“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刃填溢,百倍先朝”。宋徽宗时曾将古今名人画编辑成《宣和睿览集》,徽宗本人还画有《池塘秋晚图》等。酷爱书画艺术,具有艺术家、美学家气质,被邓椿称为“艺极于神”的宋徽宗,极大地推动了绘事尤其是山水风景画的成熟与发展。
后来,清代布颜图在《读画辑略》和《画学心法问答》中写道:“东晋以来,有顾长康、陆探微、张僧繇,为画家三祖。虽有尺山片水,亦只画中衬贴,而无专学。迨至盛唐,王右丞……而山水始有专学矣,从而学者,谓之南宗。”“盖山水画学,始于唐,成于宋,全于元。”
明代以来,画风及舆论转向明显,明朱濂“古之善绘者……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烈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书并传,助明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寝不古若。往往溺志于车马士女之华,怡神于花鸟之丽,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
明吴宽云:“古图画多圣贤与贞妃烈妇事迹,可以补世道者。后世始流为山水禽鱼草木之类,而古意荡然。”(《佩文斋书画谱》)
明唐志契云:“画以山水第一,竹树阑石次之,人物花鸟次之”(《绘事微言看画诀》);明屠隆“画以山水为上,人物小者次之”(《画笺》);清钱杜“画以山水为上,写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此风延续至今未衰,乃至中国的山水画,几乎成了国画的代名词。
这种转变除了宋朝初叶“肇建皇基,肃清六合,沃野讴歌之际,复见尧风”,有当朝文人歌功颂德,绘事中山水风景画“成于宋”且长足发展之因;亦有元明以来,“世道日降”“人心寝不古若”“古意荡然”,士大夫阶级“寄兴于笔墨,假道于山水”的隐遁之情。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画景和画山水风景并不是一回事,如西晋画家卫协有《穆天子宴瑶池图》只是画有人物的场景,至于人物背后的山石树木花鸟,不过是一种衬托或背景而已。
山水风景入画,与闲暇和旅游也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像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吟诵称赞“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剪取吴淞半江水”的王宰,毕竟是殷实之家的官吏与有闲之人。明代莫是龙在《画说》中写道:“写胸中丘壑”“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而自晋代以来文人学士的游历、归隐、纵情山水也渐成风尚,例如仅江西的庐山、杭州的西湖两地,历代文人学士“游踪不绝”。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与中国最早的游记在创作上有某种时间上的吻合,看来也绝非偶然。
在当代学者倪志云等编《中国历代游记精华大全》收入游记662篇,其中宋代之前24篇,宋代56篇;收入最早的游记为东晋慧远的《庐山记》和袁嵩的《西陵峡》(即为其《宜都记》中的片段)仅2篇。学者柳肃教授认为:魏晋之前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观赏自然风景,“能够欣赏自然之美的必定是有较为优裕的生活和较高文化修养的人”。用唐代张彦远的话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以能为也。”中国历史上山水风景画及游记即是一种明证。
我国地域辽阔,自然风光美不胜收。面对如此多娇的锦绣河山,不论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难免触景生情,画兴、诗兴及游兴大发,甚至在某些人身上合为一体。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即被尊为中国南宗“山水画第一人”。
山水风景入画,可谓时也、势也、心也、性也。从中不难看到中国社会的治乱兴衰、世风的转折激荡;亦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文化生活与精神追求的取向,以及所展示的群体与个体心性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