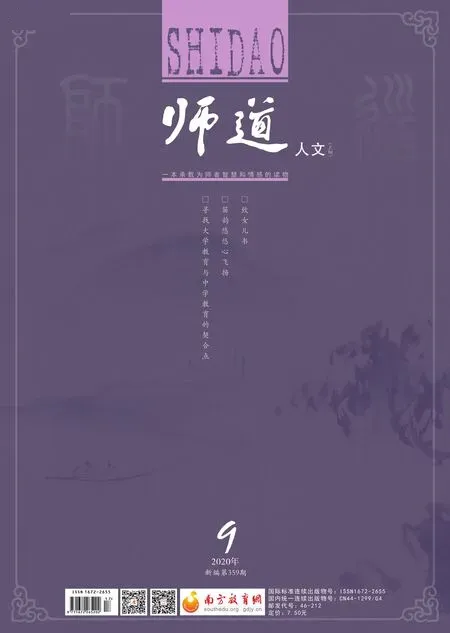留住教育语境中的“童年” 及“乡愁”
2020-09-25周世恩
周世恩
我问讲台下的学生: 你的故乡在哪里?
45 个学生, 一部分学生摇头,他们不知道故乡是什么, 有一部分学生起身回答问题, 告诉我他的故乡是广州。 实际上, 他们说错了,他们长于斯, 却没有生于斯, 而他们的父母, 并非广州的原住民, 而是来自于相邻的湖广浙赣、 四面八方。 只有极少数的孩子, 他们知晓自己的故乡, 或者是父亲母亲出生的地方——是自己的老家, 或者是自己出生一直居住的地方——广州。 看着讲台下这群纯净而天真的学生, 我有一些黯然, 因为, “故乡” 这个情感饱满的词汇, “故乡” 这个生动而真切的文化语境,会在这些孩子的脑海中慢慢地模糊、 混沌, 他们将渐渐缺失对故乡的认同及思念。
五年级上册的第一单元的课文, 以 “童年和故乡” 为主线, 编排了萧红的 《祖父的园子》、 季羡林的 《月是故乡明》、 还有一篇《梅花魂》。 教授这一单元的文章,我领着孩子们朗诵课文: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 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朵花, 就开一朵花, 愿意结一个瓜, 就结一个瓜。 若都不愿意, 就是一个瓜也不结, 一朵花也不开, 也没有人问它。 ……” 童音袅袅, 唇齿飘香,他们朗诵得很齐整, 也很美。 这些带着童年气息的文字, 这些自由飞翔的文字, 这些从萧红故土里飘出的具有浓浓乡土气息的文字, 我很喜欢, 我的学生也很喜欢。
我让孩子们说一说文字背后包含的情感, 才发现多数的孩子们或一知半解, 词不达意; 或流于肤浅, 隔靴搔痒。 从萧红笔端流淌出的优美词句, 仅仅停留在了他们的朗诵之上, 也仅仅停留在他们的喜欢之中, 却没有真正内化为一种“故乡” 的情感, 一种感同身受的“乡愁” 情绪。 我有些无可奈何,我知道, 这不能怪他们, 因为, 他们中的大多数, 生在城市, 打小,就从未见过肥绿的倭瓜, 也从未见过黄瓜的花。 是的, 在网络上, 这群孩子是可以认识这些事物的, 而我, 完全也可以让孩子们在幻灯片上, 看到倭瓜的图片, 看到黄瓜开出的金黄的花。 可是, 我在想: 高科技所呈现的画面、 视频, 真的能让他们管窥到萧红的故乡么? 能触摸到萧红在出走故乡后的想念和魂牵梦绕么? 毕竟, 故乡这一个深情而模糊的概念, 只有亲自的体验、经历、 体会, 甚至远离之后, 才能渐渐明白, 慢慢知晓。

故乡是什么? 汉语词典上的解释是: 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泛指家乡、 老家。 这个角度去解释“故乡”, 无疑强调了地理上的认同感、 归属感。 其实, 如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说, 从文化现象的解读来说, 故乡的概念与外延, 已经远远超过了汉语词典的解释——因为, 故乡, 是地理上的, 也是心理上的, 更是文化上的。 归根结底, 故乡的文化心理的含义, 比地理上的含义丰厚得多。
即使按照 “地理” 范畴去界定故乡, 阐释故乡, 目前的 “母语”教学和 “德育” 教育中, 尤其是故土故乡的认知教育、 情感教育中,都有一道绕不过去的难题, 也面对着尴尬和困窘——因为, 这一代人, 正在迅速地失去地理意义上的故乡。 第二次 (2006 年)、 第三次(2016 年) 全国农业普查调查结果显示, 第一次农业普查, 中国还有637011 个村, 第三次农业普查,只剩下了596450 个。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 农村正在快速地消失。
“00 后” 的一代, 许多是跟随着父母, 扎根城市的, 他们的背后, 是无数的以农村山村、 平原、丘陵为背景而形成故乡图景: 有清澈的河流逶迤流向远方, 有高高矮矮的或青砖或土墙堆砌的房子, 有金黄的麦垛, 有葱郁的树林, 有小伙伴打雪仗、 躲迷藏而飘散的笑声……
“00 后” 的父母, 也有纯粹在都市里出生、 成长的, 可是, 他们眼中的故乡依旧支离破碎。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也让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 日新月异。 造城运动, 让一座座城市, 旧貌换新颜, 步入了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列之中。 但是, 它也同样改变了人的记忆。 填河、 造桥、 铺路、 圈地、 建房、 挖地铁、建高速、 盖厂房、 拆迁……改变了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将熟悉的地理风貌改变得面目全非, 小桥流水,变摩天大厦, 古巷老街, 成立交高速, 一栋栋的老房子被拆平, 一条条的老街被改造……城市地形地貌的改变, 建筑的消逝, 环境的变迁, 比之乡村、 城镇, 还要迅速、彻底, 可能孩子昨日嬉戏的草地,时隔数日就高楼林立; 可能昔日流淌的河涌溪流, 填平成为平整马路; 可能孩子前天攀爬过的一棵大树, 今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地理上的故乡, 不停变化, 不断地易容, 让人愈发难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齐全的概念。
这些承载记忆的风物消失殆尽或者改天换地后, 地理的故乡将如何依存?
心理故乡, 地理为基, 抽象缥缈, 但也具象。 所有的乡愁, 皆有物指: 三月的桃花、 村前的流水、低飞的白鹭、 漠漠的稻田、 如席的雪花、 村口的社庙、 社庙前蹲着的石狮子, 爬过的山、 涉过的水、 走过的路、 钻过的小树林、 漫步过的小巷、 住过的老房子、 倚靠过的黄土墙根, 还有那一口老酒、 一张烧饼、 一棵歪脖子的槐树……离开“物” 的故乡, 隔绝了 “物” 的乡愁, 宛若浮萍, 无处可倚。 你一切能看到的、 听到的、 闻到的、 尝到的, 都是乡愁的载体。 离开具象的感知, 则无法形成心理的起伏波澜, 心理的故乡, 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只有地理故乡的存在, 才有心理故乡的依托, 文化故乡的延续,这一代的孩子, 才能真正认同故乡、 理解故乡, 才会激荡其故土之念、 故土之情。 如此看来, 孩子对故乡概念的模糊, 对故土概念的偏差, 对乡愁的理解肤浅, 也有其根源、 缘由。
特级老师赵志祥, 曾在我们学校示范过一节公开课 《秋思》。 这首来自元代马致远的小令, 短短28 字, 宛若一杯浓浓的俨茶, 氤氲之间, 缥缈着旷古的乡愁, 飘荡着孤美而凄凉的思念。 课堂也被赵志祥老师演绎得宛若一首起承转合的小令, 一贯的风趣幽默, 旁征博引, 加上赵老师字正腔圆的吟诵,让学生如痴如醉。 赵老师的课堂设计, 也精彩绝妙, 以 “列锦” 的修辞手法作为教学重点, 又选取电影的 “蒙太奇手法” 作为了教学的难点。 课堂如抽丝剥茧, 一步一步地把孩子牵引到了遥远的元代, 和马致远一起走到异乡, 走进了黄昏,让在座的师生, 都感受到散曲本身的魅力, 沉浸其中, 回味无穷。
一课终了, 学校的语文老师想利用一下赵老师课堂的余热, 延伸一下学生对 “列锦” 的修辞手法的认识, 于是, 让学生仿 《秋思》,也写一写自己的乡愁。 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各异: 有很快就写出来的,也有摸着脑袋, 无从下笔的。 老师拿来了写完同学的本子, 才发现,孩子所写的物事, 根本无法引起乡愁的遐思, 大部分的词汇, 都是“马路” “榕树” “商铺” “花园”“行人” ……无可厚非, 这就是孩子眼中的故乡, 但他们抓不住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脉络, 这一座座日新月异的城市, 也不容他们抓得住乡愁的根脉。 他们太小, 而城市又千篇一律的相似, 街道也大同小异的笔直, 连行道树都是统一的品种,长得又如此的相似! 老师问无法下笔的孩子: “为什么你写不出来?”一位学生说: “老师, 我能理解马致远的乡愁, 只是我真的没有乡愁, 我甚至连故乡的概念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写!”
无独有偶, 五年级有一单元的作文, 主题是 “二十年后回故乡”。作文的要求是这样的: 大胆想象二十年后家乡人、 事、 景、 物的巨大变化, 学习用人事景物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怀念之情; 用具体的人、事、 景、 物按一定的顺序把家乡的巨大变化写具体; 指导学生修改习作, 并把修改后的习作读给大家听。 这一篇以想象为主的作文, 学生喜欢写, 写起来也十分容易。 可是真正将作文收起来一看时, 才发现学生想象丰富有余, 但是文中对家乡的热爱、 怀念之情, 却品不出, 读不出。 刚开始, 我还以为是学生作文技巧的问题, 但是深入分析和思考之后, 才知道: 讲台下的这一代学生, 正在远离乡愁, 地理上的、 心理上的, 文化上的。
文学, 允许虚构。 不可否认,优秀的孩子可以凭借语言文字的感悟力, 凭借文字的技术性操作, 照样能写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照样能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 心理的离愁别绪、 黯淡明亮, 却是不能虚构的, 毕竟, 心理的感受, 无法虚构, 也不能虚构。女儿今年上四年级, 每逢写邻里之间、 乡村风景、 童年趣事时, 她就不由自主地犯怵, 作文水平尚好的她, 也曾经回过我的故乡的她, 向我抱怨: “在小区里居住了近十年, 楼上的邻居, 长得是什么模样, 一无所知, 你说, 我怎么能写好邻居呢?” 长这么大了, 她唯一熟悉的路, 是学校到家里的路, 平日上课, 根本没有时间到乡村田野去溜逛一下, 你说, 她怎么能写好乡下的风景呢? “我的童年, 几乎是在上学、 放学、 跑培训班的路上度过的, 不是没有发生过有趣的事情, 不过, 缺少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声, 缺少无忧无虑的心情, 又如何将自己的童年写得生动有趣呢?”孩子的语言虽然有一些夸张, 但是的确是存在的事实, 这一代的孩子, 不仅连自己的故乡丢失了, 而且连自己的童年也丢失了。
以前的故乡, 像木心描绘的《从前慢》 一样: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 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有故乡的风貌, 有车, 有马,有挑檐的老房子, 有青石板铺成的古巷; 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有早上 “您吃了吧” 的问候, 有东家长李家短的唠嗑、 聊天, 有几家人蹲在墙根底下吃饭晒太阳的滋味; 有生活的人间烟火模样, 炊烟袅袅地升起, 小河静静地流淌, 夕阳下,母亲在村口喊孩子回家吃饭; 有精神的纯粹和干净, 邻里之间, 守望相助, 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 扶持。 这些, 才是 “故乡” 真正的精神内核, 才是乡愁的源头——温暖、 纯粹、 干净, 才会让人常常忆起、 念念不忘。 可惜, 现代化的进程, 城市化的改造, 带来了乡村宗族文化的消亡、 城市里的邻里之间的隔阂, 将 “故乡” 这一精神内核, 逐渐瓦解, 最后, 支离破碎,难以还原。
变化, 才是这个世界的永恒。自然, 我们不能以怀旧的心绪去阻挡这个社会的发展、 变革, 我们也不能阻挡这一代人乡土观念的消失, 故乡、 乡愁认同感的慢慢烟消云散。 或者说, 我的担心只是多余, 或许未来, 故土、 乡愁、 故园、 童年, 会以一种迥异于这一代人的心理感受、 文化认同出现。 只是, 我觉得在目前的文化大背景中, 在教育的语境中, 这种 “消失” 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或者,有待于我们全社会想千方、 设百计去减缓这一种 “消失”, 或者阻挡这一种消失。 毕竟, 在母语的长空中, 有那么多美丽的诗句和词汇,都与 “故土” “故园” “故乡” 息息相关, 休戚与共! “消失” 了故乡、 故土、 故园, 就代表着无数的人, 在教育的背景下, 在文化语文的旅途中, 与这些浩瀚、 博大, 有着中国特有的语言文字的深刻内涵失之交臂, 那将是这一代学生的遗憾, 也是教育的遗憾, 母语的遗憾。
2013 年12 月1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 明确地提出城镇建设的要求: “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 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 避免走弯路; 要体现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天人合一的理念, 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这是对 “乡愁” “故土” 最好的阐述: 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乡才有依托; 也对 “故乡” “故土” 的建设、 规划, 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 要注意保留城市原有的地貌风光, 留住山, 留住水, 莫要突飞猛进, 砍树、 填湖、 盖楼, 让大量自然山水、 乡村田园被蚕食, 到处是刺眼的钢筋水泥 “森林”, 自然风光难觅, 青山越来越远, 绿水越来越少, 乡愁无处寄托。 要加强对城市的空间立体性、 平面协调性、 风貌整体性、 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 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 建筑风格等“基因”。
乡愁是接地气的。 地理的延续、 不变, 是接地气的第一步, 也是关键的一步。 如果这些高屋建瓴的政策能真正落地实施, 推进实行, 我相信这一代学生, 会慢慢地找回 “故土” 的概念, 在长大以后远离故土, 升腾起美好而悠远的“乡愁”, 也会渐渐地理解中国文化中的 “离愁别怨”, 理解那些包含着乡愁的古诗、 古句的, 也会妙笔生花, 写出一篇篇饱蘸着乡愁的文字的。 “乡愁” 是铭记历史的精神坐标, 工业化、 城镇化不能割断乡愁; “乡愁” 是教育中珍贵的一部分, 靠的不仅仅是教育工作者对文本的认真解读、 对课堂的精心设计, 更靠全社会齐心协力, 努力保留下 “乡愁” 赖以生存的 “不变”和 “传承” ——青山依旧, 绿水长流; 邻里相助, 和睦共处。
“乡愁” 也与童年紧密相连。童年时代所拥有的快乐, 会滋养“乡愁” 的内涵, 会丰富 “故乡”的内核。 解决地理上 “乡愁” 的难题, 是全社会的责任, 而让童年快乐, 让 “乡愁” “故土” 的内涵更加丰富, 则依赖教育的力量。 让孩子不要焦躁地奔跑在学习的道路上, 留下一些时间, 让他们在小树林里爬树、 捉迷藏、 捡石头、 编花环; 让他们在小区的荷花池边观花, 听蛙鼓声声, 看水草招摇; 让他们在古旧的巷道里看人来人往、墙影斑驳、 青苔苍苍; 或者什么也不干, 坐在石板上发呆、 出神, 河流自然地流向远方, 清风不说话,悠悠向前。
教育的语境中, 拥有了 “乡愁” “童年” 这些热腾腾的词汇,我们的孩子, 就会更加幸福, 更加快乐, 更会拥有一个完整而富有的人生。 期待着, 在教育的语境中,在孩子的儿童视角中, 在母语的文化内涵中, 有故土, 有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