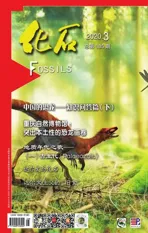三叠纪生物复苏
2020-09-23冯伟民
冯伟民
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是显生宙以来最大的灭绝事件,它重创和毁坏了古生代生态系统,打破了生物与环境间长期的相对平衡,中断了生物演化的连续进程,使得生物多样性大幅下降,极大地弱化了旧生物屏障,并迎来了中生代新的生物演化时代。
但是,在经历了二叠纪末大灭绝后,生物界进入了很长的残存期,其延续时间长达约10Ma。残存期是大灭绝事件的后续,深深地打上了大灭绝的烙印,同时,它又是随后复苏期的先兆,生物在此艰难的过程中是如何度过的呢?它们又采用了哪些策略和途径呢?
大灭绝后的残留局面
大灭绝后的残存期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生物多样性最低,灭绝量和新生率也最低,群落类型和生物地理区系最单调;各种生物类型中,最发育的是幸存者,世界性分子常见,但大多数分子的丰度并不高。危机先驱型分子的出现显得很重要,灾后泛滥种成功地适应并占领尚未改善的空缺生态位;在演化进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复活分子等通常尚未出现。这些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全球环境的恶劣程度,表明物种与生物量的大规模丧失,生物链和食物链的裂解破坏,生存空间极大地空缺,都需要漫长时间去恢复生物生存的环境。
早三叠世属残存期,其特点是幸存者占绝对主导地位,灾后泛滥鼎盛,属级分异度很低,生态群落类型较简单、成种现象极少,表明生态环境始终比较恶劣,如双壳类克氏蛤(Claraia)和Eumorphotis突然开始灾后泛滥,成为早三叠世最为常见的优势分子,它们与Unionites,Promyalina,Leptochondria等属一起组成的浅海底栖组合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地,并广见于各个古纬度带,给萧条已久的海底世界带来了一丝生机。
不同生物复苏中的表现
1、微体生物复苏表现
经历了晚二叠世的大灭绝后,早三叠世大多数时间生物族群都是以一些低分异度组合为特征,大多数正常的海洋动物类群至中三叠世早期才开始复苏。放射虫的复苏始于早三叠世晚期。三叠纪初有孔虫的复苏经历了两个阶段:早三叠世,以砂盘虫类和节房虫类占优势,但复杂胶结壳的其他串珠虫类和钙质多孔壳的其他类群迅速增长。小栗虫类也在早三叠世后期有较大的发展,残存的内卷虫类平稳延续。于是诱发了早三叠世末期中生代有孔虫的首次辐射。至中三叠世,各类有孔虫已逐步发展均衡,类群多样性稳步增高,尤其各类群中复杂壳体结构类型渐占主导。到中三叠世末再次辐射,晚三叠世已形成中生代有孔虫动物群的面貌。
2、无脊椎动物复苏表现
游泳生物菊石类、营穴居生物腕足类海豆芽和具有更强适应能力的双壳类得到了迅速发展。双壳类在早三叠世分异度很低,多数亚纲萧条,特别是隐齿亚纲、异韧亚纲及壳体固着类极度贫乏,惟适应性能较强的翼型亚纲中的足丝附着类较丰富;中三叠世Anisian早期多数亚纲开始复苏、但隐齿亚纲和异韧亚纲仍未出现;Anisian晚期各亚纲呈现明显的繁盛趋势,属、科和异韧亚纲的分异度均达到新的高潮。早三叠世腹足类软体动物有30%复活种类,包括神螺类和锥螺类,但在成种速率增加和其他一些复活者再次出现时却迅速消亡。

德国南部的三叠纪拉丁阶菊石——大齿菊石Ceratites laevigatus
在早三叠世的创业者中还有游泳健将头足类,以蛇菊石和齿菊石为主,它们在近乎死寂的海洋中孤独地寻找着食物。之后到了早三叠世晚期,随着环境的改善,食物来源日益丰富,菊石大量繁盛起来。鹦鹉螺从幸存的一支恢复起来,形成新的种类。
在海洋中新的珊瑚种类诞生了,它们组成比较小的珊瑚群。
3、脊椎动物复苏表现
三叠纪之初的鱼类种类比较少,说明只有少数种类在不久前的那次灾难中幸存下来。但是研究表明,在华南地区鱼类和牙形类动物一样都是大灭绝后在三叠纪最早复苏的类群,最早复苏的鱼类为裂齿鱼类。鱼类从灭绝期到辐射期仅用了130-400万年。
离片椎目两栖动物经历大灭绝后旋即进入辐射期,而爬行动物也有了新的重大变化。此时,中生代海洋霸主鱼龙类的祖先产生了,而且其演化相当迅速,至早三叠世晚期,多种形态的鱼龙类开始出现,于是进入了鱼龙类的发展期。陆地上由于高大陆生植物消失,地表菌类非常繁盛,表明当时地球环境非常恶劣。我国北方孢粉资料表明,晚二叠世植物有54个类别,早三叠世早期剧减为16个类别,而到了早三叠世晚期又增加到58个类别,之后继续增长。显然,早三叠世为植物复苏期。
4、生物礁的复苏
礁生态系的演化在早三叠世达到了历史最低点,主要表现为具有骨骼造礁生物(后生动物、真核藻类)的灭绝,使礁生态系中的酶控碳酸盐基本消失,导致后生动物礁的消失长达10Ma以上(长兴期至安尼中期),然而微生物岩礁依然存在。

三叠纪的古菊石Arcestes复原图
在二叠-三叠纪转折时期,世界许多地方的正常浅海环境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小型丘状礁体,以蓝菌为主的BMC成为仅存的造礁群落,分异度降到了最低点,群落结构极其原始而简单。这正是“长兴期”末大灭绝后残存期礁生态系的最重要特征,表明显生宙礁生态系发生了严重的倒退现象。
大灭绝后微生物岩在正常浅海环境的泛滥,一方面是因为后生动物的大量灭绝,导致生物扰动水平大大降低,使微生物席基底得以顺利形成;另一方面是因为古海洋的异常事件大大改变了海洋的物理化学环境。相对稳定的底质状况和有利的海水物理化学条件是微生物岩灾后泛滥的两大前提条件。
二叠纪时微生物岩和微生物岩礁主要见于高盐度环境,如欧洲的镁灰海。当盐度趋于正常时,动物群变得丰富,微生物席基底则变得罕见;反之,则动物群变得贫乏,最后甚至只剩下微生物席。以蓝菌为代表的自养细菌在大灭绝后所出现的灾后泛滥现象,表明灾后海洋的初级生产力很可能并未像过去设想的那样降到最低点,而是依然保持着相当的水平,而以海洋无脊椎动物为代表的消费者的大量灭绝使灾后海洋生态系统的营养结构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初级生产力相对“过剩”的现象,漂浮生活的颗粒状钙化蓝菌在早三叠世初的发现可以作为初级生产力相对过剩假说的证据之一。
早三叠世末至中三叠世早期,机遇色彩甚浓的微生物岩从正常浅海环境退回到非正常的高选择压力环境,与此同时,竹叶状内碎屑灰岩也基本消失,表明当时的海洋环境已大致恢复正常,平底生物群落和藻类开始复苏,内栖动物重新趋向活跃。正常浅海环境中时错相沉积的消失,是礁生态系行将复苏的前奏。
5、生物复苏的策略
生物族群为什么会复苏,不同生物有不同的策略。1、腕足动物几乎缺失幸存分子和复活分子。Lingula和Orbiculoidea被认为是穿越该事件的幸存属,然而近来研究,真正的Lingula限于新生代,Orbiculoidea只见于古生代,它们似乎都不属于幸存分子。中生代腕足类的复苏主要靠外来分子和新生分子。2、双壳类与腕足动物不同,它们所含的幸存者比例很高(占总数3/5),另一方面组分是新进化的类型重新出现,共同组成复苏的群体。迁移能力较强的各种表栖双壳类在界线层中是最为常见、最为活跃的类型,占据明显优势,内栖双壳类却较为少见,而且大都是近岸浅水和比较适应贫氧环境的类型。3、有孔虫的复苏靠的不是古生代残存类群,而是残存期的新生类群,包括危机先驱分子。4、腹足类则发育大量复活分子,它们是复苏的重要根源;还依赖早三叠世初期由某些种系变而产生的新支系。5、菊石因新生率较高,大事件之后进入残存-复苏期,然后很快进入到辐射阶段。6、后生动物礁的复苏发生在中三叠世早期,距二叠纪末一千万年;由于种种原因,中生代礁生态系的确立和辐射迟至早侏罗世晚期才告完成。
罗平生物群代表了生物完全复苏
经历了长达一千万年的残留与复苏过程,中生代真正的生态系统终于建立了起来,距今2.44亿年前的云南罗平生物群代表着生物复苏后,海洋生态系统完全恢复,彻底摆脱了二叠纪绝灭带来的灾难性阴影。当时的罗平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条件,吸引了大量的海生生物,鱼虾以丰富的海洋微生物为食,鱼龙、幻龙有享用不尽的鱼类美食。罗平成为了大灭绝后生命复苏的伊甸乐园。
显然,生物在痛苦的残存期和艰难的复苏期所表现出来的坚守和智慧,都是我们人类需要学习并用之于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中,信心是坚守的动力,智慧是度尽劫难前景在的基础。相信我们人类所学到的不仅是远古生物应对自然灾变的策略和方法,更是学到了生物界自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一直所表现出来的那份顽强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