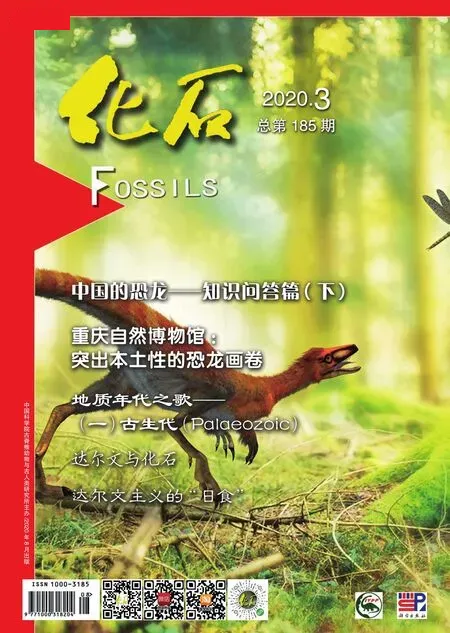达尔文与化石
2020-09-23苗德岁
苗德岁
达尔文堪称全能型的博物学家,他在博物学的各个领域都卓有建树。然而,相对说来,古生物学却是他知识领域的短板,尽管在他提出生物演化论的过程中,古生物学占有极为重要的份量——毕竟化石才是生物演化的“实证”。

达尔文研究的藤壶
当然,这与达尔文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他基本上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学成才”型学者。他的动物学基础主要是在爱丁堡大学读医学院的一年间,非常“不务正业”(以至于一年后即中途退学),不惜“翘课”跟着动物学家格兰特先生学习海洋无脊椎动物而打下来的;后来,他还花了长达八年时间专门研究藤壶,因此,他是实至名归的藤壶专家。在昆虫学方面,由于他长期执著地爱好和收集昆虫(尤其是甲壳虫),故也有相当好的基础。不过,达尔文的最强项当数植物学了;他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受其良师益友、植物学教授亨斯洛先生的影响最大,因而在植物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反映在他日后出版的好几部植物学著作中。
相形之下,地质古生物学是达尔文博物学知识中比较薄弱的一环。他在大学期间从未系统地学习过地质古生物学。这也毫不足怪,一是因为他原本是准备读神学的,二是在那个时代,剑桥大学尚未开设地质古生物学的正规课程。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研究,远不像今天的情形。那时候各门学科都在草创阶段,很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依据今天的标准,大概都只能算是“民科”。大学里也还没有正规的科学专业设置,远不像今天如此按部就班地训练专业人才。所幸在达尔文自剑桥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里,经亨斯洛教授介绍和推荐,达尔文曾跟随剑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塞奇威克去北威尔士做了为期两周的地质考察。塞奇威克是英国当时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与地层古生物学家之一,寒武纪就是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古生物学便遇上这样的名师,这就像一个人刚学炒股,就拜上巴菲特做师傅——这在当时主要靠师傅私授知识的时代,达尔文是何其幸运啊!

达尔文随小猎犬号战舰环球考察的路线
极具喜剧意味的是,达尔文在成为生物学家之前,主要身份是地质学家。事实上,在达尔文跟随小猎犬号战舰环球考察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本人也是以地质学家的身份自况的。由于他在地质学方面的杰出贡献,环球科考归来不久,即应邀加入伦敦地质学会并很快被选为学会理事——这在当时,是科学界非常崇高的学术地位,因为那时伦敦地质学会汇聚了一批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咖,包括莱尔、塞奇威克、默奇森、巴克兰、帕金森,等等。
当然,达尔文在环球科考期间,在地质古生物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不是他行前跟随塞奇威克在北威尔士做短期地质考察所受的训练就能达到的。他登上小猎犬号战舰的时候,莱尔的新著《地质学原理》刚刚出炉,舰长亲自送了他一本。他在环球之旅期间认真研读了《地质学原理》,并把书中的原理运用到他的环球考察实践中,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就是“部分地用莱尔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尽管莱尔写作此书时,他的经验和观察只局限在英伦三岛,达尔文却把莱尔的真知灼见放到了全球地质框架中去考量和验证。
作为地质古生物学家的达尔文,其贡献不仅仅在于采集珍贵标本以及野外观察,更主要的在于他能把野外观察的现象和问题与抽象的理论和因果关系紧密联系起来,他的这种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的技能,是把亨斯洛教授在剑桥传授给他的绝活,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结果,甚至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譬如,他后来把莱尔《地质学原理》中的将今论古的原理以及均变说,巧妙地运用到生物演化论之中,把物种在空间与时间分布上的变化,进行举一反三的类比,足以展现达尔文的过人之处。

达尔文挖掘的箭齿兽头骨
达尔文的地质古生物学知识帮了他太大的忙啦!在《物种起源》(苗德岁译“插图收藏版”,译林出版社2018)初版14章中,有两章是专门讨论地质古生物学的。即便今天读来,他的地质古生物学知识也算是相当扎实的。比如,达尔文对南美古哺乳动物化石的研究,启发了他对地史上生物绝灭现象以及物种可变性的正确理解,为提出生物演化论奠定了基础。在《小猎犬号航海记》(陈红译“插图全译本”,译林出版社2020)第五章中,达尔文详细记录了他在阿根廷发现和挖掘贫齿类哺乳动物化石(大树懒、箭齿兽等)的情景;当然,他当时的知识背景还无法让他马上认识到这些化石与现生哺乳动物之间具体的演化关系,还需等到回国后交给欧文那样的专家去鉴定和研究。
然而,即令如此,达尔文还是从这些化石与现代同类哺乳动物的相似性上,窥见了生物演化的“大图景”:他初到南美时,发现那里现已完全灭绝的大懒兽等化石与现生的树懒十分相似。他还发现,在巴西的洞穴里,有很多灭绝了的物种,其个头大小与骨骼形态,跟现生的物种也十分相近。同样,当他到了澳大利亚,发现那里的哺乳动物化石,也与现生的有袋类很相似,而与其他大陆上的化石或现生哺乳动物迥异。于是他想:如果这些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为什么上帝在同一个地区两次创造同一类动物?既然第一次创造的动物灭绝了,那至少说明是不太成功的,为什么不加以改进却再次创造与前一次如此相似的类型?达尔文据此推断:物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历了逐渐演化,这些化石中的一些物种或许就是现生物种的祖先。
这就是达尔文见微知著以及非凡的推理能力!按今天的标准,他在还不能准确鉴定化石属种的情况下,就洞悉了它们在生物演化上的意义,这是何等地了不起啊!长期以来,一般人一直都有一个误解:达尔文最早对神创论与物种固定论产生怀疑,始于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考察结果。实际上,这发生远在他抵达加拉帕格斯群岛之前的南美大陆上;当他在那里发现了那些哺乳动物化石时,他就开始产生了上述疑问。正如他在《物种起源》“绪论”一开头就写道的:南美大陆“……的现代生物与古生物间地质关系的一些事实,令我印象至深。这些事实似乎对物种起源的问题有所启发”。显然,南美大陆的古生物与现代生物之间的关系,使他开始心生疑团,而加拉帕格斯群岛不过是最后固化了他的信念而已。
此外,当时演化论面临令他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即是化石的稀缺。尤其是不同种类之间的过渡类型的化石,几乎闻所未闻。他很聪明地将其归结于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并且令人信服地阐明为什么地质记录会如此支离破碎。不仅如此,他又巧妙地利用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来应对另一个令人头痛的挑战,即生物演化缓慢所需要的漫长地质时间从何而来?达尔文指出,正因为地质记录的不完整性,现有的记录只代表了漫长地质年代沉积产物的“冰山一角”,因此从漫长的地质历史来看,时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百多年来的地质古生物学研究进展表明,达尔文当年的观点和理论都是颠扑不破的。
近年来,有些学者持有跟我上述类似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倘若当年小猎犬号的航程是先到加拉帕格斯群岛,尔后才靠岸南美大陆的话,或许这段发现的历史就要重新写了。理由之一是,达尔文当时对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地雀并没有特别地在意,反而是那里的植物更引起他的好奇。当他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各个小岛上看到了形态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植物种类时,他立刻意识到这很可能就是亨斯洛教授当年在课堂上所说的同种植物的不同“变种”(达尔文后来在《物种起源》中称之为“雏形种”)。因此,达尔文仔细采集了这些植物标本,并把它们的确切产地以及采集日期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十多年后,这些植物标本经他的好朋友、著名植物学家胡克先生研究,证实了达尔文最初的猜想。相比之下,达尔文采集各个小岛上的地雀标本时,就没有做同样详细的标记,以至于后来鸟类学家古尔德先生研究时,曾为缺乏确切的产地信息而大伤脑筋。因此,科恩等人写道:“委实,当达尔文最初登上加拉帕格斯群岛时,他显然认为植物比鸟类更有趣,因此他就没有同样仔细地标记鸟类的确切产地。”

达尔文在南美内陆的8次考察
当然,今天我们无法(甚至也不应该)用“后知后觉”来重建达尔文当年的思想路程。我们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他不仅证实了生物演化的事实,而且发现了生物演化的主要机制——自然选择。160多年来,达尔文生物演化论带来的最大冲击力,无疑是把上帝无所不能的创造力彻底否定了。这种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范畴,进而引发了深刻的思想革命。它不仅奠定了生命科学这个大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了全人类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而在发生这一场科学革命的过程中,化石曾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时至今日,尽管分子生物学与基因组学等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古老的古生物学依然在演化生物学中十分活跃,有时候甚至于显得一枝独秀,因为只有化石才称得上是重建生物演化历史的“实锤”证据,并常常被比喻成发现于刑事案件案发现场的“冒烟的枪膛”(the smoking g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