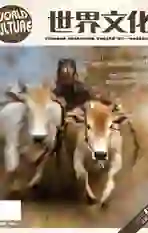热血柔肠 礼赞生命
2020-08-20高丽霞
高丽霞

有吉佐和子(1931—1984)是顶着“才女”称号登上日本现代文坛的。1950年代中期,有吉佐和子与曽野绫子、山崎丰子、原田康子等一批女作家连续推出佳作,引起评论界关注,评论家臼井吉见将这一时期称为“才女时代”。但是,有吉本人对这个称号并不抱有认同感。当时语境下的“才女”一词不乏揶揄之意——评论家们认为这些女作家早早成名,缺少丰富的人生经验做铺垫,仅是靠着头脑和才情写作。对此,同为女作家的圆地文子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过去日本女作家的一个弱点是视野狭窄,而有吉佐和子和曾野绫子等人无论是时代、社会提供的外部条件,还是她们自身的条件,在视野上都有了很大突破。
有吉的创作形式与以往女作家惯常采用的“私小说”确有明显不同,她的作品自由穿梭于古代和现代社会,内容涉及艺术、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有吉在探讨社会人生问题时,并不满足于旁观者式的如实记录,而是从女性视角出发,作为一个有自我主张的女作家,对诸如家族制度、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各类问题提出独到见解。
最早使有吉佐和子受到关注的作品是发表于1956年的《地歌》。在这部作品中,有吉通过描写父女两代人家——菊泽寿久与邦枝在继承传统音乐方面的分歧,敏锐地提出了日本传统艺术在战后新环境下何去何从的问题。此后,有吉陆续创作的《连舞》《墨》《黑衣》《木偶净琉璃》等作品,也都围绕着古典艺术和艺人生活展开。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有吉对传统艺术的关注和兴趣显得有些异乎寻常,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她独特的成长经历中发现端倪。
有吉的父亲是横滨正金银行的高级职员,有长期海外工作的经历。有吉出生前,父亲曾先后在上海、纽约支行工作,因此有吉本人也是成长于异邦的“归国子女”。1937—1941年,有吉跟随父母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生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回到日本。回国后的有吉饱尝到了幻灭感,处在战争阴影下的日本看上去非常粗鄙,只有歌舞伎和和歌山县深深地吸引了她,让她感叹只有那里才存在着她想描写的日本。
这份感触变成了有吉日后创作的动力。除了将对传统艺术的喜爱融入小说创作之外,“和歌山”也作为一个重要符号被纳入了有吉的文学世界。和歌山是有吉母亲的故乡,也是有吉的出生地。1945年,有吉一家从东京疏散到和歌山,与出身于名门世家、行事传统的外祖母一起生活。在此期间,有吉开始注意到外祖母与父母新潮西化作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外祖母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促使她开始思考女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存意义。
传统继承者
1959年,有吉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纪之川》,描写了旧式家族的盛衰兴亡和三代女性不同的人生轨迹。外祖母阿花成长于明治时代,她一生遵循祖母丰乃的教诲和《女大学》提倡的妇德,堪称旧时代贤妻良母的代表。阿花从名门望族嫁入真谷家后,放下门第意识,努力适应新身份,搁置起茶道、花道等高雅修养,全力辅佐丈夫真谷敬策由村长一步步做到众议院议员。同时,她也尽心孝顺婆婆,生儿育女,为实现家族的繁荣倾尽心血。
阿花的女儿文绪成长于大正时代,是创办杂志、出入咖啡馆、号召女权、强调反抗的新女性。文绪激烈反对母亲的生活方式,认为母亲被封建思想束缚,只知忍耐顺从,把自己变成全家人的奴隶,是“全体日本女性的敌人”。不能否认,阿花的确有为了传承家系克己奉献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阿花所维护的“家”与父权制社会强调的“家”是有区别的。阿花将养育子女奉为至高无上的信念,将延续生命视为女人一生最大的成功,富有浓厚的母性思想。阿花期冀的是作为家庭成员安居之所的家,而父权家长制支配下的家比起各个家庭成员,更重视家业和家号的传承。所以,当阿花作为真谷家的主妇迎来封建家长制的解体时,非但没有为此痛苦,反而倍感轻松。
阿花也并不像文绪抨击的那样,是屈服于父权规训的软弱形象,从她订阅全套的《女学杂志》一事可见一斑。《女学杂志》是近代日本第一份女性启蒙杂志,呼吁男女同权和妇女解放。阿花曾以“纪本花子”的本名给杂志投稿,阐述她对家的看法,并获得征文比赛的一等奖。阿花不仅保有自我主张,还依靠智慧为自己在家族制度内争取到了一定权利。举个例子:真谷家的女性纹章是三切横木瓜纹,阿花成为当家主妇后,没跟任何人商量,果决地弃用了这个纹样,继承了祖母丰乃的茑纹,并在女儿文绪结婚时,将茑纹染在了她的嫁衣上。茑是藤本植物,本身柔弱,但攀爬在高大的植物上可以生长得枝繁叶茂。茑纹的寓意契合了阿花和丰乃等女性对男女关系理想形态的理解,也象征了阿花作为女性的生存之道,因此阿花希望将茑纹作为女性纹章让下一代传承下去。阿花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如敬策的弟弟浩策所说,和碧绿美丽的大河纪之川也极为相似,表面看起来安静温柔,却极富力量,一方面想把流经身边的小河都吸纳进来,另一方面又能顺势而为,有勇气汇入水势更为汹涌的河流,以获得更好的发展。
小说结尾,文绪和孙女华子在和歌山城看到纪之川河口已经烟囱林立——正如这幅现代化景象所象征的那样,旧的家族制度以及阿花一心想维系的家族走向消解已是必然。但是,阿花的处世之道被有吉视为女性理想的生存方式,在之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并不断得到升华。

母性问道者
发表于1961年的《香华》仍以母女之间的纠葛为主线展开。有吉刻意塑造了生孩子却不养育的母亲和没生过孩子却极富母性的女儿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须永郁代出生于和歌山的地主家庭,她耽于追求个人享受,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门小姐。丈夫去世后,郁代不顾母亲反对,抛下女儿朋子,和再婚对象私奔到东京。外祖母去世后,朋子好不容易来到朝思暮想的郁代身边,又因为生活贫困,被母亲卖去做艺伎。不久,郁代自己也被第二任丈夫卖入青楼。朋子怜惜母亲,自立门户之后,接郁代至身边生活。然而,郁代不甘寂寞,执意与杂役八郎结婚,跟随他去了大阪生活。此后,郁代遭遇車祸去世,朋子送母亲的骨灰回和歌山的祖父家,却被拒绝。朋子为母亲不平,感叹将那样封建顽固的家“一把火烧掉就好了”。
郁代虽是母亲,却生而不养,对朋子渴望的“母女一体”的亲密关系始终没有给予呼应。而终生未婚未育的朋子,为外祖母送终,照顾同母异父的妹妹,不仅代替母亲尽了义务,还处处照顾母亲,甚至为母亲置办了嫁妆,送母亲出嫁。两人的身份和责任明显发生了反转,尤其是郁代的行为举动颠覆了明治社会以来宣扬的母亲形象,促使人们不由得思考何为母性,克己奉献的母亲是虚构的想象还是真实的存在?
1960年代,日本社会推崇母性神话,与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相呼应,主张“母性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本能”的观点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论调。众多女性成为被社会期待的贤妻良母,承担起照顾家庭、养育子女的责任。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觉醒了的女作家对这种论调极为反感,她们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生育和母性的“憎恶”。1960年,在《新潮》杂志举办的文学座谈会上,三枝和子指出近来女作家们在抱着“杀婴戮子”的文学观写作,她们描写的人物不愿意成为母亲,即使怀了孕也要堕胎。女作家们是想借杀婴“捣毁男人们建筑的母性神话的宫殿”,只有挣脱母性神话的束缚,女性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与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同,有吉一贯认同母性,但又不赞成母性本能说。1960年,有吉在《新女大学》中指出:“母性是最高的德性。但不是生了孩子就自然具有母性。”“作为女性,如果不靠自身的力量去孕育母性,就无法为自己构筑幸福的环境。”《香华》直接体现了有吉的这种观点。郁代对子女漠不关心,对身为母亲缺乏自觉。她不像朋子及世人那样,以曾经的青楼经历为耻,而是从其中发现了享受自由、不受拘束的价值,她选择了作为女人忠于自我欲望的生活方式。而朋子虽然没有生育,但在精神上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可见是否具有母性与是否生过孩子没有必然联系。不仅如此,有吉明确指出女性身上既有母性的一面,也有女性性爱的一面。就像朋子,虽然也曾抱怨母亲,“就是因为妈妈几次结婚,导致我一次婚也结不了,没有办法体会普通女孩的幸福”,但最后她还是接纳、包容了郁代。两种属性的存在都应得到承认,不能被掩盖。有吉对母性的独特解读,为女性选择何种生存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也是《香华》在读者中引起轰动并获得“第一届妇人公论读者奖”的原因。

歧视抗争者
《非色》是1963年开始连载于《中央公论》的长篇小说,被视为有吉社会问题小说的开篇之作。1959年11月,有吉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留学一年。留学期间,有吉开始关注种族歧视问题,《非色》就是以她留学期间的采访调查和所见所闻为基础而创作的。
小说仍是以女性视角展开,四位主要人物——笑子、竹子、志满子和丽子,都是战后嫁给驻日美军的战争新娘。笑子因为嫁给黑人士兵托姆并生下黑皮肤的混血儿梅丽,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遭受冷眼和排挤。连家人也以笑子的婚姻为耻,妹妹要与她断绝关系,母亲劝笑子把女儿送进孤儿院。为了不让梅丽把遭到的歧视(被丢石头、被喊成“黑鬼”)转化为仇恨,笑子决意离开日本到美国追随托姆。
到了纽约后,笑子发现她要面对的身心考验比在日本时更为严峻。托姆住在贫民窟的地下室,只能从事收入微薄的低贱工作。为了维持生计,笑子在日本料理店做服务员,在白人家当保姆。但是无论她怎样努力工作,都改变不了被歧视、被边缘化的命运。
起初,笑子把不公平的境遇归因于丈夫和孩子的肤色,但通过和其他几位战争新娘的交流,她发现肤色不是受歧视的唯一原因。志满子和丽子嫁给了白人,在日本时自感高人一等,来到美国后,优越感折戟,因为所嫁的丈夫是意大利和波多黎各后裔,一样辛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特别是家境优越,像“仙鹤那样美丽”,为了追求浪漫爱情漂洋过海而来的丽子,遭遇最为悲惨。丈夫一家是地位连黑人都不如的波多黎各籍,生计都成问题。丽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忍受屈辱,又出于虚荣心不愿把实情告诉远在日本的父母,最后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丽子的遭遇令人同情,她对美国怀有的虚幻想象和富贵梦也不得不使人反思人性中的弱点。但客观来说,笑子比丽子更为不幸——因家庭贫困而成为战争新娘,在日本时已经饱尝被同胞轻贱的滋味。令人欣慰的是,笑子经受住了生活历练,没有向命运低头,在她身上更能体现出自《纪之川》以来有吉一直在思考的女性生存之道。
笑子做的最后一份保姆工作是在莱登夫人家,莱登夫人也是日本人,嫁给了犹太裔学者,在联合国工作。在莱登夫人的帮助下,笑子鼓起勇气参加了一次研讨会,在会上向与会的非洲黑人诉说托姆的境况,希望从黑人同胞那里得到认同和鼓励。但是,听众们得知笑子的身份后,脸色立刻变了,肯尼亚的年轻人表示黑人问题是美国的内政问题;加纳的年轻人表示美国的黑人是因为懒惰才沦落到这般田地,和他们没有关系。同为黑人的蔑视摧毁了笑子的最后一线希望,她因此彻底体悟到歧视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肤色,而是阶级歧视,“在支配者和被支配者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痛定思痛的笑子开始正视现实,反思自己的处境:“我的丈夫是黑人,孩子也是黑人……在哈莱姆怎么会唯独我是日本人?”如同《纪之川》中的阿花一样,笑子决定彻底放下过去,勇敢地接受新的身份,于是从莱登夫人家辞职,到全是黑人的工厂去工作。
与有吉的其他作品一样,《非色》不强调正面冲突,笑子离开歧视人群,选择作为一个“黑人”活下去,是决意以自己的方式抵制种族歧视的压迫,维护人性的尊严。当她下定决心完全融入到黑人世界时,感到自己身体里喷涌出巨大的力量。这说明笑子从种族、血统观念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获得了精神层面的自由。
生命礼赞者
从1960年代开始,有吉在关注女性生存的同时,逐渐将视野扩展到社会、种族、人类命运层面,写出了多部反映现实问题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发表于1972年的《恍惚的人》聚焦于之前鮮有人关注的阿尔茨海默症,引发人们对衰老、死亡以及晚年生活、养老问题的关注,兼具现实意义和前瞻性,被森干郎赞誉为“发挥了教科书式作用”。
立花茂造在妻子突然去世后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精神恍惚。随着病情的进展,茂造食欲异常、四处游走、大小便失禁、涂抹排泄物等失智状况日益严重。和茂造一起生活的儿子立花信利一家虽然忧心忡忡,但又感到无力招架。儿子忙于工作,孙子要准备高考,照顾老人的重担便全部落在了儿媳昭子身上。
小说写作的1970年代初,伴随衰老而来的阿尔茨海默症还不是广为人知的疾病。之前的文学作品在描写类似症状时,多会使用“发狂”“发疯”“精神病”等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恍惚的人》的出场人物对阿尔茨海默症同样缺少足够的认识,将因病丧失了生活能力和自我意识的老人视为累赘和包袱,并且羞于让外人知道家人的症状。信利作为儿子,完全不敢正视父亲的老态,将父亲视作“留恋枝头的病叶”“高悬在枝头让人摘不到,又不肯自己腐烂的柿子”,对他的病情不管不问。女儿京子听说父亲挺过了肺炎没有死去,竟然有些失望。孙子敏目睹茂造的变化,更是直接对父母说出“你们可不要活到这么大年纪”的无情话语。他们对走向衰亡的骨肉至亲表现出如此的冷漠和拒绝,一方面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带来的损害过于残酷;另一方面,身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人们更愿意陶醉于眼前的繁荣景象,关心如何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少有人关注疾病和衰老,人生终极命题——“生老病死”常常被作为负面事物加以遮蔽,人们很少静下心来认真地思考生命如何落幕的问题。所以,当茂造的妻子猝死去世时,立花一家陷入了慌乱状态,完全不知该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更没有做好和久病的老人共同生活的准备。
在这种环境下,昭子起初也和信利一样,畏惧茂造带来的衰老阴影,而且作为职业妇女,她不愿放弃工作,希望能继续兼顾工作和家庭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经历了一次给茂造洗澡,差点造成老人溺亡的意外事件之后,昭子意识到了被漠然视之的生命的分量。当她发现茂造在回家路上会停下脚步认真地欣赏广玉兰的花朵时,心灵更是受到了触动。茂造虽然是个病人,但也是一个应该被善待的生命。昭子不再把茂造当作累赘,打算依靠自己的努力,好好照顾老人,让他有尊严地活下去。而茂造作为衰老的象征,他的存在给周围人带来的也不完全只是麻烦。昭子在照顾茂造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生命由盛及衰的必然规律,并且深刻体会到衰老比死亡更可怕,更令人绝望,但又无人能够避免。她给茂造买来小鸟,在院子里种植花草,这些改变既是昭子对老人的体恤,也是她对一生努力劳作,老来却只有悲惨晚年生活的反思。一对在立花家借住的年轻恋人将茂造每天看鸟度日的生活视为“仙人一般的幸福”,确切地说,他们欣赏的是在风烛残年时能够得到家人的细心照料,在温情氛围中安稳生活的状态。茂造突然发病,看似是不幸的意外,实则是自然的法则,破除了现代社会的不老假象,让儿女后代认清生命的本真形态。昭子对茂造的接纳以及面对疾病与死亡的态度,给下一代带来了明显影响,孙子敏在祖父去世后怅然若失,对昭子说:“让爷爷活得更久一些就好了。”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有吉花费了10年时间准备,通过调查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小说以此为基础,对病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又从女性立场出发,兼顾护理者昭子的内心纠葛,使故事内容显得更为真实,极富代入感,因此一问世就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恍惚的人》让人们了解到阿尔茨海默症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和给家人带来的沉重负担,从而引发社会对老年生活和家庭护理的重视,给老龄化社会敲響了警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现代社会,患病老人常常被视为丧失了生产力的多余人而遭受各种冷遇。《恍惚的人》中,无论是老人自己还是子女后代,都将像昭子婆婆那样猝死视作一种幸运,这暴露出现代社会追求功利、人情冷漠的一面。有吉借助昭子传达出对生命的关爱与悲悯情怀。
1984年,53岁的有吉佐和子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池田大作在追忆有吉时曾鞭辟入里地评价她是“站在生命的立场上写作”,通过写作“为大多数人做有益的事”。支撑着有吉文学世界根基的,与其说是才气,不如说是热情。她的作品对女性和弱势群体的命运和生存方式给予了热切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察范围逐渐从家族拓展到社会、种族、生命层面,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情结。有吉通过塑造独立自主、敢于担当的女性形象,描写她们为破旧立新而进行的种种探索,表达了她对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融的美好希冀。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