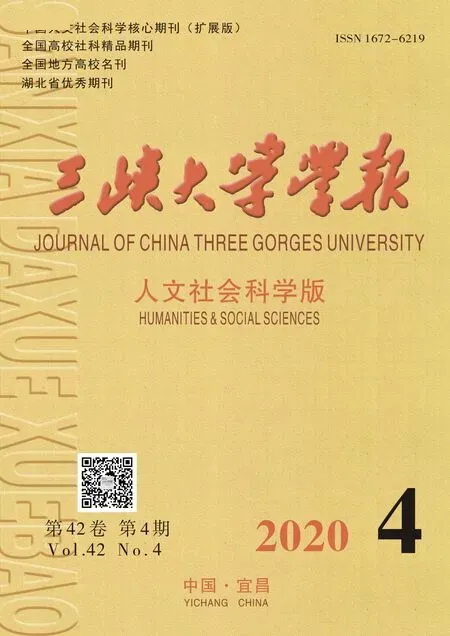论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文化意蕴和形式美
2020-07-14邱紫华
邱紫华
(华中师范大学 东方美学与文化研究所, 湖北 武汉 430074)
2001年2月,在成都市区金沙村地下出土大批珍贵文物,这是继1986年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一遗址被命名为“金沙文化遗址”。考古学家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从文物显示的时代看,“金沙文化”的时限大约为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前10世纪左右),少部分为春秋时期。“金沙文化”是古代蜀国“鱼凫氏”人的创造成果。
在金沙文化遗址东南梅园出土了31件金器,其中有一件用黄金薄片制作的“四鸟绕日旋转飞翔”的饰件格外引人注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印的《金沙淘珍》(2002年)一书中,把这件呈现为标准圆形的金片饰品称之为“金四鸟绕日饰”,后被人们称之为“太阳神鸟”金饰。“太阳神鸟”金饰因其图案设计的精妙而引人注目,它很快就成为成都市的“城市标志”和文化符号。但是,对“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进行深层次文化解读的文章还较少,本文试图从文化人类学和美学的角度加以探讨和解读。
一、“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文化意蕴
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在简约的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这些文化意蕴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金沙“太阳神鸟”金饰显示出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工艺审美特性。
首先,金饰材料的加工方法具有文化人类学上典型的范式意义。
根据20世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远古的“人类在制造石器搜索原料的时候,一定很早便发现有某种‘石块’特别沉重或坚硬,或者有美丽的光泽。这种‘石块’因其美观便被采用为妆饰品。人类最初晓得的金属物便是这种自然状态的金、银、铜等。这种自然状态的金属物便叫做自然金属……自然金属可以拿起来便用,所以被人类采用较早……自然金属大都柔软可捶薄,且有美丽的色泽……其法是先加热于铜块;然后用石器捶击;再烧再击,渐渐成薄片,然后由薄片裁出所要的形状以制造装饰。还有捶得更薄的,则用以包装木、石、骨等物。”[1]金沙“太阳神鸟”金饰片经专家科学测定,其金片的含金量高达94.2%。其制作工艺程序是:先把河沙中淘得的自然砂金熔化成块状,然后再反复加热锤打成薄片。这件金片饰品的厚度仅有0.2毫米(约2张复印纸的厚度);其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重20克。此后,工匠在金片上描绘纹饰图案并根据图样对金片加以刻画切割;现在仍可以看到在“太阳神鸟”图案的周边留下的切割痕迹。由于这件饰品是较薄的金片,应该是贴附在某种器物(可能是红色的漆器)上当作装饰品用。

可见,金沙早期先民——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已掌握了复杂而具有相当难度的金属冶炼和打制技术,也拥有了对金属材料质地和亮丽色泽的审美鉴赏能力。因此,金沙“太阳神鸟”金饰的材料加工方法具有文化人类学上典型的范式意义。
其次,该金饰片的图案设计非常精妙,制作工艺相当精细。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是用镂空的形象表现“四鸟绕日旋转飞翔”。为什么要采取镂空的方式来表达实体的“日”(太阳)和“飞鸟”呢?这是因为古代器物的制作条件和工具简陋(大约是青铜刻刀或玉质刻刀)等因素所决定的。在古代,如果要在器物捶打出凸拱的形象,其难度远远大于镂空的形象。用镂空的手法来表达实体的形象的方法,至今仍然保留在中国民间的剪纸艺术之中。镂空的实体形象同其他颜色,例如红色、黑色的衬底相映衬,形成了一明一暗、双方互补的两种色彩。
第二,“太阳神鸟”金饰展示出了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原始的“寰道观”。
所谓“寰道”即循环之道、循环之理。中国早期先民认为,宇宙和万物的生命都是处在不断的、“周而复始”的发生、存在、消亡之中。华夏民族的“寰道观”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的自然经验而成的,远古时期就已成型。“寰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最根本的观念之一。《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周易·系辞》中就有“原始返终”的思想。《易传·系辞下》说:“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这表明了万物生生不息正是在日月、寒暑、伸屈,即“阴阳”的往复循环中才得以实现。因此,“循环”即“寰道”的思想是《周易》作者心目中最重要的规律之一。
古代的人为了表达心中的观念,往往借用象征比喻的、形象的方式加以表达。《周易·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据此,古代的圣哲形象地把“寰道”比喻为一个封闭的“圆环”。例如,《庄子·齐物论》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寓言》)再如,帛书《十大经·姓争》说:“天道环(周),于人反为之客。”《白虎通义》说:“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返本”(《三教》)。
可以说,华夏民族思维中的“寰道”观念就像一个无形的圆形“思维场”制约着古代各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国文化的诸多品性,或者是循环观念的派生物,或者与其有密切关联。以致从思维方式上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可以用一个圆圈来表示,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圜道文化。”[2]
“太阳神鸟”金饰的整体图案是一个标准圆的形状,就是古代华夏民族“寰道”观念的物化的再现,或者说形象化的表现。众所周知,从金属工艺学的技术层面上讲,在古代,打制标准圆形器物的工艺难度远远高于方形或其他的几何形状。那么,为什么金饰图案要采取标准圆形呢?这一标准圆的形制既然承载的是太阳和神鸟,那么它象征的是什么?它企图表达什么思想意蕴?
古代人把“天”视作为“圆盘”或“穹庐”。直至汉代还有《敕勒川》诗句“天似穹庐,笼罩四野”的说法。可以说,圆形的形制图案不仅象征着“寰道”宇宙观念,而且具体地反映出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对“天”的形象化的认识和再现。太阳和神鸟运行的“天”是具体的、圆形的。“太阳神鸟”金饰外圆图形是象征无限广阔的天宇,是太阳、星辰运行的空间,是神鸟飞行的空间。
第三,“太阳神鸟”金饰图案透露出了古代蜀国“鱼凫氏”人的宗教信仰状态。
原始宗教的重要特点是思维观念中的“万物有灵观”和“万物生命同一观”。原始宗教最主要的崇拜形式是“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太阳崇拜”是生命、生殖崇拜升华出来的崇拜形式——只有当人类观察、猜测到太阳对于万物生命及人类生命的重要性之后,才产生出“太阳崇拜”的信仰。周代的《礼记·郊特牲》说:“大报天而主日”;《汉书·魏相传》中也说:“天地变化必由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可见,太阳崇拜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仍然拥有的一种宗教崇拜形式。“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揭示出了“金沙文化”的宗教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单一自然神崇拜),说明了古代蜀国“鱼凫氏”的人们已充分认识到太阳具有使大自然万物生命复苏和生长的神秘力量。
当然,同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古代蜀国“鱼凫氏”的人们崇拜太阳的同时,也依然保持着对生命、生殖崇拜的信仰(在“泛神”观念支配下的多种自然神崇拜)。与“太阳神鸟”金饰同时出土的8件金质锻制的“青蛙”薄片制品和一个石头雕制的青蛙就是证明。这8件镂空的金质“青蛙”饰片宽约6厘米、长约7厘米;蛙的头部呈尖桃形,压有两个溜圆的凸眼,身体肥大;在身体的外轮廓边上压了些小点,以表示青蛙身上的斑纹。在文化人类学象征性的话语体系中,青蛙是多产、丰产的象征。古代世界各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民族都有用青蛙的形象来象征对生命、生殖多产崇拜的实例。
“太阳神鸟”金饰揭示出了古代蜀国“鱼凫氏”人的宗教信仰状况是从对自然生命、生殖的泛神崇拜转向对单一自然神崇拜的进程中。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的“太阳”和“鸟”的形象是凝结着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宗教思想和审美情感的意象,这些意象既是“实象”,又是“灵象”和“情象”。
我国研究思维活动的著名哲学家刘文英指出:原始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意象,尤其是类化意象。”[3]5类化意象可分为“实象”“灵象”与“情象”。
“实象中的‘象’,都是来自客观世界的。由于它有现实的原形,因而负载着真实的信息。例如,日出日落的空间意象……这些意象都直接关乎着原始人的生存,只有内容基本正确才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3]181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的天宇(圆盘)、太阳、四只鸟就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物象。
所谓“灵象”主要是在巫术、宗教活动中产生的思维意象。“它的特征是,主体虚构了一种非现实的形象,并赋予它以灵性(Animation)。灵象中的‘象’,其材料也来自客观世界。但其整体性质和功能,则是主体想象或幻想的产物。”[3]182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天宇、太阳和光芒、四只鸟都具有了神性,它们都被古代蜀国“鱼凫氏”人赋予了巫术和宗教意义上的生命和灵性,“这既是对精神、意识的歪曲,也是对外物的歪曲。”[3]182
“情象主要存在于有关各种艺术的思维活动中。它的特征是,主体创造了一种生动具体的形象,并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感情。情象中的‘象’,有的来自客观世界,有的则出自想象或幻想,但都是感情的载体。它的功能不在于面向客体而提供信息,主要地是寄托和表达主体的思想感情。”[3]183-184“灵象是主体把自己的‘灵性’赋予一定的形象,因而灵象也总是带有感情色彩。这样,灵象大多同时也是情象,两者的界限很难划分……不过,并非任何灵象都具有审美价值,也不是任何情象都具有宗教意义。对原始人来说,灵象是崇拜对象,情象是观赏的对象,两者仍然是有界限的。”[3]185
有学者指出:“目前不少研究者用太阳崇拜来解释“太阳神鸟”的一切,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但金沙时代已经进入西周,民智已开,不能再把蜀人看作蒙昧时期什么都崇拜的愚氓。能够设计和制作出如此精妙的徽记,那些人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简单的太阳崇拜浅层次信仰上。”[4]笔者认为,不能对古代蜀国“鱼凫氏”人的宗教信仰状况做过高的、过于成熟的解读。20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所有的真正而完整的原始宗教,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是一种对于丰收的崇拜。一个原始社会所崇的主要是他们自己的生长力量,或是繁殖子女,或是生产粮食,而对于破坏力量的崇拜现象则或是次要的,或是根本不存在。”[5]不仅如此,人类的信仰,尤其是东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往往具有延续性。大量的事实证明:某一民族的宗教信仰非常发达之后,却仍旧保留着某些原始信仰的痕迹和习惯。古埃及文明进入“王国时代”后,文明非常发达,但还存在着浓厚的太阳崇拜;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就被臣民称为“太阳王”;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狂热的“太阳崇拜”以及中国人现今的生活中还保留有浓厚的巫术宗教习俗(灵魂轮回、烧纸钱、算命、占卜、放“蛊”等)就是证明。
第四,“太阳神鸟”金饰显示了古代蜀国“鱼凫氏”人的时间观念。
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讲,象征的本质就是“以此物比此物”;象征的特点往往是“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说象征是就两事物之间某方面的相似性、相同性、可比性加以比附和暗示,并不是完全的相似和相同。因此,象征的意义具有多重性、多面性、多义性。人们对于某一事物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象征。同理,“太阳神鸟”图案中的象征性也可以是多重的、多义的,既可以认为图案中的“四只飞鸟”是神话中帝俊的四只鸟,也可以认为外层均匀分布的四只“神鸟”分别象征着一年中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回。既可以认为“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的内层12道芒纹象征着一年中的12个月,又可以认为设计制作者是为了满足图案“对称”之美的需要。
如果从象征时间的角度看,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对“年”的概念和“年”的分期的观念通过12个芒纹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它们通过不间断的周而复始旋转着光芒纹样展现。这一图案不仅传递出了古代蜀人太阳崇拜的宗教观念,而且也曲折地暗示出当时古蜀人已经拥有了明确的年、四季、12个月的时间观念。与“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平行存在的《周易》对一年的分期有明确的表述。天“期”(年)是一岁;一岁分“四时”;“四时”有寒暑;以“地”来说,一“期”中有生有成,有荣有枯。天、地、四时是变化更迭的,“太阳神鸟”用四只鸟和太阳的形象就是象征天宇是不断变动的、循环往复的。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通过图形来表达年、季、月的传统,例如,古埃及人就用棕榈树图形代表“年”(古埃及人每年剪一次棕榈树叶)。
第五,“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显示了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原始的质朴的带有哲学意味的“阴阳”观念。
古代人的原始思维特点主要是认为“万物有灵”“万物同一”“物我不分”,因此,“物我互渗”“物我轮回转化”。只有当人们已觉察到、认识到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和一切现象都是“有同又有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存在事实,并且,认识到“差异”才是万事万物存在的“真像”时,才会出现“对比”“对称”“衬托”的抽象观念,并采取形象的方式加以表达。“阴阳”观念就是观察到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男女、干湿、大小、冷热等对立、差异现象后的表达。“阴阳”就是中国哲学对于自然现象中的对立、对比、差异、对称、互衬的另一种话语的表达。“阴阳”观念的确立说明人们的思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达到了对事物认识的新的高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阴阳”观念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
从“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和形象设计看,古代蜀国“鱼凫氏”人已有了明确的对立、对比、对称、互衬等鲜明的“阴阳”观念。
其一,在古代中国人就采用数字(奇数、偶数)来表示“阴阳”观念。古代的“三易”(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和《周易》)中,“阳爻用‘一’这个符号表示,因为‘一’是奇,奇是阳数。与阳爻相对应的阴爻用‘――’这个符号表示,因为‘――’是偶,偶是阴数。”[6]在四川,用数字代表“阴阳”观念的实例,很早就体现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上,例如著名的“青铜神树”上就铸有10只神鸟的实体形象。
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一个圆形的焕发着尖齿状的光芒的太阳(阳)与四只细长条形的鸟儿形象(阴)形成了“形象”上的鲜明对立、对比。由此,可以证明,同《周易》时代较为相近的古代蜀国“鱼凫氏”人也同样采用“一”(奇数)个太阳代表“阳”和四只(偶数)“神鸟”代表“阴”的观念。2002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印的《金沙淘珍》一书中,还公布了在金沙出土的另一件器物——“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该璧面上均匀刻有“三只飞鸟”。这也是用“奇”数来象征“阳”的观念的证明。
其二,太阳与神鸟的旋转运动的方向上看:向右旋转的太阳同向左旋转飞翔的神鸟的方向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正是阴(神鸟)阳(太阳)的逆向旋转飞行,呈现出阴阳的永恒性运动。这一设计图形除却它的象征意义外,从形式美的角度讲,这一图案改变了同向飞行在构图上的“单调性”,使总体图像显得生动、流畅、活泼。
其三,在“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金色的圆盘同镂空的实体形象所衬托的颜色,例如红色、黑色的衬底相映衬,形成了一明一暗、对立互补的两种色彩。
二、“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独特的形式美
器物审美主要是对器物样式、形式因素的审美。这种美,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形式外在美与感性材料的抽象统一的外在美。”[7]172从美学艺术学的角度来讲,最高妙的艺术形式有两种:
一是“简单的形式蕴含丰富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崇尚简易是人类古老的思想传统,越是原始的艺术越显得简易,但是简易绝非简单。《周易》就尚简,以简洁明快为好。《周易·系辞上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这是说,“容易”的事理就易于让人知晓,“简易”的事理就易于让人遵从。一个人能把“容易”“简单”的原理明白了,那么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就可以知道了。中国传统美学把这高水平的、“简易”的艺术形式表述为“以一当十”“以少总多”“以近指远”“咫尺天涯”。从现代设计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构思高妙的徽记、标识、图案都具有构图简单明快而含义丰富的特点。
二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是20世纪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极力推崇的“美的形式”。现实生活中,任何实体和事物都有具体的形状、形态、形式,但它们不一定是“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主要指那种潜藏着创造性智慧的“艺术的形式”,它以婉转含蓄的方式承载着丰富思想情趣。“有意味的形式”的审美特性在于形式中所蕴藏的美,需要“细细品味”,反复咀嚼才能获得。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很接近中国古典诗学所推崇的诗歌语言:“言有尽而意有余”“言有尽而意无穷”或“意境幽远”等审美形式。
“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然而,就在这简单的图形中,却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象征意蕴。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具备了美的艺术图案两个重要的形式美特征。
第一,在简洁明快的构图形式中体现了多个形式美的要素。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设计精妙:在一个金质的薄圆片上,仅镂刻有太阳光芒和四只飞鸟的形象,构图简洁明快,形象鲜明突出。
一般来说,最容易引起人们美感的自然事物或器物的形式都具有下面这些“形式美”的要素:
首先是“秩序感”,即“整齐一律”。“整齐一律”“是同一形状的一致的重复。”[7]173“太阳神鸟”金饰之所以吸引人们审美的目光,主要在于它具有简洁的构图和鲜明的秩序感。其构图表现为在黄金质地的圆盘上只有一个太阳和四只飞鸟。它表现出的秩序感,就是很少的物像却分布均匀,位置准确。例如,“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中的太阳光芒分布精确,都呈均匀、一致的渐开线形式展开;四只翔鹭鸟的形态一致,排列整齐一律,神鸟的形状和飞行方向完全一致,这就显示出整齐一律之美和强烈的秩序感。
其次,是“平衡对称”,“要有平衡对称,就须有大小、地位、形状、颜色、音调之类的定性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还要以一致的方式结合起来。只有这种把彼此不一致的定性结合为一致的形式,才能产生平衡对称。”[7]174
对比,就是突现差异的重要手段。“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有着强烈的对比感。例如,太阳的圆形、齿状同长而直伸的飞鸟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阳同飞鸟彼此方向逆行的对比;太阳和鸟儿的实体色彩的对比。众所周知,在视知觉理论中,色彩拥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在镂空的太阳与飞鸟的实体形象上,其底色可以衬托任何一种色彩,这就使实体形象拥有多种色彩的可能。
在“太阳神鸟”图案中,平衡对称不仅表现为:呈顺时针旋转状态的太阳光芒同四只神鸟呈反时针方向飞行的差异构成了明显的对比、对称和平衡之美,而且“太阳神鸟”金饰片的构图非常富于对比性的节奏感、动感。“太阳神鸟”金饰片通过镂空的实体形象表现,使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的圆圈是太阳;太阳圆周的边缘等分为十二个尖齿光芒;光芒呈现出向右旋转的“渐开线”。众所周知,渐开线上的“点”的轨迹是呈曲线运行的,像旋涡一样展开,显示出极强的动感。外层的图案是由四只呈均匀分布的、同类的镂空的鸟,它们同向飞行,构成了一个圆圈。四只飞鸟的形体略呈弯曲的直线同太阳逆向飞行,使物像的运动产生交错和变化。
再次,形式美要求显现出“差异中的和谐”。“和谐一方面见出本质上的差异面的整体,另一方面也消除了这些差异面的纯然对立,因此它们的相互依存和内在联系就显现为它们的统一。”[7]180-181这就是说,“和谐”是包含有着差异因素的一种统一。这种统一不是生硬地捆绑在一起,而是要表现出差异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联系。“太阳神鸟”金饰片中的太阳、神鸟的形体差异是明显的,但是通过不同的形体和相反的旋转使两个物象表现出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生动地融合为一个富有视角冲击力的图案。
第二,“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造型流畅生动、富有动感和变化。
为什么说“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造型流畅生动、富有动感和变化呢?其秘密在于古代蜀国“鱼凫氏”的设计师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智慧,在构图上取得了“化静为动”的效果。“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化静为动”的手法有二:
一方面,把鸟原本的团块的身躯加以了“线性”化的处理。图案中四只鸟的造型很像是成都地区常见的“白鹭”(翔鹭);四只鸟引颈伸腿,翅短尾小,鸟喙微张,三个趾爪向内紧缩。鸟儿的翅膀通过变形而显得格外短小,使鸟儿的身体拉长成一条“线”,从而让鸟儿的身体形态从团块状变形为“线”性结构,使鸟的形态更显细长、轻盈,更富有动感。
另一方面,设计师把太阳的光芒处理为向右方(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渐开线形状。在几何图形渐开线中,“点”的生成轨迹是沿圆弧线逐渐展开的曲线。曲线是最富于变化的、动感的线,整个图案的生动感由此而生。正是这一巧妙的构图,使“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显得生动流畅,极富动感和变化。相比较,古代欧洲民族在铜板画或器物上绘制的太阳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在铜鼓上铸造的太阳光芒图案,基本上都是沿太阳的360°圆周,呈现为标准的等腰三角形的齿形。这种造型虽然显得精准工整,但在视觉审美上却显得较呆板僵化。这就是“太阳神鸟”金饰图案造型为什么显得流畅生动、富有动感和变化的秘密所在。
通过上述论证与分析可以充分说明,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是古代中国器物图形的设计中十分罕见的“美的图案”,甚至可以说是空前而绝后的艺术图案。
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不仅在简约的图案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而且“太阳神鸟”图形是言简意赅的“美的形式”,是典范的“有意味的形式”,它以极其简洁的形式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思想,储存了多重的信息。综观中国古代器物中的“美的形式”或者说最“完美的图形”,大概只有“太极(阴阳鱼)”的图案达到或者超越了它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