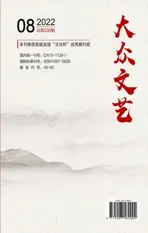柏拉图《会饮篇》中三种神话言说的比较研究
2020-07-12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550000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550000)
在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书著中我们可以发现神话元素的痕迹遍布于其作品之中。因此,思考与分析柏拉图著作中的神话对于研究柏拉图著作至关重要。
柏拉图的《会饮篇》是其著作中唯一一篇颂神的作品,同时也是神话元素占据了很大篇幅的一部作品。六位主要的讲辞人,除了医生厄里什马克的讲辞神话色彩略淡之外,其余五人的讲辞都含有较为浓厚的神话成分。
在这篇文章中体现了三种不同的神话言说方式:第一种是智术师的神话言说方式,他们并未构造新的神话,而是将传统神话作为论据来支撑自己颂词的中心观点。智术师对神话的自觉运用更像是将其当作是一种与修辞术具有相同性质的话术工具。第二种是诗人的神话言说方式,他们从各自的思维模式出发创制了新的神话。但在柏拉图看来这样的神话并不具备真实性。第三种是哲人的神话言说方式。哲人也构造了新的神话,并在神话言说完毕后引导朝向美本身之景观的逐渐上升。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展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具有真实性的神话范式:只有与哲学话语相一致的神话言说才具有真实性。由此可知,柏拉图并非完全排斥神话这一创作方式,而是反感作为精神指引却充满谬误的那类神话。弥合了局限性的神话也能与辩证法共同构筑真理世界。
一、神话言说:作为话术工具
斐德诺是《会饮篇》中第一位对爱神进行颂扬的言说者。他认为爱神之所以值得颂扬,一方面是因为爱神是最古老尊严的神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爱神能为人类带来德性与幸福。
在自己的颂词中斐德诺提及了阿尔刻提斯、俄耳浦斯和阿喀琉斯的神话故事。阿尔刻提斯是唯一愿意替代丈夫死亡的人,而阿喀琉斯在明知道杀死赫克托耳自己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前提下依然选择去营救他的情人帕特罗尔克斯,替他报仇。在斐德诺的解读下,阿尔刻提斯和阿喀琉斯的神话故事的意义被诠释为:自我牺牲精神是成就爱欲的最高标准。但正如后文中弟俄提玛对斐德诺真实目的的揭露:“除非你彻底了解我所说过的话,想通了他们那样奇怪地利欲熏心,是为着要成名,要流芳百世。为着声明,还有甚于为着儿女,他们不怕冒尽危险,倾家荡产,忍受痛苦,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你以为阿尔刻提斯会做她丈夫的替死鬼,阿喀琉斯会跟着帕特洛克斯死,或是你们自己的科德洛斯会舍身救国,为后人建立忠义的模范吗?如果他们不想博得不朽的英明,现在我们还在纪念英明?没有那回事!”1可以看出斐德诺心中所憧憬的爱欲并不是真正的爱欲,而只是披着爱欲的高尚外衣所捕获的种种好处,如人世间的荣誉以及不朽的声名。在斐德诺那里人的羞愧与崇敬之心不是源于自我意识的反思而是源于外因的刺激,爱欲力量的终极来源不在于真理与内疚,而在于由他人的观看所产生的羞耻感。“在第俄提玛的讲辞中,阿尔克提斯和阿喀琉斯的自我牺牲,不是因为他们渴望死亡,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永垂不朽。那些拥抱死亡的人所挣得的荣誉,被斐德诺理解为爱欲的见证。”2
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在斐德诺神话言说中可以看到,虽然俄耳浦斯爱自己的妻子欧律狄刻,但他并不会为欧律狄刻赴死。而阿喀琉斯却愿意为自己的爱人帕特洛克罗斯献出生命。“斐德诺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关于获利的利益的观点,是关于获利的计算的观点。斐德诺还说爱若斯是最古老的神。最古老意味着最值得崇敬。但何以爱若斯最值得崇敬?因为他对情伴最有用,对像斐德诺这样的人来说最有用。”3尽管情人体现着爱若斯的神性,但爱人才是利益的最终获得者。斐德诺对爱欲的思考中夹杂了很多自己的私欲。
从斐德诺的神话言说方式中可知:尽管希腊传统神话可以被传承,但对它的理解并不是重复与保持不变的,由于对传统神话的解读并不存在一个官方的标准答案,这就暗示了对于传统神话意义的解读具有含混价值、多重性甚至具有危险性。人们可以利用已存的文本和故事,向着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阐释。
泡赛尼阿斯同样也是站在利己的角度进行神话言说。他在正式开始颂扬爱神之前便先对爱神的身世进行划分。根据雅典官方宗教礼仪的公共意见他将爱神分为高尚女爱神与凡俗女爱神,认为只有拥有父性的高尚女爱神才值得颂扬,而依靠男女生殖繁衍的凡俗女爱神并不值得颂扬。
泡赛尼阿斯利用雅典官方宗教礼仪的公共意见的公信力让人们承认爱神具有两个身世,再进一步根据自己的立场引导听众相信只有高尚女爱神才具有颂扬价值,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为男童恋的合法性找说辞。他在其后的颂词中说:“至于天上女爱神的出生却与女的无关,她只是由男的生出的,所以他的爱情对象只是少年男子。”4他想通过自己的辩护让不合法的行为变得合法,实质是在为他自己的行为争取自由。
斐德诺和泡赛尼阿斯是在《会饮篇》中出场的两位智术师。二者的神话言说方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也有一定的相异性。相似性在于,首先,他们都并未构筑新的神话,而是沿用传统希腊神话,将希腊神话当作论据为佐证自己的中心观点而服务。其次,二者都是站在利己的角度对神话进行解读与运用。相异性在于,斐德诺站在爱人的角度进行言说,而泡赛尼阿斯则是站在情人的角度进行言说。并且,虽然二者都身处利己立场进行神话言说,但对神话的处理方式却不尽相同。斐德诺将神话当作例子,他从自己的角度诠释神话并用于支撑自己言说的中心观点。而在泡塞尼阿斯颂词中,神话所承担的是“抛砖引玉”的引言功能角色,其旨在为后面所需论述的观点——“男童恋是合法的”——寻找一个合理的出发点,为其不法目的的合法性寻找出路。但二者神话言说的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站在利己的角度宣扬“利己之爱”。
二人对神话的自觉运用更像是将其当作是一种与修辞术具有相同性质的话术工具。“在智术师手中,修辞术可以为一个论题的任何一方说话,修辞术并不受真理的束缚。”5而神话之于智术师也有同样的作用。当持情人立场的泡塞尼阿斯运用神话进行言说时,神话便为情人作辩护。而当身处爱人立场的斐德诺运用神话言说时,神话又会成为为斐德诺的话术工具。
二、神话言说:“丑”的神话与“美”的神话
《会饮篇》中出场的两位诗人,一位是肃剧诗人阿伽通另一位则是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两位诗人并未沿用传统神话,而是创制了新的神话。
阿里斯托芬所创造的神话呈现出溯因式的叙述风格,这种风格多见于许多民间故事之中。溯因式叙述风格是指通过讲述事物的起源,让听者在讲述事物起源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事物所具有的特性。阿里斯托芬并未像之前的言说者一样颂扬爱神为人类带来了哪些好处而是另辟蹊径言说“爱欲是如何生成的”。“溯因式的叙述可以利用古时候人们想象中的历史来阐明当前而非往昔事物的存在。在民间故事的层面上,溯因论教导孩子们豹是长斑点的猫科动物,而且(虚假的)演化的魔力把能够将豹与斑纹猫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铭刻在孩子的记忆里。”6溯因论的叙述风格能在言说过程中将所述事物的特点展现出来。阿里斯托芬的神话能让我们回忆起爱欲的显著特征:爱欲是缺失,因而追求完整性,且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完整性和统一性,所以需要通过性的舒缓让人们可以继续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阿里斯托芬的诗人神话尽管所讲述的是远古人民反抗天神,被神惩罚导致后来一直在找寻的故事,但却比前者厄利什马克的科学阐释更好的表现出爱欲的特征。可见运用神话阐释诸如灵魂、爱欲等非理性话题时会比科学阐释或纯粹的理辞更具优势。
阿里斯托芬的神话言说方式与其喜剧诗人立场也有着亲缘性联系:第一,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充斥着大量粗俗的元素,而在《会饮篇》阿里斯托芬所讲述的神话中也得到了再现。比如性的话题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与神话中都有大胆的体现。第二,阿里斯托芬察觉到人是具体而特殊的存在,他曾在其剧作中指出自然的必然性,但人类生活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并不严格完全遵守必然性的事物,否则人与禽兽别无二致。而在《会饮篇》的神话中阿里斯托芬对性的理解也是如此。首先人类生殖繁衍的自然必然性证明了性的存在,但性又不仅仅是生殖繁衍的手段,否则人与动物别无二致。于人类而言,性还具有舒缓欲望缺失的功效,让人们可以继续投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正如阿里斯托芬所说,宙斯不愿看到人们死掉,于是创造了性,虽不能给予人所期冀的完美结合,但通过梳泻欲望,人们又可以去关心“人生中的其他事物”。
与阿里斯托芬所构筑的神话与其喜剧诗人立场有着密切关联一样,阿伽通所构造的神话以及其神话言说方式与他肃剧诗人的职业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肃剧诗人是诸神的创造者。”7诗人对美的爱慕使他们创造了诸神。肃剧诗人阿伽通也在爱欲与美的指引下创造了关于爱若斯神话。阿伽通是在场所有讲辞人中第一个将爱神本身作为主题的讲辞人,他赋予了爱神自在自立的形象,并且将所有最美好的品性都加诸于爱神身上。
但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在其著作《论柏拉图的〈会饮〉》中所说:“他(阿伽通)作为肃剧诗人,却跟阿里斯托芬作为喜剧诗人不同。他的虚荣,他的伪善,他的柔软以及过于明显过于外露的漂亮讲词,都表明他的层次较低。他所描绘的爱欲是娇嫩的,他自己关于爱欲的讲词亦是如此,其中没有任何粗粝的东西。”8他所讲述的神话呈现出一个美丽的姿态:选择优美的词汇构筑神话的场景,并赋予其神话人物最完美的形象。对比前者阿里斯托芬所讲述的神话,就会发现其所讲述的爱欲太过美好与一帆风顺,这样的爱欲摆脱了一切苦痛,苦难能引起觉醒与反思,这样的爱欲缺乏激情。
尽管阿伽通的神话在内容上并不如前者阿里斯托芬,但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结束演讲后却收获了比前者更加热烈的掌声。这是因为,首先,他的颂词既讲究文采, 又具有条理性与美的形式。其次,他的颂词追求让听众“易于理解”,并没有讲述过于承重与深刻的哲理,只是将美好品质进行堆砌。并且他善于掌控自己的声音与节奏,在演说时极易煽动听者的情绪,让听者接受认同。所以尽管他并未真正触碰到爱欲的实质,但爱伽通运用他颇具迷惑性的言说方式赢得了比前者阿里斯托芬更多的掌声。
但这看似十分具有条理性并且非常优美的神话言说实际上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漏洞。阿伽通曾在其颂词中说:“爱神在本质上原来就具有高尚的美与高尚的善,后来一切神人之间有同样优美的品质,都因爱神种下善因。”9他的颂词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爱欲即善与美。但由此又会产生一个悖论:慕求的对象是欲望生成的必要条件,爱欲作为欲望的一种类型同样也需要一个慕求的对象。美与善是爱欲慕求的对象而不应该是爱欲本身。由此可见,阿伽通的神话言说为了追求修辞上的成功而忽略了神话与逻辑间的相互冲突。阿伽通在他看似有条理且形式美丽的神话故事的虚掩下,鼓吹着自己的宣称。基于颂扬的目的将一切美好的品质都赋予他辞神话中的人物,却从未考虑过所颂的事物是否能与逻辑相契合。
通过对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和肃剧诗人阿伽通的神话言说方式的分析,可知,神话在阐释非理性话题时具有优势。但正如前文所述,二人所构筑的神话与二者的思维方式特性有着密切联系,这意味着话语域与思维域具有同质关系。话语的陈述也可以看成是其思维的运用。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神话中出现了粗粝丑陋的元素,其神话展现了对人类自然性的关注,但却缺少了对于爱神神性的关注。而在肃剧诗人阿伽通的神话言说中,对爱神神性的高度理想化赞颂使最基本的自然属性在其颂词中没有得到丝毫体现,并且对神性不假思索的虚假赞颂也正是其颂词显得轻浮的重要原因。在他们二者之后出场的苏格拉底对二者爱欲基本观念的驳斥完美的消解了诗人神话的构建,在苏格拉底的神话言说中,爱若斯既不是自然属性也不是神性的极端代表,而是居于二者之间,同时拥有两种属性的命相精灵。
三、神话言说:内化于真理世界
苏格拉低的神话言说方式融合了智术师与诗人二者的言说特色,既构筑了新神话,同时还将新神话用于颂词之中辅助其爱欲观的阐释。苏格拉底的神话言说弥补了传统神话的不可证伪性与不可论证性,创造出与哲人思维域相一致的哲人神话,并将这种神话内化于真理世界之中。
法国学者布里松在其著作《柏拉图的神话观》中对神话的不可证伪性进行过分析。他认为,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语言首先被界定为是一种可证伪的话语,在《智术师》中,埃利亚客人将话语界定为三个基本要素:1.名词与动词的相互搭配是构成话语陈述的最基本形式。2.话语陈述总是与某一事态相联系。3.由此就可以判断该陈述的真伪性。“如果名词与动词所承载的关系恰当,那么其搭配为真。反之,则搭配为伪。”10关系的界定一般由主体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什么行动来判定其真伪。这也就意味着,在可感世界中判定陈述真伪必定有时间性的限制。因为某物在一段时间中呈现出真性质的话语陈述,在另一段时间中可能就变成了伪陈述。例如,“天正在下雨。”天现在正在下雨,但过去与将来并不是都在下雨。因而只有当指称能够被陈述者亲历或者指称与陈述者处于一种当切亦或是足够近的状态时,这类话语与指称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才能被证伪。
而传统神话不能够被证伪的原因就在于:首先,神话所描述的都是关于遥远过去的事情。遥远的过去与遥不可及的将来超越了陈述的时间性限制,因此不能被当作是有效的指称。其次,神话的指称,比如灵魂等话题是人类的理智与感官无法触及的话题,如此也就不能准确的判断所指涉的内容。因而神话是不能够进行证伪的话语形式。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又会发现,柏拉图本人有时会用真实与虚伪来界定神话。比如在《王制》中柏拉图认为神话是虚假话语,而在《高尔吉亚》中又被看作是真实话语。这暗示了,柏拉图判断神话的真伪有其自己的标准。在柏拉图处“神话的真实性取决于它是否与哲人关于可知形式的话语一致。”11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知形式的话语是与感官世界中的可感事物相对的概念,是构成真正现实世界的样式,它们不可更改,具有永恒性并且总是为真。因此,在柏拉图的观念中,神话只有与哲学话语相一致时才具有真实意义。
在苏格拉底所讲述的神话中可以看到神话与可知形式的统一性。苏格拉底在言说神话之前先对爱欲的普遍本质概念进行了界定:1.爱需要有对象,即爱美。2.爱并不是完满,相反,爱是匮乏。3.爱是欲望,是想要拥有自己的缺失之物。概念表述的是普遍性的东西,因此包含着真实性于确定性。爱欲在此处即是指用心灵或理智所看到的具有“一”的统一性和“存在”的实在性的观念,是一种普遍的共相与形式。因而苏格拉底所言说的神话是在“爱欲”概念的指导下所构建的神话。所以,这个神话与柏拉图的哲学理念相一致,具有真实的意义。
论证性话语由于所遵循的是理性秩序的推导,因而其结果指向一个必然性的结论。而与论证性话语相对立的叙事性话语则呈现出非论证性的形态。因为在叙事性话语中,其内部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呈偶然组合的状态,这种偶然组合的状态是指某一门叙事性话语讲述事件的方式就是将叙事之外的片段化、零散化与复杂化的感官经验世界编制在一起,制造出一种整体性、统一性与真实性的完美幻觉,因而其话语内部的构成要素呈现出偶然组合状态。而神话作为一种叙事性话语,其叙事的方式就是对神话之外的片段零散的感官经验世界加以想象化处理并缝合,由此营造出一种内时空的幻觉。神话的叙事方式体现了叙事写作的虚假性,同样的虚假性也体现在一样具有叙事性结构的小说创作之中。但同时,神话还需与同样具有叙事性特征的历史语言相区分,历史语言虽也属于叙事性话语,但其所展现的是已然发生过的必然性事件,因而与一般的叙事性话语不同。
因此,神话的不可论证性体现在:1.其内部结构要素是以偶然组合的方式构成。2.其最终的结果指向非必然性。而在苏格拉底所讲述的神话并不是根据搜集感官经验世界中片段化、碎片化的信息加以提炼拼接缝合而成。他的创作方式是先将爱欲的本质进行澄明,再以经过澄明的概念推导构建出神话。
其推导过程首先是梳理出爱欲的三大普遍本质,在此基础上创制出由丰饶神和贫困神所生的爱若斯的神话。神话结构内部的每种要素都根据爱欲的本质理性构建:第一,因为爱若斯慕求美与善就意味着他并不拥有美与善。而尽善尽美是神的根本特性。因此缺少美与善特性的爱若斯就不是神明。他的真实面貌是介乎于神人之间的命相精灵。第二,因为爱若斯追求美与善,那么必定美要存在于他之前,因此爱若斯必定不是最古老的。最后,他既追求美与善这样美好的品质,又缺乏这两个品质,说明他有一个贫乏的母亲和一个常在想法上追求美与和谐的父亲,即贫乏神与丰盈神。苏格拉底所言说的神话体现了哲人话语域与思维域的统一,具有可论证性的结构特点。
综上所示,能够看到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多讲述的神话弥合了传统诗人思维域所构筑的神话的局限,书写了一个他心目中认为真正正确的神话,这一神话语言与其哲人的思维域相一致。
但苏格拉底为何要运用神话进行言说?爱若斯的神话与后面的美善理念的关系又是什么?
其原因在于,“人类的理性只能把握那些一直存在、永不改变的东西;只能把握永恒的样式或理念。如果有谁想要谈论变化和生成,那么它只能通过讲述一个故事,一个神话来这样做,这个故事或神话的诸连续部分反映和模仿了变化。”12理性所对应与思考的是永恒不变的样式或概念,而神话则能反映出变化与发展的过程。并且神话能够以形象的方式展现世界的源初情景,将人类在经验世界中获取的诸多经验整合到一个统一的视野之中。当苏格拉底需要阐述“爱若斯的生世”即“爱欲是怎么生成的以及具有哪些特征”时,运用神话能够更好的表现这一生发的过程并加深人们对于所描述事物特征的认识与印象,因而苏格拉底在颂词的开头部分讲述了一个神话。
但正如上文所述,柏拉图对于神话的真伪有其自己的判断标准,即神话要与其哲学话语相一致。因而在《会饮》中,苏格拉底重新构筑了新的神话,这一新的神话反驳了前面言说者的虚假讲辞,并将“真理”以神话的方式讲述出来。但如果苏格拉底的神话是为了展现其哲学真理而服务,又为何不像智术师一样选择传统神话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佐证?原因就在于如果运用传统神话佐证自己的哲学思想,那么与此同时哲学就会成为神话的阐释工具,神话将与哲学一样都会成为真实的栖身场所。
同时如果细究我们会发现,在苏格拉底的神话言说中似乎也存在着逻辑漏洞。
既然神都是自足的,那为何爱若斯的母亲贫乏神要去追求爱若斯的父亲丰盈神并生下爱若斯呢?其实并不矛盾,正如前文已提到,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与可知形式相统一的神话才具有真实性,苏格拉底所讲述的神话已论证了其真实性,这就意味着苏格拉底的神话与可知形式相统一。在苏格拉底的神话中所出现的人物不能仅将其当作一般的人类高度理想化的那类神话人物,而应与柏拉图理念世界中的理式相联系。因此,贫乏神并非不自足,贫乏神在她的理式“贫乏”之中是一直处于自足状态。
苏格拉底在神话言说完成后并未结束其讲辞,而是引向了美本身景观的逐级上升。苏格拉底的神话具有了和命相精灵爱若斯一样的“居间者”意味。“居间者”体现了一种过渡状态且具有引导沟通的功能项。在其后的讲辞中,爱的隐喻性概念被放到中间,爱并不是人的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引导人向美向善。如此,爱若斯神话便内化于柏拉图的真理世界之中。
四、结论
《会饮篇》是柏拉图著作中唯一一篇颂神的作品,柏拉图在这篇作品中通过展示智术师与诗人的神话言说方式,揭露了传统神话的局限性以及在诗人思维域下所构筑的神话的不真实性。并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展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具有真实性的神话范式。因此,笔者认为,柏拉图并非排斥神话这种创作方式,而只是抗拒不具备真实性的神话。弥合了局限性的哲人神话也能和辩证法一同为构筑真理世界服务。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虽然《会饮篇》是一篇颂神的文章,但苏格拉底所颂扬的爱若斯并不是真正的神,而是一个介于人神之间的命相精灵。但为何柏拉图要选择非神的爱若斯进行赞颂呢?笔者认为,柏拉图并不仅仅想停留于颂扬层面,留驻于表面的颂扬只会像前者阿伽通一样盘桓与虚假浮华的赞美之中。柏拉图颂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引导人们去攀登能够抵达美善世界的阶梯,而只有拥有爱慕美善的内在驱动力才会尝试去攀登抵达美善的阶梯。
注释:
1.[古希腊]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教研出版社,2018年,第224页.
2.[美]罗娜·伯格著.贺晴川,李明坤译.《为哲学写作技艺的一辩—柏拉图斐德诺疏证》[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32页.
3.[美]列奥·斯特莱特著.邱立波译.《论柏拉图的<会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4.[古希腊]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教研出版社,2018年,第194页.
5.[美]尼柯尔斯著.王双洪译.《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王制>义疏:一场古老的战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102页.
6.张文涛选编.董赟,胥瑾等译.《神话诗人柏拉图》[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7.[美]列奥·斯特莱特著.邱立波译:《论柏拉图的<会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8.[美]列奥·斯特莱特著.邱立波译:《论柏拉图的<会饮>》[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9.[古希腊]柏拉图著.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教研出版社,2018年,第210页.
10.张文涛选编.董赟,胥瑾等译:《神话诗人柏拉图》.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1.张文涛选编.董赟,胥瑾等译:《神话诗人柏拉图》[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12.张文涛选编.董赟,胥瑾等译:《神话诗人柏拉图》[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