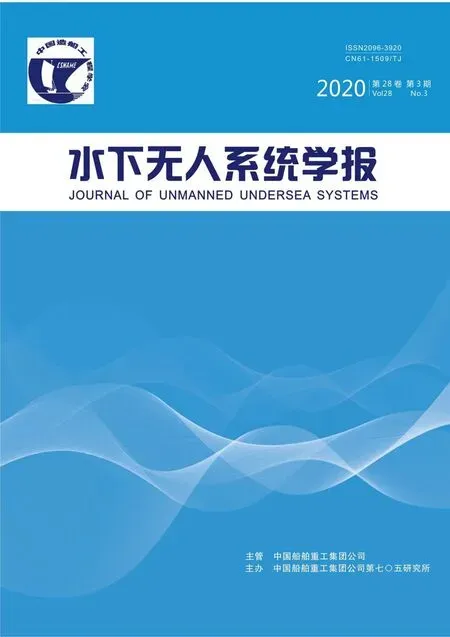海上实兵作战实验综述——概念、案例与方法
2020-07-01钱东,赵江
钱 东, 赵 江
海上实兵作战实验综述——概念、案例与方法
钱 东, 赵 江
(海军研究院, 北京, 100161)
实兵作战实验是作战概念开发、战法开发、兵力运用和兵力结构优化中的关键环节和军事转型的重要支柱。文中对作战实验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 阐述了作战实验的科学及军事意义; 简述了美海军的主要作战实验机构和作战实验活动; 介绍了实兵作战实验的历史案例和现代案例, 重点介绍了美海军著名的“舰队问题”演习和二战水下战的实验探索; 讨论了实兵实验设计和实施中的有关问题。指出: 应明确实验目的和目标, 通过发现新现象和探索机理来获得新知识; 建立相对完整和合理的问题框架是实验成功的先决条件; 应对系列化实验进行系统规划, 避免针对某些孤立问题、缺乏基础的“跳跃式”实验; 应合理选取实验因素及水平数, 把握作战想定的粒度和特异性, 以保证实验结果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在实施中应注意与演训的结合, 适时运用模拟兵力, 以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最佳效益; 应建立专业化的分析评估队伍和专家队伍, 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结果和证据进行分析, 以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指出实兵实验是发展现代作战学说的必要途径。
实兵作战实验; 演习; 水下战
0 引言
过去研究战争的方法主要是基于经验的定性分析和战例分析, 但在现代技术飞速发展、长期未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今天, 这些传统方法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作战实验已日益成为研究现代战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作战实验的作用主要体现为超前实践——提前进行战争预演, 揭示和认识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找到对策和方法。作战实验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不同层次和方面, 例如: 作战概念开发, 作战条令开发, 战术、技术和程序(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TTPs)开发, 兵力结构优化, 装备运用等。作战实验本身就是重要的创新途径, 因此美军将作战实验视为军事转型的重要支柱、发展未来作战理论的温床、实现任务能力群的重要途径。例如: 虽然网络中心战、分布式作战及无人化作战几乎已成为共识, 但是具体到指挥控制、组织结构、作战原则和战术流程等细节, 都还有待深入研究, 须经过作战实验验证。
作战实验是研究作战问题的军事科学活动, 旨在运用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作战概念、理论和方法, 为军事决策和战争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实验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所产生的知识, 更在于它在科学知识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关于作战实验问题, 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绝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实验室中的建模与仿真——基于构造仿真和虚拟仿真的作战实验, 较少涉及实兵实验。文中主要讨论基于实兵的海上作战实验问题。
1 作战实验的概念、分类及意义
1.1 概念
“实验”( experiment)一词源于拉丁语experiri, 意为“尝试”(to try)。在英语中, experiment是指“A test under controlled conditions that is made to demonstrate a known truth,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a hypothesis, or determine the efficacy of something previously untried”, 即在受控条件下为演示一个已知真理、检验假说的正确性或确定以前未尝试过的某些事物的效能而做的试验[1]。《辞海》中给出的定义是: “实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 运用必要的手段, 在人为控制条件下, 观察研究事物本质和规律的一种实践活动”。实验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研究对变量进行操纵的结果”的过程[2]。有人则将实验(基本要素)定义为: 一个问题、一组可能的答案、一个事件、一组可能发生的结果, 以及事件结果与问题答案之间的关联关系[3]。
严格地说, “实验”(experiment)与“试验”(test)是2类目的不同的科学活动。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 实验是“为了检验某种科学理论或假设而进行某种操作或从事某种活动”; 试验是“为了察看某事的结果或某物的性能而从事某种活动”。英语中的解释与此类似。一般而言, 实验是一种探索性活动, 用来证明理论或发现新现象、推导新结论; 而试验是一种检测性活动, 用来检测正常或临界运行过程及结果, 如工业产品的各种试验。例如有人认为, 从事物理化学研究的人主要是在做实验, 目的是探求化学现象背后的道理, 主要进行科学研究; 而从事分析化学的人主要是在做试验, 主要目的是进行化学鉴定和分析, 主要从事技术工作。从某种角度看, 实验是评估系统对某些事物的影响, 而试验(测试)是评估系统自身的特性。
有时, “实验”(experiment)和“试验”(test)会同时出现, 用于表达不同层次的测试活动概念, 例如美国报告中出现“proof-of-concept experiment test plan”的表述, 显然其中的experiment代表实验项目或活动的大概念, 而test表示其中一系列分解后的具体试验子项目和实施活动, 即实验中相对较小的技术验证子过程。在此场合, 多少有些类似mission(使命)与task(任务)之间的关系[4]。
“作战实验”(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是研究作战问题的科学实验活动。在作战实验中, 实验者运用科学实验的原理、方法和技术, 在可控、可测的近似实战或模拟对抗环境中, 根据特定实验目的, 有计划地改变实验中的兵力、战法和作战环境等因素和条件, 考察各种因素和条件影响下的作战进程和结局, 从而深入认识战争规律, 为军事决策和战争实践提供科学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2011 年版)将作战实验定义为: “在可控可测近似真实的模拟对抗环境中, 运用作战模拟手段研究作战问题的实践活动。包括作战实验的规划设计、组织实施、分析评估等环节。”有人将作战实验概念表述为: 探索对特定作战能力或条件进行操控所带来的影响或效果。美国和北约已将“作战实验”一词纳入军语[5]。
在西方出版物中先后出现过一些类似的术语和概念, 主要有: 防务实验(defense experimentation)[2](泛指国防领域内包括正规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所有冲突类型的实验方法)、舰队实验(fleet experiment)[6]、战斗实验(battle experiment)、舰队战斗实验(fleet battle experiment, FBE)以及实验战役(campaigns of experimentation)(一系列相关实验的集合)[7]等。这些术语的内涵大同小异, 文中引用时尊重原文的表达。
作战实验主要运用于作战实践上升为作战理论和方法的科学认识阶段, 通过实践、分析和归纳, 完成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以此来完成对作战概念和TTPs[8]的开发, 达到设计作战样式和方法、设计未来战争的目的, 如: 澳大利亚“游隼”系列作战实验就是为武装侦察直升机配合营连级战斗而开发条令和TTPs的一系列人在回路的综合实验[2]。本质上, 作战实验是战术和技术开发工作的一部分, 而不仅仅是试验验证。有些国家将能力开发和建立原型系统的过程称为“概念开发和实验(concept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tion, CD&E)”[2], 应该也是基于这种认识。总之, 作战实验是为了探索和检验作战理论、方法及技术而进行的研究活动和预实践活动。
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比较, 作战实验有其特殊性, 主要体现在军事问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对抗性和不可控性等方面。
值得指出的是, 有些探索研究中的测试活动兼具实验和试验的目的和特点, 许多演习同时包括实验和试验的内容, 如美军近年来将“超重型两栖连接器”(ultra heavy-lift amphibious connector, UHAC)和“机器驴”等新概念装备投入部队演习和实验, 既探索和验证新的作战概念, 也同时考核装备原型的性能和能力。
1.2 分类
根据不同的视角和理解, 对作战实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2-3,5,7,9-16]。总体上看, 下面几种分类得到广泛认同, 基本形成了目前的主流观点。
1.2.1 按实验目的分类
从实验目的看, 作战实验主要可分为3种: 发现型实验、验证型实验和演示型实验, 这是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认可的一种分类方法, 但DoD也指出, 几乎不存在“纯粹”的某类实验, 实验活动几乎都是多类实验的混合体[5,11-12,14,17]。
1) 发现型实验——也称探索性实验, 主要目的是发现新现象、探索新知识、揭示新特点、开发新概念。受这类实验的次数限制和精度影响, 一般难以推断明确的因果关系, 不足以形成对战法的清晰认识。
2) 验证型实验——即假设验证型实验, 是以分析、检验和证实为核心, 对已有的经验、设想或预测进行验证和评估。在军事领域, 这类实验主要是指为验证作战理论、战法或作战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而进行的实验。实验主要用于检验战法中的假设, 发现错误假设或发现假设中的限制条件, 对一些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以此来形成对作战概念和战法的深刻理解。在实际作战实验过程中, 对象复杂, 各种因素交织, 因此实验设计十分重要。
3) 演示型实验——主要目的是向决策部门和部队展现已有的科学方法和结论, 展示和传播新思想、新战法和新技术, 以期推动实战应用。
概括地说, 发现型实验旨在发现现象, 验证性实验旨在揭示机理, 演示型实验旨在传播思想和概念。
1.2.2 按实验方法和手段分类
从实验方法和手段看, 主要可分为3种: 仿真、推演和实兵实验(演习)。在国内, 当不特指“实兵”时, 通常将作战实验理解为基于仿真或推演的作战实验。
1) 仿真——作战仿真包括数学仿真和半实物仿真, 是作战实验中最基本、高效的方法。仿真实验的突出优点是, 能够通过大量计算给出统计结果, 可进行敏感度分析, 也能进行详细的因素分析和过程分析, 从而揭示仿真结果与关键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和规律。因此, 仿真已成为对抗推演和实兵演习方案设计的基础。但受模型、数据和假设等的影响, 仿真结果毕竟与客观实际之间存在差距, 且对人行为的解释有很大困难, 所以仿真方法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按照现在较为流行的观点, 仿真主要可分为3类[11, 18]:
①实景仿真(live simulation)——指真实的人员在实际条件下操纵真实的装备, 主要指试验和训练。
②虚拟仿真(virtual simulation)——真实的人员操纵仿真的装备(模拟的系统), 主要手段是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如飞行模拟器。
③构造仿真(constructive simulation)——仿真的人员操纵仿真的装备, 例如全数字仿真。
LVC仿真是指同时具有实景(live)、虚拟(virtual)和构造(constructive)仿真的综合仿真活动, 主要用于军事训练和试验, 也可用于初级作战实验。越战后, 美空军调查发现, 飞行员参加约10次作战任务后, 其战场生存能力显著提高, 于是设立了著名的“红旗”军演。飞行员在贴近实战环境中进行对抗, 积累经验。这类实兵演习虽可提供宝贵的练兵机会, 但成本过高、保障复杂, 于是提出了将实装嵌入仿真网络的需求, 由此出现了LVC集成系统。LVC集成中的实兵部分通常包括真实的作战平台、任务系统和受训人员; 虚拟部分则包括部分人员、装备、系统及其接口, 支持人在回路的实时交互; 构造部分是计算机生成的实体, 表征装备和人员的能力和行为, 并根据预定规则和行为模型来决定实体的行动。
在水下战领域, LVC集成的典型代表是美海军水下战中心(naval undersea warfare center, NUWC)构建的战术集成综合环境(synthetic environment tactical integration, SETI)。SETI利用水下跟踪遥测系统和网络, 将高置信度的鱼雷仿真能力与实航状态下真实潜艇上的声呐和火控系统集成在一起, 实现了在真实潜艇上发射模拟鱼雷, 使艇员可利用NUWC的硬件在回路(hardware- in-the-loop, HWIL)模拟的鱼雷来攻击真实或虚拟的目标。潜艇能在水下实时“感知”到所发射的模拟鱼雷, 并可进行线导。这种能力可用于早期战术开发和实验、对抗训练和武器试验。1998年, 美海军利用“洛杉矶”级潜艇上的建制作战系统, 完成了对1枚MK48 ADCAP模拟鱼雷实施线导导引的演示验证[19]。
2) 推演(wargame) ——亦称兵棋推演, 指对抗双方按演习问题的顺序和战役、战斗可能发展的进程而连贯进行的模拟对抗和剧情化博弈。早期的推演形式一般是研讨会式的决策演习和桌面或图上作业, 现在都采用计算机辅助推演方式, 加入实战或实兵演习数据, 交战各方运用作战模拟手段, 对作战方案和行动进行“人在回路”的模拟, 对决策和方案进行评估与优化。这种对抗模拟实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验, 适合于研究决策的过程、原因和影响因素, 探索与人相关的不确定、难以量化的非装备因素。推演在装备效能评估及其相关研发决策上的作用日益显现, 例如, 有人在推演中引入无人水下航行器(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 UUV), 以研究其对交战双方作战决策和对抗过程的影响, 促使人们从新的高度来审视UUV在兵力结构中的地位。
推演主要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博弈过程的对抗模拟, 重点着眼于作战决策及其后果, 而不是装备和操作细节。虽然“人在回路”的仿真也有人介入, 但一般多指针对具体装备运用过程的模拟, 关注的重点是“人-机-环”及其基于武器装备的战术对抗策略和武器运用方法, 如为开发TTPs而进行的仿真。
3) 实兵演习/实验——是指动用真实兵力(人员和装备)在近似实战环境下的演习。许多演习同时兼顾训练、考核、试验和实验研究等多个目的。在实验设计完善的情况下, 实兵演习/实验所得结论的可信度高, 但组织复杂、成本高、重复难度大。今后将主要依托大型专业训练基地(中心)借助现代化手段来组织实施。
仿真分析的优点在于能够提供对作战过程的基本理解、模型和定量结果, 可作为推演的基础; 推演的长处在于能够用于探讨决策过程, 可体现出一些非军事和非技术因素对决策的影响, 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角发现问题和提出建议; 实兵演习/实验通过运用真实装备和作战人员来测试有关战术和技术概念, 获取真实数据, 既能检验决策的合理性, 也能近似模拟实战过程, 从而验证一些假设和预测, 发现问题, 为下一步仿真分析、推演以及后续实兵演习提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建议。完整的作战实验应将运筹分析、作战仿真、推演和实兵演习结合在一起, 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 用实践结果来完善、修正理论和模型, 经过不断交互循环, 不断逼近“合理解”, 科学引导作战条令和战法开发及新装备研制。只有综合这些功能互补的方法, 才能对真实作战中的问题获得完整和全面的理解。
1.3 实兵作战实验与作战试验、演习、技术演示验证试验的异同
1.3.1 实兵作战实验与作战试验的异同
在DoD的装备采办过程中, 试验与评估(test & evaluation, T&E)主要分为3类: 研制试验与评估(development test & evaluation, DT&E), 作战试验与评估(operational test & evaluation, OT&E), 实弹试验与评估(live fire test and evaluation, LFT&E)。
OT&E主要目的是解决武器系统的关键使用问题, 在作战试验设计中应关注“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做该做的事”和“评价是否有意义”这2个基本问题[20]。实际上, 作战实验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区别在于评价的对象已不限于武器装备, 而是扩展到作战指挥、编制和战法等更高层次的内容。
作战试验与作战实验关注的对象不同。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武器装备在现有作战理论和实战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后者主要关注的是军兵种以及军队未来发展、建设和作战等方面的关键环节, 如新的作战概念、新的作战思想、组织结构, 以及重大技术的运用对作战的影响等。
1.3.2 实兵作战实验与作战演习的异同
作战演习是部队战备训练的高级形式, 是在想定下进行的作战指挥和作战行动的演练, 主要用于检验部队的战备程度与作战能力、武器装备技术状态和实际能力, 以及战术的合理性。作战实验和作战演习都可以验证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战场环境对作战行动的影响以及组织指挥在作战行动中的作用, 区别主要在于: 作战实验侧重于研究, 用于探索作战问题; 而作战演习侧重于训练, 用于锻炼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以, 二者在目的、目标、组织方式、实施方法以及技术手段运用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但在实践中, 两者经常穿插在一起进行, 在作战演习中进行部分项目的作战实验[1]。
1.3.3 实兵作战实验与先期概念技术演示验证试验的异同
在预研阶段, 美国利用先期技术演示验证(advanced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TD)和先期概念技术演示验证(advanced concept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ACTD)来实现先进技术向装备型号的快速转化。ACTD是面向新型系统概念或方案的演示验证试验, 目的是加速成熟技术向新系统的过渡, 在接近真实的作战环境中进行, 一旦技术性能和实用性得到验证, 即可启动正式研制或采办程序[21]。ACTD强调的是对成熟技术的集成, 而不是技术开发, 其目标是提供原型作战能力、体现军事价值、形成新装备使用概念。
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 但ACTD与一般意义上的作战实验的区别是明显的: ACTD试验主要面向装备技术(尽管有时也会涉及到有限的作战概念和组织结构), 目的是为装备采办决策提供依据; 作战实验主要面向作战概念、条令、战法、兵力组织结构、新型装备, 目的是考察各种条件影响下的作战进程和结局, 认识战争规律, 为军事决策和战争实践提供依据。两者出发点不同, 这也体现出“试验”和“实验”的区别。
但在另一方面, 有些引入了新概念装备的小规模作战实验与ACTD的界限有时变得比较模糊, 经常是两者联合进行, 一次活动同时达到多个目的。如美军近年来将UHAC和“机器驴”等新概念装备直接投入部队演习, 并将其称为作战实验。但从传统观念看, 它们更像是典型的ACTD或作战试验。
总之, 实验主要是评估系统对某些事物的影响, 试验则主要是评估系统特性[2]。
1.4 作战实验的科学及军事意义
过去研究战争的主要方法是依靠经验进行定性分析, 以局部经验或历史战例分析、逻辑推理、反复研讨形成对战争规律的认识。这种依靠战例研究未来战争的方法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很大作用, 指导了人们对战争的认识, 但在军事科技现代化的今天, 已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限于当时有限的观察条件、片段的记忆和记录等因素, 并不能清楚地了解历史战例中一些事件的细节、原因和战术决策等, 从而使许多战例被掺入了大量文学创作成分, 从而影响到实际启示效果, 特别是人机结合问题, 仅通过理论和历史研究常难以得出结论[17]。
如果认为战争研究既是科学也是艺术, 则作战实验的价值就主要在于对战争的科学问题进行实证。许多人仅满足于从表象上寻找一些能说明现有理论的现象和案例, 而不愿进行深入、严谨、系统的实验探索, 对于新的现象, 总是习惯性地归结于某个未知的偶然因素。例如: 在战例研究中, 军事史学家们往往不自觉地去为一些偶然事件寻找依据并进行解释, 常将原因归结于特定环境, 这就难以进行科学、全面的概括和发现其中的潜在规律和机理, 也难以有新的发现。而通过反复进行的作战实验, 可合理地解释常见和偶然现象, 认识因果关系和主次因素。因此,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 没有先进的作战实验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军事理论。
美军将作战实验视为军事转型的重要支柱, 认为未来作战理论的发展与作战实验密切相关, 实验的目的在于评估和完善新的作战理论, 必须通过作战实验开发与实验新的作战方案、编制体制、程序和技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美陆军开始了一项长达十年的作战实验行动计划, 相继成立了多个功能性实验室, 进行以作战概念开发、验证、演示和传播为主的作战实验活动, 美陆军几乎所有院校和师级单位都划入实验挂靠单位。美军在多次局部战争中的许多战法实际上都源于作战实验。
作战实验的作用体现在作战概念开发、条令开发、TTPs开发、兵力和装备结构优化, 以及装备运用等各个方面, 作战实验本身就是重要的创新途径。在历史上, 美军利用作战实验开发了航母及特混舰队运用方法,德军利用作战实验验证了“狼群”战术和“闪电战”战法。在大量UxVs不断涌现的今天, 显然必须通过作战实验来摸索新的交战形式, 开发新的联合作战方法。实兵实验除了可为仿真、建模、验模提供真实数据外, 更重要的是, 只有通过实兵实验, 才能更真实地展现战斗人员在近似实战条件下的行为表现, 揭示出装备、方法和程序中的潜在问题。
战争手段的每一项重要发明, 都要求重新检验和评估战略和战术的思想、兵力结构、装备和条令, 这种评估要求对战争中各因素的交互作用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 这是作战实验乃至现代军事变革的原动力。作战实验将催生对现代军事领域的新的认知[17]。
2 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作战实验机构及作战实验活动
2.1 主要作战实验机构
美海军的作战实验机构主要有: 海军分析中心、海上战斗中心、海基战斗实验室(sea based battle lab, SBBL)、系统技术战斗实验室(system technology battle lab, STBL)等, 还有空间和海军作战系统司令部(space and naval warfare systems command, SPAWAR)、海军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NPS)、海军空战中心训练系统分部(naval air warfare center training systems division, NAWC TSD)下属的作战实验室。海军陆战队下属的作战实验机构主要有: 海军陆战队作战实验室(marine corps warfighting laboratory, MCWL)、海军陆战队战术系统支持行动中心(marine corps tactical system support activity, MCTSSA)等。
美军的作战实验机构并非都设置在军队中, 一些科研和教学机构、甚至民企也参加作战实验活动, 如美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CNA), 尽管是一家民间机构, 却是作战实验的重要参与者。
1) CNA
CNA是美海军的重要思想库, 有“海军的兰德公司”之称。作为独立的非营利组织, 主要服务于美海军和国防部门, 聚焦于海军战略、战役战术、作战评估和资源分析等问题研究[11]。
美海军的战争及作战分析可分为3个层次: ① 战略分析, 由海军学院和海军作战部进行; ②战役级分析, 主要是海军兵力结构分析, 由海军学院和CNA进行; ③ 作战分析, 主要研究海军装备性能和战法, 由CNA、海军实验室及研制方进行。CNA主要从事海军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编制体制和后勤建设等各方面的研究, 尤以研究水下战技术和战术著称。通过技术和系统分析、作战分析, 协助海军生成作战需求和开发新的作战概念; 通过作战实验和试验、分析和评估, 协助部队改进作战、训练和保障方法及组织结构[22]。
CNA常年保持数十人在海军及陆战队各指挥部和机关担任顾问, 另通过战场项目(field program)派人深入一线部队提供支援。现场分析人员从各个角度观察实际作战、训练和实验过程, 收集第一手数据, 然后与中心的研究团队共同分析和评估。这种常态化交流使研究部门和部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促进了新的作战概念和战法的开发。
2) 海上战斗中心与SBBL
美海军的作战实验一般由海军各舰队轮流承担, 因此各舰队都是事实上的作战实验室。除此之外, 还成立了专门的作战实验机构——海上战斗中心, 由一名中将领导, 实际上是舰队作战实验的协调和管理机构, 也是联合作战实验中的跨军种协调机构。2000年, 在第3舰队“克罗拉多”号上又正式组建了SBBL, 该舰为各种海上作战实验活动提供技术支援。海上战斗中心下设概念研究、技术评估和行动协调3个小组, 分设在海军学院、SPAWAR等单位, 主要通过仿真和舰队战斗实验2种形式对海战方案和相关技术进行验证[5,11,13,23]。
3) 其他战斗实验室
“战斗实验室”(battle lab)的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诞生于美军, 其目的是“能够迅速和深入分析由新兴技术产生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法”。战斗实验室本身也可被赋予某些作战能力, 如指挥控制。多数战斗实验室并非独立机构, 而是某一部门和机构下的研究组织, 或是现有组织被冠以新的名称, 如海军研究生院、海军空战中心下都设有这类实验室。许多战斗实验室规模不大, 且针对某些具体专业方向, 如: 美陆军的“火力战斗实验室”和“情报战斗实验室”等,其主要任务一般是: 规划和实施各种实验、提炼作战概念、评估潜在解决方案、审查想定、提供决策支持等。战斗实验室并不一定以战斗实验室标榜, 许多研究机构本身从事相关研究和实验, 也被视为战斗实验室, 如关塔那摩基地就被视为是美军从事心理战和情报挖掘的“战斗实验室”, 他们利用关押的对象和工作环境获取数据、训练审讯者、开发情报审讯TTPs[24]。“战斗实验室”这一名称现在也开始被推广到其他非军事领域, 如: “霍普金斯大学战斗实验室”实际上仅是一个利用仿真和数据分析手段进行生物系统研究的实验室。
2.2 主要作战实验活动
美军的作战实验着眼于未来5~10 年需求, 通常分为一般实验和高级实验, 实验周期1~5年。海军的高级作战实验主要通过舰队海上战斗实验来进行, 每年组织2次, 每次赋予不同的主题和目标, 由各舰队轮流承担实验任务。
舰队战斗实验(fleet battle experiment, FBE)是美海军最主要的实兵实验, 美海军利用FBE分别进行了“火力圈”及“武库舰”概念和方案的验证, 联合火力支援TTPs, 以及极浅水反水雷特遣队(very-shallow water mine countermeasue, VSWMCM)运用高速艇(HSV-X1)、无人水下航行器(unmanned undersea vehicle, UUV)REMUS(Re- mus remote environmental measuring units)和战场准备自主水下航行器(battlespace preparation autonomous undersea vehicle, BPAUV)等UUV的反水雷作战实验。美海军还每年举行“三叉戟勇士”(Trident warrior)实兵作战实验, 分别演示了部队网、海域感知与远征作战等能力。MCWL开展的实验有: “猎人勇士”开阔地带作战实验、“城市勇士”城市作战实验、“干练勇士”机动作战与战役欺骗实验、“千年龙”登陆夺港与城市作战实验、“海盗”分布式作战实验、“远征勇士”海上基地概念验证、“联合城市勇士”联合城市作战概念开发实验等[5,11,23]。
3 实兵作战实验案例
在历史上, 航母及特混编队作战概念的产生, 以及二战中一些水下战和闪电战等战术的产生, 都直接来源或曾借助于作战实验。战后60年后的今天, 实兵实验与作战仿真相结合, 正催生网络中心战、无人作战等新型作战概念的产生和发展。
3.1 历史案例
3.1.1 美海军“舰队问题”系列演习——作战概念和战术的开发平台
历史上最经典的作战实验案例应是美海军在1923~1940年间举行的21次“舰队问题”(fleet problem)演习。演习名称表明, 其目的不仅是训练部队, 更重要是通过演练发现舰队作战中的问题, 探索和验证新的作战概念和战法、兵力编成与组织、指挥协同及装备运用方法等。因此, “舰队问题”演习实际上是“实兵演习+实兵实验”。军事史学家给予了“舰队问题”系列演习极高的评价, 因为它孕育、孵化了航母装备和使用的诸多概念。通过一系列作战实验, 使美海军一步步认清和理解了航母设计和运用中的一些未知问题, 逐步形成了航母及特混舰队作战运用的完整概念和实际作战能力, 其基本概念和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面对21世纪的各种颠覆传统的战争形态, 美海军又于2015年重启了“舰队问题”演习, 可见“舰队问题”演习的深远影响力。
“舰队问题”演习是美海军用于描述27次海军演习的名称。原定于1941年举行第22次舰队问题演习, 由于二战爆发而取消, “舰队问题”演习就此中断, 以后的演习采用了其他名称。然而, 在海军上将Swift的倡导下, 这一名称在2015年又恢复了使用, 第23~28次“舰队问题”演习相继举行。该演习通常每年举行1次, 有时举行多次。
“舰队问题”演习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性的作战实验和超前实践。每次演习聚焦1~2个重点问题寻求答案, 在特定作战想定下探索作战概念和战法, 检验能力。通过早年的“舰队问题”演习和二战实践, 逐步确定了航母在美海军兵力结构中的定位, 明确了其角色、任务和目标, 成功牵引和驱动了航母技术和战术的发展。
1) 航母作用与地位的确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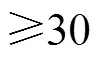
为探索航母的运用方式, 美海军充分利用1923~1940年间的年度舰队演习进行了一系列近似实战条件下的作战实验。虽然演习并非专为航母设立, 但美海军在不断开发、提炼海军舰队战术的同时, 也逐步确立了航母在海军中的地位。因而, 一系列“舰队问题”演习也就成为航母发展的里程碑。
1923年, 美海军在巴拿马运河区太平洋一侧举行了第1次“舰队问题”演习, 围绕运河攻防展开对抗, 双方用其他舰船来模拟航母。“敌机”在美军未察觉的情况下, 用10枚模拟炸弹“炸毁”了“卡通”泄洪道。这次简单的演习引起了很大震动, 美海军开始意识到, 航母绝不仅仅是侦察舰或者护卫舰, 它是一种有效的新型攻击平台。虽然那时飞机能否战胜战列舰队尚无定论, 但大家都已认识到, 航母的出现必将改变未来海战规则[25-26]。
在航母出现的最初10年里, 各国海军从零开始摸索, 逐渐明晰了任务和目标, 航母的作战运用概念和方法逐步成型。1929年, 刚服役的“列克星敦”(CV-2)和“萨拉托加”(CV-3) 2艘航母首次参加演习就引起了军事界和媒体界的轰动, 这就是日后被军事学者们反复提及、十分著名的“第9次舰队问题演习”。人们普遍认为, 此次演习是海军史上的一次飞跃, 演习所获的经验和结论, 对于舰队战术和海军整体战略, 尤其是对海军航空兵的战略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次演习的想定是蓝方(美国)同时与2个敌国交战, 分别是太平洋上的黑方和大西洋上的棕方。为将美国分割在两洋, 黑方要对巴拿马运河发动突袭, 而蓝方则要保护运河。黑方兵力中配属有“萨拉托加”号航母, 用扫雷舰“阿卢斯图克”号代替正在大修的“兰利”号航母, 用搭载的1架水陆两用飞机代表“兰利”号上的18架战斗机和6架侦察机。蓝方兵力中配属了“列克星敦”号航母。棕方则只是一支无实际人员和装备的虚拟兵力, 配合黑方夹击蓝方。黑方此次行动的基本策略是战列舰队的常规攻击和航母的突然袭击并举, 这一战术安排完全体现了此前美海军对航母的理解: 既要利用速度优势离开主力舰队执行先期作战任务, 完成任务后又要伴随主力舰队行动。1929年1月26日, “萨拉托加”号放出了由83架各型飞机组成的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舰载机攻击群, 对巴拿马运河太平洋一侧的两处船闸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并大获成功。第2天, 黑方扫雷舰“阿卢斯图克”号又放飞了1架水陆两用飞机, 用以模拟“兰利”号上的机群, “摧毁”了大西洋一侧的船闸和机场。黑方最终以彻底摧毁巴拿马运河而取得了胜利。当年由海军战争学院提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得到了解答, 航母的威力得到前所未有的体现[25-27]。
第9次“舰队问题”演习的结果震惊了各国海军, 引发了各方激烈的讨论。由于“萨拉托加”号的卓越表现, 美海军完全确定了大甲板、大载机量和高速航母的价值, 随之放弃了已开展的建造小吨位航母的计划。同时, 航母的运用也成了随后几次舰队演习的主要内容。第9次“舰队问题”演习标志着美海军取得了巨大成就, 航母不但能与其他水面舰协同作战, 也可成为一支独立的打击力量。这一变化很快对美海军的航母作战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下一年度的舰队演习中, 以航母为中心的战术编队首次出现, 这一战术组织形式在此后的一系列演习中得到了不断检验和完善[25]。
2) 航母特混舰队的形成
特混舰队的概念产生于第9次“舰队问题”演习之后。通过一系列“舰队问题”演习, 美海军对航母及其战术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演习中的教训使美海军开始意识到, 航母不能靠自身大口径舰炮与敌方战列舰展开对攻。一些经历了演习的军官认为, 航母必须由多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舰队来护航, 以免遭对方水面舰队的打击。这一观点被视为是美航母特混舰队的最初萌芽。经过第9次及随后的系列“舰队问题”演习, 美海军的作战/侦察舰队编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战列舰队继续担当海战核心, 以重型巡洋舰为核心的侦察舰队则逐渐演化成了多支以1艘航母为核心, 由多艘重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提供保护的航母特混舰队。美海军二战前的重型和轻型巡洋舰有明确的分工: 重型巡洋舰主要编入侦察舰队和航母特混舰队, 独立执行侦察等任务; 轻型巡洋舰则主要伴随作战舰队, 负责近距离掩护和战术侦察[25]。
第9次“舰队问题”演习中, 虽然“萨拉托加”号航母攻击运河成功, 但在随后的行动中被判因遭敌反击而被“击沉”了3次。这一结果使美海军意识到, 航母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但独自作战时自身也面临着极大危险。于是, 美海军内部对航母应独立作战还是与主力舰队协同行动的问题形成了两派意见。激进派认为, 航母平台应独自作战以发挥速度优势, 与主力舰队分进合击以形成有利的战场态势。但脱离主力舰保护的航母一旦遭遇对方战列舰会十分危险, 几次演习结果都证明了这点。为此提出, 应为航母建立一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战列舰的速度不够), 护航军舰在遭遇敌方时要舍身而出。保守派则认为, 只有让航母和战列舰共同行动, 相互掩护, 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 但其代价是牺牲航母的速度优势。带着这样的问题, 美海军在1930年接连举行了2次舰队演习——第10和第11次“舰队问题”演习[25-26]。
第10次“舰队问题”演习的想定是: 蓝方(美国)在加勒比海被黑方打败, 于是派太平洋舰队进入加勒比海, 消灭黑方舰队。虽然基本任务相同, 但双方采取了2种截然不同的航母运用方式: 航母兵力较强的蓝方选择了保守派的方案, 让航母伴随主力舰队行动; 而仅有1艘航母的黑方则采纳了激进派的意见, 首次组建了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特混舰队, 多艘驱逐舰部署在前方, 任务是搜索敌方舰队, 摧毁敌航母, 支援己方战列舰作战。特混舰队正式亮相。在这次演习中, 蓝方的2艘航母因遭到“列克星敦”号航母的袭击而瘫痪, 表明快速空中攻击兵力能够打破海上力量平衡。演习的结局令人意外: 在演习的大部分时间里, 双方都是在竭力搜寻对方, 一旦某一方先机发现对手, 立决胜负。此次演习使美海军澄清了第7次演习中得出的、但不能十分肯定的结论: 航母面临空中攻击时非常脆弱。几乎可以断言: 航母决战中能抢占先机的一方必取胜。黑方航空兵指挥官给出了形象的比喻: “航母对决就像是两个蒙住双眼手持大棒的人在一个小圈子里打架, 只要其中一个人眼前的眼罩被摘掉, 另一个就死定了。”根据这一结果, 美海军得出结论, 如能利用突然性优势并用航空兵发动先敌打击, 则完全可能扭转兵力上的劣势。这一结论在后来的中途岛海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5-26]。
单独成立航母舰队会对原有相对固定的编制体制带来很大影响, 实施难度大。因此, 美海军决定借用陆军“临时特遣队”的概念, 在海军中组建一种不占固定编制的临时性编队。与陆军特遣队不同的是, 海军特遣队不会随某一任务的结束而解散, 它们将相对固定地编组在一起, 共同训练和作战。这就形成了最初的“特混舰队”(task force)[25]。
3) 航母作战理念和战术的孵化、开发和实践检验
“舰队问题”演习为航母作战理念形成、战术开发与验证提供了实验平台, 形成了一系列战术成果。
在航母发展早期, 存在“战列航母”(battleline carrier)与“全能航母”之争。前者是指编在战列舰编队中的航母, 以较慢速度伴随编队行动, 吨位较小, 不需装甲和重炮。后者则是指具备独立作战能力的航母, 航速不低于巡洋舰, 吨位较大。在第10次“舰队问题”演习中, 这2个概念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演习中, 美海军第一次将摧毁对方航母作为己方航母的首要任务和主力交战的先决条件, 结果是“全能航母”取胜, 证明了航母具有很强的对海独立作战能力。随后的第11、12次舰队演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战列航母”连续3次失败显然不是偶然现象, 这表明它很难适应未来海空战[25]。
明确了航母的进攻角色、组建了独立的航母特混舰队后, 美海军开始探究航母与战列舰对抗问题, 将此作为第12次“舰队问题”演习的主题。演习表明, 虽然受当时航空兵能力所限, 航母尚无法有效摧毁战列舰, 但其本身并未受到战列舰的任何攻击, 航母特混舰队完全可独当一面, 成为海军主力。后来战争实践证明了这一点[25]。
此后的第13次“舰队问题”演习表明, 海战不会是单纯的航母对攻, 各种兵力交战交织在一起, 使得海战十分复杂。对抗结果表明, 单航母不足以完成舰队攻击和区域防御任务,因此在以后的战争实践中, 2艘以上航母在一起共同作战成为基本战法。
在对航母的运用概念已基本了解后, 美海军在随后的第14~21次“舰队问题”演习中, 进一步开展作战实验, 逐步摸清了航母的主要使用场合、最佳使用方式等问题, 使自身逐步发展成为能够熟练运用航母遂行机动作战和舰队决战的强大海军。珍珠港事件并未给美海军航空兵以实质性打击, 反而带来了新的契机: 航母不得不担当起了海军第一主力的角色。
3.1.2 二战时期的水下战——与作战实践相结合的作战实验
在很多情况下, 受兵力资源、时间等各种条件的限制, 难以通过精心设计的作战实验来验证作战概念和构想, 只能结合战争实践进行实验和检验。战场是最好的实验室和试验场, 即使一些战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也须在真实战场环境下进行实验验证, 这是因为战法的适用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未知因素的影响和假设前提是否成立。在两次大战和一些战后局部战争中, 许多战术实验是在实战中完成的。
1) 潜艇战——“狼群”战术
二战期间德军精心设计的许多潜艇战术是通过作战实验/试验进行验证和提炼, 并最终应用于战争的。其中的“狼群”战术最早由德军潜艇指挥官鲍尔提出, 而海军元帅邓尼茨基于当时的装备水平, 通过创新研究和大量的作战实验及演习, 将这一战术逐渐开发成熟和完善。在早期缺乏潜艇的年代, 他们用鱼雷艇代替潜艇进行“狼群”战术实验。

邓尼茨认为, 集群作战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战斗的基本形式。由于指挥困难, 潜艇以前几乎都是单艇作战, 为实现集群作战, 他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并指出: 潜艇兵力运用的基本设想、新战术等都必须经过实验/试验的验证[32]。
“狼群”战术在结合实验的训练过程中攻克了许多难题。起初, 最先发现“敌舰”的潜艇在报告后立即攻击, 其他潜艇再追上围攻。演习证明, 这种战法只能对付航速较低的船队。后来, 在战术巡逻线后面又配置1个或者数个艇群来对付运输船队, 使“狼群”战术进一步完善。在大量的实验和演习中, 潜艇部队尝试了各种队形, 最后发现环形配置方式的效果最好: 敌舰进入环形配置海域后, 位于环形海域弧线上的其他潜艇能够迅速赶到。演习中取得的所有经验不断加进条令中, 条令篇幅不断扩大[30]。
在1937年举行的德国大规模“国防军演习”中, 邓尼茨在1艘护卫舰上用无线电指挥潜艇群成功地搜索、跟踪和攻击了“敌方”舰队和运输船队, 初步验证了“狼群”战术的有效性。后又分别在北海、大西洋、波罗的海等不同海域举行了“狼群”战术实验。经过大量演习, 全面验证了“狼群”战术在不同海区的有效性, 并基本解决了“狼群”战术的具体细节问题[30]。
2) 反潜战
战时护航战是针对潜艇破交行动的作战, 主要作战样式是“被动反潜战”。由于条件所限, 很难在战前进行规模性实验, 盟军主要通过结合实际战斗, 在实践中进行作战实验/试验和检验。
护航船队早在一战期间就已出现, 英法试验性地采取护航船队方式后, 效果显著: ①据计算, 潜艇发现一支护航船队的概率与发现一艘独行船只的概率相差很小。在良好条件下, 水面潜艇发现单艘船只的距离约为16 km, 而发现20艘舰船规模的船队(宽约2 mile)的距离(距船队中心)则约为17.6 km。显然发现20艘单独航行船只的累积概率要大得多, 护航船队的优点明显。②沿某一航线独行的商船会形成绵延不断的目标, 潜艇攻击机会多; 而护航船队虽庞大, 但攻击窗口是有限的, 被攻击的只是船队中少数商船。③用有限的反潜兵力掩护船队比掩护整个航运交通线效益更高。实验/试验成功后, 英国立即将护航体制推广到90%的商船[28,33]。也有人认为, 护航体制使每次约有1/3的商船滞留在港口, 等待编入护航船队, 影响运输效率, 仅凭想象就认为应该用主动反潜取代被动护航。受此影响, 在二战早期, 英国在实行护航制度的同时, 将大量反潜舰编成多支猎潜编队, 在大洋上搜寻德国潜艇, 但如同大海捞针, 效果不佳。实际上, 战时护航船队是一种有效的“守株待兔”式的反潜方式, 事半功倍。战争时期的实践表明, 护航反潜的战绩远高于主动反潜大队[31,33]。
结合各种装备和战术的实验/试验始终贯穿于护航反潜的战争实践之中, 融入了实战, 催生了一些被实践证明有效的战术战法, 对盟军在大西洋战争中最终获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反潜困难时期, 英国军方要求大家献计献策, 此后相继出现了航空反潜深弹、机载雷达、无线电测向仪、“利式”探照灯、磁探仪(magnetic anomaly detectors, MAD)、声呐浮标以及机载反潜火箭弹等新式装备。
MAD出现后, 美国运筹小组提出了以下战术: 飞机进行“屏障巡逻”, 即在航道最窄处设置1个6.4 km×1.6 km的矩形区域, 2架飞机保持在长方形两对边线的相对位置上, 同时以184 km/h的速度绕圈飞行。这样, 长方形上的每一点均能每隔3 min被“访问”1次。即: 1艘60 m长的潜艇在2 kn流速下以2 kn航速潜航通过“屏障巡逻”区时, 机载MAD能有2次机会对其进行探测。发现磁扰信号后, 飞机进入“螺旋8字”跟踪飞行, 依次用发烟弹连续标示目标位置, 以此可粗估出潜艇航向和航速, 然后与水面舰进行协同攻潜。经过实验证明这种战术有效, 英国将这种战术投入使用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8]。
在封锁英吉利海峡时, 为有效使用30架装备雷达的巡逻机每30 min将2万平方海里的海区搜索一遍, 英海军设计了一套方案: 根据不同巡逻机的能力将巡逻区划分为12个大小不同的长方形框, 框的周长等于飞机30 min或60 min飞行的距离, 如周长等于60 min的航程, 就派2架飞机以30 min的间距绕圈飞行。方框的宽度及与相邻方框的距离大约是机载雷达发现水面潜艇距离的2倍。这就解决了速度、雷达各不相同的飞机之间的协同问题。可将这一严加封锁的狭长水域看作是一个堵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巨大软木塞, 因此这一战术以“软木塞”而著称。飞机沿长方框飞行时, 每隔30 min对整个区域搜索一遍。德国潜艇如发现雷达信号即行下潜, 很快就会耗完电量。为验证“软木塞”巡逻战术的可行性和检验实际效果, 英国在爱尔兰南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实兵实验/试验。英国“海盗”号潜艇奉命尽快在水面或水下完成90 n mile航程, 任务是躲避飞机的攻击, 同时确保潜艇到达目的地参加战斗。在28 h内, 潜艇只是间断性地在水面航行了2 h。潜艇曾9次浮出水面, 每次上浮的时间平均约13 min, 这显然不够充电或补充压缩空气之用。在距目的地还有5 n mile时, 潜艇因电量将尽而不得不上浮认输。在实际“参战”的19架飞机中, 只有2架飞机发现了潜艇, 且都未能在潜艇下潜前实施“攻击”。这次实验/试验回答了一个许多人长期质疑的问题: “飞机日夜巡逻, 却很少发现潜艇, 航空巡逻反潜意义何在?” 19架飞机中只有2架发现了潜艇, 却使潜艇自顾不暇, 完全丧失了作战力, 这一事实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28]。
盟军还根据实际作战需求, 进行了一些带有军事背景的科学实验。如: 英国通过海上实验证明, 白色飞机被发现的距离比黑色飞机近20%。于是将反潜飞机的下面都喷了白漆。事实上, 海鸥等海鸟就是以白色为掩护色[31]。
时至今日, 反潜战仍然是世界公认的难题。由于水下环境的复杂性, 许多因素对装备效能的影响程度并不清楚, 因此一些战术设想在不同条件下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也不十分确定, 需要通过大量的作战实验、试验、演习、甚至实战来摸索和验证。
3.1.3 二战时期的水面战和两栖战
仅靠新装备并不一定能保证取得优势, 还需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战法并进行实验/试验验证。二战初期, 美海军并未认识到应针对新出现的雷达采用新的战术, 而是采用密集单纵队占据“T”字形阵位以充分发挥舰炮火力的传统战法, 因而在所罗门群岛的早期夜战中屡遭日本“长矛”远程鱼雷的齐射攻击, 损失惨重。本来美军拥有火力和信息优势, 但却没能充分利用雷达来掌握战场态势和引导攻击, 将密集纵队暴露在敌方鱼雷攻击扇面内, 使己方的伤亡增加了4倍。后来美军尝试了新的策略, 组成了几支分别由3~4艘驱逐舰组成的小分队, 借助雷达保持分队合理位置, 舰艏对敌, 事先不再进行炮击, 协调转向, 实施鱼雷齐射。美海军通过结合实战的试验找到了利用己方雷达优势抵消敌方鱼雷优势的战术, 从而转败为胜[34]。
二战前, 美海军陆战队通过每年一度的登陆演习和相关作战实验, 开发和检验了《登陆作战试行手册》, 摸索出了火力、近距离空中支援和后勤保障方面的经验, 并在演习中结合技术试验, 推动了新型登陆装备的服役[3,35]。
在其他作战领域, 作战实验在德国著名的“闪电战”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3,17,36]。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则是通过战前作战实验不断验证新的战法, 在复杂对抗条件下接连成功击落敌机[37]。
这些战例展示了作战实验在战法创新和优化中的作用。
3.2 现代案例
现代作战实验通常包括作战概念开发、构造仿真、推演和实兵实验等环节。通过实兵实验, 可验证作战概念和模型、评估军事技术及能力, 验证战术、组织和流程。如: 美海军曾组织了长达5年的“海龙”系列作战实验, 从TTPs的基础性验证实验开始, 以大规模的综合性高级作战实验结束。
3.2.1 “寂静铁锤”实验
“寂静铁锤”实验于2004年进行, 其主要目的是验证“俄亥俄”级战略导弹核潜艇改装为战术巡航导弹核潜艇后纳入打击群的可行性。在实验主要对象“佐治亚”号潜艇上临时加装了“战斗管理中心”原形系统, 采用分布式情报监视侦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ISR)资源网络。2架有人飞机分别模拟中空和低空无人机(unmanned aircraft vehicle, UAV), 提供光电传感器功能; 一架波音707飞机搭载多任务ISR试验床(testbed)系统, 模拟星载传感器功能, 提供合成孔径雷达和地面移动目标指示; 陆上无人值守传感器提供地面态势感知; 另一艘潜艇潜望镜提供水面舰船光-电图像。前沿指挥单元、战斗管理中心的参谋人员、后方地面指挥单元及其参谋人员都可以通过一个“元数据架构”访问所有ISR信息。实验想定中还包括UAV、UUV的运用[5]。
3.2.2 新时代的“舰队问题”演习和实验
面对新的威胁, 经过数年的讨论和推演, 美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已重新恢复了“舰队问题”系列演习, 结合航母打击群(carrier strike group, CSG)的部署与训练, 探索和实践先进战术, 力图激发新一轮战术创新和变革。美太平洋舰队司令Swift上将认为, 尽管舰队具有基本战术素质, 但由于训练制度问题, 在例行训练中, 指挥官个人难有机会演练复杂的作战程序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从而限制了训练效率和TTPs的实际效能。因此, 应营造出能激发指挥官自身创造力和主动性的环境, 探索作战艺术和检验各种假设[38]。
首先要提出“舰队问题”演习中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 可通过推演来识别问题。在美海军战争学院的帮助下, 提炼出了友方兵力部署、敌方态势、作战任务(mission)及双方损失等关键要素, 将其作为“舰队问题”的输入,并设计了有助于发现问题的想定。美海军认为, 只有进行近似实战条件下的自由对抗, 才能发现问题中的关键因素, 从而找到解决方案。
当在潜艇威胁区运用CSG时, 传统做法是进行反潜, 而在“舰队问题”演习中, 舰队并不直接向CSG下达为完成某项作战任务(combat mission)而要执行的具体行动任务(task)(如“NLT 01100Z, 对……进行打击”), 而是在时间和进程上给指挥官以最大的灵活处置权。CSG的作战任务(mission)不是反潜, 而是在潜艇强威胁环境下执行核心作战任务——打击, 以支援联合作战。管控潜艇威胁是达到最终目的(打击)的手段, 若消灭了敌潜艇且己方也未受损失, 但未能完成所赋予的作战任务——打击, 则行动是失败的。演习组织者认为, 指挥应是基于作战意图而不是僵硬地执行计划, 因此并未事先规定CSG司令应如何管控潜艇威胁, 他可选择各种方案。在演习中的任务命令十分简单, 只体现了基本作战意图, 而开发(develop)具体行动任务(task)的任务由各作战单元或编队自行完成[38]。
每次“舰队问题”演习结束后, 主要指挥官都参加对抗部门(通常在舰上)的复盘, 在时间轴上来回移动, 仔细分析和讨论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每一个事件, 自我检讨, 总结技术和战术中的具体错误。通常由舰队外的高级军官充当双方的裁判和观察员。有时“舰队问题”演习与海军战争学院的推演并行进行, 随时相互通报和比较。每个“作战开发中心”和航母战斗群常派出十多名参谋参加演习, 他们在各作战部队中观察和学习, 将经验教训直接反馈到舰队训练部门, 有的参谋甚至在现场边观察学习边形成战术文件[38-39]。
2015~2017年共进行了超过6轮的“舰队问题”演习(第23~28次)。美海军认为, 恢复该系列演习是近年舰队作战中最重大的变化, 为学习作战提供了一个战斗实验室, 促使舰队全员共同思考作战问题,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完成作战任务(mission)的关键推动者(enabler)。目前的一些标准TTPs并不完善, 需要通过作战演习和实验来摸索[40]。
在2017年举行的第28次“舰队问题”演习中, “罗斯福”号航母率第9 航母打击群担任蓝军, 数艘驱逐舰组成侦察监视编队, 各舰拉开超出以往的间距, 前进到敌方能够发现CSG的安全距离之外, 引导CSG的飞机和舰船搜索目标, 并提出攻击建议。多个编队分散配置兵力可避免因一轮侦察或打击而全军覆没, 并有助于减小编队总体目标特征, 提高生存力。最新型“标准”导弹的射程已达350 km, 可在一体化火控-防空系统(naval integrated fire control-counter air, NIFC-CA)的支援下拦截各类空中目标, 为CSG提供有效的保护伞。显然, 海上分散部署是在针对远程反舰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出现后的海战进行作战实验和准备[41]。
尽管美海军一直未公布重启后的“舰队问题”系列演习的内情, 但高层透露的信息清楚地表明, 美海军正在重拾“光荣传统”, 将“舰队问题”演习作为学习战争的作战实验室和海军战术的开发平台, 驱动海上作战体系的优化重构, 开启对未来海战模式的新一轮探索。
3.2.3 海上无人装备的作战实验
美海军在2016年“海军技术演习”(ANTX)期间, 实验演示了“潜艇-UUVs-UAV” 母子式(mother-daughter)协同作战能力。潜艇先发射中型UUV, 中型UUV又发射2枚小型UUV和微型UAV, 执行侦察及通信中继任务, 实现了母平台(潜艇)对二级子平台(小型UUV)的直接指挥。
英国在2016年的“无人勇士”演习中, 实验演示了50多个UAVs、无人水面艇(unmanned surface vehicles, USVs)、UUVs等各类无人系统的侦察、反潜和反水雷能力。在反潜演习中, 首次运用4艘波浪滑翔式USV——传感器密集型自主远程艇(sensor hosting autonomous remote craft, SHARC)组成的持久机动探测网络来搜索和跟踪水下机动目标[42]。
3.2.4 “马赛克战”(Mosaic warfare)及其实验
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下属战略技术办公室(strategic technology office, STO)在2017年公布了获取非对称优势的新概念——“马赛克战”。马赛克是由无数个“马赛克碎片”组成的系统, 具有单元简单、功能多样、可快速拼装等特点, 且缺少部分片段并不会对全局造成很大影响。DARPA将未来战场描绘为: 低成本传感器、多域指挥控制节点、有人和无人系统等“碎片”实时灵活组合, 构成任务不同、灵活机动的作战网络。即使局部被毁, 系统也能及时反应, 基本维持整体作战效能。大量简单系统集成后具有很高的生命力, 可在战场上快速规划和构建作战资源网络, 配置兵力与后勤, 快速变换作战体系和交战环境, 使对手陷入判断和决策困境[43-45]。
为推动“马赛克战”概念和能力的发展, DARPA提出要发展“马赛克实验能力”。虽然“马赛克实验”目前仍处于概念开发阶段, 但美军已超前进行实验/试验技术研发和部署, 将利用各种实兵演习的机会, 针对作战规划、分布式作战、对抗环境下的通信和动态适应网络、低轨道星座、快响系统、无人装备和预置武器、多域指挥控制、智能系统等技术及集成系统, 进行一系列作战实验。
4 作战实验设计和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由于军事系统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 难以完全进行定量描述,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还需借助经验和直觉。但经验性的认识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 其客观性和稳定性较差。因此, 规范的实验方法十分重要。实验一般分为设计、实施、评估3个主要阶段, 美军在这3个环节所占时间比约为4∶2∶4[5]。对于大型实验, 一般需要数百人用1~1.5年进行计划。
作战实验设计和实施需关注如下要点。
4.1 规划与设计
4.1.1 目的与目标
实验设计应围绕目的及某项核心内容展开, 如: 开发或验证某种理论、评估某类装备或战法等。实验结果应能回答实验提出者所关心的问题。如前所述, 根据实验目的, 实验主要可分为3种: 发现型、假设验证型和演示型实验。一般而言, 发现型实验用于开发新概念和新方法; 假设验证型实验用于证伪(if-then形式的假设)或发现其限制条件; 演示型实验是对已知原理的重现, 其目的在于说服和传播[7]。
发现型实验往往开始于相对粗糙的新思想或新问题, 只是一些尚无法精确定义的概念性“命题”, 主要是对事件进行观察、定义和归类。需要通过深入的创造性思考, 将原始想法转化为有意义的变量、关系和条件。假设验证型实验的基础是发现型实验的结果, 实验的目的是形成说明性或因果性的知识, 从仅仅描述“发生了什么”(what)扩展到能解释“为什么发生”(how)。这类实验需清晰地表达一系列相关假设、确定合理可信的准则、明确一系列具体的限制条件[3]。
不同实验的区别之一在于实验的逼真度和对实验的控制。发现型实验的环境一般都是人为专门构设的, 目的是聚焦少数关键变量。需仔细选择观察对象, 确定合理的观察过程。为达到实验目的, 实验者可视情况制定新的规则、流程和组织方式。许多实验, 尤其是发现型实验, 都可能产生意料外的结果, 正是因为实验结果和预期不同, 所以往往更有意义。它们可能揭示某些理论缺陷或实验缺陷、发现新的现象和未预料到的限制条件、获取未知的因果关系等新知识。有时实验的目的就是发现问题, 而不仅仅是寻找答案。
4.1.2 问题设计
实验问题设计是对军事需求和实验目的的直接体现, 建立问题框架是实验设计的核心, 也往往是最困难的环节。
应明确基本实验问题、命题与假设、指标和准则、实验中的变量及其可能的关系。实兵实验关注的问题既可以是基于现有装备和兵力组织形式的战法开发问题, 也可是未来作战概念和思想的探索研究问题。随着实验研究的深入, 对作战问题的认识会逐步深化, 从而发现新的问题和影响因素。例如: 美海军陆战队为期2年的“城市勇士”系列实验表明, 城市战术在诸多方面很不理想, 于是开发出一套新的战术和训练课程, 并通过相关实验来考察其有效性。因此, 系列化实验、问题的逐步聚焦、相关概念的形成等, 是一个循环迭代过程[1]。
建立问题框架需要确定: 问题及其背景、问题分析目的(如概念验证、战法研究、能力评估)和目标、实验范围、实验对象、实验因素、评判准则及问题的形式化描述等。例如, 若对武器防御问题进行实验, 需确定: 实验目的是系统概念方案验证还是战法研究, 是针对单武器(如软、硬武器)系统还是综合防御系统, 若是硬武器, 评判指标是取拦截成功率还是平台总体生存率等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问题都需在问题框架设计中完成, 这样才能达到实验目的。
实验组织者一般都希望通过实验获知: 新装备及其使用方法的效能和优势, 新战术的可行性、有效性、优势和适用范围等等。要回答这些抽象问题, 就须针对具体对象设计一些分解后的详细问题。例如: 要通过实兵实验来探索和验证“海床战”等作战概念, 就需对系统及功能结构进行分解, 针对用户关心的投送、感知、目标指示、通信、载荷、响应速度及持久力等关键能力设计问题, 进而指导实验详细设计。鉴于军事问题的复杂性、关联性, 应避免过早缩小关注的问题, 也要尽量避免提出一些简单、孤立、模糊的问题。
4.1.3 实验规划
最初的想法和观点往往比较粗糙, 战争问题十分复杂, 仅靠有限的单项实验不足以产生和验证完整的作战概念, 难以完全发现全局性的问题, 为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方法, 加深对作战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并获得相关性、有效性、可重复性和可信性, 统筹规划、有计划地开展相互关联的系列化实验和综合性实验十分必要。
应避免针对某些孤立问题、或仅仅是为了响应上层意图而匆忙进行的“任务式”实验, 不应进行缺乏前期实验基础的“跳跃式”实验, 防止“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低水平重复。还要避免对某项特定实验期望过高, 超出了单项实验的能力范围。在单项实验里涵盖过多的内容, 易导致顾此失彼, 无法得到有效信息。
4.1.4 方案设计
作战实验设计是指, 根据实验目的和要求, 针对实验问题, 对实验要素、想定、方法和程序, 以及实施方案进行设计, 以达到预期目的。实验设计质量直接决定了实验结果及其事后分析的有效性。作战实验设计需部队、研究部门和实验机构共同参与。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不同的实验思路和方法, 对水下战而言, 分别关注隐蔽攻击、远程引导攻击、水下防御等不同主题的设计者, 会设计出不同的实验, 使之能回答(或部分回答)决策者、部队和分析人员提出的问题。
实验设计的主要内容有: 实验目标、分析框架、关键输入(自变量)、重点观察变量(主要因变量、关键中间变量)、输出、约束条件、实验指标及测量方法、实验想定、控制无关变量的措施、实验部队、评估人员、数据采集方法、实验步骤、统计方法, 以及评估方法等。
实验的主要风险有: 1) 在情况不明和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匆忙启动实验; 2) 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草率确定实验方案; 3) 采用试错法, 而不是依据理论指导实验; 4) 忽视部队的经验和创造力[7]。因此, 实验前应周密考虑和分析每一个步骤和可能的结果, 即进行“思想实验”。
实验指标反映了人们对实验问题的认识程度, 其主要选取原则: 1) 能表征问题的本质特征; 2)聚焦, 排除次要因素; 3) 客观公正性, 直接来自于实验, 避免引入主观因素, 不偏不倚, 最忌为某一预设结论寻找论据。
实验因素以及水平的选取——实验因素即实验变量。实验者应选择与研究目的有关的“控制因素”, 并阐述选择理由, 以便让实验人员能充分理解其对实验的影响。原则上应选取那些对实验结果影响大、相对独立、便于观察和数据收集的因素。水平是因素在实验中所取的状态, 即“实验点”。对于成本高昂的实兵作战实验, 难以承受水平数过大的实验。即使是作战仿真实验, 也尽量控制水平数。例如: 美国兰德公司在针对2005年台海军事冲突的仿真实验中共选取了7个因素, 其中有5个取2~3水平, 只有美军介入的部队数量这一项取6水平, 从实际分析结果看, 美军部队介入的数量取3水平(不介入/少量介入/中等介入)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17]。
为保证效益, 在实兵实验之前, 应通过充分的仿真实验来确定关键因素、揭示理论上的关联性、分析敏感性和敏感区间, 从而指导实兵实验方案设计。
4.1.5 想定设计
北约《指挥控制评估准则》(2002版)将“作战想定”定义为: “根据一定的研究目标和符合作战原则的情况假设,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与作战行动有关的作战区域、作战环境、作战手段、作战目标和其他事件进行的假想描述”。可见, 作战想定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 地域/海域, 参与方, 各方作战企图和目标, 各方兵力规模、作战能力和作战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 以及事态发展的时间表等。实验设计中制定作战想定的目的是为综合考察各种作战变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提供合适的条件, 确保分析的客观性、全面性[17]。简言之, “想定”是在演习和作战实验/试验中对交战双方的企图、态势以及战斗发展情况的设想和假定。实验想定应具有典型代表性, 从而能够从实验结果得出广泛意义上的结论。
想定所需的详细程度取决于实验的目标, 应合理把握想定的粒度。想定过细, 喧宾夺主, 可能会掩盖问题的本质, 难以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归纳; 想定太粗, 实验将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来支持结论[17]。
想定决定了实验的约束条件, 合理的想定是确保实验结果可信性的关键之一。在想定设计中, 应注意避免对实验结果先入为主的成见, 避免过早地排除可变因素。在实兵实验中, 为保证实验进程的可控性, 一般应给参与者以明确的提示, 如须采取的行动、不得采取的行动、何时可自行决策和行动等。
应提炼出实验的关键点和难点, 给予重点关注, 进行有针对性的想定设计。一般不应脱离实验目的套用“通用”想定, 应设计能突显问题的想定, 使实验能聚焦问题, 得到预期成果。例如: 若实验是为了探索或验证某种攻潜战术, 所设计的想定就不应让海上兵力花大量时间去搜潜。
4.2 实施
4.2.1 实兵作战实验与演习、训练、试验的结合
从形式上看, 实兵实验非常类似于演习, 但实验在目的、内容、方法及规则等方面毕竟不同于常规演习。必要时应说明两者的区别, 使参与者充分理解实验的目的——要解决什么问题。
应尽量结合训练、演习和OT&E进行作战实验, 因为平时难以获得这样丰富的兵力和保障资源。大多数国家没有专职于实验的部队和编制, 因此就需考虑如何利用常规训练、演习等活动。实验和训练、演习、试验相结合的意义不仅是节约资源, 更是可利用关联的实践活动相互支持、丰富内容, 通过实验与实践相结合, 达到探索、研究和验证的最佳效果。
4.2.2 实兵作战实验中的模拟兵力
模拟兵力主要可分为2种: 计算机虚拟兵力和替代兵力。
在美军“千年挑战2002”联合军演中, 非野战参演人员超过2000人, 野战演习有13500名官兵参加, 虚拟兵力达到7万人。演习中80%的战斗都是模拟的, 分布在17个计算机网络和模拟器上进行。该演习是美军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实兵与模拟相结合的演习, 检验了美军许多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原则[46]。NUWC则是利用SETI生成海上虚拟兵力和兵器, 与实兵一起进行海上作战训练、实验和试验[19]。
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 可用替代装备和原型装备进行作战实验。如: 美国在当年的“舰队问题”演习中, 由于航母数量不够, 曾用其他舰只代替航母, 用一架飞机代表一个机群。再如: 受“凡尔赛条约”的制约, 德国二战前很长时期没有潜艇, 邓尼茨便使用驱逐舰和鱼雷艇替代潜艇进行“狼群战术”的作战实验。德军在“闪电战”作战实验中, 则是用运输车代替坦克。
4.3 分析与评估
4.3.1 分析和评估队伍
应建立包括实验需求开发者、实验设计者、部队人员、装备设计师以及专业实验/试验人员在内的分析评估队伍。作战实验最忌虎头蛇尾、简单总结、匆匆收场。实验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得出结论, 更重要的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 找到解决问题、改善能力的途径。这需要得到更大范围的专家智囊队伍的支持, 常需要跨领域专家、科学家、军事运筹专家及数学家的协作。
专家智囊在作战分析中的作用有目共睹,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英国Blackett教授(后获诺贝尔奖)及其团队在二战反潜战中的重要贡献。他和助手们组成了运筹(operations research)小组, 在对军方提供的作战报告和大量作战数据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后, 总结出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从而大大提高了英军的反潜效率。例如: 经过对护航船队数据的分析, 布莱克特认为护航船队规模越大, 效能就越高。根据圆面积和周长的数学关系, 船队中的商船数目每增加一倍, 护航舰艇的数量只需增加33%即可。此外, 扩大护航船队规模, 减少出航次数将会减少总体被发现概率。一支护航船队所受损失到了一定程度后便不会再增加, 这是因为被“狼群”击沉的船只数量受限于潜艇数量、鱼雷携载量和再装填能力。因此, 一支艇群攻击一支大型船队所能击沉的船只数量与攻击一只小型船队时基本相同, 而一支大型护航船队的规模相当于2~3支小型护航船队, “狼群”却只有1次攻击机会。该建议在付诸实施后收到了巨大成效[33]。运筹小组还为英海军改进了航空深弹攻击方法, 提高了命中率; 甚至还和战术开发小组共同提出了一种将声呐浮标与MK 24自导鱼雷相结合的攻潜方法[28]。
美国的一些部门和机构有专门的分析评估团队, 他们将作战分析与实验评估、战场评估结合在一起, 为美海军提供广泛的支援。例如CNA就是从早期美海军反潜战运筹小组发展而来, 下属部门中包括先进技术和系统分析部门和作战评估组(operational evaluation group, OEG)。后者主要针对战场项目(field program)分析和探索作战问题, 研究部队训练程序和技术, 评估新的作战概念及其效能。在重大军事任务期间, OEG派分析人员深入到各地指挥部和一线作战部队。
4.3.2 实验结果分析
实验的目的并非仅是获得结果, 而是要找到原因、摸清机理和规律, 这就涉及到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解释问题。对实验中发现的现象做出理论解释并得出结论, 是整个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认识阶段, 也是作战实验中最深刻、最有指导意义的部分[17]。
实验报告应包括: 实验想定、模型、假设、限制条件、主要数据源、作战过程分析、实验结果及其意义、主要影响因素及敏感性等。与常规试验报告不同, 实验报告不仅是对实验过程和结果的客观描述, 更要注意阐述现象及其意义、分析原因、提出下一步实验建议[47]。有些作战实验可能得到意外的结果, 这常可产生更大的启发作用, 促使作战分析人员深入挖掘背后的原因, 激发新思路。
实验分析大都采用统计分析方法, 但目前存在的普遍现象是对数据变化分析、原因分析等工作做得不深入, 即: 重一般数据统计和平铺直叙, 轻关键变量分析和深度解释。问题分析流于简单化、表面化, 一些所谓的“综合分析”变成了模糊、粗糙、“八股文”式的定性分析的代名词, 这往往导致对数据背后的含义解释不清, 难以发现真正的规律,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作战实验作用的发挥。这种浮于表面的实验分析所导致的一个现象就是: 各次实验总结报告除一些具体数据外, 内容雷同, 建议空洞, 更像是情况通报, 而不是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报告。
作战实验就是发现问题、寻求因果关系, 但在现实世界中许多因果关系并不明晰, 大数据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将因果分析转化为相关性分析。在现实中, 这种方法能解决许多工程应用问题, 许多现代人工智能方法秉承的也是这一思路。水下作战实验十分复杂, 人们对许多现象的物理机理及因果关系尚未掌握, 大数据分析可在某些场合下发挥作用, 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实际上, 大数据分析的意义在于其多维度和完备性, 这2个特性使得看似无关的现象联系起来, 形成对客观事物全方位的完整描述。
4.3.3 关于效能评估问题
虽然上层通常最关心的是装备或战法的作战效能, 但要通过有限几次实兵实验和演习对作战效能做出准确评估是不现实的。作战效能应建立在足够数据量的统计分析之上, 一般而言, 仿真是主要分析手段, 实验和演习是主要验证手段。
效能分析和评估主要有2种途径: 1) 采用形式化的效能评估模型。如: WSEIAC(weapons systems effectiveness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模型、指数(index)法、SEA(system effectiveness analysis)法、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等。但迄今为止, 各种效能评估模型都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理论上没有得到证明, 这就使其科学性大打折扣。此外, 这些模型一般都是静态的, 很难反映出动态作战过程。2)基于仿真的统计评估方法。这种方法更直接, 相对客观、可信, 是国内外效能评估的主流方法, 当然还需结合各种实验、试验和演习对模型进行验证[48]。
4.3.4 评估结论
实验评估阶段要回答“实验收获了什么”的问题, 这是从感性到理性的知识升华过程。须避免依赖试错法和“就事论事的评估”, 而应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证性评估。
不应完全按严格的学术标准得出实兵实验的结论, 也不应以少数几个实验作为重大决策的依据。仅凭个别实验就大胆给出重大结论报告的现象经常出现, 有些研究者往往声称已掌握“证据”证明某重要概念或思想具有重大军事价值, 但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风险很大[7]。实验结论在多数情况的普适性和在对抗条件下的适用性值得重点关注。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不能仅靠直觉, 而要靠严密的理论分析。这样的教训很多, 如: 二战中美潜艇艇长担心暴露而不愿使用对空雷达, 这是由于使用雷达时发现的飞机数量确实增加了, 然而, 分析表明潜艇周围敌机的密度并未增加, 而发现敌机数量的增加完全是因为雷达的探测距离增大。再如: 1943年, 德国对潜艇在比斯开湾经常到飞机夜袭一直迷惑不解——盟军飞机为何能在夜间对德国潜艇准确定位?为何曾十分有效的“梅托克斯”雷达侦察机不报警?起初, 德国情报军官曾正确地猜测出盟军使用了厘米波雷达, 于是加装试用了新型雷达接收机, 但因产品不成熟而效果不佳, 德国人转而误认为是老式“梅托克斯”接收机本身的电磁辐射暴露了潜艇位置。尽管大多数无线电专家对此不认同, 邓尼茨还是下令停用, 这成了二战中“电磁辐射恐慌”的大笑话。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只要千方百计去寻找, 几乎任何观点都可能找到论据加以证实。邓尼茨竟将“梅托克斯”接收机的辐射现象同过去许多难以理解的事情联系起来。巧合的是, 在该型接收机停用的时段内, 德国潜艇在比斯开湾的损失为零, 这使希特勒信以为真。而实际原因是, 德国潜艇通过该区域的数量减少了, 且采取了夜间在水面沿雷达不易发现的海岸航行的措施[28]。另一个例子是1940年德国V2导弹对伦敦的大轰炸。从报纸上公布的标记有遭轰炸地点的伦敦地图中, 人们发现轰炸点分布很不均匀, 于是引起了各种猜疑, 军方担心V2导弹具有很高的精度, 以至于德军能够选择攻击目标; 民众则以为那些未遭攻击的地区是德国间谍居住地, 有人甚至开始搬家。更有甚者, 有人根据导弹落点更多散布在伦敦东部平民区而推测, 德国是故意激发英国的阶级对立, 影响民众的抵抗意志。直到战后, 有人用网格法从数学角度分析了轰炸数据后发现, 虽然落点不均匀, 但完全符合特定随机分布。事实上V2导弹在当时是精度很差的武器。可见, 依据事实的深入科学分析和仅凭表象的主观臆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要使评估结论具有说服力, 就应给出充分的证据。但正如上例所述, 对于任何观点, 只要有目的地去竭力寻找, 几乎都可能找到支持的论据, 这往往来源于人们先入为主的“选择性偏倚”。这就提出了证据的有效性和可信性问题, 具体涉及到证据的真实性、相关性、稳定性和时效性等。尽管有些证据是真实的, 但可能并非主要因素, 且与主题的相关性弱、重要性低。稳定的证据应具有可重复性, 对于多平台、多区域、多时段具有一致性。应关注证据的时效性, 有些证据强度会随时间减弱。对证据本身的评价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可尝试根据置信程度对证据进行分级, 如询证医学中的5级证据分级方法。同样的事实用作不同领域的证据时, 有效性是不同的。对于军事领域而言, 数据来源的权威性直接决定了证据的质量, 可作为证据分级的参考依据。总之, 证据是科学评价的基础, 证据质量决定了评估结论的置信度。因此应对实验证据问题高度关注。
5 结束语
作战实验作为现代军事科学的助推器, 正受到广泛重视。西方在进行实验活动的同时, 也在进行作战实验问题的理论研究。1999年, 美军指挥与控制研究项目组(command and control research program, CCRP)发布了首版《作战实验法规》及“实验程序清单”, 此后又根据实践不断更新; 2002年, 北约发布了《指挥与控制评估法规》。这些文件的发布规范了作战实验活动, 推动了作战实验向科学、有效的方向深入。
实兵作战实验之所以重要, 其中一个原因是作战过程中的“涌现性”。涌现性(emergent properties)是指系统具有各构成要素所不具备的性质, 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一般认为, 系统结构、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系统整体性能, 有些性质只有在高层次系统中才会出现, 即所谓“涌现”。在自然界中, “涌现性”典型的例子有: 蚂蚁和蚁群、神经元和大脑等。作战过程显然具有涌现性, 尤其是复杂的水下战, 往往会因各种未知要素的交互作用而出现意料外的情况。正如美海军Fitzgerald将军当年为一个水下战研究项目在美众议院听证时的形象比喻: “反潜战是一个取决于环境的、巨大的复杂问题。只靠买潜艇和飞机解决不了这一问题。它就像一个拼图, 需要100拼块才能构建出完整图像, 而我们可能只掌握了45块……。某一天运气好, 我们可能又掌握了30块……。”[49]。水下战的复杂性正是源于环境的复杂性和诸多因素交织而产生的涌现性。因此, 现有许多理论模型往往是不很可靠的, 仅靠理论分析和仿真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需要通过近似实战条件下的作战实验来发现现象, 为下一步揭示机理、利用现象和制定对策提供输入。
作战实验是作战开发及验证的主要手段, 西方国家将作战概念和战法创新建立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近年来, 美军对未来作战概念进行了大量开发和早期实验。如美军提出了可用于支援未来多种作战行动的信息引诱战, 其目的是诱敌机动—开启主动传感器—使用武器。其下的一系列战术概念与美AUV发展规划中的电磁机动战(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maneuver warfare,EMMW)、“欺骗战”、“海床战”等概念一脉相承。例如: “猎手-杀手”概念是指用低成本的非隐身平台唤醒敌方目标, 如使用可模拟潜艇或鱼雷特征信号的UUV, 诱使敌方潜艇做出反应, 再由杀手平台摧毁目标; “武器海绵”战术是指用多谱诱饵和信息欺骗技术, 引诱对手向假目标发射武器, 使敌方浪费武器和暴露位置, 增加敌方目标识别的负担, 通过信息过载造成反应滞后, 从而使本方获得主动权; “虚拟佯攻”战术是指使用多谱诱饵和其他欺骗技术, 误导对手, 使其将ISR资产投入到错误方向上; “信号特征增强”战术是指通过在敌平台上附着某些信标或浮标进行“标记”。此外, 还有“通道作战”、“反堡垒区”、“水下打击模块”等其他作战概念。美国正在开发一系列与这些作战概念相关的新型水下战装备和技术, 并将进行相关作战实验和试验[50]。
在军事科学领域, 军事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和作战实验是相辅相成的3个基本支柱, 作战实验的主要作用在于对军事科学问题进行实证[51]。要想避免“坐而论道”、“纸上谈兵”, 就要勇于进行实兵实验, 通过不断实践, 逐渐发展出顺应时代潮流的、科学合理的作战学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预实践”是探索真理、寻求真谛的必要途径——这就是实兵实验的意义所在。
[1] 曹欲华, 管清波, 白洪波, 等. 作战实验理论与技术[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3.
[2]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Guide for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Defense Experimentation[R]. US: The Technical Cooperation Program, 2006.
[3] McCue B. Military Experiments before World War II[M]. US: Wotan’s Workshop, 2009.
[4] 钱东, 赵江, 杨芸. 军用UUV发展方向与趋势(上)——美军用无人系统发展规划分析解读[J]. 水下无人系统学报, 2017, 25(1): 1-30.Qian Dong, Zhao Jiang, Yang Yun.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UUV(Ⅰ): A Review of U.S. Military Unmanned System Development Plan[J]. Journal of Unmanned Undersea Systems, 2017, 25(1): 1-30.
[5] 李辉. 美军作战实验研究教程[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3.
[6] Shephard News Team. SeaFox Takes Part in US Navy Fleet Experiment[EB/OL]. (2012-09-10)[2015-05-29]. http://www.shephardmedia.com/news/uv-online/seafox-takes-part-us-navy-fleet-experiment/.
[7] Alberts D S, Hayes R E. Campaigns of Experimentation: Pathways to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Code of Best Practice)[M]. US: DoD CCRP, 2005.
[8] 钱东, 赵江. 关于战术、技术与程序的思考与启示[J]. 鱼雷技术, 2015, 23(4): 241-256.Qian Dong, Zhao Jiang. Discussion on Tactics,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J]. Torpedo Technology, 2015, 23(4): 241-256.
[9] 王凯, 赵定海, 闫耀东.武器装备作战试验[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
[10] Kass R A, Alblerts D S, Hayes R E. 作战试验及其逻辑[M]. 马增军, 孟凡松, 车福德, 等译.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11] 吕广跃, 方胜良.作战实验[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12] 江敬灼.作战实验若干问题研究[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0.
[13] 陈建华, 李刚强, 傅调平.舰艇战法实验与分析[M].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14] 卜先锦, 张德群. 作战实验学教程[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3.
[15] 战晓苏. 作战实验工程基础教程[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3.
[16] Albers D S(美). 军事实验最佳规程[M]. 郁军, 周学广, 译.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9.
[17] 王本胜, 赵子海. 战法实验理论与方法[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7.
[18] 周玉芳, 余云智, 翟永翠. LVC仿真技术综述[J]. 指挥控制与仿真, 2010, 32(4): 1-7.Zhou Yu-fang, Yu Yun-zhi, Zhai Yong-cui. Review on LVC Simulation Technology[J]. Command Control & Simulation, 2010, 32(4): 1-7.
[19] 钱东, 唐献平, 崔立. 美国海军预研中的鱼雷新技术[J]. 鱼雷技术, 2003, 11(1): 1-5.
[20] 廖德力, 钱东, 高军保, 等. 鱼雷及其武器系统的作战试验与评估(OT&E)[J]. 鱼雷技术, 1998, 6(4): 39-43.
[21] 钱东, 崔立. 美军的先期概念技术演示验证[J]. 鱼雷技术, 2002, 10(4): 1-5.
[22] Center for Naval Analyses. CNA 1942~2017[EB/OL]. 2017[2017-08-12]. https://www.cna.org/.
[23] 胡斌, 王晓彪. 美军作战实验室发展综述[J]. 军事系统工程, 2000(3): 32-36.
[24] Leopold J. How Guantanamo Became America’s Interrogation ‘Battle Lab’[EB/OL]. (2015-01-12)[2015-05-10]. https:// news.vice.com/article/how-guantanamo-became-americas-interrogation-battle-lab.
[25] 谭星. 全甲板攻击——战火中成长的美国航母[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26] Wadle R D. United States Navy Fleet Probl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rrier Aviation, 1929-1933[R]. US: Texas A&M University, 2005.
[27] Ensign Hederman. Blocks up the Panama Canal[EB/OL]. (2018-07-04)[2018-07-04]. http://www.strategypage.com/ cic/docs/cic127b.asp.
[28] 普赖斯A(英). 空潜战[M]. 韦晋光, 李安林, 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0.
[29] 安东尼·普雷斯顿(英). 潜艇发展史[M]. 李加运, 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9.
[30] 刘桓. 大西洋上的狼群——希特勒的狼群[M].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3.
[31] 王志强. 护航大海战[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0.
[32] 卡尔·邓尼茨(德). 德国海军战略[M]. 上海外国语学院,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33] 戴维·乔丹(英). 大西洋潜艇战——希特勒的狼群[M]. 张国良, 胡伟, 谢伏娅, 译.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10.
[34] 韦恩·休斯(美). 舰队战术和近岸战斗[M]. 易亮, 译.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6.
[35] 伊恩·斯佩勒, 克里斯托弗·塔克(英). 抢滩——两栖战的战略、战术和战例[M]. 张国良, 谷素, 译.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10.
[36] 富勒J F C(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略与战术[M]. 胡毅秉,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37] 陈辉亭. 中国地空导弹部队作战实录[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38] Swift A S H. Fleet Problems Offer Opportunities[J/OL]. Proceedings, 2018, 144/3/1, 381. (2018-07-05)[2018-06- 16].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8-03/fleet-problems-for-opportunities.
[39] Rielage D. Bring Back Fleet Battle Problems[J/OL]. Proceedings, 2017, 143/6/1, 372. (2017-06)[2018-08-04].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7-06/bring-back-fleet-battle-problems.
[40] Eckstein M. Fight to Hawaii: How the U.S. Navy is Training Carrier Strike Groups for Future War[EB/OL]. (2018-03-22)[2018-08-04]. https://news.usni.org/2018/03/ 22/fight-hawaii-u-s-navy-training-carrier-strike-groups- future-war.
[41] 羽旌. 决胜未来海战场——美海军重启“舰队问题”演习原因浅析[J]. 舰船知识, 2018(6): 34-39.
[42] 钱东, 赵江, 杨芸. 军用UUV发展方向与趋势(下)——美军用无人系统发展规划分析解读[J]. 水下无人系统学报, 2017, 25(2): 107-150.Qian Dong, Zhao Jiang, Yang Yun.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UUV(Ⅱ): A Review of U.S. Military Unmanned System Development Plan[J]. Journal of Unmanned Undersea Systems, 2017, 25(2): 107-150.
[43] Bellamy W. DARPA Seeks ‘Mosaic Warfare’ Approach to Future Conflicts[EB/OL]. (2018-09-06)[2019-09-15]. https://www.aviationtoday.com/2018/09/06/darpa-seeks-mosaic-warfare-approach-future-conflicts/.
[44] Magnuson S. DARPA Tiles Together a Vision of Mosaic Warfare[EB/OL]. (2018-01-08)[2019-09-15]. https:// www.defensemedianetwork.com/stories/darpa-tiles-together-a-vision-of-mosaic-warfare/.
[45] Williams B D. DARPA’s ‘Mosaic Warfare’ Concept Turns Complexity Intoasymmetric Advantage[EB/OL]. (2017- 08-14)[2019-09-15]. https://www.fifthdomain.com/dod/20 17/08/14/darpas-mosaic-warfare-concept-turns-complexity-into-asymmetric-advantage/.
[46] 柯林. 作战模拟与伊拉克战争[J]. 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 2003, 17(3): 54-57.
[47] 王剑飞, 张辉, 岳秀清, 等. 关于加强我军作战实验结果分析和解释的思考[J]. 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 2007, 21(4): 59-61.
[48] 钱东. 关于战术、对装备论证中有关问题的认识[J]. 鱼雷技术, 2006, 14(4): 1-6.Qian Dong. An Understanding of Equipment Demonstration[J]. Torpedo Technology, 2006, 14(4): 1-6.
[49]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dvanced Submarine Technology and Antisubmarine Warfare[M]. US: Uni- versity Press of the Pacific, 2005.
[50] 黄承静, 魏佳宁, 姜百汇, 等. 预己从严: 兵棋推演及其应用[M].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5.
[51] 王辉青. 作战实验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J]. 军事运筹与系统工程, 2008, 22(1): 3-8.
作者.题目(年-卷-期)
1. 黄颖淞, 葛辉良, 王付印, 等. 蛙人探测声呐系统发展综述(2020-28-1)
2. 孙芹东, 兰世泉, 王超, 等. 水下声学滑翔机研究进展及关键技术(2020-28-1)
3. 何心怡, 陈双, 陈菁, 等. 国外反潜训练靶标应用现状与启示(2019-27-6)
4. 钱洪宝, 卢晓亭. 我国水下滑翔机技术发展建议与思考(2019-27-5)
5. 吴尚尚, 李阁阁, 兰世泉. 水下滑翔机导航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2019-27-5)
6. 文海兵, 宋保维, 张克涵, 等. 水下磁耦合谐振无线电能传输技术及应用研究综述(2019-27-4)
7. 刘伟, 范辉, 吕建国, 等. 超高速水下航行器控制方法研究热点综述(2019-27-4)
8. 严浙平, 刘祥玲. 多UUV协调控制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2019-27-3)
9. 黄玉龙, 张永刚, 赵玉新. 自主水下航行器导航方法综述(2019-27-3)
10. 胡桥, 刘钰, 赵振轶, 等. 水下无人集群仿生人工侧线探测技术研究进展(2019-27-2)
11. 王延杰, 郝牧宇, 张霖, 等. 基于智能驱动材料的水下仿生机器人发展综述(2019-27-2)
12. 魏博文, 吕文红, 范晓静, 等. AUV导航技术发展现状与展望(2019-27-1).
13. 张萌, 谭思炜, 张林森. 美海军三型鱼雷最新研发进展及技术途径(2019-27-1)
Summary of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at Sea——Concepts, Cases and Methods
QIAN Dong, ZHAO Jiang
(Naval Research Academy, Beijing 100161, China)
The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is the key part in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 concept and tactics, force application and forc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 scientific and military significance of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main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organizations and activities of the U.S. Navy. Some historical and modern cases of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s are introduced, including the famous “Fleet Problem” exercise of the U.S. Navy and the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of undersea warfare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Some issues abou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experiment are discuss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objective of the experiment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aiming at discovering new phenomena and mechanisms. A reasonable problem frame is a prerequisite for a successful experiment. Systematic planning should be made for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avoid isolated and “jumping”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al factors and levels, and the partitions and specificity of operational scenarios should be considered properly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nfidence of experiment results. A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should combine with exercise or training to achieve best results in limited resources condition. Professional teams of analysts and experts are needed to analyz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evidence with scientific method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is a necessary way to develop modern warfighting theory.
live warfighting experimentation; military excise; undersea warfare
E0-03; E112; E139
R
2096-3920(2020)03-0231-21
10.11993/j.issn.2096-3920.2020.03.001
2018-12-06;
2019-01-04.
钱 东(1958-), 男, 高级工程师, 长期从事鱼雷武器系统总体技术研究.
钱东, 赵江. 海上实兵作战实验综述——概念、案例与方法[J]. 水下无人系统学报, 2020, 28(3): 231-251.
(责任编辑: 陈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