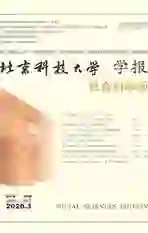打开女性叙事的空间
2020-06-22吕欣桐
吕欣桐
〔摘要〕 文章基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对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中女性叙事空间的建构展开分析。文章兼具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从多重女性叙事声音、叙事节奏与层次、隐喻的叙事系统等方面探讨了《盲刺客》如何展现处于失语状态的女性生存境遇,并借由文本中的隐喻象征系统打开新的叙事空间,建构起女性书写的权威。
〔关键词〕 女性叙事;声音;叙事空间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3-0111-0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是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在《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这部小说中,阿特伍德所展现的多元后现代叙事技巧,与作品本身浓烈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颇具震撼的张力。小说之所以触动读者,不单单源于其技巧的繁复奇绝,更是因它蕴含的丰厚充沛的情感和文学性。阿特伍德的创作高峰始于1970年代,正值西方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浪潮兴盛时期,其作品呈现了女性主义文学实践的丰厚与深度。阿特伍德始终关切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其多部长篇小说如《使女的故事》《别名格雷斯》《猫眼》等都采用女性叙述者的视角,随着作者年纪的增长,作品主人公的年龄也在相应地变化。
获得2000年布克奖的《盲刺客》是阿特伍德的第十部作品,亦是她笔力成熟的代表作。目前对于《盲刺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剖析作者迷宫式的写作技巧、结构架设,并从历史元小说等角度讨论叙事与历史真实性的复杂关联[1];二是将作品置于女性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兴发之中,从女性主义角度分析文本所揭示的20世纪前半叶西方社会中的阶级问题与父权制度下的性别压迫与不平等 [2]。现有研究或侧重于文本形式分析,或聚焦于主题内容讨论,较少将表层书写与主旨辨析建立起更为有机的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一脉,注重以性别政治视角弥补传统叙事学对历史语境的忽略。笔者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出发,力图打通话语层次与故事层次的分隔,探讨小说作者是如何通过文本表层系统的叙事技巧来建构女性作者与女性主人公的声音权威,并呈现了具有穿透力的女性生命境遇。
一、 叙事声音中的多重女性
叙事学上所说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者。詹姆斯·费伦是这样给声音做定义的,“声音尽管以文体为中介,但就像巴赫金所说,声音比文体具有更多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终将是超文体的。它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3](20)作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创始人,苏珊·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中提出,文本中的女性声音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4]。女性的叙述声音背后是社会权力问题,用声音建构权威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目标。
(一) 作为“叙述者”的艾丽丝
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按照叙述者在叙述中是否参与故事,将其分为“异故事”的叙述者和“同故事”的叙述者。在《盲刺客》文本中,女主人公艾丽丝即为同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小说主干部分是艾丽丝对家族历史与人生往事的回忆。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视点在阿特伍德笔下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关于叙述视点,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有这样的论述:“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5](128)在《盲刺客》中,正是叙事视点的交错与裂隙创造了阅读的兴趣、冲突与悬念。老年艾丽丝是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年轻的艾丽丝则是她所叙述的一个人物,她们二人发出的声音是参差不齐的。老年爱丽丝的声音是怀旧苍凉的,常以讽刺的语气出现,在描述晚年日常生活时,她不断地对过去的自己进行省察与反思。回忆中年轻艾丽丝的声音则是无助、软弱而充满牺牲精神的。对于二者的分裂,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可以充分呈现出来,即艾丽丝在晚年看到自己年轻时结婚照片时的感受:
“这是那个婚礼的场面:一个年轻女子身穿斜裁的白色缎子连衫裙……我之所以称‘她,因为我不记得自己在场;我的心并不在,在场的只是我的軀体。我和照片上的那个女孩不再是同一个人。我只是她在生活道路上一往无前的结果。”[6](122)
通过这种多元的、不断深入又跳出人物内心世界的叙述视角,读者看到了叙述者艾丽丝在晚年的生活状态,看到了她在回忆家族史时对男权中心社会氛围的反思,在身处其中时对父权制度的盲视。多重叙述视角的采用,不是因为作者想要炫技,而是她以“隐含作者”之姿表现出自己对女性话语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追求。阿特伍德在谈及加拿大的生存境遇时曾说:“只有你在时空中是有定位的、有方向的,你才能拥有寻求自我的奢侈自由,加拿大曾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所以它缺失了那种位置感和方向感。”[7](21)年轻的艾丽丝就像是父权制下的被殖民者,她被男权话语边缘化、失语化,因此失去了自我定位和方向。但是老年艾丽丝在回忆中不断使用内在聚焦的叙事方法提升话语权,借助诉说往事来反驳社会对她的规训与控制。这种内部聚焦的叙事策略赋予了女性叙述者一种独特的力量,能够穿透传统的两性权力关系,建立起一种女性独有的声音空间。
艾丽丝的英文名Iris,在古希腊神话中指彩虹女神。作为神的信使,彩虹女神不会根据主观喜好擅自改变神的命令,她总是在传播真实。但是在《盲刺客》故事中,艾丽丝却是一个现代主义小说中常见的“不可靠叙述者”。她常常是先给出了一个事实,然后又否定它,或者是提出一个疑问,又把这个疑问悬置起来不给出回答,或者说叙述者自己也不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作者以传播绝对真实的彩虹女神之名来命名叙述者,正暗含一层反讽的意味。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认为“构成故事环境的各种事实从来不是‘以它们自身出现,而总是根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呈现在我们面前”[8](65)。当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不同的事实。阿特伍德将艾丽丝的回忆录与新闻报道并置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叙事性的试验探究。根据历史编纂元小说理论,历史与小说均属人为建构物,历史元小说即是对此有清晰自我认知的作品。艾丽丝撰写的回忆录既具有元小说的自我指涉性,同时又不断强调历史书写与写作的不可靠和随意性,文本中充满了对历史和个人事实的涂改、操纵和回避。这一对虚构性的有意呈现使得叙述者的声音更加驳杂,在同一叙事层面上引发出异响与变形的回声。不同的叙事层次编织在一起,像是小说中盲童编织的炫目的毯子,而小说所具有的拼贴画般的形式本身则成为了艾丽丝个人回忆拼贴性的一个隐喻。
(二) 作为“聚焦”的劳拉
小说中,虽然艾丽丝是叙述者,但文本的聚焦中心却常常在她的妹妹劳拉身上。小说的开头就是描写劳拉的死亡:“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6](1)这是小说得以展开的中心事件,劳拉的自杀不仅影响着叙述者对于家族历史的追溯方式,而且在几十年后还影响着她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第一章,叙述者显然无意为读者揭晓劳拉自杀的原因,她说,劳拉的汽车坠下桥的一刹那,“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她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亚力克斯,想到了理查德,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也许想到了上帝,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6](2)这一连串的疑问聚焦在劳拉的所思所想上,或者说是聚焦在艾丽丝所想象的劳拉的所思所想上。虽然叙述者的声音没有变化,但这个场面的聚焦却从叙述者转移到了人物劳拉身上。在小说中,这样的场面出现过无数次,我们不断透过艾丽丝的眼睛去看劳拉。劳拉作为一个被聚焦者,她的主观性其实并不属于她,而是与叙述者艾丽丝的主观性息息相关,她在不断被观察着,她的内心生活被揭示,外部聚焦者被赋予了深入被聚焦者意识的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充满了对劳拉外貌的详细描写,但年轻艾丽丝的形象描写却呈现空缺状态。以色列叙事学家施劳密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认为,“人物”作为抽象故事的一个内部构成,可以通过一个完整的人物特征网络来加以描述,而文本中分布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标记,一是形容词和抽象名词对人物的直接形容,二是通过言语、行动、外表、环境等间接表现。[9](106)在间接表现中,外表与性格之间的转喻关系成为了许多作家有力的工具。在小说中,我们多次看到叙述者对于劳拉形象的描写颇具人物性格或处境的暗示性,譬如:
“她披着金黄色的长发……长着挺直的鼻子;鹅蛋脸;一对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两道弯弯的眉毛茫然地微微翘着。下巴的线条略带固执,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是不会发现的。”“漂亮、优美、天然。它具有那个时代所有那些有教养的女孩子的纯洁和娴静。这张脸像一张白纸,应该是让别人写的,而不是去写别人。”[6](45)
通过外貌描写,作者烘托并暗示出劳拉身处的压抑传统社会环境。与对劳拉的详细描写不同,我们几乎找不到对于青年时期艾丽丝外貌或形象的直接描写。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艾丽丝有意将自己的形象隐藏在劳拉的形象之后,她躲在“劳拉投下的长长的阴影里”,认为那“是个安全的地方”。其次,刻意回避或是作者为误导读者所设计的文字圈套。减少对艾丽丝形象的具体描绘,会把读者的目光和兴趣更多集中在劳拉身上,也会天然倾向于认为《盲刺客》小说中的金发女主人公“她”是指劳拉。
小说中一组有意味的对照是“劳拉形象阴影下的艾丽丝”和“艾丽丝声音覆盖下的劳拉”。艾丽丝的形象隐身于劳拉之后,而劳拉的个人声音却被艾丽丝的叙事权威所覆盖,这种矛盾和龃龉增强了二人之间的联系,也暗示了她们关系中权力交错的状态。通过叙述者的聚焦,读者看到了劳拉短暂一生中的火花,观察到复杂微妙的姐妹感情和艾丽丝不断试图去否认、压制但始终无法摆脱释怀的那份对劳拉的负罪与后悔之情。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劳拉的声音却始终被叙述者的声音所覆盖,因此呈现为奇妙的对照——劳拉既是文本的聚焦中心,又是文本中最大的空缺,是那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
(三) 其他女性人物的声音
1 瑞妮:代行母职与传统沿袭者
在艾丽丝和劳拉的母亲去世后,保姆瑞妮实际上代替了母亲的形象与职责,照顾着姐妹俩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另外,她还是纯朴的女性智慧的传达者,既强势又充满保护欲,并且格外看重当时的社会规范和行为道德。在姐妹俩母爱缺失,父爱也职责缺位的少年时期,是瑞妮将关于女性气质的要求灌输给年轻的艾丽丝和劳拉。很明显,瑞妮有着一种难以避免的标签化、刻版化的性别观念,这一点对艾丽丝有难以消褪的影響,在回忆少年时光时,她不断想起瑞妮的种种教导,这一柔性却权威的声音作为艾丽丝成长史的背景音一直在回荡着。
譬如说,艾丽丝想到“瑞妮说,一个女孩子与男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膝盖间的距离不能超过一枚硬币的宽度。”[6](189)在提到电影院时,她回想“我结婚前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因为瑞妮说,珑玉电影院是个低级场所,年轻姑娘无论如何是不该独自进去的。”[6](213)显然,艾丽丝一直被教导女性应该是保守自持的,同时应该富于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是她祖母和母亲的形象在代际间传递的信息,亦被年轻的艾丽丝内化为对自我的要求。
2 威妮弗雷德:代行父职的母权
艾丽丝丈夫的妹妹威妮弗雷德是小说中另一个很容易引起警觉的声音。在艾丽丝的回忆中,威妮弗雷德的声音总是以代词“她”的形式出现并不断回响。威妮与理查德紧密信任的兄妹关系常常是以“他们”这一声音同构体得以彰显的,正如威尼弗雷德对艾丽丝所说的:“我们俩是极好的伙伴”。“如此坦率又轻描淡写地说这话自然是带一种威胁。这不仅意味着她比我早先获得理查德的信任,以及我不可企及的忠诚,而且如果我胆敢冒犯理查德,那么要面对的就是他们两个人。”[6](214)显然,兄妹二人的声音、语气和规劝震慑的态度已然合二为一。
威妮弗雷德使人联想到阿特伍德另一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的莉迪亚姑姑,此类角色的结构功能就是改造女性的身体与行为规范,剥离她们的主体性并使其学会服从。这一类女性声音代表的是代行父职的母权,她们是父权的同谋者,当父亲不在场,母亲即以父亲、长者、尊者之名来维持秩序。显然,在压迫女性的男权中心性别结构中不仅仅只有男性,部分女性成为了父权体制的帮凶乃至具体惩罚的执行者。
二、 阅读的动力学:叙述层次与叙述节奏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小说的阅读受制于两个层面。首先,它必须使自己能够被读者理解,即根植于其熟悉的结构、语法、母题。可是,如果文本过于迅速地被理解了,它也就过早地结束了生命。所以出于自身的利益,文本必须延长读者的理解过程,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需合理地引入一些读者所不熟悉的元素,恰如其分地布置障碍,延迟展示预期的有趣内容。
阿特伍德的小說以厚重的情节见长,在《盲刺客》中,作者精巧地布局了叙述的层次,昭显了在长篇幅的叙述中保持读者兴趣的功力。故事是叙述的对象,但故事中往往还含有“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故事”就形成了层次,每个内部叙述故事都从属于使它得以存在的那个外围叙述故事,从而形成了一种等级结构。里蒙—凯南把这种结构分为超故事层、故事层、次故事层等等[9](170),在次故事层和故事层之间可能会存在着类比关系,次故事层作为故事层的镜子和复制品而存在。
(一) 互文结构中的女性镜像
《盲刺客》以繁复的故事结构闻名,其故事一共可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老年艾丽丝对自己垂暮之年日常生活的记录;第二层为艾丽丝撰写的回忆录,是对家族历史的叙述和对自己与劳拉早年生活的追述;第三层是艾丽丝假托劳拉之名写作的盲刺客小说文本,讲述了一个跨阶层的、浪漫与绝望并存的哥特式爱情故事;最内层即第四层,则是盲刺客小说中无名的男主人公“他”讲述的关于盲刺客X与献祭的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在上述不同的故事层中,作者特意埋伏下了诸多的线索和痕迹,使得叙述层次之间形成了文本内的互文性,不同层次中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对照的镜像。显然,盲刺客X、男主人公“他”和亚力克斯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更重要的一组对应是献祭的哑女、女主人公“她”与艾丽丝/劳拉。小说所描写的被献祭的女孩是一个“没有舌头而却有满肚子话要说的女孩……换到现在,你也许会说她像一个娇滴滴的上流社会的新娘。”[6](1290 “事实上,她不过是个穿着盛装、戴着珠宝的囚徒而已”,“那些把他变成瞎子的人也把她变成了哑巴”[6](137)。这个想要表达却无法开口的哑女形象,不仅可以指向被困在无爱婚姻与责任枷锁中的艾丽丝,更可以指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曾两次遭遇性侵犯但始终迫于压力不能表露真相的劳拉。
女性被定位为声音的客体,她们不能自我表达,只能被叙述、被呈现,在传统男性视角中的“永恒之女性”或“天使与魔鬼”的两极飘荡。直到拥有了写作的权利与自由,艾丽丝才终于成为了声音的主体,从虚幻的“他者”中走出,在回忆中完成了对过去的重建。这一对女性叙事权的重视亦可见于阿特伍德的另一部小说《别名格雷斯》。作为少见的女性杀人犯,主人公格雷斯的犯罪事迹拥有多个版本的新闻报道,真相则混杂其中难以分辨。而只有在与心理医生的对话中,她才重构了自我的历史,掌控了叙述真相的权力,进而构筑了自身的主体价值。
(二) 叙事节奏的把握
文本引诱读者继续阅读的关键在于对叙事节奏的把握。作者采用了延宕与间断的信息压制策略,不断延缓理解、制造悬念,在文本中应当透露信息的地方不透露,故意留到后面才说出来。延宕把阅读过程变成了猜谜游戏。一方面,它好像在向一个解答推进,另一方面它又力图长久地保持这个谜。为此,作者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拖延办法,包括设置圈套、引入歧途的线索、含糊其辞、封锁消息、悬置答案等等。作者大量使用了对未来事件的铺陈或暗示,在遇到这些“引线”时,有经验的读者能够意识到这些掩埋着的信息在其后的阅读中会起到关键作用。
《盲刺客》具有俄罗斯套娃式的设计结构,但实际上这种叙述结构不是简单的叠加或嵌套,而是相互渗透、彼此交织的状态。作者精心设置了叙述的圈套,并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泄露出一些裂隙,让线索逐渐浮出水面但是又引而不发,最后在一个突然的瞬间爆发出真相。实际上,故事的真相一直隐藏在结构交接之处的缝隙中,等待读者去一一捡拾并将其连缀起来。隐藏在文本间隙的线索无一不是在暗示《盲刺客》小说女主人公的真实身份。通过“谜面”的设置和解谜式的推进,叙述者老年艾丽丝拒绝作为被动客体而存在,打破了衰老与沉默的界限,在架构叙事游戏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父权结构的解构。
有研究者认为,《盲刺客》的结构与其说是“拼贴马赛克”式的,不如说是“万花筒”式的[10],文本不是简单地裁剪粘贴,而是充满了变形与幻象。文本具有罗兰·巴特所谓的后现代文本的“可写性”,阅读即是读者参与虚构的同构进程,在甄别信息源的虚假与真实时,无疑增添了阅读的解读意味与能动性。正如罗伯·格里耶所说,“作者需要读者的协助,而读者的任务不再是接受一个已完成的、自我封闭的世界,相反,他必须参与创造,自行构筑作品与世界的联系并创造自己的世界”[11](226)。
三、 隐喻系统中的女性叙事空间
在《盲刺客》小说中,阿特伍德的诗人气质显露得相当充分。在阅读英文原文时,读者可以轻松地捕捉到语句流淌中的韵律起伏、节奏的缓急错落与段落间萦绕的诗意的氛围,即使经过了语言的转译,小说仍然保留了足够多的诗意留待阅读者细细品味。这一效果既来自于作者语言的天赋,也来自于她所运用的大量的意象、隐喻和象征手法。通过巧妙而繁复的明喻、暗喻和象征,阿特伍德创造除了一个充满隐喻的文本系统。那么这一隐喻的文本系统对于塑造虚构作品中的女性叙事权威是否具有帮助呢?
张旭东在为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作序时论及“隐喻”:“这些隐喻形象在由自己构成的总体里完全敞开了,在此,隐喻成为事物之间的真正的关系。隐喻的基础首先是一种语言上的张力的可能性,而这种张力只能以精神的力量加以解释。因而,词与词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精神与物的紧张关系的再现。”[12](17)关于“张力”的涵义,英美新批评学派认为,张力是指词语的外延和内涵是否构成一种相互指涉、相互推动的关系,它们构成的诸意象是否前后连贯,构成符合逻辑的有机体。笔者将从文本中众多的隐喻和象征手法中选择部分内容,剖析它们如何形成了语言上的张力,并如何通过“词与词之间的紧张关系”表征或再现了“精神与物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 服饰与外貌的隐喻
小说中有着大量对于人物服饰装扮的描写,且有多个小章节直接以服饰或配件的名称做标题,如“黑丝带”“裘皮大衣”“犬牙纹套裙”“蛋壳色的帽子”等。同外貌描写一样,服饰的色调、质地、形式几乎成为了人物性格与命运的绝佳隐喻。小说中人物常常身着绿色衣物,与《使女的故事》中使女们统一穿着的象征生育、色彩浓厚的红色衣物不同,绿色(特别是冷色调的绿)代表着冰凉寒冷、或压抑或恐惧的情绪征兆。例如在劳拉坠桥后,艾丽丝还未见到事发现场便“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她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海军蓝,或青灰色,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6](2)此处艾丽丝设想劳拉所穿的裙子都是偏冷的绿色系的,她不仅身着绿色,而且“被关在这种颜色里”。在这种服饰的隐喻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窒息般的紧张与压迫。
主人公曾多次提到帽子这一饰物。譬如“要去停尸所,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6](20)又如“我们出去游玩时总是戴着帽子。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可以让我们多少免受一些注意。瑞妮说,淑女出门从来都是要戴帽子的。”[6](109)帽子本来只是一种装饰而已,但在文本中显然有了更深一层的意味,由佩戴帽饰构筑起女性主体的限定空间,既是遮掩保护,也是封闭束缚。
(二) 人物关系的隐喻
1 “我”与父亲
在主人公艾丽丝与父亲之间体现了家长式的世俗事务压力的代际传承。沉重的家族责任和二战后创伤焦虑几乎压垮了父亲,在父亲失去了掌控权后,这一职责转移到了“我”的身上,“我被困在了提康德罗加港——一个普通纽扣的光荣城堡……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恐惧。我想去别的地方,然而却没有途径。”[6](85)为了保住蔡斯纽扣厂,在艾丽丝十八岁时,父亲将她嫁给商业巨贾理查德,这无异于是一种交换行为。就像女性主义者盖尔·卢宾(Gayle Rubin)所述,婚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无关于女性,而是男性交换利益的产物[13]。艾丽丝的婚姻成为两个男人、两个家族利益互通的“导管”,而她的自我被封锁在这个管道中被客体化了。父亲于“我”当然是有爱与关切的,但这份爱上面有太多别的东西,“即便爱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它上面还有一大堆东西;这样的爱是某种护身符,却很沉重;它如同一个重物,把铁链套在我的脖子上,压得我难以前行。”[6](107)爱的护身符的隐喻象征了父亲于我、家庭于我的意义和重担。
2 “我”与理查德
在艾丽丝与理查德结婚后,理查德并没有帮助父亲挽救纽扣厂,父亲也因为经受不住打击去世了。从此以后,艾丽丝便彻底地沦为婚姻中一个被人主宰命运的欲望客体。在叙述两人生活细节时,作者不断使用各种譬喻描述主人公的内心。例如,“看着镜中的我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似乎被抹去了,失去了五官,就像一块用剩的蛋形肥皂,又像亏缺的月亮。”[6](251)这是艾丽丝新婚前夜的内心所想,亦是她主体性被剥蚀与失控自我的鲜明隐喻。除此之外,她还遭受了家庭暴力的侵害,“我觉得身上这些伤痕是某种密码……我仿佛是沙子,我仿佛是白雪——别人在上面写了又写,轻轻一抹就平了。”[6](396)但为了維持生计,艾丽丝一直没有勇气离开理查德,他们“维持着体面的夫妻关系……仍然在事物的表面上滑行——在良好风度的薄冰上滑行,掩盖了下面黑暗的湖水:一旦冰融化了,你就沉下去了。半个生活总比没有强。”[6](508)直到劳拉自杀之后,艾丽丝才终于带着女儿逃离理查德。
3 “我”与劳拉
艾丽丝与劳拉之间复杂微妙的姐妹情谊无疑是小说竭力刻画表现的对象,也是小说中最幽暗难测的核心关系。在父母相继去世后,劳拉与艾丽丝彼此依靠,但是这种命运的捆绑并没有将她们拉近,反而让她们生出更多的嫌隙。艾丽丝感到对劳拉负有责任,但她其实内心深处并不想承担这些责任。此外,她还对劳拉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执拗的精神力量表现出了强烈的嫉妒,这点在二人童年时期就已显露出征兆。譬如母亲临终时嘱托艾丽丝要做劳拉的好姐姐,在这个即将失去最亲爱的人的悲痛时刻,年少的艾丽丝没有抒发她的伤心,反而对这一要求产生了不满:
“我感到自己像是一个不公平的牺牲品:为什么总要求我做劳拉的好姐姐,而不是要求劳拉做我的好妹妹?毫无疑问,母亲爱劳拉胜过爱我……她给我们的爱实在而具体,就像是一块蛋糕。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姐妹俩中谁会分到那较大的一份。”[6](98)
家庭中的资源是有限的,长辈的爱也并非无穷无尽,因此年龄相仿的兄弟或姐妹在年幼时经常会争夺父母的注意力与宠爱,产生龃龉和纷争。小说中此类关于姐妹之间复杂情感和人类心灵最幽微深暗之处的描写不胜枚举,体现了阿特伍德笔法最精准细致的触点。在某些时刻,作者着重呈现艾丽丝与劳拉之间无法割断的依恋。例如小时候有一次劳拉弄坏了艾丽丝的笔,艾丽丝“自然原谅了她”,“我总是在原谅她;我只能这样做,因为在那个荆棘丛生的‘孤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等待营救”[6](41)。在另一些时刻,作者突出了艾丽丝对劳拉的不耐烦和莫名的敌意,例如“她具有忠实信徒那种铁一般的信心,令我十分恼火……我恨得手指发痒”。[6](99)又如母亲去世后,姐妹俩坐在池塘边,劳拉不相信妈妈已经死了,她喜滋滋地认为妈妈是“和天堂里的小婴儿在一起”,艾丽丝于是把她推下了池沿,并且想到:
“我得承认,我对自己的举动感到满足。我早就想让她像我一样吃点苦头了。对于她总是可以因年纪小而逃避很多事,我感到烦透了。”[6](102)
在诸如此类的描写中,读者不断看到艾丽丝嫉妒和缺失责任心的黑暗面,而劳拉则被表现为具有强烈精神信仰和纯粹力量的光明一面。但是,至明至刚的性格特征使得劳拉脆弱易折,“她曾经依赖这些词,在上面建造她的卡片房子,相信它们是坚实的;而这些词却翻了过来,让她看到它们空洞的中心,然后像许多废纸一样飞掠而去。上帝。信任。牺牲。公正。忠诚。希望。爱情。更不用说姐妹之情了。噢,没错。这种情感总是如此。”[6](521)艾丽丝意识到所谓“姐妹之情”的反讽意味,正是纯粹光明的情感崩塌摧毁了劳拉。
艾丽丝在小说中曾反问自己也反问读者:“我是我妹妹的监护人吗?”这句话出自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该隐出于强烈的嫉妒杀死了弟弟,当上帝询问亚伯的去向时,该隐反问上帝“我是我弟弟的监护人吗?”艾丽丝引用这句话,暗含了她对于当劳拉的“好姐姐”所要承担的责任感到无法承受,更暗示了劳拉之死于她有着不可推脱的关键责任。
四、 结语:女性叙事空间的建构
虚构叙事作品中的权威是一种空间效应,与叙述者的位置、被潜在读者感知的程度相关。话语权威体现在对叙述空间的占有上,而影响话语的根本因素是权力。在不同类型的叙述者中,全知全能视角能够驾驭真实与虚构的两个世界,最具有权威性。通常来讲,声音的强弱与权威的表现成正比,越是暴露自己的在场者,越是具有权威性。德里达认为,之所以存在语音中心主义的霸权,是因为口头语意味着说话主体的“在场”,从言语主体出发人们能找到话语的完整源头,而“书写”则与声音不同,是一种心灵的创造,具有反叛中心与解构权威的力量[14]。在阿特伍德的叙事中,彰显了女性书写的解构力与建构性。作者对不同女性视角的参差运用、回忆与现实的交替、虚构与真实的置换等技法都是建构女性叙事空间的尝试。
虽然真实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可以持有不同的身份,但是真实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性别意识会影响隐含作者创作时的自我意识,也必然反映到叙述者身上。陈顺馨认为,叙述权威和性别差异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她在研究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男作家的作品的叙述者所表现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比女作家要高。[15](61-62)这种权威性的差异与叙述者的策略相关。如果一个叙述倾向于与故事同步,或投入故事之中,这样的叙述策略所取得的效果是贴近故事,拉近了与隐含读者之间的距离,权威性也因此而降低,而这常常是女性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的叙述姿态。权威的性别差异在文本话语中的表现是社会文化结构的折射。凯瑟琳·琼斯(Kathleen Jones)认为“权威这个概念的构成已经把女性的声音排除于外,借用福柯的谱系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见主导的权威话语如何使那种在隐喻上和象征上与‘女性语言相连的表达形式变得沉默”。[15](63)女性话语倾向于建立情感的联结而非权威的陈述,这种同情的特质拉近了距离,却也远离了权威。
在《盲刺客》小说中,叙事声音是隐喻的、有限权威的、遭受创伤的女性,而非直接有力的、无需铺垫的、天生具有不可剥夺主体性的男性声音。叙述者“我”的声音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压抑的情绪中,即使“我”是文本中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我”也并不具有男性叙述者那种确凿无疑的自信语气。相反,在表达那些最关键隐秘的真实想法时,叙述者只能采用隐喻、暗示、象征的手法,无法直接说出最惨烈的事件真相,亦从未对其直白批判,只是在不断迂回的修辞中“暗示”這一系列事件对“我”和劳拉所造成的内心创伤。虚构的叙述者艾丽丝即使在认清丈夫虚伪的表象后,仍然不能直接控诉他的行为,只能通过撰写小说并默默发表(以劳拉的名义而不是“我”的真实身份)来谴责、控诉和讽刺。每每提及创伤经验,叙述者选择的修辞总是隐晦的,蒙上了一层隐喻的修辞阴影。这一叙事方式与弗洛伊德所述的个体创伤经验的“滞后性”(Nachtrglichkeit)、反复性、破碎性和不可言说性等特质不谋而合。
但这种隐喻的修辞并非没有力度,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女性创伤书写的可能性。文学对于人类内心情感世界的探索是无法穷竭的,当它以一种看似间离的象征手法呈示创伤的破碎经验,反而更能抵达读者心灵的深处,阿特伍德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触及了她的读者。苏珊·兰瑟在探讨女性主义叙事学时,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埃特金森的匣子》一诗为例[4](16),探究了女性语言的产生机制,发现了在表层文本的软弱无力、没有权威强音的女性文本之下,以巧妙的藏头诗形式隐藏着另一层具有男性语言特点的隐含文本,这一隐含文本可以是强健的、有力度、有效率、坦率直言的。当我们再次审视《盲刺客》文本中弥漫的隐喻与象征的书写策略,会发现这种表述方式不仅给文本增添诗意和压抑忧郁的艺术氛围,而且印证了一个事实:女性叙述者可以通过一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方式建构起占据文本空间的权威,这一虚构的权威空间并非是“权威的虚构”,而足以凭借言语的力量直指我们的心灵。
〔参考文献〕
[1] Staels, H. Atwoods specular narrative: The Blind Assassin[J]. English Studies, 2004, 85(2): 147-160.
[2] Bouson, J. B. “A commemoration of wounds endured and resented”: Margaret Atwoods he Blind Assassin as feminist memoir[J].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3, 44(3): 251-262.
[3]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 [美]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盲刺客[M].韩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7] Atwood, M. The Essential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ture[M]. London: Vintage, 2002.
[8] [法]兹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A].张寅德.叙述学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9] [以]施劳密斯·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0] ParkinGounelas, R. What isnt there: the psychoanalysis of duplicity[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004, 50(3): 681-700.
[11] [法]阿兰·罗伯-格里耶.今日叙述中的时间与描述[A].快照集:为了一种新小说[C].余中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
[12] [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3] [美]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A].佩吉·麦克拉肯.女权主义理论读本[C].艾晓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4] [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5]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夏 雪)
Opening Up the Space of Female Narrative
— Interpretation of Margaret Atwoods The Blind Assassin
L Xin-tong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feminist narrative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narrative space in Margaret Atwoods novel The Blind Assassin.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structuralist narratology and feminism. It explores how The Blind Assassin shows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aph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female narrative voices, narrative rhythm and hierarchy, and metaphoric narrative system. The metaphorical symbol in the system opens a new narrative space and builds the authority of female writing.
Key words: female narrative; voice; narrative sp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