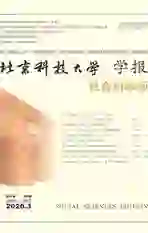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路向
2020-06-22魏琛
〔摘要〕 Shu, Zhang & Zhang主编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2019)是对认知语言学在中国30余年来研究现状的全面评述,突出了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的3大转向,指出了语言学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该书全面梳理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导向作用。文章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及其“前沿性与应用性、本土性和导向性、批判反思性与主动求变性、交叉融合性与双向互动性”等特色进行了评述,并以新文科建设理念为指导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跨学科深度融合发展模型、跨语言对比验证研究及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4个维度展望了基于汉语事实的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研究路向。基于《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汉语特异性的语言事实研究将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向之一。认知语言学理论创新与汉语语法理论体系创建是一个生态系统,二者形成一种有机、双向互动的关系。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给养,汉语语法研究反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创新。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创新的不断深入,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将更加完备、健壮。文章对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及其他语言学流派进一步深入研究汉语事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新文科;《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本土化与理论创新;融合模型;内外部批评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3-0001-10
引 言
1975年以降,认知语言学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夏令营中诞生,此后席卷欧美及世界语言学界,从边缘走向中心,逐步成为世界语言学主流之一[1],代表着语言学研究的前沿[2]。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引入中国的这30余年来,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走过了理论的引介和吸收期、理论的初步应用期、批评与反思期和融合与主动求变期4个历程。在这30余年里,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工具的更新、研究范式的更迭,认知语言学研究在与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等相關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中[3]沿着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4]不断延伸,其疆域不断扩大,几乎涉及语言研究的各个分支领域,并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在此情境下,全面总结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热点议题、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反思当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瓶颈、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合理性,从不同维度展望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路向或许可以有效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完备性和健壮性指明方向。这既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又可满足认知语言学从“内部争鸣期”走向“接受外部批评期”[1][4]的跨越式发展的根本性内在要求。《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5]生逢其时,为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路向与理论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于2019年11月底在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该书由中国认知语言学界领军人物束定芳、张辉和张立飞3位教授主编,是一本认知语言学与汉语语法研究相结合的论文集典范。除了引言部分之外,该书由3大部分共10个章节构成,分别从汉语特定构式研究、认知语用学研究、认知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出发,对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现状和研究路向进行了全面评述,具有极大的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
三位主编开篇明义,直指该书的核心理念:认知语言学的实证转向和定量转向。这既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全球趋势,也是束定芳教授和张辉教授等中国认知语言学界领军人物这些年不断发力的方向,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界的健康发展指出了重要的研究路向,也为中国语言学界理论创新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实际上,这3大部分既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3大转向:定量转向(quantitative turn)[6]、实证转向(empirical turn)[7]和社会转向(social turn)[8],有效印证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证周期(empirical circle)[9],又突出了认知语言学对研究范式的充分关注以及在其他领域的跨界应用。当代认知语言学力主基于语料库的客观性证据与基于实验的诱导性数据之间的系统性依存关系[5],力促寻求语言证据的汇流,试图为构建Kuhn(1970)所倡导的科学哲学范式而不懈努力[10]。而当代认知语言学积极吸收其他学科已被证实的研究结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融合发展以及它对科学技术的充分关注,充分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在不断交叉融合的过程中朝广度和深度双向发展的融合模型[3]。
一、 内容概要
该书引言部分全面梳理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从引进和吸收到应用和反思,再到批判和求变的发展历程。该书三位主编勾勒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中国学者不是仅仅引进认知语言学理论,结合印欧语系相关语言事实做些本体研究,而是积极地将其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之中,在充分解释汉语特异性语法现象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认知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验证或证伪了认知语言学理论提出的部分假设[11],另一方面基于汉语特异性语言事实的研究成果修正或完善了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贯穿全书的是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路向,而语言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路向是实现语言理论跨语言解释力的关键。这不仅为汉语语法研究构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更为中国学者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了构建基于汉语事实的语法理论体系的呐喊声。
第一部分“形态、词法和句法的构式研究”包括5个章节(第1—5章)。在第1章“构式与语境:汉语‘还的多义性分析”中,Lü基于语料库,以语境为切入点,论述了“还”构式的多义性生成理据以及“还”构式的演化路径。在第2章“构式的部分能产性”中,Tian基于语料库统计分析,主要分析了“着”构式的创新性和语义限制条件。在第3章中,基于语料库数据,Li & Liu重点对比分析了“把字句”和“把个句”。在第4章中,Shen从汉英的否定类型出发,论证了英语名词范畴和动词范畴的分立关系在汉语词类分类中的水土不服现象,指出汉语的名词和动词不是分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在第5章中,Wang对汉语动作和活动的空间概念化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的5个章节重点探讨了汉语特定构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异性。具体而言,该部分涉及汉语特定构式的意义、用法和多义性问题,以及有别于印欧语系的词类分类问题,即汉语的名词范畴和动词范畴不同于以英语等印欧语系为基准而构建的词类分类体系。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基于语料库数据的计量分析,诠释了语料库数据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穷尽性,完美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定量转向。
第二部分“认知语用学研究”共2个章节(第6—7章)。该部分分别讨论了结构凸显性与指称可及性之间的关系和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學的互补性关系。在第6章中,Xu从汉语复杂句中小句间名词短语回指的认知阐释出发,探讨了汉语句子主语的位置问题。Xu指出,汉语前置从属小句中的主语可置于从属连词之前或之后,二者的位置差异性分布表明汉语前置从属小句中的名词存在共存或脱离关系,即Xu假设“汉语复杂句中小句间名词短语的回指具有特定的偏好类型”,而这一假设得到了语料统计分析数据的证实。Xu指出结构凸显性和指称可及性之间存在认知关联性,即回指的语用功能使得篇章连贯性得以实现。在第7章中,Chen指出可从认知角度出发,分析具体语境中的言语行为,认为这是对20世纪80—90年代徐盛桓语用研究传统的积极回应。Chen从汉语的两个释例出发,论证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知语言学持最大化主义(Maximalism)语言观,它不严格区分语义和语用,认为意义即概念化,意义具有百科知识性和经验基础,语言的使用具有社会性,必须考虑语用因素,即概念主体间在意义的动态传达过程中的交互性和协商性[12],体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8],即“再语境化”趋势[13](27)。第二部分的2个章节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语境对于构式义的调节作用及其交际功能实现的理解。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从认知视角出发来研究语用学相关概念的,但是该部分仅仅指出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互补性,对社会转向的关注仍需进一步地深入,比如认知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词汇语义学等。
第三部分“认知神经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研究”共3个章节(第8—10章)。该部分从ERP、时间进程和儿童致使移动构式习得的心理表征出发,探讨了认知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实验法对汉语相关语言现象的验证,涵盖了在汉语实质结构与抽象的概念结构的实验验证工作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第8章中,Zhang以ERP技术为先导探讨了汉语习语的理解问题。在第9章中,Gong & Zhou以时间进程研究了隐喻角色在范畴化中的作用。在第10章中,Ji对汉英儿童致使移动的语言表征及心理表征进行了研究。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为中国认知语言学界认知神经语言学的奠基人,Zhang多年来基于ERP、fMRI等的脑神经成像研究表明:语言特异性影响了不同语言的语法、时态、词义加工机制,使之存在差异,而跨语言的句法相似性研究也对句法加工产生影响[14]。第三部分的3个章节所采取的研究范式为构建具有可重复验证性的研究结论奠定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其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突出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实证转向,以中国学者基于汉语特异性的实验研究来验证某些具有跨语言共通性的假设,如隐喻的角色作用和致使移动构式的理解与习得等。
二、 简要评述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是对认知语言学引入中国30余年来,其研究现状、所取得的成就、问题与趋势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始终的是认知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路向,并指出了语言理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对认知语言学研究者与汉语研究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导向作用。
(一) 该书的主要特色
第一,具有前沿性与应用性。认知语言学代表着语言学研究的前沿[2],而认知构式语法则走在最前列。以印欧语言尤其是英语为蓝本而构建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注重对英语的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构式语法理论肇始于Fillmore对“let alone”和Kay & Fillmore对“Whats X doing Y”等构式的研究,认为对边缘性语言现象的研究可揭示核心现象的规律性。作为汉藏语系代表的汉语全然不同于印欧语系中的多数语言;汉语构式的特异性及其生成机制有别于英语构式,如在第1章中Lü基于汉语“还”构式(“hai”construction)的多义性研究以及该构式变体的演化路径研究[5]。Lü基于汉语口语语料库,分析了“还”构式在话语语境中语用意义的变化性。Lü指出“还”构式具有高度图式化的原型性功能。“还”构式的多种用法和意义派生于语境,正是语境促使其产生了不同的解读义,体现了语境对构式多义性的调制作用[15],如让步义、时间持续义、边缘义、附加义、对比义等。此外,“还”构式通常可与词素“有”组合、共现。基于上述汉语事实的分析,Lü预测“还”构式还可与词素“是”实现语境共现,产生新的构式化单位。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构式研究表明,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对现有语言事实的精细化描写,还需要对语言事实做出充分的解释,更要在充分解释的基础上,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语言构式或表达式做出一定的预测。
第二,具有本土性和导向性。该书各章对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应用于汉语语法现象进行了观察,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研究路向与导向性。语言理论的本土化研究路向是实现语言理论跨语言解释力的关键。第4—5章关于汉语词类范畴划分的讨论尤为如此。对汉语词类的划分是个大问题。引发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关于“词类大讨论”的根本原因在于:1898年《马氏文通》模仿印欧语法体系构建的汉语名词和动词范畴体系在中国的“水土不服”,造成了在汉语名词和动词范畴划分问题上的“形式派”、“意义派”和“形式—意义派”的争论。Shen指出,名词和动词范畴的分立现象是印欧语言的特色,但是名—动分立关系不符合汉语实情,而汉语的名词和动词范畴则为包含关系。在汉语中,名词与动词呈连续体和包孕关系,名词是大类,动词是子类,名词包含动词[16],并探讨了英汉语名词和动词范畴具有的不同认知基础和哲学根基,提出了颇具汉语特色的“名—动包含说”[16]。再如Wang基于对“形容词—动词”构式的分析而提出“名词的空间关系与动词的时间关系”假设,初步探讨了该构式的语法模式,进而进一步提出假设,认为“动作/行为/活动在汉语中常被识解为三维实体或事物的语言现象”[17],这一假设从某一方面验证了Shen的“名—动包含说”。两位作者的观点如出一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具有批判反思性与主动求变性。《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在引言部分就认知语言学当前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的评述,重在批判与反思,貴在表达主动求变性。该书旨在对认知语言学理论及其在应用实践过程中的不足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反思性整体批评,其目的在于通过理论反思和再反思实现对批评对象的认知和再认识,并最终促进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18]。其主动求变性主要体现为:中国语言学界寻求突破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牢笼,实现从描写充分性到解释充分性,再到预测性的突破。认知语言学研究视角可系统解释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所不能解释、不好解释和解释不充分的汉语现象,如汉语词序、词类范畴以及非常规组合、非常规构式等。中国语言学界不满足于引进新的语法分析理论,更是强调对引进理论的应用,在应用于汉语事实的分析中反思,在反思中进一步将其应用于更多的汉语事实分析之中,在语言理论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适切性与证伪性上双向发力,这体现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在构建符合汉语实情的语法理论体系过程中的不懈努力。
第四,具有交叉融合性与双向互动性。认知语言学的交叉融合发展不仅是其学科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更是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向[3]。学科交叉融合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19],是科学回答“认知语言学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应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已被证实的研究结论,力促自身的发展,构建语言研究的融合模型[3][20]。如该书第6—7章通过对具体实例的分析,指出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反映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和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5]。这无疑有利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健康发展,增强其理论健壮性,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认知语言学自“娘胎”以来就是交叉融合的产物[3]。因此,交叉融合理应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健康发展,从内部争鸣期[1]稳健步入接受外部批评期的关键[3]。
中国语言学界引进认知语言学理论是为了弥补、突破传统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不足之处,而对具有汉语特异性的汉语语法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则反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增强其理论的解释力度,丰富其理论体系,二者形成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传统的结构主义层次分析法无法充分解释诸如汉语“存在构式”等语法现象。比如“台上坐着主席团”[21][22][23]。结构主义、生成主义均无法对其进行充分的解释,而认知主义将其视为既可表示静态也可表示动态的“存在物+存在处所+存在方式”构式,较好地解释了该汉语存在构式的特异性。在现代汉语中,当概念主体要以存在处所为话题时,表示存在处所的词语居于句首,表示存在方式的词语居中,表示存在物的词语则位于句尾。这表明认知构式语法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之前一些不好解释或解释不充分的汉语语法现象。应该说,这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研究。汉语特定语法现象则衬托出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一些不足之处,促进了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式发展。再如沈家煊(2016)的研究成果“名—动包含说”拓展了名词的范畴[16],修正了以印欧语言为基准而构建起来的传统词类范畴观。这种基于汉语词类特异性的名词和动词范畴分类体系完善了传统的词类范畴观,是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对世界语言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贡献,有效体现了基于汉语事实的语法研究对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反哺作用。
(二) 该书有待商榷之处我们曾就本文所总结的该书研究内容方面的特色以及“有待商榷之处”求教于该书主编之一、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辉教授,并有幸得到了张教授的不吝赐教。张教授肯定了我们对该书研究内容等方面所具有的特色的总结,也首肯了我们指出的对中国认知语言学发展阶段的进一步分类和对该书的建议。在此,我们衷心感谢张辉教授长久以来对学界晚辈的支持与提携!
1 对发展阶段的分类不够精细化
我们认为该书以时间节点为划界依据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初步引入与有限应用”和“迅速拓展、大量应用与深度反思”两个阶段的分类法不够精细。我们不妨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为理论的引进与吸收期、理论的初步应用期、结合本土语言事实的理论批评与反思期以及融合与主动求变期4个阶段。
语言学史告诉我们:欧洲诸语言语法体系的构建均是以对拉丁语法体系的模仿、吸收和创造性发展中脱胎而来,比如希腊语法体系、罗马语法体系的承继与发展关系[24]。中国认知语言学3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不例外。
我们引入并应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汉语语法现象。它也确实更好地解释了不少结构主义分析框架所力不从心的语法现象,但是随着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展,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解释力也遭遇了瓶颈期。比如对内省数据的过分依赖造成了认知语言学相对忽视了语言使用的个体差异和社会性[25];而对心理因素的过分强调则夸大了概念主体的主观性因素,相对忽视了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客观性,似乎树立了一个“客观主义”的假想敌[26]。
在对认知语言学所存在缺陷的批评与反思中[5][18],认知语言学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较好地实现了其理论内部的动态性平衡[27]。如Deng & Shi(2007)的研究成果对“形义结合体”的构式观提出了质疑,认为构式定义的不当扩展带来了诸多问题,模糊了构式与句法的关系,使语法分析平添复杂性,为此构式义的来源被限制在极其狭窄的空间之内[5]。此外,对早期认知语言学主要以内省思辨法为主所获得的语言数据可信度方面的质疑催生了对语言数据全面性、客观性、穷尽性探索的语料库验证法和心理语言学实验法。过分关注假设的提出而缺乏有效论证和检验的批评则催生了认知神经语言学基于ERP、fMRI等神经成像法提供的客观证据。对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的再论证以及对研究结论的再检验则顺应了Kuhn(1970)所倡导的科学哲学范式[10]的语言理论体系。汉语的特异性为认知语言学理论及其假设的验证提供了有别于印欧语系的语言证据。为此,中国学者应吸收外来语言理论,基于汉语语料和汉外对比研究,根据外来语言理论在本土语言现象解释和预测方面的适用程度,改变它,使之满足汉语本土化研究的需要。比如汉语“存在构式”的特异表达方式使得认知语言学在与汉语研究的双向互动关系中深度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在吸收外来语言理论中反思,在反思中主动求变的意识。
2 对社会转向的关注度仍需进一步深入
该书强调了当代认知语言学关注定量转向和实证转向,但对社会转向的关注度还需进一步深入。对社会因素的关注是认知语言学再语境化的核心要旨。Geeraerts正确地指出,“再语境化倾向是当代认知—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根本趋势”[13](27)。Geeraerts等人创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词汇语义学等从历时的视角关注语言变异问题及其产生变异的社会因素,如Geeraerts通过自建的小型历时语料库对“legging”一词的词义历时变化的研究[28]即是明证。由此可见,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因素的社会转向是认知语言学研究前沿的主要支流之一。对社会性因素的关注则需考量语境因素。不同类型的语境,如社会语境、文化语境、言语语境、多模态语境等均对语言及其交际功能的理解起调制作用[12][15]。认知语言学的魅力与独特性在于:它力图将这些不同的倾向整合进一个综合的、跨界面的语言研究的融合模式之中[3][20]。
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语境之中则意味着社会性因素促使语言发生变化是一种常态,而语言运用于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变化性是语言固有的特点。在第6—7章“认知语用学”中,两位作者关于认知语用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对社会性语用因素的关注。在第7章中Chen主张将认知语言学和当代语用学的理论概念结合起来分析具体的言语行为,如“Ni chi le mo?”(你吃了么?),论证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在特定语言结构及其在不同语境中使用方面具有的互补性解释维度[5]。
稍有遗憾的是,三位主编可能出于某种更深层次的考量,该书暂未向世界语言学界介绍中国语言学界对认知社会语言学在词义历时变化性、语言间接触造成的语言变异和使用中的语义变化现象以及基于汉外历时语料库对比研究所揭示的语义共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首先,在语言接触研究中,汉语,包括地方方言(如上海话、广州话、福州话、闽南话等),在与外语的长期接触过程中而产生的洋泾浜英语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这些语言接触不仅丰富了汉语的词汇量,还对汉语的词汇语义表达力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有些词语的语义表述在接触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9][30],如“呢(ni) ”的历时语义演变[31]。此外,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与汉民族语言接触过程中产生语言变异现象也未深入涉及。因此,如何立足于汉外语言接触的历史,在分析汉外语言接触现状的基础上,深度融合认知语言学理论、服务于汉语语言变异和词义演变研究,揭示汉外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异的社会性因素,开创一条汉外语言接触与发展的研究路径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探讨的课题。
其次,对基于汉语和英语历时语料库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如历史认知音位学研究、历史词汇语义学研究、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等该书均未涉及,如杨延宁(2019)基于语法隐喻理论、从构式演化的角度对构式义的来源问题的研究[32]表明,除了Goldberg(1995)的“情景编码假设”[33]和Goldberg(2006)的“表层概括假设”[34]以及陆俭明(2009)的“认知—表达过程假设”[22]之外,构式义的另一可能来源是“人类扩充语义潜势的根本需求”[32](34),即构式义具有语言使用在社会性因素促动下的交际—心理动因,而“语义和语法层两套演变机制的互动导致构式义的不可推知性”[32](34)。 其中陆俭明(2009)关于构式义来源的新假设以及杨延宁(2019)关于构式义来源的“心理动因说”都是中国语言学界对构式语法理论,尤其是构式义来源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 基于汉语事实的认知语言学
本土化研究路向展望
基于汉语事实的认知语言学现有研究成果已向我们明示了中国认知语言学界未来的发展方向。本土化研究路向既是现有语言理论实现跨语言解释的关键所在,也是现有语言理论突破自身局限性、促进其自身理论健壮性成长的关键所在。语言理论的本土化研究是世界语言学理论创新式发展的重要路向[35][36][37]。基于《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汉语特异性的语言事实研究将成为认知语言学理论创新的重要路向之一。
展望认知语言学本土化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向,我们觉得有必要首先思考并回答以下2个问题:1)认知语言学理论如何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中提升本土意识?2)认知语言学理论如何在与本土语言事实的双向交互中实现其自身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什么是语言研究的本土意识?我们认为,世界语言学理论的深度发展日益呼唤一种语言研究的本土意识,从本质上讲,它是语言研究中的民族意识、创新意识、自主意识、求真意识和求实意识。正如Humboldt[38]和Apresjan[39]指出的“朴素的语言世界图景”[40]那样,语言的民族性使其所具有的语言特异性必须深刻地反映在语言理论之中。当下的中国语言学界正处于自1898年《马氏文通》出版120余年来语言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深度反思的十字路口之上。如果中国语言学界缺乏本土意识和问题意识、对外来语言理论采取仆从心态或者过于依赖、仅限于运用外来理论来解释本土语言现象的话,那么它将危及到汉语语言理论自身的发展,弱化漢语研究者的专业敬畏感与自我身份认同。
其次,如上文所述,认知语言学理论创新与汉语语法理论体系创建是一个生态系统,二者形成一种有机、双向互动的关系。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汉语语法研究提供给养,汉语语法研究反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创新。《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致力于本土问题域的转向[41],伫立于时代发展的前沿,吸收最新的研究范式,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探求基于汉语事实的语言研究对外来理论的证伪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创建等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可以作为提高语言理论本土意识的现实路径。可以说,语言研究应该在本土化、多样性与异质性的多重互动中[42][43],在追求世界语言的共性与差异性以及在实现语言理论普遍解释力中进一步发展,实现语言理论普遍性解释力与跨语言特殊现象之间的动态性平衡。
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下新文科建设的大语境下,中国认知语言学界可以以新文科建设理念为指导从科学哲学研究范式、跨学科深度融合发展模型、跨语言对比验证研究及共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4个维度实现汉语本土语言理论从跟随到创新,再到超越的跨越性发展[3]。
首先,应致力于创建语言研究的科学哲学范式[10]。中国语言理论的发展应在科学哲学范式指导下,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汉语经典问题提供全新的、可靠的、多维度的证据,不仅实现对汉语事实的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和充分解释,更要实现对汉语未来可能的语言现象的充分预测。正如该书第8章,Zhang应用ERP等神经成像技术对汉语习语理解所做的研究,为汉语习语非组合性意义理解提供了来自神经认知科学方面的汇流证据。
其次,应致力于语言研究的跨学科深度融合发展[3][44],在借鉴融通之中合力创新[45][46],在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已被证实的研究结论,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研究方法,促进语言学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互补性融合发展,如语义学注重对语义实现的语言内部结构之间关系的静态分析与语用学注重对语言在外部使用中的语义实现的动态分析的互补性关系。诚如该书第7章,Chen指出的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交叉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可从语言类型学出发,致力于语言理论的跨语言对比和验证研究。实现语言理论跨语言解释力的关键应立足于充分的跨語言对比研究,发现现有语言理论可充分解释哪些语言现象,更要发现现有语言理论的解释力之不足之处。从语言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历史语文主义在其研究中常引用大量跨语言例子来说明和定义相关理论概念,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对当代的语言学研究极具启发性,而且为基于使用的语言研究范式,如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研究等树立了跨语言对比研究的典范[47]。比如该书第一部分5个章节对汉语构式特异性和多义性的研究,第二部分第6章Xu对汉语复杂句句间名词短语回指现象的对比研究所揭示的民族思维和语言表达形式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以及第10章Ji对儿童致使移动构式的语言表征和心理表征方面的实验研究验证了致使移动构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跨语言普遍性。再如,施春宏等(2017)基于中介语语料的汉语句式和语块的习得研究[48]以及施春宏(2018)基于汉语动结式、动词拷贝句构造和构式化、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构造和构式分析路径等的研究而构建的形式和意义互动—派生模型[49]都表明无论是本族语者还是二语学习者对汉语构式的习得和学得研究都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为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的跨语言发展贡献了中国学派的力量。而李宇明(2019)对其女儿“冬冬”长达6年的语言习得日志的详细记录与分析的研究[50]不仅为语言研究,特别是为早期儿童母语习得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语言数据,也表明对早期儿童汉语构式的习得研究很有可能为Goldberg(1995, 2006)提出的“情景编码假设”和“表层概括假设”提供全新的关键性证据。从跨语言数据的验证角度上说,李宇明先生多年来的努力既丰富了Goldberg上述2大假设的理论内涵,又实现了中国语言学派在相关领域从理论引介期的“传声筒”角色到理论反思与求变期的主动接过“话筒”的接力式发言的角色转变。
第四,应致力于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自Saussure区分共时研究以来[51],共时理念深入人心,在语言现象的描写充分性方面取得突出的成就,但在语言现象历时演化的动态性描写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而未来的研究还应站在传统共时研究所打下坚实基础上加强历时研究,实现对语言现象共时共现和语言现象发展脉络的多维性、整体性考察。比如杨延宁基于英语和汉语历时语料库从历时演化和语法隐喻化视角对构式义交际—心理动因的再认识[32],拓展了构式义来源的理据性分析,也让我们看到:在共时研究为主的天地里,历史语文主义的历时观和心理因素观在当代语言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47]。因而,对历史语文主义、结构主义、生成主义、新结构主义等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中合理成分的继承、发展,形成一种学术传统上的承继与互补多重关系[47][52][53]。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立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前一阶段的理论和范式探索构成后一阶段探索的暂时支撑点或出发点,其间的内在逻辑性将它们有机地连接为一个整体[47][52][53][54](14, 19, 287)。为此,Geeraerts总结道,“从某种维度上看,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对历史语文主义的一种回归”[54](42, 298)。显然,这种回归不是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语言研究视野的上升过程,更是语言研究的时代新“站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语言理论或流派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竞争关系,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互补关系?答案是显然的。就语言理论解释力的覆盖面而言,单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或理论流派无法实现对复杂语言现象的充分解释;每一种语言理论实现对复杂语言现象的充分性解释肯定需要多维的视角,也需要基于本土化语言现象的、跨语言的类型对比研究,从而实现语言—认知—社会的整合性研究范式。就语言理论的共享面而言,竞合关系成为语言理论流派之间形成一种横向相连、纵向相接的理论关系网。套用Saussure的话来说,实现对语言现象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关键在于发现其理论解释力在相关理论编织的关系网中的“关系值”[51][55]。那么,语言理论不仅仅是在与同一学科不同流派之间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横向相连中不断向前发展、渐趋完备、健壮[3][47][52][53],更是在理论与理论或流派与流派以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竞合、互动、互补关系中实现创新式、跨越式发展的。
事实上,上述4个维度的思考正是基于《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这本专著给我们的启示。总而言之,随着认知语言学理论与汉语语言事实的本土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认知语言学界不仅要在基于汉语特异性语言事实研究方面上实现研究成果的增量性研究,更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汉语界与外语界、语言界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甚至与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有效互动,进而在基于汉语本土语言事实的理论创造性研究方面实现突破。这是因为,基于汉语本土化语言现象的研究既可为认知语言学理论提供多语种的、多维度的、全新的语言证据,也可使认知语言学理论的解释力更具普遍性,使其理论体系更加完备、健壮。诚然,实现中国语言学界语言研究成果从增量性研究到创造性研究的突破并非易事,但是我们相信中国相关学科领域领军人物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中所付出的不懈努力正引领着一波又一波的“后浪”不断冲向前方。
四、 结 语
全面梳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从引进和吸收到应用和反思,再到批判和求变的发展脉络不仅勾勒了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展及结果的全过程,而且也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界“破”与“立”相结合的哲学思想。因此,认知语言学在中国这30年来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一个有“破”也有“立”的辩证过程。“破”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生成主义语言学等形式主义研究范式在解释汉语事实方面存在的不充分性以及对语言形式和意义或功能离散性、自治性的充分反思;“立”的是认知—功能语言学在解释、预测语言形式和语言意义或功能非离散性、整体性等方面的充分性,原型范畴理论以及语法现象连续体思想在解释自然语言意义的模糊性、多义性等尤为如此。此外,中国认知语言学界30余年的发展历程还体现了中国语言学界立足民族语言现实、合理借鉴和吸收世界语言理论之精华、树立本土化研究典范的安身“立”命之本。
瑕不掩瑜,《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的本土化研究路向注定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积极投身于汉语研究之中。必须肯定的是,中国认知语言学界立足于中国立场、立足于汉语实情的本土化研究路向必将在中国的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认知语言学在理论创新方面的持续深入,随着其已有理论假设的逐步验证或证伪,以及其在与跨语言現象解释的不断双向互动之中,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将更加完备、健壮。而中国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将提升中国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大语境中实现学术自觉、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在解决重大语言问题等方面做出中国语言学的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Geeraerts, D. The sociosemiotic commitment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6, 27(4): 527-542.
[2] 王寅. 体认语言学发凡[J]. 中国外语, 2019,16(6):18-25.
[3] 魏琛. 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6(1):39-50.
[4] 牛保义. 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 现代外语,2018,41(6):852-863.
[5] Shu, D., Zhang, H. & Zhang, L. F.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6] Janda, L.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A]. In Janda, L.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Quantitative Turn. The Essential Reader [C].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1-32.
[7] Langacker, R. W. Working towards a synthesi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6, 27(4): 465-477.
[8] Geeraerts, D. et al. 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Vol. 45) [C].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10.
[9] Geeraerts, D. Recontextualizing grammar: underlying trends in thirty year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In Tabakowska, E., Choinski, M. & Wiraszka, L.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Action: From Theory to Application and Back [C].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2011: 71-102.
[10] Kuhn, T.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2nd edi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11] 孙崇飞, 王恒兰, 张辉. 汉语句构“以义统形”, 印欧语句构“以形制义”——来自ERP的证据[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3):396-408,480.
[12] 魏琛. 交际能力与交际语境的交互性、动态性与社会性[J]. 武夷学院学报,2019,38(5):70-76.
[13] Geeraerts,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C].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2006.
[14] 张辉, 余芳, 卞京. 跨语言句法相似性对二语句法加工的影响——来自中国英语学习者的ERP证据[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49(6):803-817,959.
[15] 魏琛. 词义表征理论在大学英语多义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18.
[16] 沈家煊. 名词和动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17]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18] 王馥芳. 认知语言学反思性批评[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1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 新华网,(2016-05-18) [2019-06-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
[20] 束定芳. 認知语言学研究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21] 陆俭明. 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性[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142-151.
[22] 陆俭明. 构式与意象图式[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6(3):103-107.
[23] 陆俭明. 对构式语法理论的三点思考[J]. 外国语,2016,39(2):2-10.
[24] Robins, R. H.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3rd edition) [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6.
[25] Dbrowska, E.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6, 27(4): 479-491.
[26] 张炜炜. 体验性假说[A]. 载李福印编著(ed.). 认知语言学概论[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7-257.
[27] Ibáňez, F. J. & Cervel, M. S. P.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5.
[28] Geeraerts, D. Ten Lectures 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0.
[29] 苏琳. 新时期汉语新词语构造机制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2018.
[30] 肖慧. 现代汉语词汇、语义及语法变异现象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18.
[31] 黄玉花,刘定慧. 关于朝汉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2019,(8):261-265.
[32] 杨延宁. 基于古英语语料的使役构式演化研究[J]. 英语研究,2019,(1):34-47.
[33] Goldberg, A. E.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4] Goldberg, A. E.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6.
[35] Hunston, S. & Su, H. Patterns, constructions, and local grammar: a case study of ‘evaluation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17: 1-28. Doi:10.1093/applin/amx046.
[36] Chandlee, J. & Heinz, J. Strict locality and phonological maps [J]. Linguistic Inquiry, 2018, 49(1): 23-60.
[37] Mackay, J. Subjunctive conditionals local contexts [J].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19, 42(3): 207-221.
[38] Von Humboldt, W. & von Humboldt, W. F.Humboldt: ‘On Language: On the Diversity of Human Languag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en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peci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39] Apresjan, J. D. O moskovskoj semantieskoj kole [J]. Voprosy jazykoznanija, 2005, (1): 3-30.
[40] 徐涛. 莫斯科语义学派的语言世界图景观[J]. 外语学刊,2011,(3):72-75.
[41] Choi, J. & Harley, H. Locality domains and morphological rules [J].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019: 1-47. https://doi.org/10.1007/s11049-018-09438-3.
[42] Boi, J. Strictly local impoverishment: an intervention effect [J]. Linguistic Inquiry, 2019: 1-15. https://doi.org/10.1162/ling_a_00339.
[43] Mehta, S. Local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heterogeneity: understanding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logics of Indian new media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9. https://doi.org/10.1177/1367877919880304.
[44] 何偉, 王连柱. 系统功能语言学学术思想的源起、流变、融合与发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2):212-224,320.
[45] 许余龙. 借鉴融通 合力创新——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进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50(6):809-812.
[46] 许余龙, 刘海涛, 刘正光. 关于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52(1):3-11.
[47] 魏琛,倪盛俭. 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回答: 经典词汇语义学视角[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1):47-60.
[48] 施春宏等. 汉语构式的二语习得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9] 施春宏. 形式和意义互动的句式系统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50] 李宇明. 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51] Saussure, de. F.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Baskin, W. (tran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52] 魏琛,倪盛俭. 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回答:新结构主义语义学视角[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0,42(7):待刊.
[53] 魏琛,倪盛俭. 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回答:认知词汇语义学视角[J]. 武夷学院学报,2020,39(7):待刊.
[54] Geeraerts, D.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1st edi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5] 刘慧,李葆嘉. 关系语义:基于指称意义的特定关系联想——揭开“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第三个谜[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2):142-153.
(责任编辑:高生文)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WEI Ch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eachers Education,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354300,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Dingfang Shu, Hui Zhang & Lifei Zhang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2019) surveys comprehensively throughout the 30 year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study in China, which highlights the three tur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localiz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y. It comprehensively combs the hottest trends, research paradigm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 is of great valu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his thesis gives a brief review of the book and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ioneering, applicability, localization, guidance, critical reflection, striving for chang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ased up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we believe that, researches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Chinese facts might be one approach of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u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hilosophy of New Liberal Arts, a prospect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upon Chinese facts is also drawn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dimensions: research paradigm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odel, crosslinguistic contrastive verification as well as the combination of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research. It is an ecological system for the combin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grammar theories,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an organic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of the two: Cognitive Linguistics offers the basic affordance for Chinese grammar studies, and in converse, the study of Chinese grammar might feed in return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deep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y goes, the stronger its theoretical robustness might become. The thesis might offer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oth f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Circle and for the other linguistics schools in China.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localiz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tegration model; criticism from inner and out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