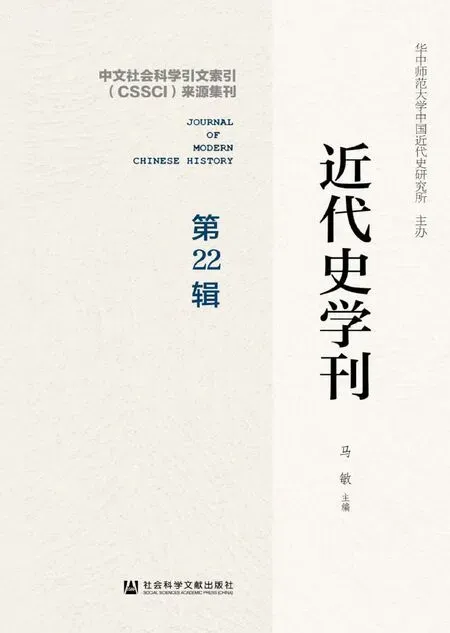从经世到学术:北京大学政治学课程体系的建立与演变*
2020-04-13桂运奇
桂运奇
内容提要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中体西用”论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其立学宗旨是培养体用兼备的经世人才,当局选择经由日本输入的国家学作为京师大学堂法政教育的主体,力求法政教育服务于国家治理。进入民国,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及法科推行一系列的学科制度改革,引导注重学术的教育取径。同时,周鲠生等英美派教师在执掌政治学系时,将课程设置改为兼重“宽大基础”与“专门研究”。1930年代后,课程设置基本不出20年代的课程体系范围,开始由“基本学问”转向“高深学术”,学术化课程日益增多。
大学史和学科史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热点,以学术机构或学系为视角的研究正悄然兴起,并成为受到学术界青睐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路径。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在中国大学政治学教育及政治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毋庸置疑,①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百年回眸》一文指出,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科,“是中国大学设立的第一门政治学课程”(《紫光阁杂志》2001年第2 期);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一文认为,“京师大学堂课程中的 ‘政治科’,是中国在大学中开设的第一门政治学课”(《东南学术》2000年第2 期);何子健《北大百年与政治学的发展》一文则称“北大是中国政治学的发源地”,“政治学与北大可谓政治学与现代中国”的缩影(《读书》1999年第5 期);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一书认为,相较于清华政治学系而言,从现代中国政治学科演进的较完整过程来看,“北大政治学系无疑更具代表性,应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三联书店,2005,第7 页)。不过,现代政治学是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在北大等中国新式教育机构确立起自身的学科地位与课程体系,其背后潜在的学派转化与制度规训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形态,这一切都需要依据史实来加以揭示。
一 “造就经世通才”:京师大学堂时期政治学课程的设置情况及其学科背景
北京大学的政治学教育可追溯至京师大学堂时期。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谕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为举办京师大学堂上谕》,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43 页。6月26日,复令“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迟延”,“倘再仍前玩愒,并不依限复奏,定即从严惩处不贷”。②《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为开办京师大学堂上谕》,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43 页。后者随即奏拟《大学堂章程》八十余条,恭呈御览。9月21日,戊戌政变爆发,10月1日,谕令声明保留大学堂。
按照《大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应为三级制,“今当于大学堂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立学宗旨则,“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标举“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义理。学堂功课方面,参照日本学校所开课程种类,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各十门,外加英、法、俄、德、日五门外语课。“溥通学”包括经学、理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等。学生应将“溥通学”全部学完,然后每人可以各学习一门或两门“专门学”。“专门学”包括高等算学、高等政治学(法律学归此门)、高等地理学等。③《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82 页。初级政治学、高等政治学课程的出现,说明京师大学堂在规划之初已将政治学视为一个专门学科。
1898年12月31日,大学堂正式开学。④《学堂纪事》,《申报》1899年1月17日,第1 版。由于戊戌政变刚刚结束,时局艰难,开学之初“学生不及百人”,无法分科设堂,至“己亥秋,学生招徕渐多,将近二百人,乃拨其尤者,别立史学、地理、政治三堂”。①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684 页。在此,政治学课堂首次出现。次年7月17日,因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遭御史吴鸿甲弹劾离职,总教习许景澄接任管学大臣,后者于1900年2月18日上奏朝廷报告自己任职半年来的办学成效,其中一项成绩是设“专门讲堂,史学、政治、舆地,计三处”。②《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奏覆大学堂功效折》,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87 页。这是文献中首次提到京师大学堂设有政治学“专门讲堂”,表明政治学正逐步独立出来,变成学校教育中的一个专门学科。
1900年7月京师大学堂因庚子之变被迫暂停,1902年张百熙受命出任官学大臣,开始着手恢复京师大学堂的日常工作。张百熙主持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大学堂内设大学院、大学专门分科及大学预备科,附设仕学馆、师范馆。大学专门分科略仿日本例,分为政治科、文学科、农学科等七科,其中政治科下设政治学、法律学二目。在此,政治学“专门讲堂”改成政治学“目”。③《钦定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87 页。不久张之洞等人又重新修订京师大学堂章程,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大学堂分科大学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等八科,其中政法科大学分为政治门和法律门。在此,政治学“目”又进一步演变为“政治门”。④《奏定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97 页。1910年3月31日,包括政法科“政治门”在内的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正式开学,⑤《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202 页。“政治门”的设立标志着北京大学政治学本科教育从此开始。
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后,因缺少生源,分科大学并不急于创办,而仕学馆则开办在即,故《钦定大学堂章程》并没有制定详细的分科大学课程,但对仕学馆课程有比较具体的规定,而事实上这一阶段大学堂的法政课程也主要是在仕学馆讲授。仕学馆课程包括算学、政治学等十一门。⑥仕学馆课程包括算学、博物、物理、外国文、舆地、史学、掌故、理财学、交涉学、法律学、政治学。《钦定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87 页。仕学馆生源多为“已入仕途之人”,所以课程“趋重政法”,如交涉学讲授内容包括公法、约章使命交涉史、通商传教,政治学讲授内容包括行政法、国法、民法、商法。可见当时的课程基本都是关于政事和法律,且时人的分科观念“政治学”尚属于法律的一部分。1904年颁发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对设置分科大学做了规划,且具体规定了各科各门所应修习的科目。其中政法科“政治门”科目设置分15 门主课及4 门补助课。①政治门科目主课包括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全国人民财用学、国家财政学、各国理财史、各国理财学术史、全国土地民物统计学、各国行政机关学、警察监狱学、教育学、交涉法、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海陆军政学;补助课包括各国政治史、法律原理学、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97 页。这份“政治门”课程设计意义非同寻常,它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本科政治学教育课程规划。
仕学馆和政治门的课程设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内容广泛、讲究致用,涉及政治制度、警察监狱、军政、财政、教育、地理、科技、外语、法律、统计、外交等与国家活动和社会管理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囊括了“中西各门政治之学”。②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 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483—1502 页。这一现象显然与清政府的立学宗旨有关,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的目的就是培养体用兼备的经世人才,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③《大学堂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97 页。于是入校学员被当局要求“以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学校、理财、交涉、农、工、兵、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为成效”,“所列各科学,均系当官必须通晓之学”。④《奏定进士馆章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 卷,第153—156 页。可见,培养“博通”的经世人才是当局创办大学堂及开设相关政治学课程的主要目的,至于学术人才的养成,当局也不是没有考虑,如大学堂章程就明确表示会设立大学院,“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为成效”,然而囿于时局、经费、人事艰难,这一目标流于画饼,直到1920—1930年代才得以逐步实现。
政治学课程设置内容广泛、讲究致用,除与清政府的立学宗旨有直接关系外,其更深层次的学科背景则要追溯至经日本输入的欧陆政治学。1898—1911年,京师大学堂前后三次聘请法政教员,⑤萧超然等主编《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印,1998,第83 页。其中中国教员基本上是留日学生,如林棨、王家驹、嵇镜、程树德、王基磐,其余多自德、法等欧陆国家留学归来。聘请的外国教员大部分为日本学者,其余基本来自欧陆国家。如此,北京大学的政治学课程设置一开始就是以日本和欧陆为榜样。德国人所说的政治学是纯粹研究主权概念、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的学问,所以“德国的大学中没有政治学的分门”,“盖德人之观念,政治无他,不属于经济则属于法律,大学生用的两种教本是:一为学理,一为政策”。①马亮宽、王强选编《何思源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35 页。法国的政治学则被设想为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技能有关的各种学科,甚至包括外语。②〔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卷,竺乾威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6—36 页。“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习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③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疏》,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 册,中华书局,1928,第36—40 页。可见,以德、法政治学为代表的欧陆政治学是国家干涉主义的反映,凡是与国家现象相关的知识皆属于政治学,可以覆盖经济、法律等很多方面,学科内容自然是非常广泛且富有实用色彩。
明治日本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制实模仿德国,在政治学科设置方面也就主要受德国学科体系影响。被誉为日本科学的政治学创始人、近代日本国家学派代表性人物的小野塚喜平次曾留学德、法且深受德国国家学影响,他说,“日本向来多在广泛意义上将国家学和政治学加以通用”,政治学的内容分“纯理研究,如政治史、政治统计、政治地理、国法、行政法、国际公法、国家原论”。“应用研究,如政策原论、行政学、经济学之政策论。”④孙宏云:《小野塚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历史研究》2009年第4 期。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接连派遣大臣和学生东渡日本取经,此时清政府看到了德国国家学说被明治日本采纳后对其建设现代官僚国家所产生的巨大理论价值,希望通过自日本引入的德国国家学来指导自身建立一个与日本乃至德国相似的现代官僚体制国家。于是,德日政治学学科规划迅速被京师大学堂及各地法政学堂模仿,再配合当局培养体用兼备经世通才的办学主旨,最终形成了北京大学政治学课程早期偏重博通、致用的课程特点。
二 先“宽大基础”后“专门研究”:英美派教师的课程改革及其学科背景
辛亥革命爆发后,学界停散,学期延误,各科学生多有散去未尽归来者,京师大学堂一时被迫停办。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①《教育部总长呈荐任大学校校长等文》,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 卷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 页。5月3日,北京政府又批文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亦改称大学校校长,这样严复成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长校后立即“召集职员复开教员会议,提议各科改良办法”,“各科科目均有更改闻尤以法政科最甚”。②《燕京零拾》,《申报》1912年4月8日,第2 版。此时严复接手的北京大学实为一烂摊子,“大学的内容缺点,久为社会所洞悉”,社会“咸有不满之意”,为此严复起草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希图补救。
在这个说帖中,严复就法科改良办法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为防止学生“新旧参差,教法不能一致”,对于前清入学学生,“拟缩短原定学期”,“每门各择一二主要学科择要讲授”,计划将旧班于当年底结束,让学生提前毕业。第二,前清时期,大学堂政治门、法律门分别用英文、法文教授,且授课内容为外国法律、政策等。严复注意到“各国法律学校无不以本国法律为主者”,提议“以本国法律为主课,用国文教授”,而外国法律只应为辅助课,可用英文、德文授课。第三,严复认为“约法及参议院法皆现行之法律”,“皆学者所当购贯”,“外国法律与吾国前朝成宪,只以借资考镜,研究法理而已,不能作为主要科目也”。③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 卷上册,第30 页。严复的上述观点实际上为后来北京大学政治、法律学科的本土化、社会化奠定了认识基础,或者说至少成为一种先见之明。由于政治、人事、经费纠葛,严复与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矛盾冲突不断,心灰意冷,旋即隐退,④皮后峰:《严复辞北大校长之职的原因》,《学海》2002年第6 期。但他在北京大学及政治学科早期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时的北大实际情况是,“学校像个衙门”,不少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⑤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 辑,北京出版社,1979,第47 页。学生“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 卷,中华书局,1984,第5 页。鉴于学校的这种现状,蔡元培上任伊始就着手校务改革,并将矛头对准法科。他主张“学”、“术”分校,理由是“文、理,学也”,“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法、商、医、工术也”,“致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①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 卷,第149—150 页。按此“学”、“术”区分的标准,法科属于“术”和“高等专门学校”的范畴,应该予以独立。蔡元培也确实计划裁去法科,使之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合并,但终因“多人反对,故仍存留”。②《北京大学之改革》,《教育杂志》1917年第5 期。蔡氏分出法科的计划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法科官僚腐化现状的反感与厌恶,另一方面与其对“学”、“术”性质不同的看法有关。
1919年,北京大学改革学科组织,决定在注重学理不在应用的前提下,废除文、理、法科之名,废门改系分组。在12月3日评议会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中,大学本科被分为五组十八系,其中政治学系、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史学系属于第五组。③前四组分别是:组一,数学系、天文系(组织中)、物理学系;组二,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组织中);组三,哲学系、心理学系(组织中)、教育学系(组织中);组四,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组织中)。《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 卷上册,第80 页。这一新的学制改革方案,形式上要促使各系在各自学科所列科目基础上,多汲取其他学科的科学知识,“融通文理两科界限”,进而“得完全明确之精深学术,专为养成学者”。④《国立北京大学之内容》,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 卷下册,第3156 页。它是蔡元培“学”、“术”分校思想在学科组织方面的具体延伸。在此,“政治学系”作为一个专业系别名称,在北京大学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政治学学科史上第一次出现。
蔡元培一心想将北京大学打造成德国柏林大学那样研究学理的高深学府,上任之初他就表示要“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⑤蔡元培:《复吴敬恒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 卷,第11 页。他为政治学系先后聘请了一批新近留学归国的优秀师资,如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周鲠生、王世杰等,这些新聘教师在学派背景上多属英美派。当时的报刊登载,“在前清光宣之际,法科则东洋留学生握有实权”,“近来英美留学生势力较盛”。⑥《国立北京大学之内容》,《申报》1918年12月29日,第6 版。至1920年代后期,英美派教师的学术职位与影响力在法科已成绝对优势,如1923—1927年,留美归来的周鲠生接连以多数票当选政治学系主任,王世杰则一直担任法律系主任。系主任是由系教授会民主选举,周、王二人能连续当选,英美派教师的学术理念与人脉关系在法科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由于掌握了法科学术、行政要职,英美派教师开始将清末以来模仿日本所建立的德国学科体系转换为英美学科体系,法科的教学和研究风气也随之一变。蔡元培曾说,北大旧日的法科改革十分不易,“直到王学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后”,“学生渐去猎官的陋习,引起求学的兴会”。①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 卷,第199 页。李叔华也说,王世杰、周鲠生等人“对于法科方面的充实及提高课程水准,贡献颇多”。②李书华:《七年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第93—100 页。就政治学系课程而言,实质性的变革正是发生在周鲠生担任系主任前后,此时课程内容开始由国家学向社会科学发生重大转变,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开始成为学习政治学的基础。
此时,英美派教师改革政治学系课程的主要方向是追求课程设置齐全,使学生能够获得一个“广阔之基础”。在1923年11月的一次师生交流会上,周鲠生告诫学生治学须先有“宽大的基础”,然后才能进行“专门的研究”,否则会导致“研究时各自为说,不能统观全豹”。只有“一般基本学问均富有后”,才能“从事专门之研究”。王世杰提醒学生“专门研究系指专于某科及某几科而言,非云专门问题研究也。盖此等研究非先有顶丰富之基本学问不能也”。他要求学生若有志于做某科研究,必须将“此科及其相关之书籍,多多研读,以作将来专门问题研究之基础”。③《北大政治学会欢迎导师各导师谈话记录》,《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22日,第2—3 版。顾孟余也说道:“专门太早,往往拘于一隅,以致结果便反不甚满意。关于这一点,英美的大学确是要好些,就是先给学生一个宽大的基础。”④《顾梦渔先生在政治学会的谈话》,《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1月27日,第3 版。可见,英美派教师希望学生不要急于做专门研究,而是广泛钻研与政治学相关的学科和书籍,为自己打下一个广博的学术基础。
从民元以来政治学系历年课程表中可看出,1920年度之前课程内容大体因袭了晚清时期的风格,深受德日课程体系影响,基本都是些法律、政策类科目。而1920—1921年度政治学系的课程内容变化是很大的,若干“无谓的”政策、法律类科目开始被删除,最重要的是,第一学年增加“人类学及人种学”、“日本近世史”为选修课;第三学年增加“社会学”、“统计学”为必修课,显示出追求政治学基础宽广的趋势。①《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九年至十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19029。1921—1922年度,课程内容又有一定变动,进一步将政治性较强的法律、经济类科目如“宪法”、“行政法”、“经济学原理”改为选修科目。1922—1923年度课程变化不大。1923—1924年度,复将政治性较强的法律类科目如“宪法”、“国际公法”、“行政法”改为必修课,但经济类课程如商法遭删除,民法和刑法仅各自保留总则和总论分别作为必修和选修。②《政治学系课程沿革说明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6月16日,第2 版。1925—1926 学年,课程分新旧两种,其中旧课程适用于第四学年学生,在该种课程选修课中增加了“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欧洲社会变迁史”等政治学应有的“基本学问”。③《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四至十五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19025。
应该说,强调学生学习政治学必先拥有一个宽广的基础,使自己具备丰富的“基本学问”这一见解,在蔡元培1919年推行分组选科制时,就已初现端倪。在蔡氏看来,选科制的一大功效就是“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他认为“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④蔡元培:《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21 页。在分组选科制下,本科一年级学生不划分具体系别,需要学习“大学学生所不可少之基本学科”,主要有“哲学史大纲”、“社会学大意”、“科学概论”等。二年级开始划分具体系别,以政治学系为例,学生除需学习本学科课程外,尚需要选修大量相关系科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科目知识。另外,选科制下,各系学生还需“在不相关之系内得选习六单位课程”,这意味着政治学系学生如欲毕业还必须选修诸如物理、化学等理科课程。⑤《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新制大旨》,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 卷中册,第1078 页。
周鲠生等英美派教师对政治学系课程的改革,重视为学生造就一个宽大、广博的学术基础,这一点某种程度上可视为蔡元培学制改革精神的继续,况且选科制本身就是对哈佛等美国大学学科制度的学习与模仿。但周鲠生等人进行课程改革的更深层次原因,恐怕还要追溯到当时正在美国兴起的“新政治学”。新政治学“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时期在美国急速发展起来的”,它是“与在英国和德国发展起来的建立在旧有基础之上的以法学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传统政治学的诀别”。至1920年代前后,以默瑞阿姆①默瑞阿姆,美国现代政治学之父,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曾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部部长、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等职。所开创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政治学,渐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中心,享有“指导的地位”。默瑞阿姆所倡导的新政治学是要“将诸科学与政治学异花受粉”,他指出,“政治,于结局之处不单单包括了法律、规则的文书”,它是“基于各种各样的样态的状况之下的各种各样的pattern行为得以形成的”。他指导学生将“政治学同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等结缘”,“得以把政治学和法律紧紧搅在一起的枷锁放松开”。②〔日〕内田满:《早稻田与现代美国政治学》,唐亦农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205—275 页。显然,美国新政治学认为政治学研究不是法学研究,应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目。
新政治学对周鲠生、张慰慈、王世杰等人到底有怎样的影响,目前尚无直接资料证明,但这种影响仍有迹可寻。张慰慈在其编写的教材《政治学大纲》③张慰慈,留学美国,回国后任教北大政治学系,其所编教材《政治学大纲》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一直被选为北大政治学教科书,并被印至第8 版,该书所折射出的政治学概念对北大政治学系师生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中认为,政治学属于社会科学之一种,社会科学可分为“研究个人的动作和智识”、“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两大类。前者包括伦理学、心理学,后者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等。这其中政治学研究人与人在政治组织的社会中的关系,社会学研究人与人在社会上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社会学是政治科学的基础。在谈及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时,他认为,历史学确实是政治学的中心,是研究政治学的材料和基础;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是教人怎样行为的工具,伦理观念也有很多可以做政治上的政治观念。不过,他没有提到法律学。他还介绍了研究政治学的方法,依次是生物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试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④张慰慈:《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3,第1—28 页。可见,周、张等英美派教师的课程主张所反映出的政治学概念与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新政治学的特征是十分接近的,二者的学术渊源亦复明了。
三 由“基本学问”到“高深学术”:现代政治学课程体系的形成
1927年6月,张作霖入主北京政府,任刘哲为教育总长,将包括北大在内原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至此,“国立北京大学之历史,遂暂归中缀”。①何基鸿:《国立北京大学沿革述略》,《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1929年第1 期。由于时局动荡,北大旧教授纷纷离去,原政治学系教授周鲠生、王世杰、陈启修等人或离京南下或赋闲停课。1928年夏,北伐军克复北京,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成立“国立北平大学”,并开始实行北平大学区制度,北京大学并入北平大学,改称“北平大学北大学院”。1929年初,原北大师生为恢复北京大学原来的建置规模,与南京政府当局进行斡旋,展开了艰难的“复校运动”,最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于该年8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北大学院恢复“国立北京大学”旧称,并直属教育部。至此,北大复校基本实现。
1930年12月,蒋梦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②《国民政府令(十九年十二月四日):为任免教育部长由》,《教育部公报》1930年第49 期。他执校后决心整顿北大,推动学校的学术化进程。为此,他一方面与各方斡旋,煞费苦心为学校聘请有学识的教授,另一方面计划“今后拟减少钟点,提高教授待遇,使教授有充分时间研究学问,富藏高深学问之储蓄”。③《蒋梦麟昨日之重要谈话》,《京报》1931年4月28日,第7 版。经过一番整顿,北京大学于1932年夏公布新的组织大纲,全校分为文、理、法三院,其中法学院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三学系,并宣布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办学宗旨。
事实上,追求北京大学教育学术化的理念在蔡元培时代已显端倪。蔡氏长校后,推行选科制,其目的虽为融通文理界限,但蔡元培内心深处认为大学应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蔡元培是以教育学术化的理念来办北大的,只是这种学术化精神,各学系吸纳程度高低不同。就政治学系而言,主系的英美派教师显然受此时美国新政治学影响更多,该系课程主要还是注重博通的通才教育,强调要给学生打下一个广阔的学术基础。从学生方面看,他们中很多人对从事政治学研究有强烈的兴趣,对本系的通才教育模式多少有一定抵触。甚至有部分学生建议修改课程,理由之一是“入政治系者其志或在研究高深的政治学理,故不必强令其学习漠不相关之学科,以耗费其可以不必耗费的宝贵光阴”。①周杰人:《修改政治系课程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6月16日,第1—2 版。不过,学术化的课程在20年代的政治学系课程体系中还是占有小部分比例,如设置“演习”课,使教员和学生“关于政治学理,可以常常有共同研究的机会”;开设“现代政治”课,让教员在课堂上针对一些“现代的政治问题”发表讲演,“帮助大家一同研究”。②《陈启修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第3—4 版。
可见,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政治学系课程设置背景较为复杂,既要适应校长的“学术”化方针,又要符合学生方面的要求,还要迎合英美课程体系这一时代潮流。最终确立和实行的课程方案显然只能是各方碰撞与调适的结果,具体则表现为以通才教育为主,兼重学术教育。进入30年代后,政治学系课程设置基本不出20年代的课程体系范围,只是博与专之间的侧重点发生变化,政治学学术教育的要求明显增强。由1931—1935年政治学系历年课程表可见,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中国通史、伦理学等社会科学以及政治性较强的法学类科目几乎列入每一年的课程表中,或为必修课,或为选修课,且占有较大比例。另外,从1932年开始,课表中开始列入逻辑、哲学概论、科学概论三门课作为学生选修课,且从第一至第四学年每学年都会列入,意在提醒学生务必选修,这类课程是20年代课程体系中所没有的。
新课程体系与20年代的课程设置相比,相似的地方实有不少,如都注重学生“基本学问”教育,这种“基本学问”包括之前已经开设的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以及此时新开的逻辑学等课目。但“基本学问”既可以视作学术研究的基础,也可看作研究高深学术的手段。从周鲠生等人对于政治学与各社会科学关系的论述来看,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政治学的广阔基础,在从事政治学学术研究之前必须加以“博通”,而新课程体系新开的逻辑学等社会科学的目的却是帮助学生学会一种研究高深学术的手段,是对课程学术化趋势的一种回应。如逻辑学课,“分绪论、原来论、方法论三部分”,旨在“详论概念、判断和推理底性质”。③《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课程说明书(民国二十二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3014。显然,其开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这一类课程的学习与训练,养成缜密思维及严谨的叙述习惯,使学生从事高深学术研究时具备一定的思辨能力及洞察力。
周鲠生时期的课程虽然广博,但也显得十分杂泛,因为周鲠生等人一直强调要给学生一个“广阔的基础”,因此那时课程体系的中心和重点均不明确。新的课程体系同1927年之前的课程设置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将四年的课程一分为二,从1932年开始,“本学系课目分为两种,一种为共同必修课目,一种为主修选读课目。共同必修课目必须于第一第二两学年内学习完毕,至于第三第四学年,本学系学生需按照各人兴趣,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或国际关系三组课目中主修一组”。①《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一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0014。实际上就是将四年的课程分配为一、二两年偏重基础知识讲授,三、四两年兼重学术研究,这一课程设置明确规定将三、四两学年用于养成学生学术研究能力,与20年代强调给学生一个“广阔的基础”,且学术化课程只占很小比例的课程体系相比,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进步。为贯彻新课程体系的规定,“社会学”、“心理学”、“中国通史”、“西洋近百年史”等作为政治学之“基本学问”必须在一、二两学年作为必修课先行学习。此外,统计学、伦理学等科目可以在一、二年级选修,三、四年级也仍有补选的机会。②《政治学系二十二年度课程表》,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3014;《国立北京大学政治学系课程指导书及课表(民国二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4009;《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各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5008。
至于三、四年级的开设科目,自1932 学年开始渐趋系统,课程被设置成主修选读课目,分为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组。学生“务须按照个人志趣,于各该组内,依各种课目之性质,分类选修,不得杂选不成系统之课程”。③《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各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二十四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北京大学档案BD1935008。然后随专治该组的教员专攻两年,并于毕业时以毕业论文的形式提交研究成果。至1934 学年,分组专攻、重视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教学理念进一步增强,从该年起,一、二年级在偏重基础知识讲授的同时,选修课被按照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三组进行了划分,这意味着从该年开始要求学生一年级入学后即考虑自己以后学术专攻的方向,形成分组专攻的学习习惯,以为三、四年级完全进入学术研究状态打好基础。分组选课制度“使学生们可以专门钻研某一领域,有利于培养专门化人才,这种‘专’与前面的‘博’相互辉映,这样的教学安排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是高素质的”。①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史(1898—1998)》,第33 页。分组选课制度是对20年代课程体系的继承与发扬,它既照顾到通才教育这一传统设置,又极大地兼顾到学术教育,并使后者有后来居上之势。
考虑到三、四年级应该偏重研究,课程不再严格分年级设置,不分必修、选修,一律设置成选修课,且门类十分丰富。三、四年级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选择自己有志专攻的课程,而不必全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分组专攻的前提下,各组还长期配置了一些更精深的课程,类似于专题研究,如政治思想组开设马克思学说研究、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政治制度组开设中国行政制度研究,国际关系组开设中日外交史、远东政治研究,这些专题研究无疑是在各组内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由面向点、朝着更精专的方向做了进一步推进。
总之,30年代的课程设置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可以说,至抗战前,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注重在一、二年级进行“基本学问”的讲授,帮助学生打下一个广阔的学术基础,使学生对政治学基本原理、古今中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基本社会科学等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掌握,尽量做到“博通”;也注意在三、四年级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分组专攻,并结合教师的研究专长,在导师的指导下,使学生在专业学术研究方面得到一定训练。该课程体系实际上为此后数十年北大政治学系的课程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 结语
现代政治学课程体系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演进,首先是域外政治学知识援外入中的结果。京师大学堂建立后,所聘教员或留学日本或本身即为日本学者,这注定了京师大学堂时期的政治学教育和课程设置深受明治日本的教科体系影响。此时日本的政治学又主要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学影响,主要关注国家、法律、主权、经济政策等与政权性质、国家治理相关的理论问题。因此,京师大学堂时期政治学相关课程设置表现出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涉及国家管理、国家权力的各个方面,并以法律类、政策类课程为主。进入民国后,北大政治学课程设置仍然长期保持着比较明显的国家学风格,至1920年代中后期,周鲠生等英美派教师逐渐执掌政治学系,该系课程设置随即转向美国学科体系,受到美国新政治学的影响,大量增设相关社会科学科目,强调为学生打下一个广阔的学术基础。
现代政治学课程体系在北京大学的建立与演进同时是学科制度规训的结果。经日本输入中国的欧陆国家学之所以能成为京师大学堂、各地法政学堂政治学教育的主要形态,与清政府所订立的学科制度密切相关。从1898年的《大学堂章程》到1902年《钦定大学堂章程》及隔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始终是培养体用兼备的经世人才,而欧陆的国家学正好适应了这一要求。于是,经由日本输入中国并被当局认可且允许其在各学校讲授、传播的政治学形态只可能是国家学而非革命性的自由民权学说。1919年蔡元培长校北大后,先后推行“学术分校”、“废门该系”、“分组选科”制度,为1920年代政治学系所追求的学术教育模式打下了基础;同时该系在周鲠生等英美派教师的大力改革下,课程体系开始朝社会科学的方向转型,兼重“宽大基础”与“专门研究”。进入30年代后,政治学系课程设置基本不出20年代的课程体系范围,只是博与专之间发生了由“基本学问”到“高深学术”的侧重变化,学术化课程日益增多,整个课程体系也更趋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