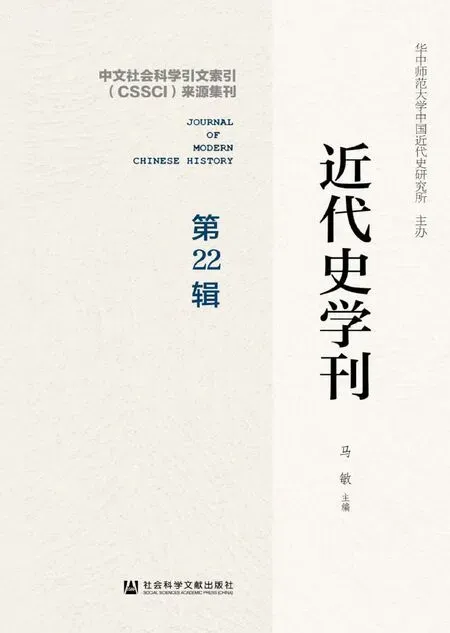成与败:清末的州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
——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一书述评
2020-04-13万海荞
万海荞
关于清代州县体制,学界众多名人有出色的研究。瞿同祖分析了清代县官、州县衙署四类助员(书吏、衙役、长随、幕友)的职能,认为清代州县为“一人政府”。①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11。在此基础上,魏光奇叙述了州县行政的治理结构、衙署组织及其各种职能,他从清代州县财政的制度设计、实际运作情况认为州县财政具有家产制性质。②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2010。他的另一本著作《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则将重点放在北洋时期、国民政府前期及新县制时期的县体制。③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萧公权从乡村地区组织、基层行政组织、乡村的治安、税收、饥荒、思想控制等方面探讨19世纪的州县地方治理。④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关晓红从“内外相维”探讨近代政体转型,认为内外官改制失序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由于她认为外官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在省制方面,对州县改制着墨不多。⑤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三联书店,2014;《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中华书局,2019。由于研究对象及论述视角的差异,以上学者没有对晚清州县改制进行详细的论述。而最近,刘伟教授出版了《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⑥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以下简称“刘著”)一书,以各种政书报告、报刊、地方志及地方档案为基础,结合中央制度规定及地方运作实态,从宏观上介绍了各地州县体制变革情况,对清末州县体制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层面的转变进行了考察,展现了新旧制度之间的纠葛与转换。目力所及,到目前为止,该书应是研究清末州县改制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一 立宪改官序列中的州县改制
清代州县为“一人政府”,实行正印官独任制,县丞、主簿等佐贰官不普设,主要依靠幕友、长随、书役等衙署群体及里甲、保甲、乡地、乡约等地方役职来管理征税、司法、治安、教育、赈济等事务。这种落后的管理体制弊端重重,不健全的职能机构难以深入乡村,以私人身份履行公职导致大量营私舞弊。鉴于州县体制的以上弊端,进行官制改革、增设职能部门、建立基层自治组织是清末州县改制的基本方向,这也是刘著论述的重点。
清末官制进行了剧烈变革,废除科举,设立民政部、度支部、学部、农工商部、法部等部,突破了传统的六部格局,1906年后又实行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①〔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第215 页。在省级方面,设置了督抚衙门会议厅,设立了布政使司、提法使司、提学使司和劝业道、巡警道及谘议局。部分学者认为清末新政的官制变革成效集中于中央和省级层面,对州县关注不多。从中国县政发展的历史看,晚清县政是中国县政近代化的重要时期,县政结构及县职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刘伟教授自2003年出版《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②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一书后,研究视野开始向下转移,注意省制与州县问题。与彭剑、肖宗志合著的《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③刘伟等:《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一书重点论述中央关于外官制改革的设计与实行,内容涉及省制与州县改制。正是由于这么多年的知识积累与相关制度变革的研究,在《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一书中,作者能清晰地论述州县改制在整个新政变革中是如何展开的及州县改制相关制度规定的因果延续。
制度的演变分为渐变和突变两种方式,就清代官制而言,清末新政变革是一次突变,而刘著认为晚清州县改制是渐变和突变的结合。晚清以降是中国“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西方制度的冲击及中央权力的下移,州县的司法、财政与社会控制发生了变化。刘著从“就地正法”与州县司法审判权的变化、州县官的教案审理、州县外销经费的演变、州县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州县官的选任变更论述了这个渐变过程。
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是人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利益冲突会制约制度的演进和发展。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依靠强制力量自上而下进行官制变革,因而清政府对州县改制的计划策略和主要领导者的思想认识能够影响州县改制的方向。清末仿行立宪,方式取法日本,内容涵盖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板块。对州县的设计为:第一,改革州县行政隶属层级,将地方分为府、州、县三等;第二,改变正印官独任制,设置佐治各员管理州县事务;第三,改革州县司法审判制度,司法行政分立,设立地方审判厅;第四,实行地方自治,设立城镇乡议事会及董事会。①《编改外省官制办法及各疆臣之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21 页。关于州县改制的步骤及时间,清政府没有明确的计划,随着时局和改革主导者的意图而改变。
在建立责任内阁流产时,清政府于1906年进行外官制改革。外官制有省制和府厅州县制,清政府先规定以州县改制为先,彭剑教授认为这与人们对宪政建设的认识及官制改革核心人物孙家鼐的态度有关。②刘伟等:《清季外官制改革研究》,第26 页。由于地方督抚的疑虑,到1907年《直省官制通则》时期,清政府放弃了从州县入手的方式,改为从省级机构入手。省级设置了三司两道,完成了新政事务管理机构,加之1908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的公布,清政府进行了州县新政改革。在筹办地方自治时,中国仿照日本体制,实行城镇乡和府州县两级自治。关于先筹备哪一级自治,清政府的意图是先办府州县一级,再进行城镇乡一级。而1908年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的颁布认可了先办理城镇乡一级,府州县官制未定及新政在学堂、农工商政、巡警方面的压力是重要原因。但在实际运行中,也没有按照顺序办理。也就是说,在立宪改官的背景下,州县改制没有按预定计划来。
二 整体视野下的州县职能转变
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界由此前聚焦的革命、政治等宏大叙事转向为一些微观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研究的碎片化,论题小而微,细碎而零散,割裂了碎片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王先明教授认为在新史学的构建方面,超越“系统性的缺失”和将理论导向整体性观照与系统理论构建是新史学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改革,①王先明:《“新史学”的开拓与建构——评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 期。州县改制论述很容易陷入通史的地方化困境,而刘著在超越碎片化和统合区域方面进行了努力。清末州县改制由一个个别地方试点到大规模推行的过程,刘著对先期试点个案进行了考察,然后比较先期试点和大规模推行的差异,最后对执行中的变异进行了考察。天津县的改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巡警、劝学、自治带有实验的性质,和后来通行的制度有一些差异,刘著详细分析了天津县的制度异同,在超越碎片化的取向中展现了州县改制的脉络及演进。在州县改制各具体方面,刘著也花大力气整理了全国的实际情况。晚清州县致力于两个功能,一是财政汲取能力,一是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州县政府的职能不断扩大。刘著从教育、治安、司法、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依据州县改制的顺序,刘著首先介绍了劝学所与州县教育管理体系的转变。清代州县的教育机构为书院、社学、义学、私塾,由于科举的影响,当时的教育主要是培养科举人才,所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学官设有教谕、训导,但不是教育管理部门,只管理涉及科考的生员。新政时期出现了新式教育机构劝学所,劝学所的职责为劝学、兴学、筹款和开风气。经过劝学所的努力,新式学堂教育渐成规模,各种高等、初等小学堂、半日学堂、实业及师范学堂先后建立,课程内容也以儒家经典转向德、智、体方面发展。刘著认为劝学所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行政机构,在“条块”中,它归入中央学部—省提学司—州县劝学所序列,同时归入州县官监督考察。在运行中,则为“官督绅办”,行政介于官治、自治之间。其后实行地方自治,劝学所改为官办。
刘著第三章讨论州县治安体系的变动。清代的治安主要依靠保甲,十户为一牌,设牌头。十牌立一甲,设甲长。十甲立一保,设保长,管理户口、治安和赋税等,但保甲管理烦琐,日益废弛。晚清对保甲进行了整顿,注入了新的元素,任用士绅、设立保甲局来强化治安。团练的大规模兴起与太平天国有关,基本模式为团保结合,以保甲为基础,将牌、甲、保结合到团练之中。但团练不具有普遍性,是一时一地的行为,且兴废无常。清末治安体系变革的重要标志为巡警的建立,传统的治安体制以防盗为限,而警政的建立除治安外,还履行户口调查、消防卫生及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等职能。巡警建制为设警务长一人,采用总局—分局—巡所体制分区办理。1908年各州县加快了警政建设步伐,清覆亡前大部分州县巡警已建立,但数量和质量不平衡。刘教授认为巡警的建立是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但清末巡警是否能发挥实效还有待更多的证据。
第四章,州县司法变革。刘著认为晚清州县司法变化表现在“就地正法”制、审理教民案件和预备立宪的司法改革等三个方面。清代州县有权决定笞杖之刑,徒罪由督抚批结,军流、死刑须上报刑部。①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司法职能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14。咸同之际的“就地正法”使得州县官拥有了死刑决定权,但“就地正法”的司法程序不断变化,起先是讯明后即可执行,后来增加了一个府州或道复审环节,死刑审核权在督抚。预备立宪时期,进行司法改革,死刑的审核权复归中央,就地正法被限制在军事范围。清末新政时期,刘坤一、张之洞的《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提出“恤刑狱”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改革刑讯制度,改笞杖为罚金,是刑事新制的起点。监狱改良、看守所和习艺所的建立,使监狱由羁押人犯变为了罪犯服刑场所。预备立宪时期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离,在州县筹办审判厅和检察厅,但大部分州县没有按此实行。刘著认为尽管如此,但审判厅的设立部分改变了州县司法。
第六章,州县财政、经济职能的调整。清代州县财政分为起运和存留两部分,起运上交府省,存留用于俸食、祭祀、驿传、廪膳及孤贫等地方开支,由于赋役的定额化,存留部分无法满足地方需求,一些学者注意到了陋规,②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魏光奇:《清代州县财政探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 期。岁有生提出了二元财政的概念。③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大象出版社,2013。刘著从外销论述晚清财政的变化,认为清代高度集中的财政制度和僵硬的奏销制度不能满足财政需求是外销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大规模的外销是在新政时期。①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第348 页。此前“化私为公”的努力无法取得制度性的突破,宣统年间的预算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官员的职务津贴和办公经费逐渐分离。咸同时期,清政府为筹措经费建立了厘金制度,随后各地杂捐泛起,②“豫省近数年来,各属举办新政,因地筹捐……有抽之于花户者,如串票捐、契税捐、契尾捐、房捐、亩捐、随粮捐之类是也。有抽之于坐贾者,如斗捐、商捐、铺捐、油捐、火柴捐、煤油捐、粮坊捐、变蛋捐之类是也。又如枣捐、瓜子捐、柿饼捐、柳条捐,柿花、芝麻、花生等捐,则就出产之物而抽收。如戏捐、会捐、庙捐、巡警捐、册书捐等,则因特定之事而抽收。”《河南财政说明书·岁入部厘金》,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3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第645 页。一些省份进行了经征改革。梁勇考察了四川经征局的运作实态,认为四川设立经征局,由省级税收机构统一征税,反映了晚清州县行政机构行政权、财政权逐渐分离的“近代化”过程。③梁勇:《清末四川经征局的设置与州县财政改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 期。而刘著认为经征局的设立有助于州县官经济职能的转型,传统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赋税征收、开荒种植及通过牙行管理手工业和工商业,而新政时期州县转向发展农工商业,成立劝业所。
第七章,州县人事制度变更。捐纳和保举为选官制度中的异途,咸同军兴,为筹集资金,捐纳频繁,导致候补官员激增,仕途阻滞。保举也华而不实,冒乱严重,加剧了选官制度的紊乱。在地方督抚与吏部选任权方面,吏部选缺多为中、简缺,地方选缺为要缺和最要缺,伴随中央权力的下移,督抚逐渐侵蚀吏部的选任权,利用人地相宜借口突破成例,运用委署来鸠占鹊巢。同光年间实行了强化部选、调整委署、规范保举等措施,但收效甚微。新政时期的改革包括通过考试选拔、变通回避制度及停止部选。刘著认为停部选只是一个从“部选与外补并存”向“全归外补”的过渡过程,督抚的选任权仍受制约。④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第448 页。考核制度的变革也是重要部分,州县官的考核为大计,以“守、才、政、年”四格评等级,以“贪、酷、罢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法处分官员。⑤《清文献通考》卷八十《职官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3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901 页。清末新政时期则转向实际工作的成绩,涉及民政、教育、自治、农工商政、词讼、钱粮、保息善政等方面,与之相关的建立册报制及各职能部门分别考核,有助于新政事务的开展,但也出现流于形式的现象。
三 官治与自治:清末州县治理模式的转变
关于传统中国乡村治理,黄宗智认为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①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年第2 期。政府的规模有限,法律规定将每个县的衙役和书吏控制在几十人之内,“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②〔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24 页。任用来自乡村的半正式人员如乡保、乡地、保甲、村长等进行半正式行政实践。③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中华书局,2008。此外,地方士绅和宗族也承担部分公共事务。但这些半正式人员以私人身份履行公职,营私舞弊层出不穷,“动行乡约、社仓、保甲、社学,纷纷杂出”。④陆世仪:《论治邑》,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第811 页。嘉道之际,“教匪”作乱,这种官役制无法维系地方社会秩序。而从嘉庆朝开始,“文字狱”已放松,地方精英的权力已增长,大量投身地方公共事业。⑤〔美〕罗威廉:《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6 页。咸同以后形成的绅董制在乡村治理体制中起着关键作用。⑥王先明:《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 期。这种地方治理的转型也将现代地方自治制度导入政治制度的建构中,此后,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官员运作的国家行政与由地方社会自下而上推选本地人士运作的地方自治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县制改革和演变的主轴。⑦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第1 页。
在实行地方自治之前,不少官员有设乡官之议,如冯桂芬“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设立丞簿和巡检,以达到“大小相维,远近相联”。⑧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12、13 页。由于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没有欧洲那种“普遍的抵制、广泛的讨价还价和市民权利和额外补贴的建立为代价”,⑨〔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31 页。官方的设计是乡官由官府选任,而非民选。但1908年则确定地方自治为基本国策,乡官之制不了了之。关于地方自治,大多数学者注意到了其以自治补官治不足的特点,但忽略了府厅州县和城镇乡两级自治的不同。①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法律出版社,2009;徐秀丽编《中国近代乡村自治法规选编》,中华书局,2004。而刘著对这两级自治的异同有精彩的分析,认为城镇乡自治为下级自治,“以自治辅官治之不足”,官治处于监督地位。而府厅州县是上级自治,“地位介于官府与下级自治之间,兼有官治与自治之性质”。②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第283 页。在机构设置上,城镇的议决机构是议事会,执行是董事会。乡的议决机构是议事会,执行机构是乡董。而在府厅州县一级,改董事会为参事会,参事会与议事会同为议决机关,执行机关为府厅州县长官。如宣统三年(1911)四川南部县的规定为“南部县知县须先将议案提交参事会,由参事会审核后再提交议事会”,③《南部档案》,宣统三年八月十四日,22-843-1。由州县官负责执行,州县则设置自治员辅佐知县执行自治事宜,这样在府厅州县一级,议事会的权限大大缩小。刘教授认为,这种两级自治制度主要模仿日本,同时受中国古代乡绅之治及中国自身情况的影响。日本的行政体制为内务省—府县—郡—町村,通过府县、町村自治而强化中央集权。而中国城镇乡的自治权力比日本町村大,自治与官治的结合点在府厅州县一级。
关于地方自治的影响,刘著认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由州县官—胥吏—保甲转变为官治与自治共存。王先明教授认为传统社会士绅的影响不可小觑,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影响或支配没有获得制度支持,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及新政的地方自治制度使“绅士”经历了“绅权体制化”和“士绅权绅化”的演变,传统社会官、绅、民三者之间的平衡逐渐被打破。④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1901—1949)》(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刘著大体采用了这一观点,但有一些不同,她认为不是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有助于绅士权力的扩张,在乡村巡警建立方面,从制度构建看,巡警是国家权力的工具,士绅在其中只能充当巡董、区正,权力十分有限。随着保甲、团练等逐渐萎缩,警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社会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体系。由于制度规定与实际运行有差异,关于二者权力的演进还需进一步的实例论证。在自治制度的设计上,没有赋予自治团体独立的法人地位,官府常插手地方自治,士绅与官府矛盾日益显现。加之绅治无法转换为现代地方自治,一些地方士绅借制度权力来压榨百姓,将绅士推向了民众的对立面。
四 对清末州县改制成败的反思
关于清末新政的成败,关晓红认为清末仿行宪政若邯郸学步,官制改革如东施效颦,域外政制最终淮橘为枳,非但没能由内外相维转向上下有序,反而导致轻重失衡,统治秩序严重失范。在基础薄弱、财政匮乏之际,新政兴学、警政、实业一拥而上,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致使清政府速亡。①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第378、385 页。吴春梅认为立宪的诸多措施削弱了中央权力,立宪派盲目的政治热情及新政时期民众负担的增加使清政府走入绝境。②吴春梅:《预备立宪和清末政局演变》,《安徽史学》1996年第1 期。在地方官制方面,一些学者从革命史观出发,认为清政府改革缺乏诚意,因地方督抚的反对,实质性的变动很少。③高放等:《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第141 页;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393 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 卷,中华书局,2011,第453 页。另一些学者从现代化史观出发,认为其虽有不足之处,但促进了地方官制的近代化,以佐治官代替佐贰杂职分掌巡警、教育、农工商等事宜使地方行政机构区域合理化;设立高等、地方和初级审判厅,实行行政与审判相分离,为司法独立奠定基础;在府州县设立议事会、董事会为地方自治打下基础。④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高旺:《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由于清代州县体制的弊病,预备立宪时期州县改制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改变“一人政府”的状态,设佐治员分任事务,建立科层政府;第二,设地方、初级审判厅,分任州县官的审判事务;第三,建立府厅州县和城镇乡两级自治,补官治之不足;⑤刘伟:《清季州县改制与地方社会》,第468 页。第四,转变州县政府职能。刘著对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但仍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1.局所与州县行政
晚清州县由于“一人政府”,行政架构不健全,无法平内乱外患,局所在建制、用人、施政、财务等方面比较灵活,被大量采用,成为晚清州县行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咸同年间以军事和厘税局所居多,同光新政以洋务、军工类局所为主,清末新政时期巡警、商务、政务、实业、教育等局所层出不穷。①关晓红:《清末新政制度变革研究》,第272 页。局所也成为部分官员的升转之地,“现办速成科仕学馆人员,应俟三年卒业,由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覆考如格,择优褒奖,予以应升之阶,或给虚衔加级,或咨送京外各局所当差”。②《京师大学堂章程》,《大公报》1902年9月5日,第5 版。清末州县履行职能大多依靠局所,局所的设立与设佐治员以分任具体事务的要求暗合。就中国中央集权制度而言,一直存在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中央设有六部,州县设有对应的六房,但条块体系不明显。而晚清州县局所受地方长官和上级职能部门的双重管辖,条块体系有了新的发展。刘著有多处论述局所,对个别局所有精彩的分析,但没有就局所与州县行政进行专论。为避免碎片化,刘著对新政事务的推行进行了宏观考察,但如果从下往上看,州县官依靠地方主要士绅设局推行,尽管新政事务类型不断增加,还是同一波士绅在原有设局情况下的叠加与变形。《四川官报》记载的四川璧山县育婴局、恤剺局、三费局、保甲局、警察局、学务局都是由文生徐邦彦负责,③《布政使司批璧山县监生巫荣光等具控保甲局绅徐邦彦侵蚀公款一案文》,《四川官报》1910年第16 期。南部县的部分局所情况也类似。
清末至民国时期国家机构日益膨胀而无法深入乡村,民众负担日益沉重而国家税收并未大幅度增加,杜赞奇称之为内卷化,④〔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从省的控制看则有另一番景象。晚清州县局所多为官督绅办,州县官作为省府代理人也有自己的利益,存在浮收和隐瞒的现象。为深入州县,地方督抚在州县设立了由省直接控制的局所,如四川、广西等设立的经征局,将州县税契、酒捐、肉厘、油捐划归其征收。宁雅矿务局也是,其章程规定,“各分局由总办派员办理,各有专司,仍须不时派人周流稽查,即总办亦须时常驰往各局厂查阅考核”。⑤《四川宁雅矿务局开办章程》,《四川官报》1904年第1 期。这显示地方督抚通过局所整顿来加强对州县的管理,原有的局所也出现了变化。
清代州县佐贰杂职被割裂在行政管理之外,清末部分州县进行了房科改革,裁改房科进行分科治事,佐贰杂职也在裁割之列。与明代佐杂在县衙成为鸡肋不同,清代佐杂分防地方,①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成为次县级长官,治民理事。如四川南部县县丞驻防新镇坝(后改为新政镇)、巡检驻防富村驿(富驿镇),分管一定的民政、词讼事务。新制度受旧制度的影响,佐贰杂职在清末州县改制中也有一定的转变,刘著有零星的论述,缺乏对这方面的综合思考。在新成立的局所中,为加强官治,州县官会派佐杂担任职务,履行职能及监督。如“隆昌县于1905年成立劝工局,委绅充当局士,并委捕厅朱典史润镛兼任该局提调”。②《督宪批隆昌县陈劝工局经费支绌量加裁减不致废弛禀》,《四川官报》1909年第11 期。科举制废除后,地方教谕、训导已无重要事务。“南部县于1908年在儒学署内设立农务局,由知县担任局长,综理一切。移请训导王嘉桢兼充总董,襄理局务。1909年农务局裁撤,改设农务所,集绅投票,选定王训导嘉桢为会长。”③《南部档案》,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21-208-2;《督宪批南部县改立农务分会成立情形酌拟章程并筹办塘堰井眼章程文附原禀章程》,《四川官报》1909年第14 期。在这一过程中,佐杂的职能与地位也在转化。
2.城镇乡地方自治与乡镇的建立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矛盾,④周雪光:《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社会》2019年第2 期。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政令自中央出,而国家规模和行政架构向下的渗透有限。清代正式的设官止于县级,保甲长、乡约、乡地等属于役职,宗族、绅士等承担部分地方公益、教育等事务。部分州县设有乡,但仅是地名,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转型除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克思)、人的理性化(韦伯)、社会分工的发展(涂尔干)之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态的变化。⑤〔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中国近代县政构建致力于资源汲取与社会控制,由观念一体化转为组织一体化,乡镇的建立则是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形态变化的表现。
刘教授对清末两级自治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从今天往回看,自治的成效不多,却是乡镇建制的开端。魏光奇、丁海秀论述了清末至北洋时期的区乡行政,包括新政新生的区乡新政和由旧乡地演变的区乡行政。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区乡行政有常设机构,行政人员按法定程序任免,有法定的公共经费制度,承担地方社会各种现代性行政职能。①魏光奇、丁海秀:《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区乡行政制度考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 期。新政时期,为推行警政、教育、实业、自治等事务,各州县陆续建立了以前社会中未曾有过之区乡,如《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府厅州县应就所辖境内划分学区,每区设劝学员一人”。巡警则是在县城设总局,于四乡设分局。对新政时期的区乡刘著有论述,但对区乡行政并没有过多关注。关于城镇乡地方自治,刘著提供了另一种思路,由于州县法定经费不足,晚清局所同时负责具体事务及筹款。杨品优关注江西宾兴局,认为江西宾兴局一方面负责科举、学堂事宜,一方面经理县经费,很多宾兴局在民国改成了财政局。②杨品优:《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这一观察与笔者对清代南部县学田局的研究相似,南部县学田局也是负责学务和为新政筹款。③万海荞:《晚清四川的州县经费研究——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5 期。在未实行城镇乡自治时,这些局所面向州县区域筹款,清末将州县划分选区后,部分筹款收归各区,这些局所逐渐转化为行政管理机构。
尽管清末州县改制的方向符合县政近代化的转向,但清政府对州县改制的步骤没有明确的计划,内外官改制失序,机构改革、财税改革、司法改革、地方自治一拥而上,财政困难和人才缺乏成为两大制约。加之改革过程中官绅、官民、绅民矛盾激化,不仅导致清朝覆亡,还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乡村社会的持续震荡。刘著的讨论廓清了清末州县改制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相信学界关于州县体制近代转型、局所体制、基层行政机构及乡镇制会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