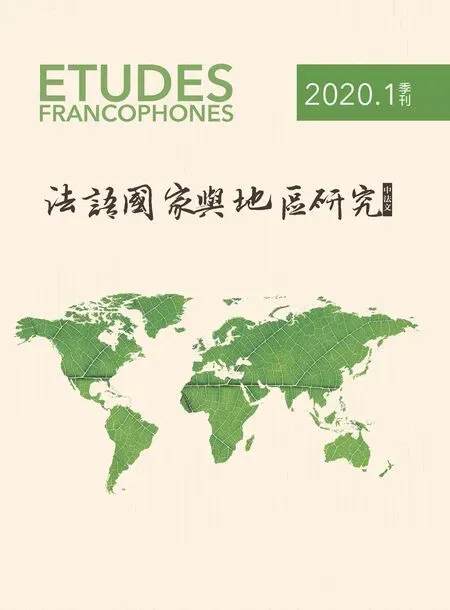中国古诗翻译策略研究
——法国诗人克洛德·罗阿的启示①
2020-04-07许玉婷
许玉婷
内容提要 作为当代法国著名诗人与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化爱好者与中国古诗翻译者,克洛德·罗阿的中国古诗翻译实践对我们了解中国古诗在当代法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翻译实践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值得关注。本文以罗阿三部著作《中国之钥》、《关于中国》和《盗诗者》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罗阿对汉语语言特性及其诗歌翻译的认识,总结罗阿的翻译策略,说明罗阿尝试通过翻译汲取中国古诗中的营养,丰富法语语言文学。
引 言
法国当代杰出诗人克洛德·罗阿(Claude Roy,1915-1997)生前作品三次入选伽利玛出版社诗歌丛书(Poésie/Gallimard)。拥有这份殊荣的法国作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阿拉贡(Louis Aragon)、雅克·卢波(Jacques Roubaud)、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等。诗人罗阿大器晚成,在后半生取得更大成就,这与他几十年里坚持翻译中国古诗、研究中国文化有着密切关系。1952年罗阿第一次访问中国,便与中国朋友罗大冈等人开始翻译中国古诗,于1967年出版了《中国诗歌宝库》(Trésor de la poésie chinoise),该书于1980年再版;1991年出版了《盗诗者:来自中国的250 首诗》(Voleur de poèmes : Chine, 250 poèmes dérobés du chinois),称得上是前者的增订本。笔者曾撰文探讨罗阿的中国诗歌翻译对其创作的影响②许玉婷.《论法国诗人罗阿的中国诗歌翻译》.跨文化对话:2015(33):124-134.,亦有其他学者指出“他欣然接受中国人的生活智慧,有意在创作中借鉴中国诗歌的广泛题材和简朴诗意的文风,拓宽了自己诗歌王国的领域”③车琳,钱林森.《主持人语》.跨文化对话,2015(33):68-69.。
罗阿认真研究汉语语言特性,大量阅读、对比中国古诗的英文、法文译本,琢磨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翻译策略,并运用到他的译诗集《盗诗者》中,从而对自己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法国当代著名诗人、文艺评论家、中国文化爱好者与中国古诗翻译者,罗阿的中国古诗翻译实践对我们理解中国古诗在当代法国的传播与接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值得关注。罗阿在《中国之钥》(Clefs pour la Chine, 1953)第十四章第二节专门讨论中国诗歌翻译;1976年6月7日及1977年9月1日,罗阿在法国大报《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两次撰文谈论法国的中国诗歌翻译,后来这两篇文章合二为一,发表在《关于中国》(Sur la Chine, 1979)上;1991年,罗阿在《盗诗者》长篇导论中再次论及中国古诗翻译。笔者主要根据以上三部分内容考察罗阿对汉语语言特性及其诗歌翻译的认识,总结罗阿的翻译策略。
一、中国古诗:不可译,但不可不译
要翻译中国古诗,首先要了解、掌握汉语这门语言。汉语对西方人的冲击首先来自语音。汉语不像大多数西方语言有语调(intonation),即感叹句语调下降,疑问句语调上升;汉语没有语调升降作为提示,西方人常常不知道一句话何时结束。④赵元任先生曾指出,汉语语调只影响句子最末的一个音节,与句子其他的任何部分都不相关。因而学者一般认为,汉语是声调语言,英语、法语等是语调语言。参见阮桂君.《跨文化交际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27 页;亦可见梁磊,石锋.《什么是语音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06 页。此外,汉语是单音节语言,总共四百多个音节,通过增添声调来弥补词汇量的不足,也给外国人带来很大的困扰。罗阿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中国人看到一个带着帽子的外国人,就说“mao zi”。外国人可能以为中国人是在说他们的帽子,其实中国人发的是第二声,即称外国人为“毛子”(Roy 1953:251)。罗阿欣赏的法国作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曾对此诟病有加:“人们越认为中国历史悠久,就越要指责其语言和文字不完美。我们难以想象,如此有才华有智慧的民族无节制地增加声调而不是增加词语的数量,增加汉字的数量而不是将它们结合起来构成新词。”⑤转引自Claude Roy.Clefs pour la Chine.Paris : Gallimard, 1953, 5e édition, p.257.罗阿初到中国,也觉得即使是日常对话,汉语会话也像“来自它处”(Roy 1953:250),让人如坠五里云雾中。不过他认为,西方人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站在中国历史、中国人的角度来了解汉语,否则对这门语言没有发言权。
西方人认为汉语语法没有规则,罗阿则认为西方人引以为傲的词形变化也毫无逻辑性可言。比如,同样是鸟,为什么bergeronnette(鹡鸰)是阴性的,要说une bergeronnette,而bouvreuil(灰雀)是阳性的,要说un bouvreuil,为什么hirondelle(燕子)不是阳性的,啄木鸟(pic-vert)不是阴性的?在汉语中,只需把男、女、雌、雄等字放在一个词语前面,即可标明其属性:雄燕、雌燕、男教师、女教师。罗阿认为,汉语语法如此简洁,“本身就是洞察力的表现”(Roy 1953:252);汉语动词无时态、省略人称代词的确会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然而这不是汉语的缺陷所在,而是反映了“中国人在宇宙面前的总体态度”⑥Claude Roy.« Introduction ».Le voleur de poèmes, Chine, 250 poèmes dérobés du chinois, Paris : Mercure de France, 1991, p.51.,即取消“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对立”(Roy 1979:108)。
罗阿注意到了汉语方块字字字独立、由字联句的特点,这也是方块字相对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优势所在。罗阿认为,西方语言遣词造句就像用钢筋水泥建造房屋一样冷冰冰、机械化,而汉语则像有机体、生命体的自然组合,更符合人的自然天性与内在需求。欧洲语言中,一个词语要根据众多规则改变词形,而汉语却将词语作为本自具足的存在摆在那里,必要的时候用介词、前置词等虚词来代替词形变化所承担的功能。罗阿认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造句子就像泥瓦匠砌墙,拿起一块砖砌上去,然后灌注水泥,而“中国人造句就像种树” (Roy 1953:252),呈现出人与自然的有机相处状态。
罗阿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使得汉语成为“中国东西南北之间最稳固的枢纽”,“保证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传承”,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亚洲的拉丁语”(Roy 1953:254-255)。汉字的表意特性决定了这门语言不仅诉诸人的听觉,还诉诸人的视觉,这也是西方语言所不具备的优点。罗阿举例说明如下:汉字“父”(père)展现一双手拿着斧头,表示力气大,受尊重;“好”(bon)则是一男一女和谐相处;“愁”(tristesse)是秋天的心情;“明”(brillant)则是日月齐耀……可见汉语方块字包含了天然的逻辑,词语就是思想本身。当然,思想通常先用形象具体的符号展现出来,之后将这些符号进一步简化、抽象化,因此并不是所有汉字都能像图画一样直接呈现其内涵。此外,大部分汉字由声旁和形旁构成,只要背记几百个声旁,就基本可以读出大多数汉字的发音;了解了几百个形旁,就基本知道大多数汉字的意思(Roy 1953:253-254)。因此汉语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难以接近。
汉字的独特构造还发展出独特的书法艺术。看到中国朋友表演书法艺术,握着细细的毛笔,直直悬垂在纸面上,不慌不忙写下一个又一个汉字,罗阿不禁感叹到:“中国诗人说出‘日升东’三个字⑦杜甫诗云:谁能凌绝顶,看取日升东。,同一个元素‘日’在三个汉字‘日’、‘昇’、‘東’中不断重复并有所变化,书写起来就像是视觉上的叠韵。与其说看你写字,不如说看你‘画’字。”(Roy 1953:257)他由此意识到,“中国书法不仅是时间艺术,也是空间艺术”(Roy 1953:256),这无疑加强了中国古诗的诗意,使其成为“空间上的动画”(Roy 1953:257),引人凝神注视。
在了解了汉语的语言特性之后,罗阿认为,要把中国古诗翻译成法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中国古诗翻译成法语诗歌,首先就是“把单音节语言转换成多音节语言,把有声调的语言转换成基本没有轻重音的语言,把表意文字(在这种语言中,每个单词包含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转换到表音文字”(Roy 1979:103),也就是把令人浮想联翩的方块字转换成枯燥无味的字母文字,把一棵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的绿树用做工粗糙的柱子取而代之。另外,在五言、七言四行诗、八行诗中,四个声调往返交替、抑扬顿挫所形成的韵律规则、音乐效果又如何用法语表达出来?(Roy 1953:260)总之,罗阿认为,把汉语翻译成法语,首先就是“最大的背叛”(Roy 1953:260-261)。尽管如此,罗阿认为,中国古诗虽然是不可翻译的(Roy 1953:253),却是必须翻译的,而且必须大量翻译,因为中国古诗是汉语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和载体,是流淌在中国人身上的血液,是浸润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灵魂,要了解中国人的精神,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最好的方式就是阅读、翻译中国诗歌”(Roy 1953:260)。
二、法译中国古诗一窥
罗阿非常遗憾地指出,英国读者非常幸福,阿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埃兹拉·庞德(Eza Pound, 1885-1972)、戴 维·霍 克 思(David Hawkes, 1923-2009)、葛 瑞 汉(A.C.Graham, 1919-1991)、布尔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等人提供了数量众多且质量上乘的中国古诗翻译佳作,而中国古诗法译本则屈指可数(Roy 1979:102)。罗阿接着评点了最具代表性的三个中国古诗法译本,分别来自著名的德理文侯爵(Le Marquis d’Hervey Saint Denys, 1823-1892)、汉学家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1934-)与华裔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程抱一。罗阿对德理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译本还原了中国古诗“简单中的丰富与丰富中的简单”(Roy 1979:104),基本覆盖了唐诗的所有主题,译文精确,历久弥新。美中不足的是,德理文的优雅文笔没能体现中国古诗质地紧密的特征,但是他避免用冗长的注释阻碍普通读者的阅读,也没有使用时人热衷的十四行诗体,从而使法国读者“误将公元200年曹操写的诗看成是保尔·德罗列德(Paul Déroulède,1846-1914)⑧法国诗人。的作品”(Roy 1979:104)。
1975年由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雅克·班巴诺与他的学生们翻译出版的《达摩流浪者:寒山诗25首》(Le Clodo du Dharma : 25 poèmes de Han-shan)也备受罗阿推崇,认为该译本是少有的能够让不懂中文的法国读者了解中国古诗真貌的译本。班巴诺的译作参考了著名的寒山诗英文译本,力求理解更加精准。班巴诺为每一首五言八行诗都配上中文版及其汉语拼音,在该诗中文版右边配上逐字翻译的法语单词,然后将这些单词联结起来组成句子,再调整这些句子使之组成一首完整的法语诗。就这样由字到句,再联句成诗,让法国读者了解汉语字字独立,联字成句的特点,也为读者留下足够的想象与再创造空间,让他们有机会接近、还原中国诗歌的原貌。1977年,程抱一出版了《中国诗语言研究》(L’Écriture poétique chinoise, 1977),罗阿惊喜地看到,程抱一“确实热爱中国诗歌并对中国诗歌有深刻的理解”(Roy 1979:108),他的翻译方法与班巴诺类似,对于每一首诗,“给出原文、逐字对译和意译”⑨[法]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5.,也即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所总结的:“首先将诗句逐字译出,然后把字联合成句,最后把句变为自由诗。”⑩许渊冲.《和程抱一谈诗歌翻译》.往事新编——许渊冲散文随笔精选.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82.
罗阿也指出法译中国古诗的几个常见缺陷。首先,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中国古诗通常省略人称代词,动词主体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他;汉语没有时态与动词变位,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总之,中国诗人拒绝封闭单一的阐释。反观法语,其语法精确,法国译者将中国古诗翻译成法语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在几种意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非得确定谁在湖畔、山中,谁听到大雁飞过的叫声,或者谁的手拂过琴弦发出声音,非得确定事情发生在很久以前、昨天,还是今天……罗阿认为,如此翻译背叛了汉语的精神,背叛了中国古诗的灵魂,未能揭示中国古诗的丰富内涵。其次,将中国古诗翻译成自由体诗还是翻译成格律诗,采用现成的诗意词汇还是使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做出选择。罗阿不赞同用冗长的注释代替翻译,用肆意发挥篡改原诗,也不赞同借用法国诗歌的格律(如十四行诗)与词汇来翻译中国诗歌,认为这种做法会严重扭曲中国诗歌的原貌。比如,在某些译者笔下,中国五言、七言古诗被翻译成亚历山大体,水一律被翻译成onde(水波),女人的脸是minois(小脸),播种的节日是ébats printaniers(春日的嬉戏)……如此一来,中国汉朝或者唐朝的古诗在翻译成法语后就成了法国牧歌,让人误以为是法国18、19世纪抒情诗人的作品,中国古诗由此“丢失了内在精神,只剩一具空壳”(Roy 1979:105)。
综上,在对各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之后,罗阿秉持如下翻译理念:一要传达中国古诗的内在精神,即简单中的丰富与丰富中的简单,二要准确理解、再现中国诗歌的主题,三要还原中国古诗紧密简洁的文风,与法国诗歌相区别。为了实践以上翻译理念,罗阿又采取了何种翻译策略呢?
三、罗阿的翻译策略
为了呈现汉法迻译的步骤,罗阿以汉武帝刘彻的《落叶哀蝉曲》为例: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⑪杨端志编.《中国诗词精典》.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371.罗阿之所以选择这首诗,不仅因为这首诗多次被名家翻译成英、法文,而且因为这首诗几乎没有使用典故,其意义及情感比较容易把握,便于罗阿从语音、语法、词汇等层面比较各种译本。罗阿首先列出《落叶哀蝉曲》的汉语拼音及其在法语中的发音,呈现原诗的音韵特点,然后对该诗逐字翻译,即一个汉语音节(一个汉字)翻译成一个法语单词,展现原诗的句法与意义结构。比如,对第一个句子“罗袂兮无声”,罗阿提供了以下三种版本:

?
逐字翻译之后,如何联字成句呢?罗阿接着参考该诗的四个英文译本,分别指出各个译本的特点:1900年左右翟里斯(Giles)使用押韵八音节体翻译这首诗;1908年庞德翻译该诗,摒弃押韵,作了令人佩服的自由改写;韦利的译本行文紧凑、语言简朴;洛威尔(Amy Lowell)行文松散,与其说是 翻译,不如说是解说、阐述。这四个译本基本上都是将一个汉语诗句翻译成一个法语诗行。在翻译原诗末两句“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的时候,四个译本呈现了最大的差异,也最能体现他们各自的特点。笔者分别将他们的译文翻译如下。
翟里斯:我的爱人已经去世。/独留我活在痛苦里。
庞德:她,我的快乐之源,就安眠在地下/一片潮湿的叶子贴在门槛上。
韦利:渴望见到那可爱的美人/一颗疼痛的心如何得安宁?
洛威尔:我渴望见到最美丽的那个她,这欲望如何满足?/痛苦撕碎了我的心,再无安宁可言。
韦利和庞德一样,认为比起格律诗,自由诗能够更好地传达中国古诗的神韵,他们“用自由诗译中国诗,使得许多不懂中文的读者,惊叹中国诗的‘现代性’”⑫赵毅衡.《韦利,书呆子艺术家》.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记.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90.。庞德的翻译舍弃了原诗抒情性结尾,凭空添加了“潮湿的叶子”一句,使其译诗以意象呈现为主,诗境更为含蓄,可谓神来之笔。罗阿对庞德的译文赞叹无比,不过他最推崇的诗歌译者还是韦利,大概是因为韦利的译文“既是现代式的自由诗,却又是能成为译作标尺的名作”⑬同上。,“为把中国诗影响传到现代英语文学中做出最大最持久的贡献”⑭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184.。韦利的译诗虽然“没有任何节奏的痕迹,除了读起来很顺口的散文那种节奏”⑮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213.,其实大有讲究。韦利在他的《中国诗一百七十首》序言中说,他大致遵循的节奏形式是一个重读对应一个汉字,并且模仿中国五言、七言诗在行中有一大停;重音加上大停,如此一来,韦利译诗“每三行中约有二行节奏与中国诗行的节奏相似”⑯同上,第210 页。。此外,韦利的重音节奏与现行口语接近,“其重音正好落在我们自己说话时自然会放的位置上”⑰赵毅衡,前揭书,第212 页。。罗阿显然非常赞同韦利翻译中国诗歌时抛开传统的音步格律,采用自由诗体,使用通俗语言的做法。罗阿自己在翻译中国古诗的时候,选择追随韦利的翻译原则,用有一定节奏的自由诗来翻译中国古诗。
当然,韦利是英国人,罗阿是法国人,而英语和法语具有不同的节奏模式。英语是典型的重音节奏语言,即“英语中重音的出现是周期性的”⑱曹剑芬.《现代语音研究与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37.,而“法语的重音一般落在单词或词组的最后一个音节上”,且“法语中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差别并不是很大”⑲束嘉晨.《魅力法语入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2.,因此法语的节奏并不体现于重音。罗阿译诗的时候,可以和韦利一样模仿中国古诗行中一大停,但是不能采取韦利的重音节奏模式,而应该采取法语独有的节奏模式。法语的音节是等长的,是典型的音节节奏,在这点上,汉语和法语比较接近⑳曹剑芬,前揭书,第327 页。。体现在诗歌节奏上,法语诗歌数音节:八音节、十音节、十二音节等等,汉语诗歌讲言:四言、五言、七言等等。这样的共同点似乎为法汉诗歌互译提供了便利。但是汉语的“言”与法语的“音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一个汉字翻译成一个法语音节恐怕很难实现,因为汉语一言(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而法语中除了少数单音节词,大多是多音节词。著名法语诗歌中译者程增厚在寻求汉语“言”与法语“音节”之间的对等关系上做过有益的探索。比如,他发现了能够翻译所有法语古典诗的模式:1=1-3,就是说,“法语诗歌译成汉语,每句诗的字数可以等于原诗的音节数,也可以比原诗多一个字或两个字,当然,每首诗只能用一种模式,贯彻到底”㉑李治华著,蒋力编.《程增厚〈法语诗汉译的模式研究〉序》.里昂译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72-273.。那么,反过来,汉语诗翻译成法语,如何寻求汉语“言”与法语“音节”之间的对称呢?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é d’Hormon,1881-1965)于1939-1945年领导由中法译者组成的翻译团队翻译中国古诗,其中包括《落叶哀蝉曲》。罗阿亦抄录了铎尔孟的译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铎尔孟的尝试。现转抄该译文如下㉒转引自Claude Roy.« Introduction ».Le Voleur de poèmes, Chine, 250 poèmes dérobés du chinois.Paris : Mercure de France, 1991, p.43.:
Ses manches de gaze
Ont cessé de bruire.
Aux dalles de jade
A crû la poussière.
Froide et silencieuse
Est la chambre déserte.
Au vantail clos
Les feuilles mortes s’amoncellent.
Mes yeux cherchent encore
Celle qui fut si belle !
Peut-elle, à présent, s’émouvoir
Du deuil de mon âme inquiète ?
原诗一共包含六个诗行,每个诗行的汉字数量分别为5、5、6、6、6、7。由于原诗每个诗行基本包含一个停顿,特别是前两个诗句更明显,以“兮”顿开,铎尔孟的译本据此将每个诗行翻译成两个法语诗行,如是译诗一共包含十二个诗行,除了最后两行,每个诗行基本包括5 个音节。译诗的短音步虽然还原了原诗简洁的风格,但是奇数音节带来飘浮、跳动的节奏感,很容易令法国读者想起魏尔伦(Paul Verlaine)的诗歌㉓魏尔伦在《诗艺》中特别指出,“要巧用奇数音节”,“多用单音节词句”,因为“偶音节诗句给人稳定感”,“单音节诗句则有一种飘浮、跳动的特点”。参见董学文主编.《西方文学理论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194.。另一方面,铎尔孟团队译诗倾向于使用诗意词汇,这也是罗阿所不能认同的。比如“门”不是翻译成平常的单词porte,而是翻译成诗歌用语vantail,用aquilon 而不是vent 翻译“风”,onde(水波)必定用argentée 来修饰……如此翻译下来,中国古代皇帝所作的乐府诗变成了魏尔伦式的法语诗歌,带上了“世纪末的惆怅之感”㉔Claude Roy.« Introduction ».Le voleur de poèmes, Chine, 250 poèmes dérobés du chinois.Paris : Mercure de France, 1991, p.42-43.。
罗阿在与罗大冈合作翻译的时候,意识到原文简朴的文风和紧凑的节奏一样重要,因此他“宁愿选择平淡,也不愿意过分诗化”㉕Ibid.p.43.,他将音节增加到六个,并且运用通俗语言、自由诗体来翻译。译文如下㉖Ibid.p.44.:
Le froissement s’est tu
de ses manches de soie
La poussière ternit
La cour dallée de jade.
La chambre vide est froide
Silence.Vide.Solitude.
Sur le pas de la porte
Tombent les feuilles mortes.
Celle qui n’est plus là
Comment la retrouver ?
ô cœur rempli de larmes !
和韦利、铎尔孟一样,罗阿根据原诗的停顿、节奏,除了最末一句,基本将一个汉语诗句翻译成两个法语诗行,不过罗阿采用六音节体,节奏更加平稳、朴实,语言更加通俗、直白,更加贴合原诗的节奏与风格。此外,为了再现原文的简洁与汉语的特点,罗阿倾向于使用名词独立句。对于“虚房冷而寂寞”,罗阿显然将“寂寞”(jimo)看作是该句乃至该诗的关键字眼,在逐字翻译的版本中,连续以silence、immobile、seul 三个法语单词来解释说明这个汉语词组的意义,在意译版本中用并列的三个不带冠词的名词silence、vide、solitude 来翻译该句后半句,突出了整首诗的情调与意境;而铎尔孟则用形容词froid 和silencieux 分别翻译“冷”和“寂寞”,相比之下,法语中名词显然比形容词更有力度与厚度。
原诗末两句是抒情性的疑问句“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安?”,罗阿翻译成:
Celle qui n’est plus là/Comment la retrouver ?(以下另起一诗节)ô cœur rempli de larmes !
红颜已逝/如何再得?(以下另起一诗节)心中满是泪水!
这个句子的翻译与铎尔孟相差太多。其实这样的译文源自罗阿对原诗的不同断句。从罗阿对原诗的逐字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罗阿将停顿放在“安得”后面,并将“安得”翻译为“如何得到,怎么得到”:“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安?”。中国古诗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的,罗阿如此断句,挖掘了该诗句的另一重内涵。人们通常在“感余心之未安”后面加一个问号,罗阿则翻译成名词型感叹句:ô cœur rempli de larmes !而且这个句子自成一个诗节,简短而有冲击力,类似法语诗歌末尾的chute(精彩结尾)。
此外,如上所述,罗阿注意到,中国古诗经常省略代词,汉语动词没有变位,罗阿认为这不是汉语的缺陷,而是中国人独特宇宙观的反映,意在主客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为了还原汉语的这种精神,罗阿直接使用了动词原形,省略了主语人称代词,比如该诗“望彼美之女兮安得”翻译成Celle qui n’est plus là/comment la retrouver?如果说用疑问词直接加动词原形在法语中算是常见结构,那么《盗诗者》中没有疑问词而直接以动词原形组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在翻译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前两句“晨策寻绝壁,夕息在山栖”时,罗阿基本使用动词原形:Au matin, grimper, escalader les falaises à pic./le soir se reposer dans un abri de montagne㉗Claude Roy.Le voleur de poèmes, Chine, 250 poèmes dérobés du chinois.Paris : Mercure de France, 1991, p.137..罗阿翻译王维的时候,更是大量使用动词原形。通过翻译中国古诗,罗阿将汉语的简约引入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创造了被称为“电报体”㉘Siyan Jin, Annie Curien.Littérature chinoise : le passé et l’écrivain contemporain, regards croisés d’écrivains de sinologues.Nantes :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01, p.114.的文体。在《资料/医院》(Documentaire / Hôpital)中,罗阿描绘了他的生活状态,多次使用动词原形组句,比如Ne plus pouvoir dormir,Bouger le moins possible㉙Claude Roy.A la lisière du temps/Le voyage d’automne.Paris : Gallimard, 1990, p.160-161.,好像说明书一样简洁明了。《雨》(Pluie)这首诗第二诗节省略人称代词,直接以动词原形组句,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Renverser le visage laisser la pluie ruisseler
sur le front les joues boire les gouttes d’eau
fermer les yeux et ne plus rien désirer d’autre㉚Ibid.p.111.
结 语
综上,罗阿在研究汉语语言特性、分析比较中国古诗英法文译本之后,明确了比较容易操作的翻译策略,并运用于他的诗歌翻译实践,进一步影响其诗歌创作。其翻译策略概括如下:使用简约、朴素的语言,模仿原诗节奏与韵律,以有节奏的自由体诗来翻译中国古诗;模仿中国古诗行中间的大停顿,必要时将一句中国古诗翻译成两行法语诗歌;根据中法两种语言的节奏特征,将中国古诗的“言”与法语诗歌的“音节”相对应;组句时大量使用名词、动词原形,还原汉语语言特色;必要时,根据法语语言与诗歌特点,对原诗结构进行调整。罗阿有意通过翻译汲取中国古诗的异质营养,从而为自己的创作提供灵感㉛见许玉婷.《论法国诗人罗阿的中国诗歌翻译》.跨文化对话,2015(02):129.,大大丰富了法语语言文学。罗阿这一做法与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不谋而合,后者以法译中国古诗为例,认为“只有改变自己语言的格律,才能听到‘异’的声音,同时通过对‘异’的接受,在法国语言文化中创造新的格律,如此循环反复,使原作在译语中再生,也使译语不断丰富自身”㉜转引自曹丹红.《两种翻译诗学观之比较及其启示》.外语研究,2007(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