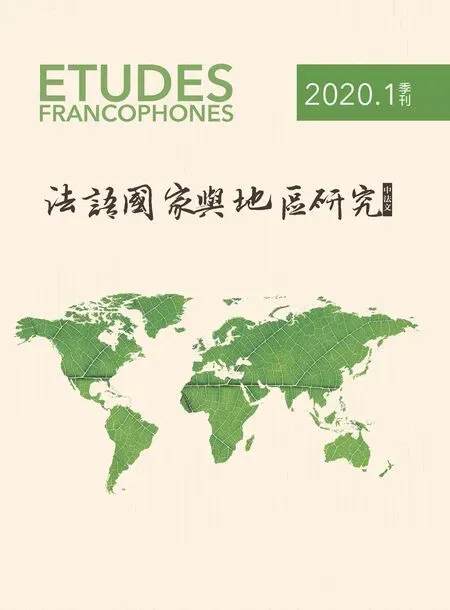从《平山冷燕》法译本看译者儒莲的多重身份
2020-02-25吕如羽
吕如羽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早期重要译作之一,《平山冷燕》法译本展现了法国汉学家儒莲作为译者的复杂角色。《平山冷燕》既为儒莲提供了教授汉语语言文学的途径,又成为了其传播和塑造东方形象的一个平台。本文从译本出发,结合译者的翻译理论及其翻译实践,探讨文本所体现的译者的多重身份。
引 言
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汉学界代表人物。他曾师从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学习汉语和满语,并接替雷慕沙担任法兰西公学汉语与满蒙语教席。尽管儒莲一生未到过中国,但“在其国中译习我邦之语言文字将四十年,于经史子集靡不穷搜遍览,讨流溯源”①王韬,海青编.《法国儒莲传》.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王韬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2.,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有着广泛而精深的了解。儒莲一生译著颇丰,且涉猎范围甚广,译有哲学经典《孟子》(Meng Tseu, 1828)、《道德经》(Le Livre de la voie et de la vertu, 1842),小说《平山冷燕》(P’ing-chan-ling-yen, ou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 1860)、《玉娇梨》(Y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1864)、戏曲《灰阑记》(Hoei-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1832)和《赵氏孤儿》(Tchao-chikou-eul, ou l’Orphelin de la Chine, 1834)等,并译有《大唐西域记》(Voyages des pèlerins bouddhistes, I, 1853, II, 1857-1858)等重要佛教典籍作品。同时,儒莲著有《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1869-1870)等汉语语言学专著。
《平山冷燕》是儒莲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译作之一。这部小说创作于清朝初期,全书共二十回,塑造了山黛和冷绛雪两位才貌出众的女子及燕白颔和平如衡两位才华横溢的男子的形象。小说中,平、山、冷、燕四位才子才女以才扬名、因才相慕,虽有小人拨乱,但终结良缘,双双成亲。1860年,《平山冷燕》经儒莲翻译,以P’ing-chan-ling-yen, ou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②Stanislas Julien.(trad.) P’ing-chan-ling-yen, ou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 tome I, II.Paris : Librairie académique Didier et Co, Libraires-Éditeurs, 1860.引文的中文翻译均出自笔者。之名于巴黎出版。
《平山冷燕》法译本诞生于19世纪中期。此时,一方面,东西方之间尚处于相对陌生的状态;另一方面,多种形态的交流甚至冲突亦已拉开帷幕。儒莲的翻译既为汉学家的个人行为,又因特殊的历史语境秉持了复杂的立场,具有影响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将从《平山冷燕》法译本及译者序言出发,解读在这一场中法语言、文学和文化的碰撞中译者身份的丰富体现。
一、以译文再现原文:作为教学者的译者
在《平山冷燕》的序言中,儒莲对自己的翻译计划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一开篇,他就宣称,翻译《平山冷燕》的目标之一是“向希望阅读小说原文的读者指点它的文体风格”(Julien 1860 : I)。在儒莲看来,这是一种“最高雅、最杰出,同时也是最困难” (Julien 1860 : I)的风格。如果说,翻译或让作者靠近读者,或让读者靠近作者,那么显然,具有汉学家和译者双重身份的儒莲在此已表明,他选择的是以教学者的态度,让欧洲读者透过译文窥见原文的样貌。
在如此目的之下,忠实再现原文的文体风貌成为了译者最重要的考量之一,亦是翻译的难点所在。在《平山冷燕》中,主人公竞相吟诗作赋,引经据典。正如儒莲所言,在行文中,小说通俗的文字会升华为高雅的风格,随之而来的是“大胆的隐喻、诗化的表达、仅凭一词指涉的掌故、一语双关的表达” (Julien 1860 : IX-X)。这种具有多义性的语言形式既是儒莲希望向读者如实再现的精髓,也是其翻译时面临的一大挑战。面对如此“高雅而艰深的文字”,儒莲提出,自己的注释“可以提供一把钥匙” (Julien 1860 : XVII),尽可能地使读者接近原文。《平山冷燕》译本中共出现了670 处注释,对于一部二十回的中长篇小说而言,这样的篇幅占比不可谓不高。通过注释与正文配合的方式,译者致力于全面再现文中出现的大量典故和双关用语。
为了行文的顺畅,儒莲时常在正文中采取意译的方式,而在注释中保留原文中的字面形式,从而调和“法语规范与忠实翻译” (Julien 1860 : XVII)之间的矛盾。例如,在第一回中,作者描述先朝盛况,提到“三十六条花柳巷”(1983:4)。儒莲在译文中将其意译为“寻欢之处”,而在注释中备注原文:“汉语:花和柳的街巷,指称妓女住所。” (Julien 1860 : 2)又如,第五回中,宋信感谢山黛宽洪大量,不计前嫌,对其父山显仁道希望至小姐楼下一拜,“以表犬马感激之心”(1983 : 57),译者将其意译为“来生愿为她效劳,以表感激”。但在脚注中,儒莲解释道:“字面含义:以犬或马的方式向其展示我的感激,即向其保证我希望在来生变成一条狗或一匹马,为其效劳,以表感激之情。”(Julien 1860 : 153)
甚至,对于一些汉语中约定俗成的用语,儒莲也对其字面本义进行了考据和解释。宋信每每被山黛激怒,斥之为“小丫头”,在译文中,儒莲先将其意译,又在脚注中备注“丫头”的字面含义“分叉的头”,并解释其由来为婢女发型。(Julien 1860 : 24)显然,原文中的意译完全不影响读者对故事情节的把握,并且能让行文更加明晓通顺。而注释中所标注的文字原义事实上也与文中内涵相去甚远,甚至可能对读者的理解造成一定干扰。但儒莲仍然不厌其烦地备注了原文的字面形式或原义,从而让读者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中文的语言结构及此结构所代表的意指方式。
儒莲的注释不止于对字面形式的展示,有时更包括了对字音的标注。例如,在翻译“垂青刮目”时,儒莲在正文中将此短语意译,又在注释中解释了“垂青”与“刮目”的字面含义:
垂青:垂下黑色(tch’ouï - tsing),即屈尊以黑色的瞳孔直视他。
刮目:擦拭眼睛(koua - mo)以便将他看得更清楚。此短语指对某人表示欢迎,示以尊敬。(Julien 1860 : 23)
此处,字音的标注对于词义的理解并无帮助,但儒莲仍将其注明。于是,读者不仅能够通过注释,了解原文的隐喻方式,还能同时习得汉语的读音。在此过程中,文字似乎已不再单纯只是情节的一部分,而是脱离语境,以独立的形式呈现在了译本之中。
儒莲对于汉语文字形式的展现方式是多样的。对于一些中国文化中的专有名词,儒莲往往在正文中保留字面形式,而在注释里对其所指进行具体解释。例如开篇第一回,钦天监正堂官向皇上报秉“紫微”星象,译者在正文中将其音译为“Tse - weï”,而在注释中解释:“紫微为星座之名,中国的天文官员认为紫微星代表皇帝之位、天子之所。”(Julien 1860 : 4)又如,在翻译“为麟为凤”时,儒莲注解道:“麒麟(Khi - lîn),为兽中之王,凤凰(Fong - hoang),鸟中之王,在中国人看来,两者为预示有德行的君主到来的奇幻动物。在这一段中,它们象征着有非凡才能之人。”(Julien 1860 : 5)
显然,在儒莲看来,无论是否在现实中存在,这些事物不再是普遍意义上的“物”,而是与中国的文化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与其“名”合为一体的特有存在。保留中文中的称谓方式,即是承认了其“名”与“物”之间的相辅相成;而在注释中对其进行注解,则是让这种相互关系完整地进入了法语译文之中。
可以看出,对于儒莲来说,对情节内容的呈现固然重要,但小说所承载的中国语言文字更是他所希望传达的重点。“为什么一门表面看来如此不完美的语言,能够响应思想的所有需求,得以让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作者在无数作品中处理人类思想所产生的所有科学或文学的主题呢?”③Stanislas Julien.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tome I.Paris : 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1869 : 2.为了解答这一问题,儒莲以各种形式对汉语文字进行了挖掘和展现。在其所编的汉语教材《汉文指南》里,儒莲即以《赵氏孤儿》等中国文学作品为例进行教学,在每一段文字后附以汉字拼音与逐字释义。比较儒莲的小说译文与其所编汉语教材,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呈现方式十分相像。而儒莲在序言中也已宣称,《平山冷燕》最高程度地体现了汉语中“对欧洲学生来说最微妙、最考究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因此成为了他在“巴黎皇家图书馆珍藏的上千部小说”(Julien 1860 : 8)中选择的翻译对象。从这一角度而言,儒莲在选择《平山冷燕》进行翻译之时,更侧重于以汉语教学的方式呈现原文。
中文文本以特殊的形式指涉内涵,而这种形式本身亦参与了内涵的构建。对于儒莲而言,在“如谜一般”的译出语中,“谜底”与“谜面”、读音与意义、外延与内涵同样重要。而唯有把握住文字的字面与其内涵意义之间特有的指涉关系,才能将文本“原样生擒”。可以看到,在这个向原文靠近的过程中,儒莲的附注作为“外围文本”,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译文不可或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伴随着注释,儒莲将中文里原本不言自明的能指与所指分离开来,又将其联系完整铺展给法语读者,以形神具备的形式呈现原文的文字。于是,在强势的译出语面前,译文内容的流畅不再占据首要位置,而“译者的任务”也悄然转换为了教学者的使命。
二、以译文诠释原文:作为批评者的译者
面对晦涩多义的中文原文,译者儒莲并未陷入“一仆二主”的困境,而是借助注释与正文配合的方式,竭力再现原文的语言特色和文体风格。然而,在阅读译文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发现,自认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积累丰富背景知识的译者并非始终甘为忠“仆”。时常,儒莲是以更加清晰主动的面貌介入到了对文本的处理之中。
在小说第四回中,宋信恭维众位先生为“金马名卿,玉堂学士”(1983:37),定能在朝廷文试中挫败山黛。“金马玉堂”典故源自汉代,“金马”指汉武帝在未央宫前建造的金马门,为学士待诏之地,“玉堂”则指玉堂殿,为待诏学士议事之地,此典代指在朝廷任职,地位显贵。然而,有趣的是,在译文中,儒莲并未将其译为“金”色的马,而是翻译为“铜”马(Cheval de Bronze)(Julien 1860 : 96)。的确,如果我们细查史实,金马门虽称“金马”,但实际上是汉武帝获大宛马后所建铜像。在此处,译者并未顾及原文中短语的字面形式,而是直接根据他所获得的信息,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翻译。而在诗句“不知何处是虞唐”(1983:4)处,我们再次看到,译者儒莲没有直接音译“虞唐”,而是根据其出处“唐尧”和“禹舜”将其译为“尧舜”(Yao et Chun),并在脚注里解释尧舜为“中国黄金时代的远古帝皇”(Julien 1860 : 3)。诚然,相对于“虞唐”,“尧舜”是更为常见的称呼。但是,在面对不熟悉中文的欧洲读者之时,译者略过文本,在同一纵聚合中做出主观的选择,则未免有“越俎代庖”之嫌。此类例子还有许多。又如,每每当文中出现略称人名,儒莲皆将姓名补全。作者描述当时天下多才,“有王、唐、瞿、薛四大家之名(……)人人争岛瘦郊寒,个个矜白仙贺鬼。”(1983:6)在法语译文中,儒莲则将其中出现的文人姓名一一补足,直接呈现在了行文当中。或许,在儒莲看来,原文中不言而喻的文化背景在法语语境中成为了需要“翻译”的内容,译者应担起传播者和教授者的角色,对涉及到文学知识和文化背景的要素进行全面而“正确”的传达。在这样的改动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儒莲对自身的定位已不仅是译者的角色,而是越过字面能指,以平行于作者的身份直接对文本所指进行诠释和再表达。
在对字面形式进行主观处理的同时,译者亦会于脚注中对作者的写作本身进行直接的分析和批评。例如,第一回中,皇帝会百官于“芙蓉阙”下 ,儒莲即在脚注中写道:“这座宫殿在唐代极富盛名,但在本书作者生活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仅见于考古文献或学者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轻易看到作者对15、16世纪建造的宫殿命以古代著名建筑之名,以显示自己的才学渊博。另外,即使它们依然存在,也不可能是文中所谈到的宫殿,因为明朝的首都(北京)不再沿用汉代或唐代的建筑风格。”(Julien 1860 : 11)
事实上,尽管“芙蓉阙”常见于唐代诗歌,但“芙蓉阙”并非唐代宫殿。但无论史实如何,儒莲在此处已超越了单纯的译者角色,他的分析并非针对小说情节,而是面向了作者的创作意图。类似地,当小说描绘当时天子有道,国泰民安,“长安城中,九门百逵,六街三市”(1983:4),在注释中,儒莲说道:“出于对渊博学识的极度热爱,作者以中国汉唐时期的首都“长安”之名代替文中所写时期的首都名称“北京”,并提及这座城市繁华时期街道、市场的数目,仿佛书中的事件的确发生在那里一样。”(Julien 1860 : 2)
小说力求制造逼真的幻觉,而才子佳人小说更是致力于营造一个繁华而诗意的理想世界,但译者儒莲屡屡对此进行“祛魅”,企图揭示或破解背后作者的存在及其创作的用意。从这一角度来说,他并未与原文“共谋”,使“读者接近作者”,而是以汉学家的身份抽离于文本之外,对其进行文学批评。
甚至,当译者认为文中引用典故错误之时,他亦会在注释中向读者指出。例如,皇帝赞誉山黛之才时提到,“昔唐婉儿梦神人赐一秤,以称天下之才”(1983:21)。儒莲即备注:“这一引用并不准确。梦见神人的并非婉儿,而是她的母亲。神人对她说,‘你的女儿将会持此称量天下士。’婉儿一个月时,其母戏问:‘汝能称量天下士么’,婴儿笑而应之。”(Julien 1860 : 57)
而在文中平如衡提到“李太白唐时一人,曾见崔颢 《黄鹤楼》诗而不敢再题”(1983:148)时,儒莲在注中宣称:“本书作者在这里犯了一个史实错误。崔颢并非唐人,而是生活于魏太武帝时代,公元424-451年间。”(Julien 1860 : 23-24)
显然,儒莲在此将唐朝诗人崔颢与北魏大臣崔浩张冠李戴了。译者的误读固然可以理解,但注释中透露出的译者态度则显示了其面对原文时所持的居高临下的“勘正者”立场。译者似乎不再只是译出语与译入语间的“中介”,而是置身于原作之上,参与到了文本的批评和校订过程之中。
译者对作品的介入不仅体现在这些细节之中,还在另一更为宏观也更加明显的方面展现:无论是在《玉娇梨》还是在《平山冷燕》中,儒莲的翻译都略去了回目的篇首部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往往有着固定的文体结构。在《平山冷燕》中,叙述者在每一回目开篇对本回情节进行梗概,并附以一首与内容密切相关的词。但在法语译本中,每一回皆直接以故事情节开篇,而不见之前的叙述者话语。我们无从确定译者用意,或许,对他来说,篇首词的文字雅俗杂糅,难以翻译和处理;又或许,译为法语的篇首词在文字上不再具有原本作为韵文与散文之间的区别性,容易落为本回目的简单预告,影响故事的可读性。然而,无论如何,当儒莲对原文进行如此直接且规律的处理,他已昭然宣称了其在翻译行为中作为批评者与二度创作者的自我定位。
自然,翻译与批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行为中必然包括对文本的理解和诠释。但从《平山冷燕》的法译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之于“译作杂糅”的儒莲而言,小说似乎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文本,而是可供译者拆解、分析和再处理的“资料”。尽管声称“忠实”,但在这场翻译过程中,译者并非一直臣服于作者,而是在翻译的同时以“僭越”的方式完成了对原作的文学批评。当我们再一次审视儒莲在序言中所言,他翻译《平山冷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向希望阅读小说原文的读者指点它的文体风格”,我们会发现,“指点”(désigner)二字已暗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强势态度。这位被描述为“躯干肥硕,精力充裕”,且“自少迄老,无一日释书不观”④王韬,前揭书,第152 页。的汉学家屡屡强调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精进研读,并毫不避讳地批评其师雷慕沙的翻译中存在的种种纰漏。显然,译者对自己的解读充满自信,甚至将其凌驾于对文本的忠实再现之上。而从另一角度而言,此种态度或许也与其所处的翻译视野密切相关。译者与原作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果将儒莲的翻译行为定位于19世纪中法交流过程之中,我们似乎能看到显隐于译者背后更加微妙而复杂的语境。
三、以译文塑造东方:一种来自西方的目光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到:“(……)《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⑤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20.的确,无论是从翻译数量还是受关注程度而言,中国古代世情小说都在法译白话小说中占了极大的比例,而才子佳人主题又是其中的一大重点。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中并不受特别瞩目的作品却在欧洲得到了热烈的欢迎。因此,我们或许不应将《平山冷燕》的法语翻译视作一个孤立行为,而应将其还原于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看作一项持续的文化现象之中的一个典型事件。
自16世纪传教士进入中国起,东西方的交流逐渐增多。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法国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更是渴望了解异域文化,建立百科知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描摹世俗生活的中国小说成为了他们了解东方的一面窗口。在《玉娇梨》序言中,雷慕沙解释说他把《玉娇梨》介绍到法国,是因为“它是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为了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中国的小说,尤其是描写民风世情的小说可谓是“必须参阅的最好回忆录”⑥Jean-Pierre Abel-Rémusat (trad.) Iu-Kiao-Li, ou Les deux cousines, tome I, II, III, IV.Paris : Librairie Moutardier, 1826 : 5.。而在儒莲看来,通过文学来理解中国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他在《平山冷燕》的序言中写道,中国人对于文学知识十分重视,文学造诣才能是在中国社会中获得升迁的关键依据,也是塑造中国人性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欧洲读者而言,阅读中国文学可以极大地帮助他们认识中国。一方面,法国读者可以借此了解到中国的文人所关心的题材和描写的视角,另一方面,借由小说的叙述,读者得以窥探到中国人家庭生活的真貌,以及渗透于日常之中的文学活动。在序言中,儒莲介绍了包括《平山冷燕》在内的“十大才子书”,并将其称为欧洲译者在选择翻译作品时的首选。由此我们亦可看出,在这一时期欧洲对中国小说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并非受制于人,而是秉承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对题材和作品做出主动的选择。
因此,当儒莲选择《平山冷燕》进行翻译时,他即赋予了这部小说于认识东方意义上的特殊价值。一方面,《平山冷燕》既为“才子书”,又“书才子”:小说不仅为才子所著,更描写了两对青年男女完全“基于对文才的欣赏而产生的感情”,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极为丰富地反映了中国的文人文化。在译名上,儒莲亦以“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eés”(两位年轻才女)之名突出了小说对主人公文才的强调。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动机和出发点之下,翻译过程中,儒莲也多次通过注释的方式向读者强调文学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尽力完整展示中国的文人文化。前文已提到,每每文中提到诗人墨客之名,儒莲即在文中以全名显示,又在注释中补足其信息。而在小说中提到与文人有关的典故或轶事之时,儒莲亦“见缝插针”地介绍相关信息。例如,当冷绛雪提及,“子建七步成诗,千秋佳话 ”(1983 :237),儒莲便在注释里介绍了曹植生平:
曹子建是一位生活于魏武帝时期(公元220-227年)的诗人。十岁时,他已能作赋。人们称之为“绣虎”,即优雅之虎(王)。一天,他写:“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⑦“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之语实为谢灵运所言。。皇帝嫉妒其才气,希望致其于死地,命其七步作诗。他因此即兴作了一首诗歌。(Julien 1860 : 181)
甚至,当小说中并未出现明确的典故指涉,只是描述文人“诗酒才名高于北斗”(1983:6)时,儒莲亦在脚注中进行补充介绍:“诗酒(Chi-thsieou),诗和酒是我们谈论诗人时两样不可分开的事物。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李太白,只有在酒兴之下才会做出优美的诗句。”(Julien 1860 : 8)
可以看出,与其说这些脚注中出现的背景知识有助于读者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如说能让受众更加了解中国文学及丰富的文人文化。在儒莲的串联和组织下,文中任何一个单独零散的元素都被纳入了一个广袤的文化体系之中,文本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浓缩了中国的文人文化及文学史的载体。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译介始终是出于某种偏好的选择结果。正如鲁迅先生所言,《玉娇梨》、《平山冷燕》在国外的有名程度远过于其在中国。诚然,才子佳人小说有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但其叙事的模式化与概念化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小说描写的失真”⑧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349.和对其艺术价值的限制。另外,儒莲在序言中提出的“十大才子书”的说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也不属主流。但是,通过儒莲及其他译者的译介,《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绘的君主开明、社会文雅、爱情自由的浪漫国度俨然被指认为了中国的象征,中国的文学及文人文化亦在不断重复的注释中被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塑造与固化了一个特殊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的符号化自然应被纳入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之中。在16世纪传教士不乏主观色彩的叙述中,中国即被描述为一个文明而繁荣的理想国度。而在启蒙运动中,这个中国神话更是成为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哲学家对抗教会和一切权威的武器。对于19世纪初的读者来说,“中国风”(Chinoiserie)的热潮仍未完全远去,才子佳人小说既是法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也加助构建了“套语化”的中国形象。尽管儒莲本人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仅来自藏于法国的海量中国典籍,但他选择了一个如此理想化的故事进行翻译,又在翻译过程中融入各种富有诗意的背景元素,并刻意以陌生的文字形式进行呈现,此时他便从读者转变为了创作者,同样参与了这场关于不可及的异国情调的塑造之中。
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建构他者的行为或许不仅只是为了营造“幻觉”。事实上,在儒莲翻译《平山冷燕》之时,鸦片战争已然打响,中国不再是一个与西方世界隔绝的神秘国度。在1864年出版的儒莲版《玉娇梨》译本序言中,译者写道:“自广阔的中国帝国彻底向欧洲人展开之时,年轻人缺少自学中国现代语言的文学途径,我为之感到震惊,因此于1860年出版了中国小说《平山冷燕》的法语译本,译本在法国和外国都受到了热烈欢迎。”⑨Stanislas Julien.(trad.) Yu-kiao-li, Les deux cousines.Paris : Librairie académique Didier et Co, Libraires-Éditeurs, 1864, p.XV.在《平山冷燕》序言中,儒莲也宣称,学习中文对于了解“今后将来往通商的人民的道德风俗和性格习惯”(Julien 1860 : IX)来说十分重要。在这一角度而言,小说的翻译和中文的教授就有了更加复杂的意义。一方面,译者与原作的交流亦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在注释中,儒莲时常将东西方文明进行对比。例如,对于小说中提到的年份,儒莲皆附上相应的公元纪年,在解释距离、价格等古代中国的衡量单位时,他则将其与法国单位进行换算。而另一方面,对异域之“异”的强调也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一个停滞于精致颓靡的诗酒生活、与西方工业文明相隔绝的国度。在19世纪的殖民语境中,文本的“发送者”成为了被注视的“他者”,而文本的“接受者”则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导者,为这场文化交流赋予了更深的意义。
结 语
“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⑩[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比较文学形象学.孟华(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123.在中法文化交流的萌芽时期,译本既是异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再现”,更代表了译者作为主体所参与的一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展现了“注视者”复杂的身份与相应的翻译立场。
作为法兰西公学的汉语教授,在翻译小说的过程中,儒莲以译本为载体,对原文中的汉语语言进行了全面的呈现,为希望了解中文的欧洲读者提供了绝佳的学习途径。而在翻译与教学的过程中,译者亦以批评者的面貌对文本进行了“指点”。同时,译文也是一面认识中国的窗户,参与了东方想象的构建。在译者及其所代表的整个话语生态的引导之下,文本意义在接受语的文化体系中悄然进行了价值的转换与重建。
处于中法交流的特殊时期,儒莲的翻译既诠释了两种文明在相互接触中所形成的丰富面向,又体现了时空所筑造的局限性。而如果我们将其翻译行为定位于一个动态延续的文化互动过程中,对于更广泛的接受者群体而言,译者儒莲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这种局限性的塑造,又在何种意义上展开了交流的可能性,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