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蒙拉: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
2020-04-05秦岭
秦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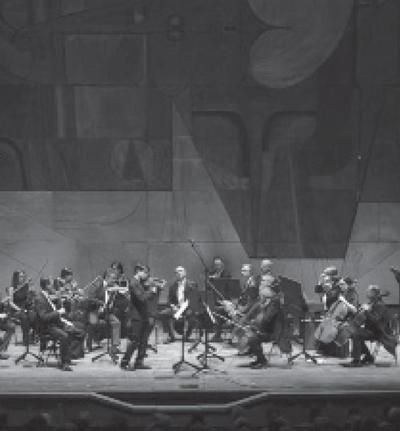
作为古典音乐爱好者,你绝对不会对黄蒙拉的名字感到陌生。
这位土生土长的“80后”上海演奏家,师承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2002年,22岁的他一举夺得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并同时获得“最佳帕格尼尼随想曲演奏奖”和“纪念马里奥·罗明内里奖”,成为继吕思清、黄滨之后,第三位获得此项赛事金奖的中国人。此后的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位“东方帕格尼尼”始终活跃于国际古典音乐舞台,用精湛的琴艺与世界对话。
“小提琴真的很难。真的,我现在都觉得他很难。小提琴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可怕的特点,就是要一直保持在‘演奏状态。我始终怀着敬畏的心情在练习和演奏小提琴。”黄蒙拉说,“经常有人问我,你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如果真的要说天赋,那一定是我太会不理睬旁边的声音。对于古典音乐或者小提琴来说,一輩子真的太短。浩如烟海的作品,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我觉得时间真是不够,不够去演奏、去学习、去感受。”
2020年,黄蒙拉正式步入了他的不惑之年。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时点。40岁,学琴36年,成名18载。现在的他会如何回顾并总结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音乐之路,如何看待并评价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变化与发展?日常生活中,他又有怎样的音乐趣味?我们与他进行了这样一番对话——
记者:从2002年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而崭露头角至今,近二十年时间过去,你觉得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黄蒙拉:我的眼睛慢慢打开了,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年轻的时候更容易感受到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偏技术性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概念性的东西,对于内心世界的理解,对于感情方面的东西,会越来越透彻,而这些东西也都体现在了我的音乐里。音乐就是阐述人的情绪,或者说得更高级一些,表现普遍的人性。当你对生活理解得更加深入、更加透彻,对于音乐的感悟也会更加贴近,更加真实。
还有一个转变。以前只是拼命地学,拼命地去吸收——不仅仅是音乐方面,因为小提琴毕竟是西方的艺术,在文化上也需要补足大量的东西,不仅仅是从音乐角度——但现在,在深入学习、充分了解之后,我反而觉得人性是相通的。演奏者其实是一个讲述者,传达的是作曲家的意图。虽然我是东方人,音乐作品是西方的,但在对文化作品的理解上,其实并没有多么巨大的“隔阂”。用我们的方式,也能够很好地去解释清楚一些事情。而我们也并不需要刻意加入所谓的“东方元素”,也不用刻意让自己变成“香蕉人”,非要像西方人那样去理解去表现。真正优秀的作品,其魅力不会局限在作者自身民族文化的范畴内。
记者:作为在国际乐坛非常活跃的音乐家,你如何看待中国古典音乐市场这些年来的发展?
黄蒙拉:获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之后,我就以踏上职业演奏舞台为目标,开始尝试做一些音乐会演出。然而当时国内的古典音乐市场并不成熟,而自小一路学琴,也从未想过今后该如何从象牙塔走向社会。那时的我痛苦地发现,一个职业的独奏音乐家,靠着一年至多十场的演出,根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没有需求,没有观众,也没有舞台。当时国内专业音乐厅并不多,我在很多“奇怪的地方”演出过——有时候,我下午在这家电影院里看电影,晚上就在同一个舞台上拉琴了。
这促使我选择了去国外留学,一方面是觉得确实需要再多学一些东西,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外有非常成熟的市场。我在国外呆了很长时间,期间音乐学习和演奏事业发展同步进行,等到2011年回国的时候,国内的音乐环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典音乐的市场环境整体都有了很好的提升。而且不只是北上广,北上广是领头羊,重要的是,二三线城市的音乐市场也都在发展,爱好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许多城市都建立起了自己的交响乐团,自己的专业音乐厅。有了好的硬件,就需要好的演出去填充。演奏家、音乐院团都带动起来了,音乐学院也随之更有起色,整个行业都在蓬勃地发展,这是个良性循环,整个市场就这样逐步盘活了。
我真心觉得自己是赶上了好时代。现在,我在国内的演出占了我总演出数的2/3,我甚至有点懒得跑国外了(笑)。而通过这些年在国外的学习经历与演出经验,我也非常切身地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是怎样影响着别人看待你的眼光,乃至与你合作的态度。作为中国人,能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记者:对于如今很多艺术家都在尝试的当代艺术“跨界”心动过吗?
黄蒙拉: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比较保守的。越是完美的东西,越是自成体系,它的封闭性就越强,如果硬要和其他东西嫁接的话,我觉得不伦不类。比起“跨界”,我可能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古典音乐本身。当然,这个市场确实要求艺术家去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跨界”。市场对于我们独奏家的要求,是你既要技艺精湛,又要全面,但你一旦追求全面,在一些特别需要专精的地方,就势必没有办法达到那些把所有精力放在那些东西上的人同样的高度。这是一个矛盾。
其实我有时也在反思我的观点,是不是艺术就必须那么“纯粹”,是不是和流量产生关系的艺术就不能说是艺术呢?我觉得也不一定,我们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任何“经典”艺术都曾经是“当代”艺术,很多“严肃”艺术家也都曾是那个时代的“流量”。西贝柳斯的音乐现在看起来很古典,但在当时,却属于某种意义上的“离经叛道”。《火鸟》和《春之祭》上演的时候被骂成什么样子?但现在看来,这是多好的音乐多伟大的创作啊。当时不被接受是因为过去人们的艺术欣赏水平不够吗?并不是。只是在之后的这五十年里,在不断地检验中,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东西而已。
记者:但是对于普通听众来说,当代作品似乎有点太难了。
黄蒙拉:我学生时代就曾经和作曲系的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永远重复贝多芬、莫扎特。但是打破一些东西容易,树立起来很难。当代音乐创作在打破了古典音乐的一些结构和原则之后,似乎很难再产生一种台上与台下的强烈共鸣。每一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熟悉的东西变少了,所以观众有时会觉得听不懂。
记者:那么作为演奏家呢?你满足于反复演奏古典作品吗?
黄蒙拉:我满足的(笑)。这样说吧,从古典主义到浪漫派再到当代作品,乐曲风格对演奏者的约束越来越少。而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是什么呢?比如曲谱上写着,这个音比那个音高四分之一音。这四分之一音落在小提琴上,就是手指的一个非常细微的移动。我们已经练到在手指快速的运行中,像这样的每一个音都能弄准。越是古早的作品,这方面的要求就越高。对演奏者来说,这种对乐曲风格的精准“刻画”是可以不断地去追求的。这可能就是作为演绎者的我们与作为创作者的作曲家不一样的地方(笑)。
记者:你平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作品?
黄蒙拉:如果撇开小提琴不谈,我现在比较喜欢舒曼的、肖邦的作品。当然也看个人的心情。早上醒来,听莫扎特的作品或者维瓦尔第的作品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心情不好的时候听舒曼的作品会特别有触动。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我会比较容易听到耳朵里,因为这些旋律比较顺耳,有时听腻了也会换到当代作品。
小提琴家里,海菲兹是我的偶像。那个高度!那个高度!那个高度真的可怕(逐渐小声)。我真的很崇拜二战前后那一批犹太音乐家,他们深刻体验过生活的冷暖,是真的用生命在演奏,他们的音乐简直无可挑剔。
日常听音乐,我的要求也很高,不好的版本我宁可不听。比如我喜欢某一部作品。我就会广泛搜罗,听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奏版本,直到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然后就感觉舒服了,反复听——这个菜、这个饭店的这个厨师,烧得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