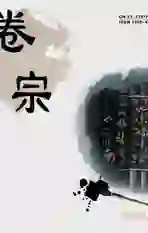王培荀交游考述
2020-03-23徐珊珊
徐珊珊
摘 要:学者的交游活动对其学术生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清代著名学者,王培荀的生平交游情况,迄无详尽的整体考察。本文以王培荀的人生经历为时间线索,通过对相关正史、文集、方志等文献的爬梳钩稽,考察其在不同时期与不同士人群体的交游,包括前期的山东士人群体和后期的四川士人群体,试图还原王培荀生平的部分原貌。
关键词:王培荀;交游;考述
王培荀(1783—1859),字景叔,号雪峤。世居淄川大窎桥(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大窎桥村)。道光元年(1821)举人,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以知县分发四川,历署酆都、荣昌、新津、兴文等县知县。著有《听雨楼随笔》《乡园忆旧录》《雪峤日记》《学庸集说》《管见举隅》《寓蜀草》《蜀道连辔集》等。
王培荀是清代地方重要学者之一,但目前对其研究仅限于笔记文献的价值,尚无专篇论文对王培荀的交游状况做整体的考察。对于一位学者而言,其学术生命的形成,最重要的外部依托莫过于家庭环境的熏陶与生平交际的影响,本文即从王培荀交游方面展开论述,聊补相关研究所未逮。
1 与山东友人的交往
王培荀在山东时的交往大都是少年相识,密友如马桐芳、周东泉,师长如杨春喈等,这些人大多是一些怀才不遇的地方文士,王培荀前半生可谓是失意困顿,好友间体触更为深刻,相互之间的感情也更为深厚。
1.1 与马桐芳的交往
马桐芳,字子琴,号憨斋居士,室名饮和堂,山东长山人(今属山东邹平)人,清道光诸生。学医,工诗,以游幕为生,曾馆益都、聊城等地。有医学著作《伤寒论直解》,未见刊行。诗学著作有《憨斋诗删》十一卷、《憨斋诗话》四卷、《饮和堂诗存》《杜诗集评》六卷。
王培荀最初知晓马桐芳其人是在二舅王祖嵋家中。马桐芳是王祖嵋的女婿,王培荀偶然在舅父家见其诗册,大为惊奇,询问后方知为子琴所作。马桐芳当时年方十六,两人自此相识、相知,经常在诗学上相互切磋规谏。
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把马桐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对其前期诗作极为赏识,赞其清真秀拔,认为风格接近王维、孟浩然,保存了五律“云飞山欲动,花落地还香”“一虫犹唧唧,万木尽萧萧”等句。对其后期炫耀才学、淹没性情之作极为不满,认为他“误以饾饤为富博,而清真秀拔之骨淹没大半”,对他“天生诗才,而不自爱惜”,以至于“莫知其趋向”深为惋惜。由这些评价大约可见马桐芳的诗学风格及其变化,亦可稍窥王培荀的诗学观念:相比于清代的学人之诗,王培荀更欣赏诗人之诗。
马桐芳在《憨斋诗话》中对挚友王培荀的诗也有评价,他认为王诗“咏古之作俱佳”,特爱“妾来非赴桑中约,郎看偏同陌上花”一句,认为‘属对工雅。在《憨斋诗话》中,马桐芳还记录了王培荀学诗的时间,说其‘年五十始为学诗。王培荀晚年才开始学诗与其家世有一定关系。前已言及,王培荀出生在名门望族,天资聪颖,祖父因此将重振家门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走科考兴家之路,所以之前王培荀一直专攻制艺,年过半百才开始学习作诗。但王培荀在诗歌创作上颇有天分,在四川做官时留下了许多诗集,曾国藩典试四川时,看了王培荀的诗,极为称赏,其诗学造诣当非凡庸。
王培荀、马桐芳不仅互相品评诗作,互为诤友,而且时常以诗寄情。如王培荀要去四川做官时,马桐芳写过一首赠别诗,此时马桐芳已经是“文园贫病甚”,只能在家中为好友祈祷祝福,担心好友适应不了“万古蚕丛国”的险峻,同时也为王培荀的坎坷仕途愤懑不平,认为其好友有天才之资,不应困于偏远一方,做一个蛮夷贫困之地的县令。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正是马桐芳为好友设身处地担心的真挚感情的体现。
1.2 杨春喈
杨春喈,字凤冈,号矞翘、旭桥,浙江孝丰人。嘉庆十二年(1807)举人。道光四年(1824),任山东淄川知县。后来调到郯城,升知府,又发贵州,历掌铜仁、都匀、黎平府事,均有政绩。在都匀时,教人民种木棉及蚕桑,一时称为能吏。
杨春喈对于地方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在淄川任上他主张搜集当地名人蒲松龄的著作并与王培荀商讨旧志的缺陷,《乡园憶旧录》记载:
“吾淄杨旭桥明府,欲刻聊斋诗、四六古文,属予往索。”
“《济南府志》不修,百余年矣,是吾乡一大缺陷。里居时,太守某公,雅意重修,征各属县志。杨旭桥明府招余商处,因取旧郡志略一翻阅,体例多宜酌定。”
王培荀去四川做官时,杨春喈及其夫人为他送行并赠以诗画:“吾淄杨旭桥春楷明府,嘉兴人。夫人吴氏善画竹,兼工诗。予来川辞行,赠以四轴搨于石者,自题五古一首,大竹王鲁之题五绝。带来川,李廉侯借去。”杨春喈夫人吴氏即吴秦妲,善画竹,道光六年(1826)杨春喈在博山任知县,当时正值春旱,杨春喈偕同僚在颜文姜祠内祈雨,第二天天降甘霖。吴秦妲画了一幅风雨竹图,杨春喈题跋于后,并刻碑永存,传为一乡佳话。杨春喈夫妇以诗画赠即将远行的王培荀,表达了对好友的真挚友爱与诚挚祝福。
1.3 周治章
周治章的祖父周士孝和王培荀的祖父王相符是好友,王培荀的父亲王思枢曾被周士孝请到家中作老师,那时周治章就与王培荀一起读书了,可见两家交往渊源之深。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和《听雨楼随笔》中多条记载周治章的祖父周士孝及其叔父辈:
从其记载可知,周士孝举孝廉来山东做官,因此得以结识王相符和周永年并交为密友,后来去直隶(今河北省)做官时还邀请王相符去游玩,辞别之后又招王培荀的父亲王思枢去蜀中教书,可知从祖父辈到父辈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周士孝的三个儿子皆是有才学之人,其长子周立规工书法、喜作诗,年少时就随父亲往来于家:“去官后,往来寒舍,与先大父小山公及松厓先生谈宴,好自写诗。佛坡亦每侍侧,年未弱冠也。”
次子周立矩诗集经过张问陶、赵翼两先生评定,文采甚高,曾驱车访王培荀之父王思枢。当时王培荀年十六,初学文,拿给立矩先生评正,先生给予肯定。当年风采王培荀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尝驱车过里门访先君,荀年十六,初学为文,持以就正,谬蒙许可。迄今风采如在目也。”
季子周梦熊,曾学于王思枢,刚满二十岁时突然就去世了,有《白雁》诗三十首,王培荀仅记其一,说其“诗带商声,少年不易有,似不宜有也”。两人曾经一块比肩随咏,王培荀说“如闻山阳之笛”,可知诗才之高。
王培荀对其家族非常熟悉,和周治章从小“侍家君共读”。王培荀《伤周峨东》一篇记载回忆初见周治章时方孩提,一转眼却物是人非了:“读书许随侍,同侪恣欢虐,是时君方孩。提抱怀未脱,转瞬沧桑变。”王培荀在荣昌任上时,周治章来游,匆匆离去,留下一首七律,诗中也是对岁月变化之快的感触,想起两人年少相识于少年,而满头华发再见时恍若隔世:“相别鸡窗岁月深,髫龄华发再相亲。须眉细认疑前世,车笠寻盟继古人。”如今有缘再聚,看到儿时好友能够成为一方循良,心甚宽慰:“诗礼相传曾共侍,关山幸聚有良因。蜀邦风俗颓顽甚,仰赖循良有脚春。”不幸的是周治章在荣一病不起,为此王培荀写下《哀周峨东》来缅怀故人,令人唏嘘。
王培荀说两家是“三世联交情不浅”,王培荀和周治章年少同窗相伴度过了最纯真美好的年纪,再相见时面貌虽已苍老,但是感情仍如少年般真挚。
2 与四川友人的交往
王培荀在四川既是当地官员又是一名文士,所以结交者不是当地有名望的学士儒者,就是在四川出仕之人。由于四川地处偏远,所以政事清闲,在闲暇之余王培荀经常与诗友仕人往来切磋,主要有四川名儒刘沅,官员茹金、杨缜亭、赵桂生等。
2.1 刘沅
刘沅(1768-1855),字止唐,一字讷如,道号清阳居士、碧霞居士,学者尊称“川西夫子”,四川双流人。一生著述颇多,于《诗》《书》《三礼》《易》《春秋》《四书》皆有恒解,都收在《槐轩全集》中。刘沅释经往往不拘于前人,而是以己见重新诠释,并且创立了儒道相结合的民间宗教“槐轩道”,在当地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儒者,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
刘沅和王培荀在经学上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两人之间频繁的往复论学,王培荀对刘沅的阐经方式赞同不已,认为:“其疏解《四书》参用他说,或出己意,不尽遵程朱,是读书求心,不苟为雷同。”
两人的学术渊源在刘沅的《槐轩杂著》中有记载。在《与王雪峤书》一篇中提及王培荀派人来索刘沅经籍著作:“今去冬,敝友来垣以先生之命来索愚弟兄韵言,闻之不胜惶悚……俞芸圃之言检两论恒解、杂著、约言、先尘、郢政,其他虽已成帙,尚待订讹,容当续呈以供雅鉴。”当时王培荀在荣县作县令,喜欢搜罗佳作,结交贤士,胡之寿称其:“雪峤廉吏耽著作,凡见闻靡弗搜採,其好士之雅不减前贤。”由此向刘沅讨索著作知胡氏所言不虚。
以此拜访为契机,王培荀和刘沅开始就四经中《大学》篇的内容来进行切磋,阐释己意,主要包括修身复性、儒佛关系等方面往复论学,双方都获益良多。刘沅与王培荀在于治经方式上也是相通的,不泥于一派,博采众家,从善如流,发明圣人之说,刘沅的四书体系是继承程朱理学而来的,如刘沅曰:“道固人人所有,圣人亦人人可为,前贤以圣人望人必不以圣人自居,好問好察从善如流程朱何独不尔耶?我辈因程朱而后稍知圣道,岂容恃己而薄前贤”,但是在此基础上又自成一派,如寄给王培荀的信中写道:“先生云发明圣人不避谤议,程朱若生必不拒人质问,此言诚堪师表矣。”
由上可以看出,王培荀和刘沅的在治学方法、观念和内容方面都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彼此之间都相互影响,不仅在学识上王培荀夸刘沅是“蜀中真留心学问人”,对于刘沅的为人也有很高的评价,在《听雨楼随笔》中王培荀赞其品格高洁,教授学生百余人不以牟利为目的:“教授生徒,从学数百人,修脯听其致送,无多寡额数,贫者无馈听之。或赠以膏火之费,多掇科第以去。”俩人交往时刘沅已是年逾古稀了,此时王培荀也已是花甲之年,彼时两人仍然孜孜不倦的做学问,往来切磋,可知古人之学今人不及之由。
2.2 茹金
茹金,字元浦,汉阴厅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六年(1826)成进士,授知县。为人寡言憨厚,幼时便已名噪艺苑,邑宰、郡守皆器重之。曾师事安康董诏、洋县岳震川诸先辈,讲宋、元、明诸儒之学。著有《衣江宦迹录》行世,又有《诗文集》若干卷。
茹金自身文采甚高,对于宋元明之学皆融汇贯通并学有渊源,以至于远近宗仰,负笈者至舍不能容。王培荀著作得其赞赏,原因之一是文笔斐然,这也是王培荀两部笔记为后世所传、经久不衰的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两人之间的交往不仅限于文学上的欣赏,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中记载茹金的诗作,说其“在都作《二十四不诗》,仿《竹枝》体,亦谐亦雅,观其诗可知其人”。记其《总起》《不谒权贵》《不狎优伶》《不吸鸦片》《不买钟表》《不闻鼻烟》《不闹娼妓》《不制玩物》《不赌博》《不下馆子》《不饮酒》《总结》《和邵莲溪先生餐菊》诸篇。观王培荀所采诸篇,便可知茹金为人洁身自好,品行端正。
王培荀和茹金同宦一方,因才学品行相契而交。两人都是耿直淡泊之人,在文学上相互欣赏,在品格上相互规谏学习,两人的关系也在这种相互学习欣赏的过程中日益亲厚。
2.3 王者政
王者政,字春舫,山东文登人,授四川仪陇知县,在任七年,政绩显著,升任巴州知州、越巂同知。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因父母年迈而乞求回乡归养。著有《蜀道联辔集》。此集是王培荀与王者政合刻的,两人在举家重返故园的途中赋诗甚多,于是联成此集,以示后世。
王者政和王培荀是同乡同地做官,本应早点相识,奈何直到两人致仕归田才相交,但这并不影响两人的感情,王者政在《蜀道联辔集·序》中提及王培荀之语:“雪峤曰:朋友居五伦之一,独至名场多数致隙末,吾二人以丙申岁定交,时相规勖,益见亲厚,十五年中有如一日,今相率归田,复歌声互答,交相切磨可谓始终不渝者矣,交谊若斯行将判袂不可无,所遗留以示子孙,称诗喻志其唯刻蜀道连辔集乎。”可知两人相识虽晚,但性情甚相契合,感情深厚。
不仅是性情,两人在诗学上更是有默契。王培荀在序中写道“同行一路,揽奇探胜,夜挑灯各写,所为诗交相赏亦相互攻,每至快心辄抚掌大笑,仆圉为之惊骇,盖共车马者两月得诗若干。”两人一路诗兴大发,随走随作,兴起时甚至秉烛达旦,最终集成《蜀道连辔集》,实为艺林佳话。
王培荀和王者政相识虽晚,但两人仅仅在短短数月回乡途中就集成了《蜀道连辔集》这本诗集,可知两人在诗学观点以及性情方面十分投缘,可谓是诗友也是契友。
2.4 赵桂生
赵桂生,号竹庵,吴江人。以诸生援例来四川候补。少时著《兰坚阁丛稿》,小赋取法齐梁,有《榆关话别图》《万里长风入陕图》,题咏甚多。
赵桂生经常给王培荀寄诗作,自所任郫县寄示绝句,都是向好友展现所见所闻以及人文风俗,如蜀地“拜杜鹃”的祭祖习俗:“我来春水桃花里,郫酒馨香拜杜鹃。”还有具有地方特色的郫筒井“郫筒池绕郫筒井,宜向冰壶濯魄来。”赵桂生通过这些诗歌使好友了解自己所在地方的人文风貌。
赵桂生和王培荀还经常分韵作诗,其诗集《寓蜀草》中有多篇记载:《和赵竹菴巴州怀友分韵诗》是两人以“何当共剪西窗竹,却话巴山夜雨时”分韵,王培荀得“烛”字所作;也有为其诗画题作之诗《题赵竹菴乘风万里入峡图》《题赵竹菴章山甫诗卷》;《题赵竹菴从军日记》则是王培荀为送赵桂生从军补作之诗,当时王培荀还未入川,可见王培荀对友人之用心至深;《别赵竹菴章山甫》是好友赴荣昌任时的赠别之诗,表达对好友的祝福:“愧无佳句留好友,岂有良谟及古人。珍重临歧劳赋赠,珠玑满箧未尝贫。”当时赵竹菴有赠别诗,可惜未记。可见两人相互题诗,以诗记事赠友抒情。
王培荀与诸多好友经常相互唱酬,《雪桥诗话三集》中记载了王培荀与好友酬唱赋诗的的场景:“硕农司马书纶汉军甘氏为忠果五世从孙,以壬午进士出宰西川,著循绩听理,得闲与香山何云陔、山左王雪峤、大梁李红樵、余杭吴音木、江左赵竹菴、蜀人潘紫垣、邮递唱酬。”
从王培荀的诗集中也能看到其与友人的日常交往,如《李红樵招饮枇杷晚翠斋》《遨头日与黄梅樵赵竹菴彭海楼杨赓堂宴香叶亭》《与白梅村吴石泉荡小舟由狮子桥至观音阁》(在荣昌三里外)《梅村遨游碧云寺》(荣昌城西南)等诗篇,大都是王培荀在四川任上与好友游山泉之间赋诗唱和的记载,都是王培荀生活境况的呈现,反应出其在政暇之余与好友交往中所体现出的欢喜心情。
从王培荀的整体交游来看,所交之士皆清廉文雅,这些交游一方面体现了王培荀与好友之间的学术交流以及学术思想的相互影响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其生活轨迹的记载,有助于补充王培荀在四川做官期间的具体经历,填补对王培荀个人研究的空白。
参考文献
[1]王培荀著,蒲泽点校.乡园忆旧录[M].山东:齐鲁书社,1993.
[2]王培荀著,魏尧西点校.听雨楼随笔[M].四川:巴蜀书社,1989.
[3]張寅彭选辑,吴忱、杨焘点校.清诗话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刘沅.槐轩杂著.[M].清咸丰二年刻本.
[5]王培荀、王者政.蜀道连辔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第三十四册,2011.
[6]王培荀.寓蜀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526册,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