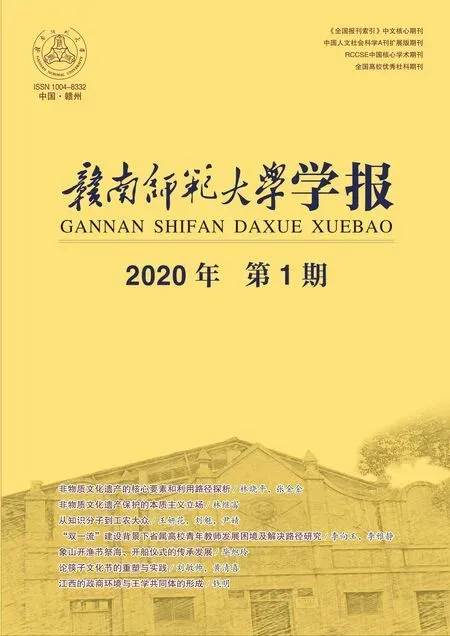从“断魂”到“返魂”
——苏轼初到黄州的心绪探微*
2020-03-15江梅玲
江梅玲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由一个朝野闻名,经世致用的才子变为了一个被侮辱、被诽谤的阶下囚。虽然最终得以免去一死,却被贬黄州。元丰四年正月下旬,苏轼前往岐亭,写下了《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诗中回忆了自己一年前被贬黄州经过关山的情形,有“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1]2237之句。之后,苏轼在岐亭拜访好友陈季常,写下了《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一诗,其中有“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1]2240之句。梅花从“断魂”到“返魂”,似乎暗示诗人的心理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分析苏轼初到黄州时的文学创作,并结合苏轼的行迹交游细致探析其心绪的转变。
一、细雨梅花正断魂:苏轼初到黄州时面对的心理危机与生存困境
在贬出汴京后,苏轼与长子苏迈相依为命,奔赴黄州。在途经陈州时,苏轼与子由的女婿文逸民相见,二人于河堤作别。苏轼写下了《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一诗:“白酒无声滑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风料峭羊角转,河水渺绵瓜蔓流。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1]2113
第一联记事,诗人与友人酒后于河堤上漫步,一个“愁”字,正是“诗眼”,也为全篇奠定了基调。风旋转摇摆,水曲折远流,诗人于是借景抒情,感叹人生的聚散就如风一般摇摆不定,如水一般不知去向何处。想想友人做梦都想回到故乡,而自己被贬黄州,前途亦未可知,再会似不可期,两人难免作楚囚之悲,相对而泣了。巨大的落差感与人生无常感笼罩着苏轼,他正是怀着这样悲凉的情绪去往黄州的。
不久之后,他在赴黄州途中写下了《红梅二首》,之后他一再地提及“红梅”,可见梅花在他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红梅二首》其一如下: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砾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1]2136-2137
草棘间的梅花面对的是可以吹裂石块的东风。苏轼以梅花自喻,写出了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而他所要面对的并非只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有笼罩在心头的政治阴影。这种深重的痛苦无法与人分享。“开自无聊落更愁”,诗人就如梅花一般,孤独地存在着,在愁绪中开落。苏轼对即将面对的贬谪生活和孤独境遇是心怀忧虑的,但一贯乐观积极的他,并没有彻底沉沦在愁苦之中。“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苏轼感受到了来自自然山水的亲近与安慰,由此诗的情绪也变得明朗昂扬起来。这固然是苏轼乐观天性使然,也是他以红梅不畏严寒的精神砥砺自己的结果。苏轼亦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得到了抚慰和乐趣,这些都是他之后得以超越苦难,走出困境的支撑。
以上可看出,苏轼是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来到黄州的。初到黄州,他对黄州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颇有不如意之处。其“断魂”的具体表现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二是对外界的恐惧与疏离;三是对黄州生活的忧虑。
(一)对自我价值的怀疑
苏轼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开头写道:“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1]2150这首诗反映了苏轼初到黄州的复杂心绪。诗的开头诗人回顾以往的生活,自嘲为了养家糊口忙忙碌碌,到了45岁越发荒唐了,竟因为“乌台诗案”险些送命,政治生涯看来已经结束。“荒唐”二字便可看出诗人对自己生活的失望。而这首诗最后两句“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透着浓浓的无奈和自嘲。由这首诗也可看出苏轼对以往的生活产生了怀疑,生出了“于世无用”的感受。
这种“于世无用”的自嘲一而再、再而三的反映在他的作品里。他初到黄州给皇帝写的《到黄州谢表》,就说自己:“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投畀麏鼯之野,保全樗栎之生。臣虽至愚,岂不知幸。”[2]2582-2583认为自己所做所为违背了天理,走向衰穷的结局在所难免,皇上能免自己一死,实在是自己的幸运。苏轼对自己辜负了皇上的信任和重用感到非常惶恐和自责,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可能就此划上句号。他称自己“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2]2583可见,苏轼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觉得多年来一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劫后余生的他也真正懂得了庄子所言的“樗栎之生”是怎么一回事,说自己不仅是罪人,更是一个无用之废物,言语之中充满了自我否定之意。在《曹既见和复次韵》中他称自己“衰老世不要”,[1]2400在《题子明诗后》称自己“为世之废物矣”。[2]7624社会价值的失落,让苏轼内心对于自身产生了怀疑和否定。
在黄州初期,苏轼频繁地自称“幽人”,如“幽人无事不出门”[1]2152“幽人无一事,午饭饱蔬菽”。[1]2433幽人有幽居无用之人之意。这一时期,苏轼亲近自然山水,黄州的一些清冷偏僻之景往往能引起他的怜惜和关注。他的《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安国寺寻春》《雨中看牡丹》《卜算子》(缺月挂疏桐)等写景诗词读来寂寞幽冷,凄怆动人。如他寓居定惠院时所作之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中有:“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1]2162-2163当苏轼和名花海棠相遇,同是天涯沦落的境遇让他对花儿备加同情,视此花为知己,流露出对人生遭际的幽怨和无奈。诗歌的最后几句,诗人表达了强烈的惜花之意。他希望海棠之美,海棠之纯洁不受任何事物的干扰和玷污,而想到明天下过雪之后,花瓣却难免零落成泥的结局,这让他无法不涌起悲伤之情。这首诗饱含了苏轼对自我命运的悲观。
(二)对外界的恐惧与疏离
苏轼是一个喜欢结交朋友的人,“乌台诗案”这场从天而降的祸事,使苏轼对外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和战栗”。[3]在与友人王定国的书信中,他说:“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及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2]2583苏轼想起由于这场祸事,有数十个朋友因他而受到了牵连,而王定国更是被贬到了荒凉之地宾州,与家人生离死别。对友人造成这样重大的伤害,苏轼感到非常自责和痛苦。因此一到黄州,他便主动割断了与友人的来往。这时的他也时常担心政敌的追加迫害,惶惶不安,每日“闭门却扫,收召魂魄”,[2]1237灾难之后的惊魂未定可见一斑。而“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2]5344亲友因害怕牵连纷纷远离,使他无人问津,倍感孤独。刚到黄州之时苏轼亦无心结交新的朋友,于是便“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2]5270
苏轼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也经常流露出颓废消极的情绪。如《与章子厚参政书》中说:“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2]5269因为会连累别人,一方面苏轼自觉脱离与亲友的来往。另一方面,世态炎凉也让苏轼感到非常寒心。对他人的不信任加深了苏轼的孤独感与恐惧感,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他也多次表示自己来到黄州之后“不复作文字”,希望友人能够将他的信件销毁,以免再次因为“文字”而得罪。
(三)对黄州生活的忧虑
初到黄州之时,苏轼在生活上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在与秦观的书信《答秦太虚书》中向秦观诉说了自己生存的困境:“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2]5754苏轼作为贬官,已经没有俸禄了。随着家眷到来,全家人迁居临皋亭,生活越发窘迫起来。在元丰三年底,家里以往的积蓄就要用尽。家中有不少人口要养活,这让他十分忧虑。
面对可能已经提前结束的政治生涯,王水照先生称苏轼“首先心理上要有做一辈子老百姓的准备”。[4]但是这个阶段,对于此,苏轼并未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在《迁居临皋亭》中说“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1]2205认为在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就坚决辞官归隐的人,并没有几个。苏轼此时正值壮年,作为一名怀抱经世致用理想的士大夫,自然是不甘心一辈子当普通老百姓的。现实的平民生活让苏轼无所适从,出仕的愿望与被迫归隐的现实让他备感矛盾。
在被贬到黄州半年之后的元丰三年九月,苏轼在与友人的书信《与王元直》中抱怨道:“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此中凡百粗遣,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2]5943可见对于这种隔绝人世的平民生活还没有完全的适应。这个时候他还十分关心来自朝廷的消息,渴望着自己命运的改变。由上可知,苏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融入黄州的生活。
二、返魂香入岭头梅:苏轼的自我救赎之道
这一时期从苏轼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的孤独和痛苦,委屈和幽愤。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这一阶段很多时候是有意与世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厌弃与疏离,因而自然亲近了庄禅。苏轼此时释道兼修。释与道在求“静”一点本有相通之处,不过相较而言,苏轼对待释道态度及其目的是有区别的:苏轼借佛以求“静心”,借修道以求“炼身”。[5]苏轼利用佛禅清净内心,而将道家之术用于养身。不仅如此,此时庄子所言的“无用之用”也是他安慰自己的理论依据。他对庄子“万物齐一”的主张有了更加深刻的感受和领悟。正是庄禅智慧使他走出了最初的惊悸,变得平静和淡然,而苏轼深藏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也是他走出困境的精神支撑。这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齐物我、齐荣辱、“与渔樵杂处”
在元丰三年末,苏轼写了《答李端叔书》,在信中痛陈了自己之前的罪过。苏轼在信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妄论厉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而已,何足为损益。”“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2]5344苏轼认为,科场之病与物之病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自身的长处和特点去博取他人的关注,自以为出类拔萃,与他人不同。其实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早在元丰三年九月的时候,苏轼在《定惠院顒师为余竹下开啸轩》一诗中就对“自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就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看待所有自然界的虫鸣之声,得出“皆缘不平鸣,恸哭等嬉笑”的结论。《答李端叔书》一信中也持相似的观点。文中从“齐是非”的角度指出“妄论是非”皆是“自鸣而已”,根本不足为损益。同时苏轼通过学习佛法,禅定静坐,进行自我的观照,试图对世俗的悲喜进行超越。
在学禅初期,苏轼还不怎么强调外界的“空”性,主要强调自性的觉悟以及如何处理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关系。苏轼还是习惯于用庄子相对主义的观点去看待问题,突出“自我”的同时,也有一个参照比较的对象。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2]5345苏轼称自己“深自闭塞”,可见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隔离,而后他“自喜渐不为人识”。[2]5345苏轼以前被众人推崇,也自认为才华过人,结果自己最为看重的东西反给自己带来了灾祸。这时候他认为庄子所言的“不材”“保身”是一切的前提,因而渐渐觉得“不为人识”“于世无用”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安全的客观环境。这时的他“与渔樵杂处”,逐渐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通过这段时间的自我调适,苏轼明白了曾经自以为的过人之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宠辱是非等外在存在,其实并不重要。所谓的长处,会招致“毁身”的严重后果,甚至还不如一般人。自己其实和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由此他渐渐洗去了自身的所谓“光环”与“尘垢”,融入了平民的生活。既然宠辱是非不再重要,也就没必要再活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之中了。在进一步理解了生命本质的平等之后,苏轼开始甘于当一个普通人了,而且也渐渐开始享受普通人身上的快乐。
(二)结交黄州友人,与隐士为伴
苏轼在黄州初期处于十分孤独的境况,然而他并未陷入孤家寡人的绝境。先是子由的来访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安慰。不久之后,他又在黄州认识了一批新的朋友。苏轼曾在《东坡八首》之七写到了他的这几个朋友:“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春。古生本将种,卖药西士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1]2254可见这几个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遇。而苏轼的好友陈季常,也是在“不遇”之后选择隐居在岐亭的。朋友们和他一样,都偏离了曾经规划好的人生道路,可见世事无常。而这些朋友能够以豁达之胸襟安然接受人世的无常,快乐潇洒地活下去,这也是苏轼与他们相交甚厚的原因。这些朋友常与苏轼宴饮谈心,相约每一年都要到定惠院一起赏花游玩。在苏轼遭遇生活困难时,友人也会及时相助。可以说,正是身边有一群这样沉沦不遇却惺惺相惜的好友,才帮助苏轼走出了困境。
在黄州时期,苏轼喜爱与隐士交往,一方面是对隐士高洁品质的欣赏和向往,一方面“与世隔绝”的客观处境,使苏轼很多时候感觉到与隐士心境的契合。《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一诗就是赠给陈季常的。陈季常是苏轼非常欣赏与敬佩的隐士,其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的逍遥生活也为苏轼所向往,但是苏轼始终也没有过上彻底的归隐生活。一方面是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便是庄子也不倡导人们去过幽居山野的隐居生活。庄子所描绘的精神世界极广大、极自由、高度理想化,因而当我们,也包括庄子自己在反观现实社会的时候,往往会对现实产生诸多不满和无奈。但这并不妨碍庄子认为要在现实人生中去寻找“道”的内涵。毕竟,庄子哲学的目的也是为了改造人生和社会的。而禅宗的精神更是让人们在世俗社会的点滴中去品味禅的真谛。这一时期,苏轼既在独孤的精神世界里进行清醒的自我观照,又在生活中不断融入黄州的世俗社会,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三)节衣缩食,专注生活,与底层人民互动
由于生活贫困,苏轼与家人不得不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2]5754苏轼将以往的积蓄存起来,每个月按照规定时间取一定数量出来日用,挂在梁上每日取用,有多余的,也要存起来以便招待宾客。
随着苏轼自我认识的升华,他渐渐放下了往日的功名荣辱,适应了平民的生活。他积极发现黄州的物产,研制美食,之后还兴致勃勃地写了《猪肉颂》《二红饭》等文学作品。而“与渔樵杂处”的客观环境也让苏轼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面对黄、鄂之间“溺婴”的不良习俗,他向朱鄂州上书改变“溺婴”习俗,并组织大家为贫民捐钱捐物。正是这种与底层人民之间的互动,加深了苏轼对于黄州的感情。苏轼在黄州常常与友人一起出游。黄州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赤壁、黄泥坂等,让他在惊叹风景之美的同时,也抚慰了他寂寞独孤的心灵。苏轼在心理上接纳了黄州,喜欢上了黄州,从而消除了对黄州生活的忧虑。这也为他之后展开农耕生活做了铺垫。
三、从“断魂”到“返魂”:红梅诗标志着苏轼心理危机的结束
在黄州一年后,苏轼在《答李端叔书》这封书信里对“旧我”之过进行了总结,指出:“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2]5344苏轼认为自身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了新的自我。这封书信宣告他已经基本走出了心理危机,标志着苏轼黄州前期心理危机基本结束的作品有元丰四年正月下旬的诗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与《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这两首写到梅花的诗作与书信几乎作于同时,更加直观地体现了苏轼心态上的变化。
经过一年的时间,苏轼前往岐亭,途中回想起了自己之前的境况,写下了可与之前梅花绝句相互对照的一首七律:《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全诗如下: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
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1]2237
这首诗与一年前的《红梅》诗描绘了基本相同的景物,却展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红梅》诗中梅花不畏严寒独孤生存,而此诗上来就写春天已在不知不觉中到来。诗歌的第二句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写了初春之景色。流水携冰块从谷中流出,火烧过的地方已经被青青绿草所覆盖,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之景象。此时苏轼正准备拜访在岐亭隐居的好友陈季常。这一年多来,他在黄州结识了新的好友潘生、古生和郭生,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第三句写几个朋友为他践行。不管是“荒”还是“浊”,都可以看出物质条件的有限性。但是友人相留,浊酒可温,可以从中体味到浓浓的温暖之意。“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正是对之前“何人把酒慰深幽”的直接回应。
逐渐走出心灵困境的苏轼又想起了一年前,他正在赶往黄州的路上戚戚苦行。“细雨梅花正断魂”一句化用了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梅花凄凉断魂,正是作者境况的自谓,而这“细雨梅花”正见证了诗人心境与处境的转变。
与此诗几乎作于同时的《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季常》一诗也吟咏了梅花:“蕙死兰枯菊亦摧,返魂香入岭头梅。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1]2240诗中写其他的花都已经枯萎了,连菊花也被摧残殆尽,只有梅花在严寒中迎接着春天的到来。前一首诗苏轼写自己去年被贬时的境况是“细雨梅花正断魂”,而之后则写“返魂香入岭头梅”“返魂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6]“返魂香”是一种可以令人起死回生的灵药。“断魂”写的是诗人前期失魂落魄的痛苦情状,这一时期他是在“寻魂”,而“返魂香入领头梅”,则是作者获得重生的写照。在这一年,苏轼经历了一场重生。这种重生,即是经过严寒摧残将死,最终跳出了名利宠辱的困扰,无畏而生的“寒梅精神”的展现,是苏轼自我人格的再确认,是生存信念的再确立。
苏轼对梅花情有独钟,在贬谪之后,他创作了很多梅花诗。“就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的这种‘寒梅情结’贯穿其一生。”[7]苏轼在贬谪到惠州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这相隔一年间的梅花诗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有:“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自注有:“昔予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张志烈先生称:“苏轼后来屡次提到这两首诗,可以窥见其极不寻常的意义。”[7]“寒梅”确实象征着一种逆境中生存的精神力量,而苏轼之所以在贬谪时期反复提及,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年的时间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元丰三年的《红梅》绝句是他在人生低谷的情绪抒写,是他身处逆境中不知如何自处的写照。他第一次遭受人生的重大挫折,领会了“断魂”的深刻痛楚,故而使他难以忘怀。可以说,贬谪黄州是他人生中最落魄最惶恐的时分,之后无论被贬惠州还是儋州,苏轼都未曾“魂断”,这是因为他在黄州找到了“返魂”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