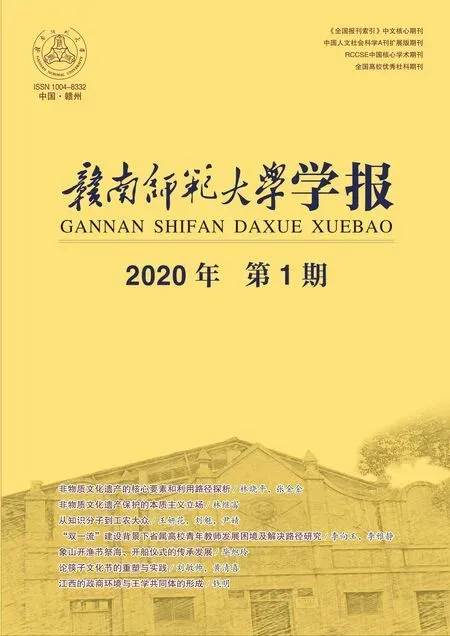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大众—中央苏区时期干部群体社会来源之转变*
2020-03-15王妍花
王妍花,刘 魁,尹 婧
(赣南师范大学 a.外国语学院;b.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干部”一词来自日语,本是日语中的一个汉字词,字面意思是“骨干部分”。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即使用了“干部”一词。[1]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2]干部既是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又是管理人员。干部是实现党的决定、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夺取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中心主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迄今为止,学界对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1)相关研究有:林蓉认为,井冈山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锻炼和各类培训学校等多种途径,选拔、培养和训练干部,造就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人才。朱平亦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党对红军干部的培养非常重视,通过培养,使红军干部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了红军干部明辨是非与反“左”反右的能力,增强了红军队伍的战斗力,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参见:林蓉.浅析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干部成长的途径[J].传承,2012(18);朱平.谈苏区时期党对红军干部哲学素质的培养[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2)。已有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苏区干部好作风”等方面,侧重的是党的作风建设,中央苏区时期干部群体的实态研究,暂付阙如。
一、苏区干部的来源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江西苏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一书认为,干部的来源可分为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等。[3]149-151若以干部的籍贯和来源地为划分标准,中央苏区干部主要可划分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两大类。在外来干部方面,其途径又可分为四个方面。
其一是由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从井冈山跟随红军转战赣南的干部。这些干部除牺牲外,其余大部分成为中央苏区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领导骨干。湖南籍的干部作为外来干部,在中央苏区党政军上层组织中是占有较大比例的。[4]106-117
其二是从其他苏区转战或转入中央苏区的干部。例如,从广西左右江苏区跟随红七军千里转战中央苏区的干部,有邓小平(四川籍)、李明瑞(广西籍)、李天佑(广西籍)、龚楚(广东籍)、张云逸(广东籍)等。又如,参加第一、二次全苏大会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会后也有一部分留在中央苏区。此外,还有一些到中央苏区学习、考察的党员干部,学习、考察结束后留在中央苏区。
其三是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干部。这些干部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战争等各方面原因,地方需要大量干部,却一时难以培训大量干部,故请求中央及省委委派干部。换言之,地方向中央要干部。[5]另一种是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各苏区的领导以及各苏区之间的联系,主动派遣干部到各苏区,直接指导和帮助当地党部的工作。[6]268这些党员干部到中央苏区以后,除一部分从事教育和技术工作以外,大部分担任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高级领导职务。
其四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以及被俘后参加革命队伍的党员干部。因战争环境下,中共党员干部,特别是红军中的“下级干部死伤太多”,国民党“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一些俘虏兵甚至在短短数月时间“有当了营长的”。[7]就国民党起义和投诚的军队而言,1931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在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指导和在该路军秘密开展工作的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发动下,于江西宁都举行的武装起义。宁都起义成功后,许多国民党官兵成为红军干部。[8]
除外来干部外,干部来源最多的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中国共产党创立不久,在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江西进步青年就开始回本省,争取在江西建立党、团组织。土地革命初期,这批党员干部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领导者,地方群众的领袖,在乡村中大半都有相当的地位和信仰。与外来干部相比,本地干部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中央苏区方言以客家话为主,县与县之间方言有所差异,甚至一县之内,不同方言区之间相互穿插,形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方言岛”。外来干部人生地不熟,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尤以宗族聚居为主,外来干部很难凭空进去。[9]发展党员,宣传革命,必须要有本地人的引介。
红色政权建立以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提拔、培训等多种途径改变党员干部的成分。产生一大批工农出身而文化水平不高的干部,这些干部熟悉当地情形,与群众有紧密的联系,有些人还担任中央机关或省级党政领导职务。以1930年6月的赣西南特委为例,该特委共有干部35位,江西籍34位,占总人数的97.1%。其中很多人曾经担任过区委委员、团委委员、区委书记、支部书记等职务。成分最多的是工农和学生,具体有码头工人、理发工人、竹工、缝纫工、铁匠工人、木匠工人、农民、佃农、自耕农、雇农、师范生、中学生和高小学生等。[10]606-614
呈上所述,中央苏区的干部来自全国各地,中下层干部以江西籍和福建籍为主,外省籍干部则在上层党政军群组织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不可否认,出于“地缘政治”或乡谊的需要等原因,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亦常发生一些摩擦。[11]但是,广大党员干部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即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之间,能够团结一致地为苏维埃革命事业奋斗,其中亦有许多党员干部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二、干部的社会构成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党员的阶级成分。干部是党组织及其它组织的领导者,成分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早期党组织的领导者大多是知识分子,有些党员所受的教育程度还特别高,甚至有留学经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既非工人,又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未经历过革命实践,也对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党的改造的重任是,以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旧干部。诚然,这并非意味着一切非工农成分的干部完全不给出路,或开除出党,而是要使无产阶级及贫农成分的干部在党组织中占据最大多数。[12]换言之,从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到市委、省委,各级党部的干部成分,尤其是农民中的党员干部成分,必须以工人或贫农为主。
1928年,受当时共产国际选拔干部时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中共六大有关党组织的决议案草案规定,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党必须不断的吸收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党应当把从工人中造就干部人才“看成是改良自己”的长期系统的工作。同时应该纠正一种错误认识,即工人一定具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观念,知识分子一定会犯机会主义的错误,对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一定要免其职务。[13]
事实上,关于干部的工人化这一改造工作,实施起来颇有难度。中央苏区时期,党组织的发展由城市转向乡村,由城市的大企业转向农村的小工厂和手工业。但是,农村工业不发达,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不健全,各级党部缺乏工人成分的干部,多不能领导革命斗争,或每次斗争失败后,党组织大半“崩溃”。中共中央认为,党若要建立和巩固农村支部组织,除向农村派遣得力的工人成分的干部,还必须吸收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入党。[14]
然而,一些领导机关虽有工农委员充任,工作上的决定权仍为知识分子所操纵,以致造成秘书或书记专政现象,或地方书记由工农分子担任,知识分子在幕后担任“参谋式的秘书”,“于是秘书独裁的现象又出现了”。[15]2741929年6月,《中共江西省委五月份组织工作报告》显示,江西省党员总数共9 000余人,工人占总人数的5%,佃农占总人数的23%,雇农及农村手工业者占总人数的20%,半自耕农占总人数的25%,其他占总人数的37%。全省中级干部分子约200人,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60%,工农占总人数的40%。[15]289
如果说《中共江西省委五月份组织工作报告》中,仅县委一栏能够反映知识分子干部占据主导部分,工农分子干部相对缺乏的话,那么,再以1929年8月25日《范自成关于中共江西省委和各特委、县委干部履历向中央的报告》为例。江西省委共有干部13位,其中,知识分子8位,占总人数的61.5%;农民1位,占总人数的7.7%;工人2位,占总人数的15.4%;店员1位,占总人数的7.7%;另有1位不清楚。赣西特委共有干部5位,其中,知识分子2位,工人2位,农民1位,分别占总人数的40%、40%、20%。赣南特委共有干部5位,其中,知识分子3位,工人1位,农民1位,分别占总人数的60%、20%、20%。信江特委共有干部5位,其中知识分子3位,农民2位,分别占总人数的60%、40%。九江县委共有干部5位,其中知识分子3位,工人1位,农民1位,分别占总人数的60%、20%、20%。都昌县委共有干部5位,均为知识分子。其余临川县委、南昌区委、永修县委、德安县委、鄱阳县委、浮梁县委等,均有不少知识分子担任干部。[4]106-117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江西党组织的一般情形,各级指导机关多半还是知识分子维持着,这些知识分子大都是上级机关委派的。
随着红军在各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村的豪绅大都涌向城市,乡村的政权逐渐移向接受过新式教育(高小、中学等)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知识分子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大多是共产党员,一般工农群众“自己以为不会写字,不会讲话,认为知识分子是万能的”。[16]511-512因此,工农群众多信任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人选,因其“政治认识的低和观念的不正确,往往引导农村斗争”走向“合法请愿”,“而且结果往往失败”。[10]135-141
苏维埃区域内,党的政权相对稳固,党的地位更为凸显,党员干部的无产阶级基础已有所改观。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显示,特委共有35位干部,其中,工人9位,占总人数的25.7%;自耕农2位,半自耕农2位,农民1位,佃农2位,雇农1位,总共8位,占总人数的22.9%;工农分子合计比例为48.6%。其余,士兵2位,占总人数的5.7%;农妇1位,占总人数的2.8%;知识分子15位,占总人数的42.9%。[10]606-614数据显示,知识分子干部的比例有所下降,工农分子干部的比例有所上升。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导中上层党组织的工作,即使有一些积极的贫雇农及手工业工人担任工作,但都是依附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下从事工作。
至于基层党员干部,当各地农村的土地革命还未开展的时候,上级机关派去农村工作的党员干部多是知识分子,农村中给予接洽的亦“多属富农、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引进来的当然只是他们气味相投的同类。”土地革命斗争开展的时候,这些富农、小地主出身的党员又多半成了支部以上各级指导机关的干部。[17]有些地方虽有几个无产阶级分子在机关内工作,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而是一些脱离生产的“流氓无产阶级”。[16]506-507因此,党的指导机关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能领导斗争,党员干部官僚化与绅士化。工作中表现出右倾化的富农路线和富农思想,妨碍乃至压制一切革命斗争。
为了强固红军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大量成分好的优秀党员干部涌入红军,又产生新的问题。地方得力干部锐减,干部训练满足不了地方需要,以致地方极度缺乏优秀干部。上级党部虽注意新干部,特别是工人成分干部的积极引进,可是,下级党部对于这一工作并不积极,“有的对于旧的动摇干部分子留恋,甚至许多党部连下级干部都要中央供给”。[18]党在地方的领导和动员便显得乏力。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稳固,不仅党员的数量得到迅速扩大,大量的工农干部被提拔,指导机关中的非无产阶级成分急剧减少。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片面强调党组织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工农成分。[6]475-480过去,干部的成分以知识分子为主,后来,新的干部是以农民成分为多,且以雇农和贫农占据多数,工人成分稀少。红军中是如此,地方党组织亦是这样,以1932年的万泰、公略、瑞金、乐安四县为例,贫农成分的干部的比例最高,其次是雇农、中农、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的比例已经下降到极少。[10]662如果说4个县的干部数量比较少,不具有代表性,那么,再以1933年江西省的兴国、赣县、胜利、会昌、石城、宜黄等16个县为例。据统计,这16个县县一级干部共有419名,工人成分192个,占总人数的46%;贫农184个,占总人数的44%,两者相加,比例高达90%。[10]674-698可见,提拔工农分子干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经过提拔新的干部和洗刷旧的干部,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得到改善,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独立性和主动性都提高了,然而,党组织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大多数党员干部“很年幼”,换言之,党龄很短,许多只满一年或不满一年。仍以上面的16个县为例,1928年以前入党的人数只有13个;1928年至1929年入党的有52个;1930年入党的有125个;1931年至1932年入党的有190个;1933年入党的有39个。[10]674-698
至于中央苏区党员干部的人数,暂无确切的统计资料,依据《红色中华》提供的数据显示,地方党政干部大约8万人。[19]加上中央苏区军事干部总人数2万余人,到1934年春夏间,中央苏区各级党政军干部总人数约有10万人。[3]147-148相对于中央苏区总人口450余万来说,这支干部队伍应是十分庞大的。
三、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1929年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色区域日益扩大,加上残酷与激烈的“围剿”与反“围剿”拉锯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人才损失很大,各类干部人才显得异常紧缺。干部人才的供给途径有多种,无论是短期训练班和党校培训,还是中共中央直接选派干部,都无法填补地方干部缺乏的巨大“缺口”。[20]1628因为干部训练不仅耗时,且训练人数有限。中共中央也无法短时间内选调大量干部供给各省、市、县,以致“新的干部没有造出,旧的干部不敷分配”。[10]550-551
况且,中共中央认为,上级委派干部固然必要,但地方不能总是指望上级部门委派干部。地方不是没有干部,而是许多干部人才“被埋在下面”,没有提拔上来。[21]只有不断地就地制造干部,新干部才有更多的机会产生。从党员中以及下级党部中去找干部人才,党员干部的产生由过去的“面向上级”转变为“面向下层”。换言之,健全地方党部,主要依靠地方自己在当地选拔得力的干部。毕竟地方干部更了解当地情形,亦能真正反映民意,推动当地工作的开展。[22]故而,在实际斗争中去培养与提拔干部便显得极为迫切。只有从实际斗争中提拔的党员干部,才更易接受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担负艰巨的革命任务,避免那些脱离实际的单纯“学院式”党员干部的产生。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对象是工人、佃农、雇农,特别是提拔工人成分的党员干部参加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这种参加并不是形式上的挂名,而是指导工农成分的党员干部负指导机关的实际责任。提拔的方法是,各级党部缜密地考察党的工作人员的表现,登记和统计各个工作人员的各项特长,譬如,某某擅长宣传,某某善于组织,某某长于工农运动等。召集这些考察对象,要求其参加经常的支部生活,开会讨论党的决议和精神,研究当地的实际情形,分配实际工作,发动日常斗争,在斗争中提拔新干部,在斗争中淘汰旧干部。[15]20
为了使提拔的干部能够“在其位而谋其职”,干部的提拔与调动,须严格经过党组织的决定。不得上级组织许可,绝对禁止单凭个人感情无原则与无标准的把下级干部往上级部门调动。分配干部工作,亦须按照一定的标准,首先是提拔对象的社会成分及政治的坚定性,例如,积极拥护土地革命者等;其次,工作积极并吃苦耐劳者;再次,有活动能力者。[10]209-212伴随着新的苏区的建立与国共战争的扩大,为了加强新区、边区的领导,许多党的最好的干部被调到新区与边区,担负起指挥战斗与巩固党的各项工作的任务。由此,党对新的干部的需要大大地增加了,党组织只有提拔那些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积极勇敢的新的工农分子担任干部,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才能较好地解决党员干部缺乏的问题。
苏区时期,从中央到省、县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都建立巡视制度。巡视员在巡视工作过程中,帮助地方党部进行干部训练,亦提拔一些具有培养发展前途的下级机关党员干部。此外,大力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是深入开展妇女运动、彻底解放农村劳动妇女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对此非常重视。1933年9月,江西兴国、公略、赣县、胜利、安远、南广、于都、瑞金、永丰、寻乌、博生、信丰、会昌、石城、宜黄、乐安等16县,提拔县一级干部419人,其中工人192人,约占46%;贫农184人,约占44%。所有干部被分配到县委、县政府、县保卫局、县工会工作,此前,这些干部有区级、乡级和支部等基层工作的经验。就干部的籍贯而言,兴国、公略、赣县、胜利4个县最多,共有174人,约占42%;会昌、石城、宜黄、乐安4个县共有36人,约占9%;革命斗争历史越久或阶级斗争越深入的区域,工农干部越容易被提拔,女性干部也就越多。从党龄来看,绝大多数党龄不长,1927年及以前入党的只有13个,约占3%;1928年至1929年入党的52个,约占12%;1930年入党的125个,约占30%;1931年至1932年入党的190个,约占45%;1933年入党的39个,约占9%。由此可见,党龄只有1年或不满1年的干部不在少数。至于文化程度,具有中小学水平的25个,能写通讯的129个,合计154个,约占37%;略识字而不会写的181个,约占43%;完全不识字的84人,约占20%;[23]福建党员文化程度也令人堪忧,据1933年福建省委统计,不识字者54.98%,粗识字者32.42%,能写普通信者11.3%,受过中学、大学教育者1.3%。[24]
不可否认,提拔工农干部的确有些成绩,但是,各地亦出现许多缺点,提拔干部的口号多半有敷衍的形式主义的毛病。工农分子虽参加指导机关,但能力不足,囿于文化程度不高、工作经验欠缺、党的生活过于短促等原因,并不能独当一面地开展各项党的工作。一些党员以为只有在党内做过领导工作的党员才算是干部,不相信新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以工农不识字为由,反对提拔工农分子。即使提拔工农干部,亦“只是凑凑数目”,[25]并没有积极地去教育与训练工农干部,形成指导机关仍是少数几人包办的局面。有些地方,干部的提拔不是根据对象的阶级觉悟性与政治上、组织上的坚定性,而是纯以“派别观念”“感情关系”“地方主义”等为标准,[26]将许多没有经过教育训练的工农分子“保荐”或直接“拉”到领导机关,负重要的指导责任。结果,这些被提拔的干部不能胜任工作。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苏区的贯彻执行,党员干部的提拔成效还受到肃反的严重影响。从1931年至1934年,在组织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许多干部被提拔,又有许多干部被错捕错杀。肃反造成党与群众关系紧张,民众不愿入党,“怕受社党嫌疑”“党内相互猜疑和不安”“甚至发展到闽西党的最高机关,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减弱了”。[20]2071-2072干部如此缺乏,以致县委向市委要干部,市委向省委要干部,省委向中央要干部。
四、干部训练
中共中央认为,大多数党员虽富有革命热情,却缺乏系统的开展工作的认识、工作方法和经验。因此,在努力扩大党员数量的同时,应尽可能地训练新党员。区委以上机关应有党校和训练班,下级党部亦应开设短期的训练班。各级党部之所以开办训练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党员的政治水平太低,不明了党的主义和政策,一些地方的党员干部甚至连基本的党的知识都不懂。党组织的改造是一个长期的和系统的过程。如果只是一味地增加工人成分,而不注意党员训练工作,还是难以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1928年4月,中共中央拟定江西工作大纲,江西省委立即开设短期训练班,在斗争中训练一批干部人才。[16]253-260
各级党部开办训练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干部人才的缺乏。在许多英勇斗争中,虽然涌现大量的工农干部。但在白色恐怖之下,旧的干部分子损失极大。乡村党组织常随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成百上千党员,有时又一个党员也没有。革命失败情绪在党内比较浓厚,一般干部分子亦容易消极悲观。[27]“八七”会议以后,训练了一批工农干部,可仍不够用,不仅工农干部分子缺乏,知识分子干部亦时常缺乏。各地秘书的缺乏,直接导致一些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有人能胜任。除非上级党部,乃至中共中央派遣干部,否则,许多下级党部难以解决干部人才的缺乏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随着其管辖区域的扩大,党员人数发展可观。然而,许多新的党员没经过训练,原有的干部人才又不够分配。经过李立三时期,干部缺乏现象已经突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干部缺乏问题更加凸显。特别是在反“围剿”战争中,大量地方上的优秀干部被调到红军中,许多干部在战争中又损失太多,这就加剧了各级党部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因此,党必须训练大批新的干部,去巩固各级党部,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
各省训练干部的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训练班,另一种是党校。相对而言,训练班的培训时间一般比较短,党校的培训时间比较长。省委的训练班成员来自地方党部,以各县下级干部为主,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工人、农民。每次训练的人数不多,一般是10人左右。训练的时间比较短,以1星期为限,每天2小时。训练的内容紧跟革命形势的需要,包括党的政治任务、政治现状及工作方针、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城市民权运动、党员须知、党内组织问题、宣传鼓动的方法、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游击战争、武装暴动、边境斗争、政治常识等。[28]中共中央提供训练经费、训练材料和训练的经验,各省(市)(县)(区)委也出版一些训练的刊物。刊物的内容有些是各地党部提炼的工作材料。
相对省委训练班而言,下级党部训练班的许多成员是支部中的积极分子,尤其是支部书记与支部干事等。针对党员干部的文化程度不一,有些县份举办的训练班将学员进行分班,工农分子为一班,知识分子为另一班。当然,因条件所限或军事需要,有些县亦将两者合办。组织各种问题研究会和读报班,读党报、小册子和决议案,召开支部大会或特别干部会议,作浅显的政治和理论问题的报告。收集、编订、翻印或出版各种问题的训练材料供给党员,以作研究参考。[10]643-646
基层党员干部白天需要工作,只能利用夜晚的休息时间来参加训练,为此,一些地方党部定期举办流动训练班。流动训练班是流动的和短期的,每班人数不多,这也是流动训练班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29]省委帮助县委训练流动班的巡回教员,新党员一经入党,流动训练班即派一个积极的老党员与新党员谈话,解释如何做共产党员,并分派新党员以适当的能胜任的工作。[30]
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教育的学校,是锤炼骨干党员的熔炉。中共中央意图通过在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设立一个以上党校,来培养党组织、苏维埃组织以及职工会的中等干部。通过有计划地培训,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进一步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不仅要解决地方向中央要干部的现状,更要造成苏区向中央输送干部的局面。苏区地方党校的培训时间比训练班的时间要长,一般是1个月左右。特委与省委以上党校的学员为各县所派,有几十人。学员入学的资格为工作积极、政治观念正确、身体强健、无恶劣嗜好以及略通文理者。培训的课目有政治、组织、宣传、工运、军事、兵运等,[31]大致上,军事训练、实际工作的常识以及政治经济常识各占三分之一。许多学员毕业后,充任红军、游击队的政委,或担任县委书记、区委书记。
除地方党校外,中国共产党对红军中的党员干部培训问题也是非常重视。单靠红军学校培养党员干部或由地方武装中产生干部,皆不能满足党对红军中干部的需求。1932年4月,中央苏区决定开办军事教导队和政治教导队。其中,政治教导队的学员由各地方党部征调。[10]438-439训练的内容包括政治分析、组织常识、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反机会主义及托洛斯基主义及反对派问题的讨论、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共产党的认识、主张、纪律等。
在革命实践中,许多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薄弱,因此,增添了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困难。为迅速地克服这一困难,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培训除国内设点外,苏联还在莫斯科设立列宁学校中国部,训练一些中国共产党内级别较高或党籍较久和工作经验较多的干部。学习期限为半年以上,学习人数为数十人。在课程设置方面,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政治和联共中央选派马列主义“理论经验充实的老布尔塞维克(最好是地下党时代的老同志)”,向中共党员干部讲授理论知识,并进行专门工作的实习(如宣传、组织、职运和苏维埃等)。在莫斯科对中共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有其优点,学员能够学到正宗的马列主义理论,但也有不足,列宁学校的课程无法注重中国化问题,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共党员干部,妨害并不大,而对教育程度低的党员干部,接受起来,“就极感困难了”。[32]
无论是短期训练班,还是党校,或是其他培养形式,党员干部的训练方法灵活多样,不局限于哪一种。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实践的锻炼,甚至还用谈话的方式,以此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只不过,每种训练都或多或少地兼有军事训练,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训练与教育,名称虽不同,本质却无太大差异,传授知识、经验与技能,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过程,训练为短期的、片段的与治标的过程。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比较低,越到基层,越是如此。党的决议案、通告等大多只能达到区一级,每个支部中能识字的不过少数几人。苏区支部是以乡为单位,许多乡纵横几十里,支部大会不容易召开。支分部会及小组会可以经常开,不过开会的形式主义比较浓厚。故而有关文字方面的决议案、通告等材料不容易在群众中广泛传播。[33]
党员干部中的农民成分占大多数,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异常低,对党的各项决议多不能完全理解。部分党员干部对各种党的策略“只是盲目的服从或则完全不信任,认为高调”。[16]376-381农民干部难于培养,参加训练的学员又多从“农村中挑选来的,能够授课的人都不是本地人”,言语不通,学员听课感觉困难。[10]252-259加之训练时间短,训练材料缺乏。上级下发的训练材料及工作指示,还只是下级几个负责人能看见。一些党部没有经常开会,党员干部不能得到训练。新训练的党员干部与已牺牲的有经验的党员干部相比,往往相差甚远。
因作战时间多,休息时间少,红军中的党员干部训练亦非常困难。又因革命战争的需要,红军损失一批党员干部,马上就要补充一批训练过的党员干部,战斗次数越多,补充的人数也就越多。所以,红军中的党员干部训练的时间“也只是很短期的”。[10]32-34党员干部的培训虽存在着局限性,然而,党员干部的训练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毕竟训练比不训练要好得多。党员干部经过训练班或党校等“洗礼”后,一般下级干部对于党的策略和党的认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接受训练的党员高级干部更是如此。党员干部训练的群体不庞大,工人成分的党员干部稀少,文化程度亦低,多半都有家庭的负担,又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对训练没有兴趣,但训练在精不在多。
五、结语
已有研究者提出,随着清末科举制度的停废,大量的农村精英逐渐流向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共战争又助推了上述过程。[34]党的创建时期,干部成分以知识分子为主,国共分家以后,中共发动了一系列的地方武装暴动,暴动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一直强调党员干部的阶级成分。党员干部的工人化这一建党理念的实施,一些非无产阶级的党员干部不断地被清除出党,使得农村基层社会本已有限的知识分子等党员干部人才更难罗掘。
一方面,随着革命战争的深入,苏区各地苏维埃政权的次第建立,各级党组织、政权组织和群团组织不断扩大,需要大量干部去履行各项职能。另一方面,国共内战条件下干部的“消耗”和红军的发展,进一步拉大了党员干部的需求。经过选拔和任用,大量工人、贫农和雇农成分的党员干部进入党政军群机关,干部的“群众化”趋势日益凸显。由此形成中央苏区时期上层干部仍以知识分子为主,下层干部则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工农大众为主体。
苏区内的工人、贫农与雇农的文化程度不高,担任党政军群系统内的干部以后,缺乏一定的治事能力。为了充实党的指导机关,加强党的斗争力量,20世纪30年代,上至中共中央,下至各级地方党部,开始大规模培训干部,以此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管理水平和技能。干部训练以及干部的选拔与任用等措施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干部的匮乏,但短期内却很难使干部的整体素质得到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