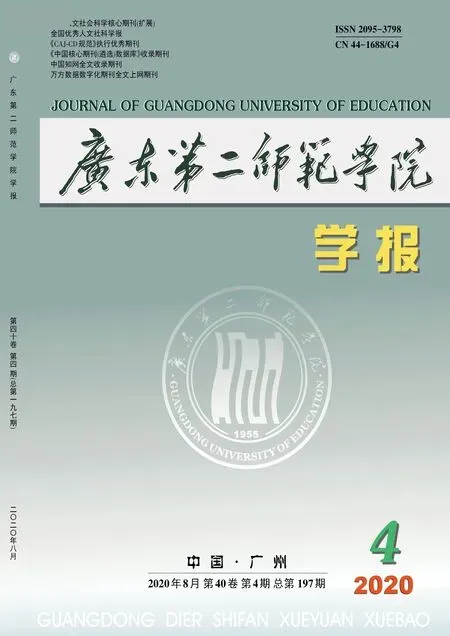乌台诗案前苏轼诗对白居易诗的接受
2020-03-15萧楚敏
萧楚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文学系, 北京 102488)
在元和诗人中,白居易的影响尤其持久和广泛。钱钟书以王禹偁、苏轼、张耒为宋代师法白居易的三位名诗人[1]。《谈艺录》赞赏苏轼《海棠》诗对白居易《惜牡丹》诗的化用“真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者也”[2]307。白居易是“元和诗变”的引领者,苏轼则是塑造宋诗风格的关键人物。二人性情与诗风都有相通之处,且都自觉地对诗风的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北宋的白诗接受史,是宋诗萌芽过程中的一个侧面记录,其研究有助于理解宋诗如何从唐诗中脱胎更生。
古人作诗,往往转益多师、递相师祖。要考察苏轼如何接受白诗,除了分析那些直接涉及白居易的文字,更应从诗人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手法入手,立足于诗歌文本,从化用的角度看苏诗对白诗有怎样的取舍和转化(1)从诗歌接受的角度而言,苏轼诗和白居易诗的关系尚有许多探究的空间。近年张海鸥《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诗学批评》(张海鸥《北宋诗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6-422页)大致梳理了苏诗中涉及白居易的内容,并认为苏轼对白诗的评价是欣赏多于批评;陈才智《苏东坡对白香山的受容与超越——咏梅诗的视角》(冷成金主编《中国苏轼研究(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4页)指出苏轼咏梅是在主动接受白诗的基础上达到审美与品格的结合、升华,从而超越了白诗。。
学界一般认为苏轼对白居易的敬慕始于乌台诗案后谪居黄州期间。当时苏轼自垦一块荒地,命名为“东坡”,因自号“东坡居士”。虽然苏轼没有直接说明,但南宋人早已发现“东坡”与白居易的特殊联系。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就说苏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3]657。同时期的洪迈也认为“苏公责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4],所举例证如“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5]1534“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5]1690等皆是苏轼谪黄州以后的诗。不过稍后的叶寘则认为应提前至苏轼首次至杭州时:“东坡之慕乐天似不尽始黄州,《吊海月辩师》云:‘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时作,已有慕白之意矣。”[6]此论颇值得注意,但仅凭一首诗并不足以表明苏轼慕白。细读苏诗,苏轼对白诗的接受应是经历了数十年渐进式的过程。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之前可视为苏轼人生的前期。以倅杭经历为中心,倅杭前(1037—1071年),苏轼对白诗长期保持疏淡的态度;倅杭时(1071—1074年),苏轼开始重视白居易并大量化用白诗;离杭知密州、徐州、湖州时(1074—1079年),苏轼依然延续对白诗的关注。随着经历的不同,苏轼对白诗的理解和择取有所变化,化用方式和个人诗风也渐趋成熟。
一、倅杭前:少年印象至渐有共鸣
在父亲苏洵的影响下,苏轼至少在12岁时已对白居易有了一定了解。绍圣元年(1094年),59岁的苏轼被贬惠州。他途经虔州时在《天竺寺》诗中回忆: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迭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5]2056
苏洵在虔州天竺寺见到的是白居易的《寄韬光禅师》。钱钟书《谈艺录》谓:“白香山律诗句法多创,尤以《寄韬光禅师》诗,极七律当句对之妙,沾匄后人不浅,东坡《天竺寺》诗至叹为连珠迭璧。”[2]307苏轼一生中至少有四次作诗怀念这首白居易诗,前三次皆是因为杭州的天竺寺而有所联想。可见,父亲的这段话给少年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
白居易、苏轼均是青年时一举登第的科场才子,但苏轼登第后即丧母返乡。嘉祐四年(1059年),苏氏父子第二次出蜀至京师,沿着长江路过忠州到江陵,这一段路也是白居易曾经走过的。唐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自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与元稹、白行简同行,在诗中记载了沿江的地点。苏轼也有一系列诗作:《白帝庙》《入峡》《巫山》《神女庙》《昭君村》《新滩》《黄牛庙》《出峡》《游三游洞》。这些地点与白诗所记几乎重合,但苏轼都没有提及白居易。
白居易一行人游览了黄牛峡石洞并赋诗题字,其《三游洞序》云:“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洞在峡州上二十里北峰下两崖相廞间。”[7]274苏氏父子也是三人同行至此,皆有题咏,而只有苏辙《题三游洞石壁》诗提到了白居易事迹:“昔年有迁客,携手过嵌岩。去我岁三百,游人忽复三。”[8]1416仅仅是到荆州时,苏轼的《荆州十首》其一有“野火烧枯草,东风动绿芒”[5]67两句似是不经意地包含了白居易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9]1042的句意。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入仕,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凤翔在长安西边,两地中间便是盩厔。而白居易登第后的第一任官职即盩厔县尉。苏轼在凤翔的诗渐有化用或暗合白居易诗文的迹象,但还不明显,如寄苏辙诗有:“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5]95宋人赵次公和徐师川已注出这首苏诗很可能是化用白诗“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9]799和“如何为不念,马瘦衣裳单”[9]738。苏轼另外两句诗“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5]120,也颇似白居易的诗句“请君屈十指,为我数交亲”[9]2337。以“屈指可数”歌咏亲情、友情、岁月并非白诗独有的写法,苏诗也未必有意化用白诗,但白诗善于叙述、数量多、描写范围广、影响大,这些因素恐不容忽视。
嘉祐六年(1061年)至治平元年(1065年)在凤翔期间,苏诗涉及白诗主要是出于应酬的需要。首先是与刘敞唱和。刘敞喜好白体平易写实的风格,有诗云:“偶寻乐天诗,往在江州日。”[10]96刘诗《新作石林亭》与白诗《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苏州所寄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见示,兼呈梦得》写法颇为相似,均是以铺排为主,先细致描写了石的来源和样貌,继而从爱石引申为向往归隐之意。刘诗末云“兹焉可娱老,讵厌终岁闲”[10]113,极具白体闲适风味。刘敞与苏轼相交甚欢,苏轼投其所好、借题发挥。白居易《太湖石记》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噫!是石也,千百载后散在天壤之内,转徙隐见,谁复知之?”[7]2059故苏轼《次韵刘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间,刘购得之》先借牛僧孺故事发论,末与白居易诗意暗合:“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尽令属牛氏,刻凿纷斑斑。嗟此本何常,聚散实循环。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区寰。君看刘李末,不能保河关。况此百株石,鸿毛于泰山。但当对石饮,万事付等闲。”[5]98然而,此诗以议论为主,慕白、效白之迹并不明显。
其次,岐山令王绅请苏轼为其“中隐堂”赋诗。“中隐”的概念为白居易所创,出自其《中隐》诗。苏轼所作《中隐堂诗》用语质直,有“好古嗟生晚,偷闲厌久劳。王孙早归隐,尘土污君袍”[5]165四句略近白诗风味。另外,盩厔县有游仙潭、游仙寺,正是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地方,但苏轼两次写纪游诗都没有提及白居易。当一件事缺乏足够的意义,即便遗迹就在眼前,也没有记录乃至歌咏的必要,说明白居易对于苏轼个人的特殊性至此还没有显现。
苏轼在凤翔任满三年,回京不久即居丧至熙宁元年(1068年),那时宋神宗已与王安石达成变法意向,朝野议论纷然,指斥新法者皆被责罚、黜落。苏轼不满新法,亦与王安石不合,升进受阻,还接连被新党污蔑弹劾。于是他主动乞补外任,除杭州通判。在京师的两年,苏轼诗作不多,风格也尚未成熟,但诗中可见不少直接沿袭白诗的地方,如将白诗“未报皇恩归未得,惭君为寄北山文”[9]1087写成“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5]266;将白诗“白发更添今日鬓,青衫犹是去年身”[9]1357“归骑纷纷满九衢,放朝三日为泥涂”[9]1080化用在“良辰乐事古难并,白发青衫我亦歌……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5]238;将白诗“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9]1198简化为“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5]242。苏轼对白居易此类诗语、诗意的沿袭也传达出他在朝为官时失望、冷淡的消极心态。
白居易在朝时曾直言敢谏,论执强鲠,不免为人所忌。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政敌构陷,贬为江州司马,于是效仿元稹作《放言》五首,直抒世事纷杂、真伪难辨、人生虚幻之意,殊为痛彻。其三最具代表性: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9]1234
此时苏轼已略有同感,他的《送蔡冠卿知饶州》诗也直接取用白诗:“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轗轲。”[5]252尽管外任杭州是暂时避祸全身的最佳选择,却与士人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苏轼怀着失落的心情写了不少像白居易那样自我排遣、放逐的诗,最典型的是《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5]282
这首诗化用了白居易的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索索”[9]961和“黄茅冈头秋日晚,苦竹岭上寒月低”[9]920。这两联分别出自《琵琶行》和《山鹧鸪》,均作于江州司马任上,所描绘的迁谪心境甚是凄凉。苏轼虽尚未如此哀伤,但当他离开京师,舟行江上,相似的景色与对政治局势的思考,或许令他逐渐感受到了白居易当时的心情。
二、倅杭时:中隐的体验与反思
元和十五年(819年),白居易自忠州回朝,面对的是牛僧孺、李德裕两党相争的局面。他既与两党中人均有私交,又坚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但不久就离京外任。白居易在杭州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而苏轼倅杭时也致力于此,并曾撰《钱塘六井记》云:“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11]379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称:“杭州巨美,得白、苏而益章,考其治绩怡情,往往酷似。”[12]相比白居易,此时苏轼在政坛上经历尚浅。新法方兴未艾,两党逐渐成形。虽然苏轼不可避免地归入旧党阵营,但从一生的政治立场来看,他就像白居易那样尽可能地在两党中间保持独立。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抵达杭州,先写《初到杭州寄子由二首》向弟弟苏辙表达了内心的惭愧,其“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5]314近似白居易诗“未报皇恩归未得,惭君为寄北山文”[9]1087。在杭三年,秀美的山水、各具妙质的友人纷至沓来,苏轼同时也得以步履白居易的行迹,进一步体验白诗的内容。以杭州为媒介,苏、白二人的思想感情、人生经历的相似之处逐渐展露。现存苏轼诗集中,首次倅杭期间有三百多首诗,大部分是酬赠之作,与白诗相似的句子不胜枚举。
(一)游禅有遗踪
白居易好佛,自言:“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9]2627其《冷泉亭记》也曾提及:“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7]286杭州寺庙众多,苏轼多次前往游览,必然接触到了白居易的遗迹和传说,尤其是在天竺山和灵隐寺。
前文已提及苏轼与白诗《寄韬光禅师》的渊源。上、中、下三座天竺寺就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苏轼少年时的白诗印象至此被唤醒。他先是登望海楼写了“天台桂子为谁香,倦听空阶点夜凉”[5]377,又在《赠上天竺辩才师》中化用作:“南北一山门,上下两天竺。”[5]46
苏轼与灵隐寺两位禅师交好,《释氏稽古略》卷四:“明智大师祖韶……有二弟子,曰慧辩,即海月禅师也;曰元净,即辩才法师也。”[13]二十一年后,苏轼作《海月辩公真赞》自叙初到杭州时“年壮气盛,不安厥官。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闻一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11]638。当时慧辩圆寂,苏轼《吊天竺海月辩师三首》其二云:
生死犹如臂屈伸,情钟我辈一酸辛。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5]479
唐会昌二年(842年),传闻有人误入蓬莱仙境,见有专为白居易所设院落,以其终归道家,故白居易作《答客说》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9]2784又白居易也有凭吊佛门友人的诗《兴果上人殁时题此诀别兼简二林僧社》:“本结菩提香火社,为嫌烦恼电泡身。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9]1366苏轼上述诗作的第三、四句即融会了这两首白诗。他在天竺灵隐寺与海月禅师、辩才禅师的交往,正如三百年前白居易与兴果上人、韬光禅师的友谊。
另外,在杭州孤山上有一座竹阁,内悬白居易画像。宋初《景德传灯录》载竹阁是白居易在杭州时为迎鸟窠禅师所建,有《宿竹阁》诗传世。苏轼由竹联想到白居易曾以《画竹歌》称赞朋友萧悦“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以来唯一人……野塘水边碕岸侧,森森两丛十五茎”[9]926,还想到白居易平生常怀念在渭村闲居的生活,于是一并入诗,为《孤山二咏·竹阁》: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两丛恰似萧郎笔,十亩空怀渭上村。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5]480
白居易以佛教兜率天为归宿,拒绝道教蓬莱仙山。但苏轼的思考更加透彻,在他看来,蓬莱与兜率天都是茫然不可捉摸的虚幻之境。无论人的精神最终归宿何方,他的存在都会成为历史,眼前的竹阁也成了悬挂画像的纪念堂。不过,即使物是人非,白居易依然在人间、在后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二)杭州风流守
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载:“杭州繁华……东坡倅杭,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倅杭为‘酒食地狱’。”[14]苏轼性情开朗,亦善调侃,在杭交游应酬极多,与白居易的世俗烟火气正可相接。世传白居易有樊素、小蛮二妾,被视为风流之事。白晚年因病放妓鬻马,作《不能忘情吟》,序曰:“妓有樊素者,年二十余,绰绰有歌舞态,善唱《杨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闻洛下。”[9]2850白诗还有“莫唱杨柳枝,无肠与君断”[9]2269之句。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载:“(李林宗)尝谓乐天为嗫嚅翁。”[15]100“嗫嚅”即说话吞吞吐吐。其实白居易曾戏称窦巩是“嗫嚅翁”。不料他晚年也被李林宗说是“嗫嚅翁”。范摅所记虽有可能是讹传,但至少宋人接受了这个说法。苏轼此时便喜好以白居易故事入诗,以调侃张先年届八十犹蓄声妓之事,如“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5]421“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5]523。虽然苏轼也堪称一代“风流守”,但自嘲不如当年的白居易。苏诗《苏州闾丘、江君二家,雨中饮酒,二首(其二)》云:“曾把四弦娱白傅,敢将百草斗吴王。从今却笑风流守,画戟空凝宴寝香。”[5]561
白居易诗中的琵琶歌女形象在宋初已经成为经典,即使天才奇纵如苏轼也难以脱出这个审美定式。不论是酬酢还是应演奏者所请,苏轼都一再化用《琵琶行》等白诗,最典型的是《古缠头曲》:
青衫不逢湓浦客,红袖漫插曹纲手。尔来一见哀骀佗,便着臂鞴躬井臼。我惭贫病百不足,强对黄花饮白酒。转关、濩索动有神,雷辊空堂战窗牖。四弦一抹拥袂立,再拜十分为我寿。世人只解锦缠头,与汝作诗传不朽。[5]535
这首诗融汇了大量白居易写琵琶的素材:“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9]2058“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就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9]920“四弦千遍语,一曲万重情”[9]1944等皆被苏轼取用糅合,加以锻炼重塑。显然苏轼也进一步感受到自己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在诗中频借江州司马的形象自况,萦绕着天涯流落的谴谪意。
另外,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与友人聚会,戏称“七老会”,有诗云:“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9]2805这种高龄退休官僚的“尚齿会”以“尚齿不尚官”为儒雅之举,在宋代颇受追捧[16]。苏轼《赠张、刁二老》化用作:“两邦山水未凄凉,二老风流总健强。共成一百七十岁,各饮三万六千觞。”[5]568在诗中陈列数字以记录年龄、岁月和俸禄是白诗写实、浅俗的特色之一,是个人趣味,也可以说是“恶趣”。苏轼意在谐谑,为盛赞张先、刁约二老之寿,用了白居易的数字加法为诗。清代纪昀就曾批评此诗“疵累太重,三四乃香山野调。”[17]将尘俗佐欢之事以直白诙谐的语言入诗,势必降低诗作的艺术水准。但在此洒脱放旷之际,白居易和苏轼都保留了诗歌冲口而出的那种情真意切、自然天成。
(三)使君聊中隐
欢愉之外也不免有落寞的时候,此时苏轼约38岁,岁月流逝、才志难伸的愁困与日俱增。他也像过去的诗人一样,设想或许最好的生活是早早罢官,和好友相约隐居。在酬酢时,苏轼常借白诗表达一个闲官的安分自守和出尘之想,不少造语明显取自白诗。例如,白诗有“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欢娱接宾客,饱暖及妻儿”[9]2797,苏轼则化为“君恩饱暖及尔孥,才者不闲拙者娱”[5]319;白诗有“因咏松雪句,永怀鸾鹤姿”[9]880,苏轼则写“羡君超然鸾鹤姿,江湖欲下还飞去”[5]334;白诗有“厌听秋猿催下泪,喜闻春鸟劝提壶”[9]1278,苏诗写作“如今胜事无人共,花下壶卢鸟劝提”[5]335;又如白诗写“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9]1172,苏诗写“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5]401。以上苏诗已非对诗意的直接沿袭重写,而是取用白诗的“陈言”添加新意写出,比原作更出色,正体现了宋诗“以故为新”的追求。
白居易颇多叹老之辞,苏轼尤其欣赏白诗中“白发感秋”“黄鸡白日”的写法。白诗《曲江感秋二首》其一写道:“晚遇何足言,白发映朱绂。销沉昔意气,改换旧容质。独有曲江秋,风烟如往日。”[9]744《醉歌》则更加生动:“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9]974苏轼将自己和友人放入上述白诗的语境中,又试图以豪放的态度解除对白发的警惧,其诗《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云:
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试呼白发感秋人,令唱黄鸡催晓曲。与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叶空残绿。黄鸡催晓不须愁,老尽世人非我独。[5]450
对于苏轼而言,即使有世人陪伴着他一起老去,面对青山,心中仍然不免遗憾。白居易曾在《自题写真》自叹:“宜当早罢去,收取云泉身。”[9]519苏轼化用为“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年来白发惊秋速,长恐青山与世新”[5]527。白诗为苏诗提供了不少现成的表达方式,两个时代、两种人生的叠加,更增添了诗意的厚度,苏轼对白诗的熟悉程度也可见一斑。另外,苏轼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一)》中有“病眼不眠非守岁”[5]533一句,直接用了白居易《除夜》的句子“病眼少眠非守岁”[9]2220,只改动一个字。这可能是苏轼觉得白诗确实应景,有意而为;也可能是苏轼向来喜好此句,不自觉取而用之。正如黄庭坚《谪居黔南十首》实为白居易诗句,可能是误记,也可能是摘句。但至少可以证明部分白诗得到了苏、黄的肯定,并在他们的诗歌记忆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在怀才不遇的人生困境里,除了惆怅与伤感,白居易还提出“中隐”的生存模式,其《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9]1765“中隐”的思路很受欢迎,而且白居易也实践并记录了自己官居“偷闲”的生活方式,其《和裴相公傍水绝句》:“行寻春水坐看山,早出中书晚未还。为报野僧岩客道,偷闲气味胜长闲。”[9]2877如此舒适,岂不诱人?深研庄子思想的苏轼也常歌咏随遇而安、旷然自放的生活态度,但他此时依然保有一股不甘心的锐气,《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曰: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5]339
苏轼并不认同白居易那接近尸位素餐的“中隐”模式。晋王康琚《反招隐》定义了“小隐隐林薮,大隐隐市朝”[18]。苏轼认为要隐居就应该彻底抛弃官职、长久地融入这美好湖山,而不是在案牍公事之间“偷闲”,更不应以此沾沾自喜。作为寄身天地之间的一个无家客,苏轼发现杭州正是宜居之地。然而这只是一时的痛快语。苏轼既不满于白居易的“中隐”模式,自己却又不上不下,无法挣脱,故他一方面在地方上勤于任事、颇有政绩;另一方面又借白居易自比为闲官,用以自嘲。
西湖依旧那么美,杭州的风土人情仿佛延续着三百年前白居易所见到的模样。苏轼在生活中体验了白居易的诗景、诗境、诗情,心领神会或有所触动时,熟悉的白式诗语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升华,他关于白居易的思考也围绕着对“中隐”生活的反思。可以说,第一次到杭州时,苏轼才真正开始注意白诗并大量化用,但他对白居易的认识一直伴随着理性的思考,未达到敬慕的程度。
三、离杭后:推称自托与乐天知命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离开杭州后接连到密州、徐州、湖州为官。在尚未抵达密州时,他就先与朋友戏说“云雨休排神女车,忠州老病畏人夸”[5]596。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载:“秭归县繁知一,闻白乐天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15]83十五年前,苏轼过巫山时写了不少诗,未曾提及白居易,如今却主动调侃自己为“忠州老病”。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苏轼一直保持着这种随时将自己与白居易联系起来的习惯。
(一)点破“自托”,直言“白俗”
苏轼在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抵达密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离开。在此期间,苏轼困于谪臣、闲官的身份,在诗中多借用白居易年老、萧索的形象,在怀念杭州、感叹岁月这两个主题中接续了白居易曾经的人生蹉跎之感。而这段时间所作《醉白堂记》与《祭柳子玉文》则直接展示了他对白居易的理性思考。
白居易曾在一次宴会中写下“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3]153之句。密州偏僻,不比杭州秀美繁华。苏轼已经远离了“笙歌鼎沸”,只好以诗自遣:“莫笑吟诗淡生活,当令阿买为君书。”[5]619张先来诗,令苏轼怀念起孤山的竹阁,苏诗《和张子野见忆三绝句·竹阁见忆》云:“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5]652白居易、苏轼都是杭州的过客,不知如今西湖美景又是谁在观赏、谁在吟咏?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曾感叹“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9]1236,苏诗《和晁同年九日见寄》化用作:“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遣子穷愁天有意,吴中山水要清诗。”[5]696
此时,40岁的苏轼对岁月如流的焦灼感屡形于诗。他修葺了一个废台,由苏辙命名“超然台”,理由在《超然台赋叙》中:“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8]331如此,超然台应该可以为苏轼暂纾苦闷。但在《和潞公超然台次韵》诗中,苏轼“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浅屡言深”[5]681的自嘲才是“超然”背后的真实心情。自问,既不能有用于世,何不全身避祸,及时行乐?白居易诗中的这些人生之思,尚且历历在目,其中不少经典诗句被苏轼点化重现,举例对比如下。
白居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9]970
苏轼:也知不作坚牢玉,无奈能开顷刻花。[5]605
白居易: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9]2090
苏轼:光阴等敲石,过眼不容玩。[5]614
苏轼:春来六十日,笑口几回开。[5]618
白居易: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9]1314
苏轼:民病何时休,吏职不可越。慎毋及世事,向空书咄咄。[5]685
白居易:朱颜今日虽欺我,白发他时不放君。[9]1385
苏轼:念当急行乐,白发不汝放。[5]690
以上苏诗全仿白诗的句意,只是锻炼得更加雅致圆熟。白居易对人生的思索是理智而通透的,他的诗语也极为擅长描写,即张戒《岁寒堂诗话》所谓“道得人心中事”[19]。以上几句白诗写出了人世间颠扑不破的道理,尤其那句“石火光中寄此身”的一个“寄”字,是苏轼尽其一生反复感受的主题。
熙宁八年(1075年),宰相韩琦逝世。韩琦曾以“醉白”为堂名,其《醉白堂》诗曰:“人生所适贵自适,斯适岂异白乐天?”[20]苏轼应其后人嘱托写了《醉白堂记》,文中论述韩琦与白居易的异同,就“醉白堂”的意义赞颂韩琦的品格。“忠言嘉谟,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与乐天之所同也。”[11]334这是宋代士大夫对白居易普遍的认同。然而,文末苏轼又写:“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将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非独自比于乐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虚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实浮于名,而世诵其美不厌。”[11]334这几句话点破时人推称白居易的目的是“自托”,苏轼还对白居易的“醉”表达了不满。白居易虽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获得闲适的合理性,但其《池上篇》《醉吟先生传》所提倡的生活过分依赖于物质条件。比起庄子哲学,白氏思想的放达虽是不彻底的,却十分贴近世俗幸福。苏轼客气地表示,韩琦应该比白居易的境界更高,只是谦虚地自托于白。这番批判仿佛预见了未来那位经历暴风骤雨之后自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5]1762的“苏东坡”。
两年后,苏轼甫离密州,而柳瑾卒。苏轼作《祭柳子玉文》盛赞其文学成就,并以四位唐代诗人作对比衬托,其中有:“独以诗鸣,天锡雄咮。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11]1938于是,后人往往误以“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为否定四家之论,乃至于讨论苏轼对白居易评价的前后矛盾。稍晚于苏轼的许顗解释了这个现象,其《彦周诗话》云:“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3]384许顗的解释未必合理,却说明当时宋人对白诗的评价已存在明显的矛盾,大诗人苏轼对白诗的态度更受到关注并影响了时人对白居易的看法。苏轼对文学有敏锐的嗅觉,他指出四家诗风的缺陷并不是对其成就一概抹杀。“白俗”之说表明:苏轼对白居易的人格和诗风早已有明确的判断和选择性接受。况且,浅切世俗本就是白诗创作的主要特色之一。苏轼称柳瑾为“雄咮”,则是认为“雄”可以敌“轻”“俗”“寒”“瘦”四种导致诗风疲弱的弊病。
(二)乐天知命,醉吟无忧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罢密州任,尚未进入京师就接到改知徐州的诏令。在徐州的两年间,岁月蹉跎之感进一步加深,苏轼渐以“乐天知命”的精神自振。他先是为司马光赋《司马君实独乐园》诗,有明显的白诗风味,尤其是“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5]732数句。明代胡应麟《诗薮》认为这四句是苏轼对白居易的模拟:“此乐天声口耳,而坡学之不已。”[21]因为白居易著名的《池上篇》就有“十亩之宅,五亩之园”[9]2845。这既有苏轼本人熟悉白诗的缘故,也与司马光喜好白居易以及社会崇白风尚有关。宋代龚颐正《芥隐笔记》称:“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22]苏轼虽然偶尔唱反调,却也不得不承认白居易一生处世的成功之处。在徐州,苏轼常直接借白诗表达自己的乐观放达,对比如下。
白居易: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9]977
白居易: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9]2629
苏轼: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不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乐天知命我无忧。[5]739
白居易:明朝又拟亲杯酒,今夕先闻理管弦。方丈若能来问疾,不妨兼有散花天。[9]2523
苏轼:醉吟不耐攲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结习渐消留不住,却须还与散花天。[5]805
白居易:鸡鸣一觉睡,不博早朝人。[9]2523
苏轼:功名正自妨行乐,迎送才堪博早朝。[5]818
“乐天知命”而无忧、“醉吟”而不拘礼节、嫌弃功名妨碍行乐、夜饮听歌时感受时光飞逝的“使君”本人,正是公事之余的苏轼“自画像”。苏轼的化用不是单纯取用白居易的造语,而是兼用诗意和白居易本人的形象,层层叠加。在这类诗境中,他暂时避开对白居易的不满,而是像白居易一样用安适乐观的心态抵抗郁郁不得志的现实。
徐州的朱陈村曾令白居易十分歆羡,其诗《朱陈村》描述村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9]777,宛如世外桃源。苏轼在徐州任上亦曾入村劝农,虽然当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两年后在黄州见到陈慥收藏的《朱陈村嫁娶图》时,苏轼十分感慨,化用白诗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叙述他在徐州时的经历:
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5]1029
白诗所述朱陈村、苏轼亲历的朱陈村,以及在黄州所见图画中的朱陈村三者得以跨时空联系起来。待到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返京师后还写诗重提此事:“奉引拾遗叨侍从,思归少傅羡朱陈”[5]1448。
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已对仕途不抱希望,他写信给范百嘉说:“承盐局乃尔繁重,君何故去逸而就劳,有可以脱去之道乎?外郡虽粗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时辰许纷纷,余萧然皆我有也。”[11]2492苏轼数次乞郡,第二年终于等来改知湖州的诏令。湖州近苏、杭,苏轼可谓如愿,时有《泗州过仓中刘景文老兄戏赠一绝》:“既聚伏波米,还数魏舒筹。应笑苏夫子,侥幸得湖州。”[5]2530白居易有《初到江州》诗云:“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9]1241苏轼这个时候写的“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5]935似乎已将自己当作那位“白使君”了。不同的是,白居易以谴谪远方为苦厄,而苏轼则全反其意。他用佛教语对僧人朋友表示,他将如达摩那样以心相随,使百姓安适,如此就算走遍天涯,他也觉得尚未尽兴。
白居易:春生何处闇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9]1355
苏轼: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5]944
在赴湖州的路上,苏轼应邀作《灵壁张氏园亭记》并借此表达了对“仕”的看法:“不必仕,不必不仕……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11]369带着这种不汲汲于功名富贵的想法,苏轼决定在湖州买田问舍,过上像白居易晚年那样的“中隐”生活。
(三)消极落寞,感同身受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湖州谢上表》有言:“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11]654谦恭洒脱的言语背后是一位孤介忠臣的失望与颓唐。在湖州,苏轼表面上如愿得一闲官,实际是主动走向了违背初心的人生低谷。在空虚、寂寞与饥贫的描写中,苏轼对白诗中的落寞与痛苦更多了一些感同身受。他注意的不再是白居易的闲适、风流、欢愉或世俗,而是悲吟。这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及其诗的体悟更进一步。
苏轼赏花时曾见桃花、杏花早开,便戏称“余波尚涓滴,乞与居易、稹。尔来谁复见,前辈风流尽”[5]962。白居易、元稹已作古,苏轼最初乐观地觉得自己和朋友也可以接续前辈风流。然而,远离理想的生活更多充斥着贫穷和寂寞。苏诗选取了白诗的诗材,但笔下的心情一改之前的达观,显得比白诗更加困苦。
白居易:客去有余趣,竟夕独酣歌。[9]507
苏轼:不知何所乐,竟夕独酣歌。[5]966
白居易:静将鹤为伴,闲与云相似。[9]2313
苏轼:使君闲如云,欲出谁肯伴。[5]974
这两首白诗保持着苦中作乐的习惯,而苏轼则不加掩饰,直接取消那份自欺欺人的乐趣。陈寅恪称白居易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23]。然而苏轼与白居易不同,他的天性更加自由、奔放和纯粹,目前的人生经历并不能让他“知足”。相比白诗《和祝苍华》中“痛饮困连宵,悲吟饥过午”[9]1730的状态,苏轼亲身体验的困苦有过之而无不及。白诗所写,尚有痛快畅饮与悲慨吟咏的能耐,反观苏诗《次韵李公择梅花》,他所写的是诗人在困饿至极时的理性思考与平静忍受,而非怨天尤人:“诗人固长贫,日午饥未动。偶然得一饱,万象困嘲弄。寻花不论命,爱雪长忍冻。天公非不怜,听饱即喧哄。”[5]978这就是与唐诗大不相同的宋格。
自倅杭以来数年,苏轼的日常生活常常能与白诗的内容对应。在密州、徐州、湖州期间,苏轼的诗风渐趋成熟,对白诗的化用方式也频出新意。他有时将自己比作白居易,有时又借诗与白居易对话。这里也显示出苏轼写诗文喜好翻案的特点。苏诗中最常见的化用方式是取白诗的“陈言”,反其意写出,即黄庭坚所谓“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24]的“点铁成金”之法。
不过,苏轼在湖州的生活没有持续下去。三个月后,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摄苏轼前往御史台,“乌台诗案”开启了苏轼的后半段人生。此后,苏轼更加需要从白居易身上汲取“乐天知命”的精神力量,他的诗风即将进入转折期,对白诗的接受也将有所不同。
四、结语
严羽《沧浪诗话》描述北宋诗坛:“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3]688白诗的影响力随着宋诗的成长逐渐受到审视、反思和削弱。尽管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7]324的诗学主张与宋人的诉求一致,但随着宋人对诗人的才、学、识和诗歌艺术的精炼含蓄提出更高的要求,白诗的浅直周详就遭到了嫌弃。陈师道的批评很有代表性:“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3]304陶渊明、杜甫、韩愈的诗逐渐被宋人认可并标举为最高典范,同时白居易诗的影响力下降。白居易诗在浩瀚诗国中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存在,这导致了他不适宜被摆上神坛,同时也注定了他能够游走人间、感动世俗,在诗史上留下深刻印痕,成为宋诗的重要源流之一。
根据前文的分析,苏轼对白诗的接受是在人生体验中渐进式完成的,伴随着他从效仿唐诗到开创宋调的过程。苏轼少年时已得到父亲传达的白诗印象;青年时他对白居易的态度较为疏淡,即使亲自游览江岸、盩厔的白居易遗迹,也没有在诗文中提及;入京后,苏轼开始注意白诗,更因为亲历了政治风波而渐有共鸣;直到首次倅杭时,天竺寺令苏轼重温记忆中的白诗,杭州的风土人情和遗迹也让他就地体验了白诗的内容。至此,苏轼才真正开始重视并大量化用白诗。其后在在密州、徐州、湖州,苏轼对白诗的化用逐渐显示出“以故为新”的宋诗特色。
历史上的白居易是否真的能够成为苏轼的异代知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苏轼并不赞成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只是终于无奈地接受了这种模式。他很清楚白诗既浅易又世俗,但依然能择其善者化为己用。乌台诗案前,苏轼可勉强称作“闲官”,那时他曾对白居易过分依赖物质生活表示不满;乌台诗案后,首先是在黄州期间,苏轼成了被安置的罪臣,可当生活离闲适愈遥远,苏轼愈是能坦然地自比白居易。所以,与其说苏轼因与白居易人生经历相似而产生敬慕之意,不如说是他通过诗歌接受的方式,主动选择并进一步强化了白居易的“乐天”精神,同时削弱了“中隐”的意义。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将再次告别杭州,他感慨道:“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5]1762人生前期所积累的对白诗的感受在此时才正式转为深刻的认同,即使这份认同也包含了苏轼的寓托和自嘲。绍圣四年(1097年)渡海到琼州以后,苏轼对白诗的热情就淡化了,因为他最终确认自己的精神榜样是白居易也敬仰的陶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