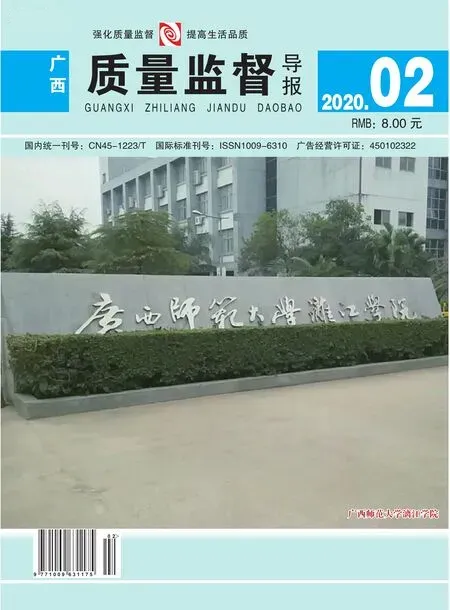非常时期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思考
2020-03-14王乐乐
王乐乐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0)
引言
近期,受非常时期影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劳动关系考验着劳动法的适用性与灵活性。部分行业企业面临较大的生产经营压力,劳动者面临待岗、失业、收入减少等风险,致使劳动关系不稳定因素增强,劳动关系矛盾逐步激化。更有甚者,许多企业因为延期复工政策、人员无法返回、物流不通、原材料等缺乏原因,无法正常复工或完全复工,但同时仍需承担房租、人员等成本,流动资金压力颇大,因此一些企业开始裁员,直接通知全体或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当前,肺炎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省市关于延迟复工、加班工资、工伤认定的通知也在陆续发布。同时,从非常时期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和经济发展的新矛盾来看,恰当平衡劳动者与企业利益,适当财政帮扶税收减免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出台相应政策稳定劳动关系,以有效缓解社会与经济发展矛盾。
一、非常时期下的劳动关系现状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纷纷启动疫情一级响应,神州大地掀起抗击疫情的浪潮,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包括隔离、封城、交通管制、延长春节假期、集中收治等一系列措施。该等情形下,在劳动关系的建立、履行、解除、终止以及劳动争议之处理、劳动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可能引发一系列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新问题。如: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关于企业停产停工后工资、病假、工伤、加班、休假等问题的认定与计算方法;劳动关系的解除与终止等。
为降低企业疫情传播的风险,应人社部门呼吁①,部分企业按机构运作需要,就雇员的工作安排做出弹性处理。重新整理工作日程表以减少会议量,并在资讯科技的帮助下,如使用视频电话会议等,减少人与人的直接接触。除了提供紧急和必须的服务外,企业通过安排雇员在家办公无需返回工作地点。然而,此种办公形式虽然有效控制了人传人的风险,却极易引发劳资双方的不满。劳动者进行全日制劳动却只能领取到待岗工资,企业效益低却不得不负担高额人力成本。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复工企业中部分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必须到工作地点的岗位实施灵活用工措施,与职工协商采取错时上下班、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对承担政府疫情防控保障任务需要紧急加班的企业,在确保排除新冠肺炎传染可能性与全面消毒的前提下,经与职工协商后,适当延长工作时间应对紧急生产任务,依法不受延长工作时间的限制。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互联网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员工受疫情影响主要表现为居家办公的工作效率不若在办公场所,工作氛围与灵感较弱。相较于体力劳动者而言所受影响较小,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之体力劳动者则深受疫情之害,无劳动则低收入的局面实为尴尬。
二、非常时期劳动关系呼唤劳动法的应急性
由于疫情的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以及企业预紧机制的缺失,劳动关系陷入突发性动荡。劳动者面临生命与生存的抉择,企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而且,我国劳动法关于非常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规定局限于原则性,且可操作性不强。目前涉及疫情期间工资发放问题的法律条文,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②与《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2020年1月24日发布)与相关规定。对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工伤认定仅有《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③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会保险经办工作的通知》这三个政策性文件可以适用。《劳动法》第四十二条与《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条文说明》有涉及到疫情期间加班问题,但并没有相关加班工资应如何认定的说明。鉴于上述所言,各级政府与人社部门积极出台稳定劳动关系的相关措施,尤其是工资发放、工伤认定、加班安排等有关劳动者生活维系的权益。
受疫情的影响,国内很多企业陷入了断崖式经济效益下滑的不利局面。此种境地下,通过优化劳动力要素的灵活性配置,实现对劳动力成本的有效控制,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最理想的选择。在由于疫情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测性,企业无法在短期内有效优化劳动力资源,解雇和适当降低待遇的方式带有极高的法律风险。劳动法为了防止企业滥用解雇的权利,通过制度对其进行了限制。但这种限制的适度性有待商榷,此类限制应当为企业解雇权利的正常行使保留足够的余地以保障劳动关系的灵活性。然而,我国当前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体系却对企业的解雇权进行了过度严厉的限制。
三、非常时期劳动法适用的困境
在疫情的影响下,企业为了度过经济不景气的困难时期,必然会加强对企业成本的控制。停产停工时期,人力资源成本占总体成本极大的比重,由此,控制人力成本以降低整体劳动力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然而,在当前以《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劳动法体系下,固于常态化立法思维,缺乏非常时期调整劳动关系的规范及沟通协调机制,企业采取正常的降低工资的手段很难取得劳动者的谅解,从而陷入了人力资源成本过高的困境。
劳动法之所以对劳动者利益保护实施倾斜政策,是因为相对于企业来说,作为自然人的劳动者天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必须通过法律对劳动者的倾斜性保护,才能弥补这种弱势对劳动者造成的不利局面。然而,疫情当下,企业与劳动者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仍旧不区分企业和劳动者的具体情况,一刀切的刻板保护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劳资双方利益失衡,从而对相关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劳动者利益的保护产生了相应的负面作用。劳动法刻板保护模式造成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劳动法并没有根据疫情对企业的影响对其进行详细的分类,而是适用统一的法律标准。另一方面,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同样不区分具体对象,对所有劳动者一视同仁。事实上,同企业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类似,劳动者的具体情况同样千差万别。劳动法当前的这种刻板保护模式,进一步削弱了作为疫情攻坚者的小微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并增加了强势劳动者滥用权利的可能,从整体上不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劳动者利益的保护,成为非常时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障碍。
四、非常时期劳动法与劳动关系适配的思考
在非常时期的防控中,劳动法体系中缺乏非常时期劳动关系维护的应对措施这一不足已经暴露出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劳动法律体系,是疫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关系领域,这次疫情体现出的是各类企业应急准备不足。疫情非常时期,企业与慌乱中只想到降薪裁员等减成本的措施而不是增收益的良策,这和劳动法律体系对应急准备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关系密切。
基于以上问题,对于疫情过后,调整非常时期劳动法与劳动关系的适配问题有几点思考。首先,完善劳动法律体系中的应急预案和管理制度,提升相关应急体系的实施效能。立足劳动关系应急法的特殊性,强化企业应急准备制度,强化政府支持。不能用平常的眼光看待应急法的制定和实施,应急法有弹性、有原则性的一面,突出地体现在应急决策和应急处置方面,也有刚性、有细致具体的一面,突出地体现在应急准备方面。
其次,企业存亡与员工权益两者需要找一个平衡点,各方均能扛过疫情战!在此劳资力量对比不明显之时,对于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应分类别。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同时兼顾企业的利益。根据企业和劳动者受疫情影响具体情况的不同进行分层分类的保护。一方面,需要根据抗风险能力对企业进行划分,建立抗风险能力低的企业劳动法有限豁免制度。对于确实难以承受疫情风险的企业,允许对其实行一定程度的豁免。从而使此类企业摆脱疫情带来的经济风险,保证其在逆境生存。另一方面,对劳动者实行分层保护。尽管当前劳动法通过工作时间、工作性质等规定,对不同劳动者进行了一定的区分,但远无法适应非常时期下针对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进行分层保护的要求。劳动法在非常时期的劳动关系中应当在将劳动者工作受疫情影响的强弱分成感染劳动者、待岗劳动者、居家办公劳动者、一线劳动者。在此基础上,对于感染劳动者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与《劳动法》相关规定侧重于其工资与社保权益的保障;对于待岗劳动者按照相关规定侧重于稳定劳动关系及待岗工资的保护;对于居家办公者按照劳动法规定进行一般保护即可;而对于一线工作人员应当着重保障其基本劳动权益尤其是工伤保险待遇。通过分类保护,在减轻弱抗风险能力企业的劳动法义务负担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对不同劳动者的保护力度,促进企业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为疫情非常时期企业与劳动者共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良好的劳动法保障基础。
五、结语
疫情在华夏儿女的共同努力下,终将会过去。但教训与经验不应随之流逝。在反思与总结中,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立法理念,从劳动法与应急法的本质要求出发,将其有效结合。全面更新劳动关系领域的应急准备制度,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柔性与刚性兼顾,适当体现规范的灵活性,才能避免在下一次公共危机来临时重蹈覆辙。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与职工共渡难关是疫情当前的重要工作,统筹处理好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优势,坚定信心、积极作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注释:
① 对因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的,要指导企业主动与职工沟通,有条件的企业可安排职工通过电话、网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在家上班完成工作任务;对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要指导企业工会积极动员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在兼顾企业和劳动者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帮助企业尽可能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的损失。
②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隔离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决定并宣布。
③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