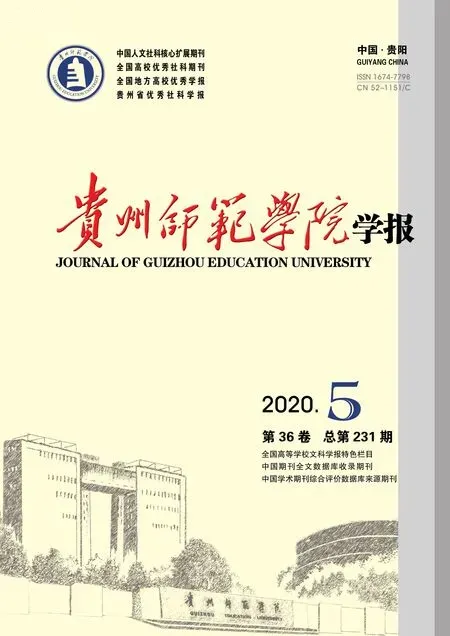莫友芝诗歌中的灾害书写探析
2020-03-14卢芮青
卢芮青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古往今来,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体认从未间断。早在先秦时期,对此关系的论断已见诸文献,《庄子·达生》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1]《孟子·梁惠王上》云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2]孟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置于“王道”施行的高度,可见其重要性。古人对于人与自然思想的建构,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能够正确对待“自然”这一生存环境:一方面自然提供给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文学上,围绕着“灾害”这一题材的文学创作,构成了别具一格的“灾害文学”。
纵观西南巨儒莫友芝的一生,其笔耕不辍、著作颇丰,与郑珍齐名,以“郑莫”之称享誉晚清诗坛。《清史稿·莫与俦传》评其“西南大师”[3]618,张之洞言其“蚤年高名动帝都”[4]182,曾国藩誉其“西南硕儒”[4]616,黎庶昌称其“黔中固有此宿学邪!”[5]。由是,晚清黔中言学者,皆以郑、莫并称,可谓声名显彰,观其诗歌之间对于晚清之际暴乱、疾病、死丧、饥馑、战争的书写,无不体现出其对社会现状的愁闷、痛楚和无奈。诗人对于灾害的书写往往所及甚深,情凄意切,以至姚永概言:“生平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6]之所以有这种情况,首先与莫友芝所生活的时代内忧外患不断、天灾人祸盛行、灾害连年、民生多艰的社会现实有关。其次也与作为诗人的莫友芝所具有的家国情怀与忧国忧民之心息息相连。此外,莫友芝终生未仕,有与师长、门生晚辈及一般民众广泛接触的经历,能更多地站在底层民众立场,加深了其对于衰世中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体验。故而对莫友芝灾害诗的研究,可一窥晚清时期的社会面貌及莫诗之风格,对莫友芝人格形象的丰满以及诗歌风格的理解亦有所帮助。
一、莫友芝诗歌中的灾害书写
莫友芝所生活的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正是皇权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日暮穷途之际。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对于“衰世”论言:“道路荒而畔岸堕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7]龚自珍同处晚清之际,此番论述置诸晚清亦堪称确论。清末内忧外患不断、天灾人祸不绝,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
盖清代灾害之频数,总计达一千一百二十一次,较明代尤为繁密也。此一千一百二十一次灾害之分配如下:旱灾二〇一,水灾一九二,地震一六九,雹灾一三一,风灾九七,蝗灾九三,歉饥九〇,疫灾七四,霜雪之灾七四。[8]28
清代立国近三百年,灾害计一千余次,可谓灾害频频,而莫友芝既生于清代,又遍游黔地,滞留京师,游历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等地。从作曾国藩幕府逾十年,到病逝客舟,这些经历使他视野更加开阔,对于连年不断的灾害体验也更加深刻,对于底层民众的苦难亦更加感同身受。而这一切,皆充分体现于其灾害诗之中。
(一)旱灾
上古先民认为,旱灾是由传说中的怪物“旱魃”所引起的。《诗经·大雅·云汉》云:“旱魃为虐,如惔如焚。”[9]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别集下》载:“金贞祐初, 洛阳大旱。登封西吉成村有旱魃为虐, 父老云:‘旱, 魃至, 必有火光, 即魃也。’少年辈入昏凭高望之, 果见火光入农家, 以大棓击之, 火焰散乱有声如驼。”[10]从描述中可知民间早有“打旱魃”这一风俗。清一代,旱灾尤甚。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对清代灾害次数的统计,可知旱灾在清代是较为常见的自然灾害。
莫友芝对于旱灾的描写颇多。夏日天气本就炎热,若逢旱灾之年,雨泽稀少,旱情迅速发展,炎热的天气还会持续到秋天,如《八月丁卯同宋龟峰、李庚仙登湘山,时秋旱酷热未退》诗中:“甲子丙寅丙不验,火云八月未曾收。学堂无计消残暑,僧径相携问古秋。”[11]123因连月炎热不退,人人争寻古木以求荫凉。“祝融不廉侵蓐收,白露有节无清秋。”[11]324(《八月六日吉堂招集云麓精舍,时秋热益酷,午后迅雷无雨》)诗人用火神祝融来形容天气之炎热,本是白露节气,却因旱热以至毫无秋高露爽之意。酷热的天气除了会让人身体上倍感不适之外,对于一年农事亦深有影响。《初夏乐安道中》言:“龟兆秧田低且坼。”[11]108诗人在仲春时节路过黄河以北地区时看见:“二月桑榆无信息,三时云汉剧辉光。”[11]207(《大河北百里间,自去秋至今无雨雪》)本该是万物复苏的时节,但桑榆之类的树木毫无萌芽之意,只见天空行夏天的时令。干旱对农作物的生长带来了很大伤害,庄稼减产,甚者颗粒无收,这对于以农为业的农夫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莫友芝在描写旱灾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其忧心如焚,恨不得自己变成可以呼风唤雨的神,发出强烈的呼声,如:“何当手挽昆仑水,遍洒中原作岁康。”[11]208(《大河北百里间,自去秋至今无雨雪》)当久旱逢干露时农民们忙着:“山农水犊同一忙,晚豆迟秧未为失。”[11]186(《喜雨》)之时,他也“笠屐正宜沾湿好”[11]186(《喜雨》)表现出与农共喜的心情。
在莫友芝的诗歌中还描写了这样一种情形,当人们面对天灾无可奈何时,会举行祈雨仪式,祈求天降甘霖。《和东坡<起伏龙行>·序》言:“南中久旱,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道光丙午夏,贵阳旱甚且火,当事者依法试诸城北龙潭而效,偶和苏诗,蒙亦成此。”[11]189此指虎骨祈雨之法,宋代苏轼《起伏龙行》云:“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南山雪毛虎……赤龙白虎战明日,倒卷黄河作飞雨。”[12]所指正是以虎头骨祈雨之事。据《太平广记》引唐李绰《尚书故实》载:“南中旱,即以长绳系虎头骨,投有龙处。入水,即数人牵制不定。俄顷,云起潭中,雨以随降。”[13]可见这一习俗或在唐时已经存在,另莫友芝诗中还描写了祈雨的应验情况:“夏甘流润满湘山”[11]50(《和太守悯头白担夫之作》)。
(二)水灾
雨少则旱,多则涝。与旱热一样,水灾也是清代发生频率较高的灾害。对此,莫友芝诗中亦多有反映:“久雨百草糜,势大更猖狂。”[11]23(《秋间杂兴》(其十))“日月供淫雨,乾坤剩草堂。”[11]187(《喜雨》)“暑雨断人行,渭水那可渡。”[11]238(《送张子佩归黔西》)可见久雨之后,草木糜烂、物舍坍塌、人行不便,又是一番惨象。在久雨不停之时,莫友芝往往幻想能倚剑挥天,斩却负责降雨的顽龙:“久雨望晴不绝雨,比旱望雨心更苦。恨无长剑倚天挥,斩却顽龙致干土。”[11]56(《喜霁定,步出来青,适得方仲坚同游,晚归双荐,用前韵》)可见久雨成灾之下诗人的苦恼与无奈。
莫友芝对水患的关注绝非停留至此,其中还有部分反映因水患造成农业灾害、民间疾苦的诗作。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诗人在赴京会试途中,路过湖北碰到了荆江惨遭水患,写下了《公安县》《李家口》为代表的诗歌。诗中描写了长江北岸的部分地区从原来的鱼米之乡惨变泽国,水灾后的公安县:“频年虚井税,结网当春耕。天地此洼县,江湖非吕营。北风吹野水,寒日下孤城。莽莽无人径,萧萧芦荻声。”[11]204(《公安县》)水患后的城市村庄似孤城一样,没有烟火气、没有喧闹声,萧萧的芦荻声穿梭在耳旁就像进入无人之地,满目凄凉。接着诗人在路过李家口时写道:“率略两三户,荒凉前后程。无从寻旧驿,迷望一心惊。”[11]204(《李家口》)驱车路过此地时,只见稀稀落落两三户人家,旧时休息停靠的驿站也无迹可寻,心中的悲凉之情更是油然而生。“一人既数死,数死才一瞬。”[11]454(《镇远水十一首》(其四))“乱瓦积淤泥,隤椽或山根。”[11]453(《遵乱纪事》(其二))诗人在路过镇远时,此地遭洪灾,人烟稀少,洪水把村庄、土地全都淹没,一片惨象。
(三)兵祸
兵祸类诗作亦是莫友芝灾害诗的一大特色,莫友芝在书写这类诗歌时敢于正视社会的现实,敢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官吏的丑行。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并不亚于天灾,晚清之际贵州地区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莫友芝身处其间,对于战乱之苦体悟甚深,皆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之中。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六日以杨龙喜领导的起义军兵围遵义城,“九坝之贼来未来,桐梓城门不敢开。儿啼女哭缒城走,县官千总空裴怀。”[11]290(《遵乱纪事》(其二))当居民听见九坝起义的风声后,纷纷都缒城逃走。一片慌乱景象,人心惶惶。又如:“稀稀朗朗天上星,密密拶拶城头灯。街街巷巷铃铎紧,门门户户刀枪明。”[11]291(《遵乱纪事》(其五))尽管起义军尚未攻城,城中早已戒备森严,每家每户出壮丁巡逻,到了晚上气氛更为紧张。遵义的官差们猖獗肆虐:“腰刀怒马四百人,前呼后涌入远村。”[11]99(《后义仓行》)知道起义军将抵遵义时,人们更加慌张,彻夜难安,诗人不由感慨:“可怜有月无中秋,一夜仓黄到天晓。”[11]291(《遵乱纪事》(其五))本是佳节团圆日,诗人发出因兵祸而无心过节的感叹。
贵州镇远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发生水灾,在这次灾难中官吏们更是无情残暴、腐败贪婪。莫友芝诗《镇远水十一首(其七)》言:“灾民拾金钱,不献者有罪。水来官亦贫,横至岂民利。”[11]454民瘼既深,加之苛政压迫,民众生业多艰。《岁晏行,用杜韵》又云:“去年农民赏不窃,今年恶少多于农。玉川储蓄定有几,亦与席捲云烟空。”[11]250诗中巧用“玉川子”卢仝的典故,说明当时的恶少太多,其横行霸道、欺瞒哄骗。弄得老百姓惶恐不安,这无疑对百姓来说是一种人为的灾难。
(四)饥荒
关于饥荒的书写,在历代文献中多见记载,如《逸周书·文傅》:“天有四殃,水、旱、饥、荒。”[14]《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15]《墨子》云:“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16]凡大灾大难后由于物质的断缺匮乏,往往会造成大面积的饥荒。
诗人在探望其弟途中,停留于黄石矶看见了战后饥民们哀嚎的惨象:“计粮三日那有歉,粗就朝餐愁夕食。”[11]417(《八月九日黄石矶阻风,记所见呈湘乡公》)莫友芝不仅记下所见,而且见此惨状特意写一书呈报给官府,希望官府可以关心帮助难民。《八月九日黄石矶阻风,记所见呈湘乡公》诗末云:“京观表山筑应缓,露布连城继还克。处功元帅雅不矜,可念灾黎浩千亿。”[11]417
闹饥荒时,难民们啃树皮、吃蕨根,《黔中杂韵十首,同平越峰太守,用郎苏门观察韵(其八)》载云:“最怜枵腹蕨根苦,尚忆调饥稗粉香。”[11]45在灾难面前,黎民们无以为生,若能充饥已属万幸,以致往往饥不择食。《记清平舁夫语》诗中载其见闻:“清平围三年,粮绝至食人。”[11]337可怕的是清朝处于动乱多年,粮食吃完后闹饥荒为了充饥竟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已堪称人间地狱。
(五)兽害
兽害指野兽对人畜、庄稼所造成的祸害。《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17]此处自然具有神话色彩,但早期人类的发展确实伴随着与野兽的斗争。因人类与野兽之间绝对的力量差异,特别是在古代生活中,面对猛兽的危害,人们也是无能为力、受害颇深,而这些在莫友芝灾害诗中亦有反映,如其《有豺》一诗:
有豺有豺深夜呼,声气狠戾非常粗。摇尻利喙索狗猪,人误值之腹立刳。东家牧儿西家渔,又待归不归哭呜。残骸断履置满途,问胡不思所驱除......强弓劲弩无所须,闭门束手相对歔。悍然复闻吏索租,正供已足胡为乎?可怜仓箱悬罄如,牵羸绁壮愤不舒。豺来百家十未殂,吏来十室九无余。幸而后官鉴厥辜,老奸束伏暂不雎。是时之豺影亦无,果谁逐之而谁驱。雉驯虎渡良非虚,迄今五年幸少虞。念及尚觉寒肌肤,令官虽仁吏则狙。仁民仁吏民已愈,我观斯豺若合符。神君神君父母且,慎无偏听为所愚。[11]455
此诗讲述的是遵义地区豺狼横行猖獗,食猪狗,当人误遇其时立即会被食之,残骸铺满路途。可恶的是:“是时豺来充四隅,公然白日张其喉。”[11]455豺狼遍满四方,尽管在白天也是肆意妄为,人们对其束手无策,只能闭门相互叹息。更有:“问胡不思所驱除。皆言此事君未喻,豺来豺去自有区。虽伤人乎吾避诸,驱亦不去徒为劬。”[11]455更令人心寒的是官吏对此置之不顾,反而认为驱豺豺不去,这是浪费时间劳力之事。在诗歌的序中,莫友芝就点明胥吏就是豺狼,是比豺狼更残暴凶狠的吏豺,使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二、莫友芝灾害诗的思想价值
白居易继承了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发。”[18]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的创作都应反映时事、为现实而作,这样创作出的文学作品才更有价值意义。在莫友芝的灾害诗中,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旁观记录,而多是亲身经历、耳闻目睹所产生的深沉慨叹。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表露了清廷的腐败无能。莫友芝言:“庚辛以降,海波方扬,水衡告匮,半壁东南,罔有安宇?”[11]601时局大势的衰颓,无疑加重了其灾害诗的悲情色彩。莫氏交友范围内有一般民众,他:“学富而身益贫,艺工而遇益拙。”[19]能够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加之其身处乱世,因此在莫友芝的灾害诗歌中,大量的作品都表现出了其对灾情的共鸣以及对当政者腐败落后的指责。
《镇远水十一首》作于镇远水灾后,发出了“天恩应缓征,便为尔民惠。”[11]454的祈求。莫友芝对灾后可能会发生的疫情有先知性的认识:“水后疫必兴,应验如一轨。思州喧疫神,幸勿意外视。若复不早图,民无孑遗矣。”[11]454在诗人行旅的过程中,目击了更为惨烈的场景:“疲民抵虐焰,谁不刀下魂。哀哀卅口家,瞬息同灰尘。”[11]337(《记清平舁夫语》)在行旅中诗人的视野得到扩大,在接触社会的各层面后,引发了其更进一步的思考,加深了他对这个乱世的愤慨以及对难民的深切同情。又如,在《八月九日黄石矶阻风,记所见呈湘公》中当他看见饥民哀啼的场景更是无比痛心,“我行利钝安足论,对此茫茫泪横臆。”[11]417他立即上书给曾国藩盼其能够关心、救助无辜的难民,即使自己束手无策,但依然尽其所能地为难民们发声、求助。《大河北百里间自去秋至今无雨雪》中有名句:“何当手挽昆仑水,遍洒中原作岁康。”[11]208这句诗可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20]相媲美。这种担忧、同情百姓灾苦的胸怀正是其思想价值的体现。
在同情难民的同时莫友芝还不忘把矛头指向政府官吏的贪腐行为。在《岁晏行,用杜韵》中既体现出他的博大胸怀,又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诗人自己住在“诛茅草创未蔽风”[11]250的小破屋中,以学者广阔的胸怀推己及人,想到了百姓的穷困以及所遭受的贫困均源于恶少的欺压“去年农民赏不窃,今年恶少多于农”[11]250,以及官府的不作为、贪官腐吏的无情,而感叹“惜哉权利不在手,为尔乞取铜山铜。”[11]250《岁晏行,用杜韵》言:“仰视白日云蔽蒙”[11]250、“横目易求亦易得”[11]250诗句直指这种现象。《有感二首》中诗人不仅指责、抨击西方列国的残暴,也痛斥清朝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在《经死哀》《南乡哀》等诗中也有对差役横向霸道的直接描写,字里行间满是诗人的呐喊。诗人在诗歌的处理方面,表现出的并非是豪情壮志而是时刻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对人性良知的认识。
三、莫友芝灾害诗的史料价值
《新唐书·杜甫传》云:“善陈时事, 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21]莫友芝灾害诗的创作无疑秉承了“诗史”的创作态度,钱仲联称其诗歌“足当诗史”[22]的评价确非虚言。莫友芝灾害诗歌之创作,有着补史之阙、纠史之误的史料价值。灾害诗与一般的诗歌相比,它可以将时代所发生的灾害用写实的文字记录下来,而非冷冰冰的数字统计,也可以替人民吐露出心声,可深入研究历史来由,故而有时其价值比史料更为珍贵。
张剑先生言:“友芝这批纪乱诗中最有特色的是26首《遵乱纪事》(《郘亭遗诗》卷二),特别是前23首七言古律诗,皆有诗注,诗与注一张一弛,相得益彰,堪称诗史。”[4]137咸丰四年(1854年)杨龙喜起义军包围遵义城,组诗共有26首详细地记录下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组诗的开篇,《遵乱纪事(其一)》中就写到四面八方的农民“揭竿一起(缺三字)”[11]290。《遵乱纪事(其六)》又言官兵听闻后便:“太守副戎齐遁逃”[11]291文字间不仅将起义军来势汹汹的气势生动描绘,更是将昏官腐吏的丑态精确地显现出来。更讥讽的是当起义军撤退后,官吏们邀功请赏,毫无羞耻之心。《遵乱纪事(其二十六)》:“当时发议不守者,遁而复还各言功。”[11]294在史料中桐梓城被义军攻破情况载为:“秋八月,桐梓贼起……初六日,贼遽人城。泰阶先遣人赍印至府,坐堂上待贼。贼褫其衣冠,逐之出城,不知所终。”[23]而在组诗的第一首、第九首中详细记录了起义军攻城前后居民的情况、攻城的措施方法以及使用的火器。这些史实在史料上都未曾记载,诗人用朴实的语言记录这场起义的经过、起义军的声势以及官府官吏的腐败无能、胆小如鼠,刻画出了史料中没有的一面。
《镇远水十一首》是莫友芝另外一组重要的组诗,该组诗张剑先生说其是“《镇远水十一首》诗可补《镇远县志》之阙。”[4]35据《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记载:“清道光十八年六月己丑(时间)镇远施秉青溪(地点)给贵州镇远、施秉、青溪三县被水,兵民口粮并房屋修费(水灾情况)。”[24]在年表中关于这场水灾的记录寥寥几字便交代完,但莫友芝用十一首组诗将其灾后情况、政府作为等详细记录并予以评价保存下来。其二写到:“坏屋不可家,葬人安可数。青山黯如泣,白水自东去。水去如复归,人死应再往。可怜万冤魂,尚欠一抔土。”[11]453年表中仅用寥寥几字记载,诗人则从更细致的角度去描写,足以补史之阙。
四、莫友芝灾害诗的艺术成就
莫友芝是宋诗派的代表诗人,一生饱读诗书、笔耕不辍,治学严谨、创作严苛,其《葑烟亭词草》序中自言:“余每持苛论,即一字清浊小戾于古,必疵乙之,而柏容常以为不谬,日锻月炼,不尽善不已。”[11]582因此,莫友芝诗歌创作在晚清为一大宗,如汪辟疆先生所言:“僻处边隅之郑珍、莫友芝,亦宗山谷。郑氏巢经巢诗,理厚思沉,工于变化,几驾程、祁而上;故同光诗人之宗宋人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25]384而灾害诗作为莫友芝诗歌创作的重要构成,亦取得了颇高的艺术成就。概而论之,则主要体现在以才学入诗,以性情入诗,以赋笔入诗三个方面。
(一)以才学入诗
莫友芝虽没有专门的诗论著作,但在其诗作及作序中可见其主张。对宋诗是十分偏爱的,作诗时常常以才学入诗,他认为作诗需:“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25]346,认为只有读万卷书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才会思路迸发,创作出来的诗歌才会有深度和广度;并且随着阅历的丰富愈加信服黄庭坚“无一字一句无来历”的理论,其本人也做到了这点。
莫友芝出生于书香门第,加之自己刻苦读书:“恒彻旦夜不息,寝食并废。”[4]623其天赋异禀,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也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学创作,对版本目录学、金石学以及经学也颇有深入研究。因此在灾害诗歌的创作时他十分注重以才学、学问入诗,表现在善于用典这一方面。
莫友芝善于用典,如其“臼杵金坛意有余”[11]108(《初夏乐安道中》)一句,见于《春秋繁露·求雨篇》:“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 家人祀灶。无举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坛,臼杵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26]这句诗中,运用的是在古代夏季求雨时,需祭祀灶神的典故。又如《有感二首(其二)》:“精卫有心衔木石,爰居何事避风波。”[11]405“精卫”是古代神话中的鸟名,取自《山海经·北山经》精卫填海的典故,以精卫代指晚清军民们在面对强敌入侵时勇于反抗的精神;“爰居”,海鸟名,出自《左转·文公二年》:“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27]在此诗人用典以比喻在晚清国家危亡之际,不顾子民而落魄逃跑的统治者,这里两处的典故用简洁的语言来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在《遵乱纪事》中诗人对起义的来龙去脉交代如此清楚,无疑也是因其有一种善于考证的热忱。
(二)以性情入诗
莫友芝的诗歌也绝非是仅仅限于考证、以才学入诗,在其灾害诗中,亦不乏触物而发的抒写心境之作。叶嘉莹先生说:“最好的,最能感动人的诗篇是诗人从自己的喜怒哀乐,从自身的体验所写出来的。”[28]莫友芝做到了这点。
莫诗《二月二十八夜大雨雹》写雨雹之大使房屋札札作响,诗人失眠披衣吟出:“仰天三叹可奈何,此际桃花已无益”[11]223的感叹。面对久雨不停的天气,力不从心地喊道:“恨无长剑倚天挥,斩却顽龙致干土。”[11]56(《喜霁定,步出来青,适得方仲坚同游,晚归双荐,用前韵》)面对旱热的天气,更是言出“吾曹热死那足恫,此事我欲笺天公。”[11]325(《八月六日吉堂招集云麓精舍,时秋热益酷,午后迅雷无雨》)的心声。《甲浪书事》描写了当地老百姓在听信谣言后仓促逃跑的场面,《辰阳道中》尽情地表达了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又有《遵纪乱事》《围城九日》《公安县》等灾害诗歌无一不表现出了诗人的真性情。《有豺》是莫友芝有感而作,揭露出当地胥吏恣意横行、长官无所作为。对百姓的同情、对胥吏的愤慨之情跃然纸上。郑珍评其诗:“性情之地,真不可解。”[11]1134诗人在写灾害的同时发出感人的肺腑之言,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以赋笔入诗
莫友芝父莫与俦对韩愈的诗歌有着深刻的认识,莫友芝之师程恩泽推崇江西诗派,旆以杜韩帜。这两位对莫友芝有着启蒙式的影响,因此莫友芝在创作灾害诗时运用了赋笔的方式进行创作。刘熙载云:“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御,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29]在莫友芝的灾害诗中引赋法作诗,铺陈扬厉,诉尽其能,如《和东坡<起伏龙行>》一诗,由序开始铺陈求雨的起因、过程以及应验结果。又如《自省南往独山,道不通,且一岁使得猷子远来书,知州人以社团自保,城尚无恙,却寄示一百韵》一诗,诗人洋洋洒洒百字,书写了遵义战乱到家人避难时的艰辛,尽情地宣泄出对太平军的咒骂怨恨。《盂兰会》:“呜呼!当途善后只如此,使我气结何能言!”[10]324整首诗的字里行间里透露出作者对官员的讽刺鄙视。《有豺》中更是层层递进,先是写豺狼祸害乡里、食畜食人。顺而一转写到更可怕的是“官豺”,他们勒索村民钱财食粮,让整个村镇民不聊生、人心惶惶。由浅到深的推进使整首诗更有层次,情感宣泄也更加鲜明。这种以赋笔入诗的创作方式让诗歌不受拘束,能够酣畅淋漓地抒写惨剧惨象,因此莫友芝的这些灾害诗感人至深。
五、结语
综上所述,莫友芝是一位为民请命、才思敏捷的诗人,分析其灾害诗的创作,能从新的角度感悟诗人,进一步窥时代之全貌。汪中对于灾害诗创作言道:“目击异灾,迫于其所不忍,而饰之以文藻。”[30]透过莫友芝的灾害诗不仅可以直观灾害发生时的惨象,还可以从中领会到诗人的忧患之情。诗人更是以才学、才情、赋笔入诗,为其灾害诗作增色添彩。莫友芝对晚清冷漠腐败的统治者、官吏进行强烈的批判讽刺,同时揭示了在灾荒面前弱者的无奈,使灾害诗的主题得到了升华,其中部分诗歌亦可补史证史,更是一大亮点。可谓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兼具,故而其灾害诗取得了不俗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