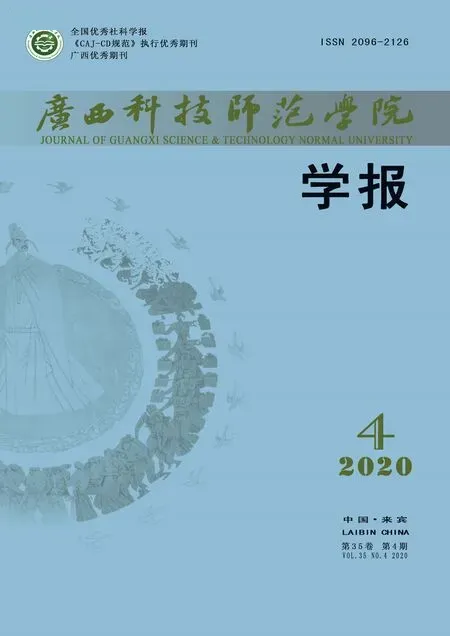法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及其关联
2020-03-13郑亚娟王忠东
郑亚娟,王忠东
(1.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大庆 163318;2.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法治是最有效的治国方略,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治理方式,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保障性和引领性作用。法治是民主的强大保障,是文明的巨大作用力,是人类理想的社会治理状态。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指导下,对中国法治实践经验的不断概括和总结,在法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次飞跃,才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一整套具体的目标与政策。
当前,我国公民还缺乏良好的法治素质,不能适应中国法治社会的未来发展需要。而要想实现法治中国梦,就必须使公民真正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因此,在法治教育和普及上,要明晰“法治是什么”,增强对“法治”的理性认识和升华,在明辨“法治”科学涵义的基础上,逐步养成良好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一、“法治”的内涵
了解“法治”的科学涵义,是明确中国法治道路的根本前提和依据。中国法治道路具有中国特色,既要汲取中国传统法治文明的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的重大成果,也要放眼世界,借鉴其他国家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要构建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法治道路规律的“法治”科学涵义。
中国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学派认为,如果没有法令的规约,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贤之君也不能治理好国家,而受到法令的约束,即使是桀纣那样的暴君也不会把国家乱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法家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4]。他们主张用外在的法规来规范人民,一切事情都通过法治的方式去解决,倡导用国法之治取代德性之治。但法家的“法治”是以强化君主专制为目的,君主本人有超越于法律的特权,君主高于法,用严刑峻法去治民。这种以信奉君主个体权威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其实质还是人治思维。这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言兴邦、一言废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结局,不可能有持续的良善之治。
清末民初,面对国家的积贫积弱和强势的西学浪潮。传统的“人治”观念逐渐受到西方“法治”理念的挑战和冲击。一些人开始构建和描绘中国法治社会的理想模式。强调社会应依法治理,全社会应信奉法律并自觉按照法律办事。中国的“法治”重新兴起,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1904 年,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写道:“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其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早)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日方盛行,而导源甚近。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夫深山大泽,龙蛇生焉,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宜也。”[5]梁启超之所以在我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就在于他既能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有深刻的理解,又能吸取西方法学家的民主独立精神,从而赋予了旧学以新的内容和新的使命,并试图从中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法治发展道路。
在西方社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系统地论述法治问题的思想家。他认为,法治优于人治,每个人都有善恶两面,如果一个人不受任何约束,那这个人就会成为这个制度的破坏者。一个国家和社会如果让一个至高无上的人来统治,这就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他在《政治学》中解释了法治的内涵,认为“法治”的含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民必须严格遵守已颁布的法律,这是法治所要达到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公民崇尚和遵守的法律应是善法,是有效公正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认为,制定良法和普遍守法是实现法治的根本所在。直到今天,立法和守法仍然是实现法治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17 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个人的权利是无限的,除非是法律所禁止,法律没有禁止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而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是法律授权的。也就是意味着法治的基本含义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法治的核心内容是合法性,法律不仅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对主体与主体之间发生冲突时进行裁判的一个中立的标准。法律要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主体性。
现代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倡导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讲话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这一情况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7]。
人治的实行是建立在个人独裁与专断的基础上。在人治国家中,一切人只服从拥有权力的人及其意志。官本位观念盛行,人们普遍地崇拜权力,漠视法律。马克思说过:“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8]按照通常的解释,法治是依法管理。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9]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号召党和人民要走法治强国之路。之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10]。这一系列举措为推进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渠道和方向。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法治建设的步伐会愈发强劲。
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内涵
法国18 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1]。全面依法治国不仅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需要建设法治文化软实力,应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尊严和正当权益,引导人民自觉履行法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让“文本上的法律”在社会实践中活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治理社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多次提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求全社会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法治思维是从合法性出发,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神为指引,运用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当前,学术界对“法治思维”有着颇为深刻的研究。如张文显认为,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12]。陈金钊认为,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13]。蒋明安认为,法治思维是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有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14]。通过对上述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法治思维”有着不同的定义,但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符合现代法治原则和法治精神。
法治思维特别强调人们要坚守“合法性”为谋划处事的底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摒弃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思维,这是公民法治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也是法治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但法治思维只能起到引导作用,它要转化为治理效能,必然要过渡到具体的行为方式,这种具体的行为方式称之为法治方式。法治方式是在用法治思维判断是非曲直的前提下,运用法治途径处理各项事务的行为方式。
当前,阻碍中国实现法治社会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法治理念和行为模式。中国社会曾经一度存在着“信权不信法”的特权思维、“信钱不信法”的潜规则思维、“找人不找法”的关系思维。究其原因,在于部分单位和个人还没有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事务,没有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国家的政治生活还没有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公民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没有普遍树立起来。因此,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上提出法治方式,目的在于改变以往的社会治理的“土办法”“土政策”等权宜治理的方式,用法治思维判断问题,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必须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15]。法治文化建设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治能否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制度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倡导法治思维和实施法治方式是政治生态的进步,是文明治理的开端。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建设。
三、“法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相互关联
从“法治”到“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够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也就是说,法治具有人性的基础,其实践主体是具体的人,在应用法律于实际情形时,不能离开人的要素。“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维护社会秩序时是遵从“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
法治思维要求摒除人治思维。社会普遍信奉法律,这是法治社会的要义。法治的基本标准应当是老百姓遇到涉法问题时,首先想到以法为鉴,通过官民共有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中去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进而去应对风险、化解矛盾、维护秩序、推动发展。
法治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基础与来源。法治思维是对法治的深化和有效扩展,是在适应法治环境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而实现法治又依赖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有力促进。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彻底摈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绝不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努力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16]。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的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就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主导作用。
法治中国的未来,需要全体公民的坚守托举。明辨法治、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科学涵义及其辩证关系,尊重和维护法律权威,培养良好的法治情怀。我们要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良好的法治保障和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