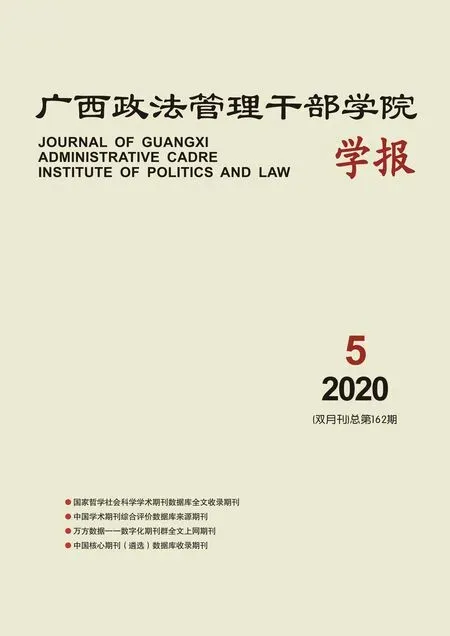黑恶势力“保护伞”之司法认定
——以公职人员韦某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为例
2020-03-12李桂华杨春艳李华文
李桂华,杨春艳,李华文
(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广西 柳州 545006)
当前,黑恶势力“保护伞”是我国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各级党委政府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决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但是,在惩治黑恶势力“保护伞”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2014年至2015年,公职人员韦某在L县国土资源局某国土资源所工作期间,接受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张某请托,与时任L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审批股副股长江某合谋,利用江某职务上的便利,为L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张某办理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合并登记手续。之后,韦某收取张某给予的好处费20万元,韦某和江某各分得10万元。此外,韦某伙同江某利用同样方式收受他人贿赂92万元。2019年10月17日,L市L区法院以被告人韦某、江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
事实上,本案在认定涉案人员是否充当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保护伞”时有很大争议。从案例涉案情况来看,本案被告人接受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张某贿赂的客观事实十分明确。主要争议是涉案人员为L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张某办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合并登记手续时,是否明知张某为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L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否属于张某为主要成员的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开办的公司,并且该公司是否被用于从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韦某为张某办理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合并登记手续的行为,是否应按照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有关刑法规定从重处罚,或以受贿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罚。这些问题实质可归结为如何准确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的问题。在此,本文对国家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性质特征进行阐述,探寻认定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分歧原因,并对其主客观罪过提出合理认定。
一、黑恶势力“保护伞”基本属性
自2018年中共中央部署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各地相继有国家公职人员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而被查处。有的公检法司部门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为涉黑恶犯罪集团或团伙提供各种保护,甚至有些地方部门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呈现塌方式腐败现象,在当地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一)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基本属性
“黑”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显著特征为团伙犯罪,其必然产生于犯罪团伙,且犯罪团伙危害治安,影响群众安全,同时也是黑社会势力的一种社会基础[1]。“恶”是指恶势力,恶势力犯罪可以说是一种团伙犯罪,既包括恶势力结伙犯罪,又包括恶势力集团犯罪[2]。黑恶势力犯罪通常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从事的犯罪,是中共中央为期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对象。黑恶势力“保护伞”,不是刑法规定的罪名,主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
(二)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主要形式
国家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要表现为:国家公职人员直接参与涉黑涉恶犯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为其站台助威、打探案情、提供便利和帮助等;充当涉黑涉恶犯罪集团“保护伞”,包括为黑恶势力提供情报、通风报信、窝藏包庇、撑腰站台等;在“两委”换届选举中,通过威胁、暴力手段操纵选举、把持基层政权等;以暴力、恐吓和威胁等手段控制农村资源、侵占集体财产;“黑白一体”充当“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欺压残害百姓、横行乡里、称霸一方;利用黑恶势力强行征地拆迁、租地、推进工程项目等,威胁群众安全和损害群众利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惩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过程中玩忽职守、失职失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等行为。上述行为是中共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惩治黑恶势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保护伞”,重点惩治的主要违法犯罪行为。
(三)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的新特点
结合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办理的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分析,呈现如下新特点。
一是公检法司部门、行政监管部门和基层政权涉及“保护伞”犯罪频发。当前,黑恶势力“保护伞”犯罪人员主要涉及公检法司部门的政法干警,国土资源局、住建局、安监局等审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以及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包括基层派出所、基层政协工作人员等等。例如,G市Y县原政协主席刘某某、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廖某某、县公安局L派出所所长李某和G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某大队长肖某为盘踞在Y县李某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伞”,被法院以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判刑。
二是黑恶势力与公职人员形成密切“关系网”。为了拉拢国家公职人员,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保护,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放贷、赠送财物、入干股分红、给予购房优惠、帮助子女入学或就业等利益输送,或者利用地缘、亲缘关系,千方百计将公职人员拉进其苦心编织的“关系网”。公职人员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半推半就中与黑恶势力结成“关系网”从而致使公职人员被拉拢、腐蚀、或被胁迫,最终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或恶势力的“保护伞”[3]。
三是政法干警成为黑恶势力“保护伞”。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壮大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为了逃避打击,涉黑涉恶团伙头目往往不直接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而是通过开办企业或经营项目,并在经营和日常交往中,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有意识地围猎政法工作人员,打好关系,必要时通过这些政法干部为自己的经营提供便利或为团伙成员从事的违法犯罪行为开脱。为涉黑涉恶人员提供便利、打探案情;有的公安人员疏通与法院、检察人员的关系,从中斡旋并共同接受涉黑涉恶集团贿赂,等等。
四是黑恶势力与“保护伞”沆瀣一气,共谋利益。黑恶势力往往信奉“打天下要靠拳头硬,坐天下要凭靠山硬”。部分党员干部权力观和金钱观错位,有的借助黑恶势力疯狂敛财,有的借助其跑官要官,有的甚至长年勾结在一起。
五是基层政法干警充当黑恶势力“帮凶”。拥有一定权力是保护伞的本质特征,没有一定权力,就不足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也就不能形成保护伞[4]。有的基层政法干警与黑恶势力长期纠缠在一起,“黑白一体”,既当“保护伞”,又充当黑恶势力的组织领导者,包庇、纵容黑恶势力从事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有的还亲自领导、组织和参与黑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行为,在当地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分歧的主要原因
司法实践中,因法律对黑恶势力“保护伞”没有明确定义,国家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涉及的犯罪种类多、各种因素掺杂,因而不仅法学理论界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认定存在分歧,司法办案人员亦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认定存在不同认识,并且在判断上存在一定误区,影响了办案质效。
(一)对黑恶势力“保护伞”概念理解不清
简单概括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即国家公职人员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其提供各种便利或非法保护;或者公职人员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犯罪组织,沆瀣一气,合伙组织并实施犯罪的行为。在办案实践中,基于对黑恶势力“保护伞”含义理解角度的不同,客观存在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准确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在办理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中,容易把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普通犯罪集团从事的刑事犯罪混淆。从法理上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和恶势力犯罪集团与普通犯罪集团是三个不同犯罪性质的概念。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其与普通犯罪集团概念的界线。按照我国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普通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普通犯罪集团可以分为单一犯罪集团和多元性犯罪集团。例如,贩毒集团、抢劫集团、盗窃集团等就属于单一犯罪集团。多元性的犯罪集团是为实施多种犯罪而组成的犯罪集团[5]。上述三者主要通过集团的形式从事犯罪,但普通犯罪集团从事犯罪产生的后果只是对侵害的个人或单位造成一定程度或恶劣影响。而黑恶势力犯罪集团则不仅对侵害的个人或单位产生恶劣影响,而且对一定区域一定行业、生产领域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当地社会秩序或经济秩序,严重影响或阻碍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对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不明确导致误断
由于黑恶势力“保护伞”涉案的国家公职人员,大多数主观上对其参与组织或者提供庇护的黑恶势力从事犯罪是知情的,也有的案件是由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惩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过程中玩忽职守、失职失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对上述行为纪委监察委或公检法司机关认定其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确信无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个别办案人员对行为人尽管是在执行公务当中为黑恶势力提供帮助并从中收受了贿赂但对其所帮助的对象是否从事犯罪行为不知情,于是就认定行为人是黑恶势力“保护伞”,这显然有失偏颇。如果行为人仅仅是利用职务便利为黑恶势力办理正当事务,从而收受贿赂的行为,或者行为人对所帮助的请托人是否属于黑恶势力成员并且对请托人从事犯罪的行为并不知情,据此将行为人认定为黑恶势力“保护伞”显然是不恰当的。
(三)对行为人提供保护的对象认识不清导致误判
在实际办案中,时常会发现有的犯罪分子为了其从事犯罪便利或者得到保护,往往对监管的行政或司法部门公职人员进行围猎,通过投资入股、干股分红利或者行贿、提供各种好处诱使公职人员参与或为其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由于此类公职人员因受贿或者渎职被查办后,办案部门通常会认定涉案公职人员为“保护伞”,如不加证明即认定其为充当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保护伞”,并且武断地认为从事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行为通常都是有多人参与的团伙犯罪并带有一定的胁迫、暴力手段,而涉案公职人员对犯罪分子从事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犯罪应当是“明知”的。如果因此就认定涉案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保护伞”,显然是由于对犯罪对象认识或查实不清而导致误判。例如,R县公安局某派出所副所长覃某某利用主持派出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同意R县H乡某村村民吴某某、廖某金、廖某龙、廖某华等4人分别在H乡的4个村屯开设赌场进行营利活动,并为4人开设赌场违法活动提供保护,多次收受上述4人送予的好处费8万余元。此案,就是典型的国家公职人员充当开设赌场违法犯罪“保护伞”案件,但因吴某某、廖某金、廖某龙、廖某华等4人从事的犯罪并非黑恶势力犯罪,因而就不能认定公职人员覃某某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四)认定案情复杂而证据缺失导致行为定性困难
查清黑恶势力相关犯罪事实,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是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前提。在办案实践中,因黑恶势力犯罪本身错综复杂,往往涉案人员众多、人员关系复杂,加之法律适用、认定标准不统一,给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主体属性带来难度。同时,涉及黑恶势力“保护伞”主体身份特殊,既有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又有政法机关干部,还有行业主管部门公职人员,有的甚至涉及高级领导干部,一些地方因担心“拔出萝卜带出泥”,往往存在不愿打、不敢打、不深打的心理,在调查取证时不积极配合,给办案人员调查取证工作带来很大阻力。有的案件往往在认定了涉案公职人员受贿行为成立的情况下,因缺乏认定涉案公职人员与黑恶势力关联的确凿证据,给认定公职人员是否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行为定性造成困难。
(五)同案涉黑恶犯罪案件移送滞后造成定性困难
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受理监察委移送的职务犯罪多为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查处的黑恶势力“保护伞”性质案件。监察委移送的涉及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大部分是在查办黑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中发现线索并被查处的。但是,因监察委移送有关公职人员涉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却是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审查起诉甚至判决之后。由于公职人员涉黑恶势力“保护伞”职务犯罪案件移送滞后,导致判断涉案公职人员是否属于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定性无法及时作出,同时因未能及时区分公职人员是涉及单纯的职务犯罪还是认定其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犯罪的“保护伞”,从而导致有关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无法顺利起诉或需要退回补充侦查。因此,黑恶势力犯罪“保护伞”案件的定性问题因职务犯罪案件起诉在先,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起诉和认定在后,在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未判决定性之前,检察机关是无法给涉案公职人员作出是否属于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属性认定。
三、国家公职人员涉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合理认定
根据上述归纳法学理论界、司法实践中出现黑恶势力“保护伞”认定分歧的原因,在分析认定国家公职人员为黑恶势力“保护伞”过程中务必高度重视。要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作出合理认定,本文建议应结合办案实际,准确界定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含义,严格区分黑恶势力“保护伞”与普通犯罪集团“保护伞”属性,依法统一认定标准,确保定性客观准确。
(一)准确界定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内涵和外延
黑恶势力“保护伞”不是刑法规定的罪名,主要包含公职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行为;为其提供各种便利或非法保护行为;公职人员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沆瀣一气,共同实施犯罪的行为[6]。在办案实践中,只有统一认定标准,才能提高打击效果。因此,纪检监察机关与公检法司各机关部门应联合制定黑恶势力“保护伞”犯罪的认定标准,促进认定标准和执法尺度的统一。同时,注重发挥指导性案例和典型案件的指导性作用,联合发布相关典型案例,切实落实案例指导制度,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办案标准,避免“一刀切”、扩大化。
(二)准确认定涉案公职人员具有明确的主观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涉案公职人员是否属于黑恶势力“保护伞”,其主观方面必须有明确的主观故意,这是构成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前提,即公职人员无论是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犯罪集团从事犯罪,还是为黑恶势力从事犯罪提供便利、庇护,或者是包庇、纵容、放任黑恶势力从事犯罪行为,其主观上必须是对黑恶势力从事涉黑涉恶犯罪是“明知”的。至于涉案公职人员是在黑恶势力开始就“明知”,还是在被有关部门查处前这一期间“明知”,均不影响对公职人员主观故意的认定。在刑法学界,对行为人是否属于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观构建的认定提出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必须明确行为人明知包庇、纵容的对象是黑恶势力犯罪组织;另一种意见是只要行为人明知包庇、纵容的对象是从事违法犯罪组织即可[7]。本文赞成第一种认定标准,主要理由为公职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通常跨越时间长,黑恶势力对其进行利益输送是常态,并且有的公职人员明知是黑恶势力犯罪,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宁愿被围猎并获利,从而包庇纵容黑恶势力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是由其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属性决定的。并且,这一认定标准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对公职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观认识再次做出的明确规定,这一规定防止了行为人借“不知道是黑恶势力组织”而逃避追责,更有利于打击和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犯罪。
(三)严格鉴别涉案公职人员包庇、纵容的对象
因黑恶势力“保护伞”犯罪的客体为双重客体,既侵害了社会秩序,也侵害了国家管理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公职人员利用职权包庇、纵容开设赌场、组织介绍卖淫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办案人员根据公职人员为上述行为提供保护,从中收受贿赂,据此认定涉案公职人员充当赌场“保护伞”、卖淫集团“保护伞”等,并作出涉案公职人员是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误判。由于开设赌场、组织介绍卖淫等犯罪行为的主体有可能是个人,也有可能是普通犯罪集团。而黑恶势力所从事的犯罪和普通犯罪集团、个人犯罪是有本质区别的,上述黑恶势力犯罪不仅给个人和单位造成损害,而且严重损害社会秩序,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因此,要首先准确认定行为人包庇、纵容的对象是黑恶势力,才能更好地厘清公职人员是为谁充当“保护伞”。如果公职人员仅是为盗窃、抢劫和开设赌场、组织介绍卖淫等普通刑事犯罪或普通犯罪集团提供保护,则不能认定其为黑恶势力“保护伞”。反之,只有公职人员领导、组织和参与黑恶势力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才应认定其为黑恶势力“保护伞”。
(四)充分考量黑恶势力“保护伞”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黑恶势力“保护伞”犯罪主要涉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罪系行为犯,即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实施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即可构成本罪,而不论其危害结果如何[8]。但是,在司法实践中,黑恶势力“保护伞”还涉及较多罪名,主要有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国家工作人员渎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等。并且,黑恶势力“保护伞”涉及的犯罪危害性也是极其严重的,不仅对侵害的个人或单位造成损害,而且扰乱国家社会秩序,损害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及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因此,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认定必须充分考虑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当然,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但要严格依纪依规依法进行处理。
(五)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要强化部门联动协作
为查清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事实,必须具有确凿充分的证据,才能有效提高查办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质效。有关办案部门要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加强监察委、公安、检察院、法院和司法局配合以及与行政执法部门沟通,形成斗争合力,为确保查办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排除干扰、阻力,切实做好“打网破伞”“打财断血”。公检法司部门应配合监察机关坚决查处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背后的职务犯罪和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以及操控、把持基层政权等犯罪问题,协助收集、提供证据和查实证据。加大黑恶势力“保护伞”办案与线索摸排力度,对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要做到人力优先、时间优先、介入优先、研判优先,依法从速办理。特别是,检察机关要依法及时介入涉及重大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的调查,引导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及时收集、固定、完善证据,为认定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提供确凿充分证据的相关办案提供指导,确保案件准确、高效办结。此外,检察机关还要加强黑恶势力“保护伞”案件审查把关,充分利用提前介入、规范时限、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程序及发现问题的解决机制,对侦查、调查部门以黑恶势力“保护伞”移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案件认真审核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