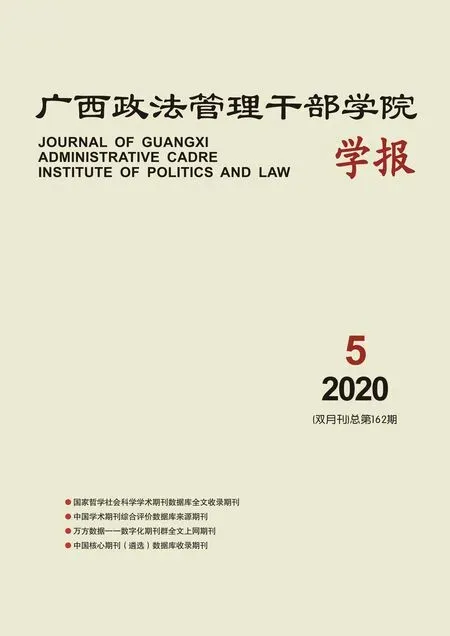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路径探析
2020-03-12张倩,周澎
张 倩,周 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当前万物互联的社会结构和商业生态环境下,姓名权的内涵已非往日可循,姓名除却其本质的人身属性,在个人使用以及商业利用的共同推动下,亦凝结了个人努力的心血和凝聚商业投入的价值。与之相呼应的姓名商业性权益也作为新型财产权益进入公众视野。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其定性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将其从姓名权中脱离出来,构成独立的财产权利[1]。亦有学者认为其并不构成独立的财产权,姓名的商业性价值并未改变姓名要素的内在属性,而仅仅是姓名权利客体的属性[2]。但是,在当前法律尚无明文规定其权利属性的前提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是姓名所包含的商业价值和利益应受保护。据此在“行为—法益”的侵权认定模式下,不当利用他人姓名的商业行为具有违法性和规制的必要性,而厘定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即是姓名商业性正当性权益保护的首要任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模式新业态的出现,不当利用姓名的行为方式层出不穷,且多以“搭便车”或“攀附”的目的体现,引发了诸多反不正当竞争纠纷,尚未明晰和统一的行为规制路径是引发纠纷的缘由。本文意在分析商业环境中经营者之间姓名商业性使用方式,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进一步解构姓名商业使用行为,通过对类型化案例的梳理和剖析,明晰不当使用行为的认定标准,以期为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认定思路,为司法实践中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廓清迷雾。
一、问题的提出
在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湖北农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侵权一案中,两审迥然不同的商业性行为性质的界定标准和认定混淆的说理过程反映了在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作为受法律保护的客体当下,对不当商业使用行为的规制缺乏清晰的认定路径和标准,也反映了在姓名商业性权益离散型法律保护模式下,不同法院基于不同目的的考量所采取的对个人姓名商业利用及其潜在价值的不同态度和重视程度。在有关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认定上,两审法院认可姓名商业性权益的财产属性和经济价值应受保护,从而为规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确定了权源基础。在对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保护上法院的认定并不冲突,但仍需注意的是姓名衍生的商业价值和利益应以权利人实际的商业使用和利用行为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引起一审、二审法院判决结果迥异的冲突点在于对竞争者商业性使用行为的不正当认定标准。
一审法院认为在企业名称后的题字不构成在产品包装或宣传行为,即不构成商业使用行为,未达到商业价值利用的程度;题字行为即便将其烙印在商品包装上,但商业标志、生产商名称明晰既不会引起一般消费者的误认或混淆,同时又承认其具有攀附袁隆平院士的良好形象和业界权威的意图。法院最后认定因缺乏前者的商业性使用行为以及行为导致混淆的可能性,即便在主观上存有一定恶意,一审法院亦未将其定性为侵权①参见湖北省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初2169号民事判决书。。
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推翻了一审法院对于是否构成混淆行为的认定说理,为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提供了大相径庭的法律证立过程。首先,法院对在商品包装上的“袁隆平”的题字落款行为认定为商业性使用行为,商业性使用并不要求是否单纯或直接地使用,通过在商品包装上的字样、广告语以及图片综合进行商品推荐和宣传即可认定属于商业使用②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3252号民事判决书。。其次,以题字落款形式使用“袁隆平”字样,并未改变其所指向的商业目的,易造成袁隆平院士认可或与该商品存在特定联系的商业宣传效果,由此认定一审法院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属性的错误定性。在明确构成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基础上,从被告的主观故意、违反商业道德以及商业性使用行为构成混淆和误认来判定其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同时,二审法院以同业竞争关系、使用行为方式所引起与姓名权对象特定关系或关联关系来对使用行为导致混淆进行判定。
通过两审法院的不同释法说理过程,可以发现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路径存在程度和适用上的差异。一审法院的裁判认为仅题字行为并未造成混淆,虽然认可被告的攀附意图,但仍不认可其行为达到构成违法性的程度,故对其使用行为的合法性做出了与二审法院相反的判定,姓名同商标虽都属于标识,但却具有不同的指向意义,商标指向商品或服务,而姓名更多的是指向个人。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正当性与否的认定需考量多种因素综合判断,而不同法院裁判结果存在出入的诱因亦须抽丝剥茧,予以解决。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本就具有衍生于姓名的特殊性,通过对权益和行为之间联系进行梳理,并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加以清晰阐明,才能准确把握其法律规制方向。
二、域内外类型案件梳理
(一)域外司法案例
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规制是一个混合问题,不仅涉及到经济性利益,更特殊的是在于需对人格尊严进行考量和保护。早期美国在隐私权下对姓名商业利用予以保护,认为其并未侵害权利主体的商业价值和利益,而仅仅是人格侮辱和诋毁。然随着姓名、肖像等人格标志的商业利用范围愈来愈宽泛,其所包含的商业价值愈加凸显,隐私权并不能给予被侵害人足够适当的损害救济。人格权的核心在于人格尊严,而商业化的价值目的与之相悖,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权利基础仍不完全。随后在海兰案③参见 202 F.2d 866(2d Cir.1953),cert.denied,346 U.S.816(1953)。中,美国通过司法判例以形象权的方式对其该权益予以确定,美国的形象权作为独立的财产权,成为规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权源基础,并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路径予以保护。随着司法实践的成熟和“名人效应”的商业模式推广,形象权最终在查西尼案④参见 433 U.S.562(1977)。中被最高法院所承认。在该案中,原告作为人体加农炮表演演员,其诉求在于阻止被告对其表演的商业价值的降低。法院依此判定的结果也表明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而非因隐私或名誉。形象权模式下,所保护的客体在于名人姓名中的商业性价值,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都表现为市场行为,以商业目的,盗用姓名所内含的商业价值可通过竞争法来予以规制,此外在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第四十六条⑤美国法学会:《反不正当竞争法重述》(三)显示,“为了商业性的目的,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或者其他身份标记,属于盗取他人身份中的商业价值,应当承担禁令和损害赔偿的责任。”有所体现。
英国的司法实践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规制采取限制性方法,在判定不当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是否导致混淆,需证明姓名在商业经营上存在商誉,被告的姓名商业利用行为与原告职业或经营存在关联性(虚假陈述),公众的混淆和误认程度以及存在实际损害(销售量、许可费)。从本质来说,人格特质是被用作交易标记来提高商品或服务适销性的,投入市场活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广告价值和对其基础性投资的回报。姓名所具有的经济利益包括既存的经营利益和潜在的认知价值,这样使得即便原被告并未属于直接竞争的经营者,但被告做出的建立联系行为的错误暗示,也损害了原告的商誉和姓名指征对象的名誉。在早期的克拉克诉弗里曼案①(1848)11 beav.112.(50EngRep 759).中,原告克拉克作为在业界具有名望的治疗肺结核疾病专家,寻求禁令以阻止被告以“克拉克爵士肺结核药丸”名义售药。尽管引起较多争议与批评,认为此禁令具有认为姓名上享有财产权利的倾向,但在随后的威廉姆斯诉霍奇一案②(1887)4 TLR.175.中,也阻止了在手术器械商品目录中使用原告(作为知名外科医生)的名字,避免引起公众误认该器械由他发明的,更具有人格特征的诉求在于该行为违反了该行业的一般伦理,会损害其名誉。早期的司法先例多基于诽谤诉因,尚未适用仿冒侵权的诉因来进行裁决,英国所采取的限制性的司法方法并未承认姓名商业使用性权益。在随后的麦卡洛克案中,法院赋予“共同活动领域”作为是否构成仿冒侵权的混淆判断标准,因为,原告麦卡洛克并非与被告属于同一经营领域,当被告利用原告的姓名制造并销售麦片时,原告需承担其个人人格的良好声誉和职业名誉损害的举证责任。因为,并无现实的风险以及损害,法官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是,在“共同活动领域”范围过于狭小的限制,且作为不够理性的推导方式,不再作为必备构成要件③See Lyngstad v.Anabas Products Ltd[1997]FSR62,67;Lego System Aktieselskab v.Lego MLemelstrich Ltd[1983]FSR155,186;Mirage Studios v.Counter-Feat ClothingCo.Ltd[1991]FSR145,157.。在“忍者神龟”④[1991]FSR 145.案中,原告作为对虚拟角色“忍者神龟”的所有权人,通过许可方式授权第三人使用该形象,未经授权的被告对该角色的商业开发则会导致原告许可使用费的损失,在该案例中实际上认可了角色商品化权,但依旧并未对真实姓名的商业利用权诉求予以正面回应,唯一可以明确的是阐明了可据以适用于姓名商业性权益的相对限制范围,即要求不论是角色或是姓名,须具有诉讼所涉商品的商标法上的意义,也就是公众基于商品与特殊标识的联系才选择此商品,且在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公众之间产生了混淆。从其案例发展过程来看,姓名商业性权益逐渐显露出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必要,同时对不当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认定标准也更为具体。英国所规定的仿冒侵权上的虚假陈述是判定是否构成混淆行为的抽象规则,具体可分为经营关联性虚假陈述、强型许可关联性虚假陈述、弱型关联性虚假陈述以及认证性虚假陈述[3],由此反映了英国司法实践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规制愈加类型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司法裁判结果的矛盾。
德国在司法实践中并未承认姓名商业性权益作为独立的财产权,而是采取人格权一元模式,从一般人格权的角度通过法律证立和续造的过程来推导个人的经济决定权。在尼汉斯案中,法院依据基本法(联邦宪法)第一条所规定的人格权的侵犯,认定尼汉斯作为活细胞疗法领域的专家,将其姓名投入到化妆品的商业广告中使用,一方面通过广告宣传的形式引导消费者误解,另一方面通过搭建起该化妆品与尼汉斯之间的特定关联关系从而损害了尼汉斯的名誉。从其本质上而言,将姓名投入到商业环境中,手段和目的的契合都共同指向该姓名所包含的商业价值,因此姓名商业性利益的预设是为了能更好地表明在姓名商业使用行为的保护对象,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规制也因伴其而生的姓名商业使用权益具有一定的限制和范围。在海因茨·埃哈特案⑤LGHamburg08.0589(Case No.3w45/89(1989)(HeinzErhardt)(translated in(1990)21 IIC,881.).中,海因茨·埃哈特作为已亡的著名喜剧演员,法院仍认为利用其嗓音的特质将其艺术人格用于商业目的是侵犯了死者的尊严以及继承者对死者人格权中商业利用中的经济利益,虽承认人格具有商业经济价值,但法院仍认为其属于对基本人格权利的违背,侵犯了基本法第二条第一款的基本权利。一元化保护模式将基本法第二条所规定的人格权与竞争法结合起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为宪法介入评价提供了契合点,当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达到混淆程度,即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善良风俗结合基本法的人格权模式下,对“依样模仿”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赋予更广泛的意蕴。德国的人格权统一保护模式所采取的路径是扩大人格权范围,在涉及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界定时,一方面将其权益指向人格权范围中,另一方面在具体适用时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四条所规定的不正当行为内涵予以判定,这也反映了姓名权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对应的受竞争法规制的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而不是传统的主动权利保护路径。
(二)中国类型化案例分析
在涉及姓名商业性行为的司法案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乔丹案”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27号再审行政判决书。对姓名商标性使用权益予以了确认,一审和二审法院在认定是否侵犯姓名权时,通过对乔丹作为姓名权客体对其人格符号的知名度适用范围、关联性和主观恶意进行了限制性认定。在再审中法院则推翻了该认定思路,通过截然相反的释法说理,承认了姓名权作为在先权利中所包含的经济价值的可保护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认可为规制不当使用姓名的商业行为提供了权利基础。在张立君一案中②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1318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作为职业作家,被告作为出版经营者,法院认定即使在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的前提下,认定其处于同一个文化市场中分享经济利益,因而认定中西书局构成损害市场秩序的不当行为。同时,张立君通过写作并获取稿酬构成在文化市场的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其真实意义在于使得姓名成为了文化市场中的商业标识,并起到了标识文化商品来源的作用,影响着相关公众的消费决定,因而张立君就其姓名享有的竞争优势和商业价值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在乔·吉拉德与福建新华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一案③参见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5)鼓民初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通过利用乔·吉拉德在销售领域的知名度造成其所销售的书籍同原告产生了特定联系,法院认可了原告人格商业化利益,原告姓名不是人格属性的体现,而是具有区分市场主体功能的商业标识。同时,认为被告进行虚假宣传,造成消费者误认其商品来源,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混淆,导致不正当竞争。在当前司法案例中法院多认可姓名在符合相应条件下衍生出来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权益应值得保护。但是,在不同的法律情境下,其具体判定和法律适用路径则有所差异。相较于“乔丹案”中直接将姓名作为商标使用的方式,具有可供实际操作的“在先权利”认定,后两者则体现出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方式的灵活性和新颖性,在市场活动中,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使用方式将通过商业使用行为施加于市场秩序、消费者以及其他经营者身上,其使用行为的范围和界限需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审视和考量。
(三)案例比较小结
通过前文域内外相关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在判断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商业性侵权使用时,姓名商业性权益的受保护性是法院判决的出发点,同时针对不同的利用方式依据具体的场景和标准进行判定。首先,在确认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造成的损害结果时,不仅仅是损害姓名所指向对象的非物质性利益或人格尊严,在商业性使用权益的基础上造成混淆的姓名商业性利用行为更会导致权利人和合法利用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损失,因而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包含了经济利益和人格利益的交叉与重合,对其合法使用范围的界定应受到来自市场准则和人格尊严的双重考验,反之不当使用行为亦会造成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人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经济价值损失。通过不同法域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规制路径和认定标准梳理,可以发现构成侵权的共同要件在于特定关联关系的指征性和导致混淆的存在,因而规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混淆,而在判定其具体构成要素时,尤需结合其所依存的人格属性和竞争内涵来进行限定和厘清认定标准。
三、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的内在机理
(一)正当权源: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形成
姓名作为人格标识,由其衍生而来的经济价值和权益的归属和认定在学界多有争议,早在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之人格权编如火如荼制定之时,姓名商业性所蕴含的经济属性认定一直处在风口浪尖的前沿,有学者认为姓名的商业性使用应纳入姓名权的范围在人格权编的大框架下进行保护[4]。草案中仅规定了姓名使用权能,并未将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作为独立财产权予以考量,随后在2020年5月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第一千零一十二条①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二条:“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姓名权的规定亦与之相呼应,依旧未确定姓名商标性使用权益的独立财产权属性。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问世的民法典,其所具有的形式价值远远大于其所具有的实质内涵,细微的调整和变化足以引起全篇章节和条文的更改与协调,为避免无法预测的“蝴蝶效应”,其意图在现有框架内对姓名权的具体内涵予以扩充,而非新增姓名商品化权的方式重新设立新的财产权。同时,有学者认为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是为姓名中有关人格因素符号化后所产生的符号价值,具有财产权属性[5]。因为,姓名所衍生的“商业性使用利益”具有独立的可保护财产价值,作为一项具有特殊指向性的财产权益,其商业性价值在于其与姓名客体之间的联系从而起到其对商品的保证或及令人信服的作用,这也是姓名内在价值“意义迁移理论”的实际体现。因此,正当的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促成了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形成,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存在又是规制不当使用姓名商业性行为的权源基础。姓名商业化权益较传统财产权不同之处在于其衍生于特定的人格权,内化并依赖于自然人的人格。但是,其并不具有绝对的对应性,在司法实践中极易引起不同法院对不同主体的姓名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混淆行为的判定冲突。因此,在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中,首先要明晰权利主体的权利基础是否存在,而这恰恰取决于姓名是否真正被权利人在实践中进行了商业性使用。
(二)价值基础: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竞争规则
民法上对姓名权的利用方式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下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的利用方式并不相同。民法上的主动使用在于权利外观上的登记或者公示作用,更体现其人身属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积极使用在于实现其所具有的商业价值[6]。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根本价值在于市场活动中所起到的识别和引导作用,当作为独立性经济权益的姓名商业使用利益通过转让或许可的方式为市场经营者所享有并投入市场活动中后,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才能真正对市场发挥作用。因此,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仅仅是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权源,当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商业运用层面,仅通过民法意义上的属性界定以及一般侵权的责任方式来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进行侵权判定,尚不足以真正解决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实际冲突和实现姓名商业性权益的内在价值。因此,在商业活动层面上,规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需符合商业活动中的竞争原则的内在机理。
姓名商业性权益本质为一种新型的无形财产权,在不同的商业使用行为下会涉及到不同的具象化权利客体,也会导致不同法律的规范适用。当姓名作为商标、商业装潢或企业名称使用时,则需更为具体全面的商标法予以规制,在其他尚未纳入的使用行为方式则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拾遗补缺。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的孵化器或培育温床,它保护的是尚未上升为合法利益或工商业成果的权益[7]。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行为规制来实现对权利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则通过赋权进行权利保护,以提前进行法律预定划清侵权与合法的界限。根据利益平衡和价值判断取向,不正当竞争行为并不以静态的预设权利,而是根据具体的行为内涵和模式来确定[8]。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制导向对姓名商业使用行为的规制具有更为实际的价值基础。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一方面涉及到人格尊严和自由发展,另一方面也关涉到对个人投入和劳动成果所应享有的相应的经济权益。在探寻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认定标准时,既应遵循其权源属性的内在机理,也要符合市场竞争行为遵守的商业伦理和基本行为准则。
四、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关键:混淆认定
混淆行为作为最古老且重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其较为完善的认定路径和稳定的构成要件不易受日渐更迭的商业模式和竞争规则束缚和影响,即便是在不同的竞争环境和商业形态下,行为混淆认定始终是不当行为规制最为核心的部分。因此,在规制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时,其关键之处在于对行为是否造成混淆的认定。
(一)竞争关系范围扩大解释
在传统反不正当竞争领域中,同业竞争关系的存在是判定是否构成混淆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但互联网的出现架起了不同市场相互连接和沟通的桥梁,也给予了姓名商业性权益更多的发展空间,姓名的商业使用方式也渗入并作用于市场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我国2017年新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第六条通过列举式条款对混淆行为进行了概括式规定,除商品混淆之外,还增加了主体关联关系、人格关系等外延。仅将经营者竞争关系囿于狭义的直接竞争关系,难谓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以最终利益相关性的广义竞争关系考量更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模式[9]。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体系下认定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市场环境和竞争关系应采取更为宽泛的界定。对竞争关系范围进行扩大解释,有利于下一步实质性混淆界定的进行,更为不当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认定提供了更广泛的规制范围。反不正当竞争法现代化趋势所反映的多元价值目标、竞争原则以及“三叠加”法益的权衡价值理念,使得竞争关系仅局限于狭窄的同业竞争领域范围内不足以平衡经营者、消费者以及社会公众的权益[10]。当前万众创业创新的背景下,任何人都是市场参与主体,不能仅仅以传统限缩式的相关市场界定来断定竞争关系存在与否,而应结合具体的适用主体、适用场景和市场价值的损害性等多元化因素综合考量。在张立君案中,法院则通过泛化性解释将职业作者和出版经营者纳入同一市场环境中,以此认定其具有间接竞争关系,这也是司法实践对竞争关系扩大解释的回应。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方式多样,新型利用方式的产生亦不影响对权利人合法经营利益的损害。
(二)“对象—行为—结果”的认定路径
除了对竞争关系的考量,具体涉及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导致混淆定性时,则需结合姓名的商业属性和混淆行为结果予以确定,即通过“对象—行为—结果”的逻辑体系建构,分别以使用对象、行为导向以及结果指向的思路进行判定。在使用对象上,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作为具有独立财产属性的经济权益,并非人人都可享有,该人格要素符号标志的商业价值和指向性是个人或市场主体劳动投入和个人成果的反映,在认定商业性使用行为构成混淆的路径分析中,对使用对象的界定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号]第二十条所要求的商标侵权行为对象,即三要素标准:一是一定的知名度;二是稳定的对应关系;三是姓名特定指征性[11]。商标法中的混淆虽不同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混淆概念,但在限制于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意义上,两者混淆的概念具有同一性,其共同所规制的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目的在于避免与姓名所指向对象的特定联系,从而造成消费者混淆和市场混乱。从前文域内外案例分析也可总结出对象认定标准的逻辑,即需在姓名上有投入和指向性,无论是“袁隆平”抑或是“乔丹”都是在相关社会公众认知范围内具有高知名度和高指征性的特定姓名。
行为导向则可通过商业性使用行为的具体表达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反映其所具有的商业宣传和指征符号主体的主观恶意。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衍生于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而商业性使用行为外化了姓名商业化使用权益,使之转换为具象化的商业利益和市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差异化商业模式和宣传策略促使具有商业潜力和价值的姓名标记通过商标性使用、商品装潢或广告宣传等多种商业性使用方式变成了具有财产属性的符号,其多样化行为方式的利用也表明其行为导向的善意与恶意。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可成为私人协议中的独立客体,通过受让或许可的方式进行商业性开发。但是,即便其作为财产性权益,所依附的依然是具有人格符号指征的姓名,因而与其相关的私人规则适用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适用范围的限制和合理避让其他权利的必要,与此对应的商业性利用行为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我国尚未将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以蕴含的商业性价值衍生出的权益保护和商业性使用行为类型为认定基础来进行法律体系和司法说理的建构。其行为导向的认定基础在于通过对行为目的的具体解构来实现对权益人的保护。在袁隆平案中,被告通过“袁隆平”字样与被告同样的使用方式以及题字的非常用行为亦可说明其具有攀附袁隆平院士的名誉以达到不当商业目的。其行为导向为主观上的恶意攀附性和商业利益的目的性。反不正当竞争法以行为规制为具体指向,这要求市场竞争行为所采取的手段或方式需符合法律规范或公认的商业道德,从而对其行为导向作出更为准确的判定[12]。
就混淆结果性指向而言,“近似是因,混淆是果”的侵权认定逻辑决定了混淆结果的形成关键在于近似的认定[13]。是否近似的判定需综合主客观因素,要求的是不当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所对应的服务或商品与正当权益人的商品或服务范围达到引起消费者误认的程度,包括因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所导致的对商业来源、关联关系以及保证关系的误认和混淆,从而造成合法利益相关人竞争优势的侵害及交易机会的丧失。因此,对混淆结果性指向需结合个案的灵活适用才可予以确定,这也反映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包容性的特点,即在法律的明确性和判决结果之间的社会妥当性予以平衡[14]。通过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使用对象和行为导向的前置性分析,才能在更为具象化的范围对混淆结果指向有更为清晰的界定,从而对混淆与否做出适当的司法回应。也就是,要求其利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的结合产生了引起消费者误认的混淆结果具体要求在于,一方面要求在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其程度为“足以引起混淆”即仅需混淆可能性,而无须达到实际混淆的程度,这与商标法的混淆要件具有一致性,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四)项规定了开放性的混淆行为,表明在严重不公平的情况下具有可突破的空间,反不正当竞争法拾遗补缺的作用也由此体现[15]。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视角下,结合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的特殊性,“对象—行为—结果”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体系构建在司法实践中蕴含着更具可操作性的价值和机理。
五、结语
在当前对姓名商业性使用权益界定尚未成熟之际,对于由市场波动所引发的新型权益纠纷而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和保护未尝不是一种灵活适宜的选择。反不正当竞争法现代化的多元保护体系和二元价值目标更契合对不断出现的新型商业行为的规制。反不正当竞争法涵摄范围的宽泛性虽多为学者所诟病,认为其模糊性和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偏离了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和对应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包容性和所体现的个案利益衡量方法为尚不能由具体法律规范保护的权益提供了保护,以弥补在市场活动中当前法律体系的不足,同时也是一种对新型商业侵权行为更为契合市场活动和利益平衡的规制路径选择。通过对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内在机理和表现形式进行剖析,为兼具人格自由、充分发展的伦理价值和成就主体经济利益的姓名商业性使用行为规制路径予以探究,为是否导致混淆的司法认定提供逻辑路径建构,从而扫清姓名商业性权益利用障碍,更利于促进姓名商业流转价值的实现,以鼓励行业内的健康发展,构建良好的竞争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