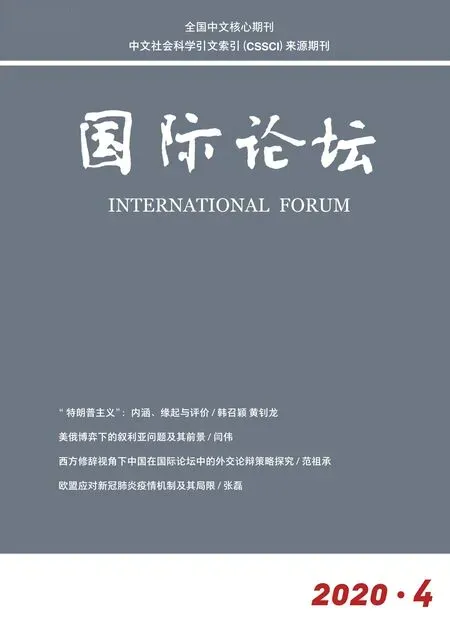西方修辞视角下中国在国际论坛中的外交论辩策略探究
2020-03-12范祖承
范祖承
【内容提要】国际论坛的举办是为了给多方提供一个以解决分歧、达成共识为主要目标的外交场合,论辩是达成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然而国际论坛中的论辩交流有时会因论辩者对各自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执著而转变为纯粹地只是对己方观点、立场的强调与对对方观点、立场的驳斥,偏离了国际论坛的应有之义。从修辞视角看,为了避免上述偏差,论辩者应该明确受众——将其与论敌区分开来,明确论辩目标——获得受众的信奉而非驳斥论敌观点,并采用受众接受而非只有论辩者自己接受的前提来展开论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国际论坛中的受众与论敌共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与论辩者的不尽相同时,论辩者想要说服受众的难度会增大。不过从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修辞视角来看,论辩者依然可通过充分挖掘受众与论敌所处的社群内部中的话语异质性,通过策略性地与一些立场结盟来反对另外的立场,进而说服受众。作为中国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话语,如能借鉴西方修辞对论辩的洞见,或可提升其在国际论坛论辩中的说服力。
一、引 言
在2020年2月召开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西方民主状态”分论坛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欧洲各国不要采用华为的5G技术,并污蔑说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输出其数字专制”。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在提问环节对此做了回应,她指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中国引入了包括电信技术在内的各种西方技术,但中国却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傅莹委员的回应不但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也赢得了国内舆论盛赞。然而,会场的另一位主发言人——德国联邦议长沃尔夫冈·肖伯尔之后的一番评论却不得不引发我们的警醒与深思。肖伯尔直言不讳地表示他赞同佩洛西“所说的一切”,并解释他刚才鼓掌并不是因为喜欢我方的观点,而是因为欧洲认为想要保障自由,那就需要多样性,必须反对单头垄断,以及双头垄断,对于欧洲而言,最好的选择不是在加利福利亚的硅谷模式或是中国的国家控制模式间做出选择,而是让更加强大的欧洲成为多样性的一部分以保障自由。①本文中对傅莹与佩洛西论辩以及肖伯尔评论引用译自论坛英文发言记录,下文从略,文稿可见于:https://pelosi.house.gov/news/press-releases/speaker-pelosi-remarks-at-munich-security-conference,February 14,2020。他的话音甫落,会场同样响起了掌声。肖伯尔的这番评论表明会场上给予我方的掌声与其说是表达对我方观点的赞同,倒不如说是在表达欧洲不愿意看到美国垄断话语权,欢迎不同声音的多边主义立场。换而言之,在我方看来十分雄辩的说辞并没能有效地说服欧洲受众,傅莹委员也坦言在这次与会期间,有德国学者向她表示,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的阐述说服力不够。②傅莹:《傅莹谈对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印象》,2020年2月22日,http://www.sss.tsinghua.edu.cn/publish/sss/8393/2020/20200222005000487853655/20200222005000487853655_.html。可见如何提升中国外交话语在国际论坛论辩中的说服力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等视角对如何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相关研究参见:刘永涛:《理解含义:理论、话语和国际关系》,《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19—25页;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绿叶》2009年第5期,第76—83页;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红旗文稿》2010年第14期,第22—24页;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72—85页;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62页。,但对外交论辩的研究仍有较大欠缺,本文力图从西方修辞②本文所使用的“修辞”一词指的是西方修辞(rhetoric),在当代语境中是指“致力于理解、掌握、开发和应用言语力量的一门实践或学科”,或更广义上的“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其内涵与中文和中国学术界所理解的“修辞”不尽相同,关于其区别的讨论可见: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页、第28页。本文为行文方便下文从略为“修辞”。这一当代国际论辩研究中最关注对受众说服效果的视角,来对具有跨文化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外交论辩进行一些探究,并结合实例来阐释如何运用该视角来改进我国在外交活动中,尤其是国际论坛中的论辩策略,以期达到更理想的论辩说服效果。
二、论辩研究的修辞视角
研究如何提升中国在以国际论坛为代表的外交活动中对西方受众的论辩说服力,选取什么样的视角进行切入十分关键。论辩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逻辑学、语言学、传播学、修辞学等学科都从其各自角度切入展开研究。外交论辩的跨文化与跨意识形态的属性意味着要与国际受众,尤其是西方受众打交道,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对当代西方论辩理论的发展趋势——论辩研究的修辞转向,有一个基本了解,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修辞视角看,论辩就是修辞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说服受众或是获得受众的认同为目的,不仅诉诸道理,而且也诉诸情感与人格,或是基于或然性而非确定性的。古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认为任何说服活动的起因都是由于存在不同意见,其以庭辩修辞为范式提出的争议点理论,包括了“事实争议点”(关于事物是否存在或者事实是否发生的争议)、“定义争议点”(围绕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属性发生的争议)、“品质争议点”(关于影响人们对事物或事件态度因素的争议)、“程序争议点”(分歧应依据何种规则、标准,何种机构才有资格来裁决的争议),只有当前一个层面无可争议后,论辩才会转移到下一个层面。③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76—78页。该理论对论辩研究影响深远。随着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科学、理性、客观性、确定性的理念备受推崇,西方论辩研究一度曾将形式逻辑视角视为论辩研究的主导范式。但在严格遵循形式逻辑论证的科学研究之外的人文学科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交流中,论辩活动是一种“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出于说服目的而进行的一种观点和道理的交锋”。自20世纪60年代末起,众多论辩学家以“非形式逻辑”“辨证”等名义对论辩学进行修辞改造,论辩研究呈现出“修辞转向”的趋势。①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309—310页。
当代论辩研究修辞转向的一大特征就是将受众置于论辩研究的核心地位。语用—辨证学派的论辩学者范·爱默伦(Frans van Eemeren)就指出修辞视角下的论辩与其他视角不同之处就在于其所包含的“不只是给出支持某一观点的理由,在合理的基础上证明一个观点的正当性,而且包括了任何能对受众有说服效果的交流特征。”②Frans van Eemeren,“Rhetoric and Argumentation,”in Michael J.MacDonald,The Oxford Handbook of Rhetorical Stud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666.当代修辞与论辩理论研究大家凯姆·帕尔曼(Chaim Perelman)就将“受众”作为构建其论辩理论的核心要素。帕尔曼认为从修辞意图来看,受众应被定义为言说者想通过他的论辩来影响的人的集合,有时不必要试图使反对者信服,只要能够得到大多数受众的信奉就够了。而论辩的目的不是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推断出正确的结论,也不是探求真理与揭露谬误,而是旨在获得论辩者想要影响的受众的信奉。③Chaim Perelman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19.受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成员对某一件事的意见、观点、态度、决定等是修辞者十分在乎并力图影响的。在作为修辞起因的那一件事情上,他们拥有可以满足修辞者的愿望和需要以及使这一愿望和需要落空的权力”。受众不应该被视为是被动的、任修辞(论辩)者摆布或操纵的对象,相反,受众相对于修辞(论辩)者处于一个“权势地位”。④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36—140页。这也就是说论辩的成败,决定权在受众。
相应地,论辩的出发点或前提必须是得到受众赞同的,这是由于论辩的本质在于顺应受众,将受众对前提的信奉转移到结论上去。在论辩时应通过顺应受众才能有效说服受众,这一道理并不难理解,但在实际论辩中有时却是知易行难。因为论辩的产生意味着参与方之间存在着观点、立场或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冲突,因此帕尔曼特别强调论辩中重要的不是论辩者认为什么才是真实或者重要,而是应该要知道其受众所持的观点。如果论辩者只关注自己所认为重要的事,那么其论辩可能会对对此易感的人有效果,但对于受众而言,他们有可能因不相信论辩者所提出的前提是可接受的而拒绝接受整个论辩。有时论辩者讲起道理来激情澎湃,似乎颇能打动人心,但这“即使能带来一些效果,却并不能发出‘真正’的声音”,因为论辩者误以为能说服他自己的论辩同样也能说服受众。①Chaim Perelman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p.23-25.
三、修辞视角下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外交论辩
修辞视角下的论辩将受众置于核心地位,这与国际关系研究在“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对受众的关注可谓不谋而合。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国际政治或外交的话语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受众对言语者使用的语言及其构建的社会事实产生了怎样的理解和形成了何种意义”。而受众总是依据其所处的社会语境、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在综合权衡身份归属、自身利益和预期的基础之后而做出接受、拒绝接受或协商接受的选择。②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62页。中国想要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取得更好的外交论辩话语效果,必须围绕受众来开展研究,因为话语产生权力的重要基础是其得到受众的认同,论辩的话语要产生效果,其含义必须符合受众既有的认知和观念。③张志洲:《如何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2011年第3期,第38—39页。这就使得从关注说服受众的修辞视角来研究外交论辩十分有必要。
从以受众为核心的修辞视角来审视外交论辩,首先应明确论辩目的与论辩受众,即论辩者通过论辩想对谁造成何种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何种效果。外交论辩有多种形态,有的是鲜明地阐述我方观点立场,兼或批驳论敌观点,如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答记者问;有的是直接对外方的一些虚假、歪曲的论述予以义正辞严的反驳,如王毅外长在本次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指出美国对中国的指责都是谎言;还有的则是以化解矛盾冲突、争取受众认同,以达成共识为目的,如在万隆会议上面对有的国家代表攻击共产主义时,周恩来总理在发言时提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原则,一举扭转外界对新中国的偏见。修辞所关注的论辩是最后一类。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绝对的两极阵营对立不复存在,虽然局部矛盾冲突不断,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旋律,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告诉我们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应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会议和论坛就提供了一个通过对话论辩而非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冲突的交流平台,在这一平台上论辩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相互攻讦,驳倒反方,而是解决分歧,达成共识。虽然不少国际论坛是由欧美主导的,会议的议程多按欧美的利益和关注点来设置,但国际论坛中常有多方参与利益博弈,即便欧美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方面等基本认定上享有众多共识,但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也有着矛盾冲突,这意味着论辩者的受众与论辩对象或是论敌可能是分离的。论辩的目的是争取从这一社群内部与论辩者有更多共同点的利益攸关方那里获得支持或与之达成共识,只有对议题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利益攸关方才是论辩受众。因此有必要将受众与论敌区分开:受众多持中立立场,即便有反对意见,也存在着被论辩者说服的可能,而且论辩者往往有求于受众,受众实际上决定了论辩的最终效果;而论敌无法被说服,对论辩成败也没有决定权,因此对论敌观点的反驳如未能服务于说服受众的目的,从修辞视角来看,则称不上是有效的论辩。套用美国修辞学大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术语,前者是论辩者的共同施事者(co-agent),而后者则是反施事者(counter-agent),论辩者在论辩中应向谁寻求支持并与谁达成共识,显然不言而喻。在跨文化与意识形态外交论辩中,如果论辩者未能准确定位自己的受众,将论敌与受众区分开来,就会导致有时在反驳论敌观点的同时也站到了受众的对立面,不免会有势单力薄之感,也势必造成论辩效果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受众与论敌有可能同属一个政治、文化语境,在价值观或意识形态上享有众多共识,而论辩者却与之有别。因此,明确受众还意味着要了解受众的态度、看法与价值观,尤其是要对受众的哪些价值观或基本认定是论辩者无法通过论辩改变、哪些是可改变的,有清晰的判断。
其次,在外交论辩中,论辩者选择的论辩出发点也应以受众信奉,至少不反对的观点为佳,应避免采用一些论辩者认为在理,但受众可能抵触或不赞同的观点。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外交论辩中论辩者容易从己方信奉的观点而非受众信奉的观点出发。外交论辩参与方往往来自有着截然不同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背景的社群,这些社群是通过一些“占支配地位的看法,不容置疑的信念,能够毫不犹豫就被接受的前提”来区分,①Chaim Perelman &L.Olbrechts-Tyteca,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9,p.20.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士往往都对本国的体制、道路、文化有着坚定的信奉。即便像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这些似乎有着“普世性”,并且在许多非西方国家政治话语中也有流通的价值或理念,非西方国家却可能对此有着不同的认知和标准,并不一定会完全认同西方国家的价值或理念。②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62页。这给外交论辩带来的问题是,如果各方都固执己见,那么将很难找到一个论辩各方所共享的基本设定或信念,就会造成一种“不可通约性”,论辩交流变成自说自话,受众会觉得论辩者难以理解,无法沟通,产生情感上的隔阂,最终导致无法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形成共识。现实中,当出现这种矛盾时,通常需要各国依据各自利益与实力做出互让,③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301.或是要诉诸国际机构或组织这些第三方仲裁调停。鉴于西方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依然享有较为强势的主流话语权这一现状,实际外交论辩中“与主流相符合的话语就容易产生权力,而与主流有差别的话语就会被审视或否定,难以产生权力效果”。④张志洲:《如何增强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对外传播》2011年第3期,第38—39页。这一现状虽然可能会随着非西方国家实力的增强而有所变化,但如果我们意识到,至少在目前所谓的“与主流相符合”的话语实质上指的就是得到受众授权和认同的话语,那么只要非西方国家是以西方国家为目标受众来进行论辩,如果非西方国家一味采用己方国家所信奉的道理来论证自己的立场,而非采用受众方信奉的道理,就可能会“引起目标受众的反感,导致说服徒劳无功”。⑤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301.
鉴于此种情况,在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论辩中,许多非西方国家采取的是汲取西方的话语资源,用得到西方话语授权的道理(论据、预设、推理模式),而非采用他们本国的道理来构筑、阐释和捍卫自己的立场。⑥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302.这样做之所以行得通,其一在于当代西方话语的异质性使得对于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人们总是可从得到授权的大量的西方修辞资源中找到在有效性上旗鼓相当的正反论点或论据。①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304.一旦非西方选择尊崇西方的论辩话语规则,“非西方及其视角被悄悄地重新置于西方的修辞视野之内”,就能够使其被西方受众理解,并且有望被其接受,因为他们“通过策略性地与一些西方立场和视角结盟来反对另外其他一些观点和立场,这就模糊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或是跨群体论辩中正方与反方的界限,使得他们的对手在聚焦他们的批评目标或者维持其论辩攻势时困难重重”。其二,相对于跨文化论辩中难以判定论辩结果的情况,如果非西方国家能将跨文化论辩转化为文化内的论辩,依据西方的论辩传统,一方若为某一观点“辩护失败”就需撤回该观点,反之,不容置疑的成功辩护将一扫对该观点有效性的质疑。②Eemeren,Frans H.van and Rob Grootendorst,et al.,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Mah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6,p.284,转引自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p.310-311.非西方的这种论辩策略会使西方论辩者陷入尴尬境地,他们要么选择忽视非西方的观点,要么将其观点斥之为诡辩,但他们如果拒绝与非西方对话,就会违背其试图在全世界推广的民主价值观,甚至会等同于放弃西方在全球公民社群或公共领域的领导权。③Liu Yameng,“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Contemporary Rhetoric,Vol.13,No.3,1999,p.306.
四、案例分析:修辞视角下如何改进中国外交论辩策略
那么从修辞视角来看,要如何才能改进我们的外交论辩策略?笔者试以本文引言中提及的中美在华为5G问题上的交锋为例来做一个阐释。佩洛西在作为论坛主发言人,以“保护与守卫我们的人民”为主题致辞时,提到威权主义正在攻击民主制度价值,并污蔑说中国正通过华为输出“数字专制”,她提出欧洲的5G基建应该走国际化(排除华为)的道路,这是其主要论点。
我方论辩者要对此做出回应,首先应明确论辩目的与论辩受众。当前欧洲正在布局5G通信的基础设施建设,华为在产品的技术与价格上都有很大优势,并且甚至表示愿意向英、德等国开放源代码,共同消除技术上的安全漏洞,英国已经批准在民用领域部分采用华为的产品,但欧洲不少国家还未做出最后的选择,有待国家议会表决,而本次论坛的参会者就包括了对此有最终表决权的欧洲多国政要,他们才是我方论辩想要争取的受众,而美方则是论敌。确定受众后,我方论辩者应明确欧洲受众在5G问题上到底持有何种态度与看法。《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中指出在5G之争中,欧洲是中美竞争的对象,这就使得5G问题从一个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大的战略问题。如果欧洲选择华为的5G技术,意味着欧洲在与中国建立影响深远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同时,不再可能是美国的全天候盟友。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欧洲不愿站在美国一边会使自由民主处于危险之中”,虽然很多迹象表明欧洲会站在美国一边,但是欧美之间的分歧在特朗普上台后也有扩大的趋势,欧洲在许多问题上没有与美国协商的份,只有领受指示的份,因此这也有可能使得欧洲在5G问题上更不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指示。欧洲的骑墙态度正是中国所欲。同时欧洲也受到了来自中方代表的压力,如果将华为完全排除出去,欧洲也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欧洲国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大多数欧洲国家认为它们应该在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该报告甚至还直言不讳地点出中国能够现实地达成的目标——“中国无法赢得整个欧洲,但它可以通过分化欧洲大陆国家和拉拢其中一些国家来使其保持中立。”①Tobias Bunde,Randolf Carr,Sophie Eisentraut,Christoph Erber,Julia Hammelehle,Laura Hartmann,Juliane Kabus,Franziska Stärk,and Julian Voje,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Munich,February 2020,p.21.这表明欧洲受众被我们影响并说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鉴于欧洲的这种基本立场,我方论辩者可以明确论辩的主要目的是稳固欧洲的中立立场,分化其与美国的共同立场,减少欧洲政界及舆论界对中国以及华为的敌意,使其尽可能地更加倾向我方。
除了表面上的态度、看法,论辩时还需特别注意欧洲受众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我方论辩者在论辩时应避免与之正面抵牾。比如美欧同属信奉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核心价值观的“西方”,是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北约也标榜自己是“自由国家的联盟”,而将中国视为政治体制上的异己,这一价值观或意识形态认定是论辩者难以通过论辩去改变的。而当美方意识到不可能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服欧洲排斥华为的5G技术时,就很自然地选择了欧洲受众与他们都认同的民主价值为话题,通过将技术与民主关联起来作为其论辩的出发点,将原本出于经济和技术考虑的5G商用选择问题转化为“选择专制还是民主”,欧洲国家不应该“为了经济利益的权衡而将电信基础设施割让给中国”,希望欧洲能掂量清民主价值与经济利益孰轻孰重,并同时由此衍生出技术与安全的话题,美方指出华为被美国视为是安全威胁。虽然美方的这种说法在我方看来是荒诞不经的,对于美国的民主口号与采用华为5G所能带来的实际经济利好,欧洲各国心中也自有一本明白账,但美方打出的这套民主牌至少在明面上欧洲受众是会买账的,因此,从修辞上讲我们不得不承认美方选择的论辩出发点大体是奏效的。我方论辩者如果在论辩时直接谴责美国污蔑我国的政治体制,未必是有效的,因为这是受众和论敌所心照不宣的共识,我方论辩者在质疑时也很明智地避开了这一点,而是选择从“技术与安全”切入,提出了“技术是一种工具”的说法。从哲学视角看,确实可以说技术是中立的,但该观点能否得到欧洲受众信奉则有待考量,因为《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中点明欧洲方面认为当前技术与国家主权有着罕见的密切联系。法国马克龙总统在2019年时就曾明确表示,“技术不再被视为政治中立的”,“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主权之战……如果我们不在所有领域(数字、人工智能)打造自己的冠军,我们的选择将受人摆布。”①Rf,“Macron Throws €5 Billion at Digital Start-ups,”September 18,2019,http://www.rfi.fr/en/france/20190918-macron-throws-5-billion-digitl-startups,转引自 Tobias Bunde,Randolf Carr,Sophie Eisentraut,Christoph Erber,Julia Hammelehle,Laura Hartmann,Juliane Kabus,Franziska Stärk,and Julian Voje,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Munich,February 2020,p.64.之后,我方论辩者又用中国引入了西方的技术,但却保持了自己的政治体制,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为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欧洲受众在多大程度上会认同这一观点却也是值得商榷的,他们有可能根本不关心技术对中国政治体制有何影响,或者可能会认为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欧洲不同,在中国不存在的问题,并不代表它不会在欧洲发生。德国议长肖伯尔在点评傅莹、佩洛西的论辩时就说到:“我所理解的中央政府对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的控制与欧洲实施的不同。”这其实就委婉地点出了欧洲方面对我方论辩者所采用的例证的看法。
在本例中,虽然要改变欧美对我国政治体制的偏见比较困难,但佩洛西将华为正常推广其技术的商业行为污名化为中国政府输出数字专制,将技术与政治体制结合的说辞,却是一个“定义争议点”。对此,我方论辩者可回应说:“佩洛西女士的上述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华为推广5G技术完全是企业的商业行为,它是一家民营企业,采取的是由全体员工持股的形式,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军方持股。2004年,贵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如果不是因为内部分歧,还差一点就收购了华为,它对华为的股权构成情况应该有清楚的了解,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也曾到华为做过专门的调查采访,亲自查阅过华为的股权簿,如果佩洛西女士不赞同该观点的话,请你拿出实际证据来。”对美方所提出的这一被打扮成事实的论辩出发点的质疑十分必要,因为如果我方论辩者没有加以驳斥的话,美方的这一说辞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没有争议的事实而进入流通领域,对我方今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辩是很不利的,我方论辩者当时没有对此反驳可能是考虑到自己的官方背景,即便做出反驳,欧美方面也有可能不予认同,因此没有对此质疑,但如果我们选用来自西方媒体所调查得出的证据,则可比官方背书还能更有力地做出反驳。
其次,既然我方论辩者提出技术是工具不会威胁到国家政体的观点无法获得受众的信奉,那倒不如选择先顺应受众的观点,大方承认技术有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这一欧洲受众也认可的基本认定,然后充分利用西方内部话语的异质性发掘源自西方社群内部与论敌观点对立,同时又可能会被受众接受的道理和论据来证明我方论辩者的立场。比如从《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来看,西方内部对于民主这个看似“普世”的价值要如何定义(全民公投式的民主?议会制民主?民粹主义的泛民主?……),民主能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以及对于多大程度上的民主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其实都还是有争议的。报告中还指出“民主祛魅”被不开明的政治家利用,以公共需要的口实来采取替代方案。①Tobias Bunde,Randolf Carr,Sophie Eisentraut,Christoph Erber,Julia Hammelehle,Laura Hartmann,Juliane Kabus,Franziska Stärk,and Julian Voje,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Munich,February 2020,p.12.一向以民主自居的美国方面就曾为了保障其国家安全,通过了《美国爱国者法案》,以反恐为名,给予了政府更大的侵犯民众个人隐私的权力,实质上是破坏民主自由,佩洛西当时是反对此法案的。在华为5G问题上佩洛西将民主与安全相联系,认为给予更多的民主就能确保国家安全,但她的立场与美国政府实际奉行的政策是相矛盾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可资利用的话题切入点,我方论辩者可引入西方国家内部还存在分歧的话题——国家能否以安全之名通过技术手段来侵犯个人通信隐私,离解美方将技术的安全性与技术来自于何种政治体制国家所建立的关联性,同时还可以引证美国依仗信息技术优势,监听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盟国的事实来分化欧美。
因此,我方论辩者可先指出正如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以及最近瑞典加密设备产商Crypto AG 事件所曝光的那样,某个民主国家(美国)曾利用其在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方面的技术优势对欧洲民主国家进行监听监控,中国与欧洲一样对此感同身受,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多年来一直遭到来自发明互联网的国家依仗自己的技术优势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攻击,国家、企业与个人的信息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据报导华为公司的网络就曾受到过美方侵入。之后我方论辩者可选择向肖伯尔议长提问:“我很理解德国对采用国外的5G技术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担忧,因为我们知道贵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曾遭到美国监听,不知道她是否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愿意出席此次与通信技术有关的安全会议?我们认同欧洲各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所提出的采用5G技术应该国际化的观点,支持中、美、欧各国企业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共同参与欧洲5G建设。但美方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即便给技术贴上民主政治标签也无法确保信息安全,而技术安全的问题只能通过技术来解决,据我所知,华为愿意向英、德等愿意采用华为5G技术的国家开放源代码,共同消除技术上的安全漏洞,这就好比大家担心华为的5G技术是特洛伊木马,那华为就把木马里面打开让大家看个究竟。即使最后不是华为而是美国政府控制的公司与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布局5G技术,我们也希望它能像华为对待它的客户一样开诚布公地对待它的盟友。不过鉴于美方之前的行径,我想问问肖伯尔议长,德国联邦议会是否完全相信与美国合作开发5G技术就能确保国家及个人信息安全?”选择对德国议长肖伯尔提问,而非向佩洛西提问不仅因德国所代表的欧洲方面是论辩者的受众,德方态度看法是论辩者所重视的,而且由于其立场的中立性,是有可能提供有利于论辩者的观点或论据,成为我方论辩的共同施事者;而后者是我们的论敌,如果我们的质疑不能切中肯綮的话,邀请其回应得到的大概率会是对其观点的重复强调,或是对我方论辩者观点的进一步攻击,那就徒劳无益了。同时或许我方论辩者还可反呛一下美方:“佩洛西女士,我的问题没有想冒犯您的意思,我想您一定事先对此并不知情,我知道您甚至曾在议会上反对美国政府为了防止恐怖主义而继续对恐怖分子监听,所以如果您知道的话,肯定也会反对民主国家的这种利用技术优势侵犯默克尔总理个人隐私的专制行径吧?”通过选择认同欧美所认为的技术有可能威胁国家主权安全的立场,并指出“民主”的美国也会利用技术优势侵犯欧洲民主国家的安全,论辩者实质上从反面论证技术是否会对国家主权安全造成危险与技术来自采用何种政治体制的国家无关,而佩洛西再怎么坚持自己的论点也会显得理屈词穷。
当然,上述拙见纯粹只是从修辞视角将国际论坛中发生的真实论辩作为个案来探讨一种学理上的可能性,目的是为研究一种宏观上的策略,以避免在大方向上的偏差,是否可行还是要取决于实践者临场的权宜机变,毕竟外交论辩波谲云诡,错综复杂。倘若本文能被认为有一些合理之处的话,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因为这是在管窥了论辩全局后的一个事后复盘,吃一堑长一智罢了。
五、结 语
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想要获得与其实力匹配的话语权,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不仅需要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中国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传播自己的观点,更需要提升话语质量,增强自身话语说服力。国际论坛不仅给予了有关各方一个开诚布公,表达观点的公共空间,也提供了让各方通过论辩来消除分歧,形成共识的渠道。虽然由于各方论辩者为捍卫自己所代表的利益、价值观、意识形态,在论坛上的论辩时常剑拔弩张,充满着浓厚的火药味,但从修辞视角看,如果论辩对己方观点的强调或对反方观点的驳斥未能赢得受众的信奉,并最终说服受众,取得我方所意欲的论辩目的,那都称不上成功。论辩者应该明确受众——将其与论敌区分开来,明确论辩目标——获得受众对我方论辩者观点的信奉而非驳斥论敌观点,并采用受众接受而非只有论辩者自己接受的前提来展开论辩。在面对国际论坛中的受众与论敌共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和论辩者迥异之时,则可考虑利用受众与论敌所属社群内部中的话语分歧,将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论辩转化为同文化或意识形态内的论辩,使得受众更易于理解与接受。中国外交论辩如能汲取修辞视角对论辩的洞见,或可提升其在国际论坛等外交场合中的话语说服力,进而助力于中国国际话语权与软实力的逐步提升。